《它们的性》 田牧歌解读
《它们的性》| 田牧歌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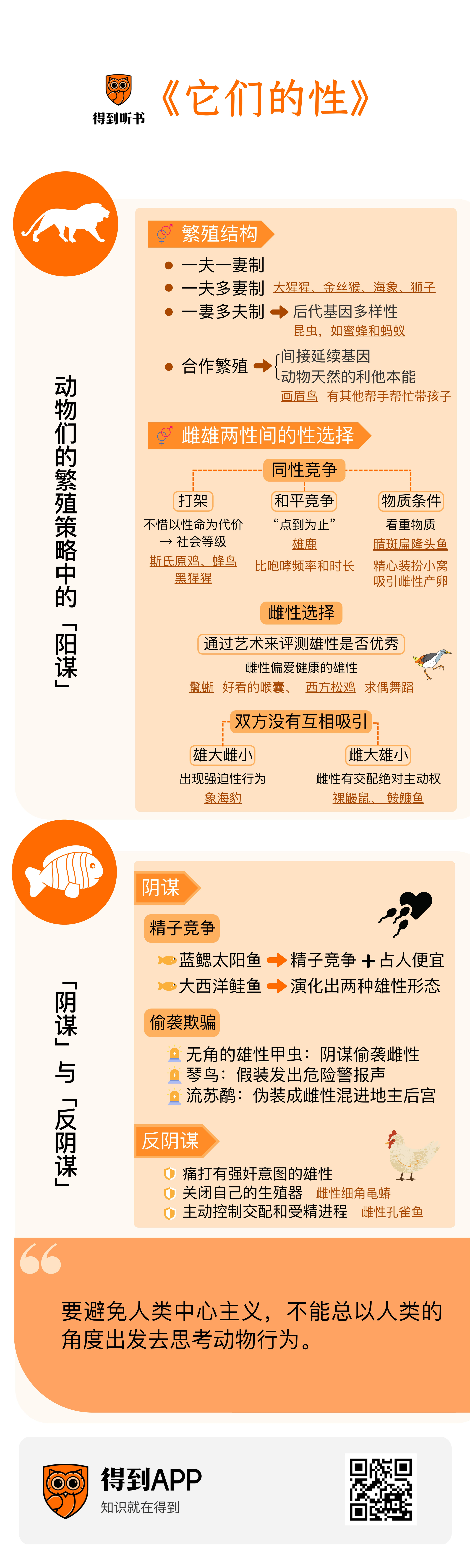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它们的性》,“它”是宝盖头的它,你可能已经猜到了,这是一本讲述动物世界性爱故事的科普书。
提起动物的性和爱,有人可能觉得,这不就是人类爱情故事的简化版嘛,动物们求偶交配主要受本能驱使,人类则在本能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更丰富的感情和更复杂的谋略,所以人类的性爱故事肯定比动物有趣得多。可事实真的如此吗?不一定。如果说动物世界的爱与性是一本书,那人类的故事也许只是其中的一个章节,动物们的故事远比我们想象得要精彩。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关心动物们的性呢?这看似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话题,但它对我们的意义并不小众。认识生命是认识世界的重要课题,所有生命来到世界上,都携带着生存和繁衍这两个最基本的使命,没有性就没有生命的延续,认识世界也就无从谈起。同时,性关系还是把动物雌雄双方联系到一起的纽带,是父母与子女羁绊的起点,堪称所有社会关系的基础。所以充分了解动物的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我们进一步认识生命、认识世界。
涉及动物性爱繁殖话题的书籍,每天听本书栏目曾经解读过一些。比如美国生物学家玛拉·哈尔特的《海洋中的爱与性》,就聚焦论述了海洋动物的繁殖方式;美国生物学大师弗朗斯·德瓦尔的《黑猩猩的政治》一书,则重点论述了在黑猩猩社会中,社会地位与性权力之间的关系。相比之下,今天这本《它们的性》,则把叙述重点放在了动物们的“繁殖策略”上。
无论是雄性还是雌性,都希望在求偶、交配和繁殖过程中占据尽可能多的利益,获得最优质的后代。但雌雄双方该谁追求谁、该如何求偶、谁能优先择偶?这些问题要想得到妥善解决,就都得讲究一定策略,策略里有大家都公认且遵循的阳谋,也有见不得光、心机满满的阴谋。通过审视动物繁殖过程中的阳谋与阴谋,我们会发现,性这个话题涉及的领域可远不止性本身,它堪称生命智慧的集中竞技场。
本书作者是“90后”青年学者王大可,她本名王云珂,是牛津大学动物学系鸟类研究所的博士,目前就职于中科院深圳先进院脑认知与脑疾病研究所。王大可长期写作科普专栏,她的文字幽默,文风活泼,本书编辑在看到王大可的文章后,和她一拍即合,这就有了这本干货满满、搞笑有趣的科普作品。本书在设计上花了不少小心思,拿到这本书时,你第一眼就会被它粉色的封皮吸引,翻开书后,还能看到很多绘制精美的博物画和生动有趣的手绘画。书中文字更是幽默诙谐,比如我们后面会提到的大西洋鲑鱼,正经繁衍的雄鱼被起名为“老公”,偷袭繁衍、抢人媳妇的雄鱼则被王大可起名为“老王”,让人读起来不禁一笑。
那么接下来,我就通过两个部分来带你了解“它们的性”。首先我们说说,在动物们的繁殖策略中,都有哪些“阳谋”?接下来我们再谈谈,在阳谋之外,动物们为了繁衍还琢磨出了哪些“阴谋”与“反阴谋”?
好,第一部分先说说,在动物们的繁殖策略中,都有哪些“阳谋”?
动物世界缤纷多彩,繁殖结构五花八门,不同的繁殖结构决定了动物们到底该使用什么繁殖策略。在所有繁殖结构中,我们最熟悉的当然是一夫一妻制,人类和很多鸟类,大多遵循这种比较专一的方式。除此以外,自然界中还普遍存在着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多妻多夫制和合作繁殖制。
其中,一夫多妻制很常见,一个雄性独占一整个后宫,大猩猩、金丝猴、海象都是如此。我们熟悉的狮子,狮群由至少一只雄狮和若干只雌狮组成,所以狮子既可以是一夫多妻制,也可以是多夫多妻制,二者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
和上述几种繁殖结构相比,一妻多夫制在哺乳动物中很少见,但在昆虫世界里很流行,比如蜜蜂和蚂蚁。或许是因为昆虫的脑子不够好使,所以雌性并不会在择偶过程中花太多精力,而是更倾向于和不同雄性多次交配,交配后再看谁的精子质量最好。而且昆虫的个体生命很脆弱,所以它们的后代需要有更多的基因多样性,来应对不同的环境挑战,比如某个雌性昆虫分别和不同雄性交配,有的雄性有抗杀虫剂基因,有的有跑得快基因,那这只雌性的后代在遇到环境挑战时,就总能有一部分后代活下来,不至于一遇打击就全军覆没。
和其他繁殖结构相比,合作繁殖比较少见,主要出现在哺乳动物、鱼类和鸟类社会中,比如画眉鸟,主要表现是有其他帮手来帮助小夫妻带孩子、喂食、筑巢等。人们至今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帮手会无私奉献,因为给别人带孩子不能给它们带来直接好处,反而会增加自己的生存风险。有人猜测,帮手通常是小夫妻的亲戚,帮小夫妻带孩子,其实也是在间接延续自己的基因,还有人认为,动物天然就有利他的本能,合作繁殖是本能的一种表现。
你看,不同物种结合自己的生存实际,发展出了不同的繁殖结构,但不管是哪种结构,不管雌雄间如何搭配,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每个个体都希望自己留下尽可能多、尽可能优秀的后代。可欲望无限资源有限,那该如何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争取尽可能多的繁殖利益呢?这本质上是雌雄两性间的性选择问题。查尔斯·达尔文曾提出,性选择可以分为两方面,分别是同性竞争和雌性选择。
我们先来说说同性竞争。要想赢得同性竞争,动物们会使用哪些阳谋?最简单直接的就是打架,动物界中的雄性往往天生好斗,尤其是发情期间攻击性格外强。因为赢了就有交配权,输了就会成为炮灰,所以雄性会不惜以性命为代价和同性竞争。
相关代表有很多,原鸡是家鸡的野生祖先,其中的斯氏原鸡就以超强的战斗力著名,决斗一旦开始就不会轻易停止,最终结局一般都是一方战死。蜂鸟的体型小巧可爱,但它们争夺配偶时却非常凶狠,两只雄性蜂鸟在空中相遇必有一场恶战,战斗结果通常是一方的舌头被撕裂,最终因无法进食而死去。
同性通过打架竞争可以理解,但打架往往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老这么打谁也受不了,所以很多社会性动物就演化出了社会等级这个阳谋,不同个体之间通过社会等级确定资源分配,等级越高的个体占有越多的交配资源。人类的近亲黑猩猩就属此类,它们会通过打斗与结盟在彼此间分出个高下,从而确定各自在群体里占据什么位置,等级确定后大家就能在一段时间内相安无事,从而减少内耗。
还有些动物追求进一步的经济适用性,它们干脆放弃了打斗,发明了和平竞争的阳谋,有点类似于传统功夫的点到为止。比如雄鹿喜欢向对手咆哮,咆哮的频率和时长可以反映雄性的打斗水平,越能吼就代表越能打,通过比拼嗓门,雄鹿就能在不动手的前提下分出个高下,竞争成本大幅降低。
还有些物种在求偶时比较看重物质,所以阳谋就是比拼物质条件。雄性睛斑扁隆头鱼为了获得雌性青睐,会四处寻找隐秘且舒适的小窝,精心装扮布置,这样才能吸引雌性前来产卵。优质的住宅有限,所以只有有房的雄性才找得到媳妇,没房的自然只能独身一人。
同性之间有自己的竞争方式,但光击败同性并不能达成繁衍目标,雄性们要想当爹,还必须得获得雌性的认可,这就涉及了性选择的第二个方面:雌性选择。
雄性说自己行,不代表雌性也觉得行。雌性有自己的择偶标准,如果说雄性竞争喜欢诉诸暴力,那雌性的择偶标准则常诉诸艺术,它们的阳谋是通过艺术来评测雄性是否优秀。
比如鬣蜥的喉囊本身没有任何实际用途,甚至可能给生存带来不利影响,但雌性鬣蜥就是喜欢好看的喉囊,所以雄性在发情期间会尽力展现自己喉囊的美。再比如雄性西方松鸡在求偶时,会竖起全身羽毛,奋力拍打翅膀,旋转跳跃闭眼,专注跳完求偶舞蹈,因为过于专心,猎人甚至可以在其跳舞期间徒手抓住它们。为什么雄性西方松鸡会这么投入于舞蹈呢?还不是因为雌性喜欢,跳得好就能博美人一笑。
不管是喉囊还是舞蹈,对生存都没什么实际意义,那为什么雌性还会以此作为择偶标准呢?1982年,美国生物学家威廉·汉密尔顿和马琳·祖克提出了健康假说,他们认为雌性偏爱健康的雄性。如果雄性不够健康,就没法长出鲜艳的羽毛或漂亮的喉囊,也没法把求偶的舞蹈跳得足够好。所以雌性其实是在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这些艺术标准来探查雄性的优秀程度。
性选择既有同性竞争又有雌性选择,如果雌雄双方相互吸引,那自然和谐愉快,但如果双方没互相看上眼,又该如何解决呢?答案很简单也很粗暴,那就是看谁打得过谁,谁强谁说了算。在鸟类和哺乳动物中,往往雄性体型较大,所以雄性占据交配的主导权,而在冷血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中,雌大雄小反而更常见,比如我们熟悉的蜘蛛就是这样,这时雌性占据交配的主导权。
在雄大雌小的物种中,由于雌性承担了绝大部分生育责任,所以它们在择偶游戏中是选择者,雄性只能以低姿态去迎合雌性。雌性喜欢长得帅的,雄性就尽量长帅一点,雌性喜欢能打架的,雄性就尽量能打一点。但雄性肯定不满足于做被挑选者,如果在同性竞争中获胜后还是得不到雌性的认可,就容易出现强迫性行为,你不愿意,我就强迫你。
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象海豹,海滩上的雄性象海豹会根据体型和武力值争夺交配权,最终只有不到三分之一雄性象海豹有交配机会,其他绝大多数雄性只能打光棍。雄性象海豹的阳谋是武力压倒一切,面对这一点,雌性象海豹没有拒绝的权利,因为雄性体型比自己大得多,反抗就意味着挨揍。
在雌大雄小的物种中,雌性则占据着交配的绝对主动权。在裸鼹鼠社会中,雌性体型较大,同时掌控着最高权力。雌性裸鼹鼠的阳谋是控制一切,高等级雌性的尿液中含有特定激素,会让低等级雌性失去性欲,既不排卵也不发情,变成女王的忠实仆人。同时,雄性也处于女王的绝对统治下,没有被宠幸的雄性会自觉增加精子的异常率,同时很好地管住下半身,绝不拈花惹草。
更极端的例子是鮟鱇鱼,这种鱼的雌雄体型差异巨大,雌性体重是雄性的几百倍甚至上千倍,海洋里较小的雄性鮟鱇鱼一旦遇上雌性,就会咬住雌性的皮肤逐渐和其融为一体,从此成为寄生在雌性身上的附属品,唯一的作用就是为雌性提供精子。一只雌性鮟鱇鱼最多可以供养六个老公,家庭地位可见一斑。
同性竞争有阳谋,异性选择也有阳谋,同性竞争和异性选择发生冲突时,则是谁强谁有理,在这些阳谋和规则的指导下,谁有资格交配、谁有资格挑选最好的配偶、谁有资格拥有更多的后宫,这些问题都有了解决的方案。
但话说回来,阳谋的优胜者可以光明正大地获得繁殖优势,但失败者可不会甘心看别人秀恩爱,所以就开始动心思了。接下来第二部分我们就谈谈,在阳谋之外,动物们为了繁衍还琢磨出了哪些“阴谋”与“反阴谋”?
强与弱并不是永恒的,某方面的优胜者在其他方面不一定优秀。深谙这一道理的很多物种琢磨出了精子竞争这条新赛道,在正面竞争中我可能比不过你,但我可以拼尽所有资源去生产尽可能多的精子,从而在微观领域超过你。在这些物种里,精子的数量、质量与社会地位呈现负相关,社会地位越低的个体,精子的数量和质量反而越高,精子竞争或许就是战败者最后的阴谋,因为如果对象找不到,精子质量又不行,那就只能等着绝后了。
在蓝鳃太阳鱼群体中,20%的雄性霸占了几乎所有资源,雌性对它们投怀送抱,却对80%的流浪汉不屑一顾。蓝鳃太阳鱼的流浪汉体型较小,根本无法用武力对抗强者,所以它们的阴谋是精子竞争加占人便宜,流浪汉们会长出格外大的睾丸,来产生更多、更快、更持久的精子,同时花费大量时间寻找正在交配的夫妻,趁着雌性排出卵子时,突然猛冲上去,把自己的精子排到卵子附近,以期能留下一儿半女。
大西洋鲑鱼在这方面做得更极端,极端到演化出两种不同的雄性形态,我们开头时提起过,这两种雄性分别是晚熟体型大的“老公”和早熟体型小的“老王”,“老王”只有“老公”体重的0.15%。不同形态代表着不同的生殖策略,“老公”们放弃了早交配的机会,选择多吃东西长身体,等强壮了再去求偶,而“老王”们选择早熟早交配。雌性当然喜欢强壮的“老公”,“老王”不受待见,所以就长出了格外大的睾丸,专趁人家交配时去捣乱,最终也能留下不少子女。
蓝鳃太阳鱼和大西洋鲑鱼的雄性弱者,都通过精子竞争的阴谋获得了自己的优势,不过有些物种的弱者在精子方面也没什么优势,所以它们就只能琢磨其他阴谋,比如提升偷袭的技巧。
雄性甲虫在发育期间,如果没有足够的食物,就无法长出带有攻击性的角,只有在食物充足、身长超过阈值后,角的生长才会被触发。有角的雄性甲虫会挖掘地道,把雌性藏在地道深处,然后自己守在门口,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没有角的甲虫肯定打不过这些家伙,它们为了交配,就会阴谋偷袭,悄无声息地凿穿地道的墙壁,围堵雌性完成交配,堪称偷袭的阴谋家。
和偷袭一样,欺骗也是一种常见的阴谋,动物们的欺骗水平,有时丝毫不在人之下。比如琴鸟在求偶时,雄性会通过歌声吸引雌性,如果雌性听了一会儿没有感觉,就会飞走离开。雄鸟费了半天劲儿唱歌,看快到手的媳妇竟然要飞走,就会立马转变声音,发出遇到捕食者时的警报声,表示外面危险。这样一来,被欺骗的雌性就只好留下来和雄性共度良宵了。
甲虫懂得偷袭,琴鸟擅长欺骗,流苏鹬则是集大成者,它们把偷袭和欺骗的阴谋运用得炉火纯青。
流苏鹬的雄鸟有三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是黑色的地主阶级,它们会占据领地吸引异性;第二种形态是白色的流浪汉,流浪汉们没有固定领地,而且不擅长打架,所以会一面臣服于地主,另一面找机会偷袭雌性,进行交配;第三种形态是长得很像雌性的伪装者,它们的阴谋是用外貌欺骗地主,伪装成雌性混进地主的后宫,然后伺机和雌性“姐妹们”交配。
流苏鹬雄鸟的这三种形态是由基因决定的,后天无法改变,但不管是哪种形态,它们都结合自身实际全力实现交配目的,地主主导并以阳谋取胜,流浪汉在阳谋之下用阴谋偷袭,伪装者则用欺骗的阴谋瞒天过海。
在阳谋失败的情况下,雄性会利用精子竞争、偷袭、欺骗等阴谋争取留下后代。那雌性又是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反抗这些阴谋,来保障后代尽可能优秀的呢?其实雌性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在交配期间、怀孕期间乃至生产后保障自己的主导权。
在动物界,强迫性行为是普遍现象,所以在交配期间,雌性也演化出了很多保护自己的反阴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权力的反转。比如雌性会痛打有强奸意图的雄性,多打几次对方就老实了,但这只适用于雌性比雄性大的生物或者是母系社会。有些雌性还可以关闭自己的生殖器,比如雌性细角黾蝽的生殖器有一扇小门,如果遇到不喜欢的雄性,雌性就会关闭生殖器拒绝交配。有的雌性还懂得雇佣保镖,保镖一般是自己的老公,比如母鸡在被骚扰时就会主动寻找老公的帮助。
此外,雌性还可以主动控制交配和受精进程。比如雌性孔雀鱼偏爱类胡萝卜素丰富的雄性,遇到喜欢的雄性后,雌性就会通过延长交配时间让这类雄性传递更多精子。我们刚才提到的睛斑扁隆头鱼,既有筑巢求偶的地主,又有专门偷袭的小偷,雌性当然喜欢家底雄厚的地主,所以它们会用自己的卵巢液去影响精子的受精概率。卵巢液能提高精子的运动表现,但对地主精子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这显然是雌性实现自己生育意志的有效方式。
如果交配期间,雌性没能和自己喜欢的雄性交配,那也没关系,雌性还能进行交配后选择。1983年,美国生物学家兰迪·桑希尔发现,许多物种的雌性都拥有储存精子的器官,比如蜻蜓和豆娘 ,它们可以选择性储存和使用某个雄性的精子,排出或消化掉不喜欢的雄性强行注入的精子,就算不小心受孕了,雌性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故意让胚胎死亡或营养不良。在极端情况下,雌性甚至会遗弃和不喜欢的雄性所生的孩子,以保障后代足够优秀,这也算是雌性面对雄性时的最终反阴谋了。
有趣的是,当雌雄双方的繁殖角色转变时,雄性也能主动控制受孕过程。比如海洋中的模范父亲海龙,雌性只负责提供卵子,雄性则负责在自己的育儿袋里孵化后代。而海龙爸爸在孕育孩子时也非常有心机,它会根据孩子母亲的质量,决定在孵化时付出多少精力。如果遇到了优秀的海龙妈妈,海龙爸爸孵化宝宝的概率会大大增加,反之则更可能流产。这与雌性控制怀孕过程的方式如出一辙,只不过角色反了过来。
雌性在争取生育利益时,不仅有对付雄性的反阴谋,也有针对雌性的阴谋。比如母鸡一方面极其呵护自己下的蛋,但同时又热衷于吃掉地位低的母鸡的蛋。因为这能保护它自己的生育优先权,还能让它从别的鸡蛋中获得丰富的蛋白质,从而下更多的蛋。
面对繁殖后代这一重要大事,雄性有自己的算盘,雌性有自己的主意,就算强者们通过阳谋取得了胜利,但各方依然会竭尽所能地用阴谋扳回一城。对所有个体都公平的繁殖策略,就算有,也会被多占便宜的贪婪所抛弃。那在性爱这件事儿上,真的就没有最优解了吗?
有人可能会说,最公平的是一夫一妻制,谁都有份,谁也别抢,看起来好像是这么回事儿,但其实仍有巨大漏洞,那就是出轨。
上世纪60年代就有科学家发现,有93%的雀形目鸟类都遵循一夫一妻制。比如红翅黑鹂理论上只拥有一个配偶,但有一次人们把一个地区的所有雄鸟都结扎了,然而39窝鸟蛋里仍有27窝孵出了小鸟,这是为什么呢?很显然,这里的雌鸟背着配偶和外地雄性交配过了。
直到上世纪90年代,DNA鉴定技术出现后,人们才终于发现,在实行一夫一妻制的鸟类中,出轨其实也很普遍。比如在雀形目中,只有14%的鸟类是真正的一夫一妻制,绝大多数鸟类物种中存在私生子。作者认为,雄性鸟类的阴谋是通过出轨留下更多后代,雌性鸟类的阴谋是想通过出轨偶遇高富帅,拥有最优质的后代,结果就是双方都出轨。可见就算是在一夫一妻制的动物中,忠诚仍然是一种珍贵而又罕见的品质。
好,到这里本书内容就介绍得差不多了,简单总结一下。
首先我们聊了,在动物们的繁殖策略中,都有哪些“阳谋”。动物的繁殖结构多种多样,包括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多妻多夫制和合作繁殖制等等。不管哪种结构,都涉及同性竞争和异性选择,同性之间通过战斗、示威、财产等阳谋比拼高下,异性则会以外貌、行为、财富等为标准权衡择偶。如果雌雄双方没有相互吸引,那么谁强谁有理。
接着我们说了,在阳谋之外,动物们为了繁衍还琢磨出了哪些“阴谋”和“反阴谋”。为了延续基因,动物世界的雄性弱者们开发出了精子竞争、偷袭、欺骗等阴谋,只为在竞争失败后争取留下一儿半女,雌性则形成了防止强迫性行为的反阴谋,同时还有主动控制交配、受精和怀孕进程的能力。就算是一夫一妻制这种看似最公平的方式,也在出轨的影响下变得不那么公平,在动物世界里,阴谋诡计无处不在。
我们在阅读动物题材的科普作品时,总是下意识地从动物身上寻找人类的影子,希望能获得来自大自然的启发,但在这本书中,作者王大可不止一次地强调,要避免人类中心主义,不能总以人类的角度出发去思考动物行为。
比如在谈到一夫一妻制时,王大可虽然引用了红翅黑鹂的例子来证明出轨的普遍存在,但也通过大山雀的例子证明了很多物种确实对彼此忠诚。牛津郊区的森林里生活着一夫一妻制的大山雀,研究人员在不同地方放置了食物基站,每次只能允许一只大山雀进去觅食,按理来说大山雀夫妻应该分头行动各吃各的,这样效率最高。可实际情况是,大山雀夫妻宁可饿着也不分开,其中一只进食时,另一只会在门口等到对方吃完,才一起去下一个基站觅食。大山雀身上表现出的这种忠诚,可能有人将之解释为爱情,正是爱情让它们不离不弃。
但在王大可看来,并没有什么能证明大山雀夫妻在一起是因为爱,也许是因为别的。爱情是人类的思想,谁能证明动物身上也存在爱呢?正所谓“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如果以人类视角看待这些现象,就容易陷入人类中心主义造成的偏见中。当然,大山雀夫妻之间有没有真爱,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是否应该以人类视角看待动物行为,每个人也有自己的答案。就我个人看来,生命演化有连续性,动物和人类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我们可以用人类眼光看待动物行为,但王大可的观点确实也能给我们启发,把我们从人类中心主义的惯性思维中拉出来一把,以更通透的视角看待一切,这也是本书的重要意义所在。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这本书的全版电子书,也已经附在文稿末尾。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看全文和脑图,也欢迎你点击右上角的“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
通过审视动物繁殖过程中的阳谋与阴谋,我们会发现,性这个话题涉及的领域可远不止性本身,它堪称生命智慧的集中竞技场。
-
生命演化有连续性,动物和人类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我们可以用人类眼光看待动物行为,但王大可的观点确实也能给我们启发,把我们从人类中心主义的惯性思维中拉出来一把,以更通透的视角看待一切,这也是本书的重要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