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塑造人类思维》 于理解读
《语言塑造人类思维》| 于理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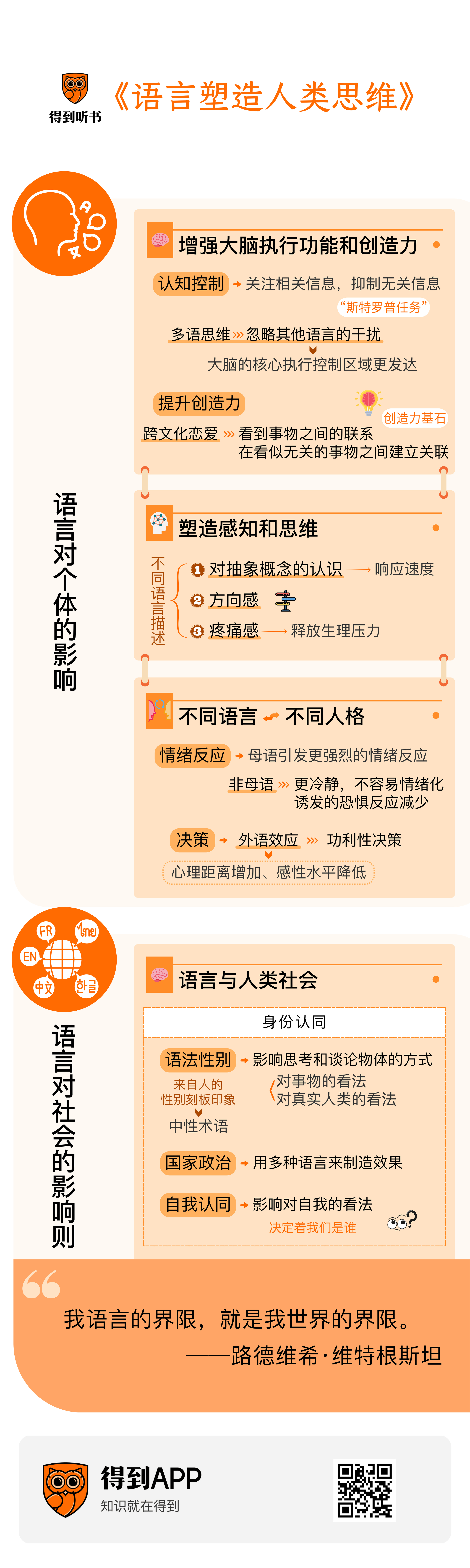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于理。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书叫做《语言塑造人类思维》,出版于2023年10月。这本书回答的问题是:我们使用的语言,如何塑造了我们的思维?更准确地说,这本书讲的其实是学习多种语言对人类思维的影响。世界上大多数人口都会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比如,大多数中国人从小就开始学英语,掌握汉语和英语这两种语言。那么,多语会对我们的思维和认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世界各地的实验室都做过一些关于双语学习的研究。研究发现,对老年人来说,使用多种语言能增加老年人的认知储备,使得老年人患上阿尔茨海默病的时间延迟4到6年。有双语经验的孩子,能更早理解物体和物体的名称并不是一一对应的,也就是理解存在一个指代现实的符号系统。再比如,语言中的性别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我们对事物的看法。在中文里,名词是没有性别的,但是在一些语言,比如俄语、法语或者德语中,名词是有语法性别的。如果你学过这类语言,你估计也在心里困惑过。为什么俄罗斯人认为桥梁是阳性的?德国人则把桥梁称为女“她”,认为桥是阴性的。罗马尼亚语就更特别了,如果只有一座桥,那么桥就是阳性的,如果你指代的是两座或两座以上的桥,那么它就是阴性的。语言中的这些语法性别,到底如何影响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呢?
今天,我们就通过这本书,来聊一聊语言如何塑造了我们的思维。我们先来聊聊语言对个体的影响,看看它如何影响了我们的思维、创造力、认知、记忆和情感。预告一下,听完这部分后,你可能会很想立马开始学习一门新的语言;然后我们再来谈语言在整个社会层面的影响,它如何影响了人们的身份认同,又造成了哪些偏见和歧视。
好,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这本书。
我们先从生理角度,来谈谈掌握多种语言对我们的大脑有哪些好处。
首先,掌握多种语言能增强大脑的执行功能。执行功能指的是一系列认知过程,包括注意力、抑制、工作记忆和认知灵活性等。有一项经典的实验叫斯特罗普任务,在这个实验中,人们会看到一些用彩色油墨打印出的代表颜色的单词,比如用黑色墨水打印出的单词“绿”,或者用绿色墨水打印出的单词“黑”。实验要求被试者忽略单词内容,说出墨水的颜色,这个时候被试者很容易被单词内容干扰。于是,当单词和墨水颜色匹配时,被试者能很快地说出墨水的颜色,但如果单词所指的颜色和油墨颜色不同的话,人们需要反应更长时间。在斯特罗普任务中,多语者通常表现得更好,他们关注油墨颜色并且忽略单词内容的能力要更强。关注相关信息,并且抑制无关信息的能力,就是大脑的执行功能之一,被称为认知控制。当我们开车时,需要能够专注于路面,忽略让你分心的东西;当学生考试时,也需要专注于试卷,忽略外界的杂音。抑制性控制是我们每个人在专注时都需要的东西,而大量实验表明,通晓多种语言的人在执行功能的各方面都表现得更好。
为什么呢?因为多语思维,恰恰能磨炼这种在忽略什么和注意什么之间跳转,以及在不同任务间切换的能力。要再深入地解释这一点,我们来看看切换语言时,多语者的大脑里发生了什么。
在很多人的想象中,大脑里可能有一个开关,在不同语言中来回切换,不使用某种语言时就把它关闭,将另一种语言打开。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科学界也是这么认为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不同语言在我们的大脑中都一直是处于打开状态,自动运行的。当你听到一个“S”开头的音时,根据语境,你大脑中“S”开头的一些中文单词和英文单词都会被自动激活。不论语种,大脑对声音可能指向的所有意义都保持了开放性。而且不仅仅是声音会激活不同的语言,字母、口型、音调,都可以是触发器。大脑随时准备好接受任何语言输入,并且快速理解和响应,这比在两个语言中来回切换效率要高。本质上来说,大脑是一个具有并行处理功能的超级有机体,对于多语者来说尤其如此。当然,语言能在多大程度上被激活,也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包括语言的掌握程度、学习语言的年龄和先后顺序、最近使用语言的情况,以及语言之间的相似程度。最近没有使用过的语言更少被激活,这也是为什么如果一个人很久没有说过某种语言,当再次需要使用该语言时,他可能需要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才能恢复流利水平。
当大脑中的多种语言被同时激活,多语者就需要学会忽略其他语言的干扰,并且在不同语言的词汇和规则之间反复切换,这就能锻炼他们大脑的控制能力。就像经过锻炼的肌肉一样,双语者大脑的核心控制区域更发达,执行功能更强。学习多种语言能改变大脑的灰质和白质区域。灰质是大脑容纳神经细胞体、处理信息的地方,白质的功能则是通过神经冲动把信号从一个灰质区域传递到另一个灰质区域。打个比方,灰质是一个个城市,白质就是连接城市的高速公路。双语者额叶区域的灰质密度就比较高,白质也比较多。尽管随着年龄的增长,灰质体积和白质的完整性会下降,但懂得多种语言能减缓这一过程,因此,掌握两种及以上语言的老年人患上认知障碍的风险比较低。一个国家所使用的语言数量和阿尔茨海默病发病率之间存在直接关系。在多语言国家,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率较低。
在执行功能之外,最近的研究表明,掌握多种语言还能提升创造力。有研究者测量过人们在跨文化恋爱前后的表现,结果发现,跨文化恋爱提高了被试者的创造力水平,恋爱时间越长,为产品营销想出创意名称的能力越强。和外国友人接触的频率越高,在创业和工作创新等方面的表现就越好。而之所以掌握多种语言能提升创造力,也和我们上面说的大脑对语言的处理模式有关。正是因为大脑让所有的语言协同激活、并行处理,加强了双语者头脑中声音、字母和单词之间的联结,多语者能看到事物之间的联系,并且能在看似无关的事物之间建立关联,这些联系对于产生创见、领悟和洞察至关重要,而这正是创造力的基石。
好了,我们刚刚说到,学习多种语言能增强大脑的执行功能,还能提升创造力。除此之外,语言的影响力还要更加强大,它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我们的感知和思维。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对很多事物的感知就不一样。就比如“注意力”,在中文里,和“注意力”搭配的动词是“集中”,我们觉得注意是需要付出努力的东西;在法语里,和“注意力”搭配的动词是“制造”,如果你不制造,它就不存在;在英语里,动词是“支付”,因为注意力很有价值;而在德语里,人们会说“赠送”注意力,注意力是一份礼物。不同语言描述注意力的方式不同,人们对注意力的感知也不同。
再比如,不同语言中描述颜色的方式不同,人们感知颜色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在中文里,我们有几十甚至上百种描述颜色的方式,简单的有大红色、天蓝色、明黄色,复杂的有中国传统色,比如朱砂、豆绿、孔雀蓝等等。但是,在一些语言里,描述颜色的词汇是非常匮乏的,世界上至少有20种语言只有三到四个基本色彩词语,一个词代表白色或浅色,一个词代表红—黄色调,一个词代表黑—绿—蓝色调。在英语中,表示蓝色的单个基本词汇只有一个词“blue”,俄语里则是有两个不同的基本单词,一个形容浅蓝色,一个形容深蓝色。当英语使用者和俄语使用者接受颜色辨别测试时,俄语使用者在区分这两种颜色时就会更快。语言中有没有表达深浅不同的蓝色的词汇,不会妨碍我们感知不同的色彩,但它会影响我们的响应速度。
语言还会影响方向感。中文和英语里,都有东西南北、前后左右。不过,有的语言里就没有其中一种。比如,有的语言里只有东西南北,他们说话的时候就要时刻弄清楚东西南北在哪。他们甚至会用东西南北来形容自己身体和四肢的方位,比如,他们会说用“南边的手”来拿苹果。
语言甚至还能影响我们的疼痛感。比如有研究者做过实验,如果允许受试者说脏话,那么他把手放进冰水里后坚持的时间会更长,这可能是因为语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释放生理压力,怪不得人们在撞到桌角或者被踩到脚趾时会忍不住飙出一句脏话。
以上我们能看到,语言能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感知和思维,包括对抽象概念的认识、方向感,以及疼痛感等等。那么,有一个问题就出现了——语言是否会限制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呢?
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和本杰明·沃尔夫曾提出一个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这一假说的一个论点是:语言决定思维。其中包含了一个有些极端的观点,那就是语言里某些词汇的缺失,会导致人们无法去思考这些词汇指代的事物。支持这一观点的一个经典例子,就是在因纽特人的语言中,关于雪的词语有超过50个。雪是因纽特人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部分,他们有很多利用雪的方式,那么他们对雪的认知就和其他人不太一样,其他人可能就无法理解他们和雪有关的一些词语。当然,语言决定论这样极端的观点受到了不少抵制,把语言等同于思想的观点太绝对了。作者就指出,他不认为所有的想法、记忆、学习和情绪都是语言导向的,比如我们有一些像是“爱”这样“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事物,再比如,有一些像是骑自行车或者游泳之类的学习,有时根本不需要语言。
虽然语言不会决定思维,但语言确实是在以强有力的方式来塑造思维的。爱德华·萨丕尔曾说过:“仅把语言想象成解决沟通和思考的具体问题的附带手段,是一个相当大的错觉。事实上,‘现实世界’很大程度上是在不知不觉中建立在群体的语言习惯之上的。”语言是我们处理信息最强大的工具之一,如果说一种语言的系统过滤了我们对现实世界的感知,那么学习另一种语言就能让我们获得另一种感知世界的方式。
在塑造感知和思维之外,语言甚至还影响着我们的人格。有时候,切换到不同的语言后,一个人表现出的人格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这是因为每种语言所关联的文化、经历、记忆、情绪和意义都不同,选择某一种语言,就像是启动了一套独特的系统。比如,有一项针对汉英双语者的研究发现,被试者在用汉语回答问题时,会表现出更多的群体性,也更加谦虚,这和汉语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特征相对应。
人的情绪反应也可能会随着语言的变化而变化。母语通常会引发更强烈的情绪反应,这可能是因为母语是我们最初生活在其中的语言。比如,“我爱你”这句话,用母语和非母语来说,感觉是不同的,用母语来说会更有情感冲击力。用母语和第二语言来说脏话或者禁忌语,人们感受到的紧张情绪也不一样。正如纳尔逊·曼德拉曾说的那样:“如果你用一个人能理解的语言和他交谈,那这交谈会进入他的大脑。如果你用他自己的语言和他交谈,那么这交谈就会走进他的心灵。”反过来说,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在需要情感距离的时候会更喜欢用非母语。大多数双语者都认为,在使用非母语时,他们会更冷静,不容易情绪化。在心理治疗的过程中,双语者就更有可能用非母语和咨询师讨论创伤和痛苦的话题。研究也表明,使用外语时,语言诱发的恐惧反应也会减少。
使用不同的语言,还可能会影响人的决策。当使用第二语言的时候,人会做出更合乎逻辑和理性的决定。比如那个经典的电车难题:一辆电车正朝着五个工人飞驰而来,但他们毫不知情,你站在火车轨道上方的桥上,旁边有一个人,如果你把这个人从桥上推下去,他会当场死亡,但电车也会停下来,那五个工人能活下来。那么,你会选择用一个人的性命来救这五个人吗?
在用母语回答时,有20%的双语者表示,可以把一个人推下桥去救五条人命。而在用外语作答时,这一比例增加到了33%。外语效应表明,当面临道德困境时,使用外语的话,人们会做出更多的功利性决策,就比如牺牲一个人来救五个人。之所以会产生这一变化,可能是因为外语导致心理距离增加、感性水平降低了。研究表明,无论是道德判断,还是涉及财务分配、健康医疗的选择,人们使用第二语言的时候都比使用母语更加理性。比如,在赌博的实验场景下,当研究人员用非母语去鼓动双语者参与赌博时,被试者会更冷静、更少参与。再比如,还有研究者曾要求双语者用母语或非母语来评估医疗问题,结果发现,使用外语会降低人们对疾病症状和治疗副作用严重性的感知,人们觉得疾病更容易治愈,身体和情感上的痛苦也更少。使用外语还能提高人们对试验性治疗的接受程度,可见,外语还能改变我们解读健康信息的方式。
我们是谁,我们相信什么,喜欢什么,都会受到语言的影响,因为每种语言都关联着不同的体验、记忆、情感和意义。因此,当我们使用不同的语言时,就会凸显自我不同的方面。
好,到这里,我们从个人的角度出发,聊了语言对大脑、感知、思维乃至人格的影响,但语言对我们的影响不仅仅关乎个体。接下来,我们把视角扩大,来看看语言对社会的影响。
还记得在开头,我们谈到了语言中的性别问题吗?在很多语言中,名词都是有语法性别的。虽然语法性别可能并不代表着人们对某种事物的性别看法,但研究表明,它会影响人们思考和谈论物体的方式。比如,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要求德语-英语双语者和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者来描述钥匙。在德语中,钥匙是阳性的;在西班牙语中,钥匙是阴性的。德英双语者描述钥匙的词有坚硬、有分量、参差不齐、金属质地、锯齿状,而西英双语者用的词则是金色、精细、小巧、可爱、袖珍等。可见,人们对物体的看法在很大程度受到了语法性别的影响,而这种语法性别的影响比我们想象中要更加深远。人类学家亚历克斯·沙姆斯使用谷歌翻译把土耳其语翻译成英语时发现,人工智能也会被语言,又或者说来自人的性别刻板印象所影响。土耳其是一种中性语言,男“他”和女“她”是用一个单词所表示的。而在谷歌的自动翻译中,土耳其语的“TA是一名医生”被翻译为英语后,这个“TA”就是男“他”,而“TA是一名护士”则会被翻译成女“她”;“TA努力工作”会被翻译成男“他”,而“TA很懒惰”则会被翻译成女“她”。沙姆斯把他的这一发现发到社交媒体上之后引起了骚动,后来谷歌的翻译算法进行了修正,在土耳其语的“TA”翻译成英语时,谷歌翻译会提供两种性别选择。可见,语言中的性别刻板印象不仅会影响我们对事物的看法,也会影响我们对真实的人类的看法。
为了抵制语法性别导致的性别刻板印象,一些国家甚至发起了社会运动,号召停止使用性别化的语言,转而使用性别中立的术语。比如,瑞典在传统阳性代词和阴性代词的基础上添加了新的无性别代词;在法国,人们也发明了一个新的性别中立代词“iel”,这个词融合了阳性的“il”和阴性的“elle”。在过去,法语中大多数代表职业的名词都只有阳性,没有阴性的形式,比如教授、律师、工程师、警察等等,这些都是一些在历史上长期被认为专属于男性的职业。随着女性职场地位的提升,逐渐有了从事这些职业的女性,于是,人们开始为一些职业名词创造阴性形式,但这些用法一直没有得到官方的正式承认。为了称呼这些女性,人们只能在这些职业名词前面加个“女士”,组成词组,比如,介绍一位男性法官的职业时,人们会说:“他是一位法官”。而介绍一位女性法官时,人们就要说:“她是一位女法官”。直到2019年,法语官方规范机构法兰西学术院才允许医生、教授等职业拥有女性化专属名称,结束了长达数年的官方禁令。
语言对社会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性别印象上,在国家政治方面,语言的力量也无处不在。作者指出,在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哪个国家,选择的词语、创造的标签,都不仅仅是为了恰到好处地反映它们的内容,而是为了改变人们对它所代表的东西的看法。比如,布什政府把“遗产税”称为“死亡税”,把石油开采称为“负责任的能源勘探”,把伐木称为“健康森林倡议”。再比如,拜登政府把移民的称谓从“非法”改成“非登记在册”,把“外国人”改成“非本国公民”。这些不同的称谓,都会引起听众不同的感受和反应,影响人们做出支持或反对的决策,可见语言的力量。许多政治人物都会在政治舞台上运用多种语言来制造效果,在一次著名的冷战演讲中,约翰·肯尼迪总统说过一句名言:“我是一名柏林人”,以表示对柏林人民的声援。这句话之所以被载入史册,是因为这句话是在英语演讲时用德语说出的,而大多数德国公民都对这句话耳熟能详,这也使得肯尼迪的这句话在当时引起了听众强烈的共鸣,让这句话有了极强的影响力。
语言不仅影响了我们对事物、对他人的看法,也影响着我们对自我的看法,它决定着我们是谁。正如个体的自我会受语言影响一样,语言还引导着文化、民俗、信仰体系、价值观和群体认同。这也是为什么在历史上,某些国家在殖民过程中会阻止人们使用他们的母语,而将一种不同的语言强加给他们。大多数人都把目光聚焦于经济、政治和身体上的统治,但事实上,语言的统治才切中了一个国家和人民的要害,因为语言和思想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紧密。
好了,以上就是这本书里我想和你分享的主要内容。我们今天从个人和社会的角度,聊了语言如何塑造了我们的感知、思维和身份认同。掌握多种语言能增强大脑的执行功能,提升创造力。语言影响着我们对颜色、方向、疼痛感等多种事物的感知,甚至还能影响我们的人格。有时候,切换到不同的语言,一个人的人格也会随之变化,做出不同的决策和行为。在社会层面上,语言中的语法性别可能导致性别偏见。而由于语言和思想之间的关系如此紧密,一种语言不仅塑造了个体的自我,还引导着文化、价值观和群体认同。语言的力量无处不在。
值得一提的是,掌握多种语言不仅有锻炼大脑、提升创造力的好处,来自世界各地的多项研究表明,掌握多种语言还能提高收入。和只掌握一种语言的人相比,双语者的收入更高。而且还有统计表明,人们认为懂得一种以上语言的人更具魅力。听到这,你是不是也想去学习一门新的语言了?作者指出,人们在任何年龄都可以学习另一种语言,并且几乎可以立马受益。学习一门语言的第一个最佳时间,是一出生就开始学,第二个最佳时间,就是当下。
传说在古巴比伦城中矗立着一座塔,它高耸入云,或许可以算作人类的第一座摩天大楼。《圣经》中提到,这个塔叫作“巴别塔”,是世界上多种语言的发祥地,而最初建造巴别塔是为了“抵达天堂”。《创世纪》中还提到,当上帝降临人间,见到人类妄图造塔上天,便说:“他们是一族之民,有一样的语言;如今既做起这事来,将来他们所图谋要做的事,就没什么能阻拦他们了。”为了阻止人们登上天堂,上帝将他们分散于世界各地,并替他们创造了不同的语言,这样他们便无法交流,也无法造塔了。可见,语言之力量的不凡。巴别塔的故事说明了语言既有包容的属性,也有排他的特征,既能促进交流,也能阻碍沟通。正如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曾说过:“我语言的界限,就是我世界的界限。”希望我们都能尽己所能多学习一门语言,去看更大的世界。
好了,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要是你喜欢这本书,也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1、仅把语言想象成解决沟通和思考的具体问题的附带手段,是一个相当大的错觉。事实上,‘现实世界’很大程度上是在不知不觉中建立在群体的语言习惯之上的。
2、正如个体的自我会受语言影响一样,语言还引导着文化、民俗、信仰体系、价值观和群体认同。
3、我语言的界限,就是我世界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