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 胡安焉、吴琦:《生活在低处》,在阅读写作中完成自己
【终版】胡安焉生活在低处.MP3
文学有什么用?胡安焉是一个答案。
他是一位处于持续探索和创作的作家,同时又做过面包店学徒、售货员、服装店主、拣货工人、快递员等等二十来份工作,一有积蓄,就重新坐下来写作;如同我们熟悉的小说家雷蒙德·卡佛,做过伐木工、保安、仓库保管员,一有积蓄就回去写作。
作家这个身份不比那些工作更高,或更低,只是代表着更主动地接近阅读和写作,更主动地接近文学。
文学有什么用?胡安焉说,“我早就清楚,文学不能帮我获得别的东西……发表和出版从来不是我写作的目的。对我来说,写作首先是我的个人表达,是一种以审美对待人生的形式……文学无法直接应用于现实,它不负责解决实际问题,否则它将是极其低效的一种手段;但是文学可以影响人,这种影响并非即时和具体地发生,而是以一种更根本和远的方式。”
我想我理解他,文学对我的意义是:只生活一次是不够的,那些生活还需要在文学里“过”一次,凝结成一种说法,我才有可能知道自己在如何生活,该如何生活。
我想知道他是否和我有共识。
胡安焉答应来《大望局》之后,我想到一位理想的对话者——《单读》主编吴琦,他对文学也有自己的观点,例如,他可以写优秀的文学作品,但是选择了编辑、翻译和访谈。他似乎对生活本身更好奇。
在这个环境里,因为《生活在低处》诚恳的底色,我们暴露自己的性格:胡安焉不大喜欢说话,我和吴琦因为工作而不得不说话然而也不大喜欢说话,你可以观察对话缝隙中的那些冷场、沉默和欲言又止。
胡安焉,作家,著有小说、非虚构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递》等
吴琦,《单读》主编,记者,与项飙合著《把自己作为方法》、翻译作品“詹姆斯·鲍德温系列”等,播客《螺丝在拧紧》主播
00:00:32 先听胡安焉分享个小故事
00:10:08 写作者的某种天赋
00:19:13 胡安焉的开店经验与体验
00:29:40 开始我们的“严肃版”介绍
00:33:49 胡安焉现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00:40:15 吴琦分享自己的生活状态
00:48:05 听贾老师发条总结性弹幕
00:50:24 哪些因素促成了他们的生活观?
01:09:50 阅读和写作对贾老师的意义
01:13:20 他们是怎样用阅读来建立自己的?
01:25:36 哪些书塑造了胡安焉的写作特点?
01:36:57 公布之后的写作/工作计划
划重点
-
生活在低处,只要把头低下,你还会看到身边有人比你的处境更艰难。
-
对事物的准确记忆是写作者的一种天赋。
-
尽管那些痛苦的经历已成往事,你仍应深入其中,用写作和阅读给它们建立一个说法。
-
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是理想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够接受它。你所接受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你的理想生活。
-
选择隐居或独自生活的人,需要放下被社会需要的期望。
-
可能真正的隐居是内心的隐居。这意味着我内心的一部分不再向别人敞开,甚至不交托于所谓的文学和书写,而是决定留给自己。
-
“历史始终在不知疲倦地败坏地理的名声。唯一的抵御方式就是成为一个流浪汉,一位游牧者,成为一道阴影,掠过倒映在水晶水面中的那些花边般、瓷器状的廊柱。”——《悲伤与理智》
-
死于远方者,即为勇敢之死。
-
“对我来说,写作既是对生活的消化和体味,也是对自我的不断深入和辨认。生活、自我和写作这三者在我身上的关系大约是,首先生活和阅读提供了经验,我通过这些经验观照自身、澄清自我;而写作最初是我对这些观照和澄清的不同形式的投射,之后则成为一种从自我到无我的超脱——在人的生命尺度内,它不大可能完成,因此我的写作也不会终止。 ”——《生活在低处》
-
“我也不是个目标清晰、意志坚定的人。假如今天我写下的这些让人觉得比较清晰和坚定,那也是因为时间的堆叠把其中的褶皱都压成了实心。”——《生活在低处》
-
也许,智慧是和柔弱相伴而行的。
-
我们常误以为人生目标是站在人生之外去选择的,就像点菜一样选择要过哪种生活。然而,事实上没有人有这样的机会,我们都是被抛入生活中的,遇上什么就是什么。
-
只生活一次是不够的,那些生活还需要在文学里“过”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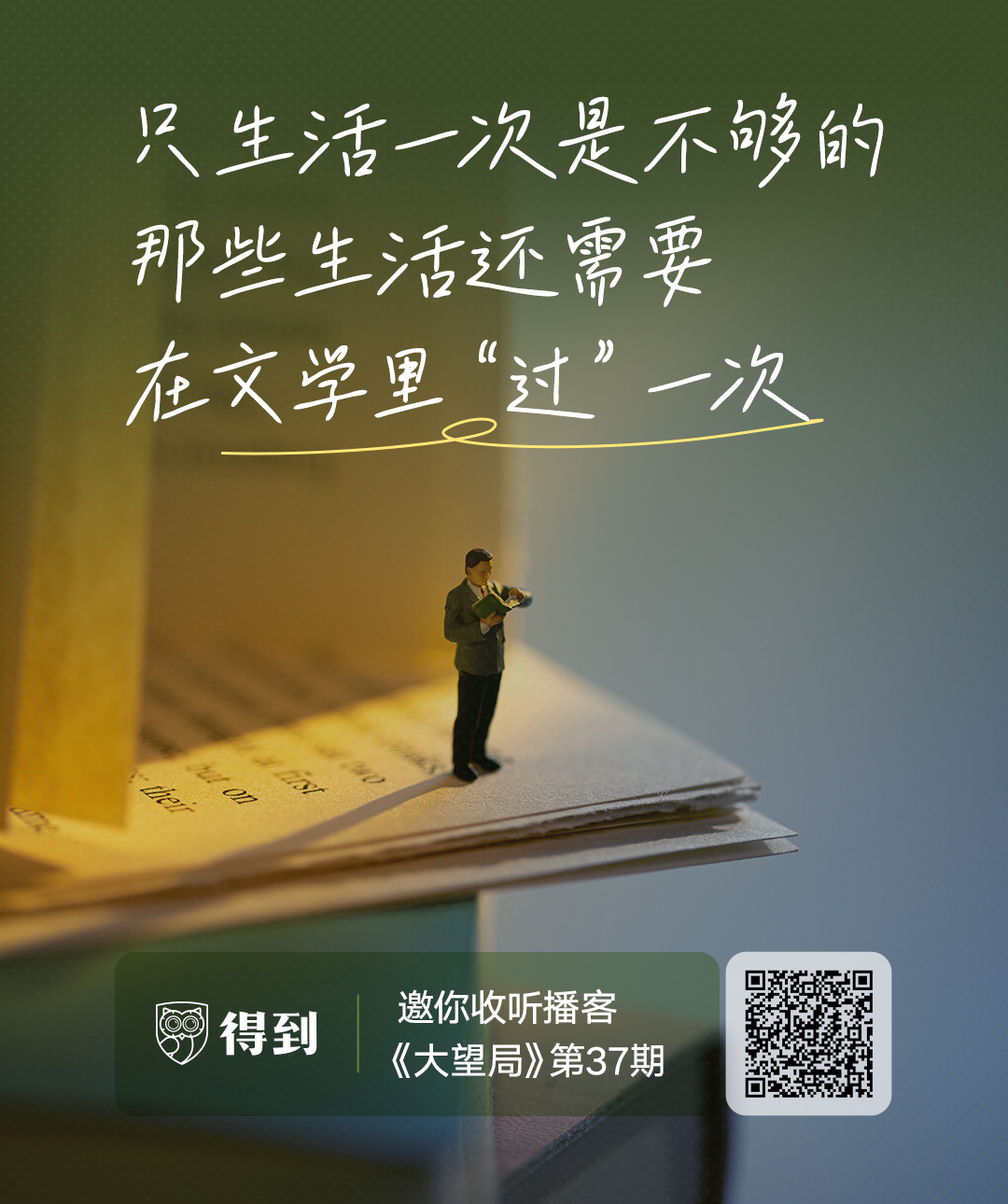
《生活在低处》自序
2016年有一段时间,我暂住在一个朋友的工厂宿舍里。有一天他对我说,和我同住的人告诉他,我每晚把所有时间都用来读书,他没想到我竟然这么好学。他用了“好学”这个词,这让我愣了一下,当时我已经三十七岁,有很多年没听到过这个词了。随即我意识到——当然不是单从这件事上,而是从我对他方方面面的了解上——对他来说,读书就是为了提升自己、掌握技能、获得知识,然后以此来改善生活;假如不带有这些目的,那读书就是浪费时间。可是我不知道,像《包法利夫人》《卡拉马佐夫兄弟》《安娜·卡列尼娜》《城堡》《追忆似水年华》这样的小说,我读了之后如何学以致用?幸好他不清楚我在读什么书,否则他就会对我失望和担忧,因为在他看来,我的阅读是在虚掷光阴。
当时,我刚读完他推荐给我的几本书,书名我现在记不起来了,内容是关于创业和互联网思维之类的,因为我和他正好在合伙搞生意。或许他是以为,我又搞来了几本同类的书,每晚在宿舍里继续进修和提升,为我们的创业打好基础。可是那几个晚上我其实是在读布考斯基。我对这件事记忆犹新,是因为当时我觉得,用“好学”来形容读布考斯基好像有点反讽——我能通过读他学到什么呢,学他如何玩世不恭、放任自流,还是如何任性地把所有事情搞砸?我读布考斯基,别无其他,仅仅因为喜欢而已。
我早就清楚,文学不能帮我获得别的东西。比如说,它不能为我找到一份工作。当然,我也不需要它为我找工作。文学只能带我进入文学,而这就是我想要的。不过我朋友的观点也无可厚非,他把读书看作一种手段,他读的也大多是工具书,那当然就要考察其有效性,去区分有用和没用的阅读。
至于文学到底有什么用,或者它应不应该有用,庄子有句话经常被人引用:“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这句作为总结的话,出现在《庄子·内篇·人间世》的结尾,在原文中有比较明确的意指:庄子认为人生于乱世,假如既有才华也有志气,就很容易受到上位者摆布,成为他人的工具,甚至沦为牺牲品;反倒是那些没有才华和志气的人,甚至是身体有残缺的人,最后得以保全自身。不过今天人们在引用这句话时,一般已摘除了原文的语境,使它的能指变得更加丰富。比如在我的印象中,做哲学的人就喜欢借此以自况,因为大众普遍认为哲学研究没什么实际用途,对此解释起来未免费劲,倒不如借庄子之言以解嘲。但“无用之用”对于哲学研究者来说,当然不是指成为废才以保命,而是指哲学一般不会直接、明确和具体地作用于我们生活的某个方面。但它会作用于我们的精神方面——它关注更根本和终极的问题,更抽象并囊括万事万物。
阅读和写作之于我的情况也与此相似,起码2020年之前,我的写作几乎不为人知,也没带来过什么经济回报。至于2020年之后情况有所改变,那是因缘和运气使然,机会掉到了我头上,我恰好接住了而已,并非出于规划或争取。我从2009年开始写作,早年也投过稿,也渴望发表或出版,但发表和出版从来不是我写作的目的。对我来说,写作首先是我的个人表达,是一种以审美对待人生的形式,能发表或出版固然好,不能我也不会为之调整。
《我在北京送快递》出版后,我经常被问到,将来会不会选择一份写作方面的工作。这个问题从前我没考虑过,因为以我的履历、学历和年龄等条件,根本就不可能找到这类工作。但是现在既然有人问了,那我也只好认真想一下。我觉得自己并不抗拒通过写作挣钱,比如从事一份文字工作——当然我会对工作内容有所挑剔——只是我不认为工作性质的写作能代表我,我仍然需要在工作之余保持个人写作,这才是对我真正重要的事情。而在个人写作方面,我所追求的就只在于写作本身,而不在写作之外的任何地方。我认为艺术是务虚的——我是指狭义的艺术——它不是工具、手段或途径,而就是目的本身。
在这本文集里,第一章的三篇讲述了我的童年和原生家庭。如今回过头看,我接受的学校教育,主要是传授知识和纪律,至于观念的培养,往往流于空洞,对我的影响很小。所谓言传不如身教,实际上,原生家庭对我的影响,要比学校教育更具决定性。尤其是父母如何看待生活和社会、他们相信和遵从些什么,以及对待我的感情形式等,都极大地影响了我的性格、气质和追求,这些与我后来的社会经历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今天的我。而这一章的内容,也是接续自《我在北京送快递》的自传写作。
第二章“我为什么写作”是我对自己写作经历的回顾和反思,也是一次通过写作理解生活、认识自我的过程。对我来说,写作既是对生活的消化和体味,也是对自我的不断深入和辨认。生活、自我和写作这三者在我身上的关系大约是,首先生活和阅读提供了经验,我通过这些经验观照自身、澄清自我;而写作最初是我对这些观照和澄清的不同形式的投射,之后则成为一种从自我到无我的超脱——在人的生命尺度内,它不大可能完成,因此我的写作也不会终止。
第三章收录的随笔,是我的一些日常观察和感想的记录,同时也是我过往写作小说时的副产物,可以理解为一种培养语感的练习。不过其实我更愿意把自己至今为止所有的写作都视为练习,而不仅仅是这些随笔。因为我从未感觉自己的写作足够完善,或者是大体可以定型、瓜熟蒂落了。我喜欢“不成熟”的状态,这意味着更开放和更丰富的可能性。我希望一生都以练习的心态对待写作。这些随笔的内容都很平常,比如:记录某个清晨我在出租屋里醒来;记录我看到一张自己照片时的感想;记录某次观察蚂蚁捕食蚯蚓的感受;记录某天在理发店理发的过程;记录另一天在理发店理发的过程……它们有些是叙事性的,有些是感受性的,有些是思辨性的,还有些可能主要是我的牢骚。不过无论是什么,它们都肯定不具有功能性或实用性,它们不能授业解惑,也不提供新知锐见。文学和哲学一样,无法直接应用于现实,它不负责解决实际问题,否则它将是极其低效的一种手段;但是文学可以影响人,这种影响并非即时和具体地发生,而是以一种更根本和深远的方式。
我对卡佛说过的一句话印象深刻:“作家要有为普通的事物,比如为落日或一只旧鞋子感到惊讶的禀赋。”在我看来,文学不是向读者传递些什么,而是触动读者身上的什么。特殊的事物往往有更明确和具体的特征、内涵、趣味、意指或意图等,要不就受到更多巧合因素的摆布,因而远离了事物的本质性和普遍性——艺术的意象其实天然地亲近普通的事物。而“普通的事物”也是我写作的耕耘之地。
和绝大多数人一样,我只是一个普通人,至少在四十岁之前,做过的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工作,经济收入还拖了人均收入的后腿;从来没有人用“优秀”来形容过我,也没有人真正关心我的内心世界。总之,我不是山尖上刻有海拔高度的那块石碑,而只是山脚下随处可见的一块小石子。某种意义上,这本书中全部的内容,都来自那些在低处生活的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