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菌记》 王朝解读
《食菌记》| 王朝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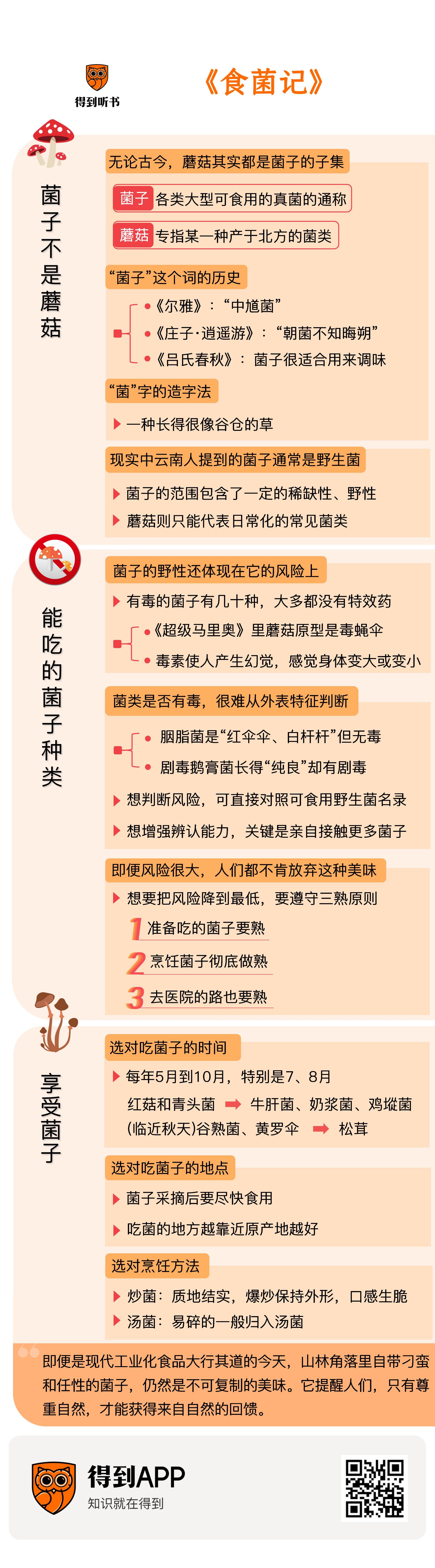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要讲的这本《食菌(jùn)记》,一目了然,讲的是和吃菌子有关的故事。
听了这个标题,你可能有很多疑问要问了,什么是菌子?菌子和蘑菇有什么区别?怎么辨认哪些菌子能吃?每年夏天,都会在新闻、自媒体上出现的那些云南人吃菌子吃出幻觉的段子,是真的吗?让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2023年访华期间一口气连吃四盘的见手青,真有那么好吃吗?很多人去了云南就去吃菌子火锅,是最好的吃菌方式吗?
这些问题,这本书里都有答案。但这本书没有在“吃”的层面停下,而是继续深挖更深刻、更广阔的“菌子宇宙”,你会了解到人类历史上和菌子有关的很多事情。这本书还有个副标题,“识菌、拾菌、食菌的山林记忆”,这里作者连玩三个谐音梗,用三个“食菌”的同音词,讲三个步骤,分别是认识菌子,拾获菌子,食用菌子。而山林记忆,则点出了菌子文化的核心意象——山林,或者更直白地说,远离人类文明,远离工业化、可预制、标准化的现代社会。
我们在这里用“菌子”这个词,一方面是名从主人,尊重当地人意见,而这里主要指西南地区方言对各类真菌的俗称,另一方面,其实也是为了强调和常见的“蘑菇”的区别。这里说的蘑菇,就是那些现在实现大规模人工培育的木耳、金针菇、香菇、平菇等等,而菌子往往说的是野生菌,是需要额外付出一些努力,离开舒适的都市环境才能获得的真菌。
作者柳开林也是这么一个敢于离开舒适环境的人。他其实并非专业的厨师,或者研究真菌的生物学家,而是一个互联网行业的资深从业者和创业者,在京东、搜狐这样的大公司干过,也自己担任过创业公司董事长,但不变的是他和菌子的情缘。柳开林是云南楚雄人,和很多云南人一样,也是从小就会捡菌子、吃菌子,当他长大后为了学习和工作离开云南,他才发现外面的菌子观念如此不同:北方山林里也长着不少菌子,但北方人对这些山珍的渴望相对有限,并没有像云南人一样趋之若鹜。相较云南人的菌子,外地的蘑菇大多都已经被驯化,成为超市里就能买到的日常食材。于是他就四处搜罗各种材料,和全世界的人们交流捡菌心得,也会寻求专业人士的进一步鉴定,辨识世界各地的菌子。
所以,现在的这本《食菌记》既饱含来自作者对故乡的温情记忆,也有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等等专业研究机构的科学把关,为我们严谨地介绍食用真菌的各类知识。即便你是一个很熟悉食用菌的人,也能在这本书里获得很多新奇的认识,比如,游戏《超级马里奥》里为什么吃蘑菇身体会变大?佛教故事中的佛陀圆寂为什么会和菌子有关?为什么松茸以前在云南不受欢迎?总之,你会发现,菌子代表的是一种不可驯化的野性,但在历史上又一直引诱着人类来“征服”,也就是食用菌子。用作者的话来说,菌子的美味是“一场人类味觉与自然、历史、文化以及期待和回忆的合谋与共振”。
当然,说来也巧,和本书的作者一样,我也是一个云南人,同样也在菌子文化中耳濡目染。所以在解读这本书时,我也会为你补充一些更加真实的故事和体验,让你有更切身的体会。
那么,我们就开始享用一场菌子的知识盛宴吧。
好,首先我们还是要解决一下基本问题——到底这个菌子,指的是什么?
如果下一个通用的定义,那么菌子说的其实就是各类大型真菌,一般说的是可食用的品类。但前面说过,这里强调菌子,具有一定地域方言意味,也是要和蘑菇做一个刻意区分。
其实,在云南话里,基本上不用“蘑菇”这个词,往往所有真菌都会被称为某种菌,比如香菇,我们在云南会叫香菌,而平菇之类的有时会被称为“人工菌”。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菌子,就是蘑菇的别名。
但这本书提醒我们,这句话不对,蘑菇的范畴其实比菌子要小,而且相比菌子,还是一个后出现的汉语词汇。所以在这,我们先来说说“菌子”这个词的历史,辨清一下词义。
早在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尔雅》的释草篇中,就记载了几种菌,比如“中馗菌”。而在同时代的《庄子·逍遥游》当中,我们能读到这么一句话,“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说是有一种菌子早上冒出来,没到太阳落下就烂了,这个菌子就和春生夏死的蝉一起,比喻寿命短,也就见识短,可见古人已经比较熟悉菌子的生命周期。此外,《吕氏春秋》甚至还写到了菌子的美味,说当时被称为“越骆”的华南地区产出的菌子很适合用来调味。
从“菌”字的造字法来看,也能看出古人的一些朴素认知,比如草字头,代表认为属于草本植物,而下面是一个四方框住的禾字,这个字是囷,属于象形字,就是装了很多稻禾的地方,也就是谷仓。所以“菌”字,意思就是一种长得很像谷仓的草。你可以回忆一下,传统的谷仓就是一个大圆柱,上面一个锥形的顶,是不是和菌子非常相似?
到了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当中,“菌”字有了比较明确的含义,书里如此解释:“菌,地蕈(xùn)也。”那这个“蕈”又是什么?实际上,这些都是对不同地方长出的真菌的不同称呼。当时古人发明了好几个字,长在木头上的称为“蕈”;长在地上的称为“菌”;柔软的耳类称为“䓴”(ruǎn),比如木耳;带有香味的称为“芝”,也就是“灵芝”的芝。但总之,“菌”字之后就基本上成了大型真菌的通用名称。
到了唐朝,“菌子”指代可食用的大型真菌的用法基本上就稳定下来了,比如唐末韩鄂所著的《四时纂要》记载“三月种菌子”,可见当时的人甚至都开始人工培育菌子了。
那蘑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词呢?这就要说到南宋,当时浙江有一个人写了一本《菌谱》,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食用菌专著,里面记载了一种“麦蕈”,说吃起来像北方的蘑菇蕈,这就算是蘑菇比较早的记载了。从这里也看得出来,菌是通称,而蘑菇是专指某一种产于北方的菌类。
那么这个蘑菇,是从哪来的词?实际上,这很可能是对蒙古语对草原常见的大型真菌通称的音译。蘑菇的本体,大约是现在我们说的“口蘑”,说的就是从草原出口,经过张家口向农耕地区贸易的真菌品类,包括好几个外貌相似的草原菌种,大多都是外表白色,有明显的伞盖状结构,这就是狭义的北方“蘑菇”。
但在那个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相互交融的时代,蒙古语的说法逐渐在北方沉淀下来,元代王祯所著的《农书》中有一条关于“菌子”的记载,说中原地区把菌叫做“磨菇”,这里的中原说的是如今河南区域。而同时代的南方人还在坚持说“菌”,比如南京人潘之恒的《广菌谱》。到明朝之后,这个新名词才逐渐在汉语中扎根下来,从专名逐渐变为统称,并在晚清时终于翻身做主,当时的《农学丛书》记载,“菌,俗名蘑菇。”这个关系的颠倒,可能与政治中心由南方转回北方,北方方言成为官话有关,也反映了以口蘑为代表的南北贸易之兴盛,使狭义的蘑菇变得更加常见,以至于代替了“菌”。
而在云南,由于当地汉族大多都是明初的江南移民,保留了原先的语言习惯,当地方言仍旧保留了自古以来的“菌子”之称。而在使用上,现在的“蘑菇”虽然变成通称,但还是受到“口蘑”外形的影响,只形容有明显伞状结构的真菌,而“菌子”的外形则更加广泛,无论是否有伞都会被称为菌子,比如木耳、银耳、扫把菌等等。
总结起来,我们可以说,无论古今,蘑菇其实都是菌子的子集。但在现实的使用中,云南人提到的菌子通常都是野生菌,而且不是所有蘑菇都能叫菌子,特别是那些已经工业化生产的。如果我说要做菌子汤,原料肯定不是香菇、海鲜菇、金针菇之类的,而多半是青头菌、鸡㙡菌等等野生菌。云南人说到菌子,就是在说一种不可多得的珍品,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菌子的范围也包含了一定的稀缺性、野性,必须要和日常生活有一定距离,而蘑菇则只能代表日常化的常见菌类。
不过,菌子的野性不仅体现在定义上,还体现在它的风险上。根据我国监测数据,从2010年至2020年,全国共有38676人菌子中毒,而云南人就占了其中的43.6%。而云南疾控的数据则显示,2011年到2019年间因食物中毒而去世的病例有445人,其中250人是因为菌类中毒。根据云南疾控对223件菌子中毒事件的研究,引起中毒的菌子种类有几十种之多,毒性比较轻的能引起肠胃炎型、神经精神型等症状,严重的有急性肝损害型、横纹肌溶解型、溶血型等等症状,而且大多数菌类的毒素都没有特效药。
那么,我们如何辨别哪些菌子能吃呢?比如传说有一些口诀,颜色鲜艳的有毒、有鳞片的有毒、菌杆上有环的有毒、被虫子吃过的没毒等等。还有一首网络上流传很广的歌谣,歌词说:“红伞伞,白杆杆,吃完一起躺板板。”的确,最典型的毒菌,毒蝇鹅膏菌,也叫毒蝇伞,长得就是红菌盖,上面点缀着白色鳞片,一根菌杆,上面还有菌环。其实《超级马里奥》里面的那种蘑菇,原型就是毒蝇伞,它含有鹅膏蕈氨酸和蝇蕈碱等毒素,会使人产生幻觉,感觉自己身体变大或者变小,可能就成为马里奥吃蘑菇变大的灵感。但是,实际上,毒蝇伞拥有的这些典型特征并不能决定菌子有毒与否,简单抓着几个特征反而很容易引起误解。
比如说,颜色鲜艳不一定有毒,颜色朴素的反而有可能有毒。实不相瞒,当年第一次听到“红伞伞”时候,我发现这首歌在常常吃菌的云南,反而是闻所未闻。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歌词显然是错的——就在听到那首歌的几天前,我还从市场上买了胭脂菌回去。这个胭脂菌,也叫红菌,外形就是字面意义上的红伞伞、白杆杆。然而,胭脂菌确确实实是无毒的,只不过因为菌盖易碎,收拾起来麻烦,所以即便味道鲜甜,在云南餐桌上地位也不算很高。不过,确实也有一种外观相似的毒红菌,体型稍小,不但味道苦辣,而且毒性很强。相较之下,有些菌类长得很“纯良”,看着就是颜色朴素的普通蘑菇,实际上却含有能够致死的毒素,比如云南急诊室中最常见的两种毒菌,致死率最高的致命鹅膏以及亚稀褶红菇,长得都和无毒种类极其相似。
事实上,菌类是否有毒,很难从外表特征判断。常见的高危品种确实有这么几个特征可以记住,能够帮你排除一部分错误答案,比如说,根据杨祝良教授2015年《中国鹅膏科真菌图志》的总结,剧毒鹅膏菌的菌柄实心、基部球形或膨大;非剧毒鹅膏菌的菌柄空心、基部不膨大。虽然也有无毒的菌类长有菌托,但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还是先排除一些错误答案更安全。
但是,注意了,这排除的只是一小部分,实际上很多毒菌品种和无毒品种长得极其相似,连专门的真菌学家都难以区分,稍有不慎就会吃进医院。比如欧洲有一道名菜,叫“凯撒菇”,学名叫橙盖鹅膏菌。没错,就是刚才说过有好多剧毒品种的鹅膏菌。它的菌盖橙色,刚长出来的时候像一颗鸡蛋,所以也有个别称“鸡蛋菇”。和它的鹅膏菌亲戚们不一样,橙盖鹅膏菌无毒,而且极其鲜美。之所以叫凯撒,传说古罗马的凯撒大帝很喜欢吃这种菌子,数千年来都是欧洲王室餐桌上的一道佳肴。但前面说过,鹅膏菌有剧毒的品种很难辨别,造成了欧洲历史上好几次影响深远的食品安全事故。其中一次的受害者,是和东汉光武帝同时代的古罗马皇帝克劳狄一世,有一天晚上吃了一盘凯撒菇,当晚开始身体不适,第二天就毒发身亡,他十七岁的继子趁势继位,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暴君尼禄。有一个说法,就是尼禄的母亲为了帮助尼禄抢班夺权,把橙盖鹅膏菌换成了类似的毒鹅膏,两种菌子熟了以后看不出区别,味道也相似,导致皇帝中毒暴毙。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对人类来说,并不是有毒的菌子就完全不吃。不少传统食用菌类都是已经清楚知道有毒,但是通过合理的加工和处理,可以减弱甚至消除毒素。
不过,这里还是要提醒,很多菌类的毒素都不会在高温下完全分解。比如,有好几种牛肝菌切开以后,切面会逐渐变成青蓝色,也就是俗称的“见手青”。见手青并不是一种菌类,而是包括红牛肝菌、黑牛肝菌等十几种,有一些毒性稍大,一旦处理不好,轻则出现呕吐、腹泻,重则有幻觉、多器官衰竭等症状,而其他品种则更安全,都属于云南常见的食用菌类。虽然云南人会说见手青多加蒜、炒熟后就无毒,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一顿吃得太多,还是有可能中毒。这种中毒的最著名受害者,可能是历史上的佛陀。根据佛教典籍记载,佛陀八十多岁时,在印度北部吃了一顿“旃檀树茸”,大概是某种菌类,他还专门嘱咐别人,这种东西最好就是只有自己吃,其他人就不要吃了。显然,佛陀这么做肯定不会是为了独占美味,而可能是认为这道菜有一定风险,怕波及他人。没想到,此后佛陀果然痢疾加重,第二天就身故涅槃了。而根据当地语言直译,这种树茸的名字就是“猪肉一样美味”。作者推测,这很可能指的就是一种牛肝菌,因为牛肝菌煮熟后有一种猪肉的油腻口感,在欧洲也被称为猪蘑菇。但是,印度北部的褐环乳牛肝菌煮熟后仍旧含有微量毒素,足以成为压倒老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是说到牛肝菌中毒,它最知名的症状,是所谓的“见小人”,也就是因为其中含有少量的裸盖菇素,导致患者出现幻觉。中国著名真菌学家臧穆在云南考察时,记录过见手青中毒的病例,留下过这么一段记载,说患者看到了几个15厘米大的小人,头戴草帽,身穿彩色衣服,在房里进进出出,还跟别人说小心别踩到他们了,除此之外,患者的思维都非常清楚。奇怪的是,别的菌类引起的幻觉可能千奇百怪,但是见手青中毒后的幻觉却普遍都是看见小人的报告,其中的科学原理至今不清楚。然而,现在因为各种网络段子的传播,很多人听了这种听起来“有趣”的幻觉,就趋之若鹜,想故意试试吃见手青中毒。这里要严肃地警告大家,见手青的毒素并不只是裸盖菇素,如果已经出现了幻觉,其他毒素可能也已经发作,严重的情况下会导致器官衰竭,是非常危险的症状。
说了这么多吓人的案例,其实也是为了让大家理解,即便吃菌风险这么大,古今中外的人们都还是不肯放弃这种美味。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因为人类是一种敢于冒险的物种,所以才能不断创新、进取。在满足口腹之欲的问题上,人类的大胆更是不可低估。有毒就再煮煮,再试试别的办法,不会轻易放弃。就像苏东坡听说河豚有毒,但极其鲜美,冒险去吃了一次,最后感慨,“也值一死!”可以想见,如果他当年被贬到云南,肯定也会冒险去尝试各种野生菌。
不过如今,这种风险也在逐渐减少。现在要判断菌子到底能不能吃,有一个简便的方法,直接对照云南省卫健委发布的可食用野生菌名录。每年到了菌子生长的季节,云南各地就会突然出现很多海报,上面是给常见的有毒菌类照的“标准照”,提醒食客们要避免误食。不仅如此,云南人还会隔三岔五收到短信通知,食用野生菌要注意安全。随着风险意识的提高,云南菌类中毒的案例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反而因为菌子在网上火了,没有风险意识的其他省份又开始出现了更多中毒案例。
作者说,要增强辨认菌类的能力,提前研究专业的著作只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要亲自去接触更多菌子。“菌子拾得多了,它们自然就认识你了。”不过,想要把风险降到最低,关键还是人类自己不能太过自信,可以遵守书中提到的三熟原则:准备吃的菌子要熟,不熟悉的菌子不吃,烹饪菌子要彻底做熟,还有一条,去医院的路也要熟。
仔细一想,这也体现了菌子难以驯服的野性。古往今来,人类食用菌类的历史已经有数千年,但人类依然没有办法简便地判断菌子到底能不能吃,仍然需要像“神农尝百草”一样,逐个尝试,不知多少代像苏轼那样勇敢的食客,前赴后继地品尝了不知多少种菌子,积累了多少经验,今天我们才能开出一张不完全令人满意的菌类“白名单”,享受难得的美味。
好,说了这么多要注意的风险,我们现在还是回到这本书的标题《食菌记》,讲讲到底怎么样享受菌子。
首先,吃菌子的时间要对。真菌生长大多需要一定湿度和温度,所以一般菌子的生长季节就是每年5月到10月,特别是7、8两个月最多。漫长的菌子季中,每一种菌子都有自己的生长节奏,标志着时间的逐渐推进。先冒出来的,一般是红菇和青头菌,然后随着夏季的深入,更多的是牛肝菌、奶浆菌,特别是七月火把节前后,也是鸡㙡菌最多的时候,所以就有“火把鸡㙡”的俗称。而且鸡㙡长出来后不能等太久,要在还没完全开伞时食用,那时口感最好。
再等到差不多临近秋天,麦子要熟了,就会出现更多的谷熟菌、黄罗伞。等到菌子季节的尾声,外省人更爱吃的松茸还能在山上的松林里继续生长。如今,不少餐馆一年四季都提供菌类餐品,但是不少都是冻品,已经丧失了原本的鲜味,自然就不好吃了。
除了时间,地点也很重要。因为菌子采摘后要尽快食用,否则大多很快腐烂,会丧失鲜味和口感,所以吃菌的地方越靠近原产地越好。为了能够保证菌子的美味,云南人的必杀技就是直接去山里捡菌子。因为菌类生长大多位置一般比较稳定,云南俗称叫“菌窝”,常去捡菌子的人,在山上都有自己专属的菌窝导航图。为了不被别人抢先,凌晨三四点就要赶着上山去捡菌,有时候去得早了,菌子才刚刚蹿出来,可以再去转几圈捡别的,等回来的时候,菌子可能就已经长好了。最好的情况下,早上从山上捡来的菌子,回到家里,招呼一家人一人搬个小板凳,这边负责用小刀把带土的根部削干净,那边把削好的放到水里清洗,有条件的还可以拿几片南瓜叶揉搓。等一切准备妥当,到了中午,就可以抓紧尝鲜了。
古人也懂这个道理,比如南宋理宗的皇后非常爱吃台州老家出产的香蕈,就叫人用双手举着长满菌子的桐木,一路送到临安城,现摘现吃。
有些菌子比较坚挺,比如牛肝菌、松茸等,在适当包装后可以长途运输,所以在产地之外也可能吃到。而有些菌子比较脆弱,比如青头菌、胭脂菌等,易碎,耐不住包装,禁不起颠簸,所以往往只在山林附近才方便吃到。所以如果要去云南吃菌子,首选肯定不是昆明的网红菜市场,或者野生菌批发市场,而是可以挑选一些靠近山区的县市,那里的野生菌种类更多,味道也更好。
不在云南也不必担心,菌子不只是在云南生长,每个地方其实都有自己的鲜味。作者就提到,比如东北的松林里有俗称红蘑、松树钉的血红铆钉菇,北京的山区有松乳菇、点柄乳牛肝菌等等,甚至西北地区的沙土地里,也有中国美味蘑菇。没错,这种菌的学名就叫中国美味蘑菇。有时候,甚至你也不用去郊区,在环境保持比较好的大公园里,也可能捡到白参,或者俗称鸡腿菇的毛头鬼伞。
除了时间和地点,还要选择相应的烹饪方法。外地客人来到云南尝菌子,最容易上当的一点,就是吃“菌子火锅”,把牛肝菌、鸡㙡、松茸之类的一起放在锅里煮。实际上,并非所有菌子都适合煮汤,而把几种菌子放到一锅混煮的烹饪方法,把各种菌类特有的鲜味都混在了一起,更是暴殄天物。
书里就提到了一个分法,很有用,也就是炒菌和汤菌之分。顾名思义,就是根据菌子更适合两种不同的烹饪方式,在生活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分类。像是牛肝菌、干巴菌之类的,质地比较结实,爆炒可以保持外形,口感生脆,就属于炒菌。炒菌当中,干巴菌又是最为名贵的,价格有时能超过黄金。著名作家汪曾祺曾经在西南联大时期在云南尝了不少菌子,他说干巴菌乍一看“有点像一堆半干的牛粪”,让人怀疑“这种东西也能吃?!”而等尝了用青椒炒过的干巴菌,“入口便会使你张目结舌:这东西这么好吃?!”
另外,像青头菌、胭脂菌、鸡㙡菌这种易碎的,虽然也能炒,一般则会归入汤菌。对于汤菌,料理的要求就稍低一些,很多鲜味相近的菌子是可以煮成一锅的。但是其中鸡㙡一般都是特殊对待。汪曾祺对鸡㙡情有独钟,他评价是“菌中之王”,这一点我非常同意。相较其他汤菌,鸡㙡汤味道鲜浓,有鸡汤的鲜甜,又有自己独特的清香,一般都是独享一锅。有一次上山吃饭,中午时分,主人家端上一盆鸡㙡汤,都是早上刚刚从山上捡来的,汤汁入口鲜香浓滑,菌子吃起来口感脆韧兼备,从此成为我对山珍美味的标准定义。当然,古人也早已熟知鸡㙡的美味。在明代,鸡㙡甚至成为皇家贡品,每斤价值数两黄金,在云南可以用来上交抵税。有明朝文人记载,“菌之美者,以滇之鸡㙡为第一,然道远而值贵也”。但其实在云南,鸡㙡并不罕见,不像干巴菌一样难得,是一道常见的佳肴。
说到这,可能你会奇怪,怎么不提松露和松茸?的确,松露在欧洲被当作与鹅肝、鱼子酱并列的三大美食之一,也被称为“黑色钻石”。而在日本古代文学经典《万叶集》中,有一句“高松岭狭茸伞立,林间满盛秋之香”。所以在日本人眼中,就像春天属于樱花,秋天就属于松茸。在中国,虽然这两种菌子都有产出,但并不那么受欢迎。松露在云南也叫猪拱菌,它的主要消费者更多时候是猪,从来没有被云南人当作餐桌美味。松茸则被叫做“臭鸡㙡”,被认为有股药味,不如造型相似的鸡㙡。有一回,我的云南亲戚被送了一筐松茸,于是按照鸡㙡的处理方法煮汤喝,结果一大家子人愣是没喝完,感慨早知道应该送给广东朋友。的确,虽然云南人自己不吃松茸,但却占了全国松茸产量的70%,其中大多都是卖给了广东和日本,占到日本进口量的90%。
松露和松茸并不是不美味,而是这两种菌子没有进入云南的饮食文化,云南人不懂使用相应的烹调手段。但对其他人来说,用合适的烹饪方法,比如松茸直接用黄油煎,能够激发出松香味,同样是难得的美食。
所以,菌子美味的奥妙也在于,它要求人去适应它,只有人顺着菌子的天性,才能激发它自身最极致的美味。这何尝不是菌子野性的一部分呢?
好,说到这,本书的解读也到最后了。
对我、对本书作者柳开林来说,菌子还有另一层意义,那就是代表云南的故乡味道。为了解读这本书,几天前我让家人专门给我邮来一箱见手青,按照祖传的猪油加大蒜爆炒之后,还是难以复制出家乡的鲜美,反倒是之后几天一直头晕,晚上做了不少光怪陆离的梦,估计是吃得太多,还有些毒素作祟。
虽然食用菌类有种种的风险,但是古今中外的人们,都没有放弃食用各类菌子,甚至敢于冒着中毒的风险大快朵颐。这里,我们还是强调,一定要先保证安全,再去尝试食用。
但这就是菌子魅力的一部分,它代表的是山林、旷野,代表人类无法控制的大自然,它不允许人类驾驭自己,既不能被人工培育,它的美味也不能离它的产地太远。正是这种刁蛮和任性,即便是现代工业化食品大行其道的今天,这些山林角落里的真菌仍然是不可复制的美味。在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菌子仍旧在提醒人们,只有尊重自然,才能获得来自自然的回馈。
好,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对书中其他内容还有兴趣,也建议你去阅读原书。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1.在明朝以前,“菌”都是汉语中对大型真菌的统称,后来才被“蘑菇”慢慢取代。现在的“菌子”往往代表野生菌,是要到山林中采摘、付出额外努力才能获得的珍稀食材。
2.辨别菌子能否食用,不能依赖简单的外观特征或民间传说,而要依靠专业的真菌学知识、长期实践经验等等,可以遵循“三熟原则”:只吃熟悉的菌类,烹饪菌类一定做熟,去医院的路更要熟。
3.享受菌子美味,不是将各种菌子随意混煮在一起,而是要讲究采摘的时令、产地的新鲜度和针对不同菌种的特定烹饪方法。比如区分炒菌和汤菌。
4.菌子代表着不可驯化的野性,它要求人类去适应它的生长规律和特性,比如遵循特定的采摘季节,尽快食用以保持新鲜度。这让菌子在现代工业化食品盛行的今天仍保持其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