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以东》 王朝解读
《耶路撒冷以东》| 王朝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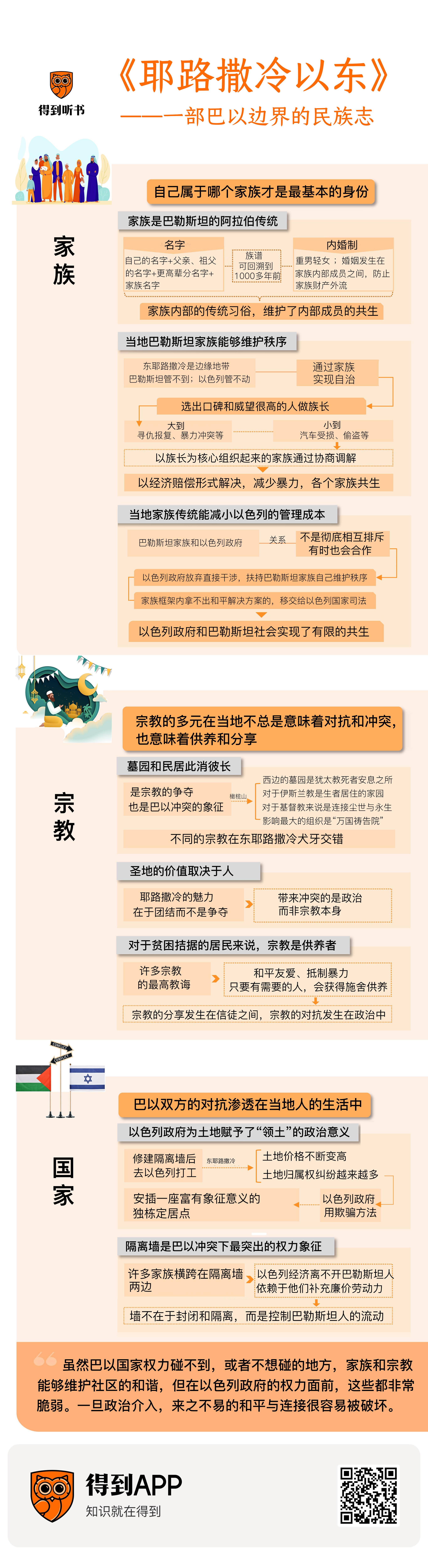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
今天这本书标题叫《耶路撒冷以东》。耶路撒冷,大家都听说过,那耶路撒冷往东是什么地方呢?是一个既代表耶路撒冷这座城市,又不属于耶路撒冷的地方,叫东耶路撒冷。为什么这么说呢?
说代表耶路撒冷,因为闻名遐迩的世界遗产“耶路撒冷旧城”就在东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最神圣的那些圣地也都坐落在这里,比如犹太教的哭墙、伊斯兰教的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等等。说不属于,则是因为东耶路撒冷在国际法上理应属于巴勒斯坦,是约旦河西岸的一部分,巴以问题的最前线。当地居民多数是阿拉伯人,而非以色列主体民族犹太人。但是,以色列1967年以来,事实上控制着整个耶路撒冷。东耶路撒冷一方面被以色列当作首都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是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首都,被以色列置于特殊的隔离控制下。这本书的副标题“一部巴以边界的民族志”,一方面是点明东耶路撒冷的地理位置在巴以边界上,另一方面也是说东耶路撒冷处在一个边界状态,地位仍然没有定论。
而副标题里说的这个“民族志”,则是一种需要通过长期的实地调查研究完成的学术研究。民族志里会详细记录社会互动的模式和参与者的观点,在当地的背景下理解社会成员的行为。这本书的作者赵萱,就是中国第一个在耶路撒冷长期调查的学者。他和那里的居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巴以问题的一个宝贵的内部视角。从这个视角去看耶路撒冷,就会发现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书中有很多理论,也有很多故事,这些故事能为我们勾勒出真正的耶路撒冷。
在东耶路撒冷,更多的故事不是围绕着民族或者宗教的冲突而发生的,而是围绕着“治理”与“被治理”的关系,是普通人在夹缝间求生存的故事。我们在新闻里看到巴以冲突,往往会想象两个互相独立、互相分割的民族。听到耶路撒冷、加沙这些地理名词,就会想象这些遥远的地方是一个简单的整体。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不是抽象的巴勒斯坦社会、以色列社会,而是共生的“巴以社会”。边界也并不是一条抽象的线,反而是一片特殊的区域。看似对立、分离的双方,在这里是纠缠在一起的。本书把视野还原到现场,从当地人的生活来展现,在宏大的地缘政治背景下,人们之间的关系不是被冲突所定义的,而是既有具体的家长里短,也有无权者和有权者的斗智斗勇。从作者赵萱的描写中,我有一个感觉:冲突我们听得太多了,但是回到他们的生活本身,“共生”是可能的。
本书从三个维度讲述了当地人的生活,分别是家族、宗教还有国家,三个维度是各有交集的。按照这三个维度,本书也分成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作者赵萱从村民的日常生活切入,发现当地人的第一认同并非阿拉伯或者穆斯林,而是自己属于哪个家族。以家族为中心的习俗在国家缺位的情况下,维护着他们的生活秩序。第二部分,作者又稍微把视角向上提升了一些,发现:宗教虽然在当地人的生活中无法绕开,但并不是总意味着冲突。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相互混杂,信徒之间其实给对方留有余地。第三部分,作者从更宏观的层面,看巴以冲突对他们生活的影响。
对生活在耶路撒冷这个巴以冲突最核心区域的居民,我们会想到一些标签,比如巴勒斯坦或者以色列的国籍,也有可能是阿拉伯或犹太民族,还是伊斯兰或者犹太教信徒。但是赵萱在东耶路撒冷发现,其实这些并不是当地人对自己的第一认同。对于他们来说,自己属于哪个家族,才是最基本的身份。我们要理解这一点,需要回到他们的生活当中去,或许你还会发现:他们的生活听起来有点耳熟,和中国的乡土社会有着相似之处。
赵萱当时住在一个叫橄榄山的地方,算是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圣地。对基督教来说,《圣经》中写到的耶稣事迹,很多都发生在这里。而对犹太教来说,这里也是他们的传统墓地。但是,橄榄山上超过九成的居民,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巴勒斯坦人,但是也有些来朝圣的外国基督教徒和阿拉伯基督徒。赵萱把自己所在的社区,按照当地人的习惯,称为“榄村”。榄村大约有两万多人,分布在橄榄山中部山峰周围。除了橄榄山西部的犹太墓地,其他区域都是密集的民居,街道狭窄迂回。当地人修的三四层小楼一栋栋紧挨在一起,按照市政规定来看,得有超过四分之一是违章建筑。榄村堪称是臭名昭著,据说是“东耶路撒冷最糟糕的地方”。传说中,那里毒品流行、道德堕落、暴力泛滥。赵萱的很多朋友听说他要去那里做研究,吓得要为他的安全祈祷。
和其他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一样,大部分橄榄山居民都住在东边,然后去西耶路撒冷的新城打工。男孩高中毕业之后,一般就直接工作了,年纪也才十七八岁,而同龄的女孩就得准备嫁人了。赵萱作为当地不常见的大龄未婚男子,起初被当作是一个危险人物,难以融入他们的生活中,很多家庭都拒绝租房给他。他不得不求一个叫贾米勒的咖啡馆老板帮忙,租住在咖啡馆楼顶天台上的违章小房间里。赵萱住下来以后,反而发现榄村虽然的确有不少社会问题,但并没有外界传说中的那么混乱。当地发达的家族组织成为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每个人都依靠族长们来主持正义。比如,赵萱迟迟租不到房,是当地家族对他存有戒心,反对成员租房给他。后来他结束研究的时候,他的房东还跟他说:路上谁欺负你,就说你是我们家族的。还有人跟他吹嘘,说警察也拿他们家族没办法。
为什么会是家族在维护秩序呢?有三层原因。
第一层,是因为家族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传统。很多家族都会有一份族谱,可以回溯到一千多年前的父系祖先。这里还可以说一个解读阿拉伯姓名的小知识。你可能发现,阿拉伯名字特别长,因为阿拉伯名字的组成,就是自己的名字加上父亲、祖父的名字,中间用“本”表示父子关系,有时还会加上曾祖父或者更高辈分长辈的名字,最后再写家族的名字。比如,沙特阿拉伯的王储,名字叫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勒沙特。穆罕默德是他的名字,萨勒曼是他的父亲,也就是现任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就是他的祖父,最后,阿勒沙特则代表他们是沙特家族。这个命名法就是阿拉伯人父系传承的一个体现。这种阿拉伯家族文化中,“重男轻女”的现象也很普遍,很多女性在高中就会辍学,被家里安排结婚生子,基本上是不参与家族的公共活动的。尽管伊斯兰教禁止近亲结婚,但是巴勒斯坦人依然保持着“内婚制”的传统,也就是婚姻一般发生在家族内部成员之间,防止家族财产外流。在结婚之后,一家的兄弟会借重大节日拜访自己的亲家,往往也就是自己的堂表亲家,强化族内关系。家族内部的传统习俗,维护了内部成员的共生。
第二层,就是因为当地巴勒斯坦家族能够维护秩序。前面我们说过,东耶路撒冷是一个边界地带,对巴勒斯坦人来说,以色列是一个占领者,他们并不愿意接受以色列,所以在很多巴勒斯坦人占大多数的社区,虽然以色列也会派驻警察,但是往往居民们不会配合,警察就很难开展工作。也就是说,巴勒斯坦管不到,以色列管不动。榄村不就没人管了吗?在这样的前提下,榄村村民通过家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治。家族会推选一个男性当终身制的族长,这个人必须有足够的资历,一般都是辈分比较高的人。但是最重要的是,族长必须服众,所以口碑和威望要求也很高,不是有钱或者有权就行的。比如,榄村最大的艾布浩瓦家族,有个开国际青旅的老板堪称是榄村最有名的人,但家族里有人觉得他天天接触乱七八糟的人,还有人说他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所以他就没有当上族长,反而选了小一辈的人。在榄村里,大到寻仇报复、暴力冲突,小到汽车受损、偷盗,都需要以族长为核心组织起来的家族,通过协商调解。很多时候,族长协商以后,纠纷都会以经济赔偿的形式解决,而不须法律介入或者暴力解决,全族还会分摊一定比例的罚金。这种非暴力的调解方式,在榄村里减少了暴力,使各个家族共生。
第三层,就是当地家族传统能够减少以色列的管理成本。巴勒斯坦家族和以色列政府的关系不是彻底互相排斥的,有时也会合作。我们再举两个例子,更好理解。第一个例子,是以色列政府控制冲突烈度,但是不干扰巴勒斯坦社会自己维护秩序。2011年,艾布浩瓦的一个已婚男子被另一个艾布厄纳姆家族指控强奸他们家族的未婚女子,两个家族发生了严重械斗。艾布浩瓦这边一个水果店被烧,艾布厄纳姆那边还有人因为枪械走火把自己给打死了。由于涉及枪械,以色列警察把村子封锁了4个小时,避免冲突影响周边,但是没有直接干涉,还是让两个家族协商解决。最后,两族商议,定性为男女婚外通奸,按伊斯兰教法应该对女性处以极刑。但是最后两族决定,由艾布浩瓦家族对走火打死自己的死者家庭和女方家庭进行经济补偿。也就是在巴勒斯坦社会内部解决矛盾,而不寻求以色列政府的法律介入。
在另一个例子中,榄村家族则主动向以色列警方求助。2013年,艾布浩瓦家族的一个小男孩被另一个家族的男子强奸,引起家族众怒,十几个青年袭击了对方家族的一户人。第二天晚上,几十个艾布浩瓦的青壮年聚集起来,准备发起总攻,把对方家族彻底赶出榄村。最后,艾布浩瓦的族长叫他们回家,说族长认为,强奸男童的案件性质极其恶劣,严重突破道德底线,不惩戒难平民愤。但是各族又应该以和为贵,不酿成更多的冲突。最后协商一致,把犯人移交给以色列国家司法。可以看到,也可能有性质恶劣到家族框架内拿不出和平解决方案,只好把烫手山芋交给以色列的情况。
你会发现,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社会关系很复杂。其实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的英国统治时期,巴勒斯坦的家族一度逐渐式微。但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色列政府扶持巴勒斯坦家族,让这些家族替自己来维护社区秩序,避免直接冲突。甚至有人告诉赵萱,包括艾布浩瓦族长在内的大家族族长,每个月都会从以色列政府领到一笔钱。2016年以后,以色列的市政府还用家族名来给榄村的土地写上路牌和标志,合法化各个家族的领地归属。此外,家族内也有以色列政府的“眼线”,向政府汇报情况。一言以蔽之,以色列政府为了避免冲突而放弃直接干涉,通过扶持巴勒斯坦的家族实现对当地的消极控制,维持社区的和谐。作者说,这也意味着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社会的共生。
我们总结一下。在赵萱看来,在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眼中,“你属于哪个家族”比“你是不是穆斯林”的问题更严重。因为生活的最基本单元就是家族,每个人都需要家族来做安全的担保者,同时当地巴勒斯坦家族文化也存在重男轻女、女孩早婚的问题。东耶路撒冷家族文化盛行的原因有三个,既是他们的历史传统,也是秩序的维护者,同时也是以色列着力扶持的自治组织。在家族框架中,家族成员、家族之间乃至外部的以色列政府与巴勒斯坦社会之间,虽然没有消灭冲突,但是实现了有限的共生。
好,我们刚刚了解了家族促进的共生。那么在接下来的第二部分,我们再来看看不同的宗教如何在东耶路撒冷共生。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据作者赵萱实地观察,宗教的多元在当地并不总是意味着对抗和冲突,也意味着供养和分享。在20世纪以前,耶路撒冷按不同宗教分为了四个区,但是如今,不同宗教混居在了一起。比如租给赵萱天台小房间的咖啡馆老板贾米勒,是一个穆斯林,但是贾米勒的店员阿卜杜拉,却是一个改信基督教的阿拉伯人。还比如拒绝赵萱租房的一个房东,曾经接受过从韩国来耶路撒冷朝圣的基督徒。
赵萱所住的橄榄山,正是一个信徒混杂的“圣地”。以前长满山坡的橄榄树,早已经被墓地和民居取代。整个橄榄山上除了一些旅游景点、住宿之类的第三产业以外,几乎没有什么经济产业。我们前面也说过,在山脚西边,是犹太教徒的传统墓园,总数超过十五万座,其中还有以色列前总理的坟墓,一些古代先知的陵墓据说也在其中。犹太教的墓碑和我们这边的不一样,平躺在地上,碑面朝向天空。而且根据犹太教先知预言,上帝会在世界末日时降临在橄榄山。在过往几十年的冲突中,橄榄山的人口仍在不断增加,生活空间的争夺愈发激烈。1967年之前,在约旦治下,很多墓碑被毁坏,用来修建基础设施。而以色列夺取东耶路撒冷之后,开始设置军警岗哨保卫墓园,并展开大规模的修复工作,甚至强拆民居,还原墓园。对犹太教来说,这里是死者的安息之所。而对于伊斯兰教来说,这里是生者居住的家园。墓园和民居此消彼长,有两个宗教的争夺,也是巴以冲突的象征。
别忘了,橄榄山上还有基督教。根据基督教的《圣经·新约》,耶稣曾经长期住在橄榄山,特别是在“最后的晚餐”之后,耶稣在橄榄山的果园里做了最后的祷告,犹大就是在这里背叛了耶稣。包括后来《圣经》上写的,耶稣复活四十天后,在门徒面前升天,也是在橄榄山。这座山对于基督教徒来说,在生死之间,是连接尘世与永生的地方,是很多信徒朝圣的目的地。虽然在橄榄山,只有不到1%的人口是基督徒,但是赵萱发现,他们在当地也有很重要的角色。
有一位来自挪威的修女,大概五十多岁,叫作西格莉德,就住在艾布浩瓦家族的土地上,给赵萱帮过不少忙。最初建议赵萱去找族长“拜码头”的正是她。西格莉德只身一人住在榄村,为附近街区的孩子缝补衣服、发放食物。每周二的下午,她还会为街区里的女孩们提供心理辅导,关心她们成长中的身心健康。就连艾布浩瓦的族长,也把她当成座上宾,为她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你可以说她是一个朝圣者,可作为“知心阿姨”的她,已经融入了巴勒斯坦社会最世俗的那一面。酗酒、吸毒、早婚、儿童教育等等问题才是她当下最关心的问题。
在贾米勒的咖啡馆里,有一位唯一的女性常客——耶路撒冷“上帝教会”的负责人塔玛拉。她是一名来自德国的传教士。“上帝教会”的主要活动区域不在东耶路撒冷,而是在约旦河西岸更远的地方。她只是来找她的好朋友,那位基督徒阿卜杜拉。塔玛拉负责的教会开办了一所对所有人开放的公益学校,每周六还会组织当地穆斯林家庭的孩子们一起做游戏。当地穆斯林居民也会在过节时,邀请对方一同聚餐,两个宗教之间逐渐增加了和解。塔玛拉一度想要邀请更多志愿者来巴勒斯坦,增强本地人对巴勒斯坦民族建国事业的信心。在某种程度上,她超越了宗教的樊篱。
不过,在橄榄山当地影响最大的基督教社团,不是塔玛拉的教会,而是一个叫“万国祷告院”的组织。他们相信上帝在末日时会降临在橄榄山,所以在橄榄山“守望”祷告。意思是:每个人轮班,保持每天24小时不间断祷告。祷告院每年都要举行一个盛大的万国祷告特会,倡议大家为建立“大同社会”而努力。在会上,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教徒聚集在一起,用自己的方法传达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愿望。2012年的一次,足足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人参与。会上,有日本基督徒为靖国神社“拜鬼”而忏悔,也有韩国牧师为日本牧师洗脚,以示谦卑与和解。一位参会的华裔基督徒对赵萱说:“灵里和好,现世的事情也会成就,战争就不会发生了。”
归根结底,圣地的价值,取决于人。在“十字军东征”背景的电影《天国王朝》当中,统领阿拉伯军队的萨拉丁攻破耶路撒冷,城内“十字军”问他,耶路撒冷有何价值?萨拉丁先回答“一文不值”,然后又回答“无价之宝”。所谓一文不值,是说耶路撒冷干旱炎热,土地荒芜,不宜居住。但他又说是“无价之宝”,正是因为耶路撒冷在宗教中有不可替代的神圣地位。在政教合一的古代社会,控制了耶路撒冷,就得到了万千信众。人类的信仰赋予圣地耶路撒冷价值,而耶路撒冷从未诱惑人类为它流血。西格莉德对赵萱说过,“在圣城生活的每一个人,都吃着用本地橄榄油烹制的食物”,这句话很像我们说的“共饮一江水”。很多宗教,最高的教诲都是和平友爱,抵制暴力。在这里,每逢伊斯兰教的斋月,还有犹太教的安息日,无论是什么教徒身份,只要是有需要的人,都会获得食物的施舍供养。斋月里的清真寺,每晚都会准备几千人份的大锅饭,穆斯林也会在家里准备给外人吃的饭,赵萱自己就领过七人份的鸡肉饭。安息日里,每个人都能在犹太圣地“哭墙”边分到甜点和食品,有些餐厅也会提供免费食物。一个经历过二战的九十岁老奶奶告诉赵萱,“供养不仅仅是食物,包括一切东西”。如作者所说,耶路撒冷除了虔诚的敬拜与神赐的供养,一无所有。我还要补充一句,正是因为曾经一无所有,更清楚分享的价值。
作者赵萱认为,撇开种种分离人们的边界,耶路撒冷的魅力在于团结,而不是争夺。比如,坐落在老城的圣墓教堂,是为了纪念耶稣受难的位置所建立的。真实历史中的萨拉丁在攻进耶路撒冷以后,为了避免有人破坏圣墓教堂,把大门钥匙交给信仰伊斯兰教的家族保管。一千多年来耶路撒冷反复易手,六个基督教派先后在这里建立教堂,但是圣地也一直遵照着原来的安排,没有被破坏。每天早上四点,掌管钥匙的侯赛尼家族代表先打开门锁,另一个叫努赛贝的阿拉伯家族推开第一道门,轮值的基督教会人员推开另一道门,其他的教派在一旁监督。晚上七点再按照相反的顺序关门,把钥匙交回侯赛尼家族。赵萱说,维护圣地的人们遵从的是历史使命,而不是民族或者国家的命令。正是国家政治的缺位,维持了圣地的活力。在赵萱看来,在今天的耶路撒冷,带来冲突的是政治,而非宗教本身。
当然,作为巴以问题的核心区,耶路撒冷的宗教不可能完全与政治切割开。比如在圣殿山上,是伊斯兰教的阿克萨清真寺,也叫“远寺”,相传就在被罗马人摧毁的犹太教第二圣殿位置上。而圣殿现在仅剩的遗址“哭墙”,在清真寺隔壁。远寺和“哭墙”本来是宗教场所,但是因为有深远的历史象征意义,往往也是政治活动的不二之选。比如,“哭墙”是犹太人的共同历史创伤,更是犹太民族国家的象征,很多纪念日都在这里举办。在“哭墙”另一边,阿克萨清真寺每年会举行阿拉伯土地日示威,抗争以色列占领。虽然以色列把每年一度的游行当成“减压阀”,放松整个老城的管控,以便巴勒斯坦人释放情绪。但是以色列会强化清真寺周边的军警戒备,强调自己对耶路撒冷的控制权,避免示威升级成暴力抗争。
总而言之,赵萱看到,不同的宗教在东耶路撒冷犬牙交错,但并不总是冲突的导火索。在家族之外,宗教对于贫困拮据的居民们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供养者”。我用一句话来总结:如今的耶路撒冷,宗教的分享发生在信徒互相之间,而宗教的对抗发生在政治中。
那么接下来的第三部分,我们也要直面东耶路撒冷政治现实下的日常生活。我选取书中的两个故事,来展示巴以双方的对抗如何渗透在当地人的生活中。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榄村山顶的一栋楼。这是整座榄村里唯一一座挂着以色列国旗的楼,还正好在势力最大的艾布浩瓦家族最中心的街区。整座村里,都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怎么会有人挂着以色列的国旗呢?这牵扯到一桩悬案。
在2006年的时候,这栋楼的主人是艾布浩瓦家族的穆罕默德三兄弟。有一天,有一个汽车销售商找到他们,开下七十万美元的高价,想买下穆罕默德的房产。销售商找来律师,背诵《古兰经》证明自己的穆斯林身份。对穆罕默德来说,这份天价也实在难以拒绝,很快就签了合同。不过奇怪的是,这笔巨款不但一次性付清了,这对生活一般不宽裕的巴勒斯坦人来说实在少见,而且装修的过程中,还在楼的外墙上加上了护栏和挡板。家族感觉事有蹊跷,怀疑可能是以色列政府在背后操作,于是要求穆罕默德取消交易。但是律师说,钱已经收了,不能取消了。又过了两个月,一帮以色列军警闯入大楼,出示房地产证件,表示这栋楼已经归以色列政府所有了,要求驱逐还没有搬走的穆罕默德三兄弟。穆罕默德这才知道,自己被以色列政府给骗了,自己的家园变成了犹太人定居点。他想反抗,但是为时已晚。只有一楼的母亲没有在合同上签字,才免于被驱逐。这栋楼就这么用欺骗的方式,合法地成为榄村第一座属于犹太人的住房,还挂着以色列国旗,每天村民是低头不见抬头见。
这个丑闻在榄村掀起了轩然大波,成为艾布浩瓦家族难以抹去的污点。没有多少人相信穆罕默德是被骗的,觉得他就是贪财,把土地出卖给了犹太人。他被赶出榄村,后来在新的家里被枪杀,身中七枪,汽车被烧、现金不翼而飞。艾布浩瓦家族展开调查以后,发现那个律师竟然是一个基督徒,穆罕默德的确是被骗了。家族虽然为穆罕默德报了案,但是以色列警察从来没有找到过杀人凶手。
如果不考虑巴以冲突的背景,土地只是财富的来源。而在修建隔离墙以后,很多巴勒斯坦人涌入东耶路撒冷,这样才方便去以色列打工赚钱,导致土地价格不断变高。巴勒斯坦家族之间,因为土地归属权发生的纠纷越来越多,经常需要协调。但是在地缘政治冲突的叙事中,以色列政府为土地赋予了“领土”的政治意义,甚至不惜用欺骗的方法,安插一座富有象征意义的独栋定居点。
第二个故事,也与隔离墙有关,主人公是一个叫亚金的村民。亚金的父亲和兄弟都是“以色列巴勒斯坦人”,也就是1967年以前就住在以色列,拥有以色列身份证的巴勒斯坦人。2012年时,亚金五十来岁,为人老实,信仰虔诚,每天做五次礼拜,周五一定要去阿克萨清真寺参加集体礼拜。每到节庆日,一定回约旦河西岸的祖籍老家拜访家族,在伊斯兰教和巴勒斯坦家族传统两方面都很守规矩,所以赵萱叫他“好人亚金”。好人亚金在以色列赚到过第一桶金,也因为以色列吃了苦头。
1990年,亚金一家在橄榄山脚下的村里买了一块地,开始在东耶路撒冷工作和生活。亚金从事木工活,他的门面在还没有修建隔离墙的时候,就在耶路撒冷老城和约旦河西岸城镇最短的公交线路旁边。那个时候公交环线出入东耶路撒冷都是很方便的,他的生意也很好,在耶路撒冷全市和西岸都有客户。有时客人就是修建定居点的犹太人,因为出价会更高,亚金也就不拒绝。
然而在2001年,以色列开始修建隔离墙,切断并控制巴勒斯坦到以色列的交通联系,断了亚金的财路。从一开始的一米矮墙,到现在两三层楼高的巨型隔离墙,亚金从用梯子翻墙,到老老实实开车绕十几公里,生意每况愈下。最后,他只能放弃开了25年的木工厂,裁掉了所有工人,变成了一个小作坊。他的孩子们也不能再像他一样干木工,而是选择去墙的另一边做装修工人、服务员、店员等等廉价的服务业职业。
赵萱看到,以色列修建的隔离墙,是巴以冲突下最突出的权力象征。比如前面讲的微观的家族,其实很多家族都横跨在隔离墙两边。又比如宗教,每天要进入阿克萨清真寺礼拜,就必须接受以色列军警的盘问,要背《古兰经》,证明自己是穆斯林。这个隔离墙限制了巴勒斯坦人的出入自由,也让他们变为事实上的二等公民。即便是那些拥有身份证的巴勒斯坦人,也无法抵抗。亚金在回顾自己的旧厂房时,对赵萱说:“这就是巴勒斯坦人的生活。”但是,在这块土地上,以色列经济离不开巴勒斯坦人,不得不依赖巴勒斯坦补充廉价劳动力。墙不在于封闭和隔离,而是控制巴勒斯坦人的流动。
最后总结一下,根据赵萱实地观察,虽然在巴以国家权力碰不到,或者不想碰的地方,家族和宗教能够维护社区的和谐,但在以色列政府的权力面前,这些都非常脆弱。一旦政治介入,来之不易的和平与连接是很容易被破坏的。
在我们的理解中,可能会认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认为耶路撒冷是自己的首都。按理来说,这里应该是冲突最核心的地方。但是赵萱看到,这里的现实更加复杂一些。
赵萱还讲了两个故事。有一个安息日,他在街上被一个老太太叫住,两个人因为语言不通,交流就靠用手比划。老太太拉他到犹太人居住区,给他茶喝,把他带到电闸开关前,示意让他拉电闸。原来,这个老太太是一个正统的犹太教徒,安息日不能开灯、点火。虽然有些电器有自动开闸,但是也有失灵的时候。老太太就只能找他这个看起来就是异教徒的人帮她一把。平时没有中国人,当然找的其实是巴勒斯坦的穆斯林。还有一个餐馆,虽然是给犹太人做符合犹太教法的“洁食”,清洁的洁,食品的食,但是店里十个员工都是穆斯林,只有一个拉比负责最后搅和一下。在赵萱看来,巴以社会就是这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按以色列的统计,以色列国内有20%的阿拉伯人,更有不计其数的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打工。完全切割,从来都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在地缘政治的冲突外,具体的人面对着具体的生活,总有比冲突更多的选项。我们开头说过,回到他们的生活本身,共生是可能的,实际上不仅是可能的,这还是一个脆弱的现实。就在脆弱之中,已经埋藏着和平的种子。
好,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也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地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
虽然在巴以国家权力碰不到,或者不想碰的地方,家族和宗教能够维护社区的和谐,但在以色列政府的权力面前,这些都非常脆弱。一旦政治介入,来之不易的和平与连接很容易被破坏。
-
回到他们的生活本身,共生是可能的,实际上不仅是可能的,还是一个脆弱的现实。就在脆弱之中,已经埋藏着和平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