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面目的人》 董鸿英解读
《没有面目的人》|董鸿英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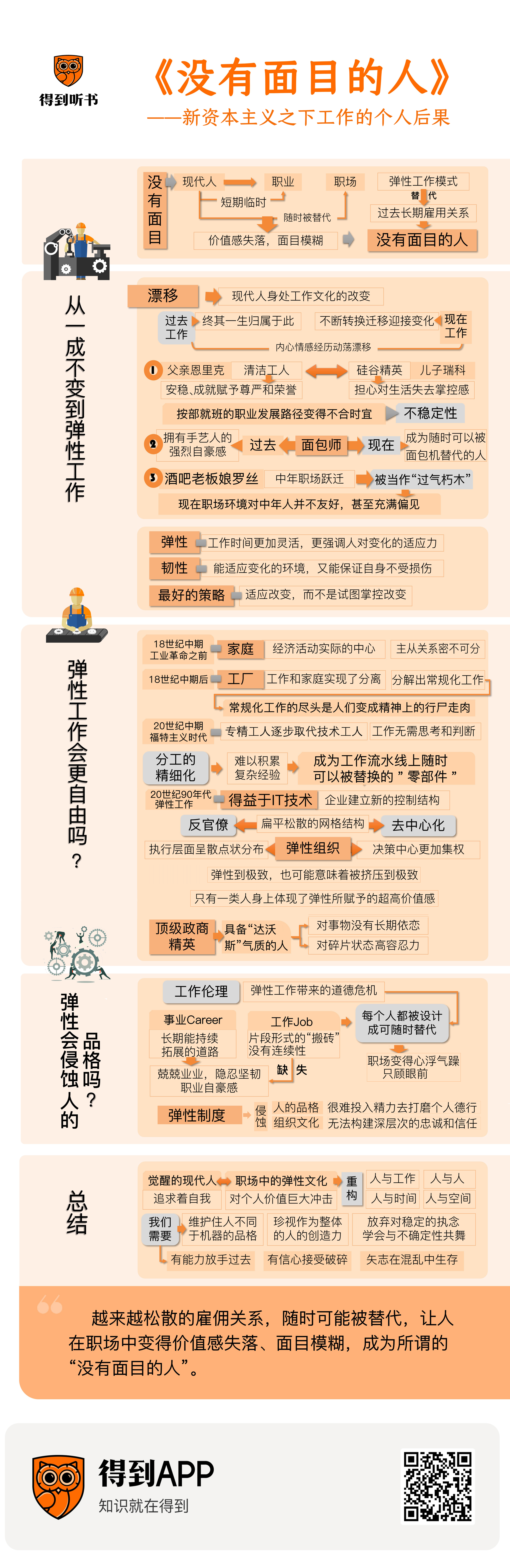
你好!欢迎你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带来的书是《没有面目的人》。听到这个书名,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不是很像一本小说?实际上,这是一本社会学著作,副标题叫做“新资本主义之下工作的个人后果”。“没有面目的人”指的就是人们身边的你我他,社会中万千的职场人。
“没有面目”这的确是一种文学化的表达,它形容的现象却很扎心。与过去相比,现代人所处的时代充满变化,他们与自己职业的关系有种短期和临时性,已经不像传统时代那样稳定。比如兼职、跳槽、裁员这些操作是现代职场中的常态,已少有人能一个饭碗端到老。这本书认为,职场正在以“弹性”工作的模式代替过去长期的雇佣关系,职场人则正在面对“用后即弃”,迅速被淘汰的可能。越来越松散的雇佣关系,随时可能被替代,让人在职场中变得价值感失落、面目模糊,成为书中所谓“没有面目的人”。
是不是听起来有种无力感,尤其是在当下,人们正谈论裁员潮、AI替代的时节。其实这是一本很有温度的书,在我看来,这本诞生于将近30年前的小书,是对“35岁危机”翔实的学术拆解。此书最早来源于一篇论文,发表于1996年的美国,跨越世纪,却能洞悉当下职场人的现实与困境。如此有先见性,这让读过它的人,感到不可思议。
联系上个世纪末的美国,正是新经济突飞猛进的时期,不仅是这本书,那时涌现出了一批趋势性著作,我们熟悉的比如《数字化生存》等。今天我们社会中的许多现象,其实在初代互联网时期的美国就已经显露了出来。那时美国人工作和生活方式的剧烈变化,就引起了一些触觉敏锐的学者的关注。本书的作者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就是其中代表。
桑内特在英美两国多所名校有任教经历,是当代顶尖的公共知识分子,被誉为与阿伦特、哈贝马斯齐名的公共生活研究者。他写的书中文译名都很有深意,像是《眼睛的良心》《肉体与石头》《阶级中隐藏的伤害》等。桑内特研究的领域有种开放性,比如城市、家庭、观念史、身体史等,总是在关注社会变迁中“人”的位置,尤其是职场中人的处境。他曾获黑格尔奖、斯宾诺莎奖,这本《没有面目的人》曾入选美国《商业周刊》年度最佳作品。
这本书体现了桑内特与众不同的写作风格。它既像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论著,又像是一份作家的访谈手记,还穿插着文学的思考,旁征博引、细腻深沉。乍一看,书挺薄,但实际上内容之丰厚,简约而不简单。它本质上讨论的是,现代社会随着生产力的革新,人与工作、人与人、人与时间之间关系的变化,以及与之相关人的品格、伦理等一系列的改变。这本书为什么能预见30年,说出当下人们的职场痛点。要知道,作者为此梳理了200多年,从启蒙思想家狄德罗、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观察到雇佣模式的变化,到后来福特汽车的模范工厂,再到IBM公司迫不得已的组织变革,当代人的遭遇只不过是工业革命以来劳动分工方式变化的一小段延伸而已。
你能看清过去,也就能看懂当前。接下来,我就和你具体地聊聊这本关于职场的趋势之作。我从书中选择三个词来和你分享,分别是“漂移”“弹性”和“工作伦理”:
第一个词,漂移:从一成不变到弹性工作。
第二个词,弹性:弹性工作会让人更自由吗?
第三个词,工作伦理:为什么作者认为,弹性工作会侵蚀人的品格?
我们先来说说第一个词“漂移”。作者用这个词来形容现代社会人们身处的工作文化的改变。过去的工作,是人脚下一块踏实的大陆,人们可以终其一生归属于此;而现在,人们需要不断地转换迁移,迎接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内心情感也在经历动荡、漂移。作者就像一位时代的记录者,用几位美国人的故事来描绘这种变化。
第一段故事的主角,是恩里克和瑞科父子。恩里克是父亲,从作者25年前采访他时,就一直从事着清洁工的工作。作者第一次认识恩里克是在1970年,那时恩里克40岁,在波士顿市中心的写字楼里做清扫厕所的工作。那时候他从事这行就已有二十年之久,并且也已清晰地知道自己的退休时间和退休金的数目。恩里克的人生故事一目了然,时间在他的生活中呈现出直线性,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恩里克所做的,就是出卖自己的劳动时间,他所换得的所有回报也都是在时间的延续中积累的。这份工作尽管地位不高,但让他养家糊口,在波士顿郊区买下了还算体面的房子,培养两个儿子上大学,令恩里克对自己的人生有掌控感。他的家和花园打理得井井有条,他每周都回到意大利熟人社区做礼拜、喝咖啡,生活过得风平浪静、有迹可循。这一切的安稳和成就,赋予了这位清洁工尊严和荣誉。
瑞科是恩里克的儿子,大学毕业后成为硅谷精英,薪资攀升到了全社会前5%的位置,向上跨越了阶层,是“美国梦”的代表。作者在机场偶遇了瑞科,瑞科身上穿的西装,已经超过了作者的购买力,手上戴的戒指,上面刻的图章代表着上流家庭背景。这枚戒指,就像是瑞科对自己出身阶层的背叛,他的父亲其实是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他完全摈弃了父亲恩里克的生活方式,职业生涯充满了变化、风险和挑战。他先是投身西海岸的科技热土,在风险投资公司担任技术顾问,在那里事业做得风生水起;然后又到芝加哥发展,也混出些名堂;后来为支持妻子的会计师事业,转去了美国中西部的密苏里州,在那里他所在的公司被并购,瑞科遭遇了裁员;最后他又回到了东海岸的纽约,创办了一家小型咨询公司。14年间,他和妻子搬了四次家。
尽管瑞科和妻子都很优秀,发展势头强劲,但双方都经常担心对生活失去掌控感,这种恐惧随着年龄的增长、经济形势的变化在不断发酵。由于工作变动,在不同的城市间迁徙,他们很难加入社区网络,不能与周围的人形成稳定的社会交往。他们生活的社区多是开发商新建的,居民缺少像父辈那样熟得不能再熟的邻里关系,没有谁能够长期见证另一个人的生活。恩里克和瑞科这两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内心状态,已发生了剧烈的改变。
作者写到,1990年代的美国,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在职场中可能会换11次工作。按部就班的职业发展路径变得不合时宜,只守住一份工作、一项技能的时代已经过去。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等企业开始推广“短期聘任”的新模式,“工作职务”被“项目”或“工作范畴”所取代,劳动力随之向更短周期、更加零散的合同制方向转变。与新经济的瞬息万变、周期起伏相对应的,是现世安稳和岁月静好不再,而“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成为常态。瑞科是个集成功和迷惘于一身的人,他在职业生涯中曾风光无限,也曾被结构性裁员。当风向一转,技能“不再被需要”时,这种残酷,从公司到员工都在劫难逃。瑞科是时代中的一个样本,从他身上折射出了更多个体的努力和挣扎。
接着我再和你聊聊书中的第二段故事,关于一家位于波士顿的面包店里的面包师。在作者1970年第一次采访这里时,这个店里的面包师大多是希腊裔的美国移民,共同的身份背景让他们自觉团结为一体。这个群体中流传着希腊族裔的工作伦理,比如只有勤劳苦干才是好的希腊人。谁要是被说“不是好的希腊人”,这句评价的羞辱性就极大。这种朴素的文化很有威慑力,能引导面包师遵守工作纪律。面包烘焙的工作并不轻松,不仅要求有好的体力,还需要训练多年才能技艺纯熟。面包师双手起起落落间像芭蕾舞一般地运动,靠鼻子、眼睛和手的经验来把握火候,他们拥有“手艺人”的强烈自豪感。那时,这个群体拥有自己的工会,让人感叹面包师的世界也条理清晰。但当1995年,作者再次回到这家面包店时,变化之大如若隔世。
这里的希腊师傅都已退休,顶替他们的是自动化的面包机,以及操作机器的年轻人。这群年轻人多是意大利籍的,也有白人新教徒、越南人,以及其他几个看不出种族身份的人。他们之间没有多年前希腊裔面包师们共通的职业文化,就连他们上下班的时间,也是相互交错开的,都很少打上照面。因为他们中不少是临时的兼职,工作时间是弹性的。更让作者惊奇的是,这些人已不再和原料及面包有任何直接的接触。他们通过屏幕上的图标来操作整个制作过程,搅拌、发酵和烘烤的时间和温度等参数,都是通过数据生成的。他们的双手并没有和面粉打交道的经验,实战知识一片空白。当电脑失误,烤坏一箱面包时,店员则把这批次品倒掉,重新设定电脑程序再来一遍;当机器故障时,店员则打电话坐等维修人员上门。员工只需经过培训就可以成为那个“摁下面包机开关的人”。
面包机让这里的员工对于“面包师”这一身份失去了认同感。他们也自认自己算不得真正的面包师。面包店只需要店员在已经设计好的Windows界面上敲击按钮。与其说懂得如何烤面包,不如说懂得如何操作电脑的技能在应聘时更重要。只要会用电脑,员工似乎可以站上各种不同的流水线。一位女店员开玩笑说:“烘焙、制鞋、印刷,你说什么技能,我就有什么技能。”但随之而来另一个冷酷的现实就是,员工和他们的工作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薄弱,他们的技能没有壁垒,对于工作的理解流于表面,成了随时可以被替代的人。
书中还有第三段故事,同样意味深长,这次出场的主人公是鳟鱼酒吧的老板娘罗丝。鳟鱼酒吧是作者在纽约常呆的休闲去处。与那些善于搞营销,能聚集城中时尚红人的酒吧不同,鳟鱼酒吧一直安安静静地吸引着一批老顾客,生意也不错,总是座无虚席。罗丝是个精明泼辣的老板娘,鳟鱼酒吧这一方小天地似乎还不能满足她的事业心,她不想只是为附近失业的演员、疲倦的作家、落魄的商人端茶送水。在两个女儿长大成人后,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离开酒吧,转身加入了一家广告公司。中年时的这次职场跃迁,带给罗丝的体验是刻骨铭心的,甚至可以说是苦涩的。事实上,她与纽约光鲜靓丽的广告行业格格不入,内心疲惫不堪。
她应聘的岗位是要重振这家公司烈酒的销售量,她以自己经营酒吧的经验为筹码,赌上一把来闯荡新行业。这家公司的办公室位于纽约上城区的公园大道,为了融入这里俊男靓女的职场形象,罗丝花钱请人帮自己置办行头,还把自己的巨型方框眼镜换成了隐形眼镜,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漂亮。但她一时间改变不了自己说话的口音和见识。当同事谈论这个“低卡”那个“轻食”的时候,她感觉自己就像博物馆里展出的文物——一个酒吧老女郎。同事从不邀请她下班后去酒吧喝一杯,而那些消息灵通的地方才是广告行业真正的战场。罗丝发现她这样的中年人在这里被当作“过气朽木”。在别人眼里,过去积累的人生经验可谓百无一用。这种否定以及人际内耗,让罗丝逐渐失去了勇气。一年后,她辞去工作,回到了鳟鱼酒吧。
罗丝的这次人生冒险以失败告终,她感到现在的职场环境对中年人并不友好,甚至充满偏见。当人过往的经验价值不被认可,雇主会越来越偏好年轻人。作者给出了一组数据,1990年代,职场中人们工作的年限已经在缩短,年长的员工比过去更早地退出了职场。这带给年轻一代流动和上升的机会,但中国话讲“长江后浪推前浪”,没有人会永远年轻,但永远有人年轻,强调变化、崇尚年轻,也就会同时强调过气,这也引发了现代人普遍的焦虚和迷惘。
好,刚才我讲的这三个故事,体现了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作者观察到美国人工作模式的变迁,人们从一成不变到弹性工作。作者使用的“弹性”这个词,跟我们现在经常说的“弹性工作制”,并不完全一样。除了工作时间更灵活以外,它更强调人对变化的适应力。或者我们借用另一个词“韧性”来体会一下:能适应变化的环境,且又能保证自身不受损伤。就像大风吹拂的竹子,弯而不折。对于“弹性”而言,更好的策略,是适应改变,而不是试图掌控改变。当今社会正在想方设法地创建更有弹性的机构,以适应变化。这也将时代中的人推向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实际上,这并不是职场人第一次经历工作模式的大变迁,在历史上,雇佣方式就一直在演变。接下来,我就带你揭开“弹性工作”背后更多的故事。
在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之前,家庭一直是经济活动实际的中心。比如,在巴黎、伦敦这样的大城市,面包师的住所中,你会看到学徒、工人以及面包师自己的一大家子人。雇员和主人吃住在一起,他们的衣食开销都是制作面包成本的一部分。主人在工资之外还提供住所和庇护,主从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
而18世纪中期之后,在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出版的《百科全书》中,用版画展示的一家实际存在的造纸厂刷新了人们的认知。这家名为安格雷的工厂空间布局精致优美,不像是一家工厂,倒像是一座拥有贵族庭院的法式庄园。安格雷工厂展现了一种新的工作秩序:那就是工厂并不为工人提供住处,工作和家庭实现了分离。与以往造纸厂恶臭熏天、混乱不堪的工作环境相比,安格雷显得井然有序、一尘不染。这种新型工业秩序的奥秘就在于精确的“常规化工作”。这里的每样东西都有指定的位置,每个工人都明确知道自己的任务。造纸的流程不断优化,分给工人不同的活儿,工人重复地操作某个特定的生产环节,直到得心应手、心手合一的境界。这就是工业时代分解出来的“常规化工作”,工人只要学会,并把控节奏,就能获得对工作的掌控力。安格雷工厂的画面中,工人的表情特别引人注目,无论手中的工作多么艰巨,他们始终一脸平静、处变不惊。
在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的《国富论》中,也说明了常规性工作的进步意义。斯密选用了一家扣针工厂作为案例,这个案例你可能也听说过。根据斯密的计算,如果一个工匠自己完成所有环节,每天他最多只能生产20枚扣针,但若是将制作工序进行分解,每个工人只完成其中一个步骤,那么平均一个工匠每天可以产出的扣针数量则达到了4800枚。这个事实说明了劳动分工的威力。
这是《国富论》中,我们熟悉的内容。其实,斯密在书里还表达了一种悲悯,这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从另一种人道的角度来看,生产一枚扣针,有18道工序,抽铁丝、拉直、裁切或是打磨……每个工人从早到晚、日复一日都只做其中的一件事,会完全麻木了。斯密也意识到,对于工人来说,常规化工作的尽头就是死路一条,人们将变成精神上的行尸走肉。斯密在《国富论》中写下了这样一段,堪称全书最残酷的段落之一:
“分工的进步使大多数劳动者的工作被局限在了少数甚至一两个简单的操作上。……如果一个人一生都在进行少数相同的简单操作……慢慢地将变成一个愚钝无知的人。”
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工人出卖的劳动时间,是“商品化时间”,这回报中或许就包括需要在工作中忍受的无聊。
到了20世纪,在福特主义的时代,劳动分工演进出新的典范。福特之前的汽车行业,很依赖技术工人,他们能进行复杂的操作,往往配有助手,享有高度的自主权,能自行决定招收和解聘助手。而到了福特的高地公园工厂时代,专精工人开始逐步取代技术工人。专精工人属于微型操作,无需思考和判断,比技术工人便宜许多。他们可能并不理解汽车运行的机械原理,而是依靠复杂的自动化机器来辅助工作。和前面讲的不会做面包的面包师一样,他们会操作机器就行。他们越是不能理解整体,就越是只能高效地专注于本职工作,从而更能成为庞大生产体系中合格的“螺丝钉”。
后来的企业效法福特模式,规模更为宏大,组织更为复杂,也将常规化工作的压抑推向了极致。比如通用汽车的柳树大道工厂,这里森严的等级制度,以及对工人时间的度量,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比如将1小时分为10个时段,每段6分钟,以工作时段来计量工资的话,这里是以6分钟为单位,非常之细碎。无论是办公室的白领还是流水线上的工人,他们的晋升和福利都受到这样琐碎的考核标准的牵制。
从亚当·斯密的扣针厂,到福特的高地公园,再到通用的柳树大道工厂,浮现出了一条共通的线索。这一点很要命,那就是所有这些场景中,常规化工作都在让人退化,让人的创造性发生降格。这些工作在改变着人的思维模式,培养出职场中的“顺民”。一些人在常规化工作中被成功驯化了,但职场危机也不言自明,分工的精细化,使人难以积累复杂的经验,从而成为工作流水线上随时可以被替换的“零部件”。
那么舍弃这种例行公事的劳动,人们是否就能在职场中找回价值感呢?弹性工作是否就意味着人们可以重获自由了呢?答案依然是否定的。作者指出,得益于IT技术的弹性组织,是扁平而松散的网络结构,它反官僚,去中心化,但它导致一种矛盾的现象出现了,那就是执行层面呈散点状分布,但决策中枢更加集权了。就拿我们最熟悉的外卖、网约车等灵活就业平台来说,劳动者更像是统一规则驱动下的数字化劳工。说到这里,“得到”听书曾为你解读过《后工作时代》,与今天这本书同一系列,里面提出的一个概念——人工智能时代的“微工作”,也像是平台经济时代的“打零工”。弹性到极致,也可能意味着被挤压到极致。
实际上,弹性并没有创造出让人们自由的条件,弹性工作制度是把员工编入一种新的管理结构之中。我们都尝试过在家远程办公,上世纪末的美国也有不少公司居家办公,雇主会担心对不在场的员工失去控制,最终结果是出台一系列新的管控手段,比如网络签到、后台任务追踪等等,来防止员工滥用自由。一些加入弹性工作环境的人很快就发现,他们不过是从一种权力的监视转移到另一种,从面对面的臣服转化为“电子化”的臣服。
作者倒是在一类人身上看到了弹性所赋予的超高价值感,那就是当他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时,所观察到的那些顶级政商精英。以最具达沃斯人特质的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为例,他有两项个人品质使他在弹性新经济中如鱼得水。第一,他对事物没有长期的依恋,他曾说,要把自己置于一个充满可能性的网络中,而不是把自身锁定在某个事物中。第二,那就是对于碎片状态的容忍能力。盖茨这样的人,没有对线性时间的执念,因此,他们有信心在混乱中生存,在时间脱节时仍蓬勃发展。企业的变革有时是非连续性的,不能理解和适应这种破碎感的人,将被淘汰出局。
在一个咖啡馆里,作者曾遇到许多被解雇的IBM员工,看到了企业变革的另一面。上世纪80年代开始,曾如日中天的IBM失去了对个人电脑市场的控制权。90年代的IBM动荡不安,开启了裁员潮。很多人离开多年后,被解雇的伤口仍隐隐作痛,他们聚集在这家叫河风咖啡馆的地方,一遍遍地讨论着他们的不幸。从公司对他们的“背叛”,到印度程序员抢夺了他们的饭碗,最后到他们到底该做些什么来应对科技行业的飞速发展。如果让达沃斯论坛的成功人士来看看河风咖啡馆里这些“不幸者”的讨论记录,他们又会作何评论呢?
弹性工作模式意味着生存环境的新变化。没有企业可以提供永久的庇护,它们自身都在经历挑战和磨难。尤其在美国这样奉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体中,变革和增长即代表正义,即使是弱者要为此付出代价。职场人一旦了解现代职场的本质,就知道在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没有救世主,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负责。
好,刚才,我们从对历史的回看中,试图去理解今天我们所生活的时代。跟随作者一起思考劳动为什么变得那么容易被替代,经验为什么失去价值,弹性工作为什么并不能让人更自由。接下来,我将和你聊到这本书里另一个重要的论题,那就是关于“工作伦理”,弹性工作正在给人们带来的道德危机。
这本书英文原名是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直译过来应该是“品格的腐蚀”。“品格”是我们与世界的联系,我们也正因此而被别人需要。现在的中文书名《没有面目的人》用的是意译,它体现的就是现代人个人品格与价值失落、不被他人看重和认可的状态。
作者一开篇,就专门解释了几个英文单词。第一个是“事业”的单词career,本意是指马车行驶的轨道,这很形象地表示了“事业”应该是一条长长的、能持续拓展的道路。第二个是“工作”的单词job,job原指可以四处运送的一块物品。job这个词倒是非常贴合当今的弹性制度,因为人们都在以片段的形式工作,不再有连续性,现在职场人戏称为“搬砖”。“事业”和“工作”的区别,对于职场人品格的塑造,可以说是大为不同。你想,从事“事业”的人,那种兢兢业业、隐忍、坚韧,以及职业自豪感,是打零工心态的人所欠缺的。
在农耕和工业时代,工作中的道德伦理是非常郑重其事的,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手艺和信仰。勤劳、自律、忠诚这些美德被世代传颂。就算是在资本主义的早期,就像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说,清教徒也在努力通过工作来荣耀上帝,证明自己的价值。但是在弹性制度下,当工作与人的长期发展脱钩,那些传统美德就变得十分空洞了。讲究个人德行、追求工作的意义,不断提高技艺并成为不可替代的行家里手,这好像成了过去的传说。在心浮气躁、只顾眼前的社会中,人们很难投入精力去打磨自我的品格。每个人都被设计成可以随时被替代的,“谁需要我”都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作者认为,弹性制度正在侵蚀人的品格以及组织的文化。因为深层次的忠诚和信任需要时间去构建,当人和组织之间不再有长期稳定的关系,那两者就难有信任感可言。缺乏情感的纽带,职场人也失去了对雇主的托付感和归属感。人们在一个接一个地完成项目,团队成员来了又走、不断变动,少了人情的组织散发出冷漠的味道。年轻的一代对这样的职场往往无力去爱,有人告诉自己:保持超然的态度,流于表面,甚至是表演出来的合作精神才是更好的自我保护。由于害怕被伤害,还有人对自己说:别做承诺,不要牺牲自我。
短期雇佣所营造的弹性文化,或许我们无法全面估量它的杀伤力。这本书中第一个故事的主人公,那个靠努力挤进了美国精英阶层的瑞科,让他深感忧虑的是,他的下一代已无从了解什么是“忠诚”和“承诺”,因为孩子已看不到他们的父母在以实际行动履行这些品格。虽然瑞科并不认同他那做了一辈子清洁工的父亲,但是父辈往往可以用工作中具体而细微的比喻,来说明品德的问题。比如“你可以忽略灰尘,但它不会就此消失”。这些智慧之语很朴素、踏实,瑞科却不确定自己是否也能从他的工作经验中,撷取一些道理说给孩子听。
好,今天这本《没有面目的人》就和你聊到这里,我们小结一下。
这本书就像是30年前,为今天的职场人写下的启示书。觉醒的现代人,追求着自我,但职场中的弹性文化,对个人价值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不仅工作在碎片化,时间在碎片化,实际上人和世界都在碎片化。现代人的自我被小说家萨尔曼·拉什迪形容为“是一栋摇摇欲坠的摩天大厦”,人们用各种信息碎片和生活经验把它拼贴出来。人已经很难获得整体连贯的生活叙事,人们需要更强的适应力,去融入这个各种元素不断转换的世界。这就是我们面对的后现代生活。
弹性工作文化,重构了人与工作、人与人、人与时间,乃至人与空间的关系。它重构人与工作的关系,比如短期雇佣代替了长期和终身雇佣;它重构人与人的关系,人们之间不再有稳定的信任和承诺;它重构人与空间的关系,人们因为工作频繁地迁移,成为新的游牧民。在这场工作文化的历史变迁中,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书写个人的历史。作者书中所列举的各色人物,实际上代表着社会中不同的阶层:蓝领恩里克、白领精英瑞科,个体经营者罗丝,IBM大厂前雇员,还有金字塔尖的弄潮儿,比尔·盖茨们。
时代更迭中,“弹性”工作方式让很多人与职场变故不期而遇。批量裁员、机器替代、35岁危机,这些现象在上世纪末的美国也已上演。今天,它们不过是在又一个经济周期中来得更猛烈了一些。在“用后即弃”的职场中,面对随时被淘汰的可能,人又该如何找回对工作的掌控感,获得自我身份的认同感和价值感?这是直击现代人灵魂的问题。
从这本书的历史讨论中,我们不难看到,劳动的精细化分工一直在迫使人“退化”,从手艺人降格为机器的附庸,这让人的可替代性不断升高。抵抗这一切,或许需要我们维护住人不同于机器的品格,珍视自身作为整体的人的创造力,放弃对连贯性和稳定的执念,学会与不确定性共舞。就像那些在新经济中如鱼得水的人所具有的品格特征:
有能力放手过去,有信心接受破碎,矢志在混乱中生存。
好,今天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里。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分享”按钮,把这个音频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1、所谓“弹性工作”,除了工作时间更灵活以外,它更强调人对变化的适应力。
2、对于“弹性”而言,更好的策略,是适应改变,而不是试图掌控改变。
3、职场人一旦了解现代职场的本质,就知道在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没有救世主,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负责。
4、有能力放手过去,有信心接受破碎,矢志在混乱中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