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不是唠叨,只是受够了》 王朝解读
《她们不是唠叨,只是受够了》| 王朝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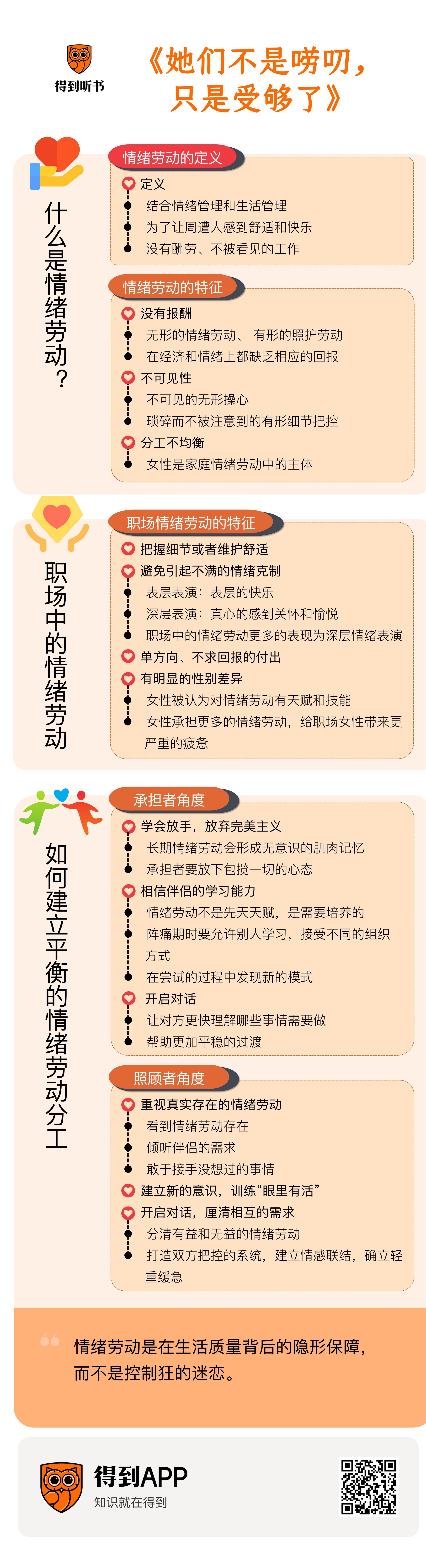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
今天这本书的标题是《她们不是唠叨,只是受够了》,这个“她们”是一个女字旁的她。
有个词叫“婆婆妈妈”,用了两个女性亲属的名词,形容一个人处事优柔寡断、在意细枝末节,可能还有点啰嗦。也许很多人小时候都有过类似的经历,自己才刚进门,就被责备说:回家脱下来的鞋子怎么没有放好?我自己就老被女朋友提醒,洗完碗记得放回消毒柜里,不要就这么堆在水池旁边。很多人就会有这么一个感觉,好像女性就是更会唠叨、更爱操心。
这本书为此提出了一个新解释,她们不是唠叨,而是受够了。受够什么了呢?作者提出了一个词,叫“情绪劳动”。简单地说,就是对生活的关怀。有句话“你必须非常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这个背后的非常努力很可能就是情绪劳动,只不过是在维持无处不见的日常生活。举个例子,倒垃圾是一种具体劳动,而注意到什么时候要去倒垃圾,就是一种隐形的情绪劳动。麻烦的是,生活中的这种劳动往往是没有酬劳、不被看见的。很多女士肯定有这种体验,某一天情绪爆发的时候,不是真的因为那双鞋没放回去,而是因为已经为了让周边的一切看起来毫不费力,已经努力了太久了。
本书作者杰玛·哈特莉是个美国记者,2017年为《时尚芭莎》写了一篇爆款网文,标题和本书一样,当时引起了很多共鸣,获得了上百万的转发,文中讨论的“情绪劳动”这个词直接变成欧美热词,连BBC都在讨论。哈特莉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又采访了上百名女性,并且加入和自己的丈夫调整关系的经历,最终写成本书。在这本书里,她不但展示了看不见的情绪劳动多么重要,还通过她与丈夫的真实经验,讲述了如何平衡情绪劳动,让每个人的生活都更充实、和谐。
接下来,我把本书分为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到底什么是情绪劳动,在家庭生活之中是怎么样体现的;第二部分我们会在更广泛的场景中看到职场和社会中的情绪劳动,并进一步理解分工的不均衡;第三部分,就要结合实际,谈谈如何建立更加平衡的情绪劳动分工。
刚才简单介绍过情绪劳动,其实很多照护类的相关名词都可以概括为情绪劳动,诸如情绪工作、精神负担、家庭管理、事务劳动等等。这种劳动就是让生活变得舒适、快乐的一种付出,是为了整个系统顺利运转而给轮子上油的工作。换句话说,要维持生活看起来井然有序,并让在其中的人感到更舒适,依靠的就是隐形的情绪劳动。但是情绪劳动的承担者只有一方,就会感到压力不断累积,被照顾的人则会感觉总是要听别人的安排,这种失衡的分工对双方都不太好。用作者的定义来说,情绪劳动是“结合情绪管理和生活管理,是我们为了让周遭人感到舒适和快乐所做的没有酬劳、不被看见的工作”。
听起来有点抽象,我们听听哈特莉的经历,更好理解。哈特莉那篇成名作,其实就是她一次情绪崩溃后有感而发。当时快到母亲节了,哈特莉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要过节了,就向丈夫罗伯特提出,自己想要的礼物是房屋保洁服务,特别是清扫浴室和地板,如果价格合适还要洗洗窗户。罗伯特却不是很乐意,希望哈特莉能改变主意,换成一个更简单的礼品,最好是那种一键下单就能网购来的礼物。哈特莉一口咬定就要这个,一直到母亲节前一天她老公才接受现实,终于开始打电话问价格。一听报价,罗伯特就说太贵了,自己能干的事情,还要花钱让别人来干吗?他们家恰好是老婆管账,罗伯特就跟哈特莉说,这有多不便宜,是不是真的想要这个?但哈特莉需要叫保洁,不仅仅是为了打扫,也是为了让自己不要再为家里的整洁操心。当时哈特莉刚成为自由职业者,工作时间变多了,家务时间变少了,自己也觉得有点内疚。更重要的原因是,她知道“叫保洁”其实没那么简单,不是滑滑手机就行,还需要问问朋友的推荐、联系几家公司比价,由老公来做这些事前准备,对她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礼物。
结果到了母亲节那天,哈特莉还真收到了两个“惊喜”:一条项链,还有一个钻进浴室清理的老公。不过,他们家还有三个孩子,所以哈特莉得自己一个人照顾三个孩子。当老公整理好浴室之后,哈特莉正好经过浴室,但她忙着收拾被老公扔在外面地上的鞋子、衣服、袜子,没有注意到浴室,罗伯特还有点失望。而压倒哈特莉情绪的最后一根稻草,正在旁边的衣帽间里埋伏着:她一进衣帽间,就被地上的大箱子给绊倒了。几天前罗伯特为了准备给礼物包装,把这个箱子从架子上搬下来,拿了里面的礼品袋和包装纸,然后就忘了放回去。箱子就这么搁在地板上。每次要收脏衣服,或者挑穿的衣服,就得把地板上的箱子踢到一边让开路,哈特莉看着就气不打一处来。但是对她来说,她还要去厨房搬个椅子,站上去,塞到原来的高架子上,而罗伯特足够高,只要把箱子举起来就行。想到这,哈特莉肯定是更生气了。
看到哈特莉生气,罗伯特也很困惑,他觉得哈特莉只要开口叫他把箱子放回去不就行了。听到这句,哈特莉终于崩溃了,她流着眼泪说,“这正是症结所在,我不希望这种事还要我开口要求。”
或许在罗伯特看来,自己不但准备了贵重的项链,还满足老婆对干净浴室的需求,应该是个好老公,结果老婆没有夸浴室打扫得干净,还要怪他没有主动搬箱子,是有点委屈。而对哈特莉来说,这个箱子明明就很碍事,对罗伯特来说就是举手之劳的事情,好几天都没做,最后还要怪她没有主动要求,难道她不问,这个箱子就不是麻烦,不需要解决吗?更何况,他只打扫了浴室,却没有照顾家里的其他家务,最开始哈特莉要求的地板、窗户都没有。哈特莉是一点就着的怨妇吗?其实不是,她只是受够了。我们看这个故事,回顾一下情绪劳动的两大特征:没有报酬、不被看见,重新理解在这次崩溃经历背后的情绪劳动。
回到争执的开头,哈特莉为什么想要家政服务?就是她想用别人的有报酬的服务,代替自己没有报酬的付出。甚至连找家政这个过程,也包含了无偿付出,所以同样是一种礼物。我们从这个想法开始,讲讲情绪劳动的无报酬性,就是提供情绪价值的情绪劳动,却收不到相应回报。说情绪劳动,我们从同样作为照护工作,但是更加有形的家务开始,家务到底是不是一种劳动,很少有人会怀疑,每天扫地拖地,腰酸背痛的,当然是劳动。但如果问家务劳动有没有经济报酬,就有人会提出疑问了。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日本著名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有非常独到的分析,她用“无薪劳动”来定义家务劳动。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家务劳动没有价值,为什么会有要收钱的家政服务公司?明明是同样的活,哈特莉每天干,不拿钱,别人来干一天,就贵得老公不想出钱,这更说明平时的家务其实价值不菲。用上野千鹤子的话来说,这种劳动与那种和物品的生产和流通相关的有薪劳动不同,并没有体现在市场内,而是在市场外围的家庭当中,孕育生命、照顾生命、为生命送终等等都是无薪劳动,是一种再生产性劳动。“再生产”听起来比较抽象,其实就是说,做饭、打扫卫生等等家务活儿,确保在疲惫的劳动生产之后,回到家里可以放松身心、恢复精力,这就是劳动力的再生产,这种照顾对于社会运转和经济生产都是必不可少的。
哈特莉主张,在有形的照护劳动之外,无形的情绪劳动也是再生产的一部分,除了统筹和安排家务,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还要注意照顾家人情绪,提供抚慰、夸奖等等,比如当老公打扫完浴室的时候记得夸他,还有他被裁员的时候让他多讲讲心里的苦闷,要安慰他不要太难过。这个环节没有身体劳动,对于家庭成员来说却可能比一桌好菜更能令人感到满足。但现在流行的家庭分工之中,双方付出比例很不平衡。比如说,在老公打扫浴室的时候,哈特莉照顾了孩子,还收拾了衣服,但她的老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当时应该夸她,反而对她没有夸自己感到失望。也就是说,负责情绪劳动的人提供了“情绪价值”,保证了经济价值的持续生产,但在经济和情绪上都缺乏相应的回报。
好,我们再来看看什么是不可见性。不可见性也包括两方面,一个是“眼里有活儿”的持续操心,还有一个是干活儿的时候对细节的把控。哈特莉的经历中,两个人都注意到箱子碍事,但是认为需要解决的那个人才会真正为此操心。我们的家务劳动不是从零开始的,而是从负开始的,得先有意识要做这件事,才会安排接下来的劳动,而这个思维过程就是不可见的,也就是不可见性。哈特莉引用了一个名词,说家里总有负责操心的那个人,叫“指定操心者”。很多家里的琐碎细节都是她们操心的结果,比如哪里该有个小挂钩挂钥匙,针线包放在什么位置,洗发水是不是该买了,茶几上摆什么东西,诸如此类。对不操心的人来说,开口一问东西在哪里就行,而对指定操心者来说,日积月累的隐形情绪劳动之下,生活变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网,只有自己才有清晰的导航图,还得负责引导其他人在这张网之间穿梭,确保每个人都感到安心。用我们中国人的说法,注意到哪里该收拾,就是“眼里有活儿”,做到“眼里有活儿”所需的操心,就是不可见的情绪劳动。
围绕在我们生活中的家务劳动里有无数的小细节值得操心,一个任务细分下来会变成二十个任务。这些家务的预备和收尾环节,虽然是身体劳动,但也是隐形的。一件家务里面会包含很多隐形的细节把控。比如说倒垃圾,仔细想一下,丢垃圾前要在全家收集没丢进去的漏网之鱼,确认还有剩余垃圾袋,倒垃圾的时机也不仅仅取决于满了没有,要结合这个垃圾桶装什么垃圾,如果是厨余垃圾就要抓紧丢,有时还需要注意垃圾分类,还要看桶里有没有漏出去的,丢完不能放着一个光桶在那,要套上新的垃圾袋,并且确保袋子服服帖帖地贴在桶边上。
总结一下,情绪劳动作为一种照顾性的劳动,在家庭中特别常见,既要照顾实体环境的舒适,也要照顾心理上的舒适,具有无报酬性和不可见性。无报酬性既有经济回报的缺失,也是情绪回报的缺失。不可见性同样有两层,既有作为心理活动不可见的无形操心,也有太琐碎而不被注意到的有形细节把控。日积月累的付出,得不到相应的回报,当然会变得唠叨,最终在某一件小事上生气。其实回顾哈特莉的案例,我们还会发现一个问题,让情绪劳动从关怀变成了一种负担,那就是分工的不均衡,操心的始终只有一方,另一方总是等待付出者的关怀,越来越依赖付出,而不提供回报。这种不平衡经常表现在性别上,一方面,“男主外、女主内”的常见家庭结构,导致家庭中付出情绪劳动的往往是女性,另一方面,作者说这种内化在心里的“注意”,职场中也往往是女性承担的,女性遭到职场和家庭两面包夹。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在家庭之外的情绪劳动,这样可以更好地理解分工不均衡。
简而言之,职场中的情绪劳动不光有把握细节或者维护舒适,除此之外,情绪劳动还包括那些避免引起不满的情绪克制,这是一种培养出来的技能。为什么说这是一种技能?这就要从“情绪劳动”这个词的源头开始说起。这个词其实不是哈特莉发明的,学者最早提出的时候就是用在职场工作的。听书之前解读过美国社会学家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的一本书,叫《职场妈妈不下班》,和本书是类似的问题,而作者霍克希尔德就是情绪劳动这个词的发明人。不过霍克希尔德当时讨论的是职场妈妈需要回家继续干家务,她称之为“第二轮班”,而我们这部分要讲的是“第一轮班”。
早在1983年,霍克希尔德在研究空姐的时候,发现她们通过控制自己的情绪,表现出愉悦的面部表情和温柔的身体语言,让乘客来感到舒适,由此提出了“情绪劳动”这个词。霍克希尔德通过研究航空公司的培训,总结控制情绪的方法包括表层表演和深层表演。怎么理解呢?通俗地说,表层表演就是“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而深层表演就是皮笑肉也要笑,要真的感到关怀和愉悦。有句话说,谎话最高境界就是把自己也骗了,深层表演的目的就是这么一回事。按照公司培训,空乘可以自己编故事,合理化乘客的行为,建立起同理心,抽离自己当下作为当事人的情绪。碰到那些不守规矩的乘客,要压制自己的愤怒和疲惫,把他们当成需要关注的小朋友,平息他们的情绪。
说到这,你注意到了没有?安抚小朋友,就是妈妈常常干的事情。也就是说,妈妈和孩子的关系是一种理想的情绪劳动模式,服务客户不是把他们当成上帝,而是要当成小孩,不仅在家里当妈,在职场上也得当妈。空乘人员要通过大量的情绪劳动,让狭窄局促的飞机空间充满温馨而又安心的氛围,乘客才能感到宾至如归,更有可能成为这家航空公司的常客。这一套让客人感觉舒服的服务方法,就是把情绪变成一种标准化的商品,训练乘务人员奉献自己的情感,这种对自己情绪的控制,就是职场中的情感劳动,在很多服务业岗位都有类似的现象。
书中讲到了一个护理师的经历,她是一名手术全期护理人员,要负责手术前、中、后期对病人的持续护理,一方面要满足医生的安排要求,另一方面还得照顾病人的情绪需求。这个护士描述,冷酷的医生老拿她们当出气筒,挨骂是家常便饭,病人还经常对她们大吼大叫,说她是个糟糕的护士。但无论是挨谁的骂,作为一个专业的护理人员,都必须硬着头皮保持镇定,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她说:“你必须确保每个人都很快乐,即使你自己并不快乐。”有一次,一个病人在洗肾期间挣脱出来,用过的针头不小心扎到了护士,由于病房里常有感染艾滋病或者其他传染病的患者,护士马上就想到如果真的被传染艾滋病之后的可怕后果,婚姻终结、不能生育、重病缠身、一命呜呼。但是她正在工作,不能马上去做检查,可那一瞬间露出的慌乱,马上被病人捕捉到,责怪她小题大作。她不得不继续微笑着陪病人四个小时,和她聊天,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之后才能去测试。等她轮班结束以后,一个人坐在车里嚎啕大哭,释放压抑了一天的恐惧和沮丧。
在这个例子中会发现,职场当中的情绪劳动的特征和家庭中类似。当护士每次用深层表演来改变自己情绪的时候,不会像计件工资一样获得回报,比如今天安抚了四个病人,也不会多拿四个鸡腿,而大家还会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因为是服务业,所以职业的情绪劳动被认为应该是单方向、不求回报的付出。这和家庭中情绪劳动无报酬、不可见的特征是相对应的。但无论哪里,情绪劳动总会带来情绪疲惫,像这个护士,她会需要发泄情绪调整心态,但是如果把这些发泄带到家庭当中,家庭的舒适就会受到打扰,她就不得不付出新的情绪劳动。于是,她只能选择在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夹缝中调整,比如下班后在车里,这让她的情绪更难得到彻底放松。
不仅如此,我们还会发现很多需要照护工作的岗位都是女性,比如护士、店员、乘务、幼教老师等等,就比如刚刚说过的职业,根据我国2022年的官方统计数据,有76%的航空乘务人员是女性,而护士的女性比例甚至高达97%。可以看到,虽然整个服务业之中普遍存在情绪劳动,但在具体的职业上,对情绪劳动有更高要求的岗位有明显的性别差异。这种性别差异,反映了人们其实对情绪劳动有一定的认知,而且这种认知和性别认知纠缠在一起,比如女性更情绪化、更擅长照顾情绪等等,尽管实际上这些技能都需要职业培训。
哈特莉认为,这是由于必须由女性来孕育生命,人们会把照顾孩子的母职工作认为是女性的天职,其中的情绪劳动则没有得到重视。当年她生完孩子后就成了全职主妇,别人问她都没上班了,为什么看起来还那么累,她给大家看了看正在哭闹的孩子,他们这才明白。女性负责母职的印象延伸到照顾性的情绪劳动上,只能是给情绪劳动的不平衡雪上加霜。这并不是说男性没有承担情绪劳动,而是说更多的情况下,情绪劳动被认为是女性特有的天赋和技能,实际上承担起了大多数情绪劳动,家庭和职业中的情绪负担都更大。中国有句话,“妇女能顶半边天”,但顶天立地也是很累的,情绪劳动背后的情绪负担应当得到重视。
好,这一部分,我们看到家庭以外的情绪劳动更多地表现为情绪表演,特别是深层表演。同时,由于社会的性别认知,女性承担了更多的情绪劳动,给职场女性带来更严重的疲惫。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这个情况呢?很巧,哈特莉走红后不久,她老公就失业了,这让他们有了机会重新调整分工关系。
刚刚提过情绪劳动可能不需要训练,但肯定需要培养,而且女性往往承担了大部分情绪工作,甚至是单独承担,这是很多家庭关系不和谐的一个根本原因。那么,我们该从哪里开始呢?我们接下来就结合哈特莉的经验,看看有什么能做的。我把这个阶段分成两个角度,一个是从承担者角度,另一个是从被照顾者角度。
先讲承担者这一边。一定有很多女性朋友想过,天天嫌我唠叨,我不操心还不行吗?这就是情绪劳动的奥妙之处了,就像工匠长期劳动以后熟能生巧,形成无意识的肌肉记忆,长期情绪劳动也能培养出一种记忆,不想操心也会操心。当你习惯付出这种关怀以后,就很难停下来,总会觉得少点什么,因为你已经“眼里有活儿”了,发现接手的人做得不够好,忍不住会说“还是我来吧”。这并不是“控制狂”,而只是一种肌肉记忆一样的情绪记忆。
这里并不是要说情绪劳动不好,我们要放弃情绪劳动,相反哈特莉是说情绪劳动可以成为一种提高生活质量的技能,而不只是只有一个人负责的嘱咐和安排。所以改变情绪劳动的第一步,对情绪劳动的承担者来说要为自己开脱,学会放手,放弃完美主义。哈特莉有一个很好的问题,可以是你改变心态的起点,“你有必要包揽一切吗?”
哈特莉在这方面不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但她的心态确实很常见,她不相信自己放手后罗伯特能做好。她从小到大学习到的也是说,那些注意叠衣服和收拾盘子的工作是妈妈负责的,从没有人说过爸爸该干这些,她非常怀疑男人能不能干好这些事情。有一次,她让罗伯特照顾孩子,自己专心写书,结果几个小时后她发现家里好像火山爆发,食物、玩具、衣服丢得到处都是,老公却一个人去骑单车了。但她实在没有更多时间来做以前她负责的事情,不得不让罗伯特试着来干。她既感谢罗伯特承担了更多的情绪劳动,又为他没有遵循以前那种行之有效的方式而感到生气。哈特莉感到很沮丧,罗伯特是不是真的学不会?
哈特莉怎么解开这个心结呢?她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世界上的确有男人像自己女性伴侣一样懂怎么照顾别人。人类学家休利特在非洲研究了一个叫“阿卡”的部落,他们有堪称“世上最棒的父亲”。休利特发现,阿卡父亲在孩子身边的时间高达47%,父母几乎是平分了照顾的任务,同样也平分了狩猎的任务。很多阿卡父亲在母亲出外时,主动泡奶粉给孩子喂奶,安抚孩子。他们还会抱着自己的孩子参加聚会,一边聚餐,一边背着孩子聊天。哈特莉突然领悟到男性并不是天生不懂照顾人,是自己的心魔阻碍了和罗伯特的关系调整。因为她不相信罗伯特,所以一直在插手,罗伯特既学不会她的那一套,也没办法建立起自己的组织体系。
所以接下来就是第二个重要的步骤,相信你的伴侣,因为情绪劳动不是一种先天天赋,而是需要培养的。在阵痛期的时候,可以提醒,但要允许别人学习,接受不同的组织方式。不是只有自己习惯的方式才是最舒适的,这也是一种不必要的情绪劳动,双方可以在尝试的过程中发现新的模式。
做到了以上这两步,接下来的第三步就很关键了:开启对话。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刚才不是说要放手和相信伴侣吗?其实并不矛盾,对话能够帮助过渡阶段更加平稳一些,让对方更快理解哪些事情需要做。不要通过安排、要求的方式,这样反而增加情绪劳动。要在负担太重时就及时开口,不要害怕求助的麻烦。哈特莉在母亲节那天崩溃的时候,就没有好好表达自己的情绪问题,实际上罗伯特并不是不愿帮忙,只是没有这种经验,他不知道从何入手。情绪劳动不只是体力活,不光是半夜陪孩子、洗碗之类的,还是那种要环顾全局,眼里有活儿,到处都是小细节的把控感,这对于没有经验的人来说是很难想象的。
这里我们就要转到照顾者这边,第一步是重视真实存在的情绪劳动。
实际上,如果现在问平时不习惯情绪劳动的人,理想生活是什么样的,得到的答案听起来会非常有极简主义精神,很可能就是简单的一份稳定的工作、一个住的地方,每餐可以点外卖,晚上回家玩游戏、睡觉。这样的生活并不是不好,只不过是过度简单化了,但如果真的要去实践,就会冒出无数无法避免的细节,生活的舒适程度很难有保证。根本原因是,有人平时把细节料理好了,所以自己不会想到。只有彻底改变我们对情绪劳动分工的预期,我们才有可能过最好、最充实的生活。重要的事情值得说两遍,平衡的第一步一定是承担者敢于放手。但被照顾者也需要看到这些劳动存在、倾听伴侣的需求,敢于接手自己没想过的事情。我们要意识到,情绪劳动是在生活质量背后的隐形保障,而不是控制狂的迷恋。
要改变这种情况,第二步就是逐步建立新的意识,自己不是“帮忙”做情绪劳动,而是一起做,要主动环顾四周是不是有没做的,训练自己“眼里有活”,而不是停留在已经做了多少活。哈特莉有几个问题,非常扎心,但我听了,也在反省,她问“你在没人要求下就主动做那些事情吗?你注意到伴侣为你、为孩子、为你的大家庭、为朋友做的一切吗?你给她的赞美跟你获得的赞美一样多吗?你说你做了很多,那是跟其他的男人相比,还是跟你的伴侣相比?”
实际上,如果用这样的眼光审视自己,我总会发现自己做得还不够,我和朋友、家人之间有很多关怀想要给出,却没有给出,就是怕付出情绪劳动的疲惫。这也是为什么作者说,情绪劳动作为一种照顾、一种关怀,是值得学习的。哈特莉说,我们可以规划放松活动,为你喜欢的活动腾出时间,这都是情绪劳动的一部分,也可以规划为你带来快乐、培养感情的节日派对,让朋友和家人都感受到你的情感付出。你可以投入一种更平等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你知道你付出的情绪劳动和得到的会一样多。
而第三步,还是开启对话,厘清相互的需求。在对话中,有几件事特别需要注意:哪一部分的情绪劳动真的对我们有益,哪一部分无益?双方要打造自己的系统,建立自己的情感联结,确立自己的轻重缓急,而不是在别人打造的生活中游走。我们可以问自己,什么情绪劳动让自己感到舒适?现在做的情绪劳动是别人的期待,还是自己的期待?这样来找出自己当下情绪劳动最必要、最有益的那一部分。哈特莉就开始放弃完美主义,放弃不必要的标准,比如毛巾不用叠那么整齐,而罗伯特同样意识到自己忽略太多细节,比如灶台其实堆了很多杂物。哈特莉学会睁一眼闭一只眼,而罗伯特主动问有什么让老婆心烦,两个人互相协调,更向对方的标准靠拢。
最后,我们再复习一次,对于承担情绪劳动的人来说,第一步是放手,第二步是相信伴侣的学习能力,第三步是与伴侣对话。而被照顾的人,第一步是重视情绪劳动,第二步是主动问自己还有没有该做的,第三步也是对话。通过对话,我们把单方面的网,变成两个人一起把控的系统,不再单方面为别人付出,或者单方面等待别人的指导。
哈特莉和罗伯特怎么样了呢?哈特莉不断写书、出席活动,事业蒸蒸日上,而罗伯特一直没找到工作。他们俩开了几次会,开始真正“交换岗位”,罗伯特多付出一些情绪劳动,而她来当那个被照顾的人。有一天下午,罗伯特坐在家里发呆,哈特莉以为他是觉得找不到工作压力很大,但实际上罗伯特回答:“我觉得有些事情是我需要做的,但我忘了,怎么也想不起来。”哈特莉明白,罗伯特真的学会了。实际上哈特莉写《时尚芭莎》文章的时候,是想警告罗伯特,再这样下去他们非离婚不可,但随着双方的情绪劳动逐渐平衡,罗伯特眼里不仅看到了活儿,也真正看到哈特莉的付出,他找到了自己在家庭中的价值,顺利走出了婚姻危机。
诚实地说,在读到这本书之前,作为家里不太喜欢打扫的那个人,我一直以为这只是个体力活问题,我已经帮忙了,为什么伴侣就是不满意。现在我才明白,实际上还真应了那句话,魔鬼藏在细节中。如果你也听过自己母亲或者妻子唠叨,就应该知道,她已经太累了。其实那一刻的失控,是不能总是把控一切的疲惫,是时候帮助你爱的人了。如果你是那个疲惫的人,也不要害怕改变,一个更平衡的关系永远不晚,相信你的伴侣,和他一起做出改变,我们双方都能成为家庭的主角。我们或许无法做到完美的平衡,但双方都能通过参与找平衡的过程,一起努力克服各自的障碍,量身打造出一个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案,满怀信心地继续前进。
好,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
情绪劳动是“结合情绪管理和生活管理,是我们为了让周遭人感到舒适和快乐所做的没有酬劳、不被看见的工作”。
-
对于承担情绪劳动的人来说,第一步是放手,第二步是相信伴侣的学习能力,第三步是与伴侣对话。而被照顾的人,第一步是重视情绪劳动,第二步是主动问自己还有没有该做的,第三步也是对话。
-
我们或许无法做到完美的平衡,但双方都能通过参与找平衡的过程,一起努力克服各自的障碍,量身打造出一个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案,满怀信心地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