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熟悉的家中向世界道别》 杨以赛解读
《在熟悉的家中向世界道别》| 杨以赛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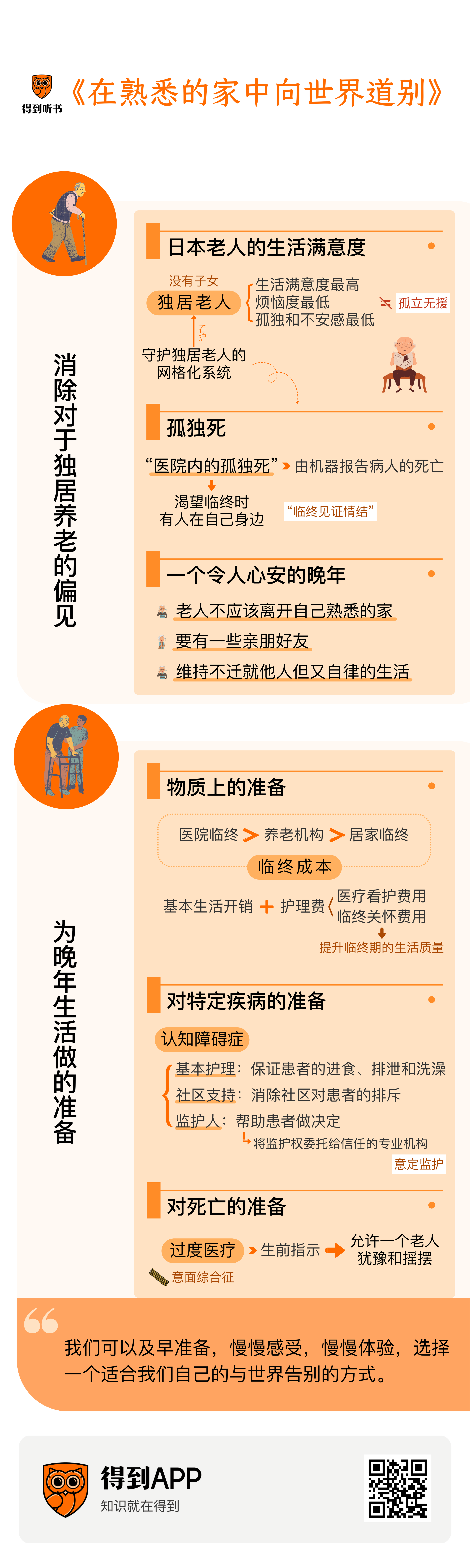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在熟悉的家中向世界道别》,这是一本讨论衰老与死亡的书。
在今天,老年人的生活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往我们常说“四世同堂”“天伦之乐”,老年人自然是要跟家人团聚,在家人的照顾下安享晚年。但今天不一样了,上一代人变得没那么想和下一代人住在一起了,就算是想住在一起,也可能因为工作等问题,面临不在一个城市的情况,所以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的原因,完全靠自己应对老年生活,变得越来越普遍了。今天这本书谈论的便是这样一个问题,它甚至考虑的是一种更为极致的情况,如果没有家人,独自一人,我们是否还能拥有一个安全且有尊严的老年呢?
这本书的作者是上野千鹤子,她是日本东京大学社会学教授,是日本女性主义研究的代表人物,2023年8月她被美国知名杂志《新闻周刊》评选为世界尊敬的百大日本人之一。凭借鞭辟入里的理论分析,以及对日常生活的关照和指引,上野千鹤子的书这几年很受中国读者欢迎,甚至出版界把2022年直接称为“上野千鹤子年”,因为她的书实在太畅销了。“得到听书”此前解读过她的《始于极限》,那本书在豆瓣获得了超过五万人的评价,打出了9.1分的高分,可见大家对她的关注和认可。
上野千鹤子的书大多有关女性话题,这本《在熟悉的家中向世界道别》在她的一众书中显得有点特别,但对上野千鹤子来说,这是她必然要写到的一本书,因为她本人就是一个独居的老人。她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写道:“我没有家人,基本上是一个人生活。死亡就像一条下坡路,我们只能缓慢地走下坡去:慢慢地失去自理能力,吃不下饭,喝不下东西……然后某一天停止呼吸,人们说这就是临终了。我想,独自一人生活的我,也将会独自一人走过这段下坡路,然后某一天独自一人在家中去世。如果某天我的死亡被人发现,我不希望被人们认为我很可怜地死去了,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动机。”
在这本书中,上野千鹤子通过对日本的医疗、看护、护理等最新情况的全面调研,分享了她自己为晚年生活所做的准备。她基于日本的实际情况,同时着重讨论了独居这种状况,这不见得适用所有人,但我想它不失为一个有价值的参考角度,来帮助我们审视和思考我们对老年的规划。尤其像前面所说,独自一人养老是最极致的一种情况,它或许最能显示出老年生活中最根本、最必不可少的需求和意愿。
好,话不多说,接下来我将分两个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第一部分,我们来讨论“独居养老”真的是可行的吗?第二部分,我们来讨论,倘若“独居养老”真的可行,它并不如我们想象中的可怕,那么我们可以为此做一些什么准备呢?
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在日本,独居老人的数量越来越多,上野千鹤子在书中提到一组数据,2007年她出版《独居者的晚年》的时候,日本独居老人的比例是15.7%,但到了2019年,这个比例激增到了27%。而住在一起的老夫老妻的比例是33%,考虑到住在一起的老年夫妻将来可能因一方去世或者离婚而变成独居老人,所以可以想见,在不远的将来,日本独居老人的比例会超过50%。
“得到听书”此前解读过一本书叫《无缘社会》,它讲的是在日本拥有成熟的社会福利制度和养老机制,但每年有近3万日本老人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最终悄无声息地死在家中,像这样的死亡被称作“无缘死”或“孤独死”。单是这一个词语,就足以让人感受到其中的凄惨。但上野千鹤子对此有不同看法,她认为“孤独死”这个词加深了社会对独居老人的偏见,她在书中写道:“一个老人独自生活,直到最后去世有什么错吗?为什么要被称作孤独死?我实在不喜欢这个叫法……我们总是一味展示‘独居者’的负面形象,但实际上周围到处都有开开心心生活着的独居老人。”
事实上,如果你是主动选择独居,你的生活满意度反而可能会更高。上野千鹤子在书中提到一位叫做辻川觉志的医生所做的调查研究。辻川医生将日本老人的居住情况分为独居、与一人同住、与两人同住、与三四人同住,然后发放问卷,调查不同居住情况的满意度情况。他的调查显示,和一人同住,也就是两人户的情况,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是最低的。三人户的生活满意度稍有上升,三人以上同住,也就是多代同堂的满意度继续上升,但也只达到和一人独居差不多的水平。在两人户,也就老两口生活的家庭里,两人的满意度都低,其中妻子的满意度要低于丈夫。
辻川医生后来还对日本有子女的老人、没有子女的老人、子女住得近的老人和子女住得远的老人各自的生活满意度、烦恼度、孤独和不安感做了调查,结果令人意外。没有子女的独居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是最高的,烦恼度最低,孤独和不安感也最低。辻川医生总结说:“如果你一开始就没有子女,也习惯了没有子女,那可能你老了以后并不会觉得寂寞。”
辻川医生的调查当然也有其局限性,其调查对象大多是住在大城市近郊的中产老人,换一句话说这是一群有足够资源支撑他们独居的老人,而那些身陷贫困的独居老人被排除在统计之外了。但辻川医生的统计显示出“独居养老”不应该是一个令人感到害怕的事情,当你有充分准备的时候,“独居养老”或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上野千鹤子就此在书中说,独居不意味着孤立无援,和家人住在一起也不意味着就可以放宽心了,“孤独死”可怕的地方不在于独居,而在于孤立无援。
日本香川县高松市政府曾与70多家私营企业合作,构建起了一个守护独居老人的网格化系统。这70家私营企业包括邮局,送报公司,收取电费、水费、煤气费的抄表公司等,它们深度参与到了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所以能发挥一定的看护作用,比如如果哪个独居老人家的水表一整天没动的话,就有理由怀疑他可能出了什么事,需要援助。但上野千鹤子在书中指出了这个系统的一个误区,它只守护独居老人,但现实里需要援助的可不只是独居老人。日本多起“孤独死”案例其实都不是单身户,比如曾有一起是两位老年姐妹,她们都在室内出了事故,还有一起是一位年迈的母亲和她40岁出头的残疾儿子,先是母亲倒下了,之后无人照顾的儿子也倒下了。上野千鹤子说,可见就算有家人也会发生整个家庭孤立无援的情况。所以,无论有没有独居的打算,人人其实都应该考虑自己陷入孤立的情况,或者说无论独居与否,人人都应该按照“独居”的状况来为晚年做准备,想着“家人在就可以放心”显然是不够的。
不过,就算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应对老年独居的生活,但我们难免还是会害怕独自去世,因为在我们传统观念中,一个人得是在家人或朋友的陪伴和见证下去世,这才算是善终。但上野千鹤子在这本书中说,其实大部分死亡都是没有见证人在场的,独自面对死亡是一件难以避免的事。比如就算和家人在一起,去世时家人也可能在睡觉,或者并不在家。在医院也是如此,护士也并不是24小时在场的,往往得要警报响起,护士才会赶来。所以在医院经常是由机器报告病人的死亡,日本居家临终关怀协会的会长小笠原医生把这种情况称为“医院内的孤独死”。
上野千鹤子怀疑老人们自己真的需要有人来见证死亡吗,还是说这其实只是身边人的一厢情愿呢。她从医生这里听到过一些故事,有老人明明已经不行了,但老人的家属强烈要求医生采取措施延长一下老人的时间,等待老人的长子赶来。还有她采访了临终关怀师柴田久美子,她也提到说曾有一位癌症晚期患者入住以后,为了避免该患者走的时候是一个人,大家分组轮流去看护,没想到最后该患者却直言:“请你们偶尔也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吧。”
上野千鹤子把这种渴望临终时有人在自己身边的情结称为“临终见证情结”,她认为抱持这种情结其实是没必要的,一来因为这难以做到,而且就算做到了,临终的人,因为极差的身体状况,不一定真能感受到陪伴。二来,有时候正是这种“临终见证情结”让我们把道别一再延后,最终让道别变得仓促又无效。在日本这样一个超级老龄化社会里,老年人死亡原因排在第一位的是癌症,第二是心血管疾病,都是一些无法治愈的慢性病,换一句话说,大多数人的死亡是可以预见的、缓慢到来的。上野千鹤子就此说道,既然如此,我们其实有充足的时间跟临终者道别,不一定非要留到最后一刻,因为到时候你说得再动听,逝者其实都已经听不到了。
在上野千鹤子看来,比起临终时有人在场,保证我们能够在熟悉的家中临终或许更重要。就像刚才讲到的,在日本老年人大多是因慢性病去世,放至全世界其实也是如此,这意味着医院其实能发挥的作用很有限了,甚至医院可能反倒让本来温和的死亡变得残忍起来。上野千鹤子说,当年轻人得了传染病或者遭遇事故的时候,赶去医院就诊大概率是有用的。但是,对于那些死期将近的老人,再做一些延长生命的治疗,这对患者好还是不好,都是需要再思考的。大家之所以会认同“在医院去世”,其实是因为过去的医疗资源十分稀缺,作为子女,只要父母还有一口气,就还是希望医生再抢救一下。但现在情况已经不一样了,对于年岁已大、身患慢性疾病的老人来说,医生的作用其实已经不在抢救了,而在于尽量减少病人痛苦,减少无谓的医疗干预,所以上野千鹤子认为,与其把老人送去医院,不如保证他在家中的基本护理,让他在熟悉的家中平缓去世。
这其实也是很多国家的做法,是一种趋势。上野千鹤子在书中提到,比如丹麦早在1988年就立法禁止建造新的养老院了,并主张将养老院改造为“护理住宅”,其实也就是在保证基本护理的情况下,让老人尽可能地独自居住,这样更能保障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上野千鹤子就此说道:“老年人就像半个残疾人,但不管是老年人还是残疾人,都应该正常地居住在满是男女老少的正常街区里。只要我们的街区能够配合做出改变,那就再也不需要什么养老机构了。”
总之,上野千鹤子在书中列举了不少针对日本老年人生活状况的研究,同时也结合了她自身的经验,试图消除我们对于独居养老的偏见。但这并不是说她鼓励我们每一个人都去追求独居养老,在她看来,这只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她更重要的目的其实是借“独居养老”这种极致的情况来探讨,一个老年人最根本的需要究竟是什么?在她看来,老人不一定需要与家人同住,不一定需要在别人的见证下去世,以及不一定需要住进养老院,也不一定需去医院处理死亡,比起这些,上野千鹤子更为看重三点:第一是老人不应该离开自己熟悉的家;第二是比起有钱,更应该有人,也就是有一些亲朋好友;第三要能维持不迁就他人但又自律的生活。对她来说,是这三点构成了一个令人心安的晚年。
以上我们说的大多是一些理念,但其实在这本书中,上野千鹤子还详细讲到了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支撑“独居养老”,要能做到“独居养老”了,其实也就可以应对老年的各种状况了吧。接下来的第二部分,我们就来讲讲上野千鹤子为晚年生活所做的准备。
首先,物质上的准备是必不可少的。上野千鹤子在书中算了一笔账,在医院临终的成本是最高的,其次是养老机构,最低是居家临终。上野千鹤子就此在书中说:“如果将那部分居住费用用于购买其他自费的医疗服务,肯定会受到更好的照顾吧?”
那日本老人居家临终到底要花多少钱呢?上野千鹤子算了一下,除开基本的生活开销,最主要的就是护理费了。而护理费又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日常的医疗看护费用,很多人觉得临终期的老人需要24小时有人看着,但上野千鹤子认为完全没必要,哪怕是在养老院和医院其实也不是24小时都有人看着,所以其实只要保证有护理人员定期上门护理就行了。日本有护理保险制度,被认定为需要护理援助的老人,会有专门的护理援助专员来对接,而且还会提供相应的医生和护士上门服务。此外还有大量的民营机构可以提供类似的服务,所以已经完全能够满足需求。另外还有一部分费用是临终关怀费用。以往我们没有“临终关怀”的概念,死亡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很被动的事情,我们只能听之任之。但临终关怀则是主张通过一系列主动的措施来提升临终期的生活质量,它牵涉大量专业知识,因此必须交由专业人士进行。在日本,保险很少覆盖临终关怀费用,只能自费购买,它的价格不等,有平价的,也有昂贵的。上野千鹤子说,这一部分费用乍看之下会有点吓人,但其实你要想到临终期并不是遥遥无期的,终有一天会结束,我们可以很早便开始为这几个月的时间做好准备,这并不是一件难事。
此外,我们显然也需要为一些特定的疾病做准备,书中上野千鹤子特别谈到了患上认知障碍症,也就是老年痴呆的情况。她说,独居的各种困难我都能克服,哪怕是癌症我也是不带怕的,因为这些都是我自己做得了主的,但如果我失去了自主决定的能力,也就是患上认知障碍症呢?在所有护理当中,认知障碍症患者的护理难度是公认最大的,上野千鹤子坦言,她对此是有些发怵的。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预测,到2025年,日本的认知障碍症患者将达到700万人,也就是说每四个日本老人当中就会有1个患有认知障碍症。日本早在2012年就制定了《认知障碍症对策推进五年计划》,简称“橙子计划”,之后又在2015年制定了《认知障碍症对策推进综合战略》,简称“新橙子计划”。但日本社会对这两个计划都评价不高,媒体甚至将其直接称为“有毒的橙子”,因为其核心主张仍然是将认知障碍症患者集中在特定地方,统一照料。上野千鹤子在书中很直接地指出,这其实就是将老人关起来。她写道:试问有哪个老人会希望自己被关起来呢?需要这类机构的不是患者本人,而是患者的家人,这类机构拯救的也不是患者本人,而是患者的家人与制度的缺陷。
上野千鹤子在书中提到日本一家叫做“明日奈良苑”的护理机构,它规模不大,但功能多样,是养老机构、服务型老年公寓、日托、短租的多元组合,用户可以选择住在里面,也可以选择白天过来,还能选择让机构提供上门服务。理事长安倍信一一直以来认为,“即便是独居的认知障碍症患者,只要当地有一个小型的多功能护理机构,他们也能在当地好好地生活下去。”
上野千鹤子还特别注意到“明日奈良苑”在做居家支援的时候,它针对的不仅仅是单独的一个用户,而是整个社区。社区的存在,既可以起到积极作用,也能起到消极作用。对于把患有认知障碍症的老人放在家里,社区更多的是排斥,而非包容。而“明日奈良苑”的工作人员所做的就是消除这种无声的压力,让大家知道,哪怕患上了认知障碍症,也能安心待在家里。甚至他们会动员社区居民,让他们知道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会遭遇这种状况,从而在互帮互助中降低风险和成本。
此外,对于认知障碍症患者而言,在保证了进食、排泄、洗澡这三大块的基本护理,也保证了必要的社区支持后,还有一个需要保证的是能够帮助我们做决定的监护人。在我们没有特别指定的情况下,一般会由我们的子女等家人来代行决定权。但一方面有些人可能并没有家人,比如上野千鹤子本人就是这种情况,另一方面就算有家人,我们的利益并不一定是一致的,所以对于独居老人而言,最明智的做法是将监护权委托给自己信任的专业机构。在日本已经有大量的社会机构在提供类似服务了,他们可以全权代理老人的监护职责,以及处理相关的财产和丧葬事宜。中国也有“意定监护”的说法,它也是说成年人在意识清醒时,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定临终监护人处理后事,这个临终监护人不必是直系亲属,不必是法定继承人,可以是任何人,甚至是陌生人。中国最早一批“意定监护”公证人李晨阳曾在一个采访中说:我们一辈子都觉得,命运在我们自己手中,我的意愿在我手中,但到了最后那个阶段,你要如何确保你的意愿,甚至你生命结束后,谁来帮你完成真实的意愿呢?“意定监护”在乎和保护的其实正是我们自身的意愿。
好,讲完对特定疾病的准备,最后我们还要来讲一讲对死亡的准备。上野千鹤子在书中很明确地讲到她并不害怕死亡,她害怕的是死亡之前的过度医疗。上野千鹤子用“意面综合征”来形容过度医疗,当我们的身体被插满了各种各样的细管和电线,那不就像是意大利面一样吗?为此,日本尊严死协会建议人们在仍有能力自主决定时,留下一份书面的预先指示,说明他们希望如何死亡。该协会认为尊严死的核心就在于抑制那些“无益的延长生命的措施”,如心脏复苏、切开气管、胃造瘘等。
但上野千鹤子在书中质疑了这类“生前指示”的有效性,当当事人失去了行动能力,“生前指示”还会有多大的约束力呢?另外,如果当事人想法改变,但他又没有行动能力告诉身边亲朋的时候,又该怎么办呢?对此,上野千鹤子提出,在究竟要怎么死去的这个问题上,你其实可以“一直犹豫到最后的”。
她会这么想,源自她护理她父亲的经历。上野千鹤子的父亲是癌症晚期病人,没有治愈的希望,他有时候会说“让我早点去死吧”,过了几天又说“还是把我转去康复医院吧”,当家人四处去找可以转过去的康复医院的时候,他又变卦说“还是算了吧”。上野千鹤子从父亲身上认识到,走向死亡的人,心情时刻都在变化,就像过山车那样忽上忽下、摇摆不定。“生前指示”这类的东西其实在真正帮助的也只是家属和医护方,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完全不用犹豫,不用思考,按照这份指示执行就好了。这不是负责任的做法,真正负责任的话,我们应该允许一个老人犹豫和摇摆,而且家人和医护方也应该陪着老人犹豫和摇摆。哪怕是一个丧失自主决定权的老人,在如何死亡这件事上,也不应是一时就决定的,也需要我们仔细斟酌和商讨。上野千鹤子说,我们都知道在死亡这件事上,不应该有任何强迫,但她还想强调的是,在这件事上,我们可以慢慢来。
好,到这里,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完了,我们再来回顾总结一下。
在这本书中,上野千鹤子介绍和梳理了日本在医疗、看护、老年人生活保障方面的一些情况,同时给出了她对于“独居养老”的看法与实际举措。上野千鹤子竭力消除人们对于“独居养老”的偏见,在第一部分,我们介绍了一系列基于日本的统计研究,结果显示老年人“独居”的生活满意度实际远高于与家人同住,并且在孤独和不安感上也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严重。所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独居养老”不失为是一种更好的选择。但这不是说上野千鹤子鼓励所有人都选择独居,她借此提倡的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考虑自己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以自己可能会要独居,甚至会患上认知障碍症为前提,来规划和准备自己的老年生活。她说:我们不是要迈向一个“即使患上认知障碍症也不要紧”的社会,而是要迈向一个“患上认知障碍症以后依然美好”的社会。下一步,我们还要迈向一个“对认知障碍症胸有成竹”的社会。
第二部分我们谈到了上野千鹤子对于“独居养老”所做的准备。首先物质准备是必不可少的,除开基本的生活开支,它还包括日常的医疗照护费用,以及临终期的临终关怀费用。其次我们也应对特定疾病有所准备,其中认知障碍症或许是最棘手的,但如果能配备有一定的护理援助和社区支持,哪怕患上认知障碍症,我们其实仍然可以留在熟悉的家中养老。再有,她提到了对死亡的处理,我们不断在强调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世,但上野千鹤子在这本书中强调了另一点,那就是这个决定有时候没那么容易做出,我们可以及早准备,慢慢感受,慢慢体验,选择一个适合我们自己的与世界告别的方式。
总之,死亡并不可怕,上野千鹤子在58岁的时候就写下了《独居者的临终》一书,那时她便已经在思考自己的晚年了,而写这本书的时候,她已经72岁了。她在书中说,她还将继续思考下去,为了一个更好的晚年,她还有很多事情要思考,有很多事情要准备。
好,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
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考虑自己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以自己可能会要独居,甚至会患上认知障碍症为前提,来规划和准备自己的老年生活。
-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独居养老”不失为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
我们可以及早准备,慢慢感受,慢慢体验,选择一个适合我们自己的与世界告别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