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解忧》 陈子昂解读
《人生解忧》| 陈子昂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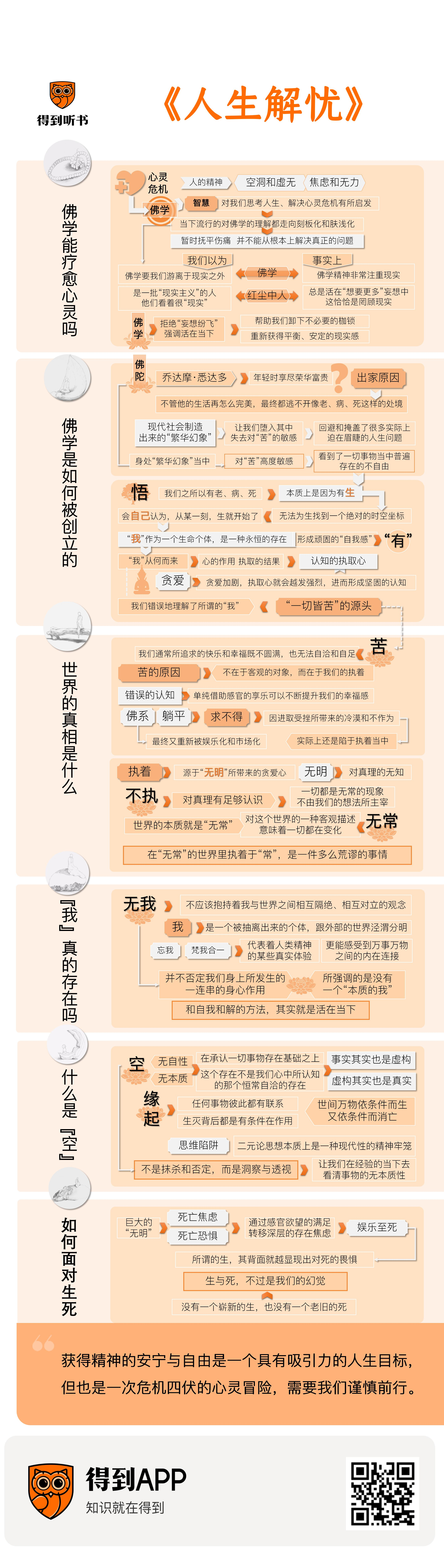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
今天这期听书,我想为你分享的书叫《人生解忧》,它的作者,是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成庆。这是成庆老师写给当代人的一本佛学入门书。
成庆老师本人的经历很有意思,他是工科出身,1999年大学毕业之后,他获得了一份令人羡慕的稳定高薪的工作。但是,那阵子,他过得并不开心。他感觉身边的人都被社会时钟推着往前走,大家聊的都是什么时候买房,什么时候结婚,似乎没有人愿意停下来去思考和讨论自己的人生。
出于想要探寻人生意义的愿望,他选择辞掉工作,重新回到高校,去读了哲学。不过,在读了哲学之后,成庆老师发现,他似乎没法从纯粹的思辨游戏当中得到身心的安顿。在博士毕业之前,他遭遇了一场心灵危机,他对手头的事儿不感兴趣,也对毕业后找工作的事情感到焦虑。他感觉自己人生过得非常失败,甚至一度陷入抑郁情绪当中。
直到后来,他遇到了佛学。在佛学这里,他收获了深刻的启发。
成庆老师的这段经历,估计在当下能够引起不少人的共鸣。书中说,在当下,基本生存已经不再是人们最迫切的问题了,但大众的心灵危机却愈发明显。人们的精神变得空洞和虚无,随之而来的,是焦虑和无力。很多人在不断追问: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人为什么而活?如何才能拥有积极主动的生活?
与此同时,一些跟佛相关的话语也开始流行,“佛系”“躺平”成了很多人挂在嘴边的词汇。
这些跟佛相关的话语之所以流行,是因为人们发现,在我们的传统思想文化当中,佛学似乎向来就是疗愈心灵的良方。提起佛学,不少人第一印象就是青灯古佛,远离尘世喧嚣,不食人间烟火。因此,很多人从佛学当中获得的启发,就是拒绝内卷,要躺平,要佛系,这样一来,就可以对抗内心当中的烦躁和焦虑了。还有人认为,佛是一种获取心理安慰的来源,于是人们纷纷跑到寺庙里去。对此,有人调侃说,今天年轻人“在上班和上学之间选择了上香,在求人和求己之间选择了求佛”。
那么,成庆老师是怎么看待这样一种现象的呢?
在成庆老师看来,佛学作为一种智慧,它确实能够对我们思考人生、解决心灵危机有所启发。但是,他又提醒我们,当下流行的很多对佛学的理解都走向了刻板化和肤浅化。这种已经被扭曲了的“佛学”,也许它能够暂时抚平我们的一些伤痛,但从根本上讲,它并不能帮我们解决真正的问题。
事实上,我们对佛学存在着很多的误解。
比如说,我们往往认为佛学要我们游离于现实之外,但事实上,佛学的精神是非常注重现实的。《坛经》当中有句话,叫“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这说的是离了现实生活来谈觉悟,就像是去兔子头上找角一样荒谬。书中说,禅宗的僧侣践行的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是紧贴着土地,过着挑水担柴的“禅生活”的,他们不是什么孤高的隐士,更不是什么绝望的厌弃世界的人。
相反,我们经常会说,生活在红尘里的人,是一批“现实主义”的人,他们看着很“现实”。但事实上,按照佛学的说法,这样的人为了满足欲望不遗余力,总是活在“想要更多”的妄想当中,这恰恰是罔顾了现实。书中说,今天的我们往往忽略当下,比如吃饭的时候不专心吃饭,脑子里想的都是一堆过去的或者是未来的别的事情,我们的思维跨越时空,无远弗届,就像是一个白日梦想家一样,看似积极地投入世俗生活,但精神却总是游离于当下。
所以,拒绝“妄想纷飞”、强调活在当下的佛学,反而是能够帮助我们卸下很多不必要的枷锁,重新获得平衡、安定的现实感。
因此,这本书的书名叫《人生解忧》。成庆老师正是希望通过对佛学的介绍,来帮我们解除烦恼忧虑,进而使我们重获心灵的自由。
也正因为这本书的基调如此,所以在接下来的分享当中,我不会把重点放在知识的讲解上,我们直接贴着我们的生活,贴着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来聊佛学。正如书中所说,“佛陀当年在菩提树下的觉悟,绝非为了发展出一套完备的知识体系,而是要让所有感到生命之苦的人,能够通过他的教导,获得心灵自由的力量”。
那么,当年佛陀究竟遭遇了什么,他的人生遇到了什么问题,而他最后又对此提出了什么样的洞见呢?接下来,我们不妨一起来看看,佛学最初是怎么诞生的。
我们知道,佛学的开创者佛陀,全名叫乔达摩·悉达多。他是古印度的一位王子,19岁成亲,29岁出家,35岁觉悟,随后花了45年的时间四处讲法,最终在80岁的时候离开人世。
既然贵为王子,那可想而知,佛陀年轻的时候是享尽荣华富贵的。那么,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会选择走上出家这条道路呢?书中说,佛陀选择出家,那肯定不是出于对世俗生活的逃避,毕竟,从世俗的眼光看,他的生活已经很好了。佛陀选择出家,恰恰是因为,他的生活已经足够好了,但他发现,不管他的生活再怎么完美,他最终都逃不开像老、病、死这样的处境。这一点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变。无论社会再怎么进步,对于生命而言,老、病、死的束缚感是永远围绕着我们的。
书中说,尽管我们大部分人为普通人,但事实上,当下的我们和当时身为王子的佛陀的处境却是非常像的。你看我们现在逛的琳琅满目的卖场,不就是当年佛陀居住的繁华宫殿吗?今天充斥在手机、电脑里的声色幻象,不就是当年佛陀身边的翩翩舞女吗?
现代社会制造出来的这种“繁华幻象”,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让我们堕入其中,失去了对“苦”的敏感,从而回避和掩盖了很多实际上迫在眉睫的人生问题。但佛陀不一样。尽管他也身处于“繁华幻象”当中,但他对“苦”是高度敏感的,他看到了一切事物当中普遍存在的不自由,而且,这种不自由并不会因为他拥有了富足的生活就能够缓解,或者让他转移了注意力。因此,他决定通过修行,来追求生命的觉悟。
那么,佛陀最终在菩提树下悟到了什么呢?
佛陀发现,我们之所以有老、病、死,本质上是因为有生。生命得先有开始,才有后面的这些对老、病、死的拒斥。那什么叫做生呢?婴儿呱呱坠地就是生吗?还是从受精卵开始就是生呢?还是要再往前追溯呢?如果我们往下细究,就会发现,其实我们无法为生找到一个绝对的时空坐标。只不过,我们会自己认为,从某一刻,生就开始了。如此之后,我们会不断地强调一个看法,那就是:“我”作为一个生命个体,是一种永恒的存在,即便我们也同时知道有衰朽和死亡。也就是说,我们形成了一种顽固的“自我感”,佛学把它称为“有”。
那这个“我”从何而来呢?佛陀认为,这是心的作用,是一种执取的结果。那为何会有这种认知的执取心呢?佛陀进一步推断,认为那是因为贪爱。一旦我们对事物产生了好坏判断,就会对喜爱的产生占有的欲望,对厌恶的产生抗拒的想法,这些都属于贪爱的念头。贪爱一旦加剧,我们的执取心也就会越发强烈,进而形成一个坚固的认知,那就是:只要“我”喜欢,就一定要得到满足。于是,这种带有强烈贪欲感的个体意识,最终就变得牢不可破了。
所以,问题在哪呢?佛陀的答案是,问题就在于,我们错误地理解了所谓的“我”。佛学当中所讲的“一切皆苦”,它的源头也在于这儿。
我们知道,佛学当中有“八苦”和“三苦”的说法。不管是哪种说法,它们说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儿,那就是我们的内心恩怨交加,喜乐无常,永远充满着躁动,无法获得真正的安定。
对于佛学当中关于“八苦”和“三苦”的论断,有些人可能会质疑:“为什么说世间都是苦呢?难道我们就没有快乐的时候吗?”这显然和我们的常识相违背。
因此,佛学讲“苦”,不是说我们人生当中没有快乐的时刻,而是在说,我们所谓的快乐其实不纯粹,也不稳定。它虽然可以给我们片刻的安慰,但也会给我们不断造出新的困境。就好比说,我们在生活中存在某些期待,比如金榜题名,比如升职加薪,在追逐它的时候,我们会焦虑,而在达成目标的那一刻,我们会获得巨大的快乐。但是,这个快乐很快就消退了,我们又得转而去追逐下一个快乐的目标。也就是说,我们通常所追求的快乐和幸福既不圆满,也无法自洽和自足。书中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说这就像是“踩在苦与乐的跷跷板上,左支右绌,狼狈不堪”。
总的来讲,就是我们永远处于一种不满足、不稳定的状态,而造成我们苦的原因,也不是这些目标本身,而是我们一旦达成了目标,就又会产生新的不满足,这样的一种躁动感永无休止。书中说:“我们在所贪的对象上造作不休,即便得到了也只是暂时开心,很快也会变得淡漠;得不到时则忧心忡忡,辗转反侧。”这样一种心态,其实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执着”。苦的原因不在于客观的对象,而在于我们的执着。
书中告诉我们,我们经常有一种错误的认知,那就是单纯借助感官的享乐可以不断提升我们的幸福感。于是,很多人将自己投身到物质主义和感官享乐的追逐当中,他们实现幸福的路径,首先是不断地搞钱,然后呢,就把这些挣来的钱投入无尽的消费当中尽情享乐。但是,这样的认知会让我们在执着当中越陷越深。
那你说,这样子不行,那我躺平呢?我佛系一点,是不是就能摆脱执着,摆脱苦了?成庆老师说,现在不少年轻人以佛系、躺平来作为对抗这种不断进取的主流价值观,但是,如果这种佛系、躺平是因为“求不得”而导致的,是因为进取受挫所带来的冷漠和不作为,那实际上还是陷于执着当中。
而且,更矛盾的是,很多时候我们这种消极的反抗和自我疗愈,会重新被消费主义给吸纳到市场逻辑里,比如说,为了缓解都市生活的压力,我们想要回到自然、过上朴素的生活,但这种需求也会被包装为一种商品之后打包销售。用书中的话讲,那就是“佛系”的努力最终又重新被娱乐化和市场化了。
所以,真正的不执着,不是要么追求,要么放弃,而是摆脱这种二元逻辑。倘若我一开始对着某些目标穷追不舍,而一旦心力交瘁,失去希望,就开始否定目标,觉得人生虚无,如此非此即彼的状态,则代表着,我依然被执着所困。
那么,要如何做到不执着呢?书中说,执着源于“无明”所带来的贪爱心。而所谓“无明”,说的是我们对真理的无知。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对真理有足够的认知。
我们常常对美好事物有着一种丧失理智的守护心,比如说我要守住我们的财富,守住我的感情,守住我的容貌,但事实上,这一切都是无常的现象,是不由我们的想法所主宰的。
到这里,我们就引出了佛学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叫“无常”。
什么是“无常”呢?在我们惯常的印象里,“无常”好像是个偏消极的词。当人们遭遇到某些人生变故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感慨一句“人生无常呐”。
但事实上,“无常”只是对这个世界的一种客观描述,它意味着一切都在变化。书中引用了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的一段话,说:“如果樱花常开,我们的生命常在,那么两厢邂逅就不会动人情怀。”他从无常当中看到的,是世间的美好,而不是世界的灰暗。
从佛学的视角来讲,无常就是世界的真相。我们之所以会在遭遇变故的时候才会感慨人生无常,是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心过于粗糙且动荡,所以我们感受不到“表面稳定的生活底下所泛起的涟漪”。
比如说,我们一般会觉得,我们每天的生活是重复的。每天起床,我们都要刷牙洗脸,吃早餐,通勤,上班,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生活单调,也是因为我们日复一日地做着相近的事情,日子就这么周而复始地过下去。
但是,我们的生活真的是重复的吗?比如说刷牙,我们每次刷牙的动作难道都是一样的?再比如说通勤,我们在通勤路上所看到的风景,所遇到的人,难道又都是一样的?
书中提到了一部讲茶道的电影叫做《日日是好日》,里头有句台词,说:“在下雨天听雨,用你的全身来品味这一刻;雨天听雨、雪天看雪。夏天感受夏天的炎热,冬天体验刺骨的寒冷。打开五感,用全身品味这一瞬间,原来这就是‘日日是好日’的意思。”
听雨、看雪,如果我们不用心觉察,就感受不到每次雨雪之间的细微差别。所以书中说:“当我们的心变得专注和细腻,我们才能观察到更多‘无常’;可一旦心变得粗糙与混沌,就像镜头失去了焦距,无法看见细节的变化。”
因此,依照佛学的说法,世界的本质就是“无常”。而我们之所以会产生“世界在‘常’与‘无常’间切换”的错觉,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没能观察到这个真相。如果认知到了“无常”的真相,我们就会发现,在“无常”的世界里执着于“常”,是一件多么荒谬的事情。
既然认识到,这个世界本身就是无常的,于“无常”当中执着于“常”是荒谬的,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跟这种现实和解呢?
可能有人会说,你要是告诉我,这个世界有一些有迹可循的路径,我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地得到我想要的,那我的焦虑感才能够得到缓解。但现在你告诉我,世界无常,别白费劲了,这一点也没有解决我的困惑,反而增加了我的无力感。那我该怎么办呢?
你看,这个问题当中,反复提及的,是“我”。而成庆老师的答案是,除了认知到“无常”之外,我们还要认知到“无我”。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这个无常的世界上,你感受到无力了,感受到痛苦了,那不是你能力的问题,不是你不够优秀,不是你运气不够好,而是你构建了一个并不存在的“我”。正是因为这样,所有的事物,不管是你喜欢的、你讨厌的,还是你无感的,都会跟这个所谓的“我”牢牢地对立起来,这才是今天我们“越努力越痛苦”的最深层原因。
诶,这个“无我”,听起来比前面的“无常”还要远离我们的常识啊。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下面,我们一层层来说。
首先,所谓“无我”,说的是我们不应该抱持着一种我与世界之间相互隔绝、相互对立的观念。
事实上,在传统的精神世界里,所谓的“我”跟今天我们常常说的“我”是很不一样的。今天我们说的“我”,是一个被抽离出来的个体,跟外部的世界泾渭分明。
但是,在传统道家学说当中,有所谓“忘我”的说法;古印度沙门追寻的也是“梵我合一”的境界。这背后其实都是代表着人类精神的某些真实体验。也就是说,他们更能感受到万事万物之间的内在连接。
这并不是什么神秘体验。在书中,成庆老师举了一个我们当代人比较好理解的例子。成庆老师本人是一个古典音乐迷,他经常去听室内音乐会。有一次,他去参加一场音乐会,当巴赫的那首D小调双提琴协奏曲响起时,他瞬间感受到像被电击了一样。他说:“(我感觉)顿时整个音乐厅充盈着和煦的阳光,自己根本无法把控自己,只是感到融入一个无法形容的精神秩序当中,就这样被圆融地包裹着,温暖而感动,虽然流淌着眼泪,却丝毫感受不到任何悲伤。”
通过这个例子,我们会发现,现今我们对所谓“我”的极端个体化的认知其实是有问题的,我们把所谓“我”想象得如此孤立、疏离和呆板,其实是受了当今狭隘的经济假设的影响。
不过,佛学所要讲的“无我”还不止于此。
书中说,后现代哲学一直在挑战的也是“‘自我’是真实存在的”这样一种观念。除此之外,脑科学领域也有类似的看法,脑科学家加扎尼加说过,我们总觉得自己控制着自己的大脑,总觉得有一个小人,一个灵魂,掌控一切,但那只是一个骗局。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能感受到一个真实的“我”,但那是一种幻觉。
为什么这么说呢?试想一下,如果分析人的身体,往深层去观察,我们会发现,我们最终能看到的只不过是基因、蛋白质和粒子而已。那么,这当中有哪一个是生命的本质吗?何者又能代表所谓“我”呢?好像没有。
如果我们从时间上去想,我们的人生不过是无数的时空切片,那哪一个切片是“我”呢?好像每个切片都是,但每个切片都不是,我们找不到那个单一的、不变的、本质的“我”。15岁的我是我,40岁的我也是我,但他们是同一个人吗?是,又不是。
值得注意的是,“无我”并不否定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一连串的身心作用,它所强调的,是没有一个“本质的我”。
成庆老师说,了解了“无我”之后,我们就更能够跟自己和解了。所谓跟自己和解,并不是说你要做成某件事,或者达成什么样的成就之后,才能和解。
事实上,和自我和解的方法,其实就是活在当下。
我们之所以跟自己和解不了,往往就是因为我们心中的执念让我们生出一种鸟瞰人生的视角,用当下的成功或失败去看过去的“我”,或者期待、害怕未来那个可能成功或失败的“我”。书中说:“这个世界,过去已灭,未来还未生,不需要妄造一个可以同时穿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不变的‘我’,去追悔过去,害怕未来。”
到这儿,你会发现,咱刚刚不管是讲“无常”,还是讲“无我”,它们的底色,都不是消极的。
很多时候我们聊到佛学,总会误以为这是一门消极的学问,因为它总在教导我们,一切都是变动不居的,一切都没有它真正的本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佛学否定一切。
佛学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空”。“空”的哲学化的表达就是“无自性”,也就是“无本质”的意思。如果我们说“有”是拥有,是指一种不可抹杀的本质性存在。那么,否定了“有”,不等于说一切都不存在了。如果我们误以为“空”说的是一切都不存在,一切都无意义,那我们就很容易滑向虚无。佛学当中的“空”,是在承认一切事物的存在基础之上,进一步告诉我们,这个存在不是我们心中所认知的那个恒常自洽的存在。
《金刚经》当中还有这样的表述,叫“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句话告诉我们,所有的真实都如梦如幻,所谓的事实,其实也是虚构。但是,与此同时,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讲,所有的虚构其实也是真实,真实的确如梦,但“梦境”也是真实不虚的。
书中说,按照佛学的说法,“这个世界仍然显现出各种生机勃勃的缘起景象,只不过不是我们过去所理解的那种‘硬邦邦’的存在而已。”
这里说的“缘起”,也是佛学当中的一个概念,说的是任何事物彼此都有联系,它们的生灭背后都是有条件在作用的。世间万物依条件而生,又依条件而消亡。
成庆老师说,只有正确理解了“空”,佛学才能具备解忧的效用。如果我们摆脱不了我们习以为常的非此即彼的二元论,那就算道理再通俗,语言再温柔,也只能起到“止痛药”的效果,而无法真正解决烦恼和问题。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思维常常不是掉到这头,就是掉到那头。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思维陷阱。
最典型的,就像咱前面说的,很多人从小就被教育到要非常努力,要非常积极,然后执着追求某个目标,比如说,成为学霸,成为优秀的职场人等等。但是,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这种单一的刺激必然会遇到瓶颈,而一旦无法满足这个想要追求的目标,人的心态就会滑向另一端的黑洞,也就是当事情的发展不如我的预期,不能被我掌控,或者说我的身心不能再承受这一切的时候,就会觉得虚无、断灭、没有意义,把自己的状态甚至人生都全盘否定。
书中说:“二元论思想本质上是一种现代性的精神牢笼。人们在其中拼命冲向一边,碰壁之后又发疯似地撞向另一边。”所以,“空”是什么?“空”不是抹杀和否定,而是洞察与透视,让我们在经验的当下去看清事物的无本质性。
按照佛学的观点,很多在我们二元论视角下看起来很悲伤的事实,就变得不会那么难以接受了。比如说,我们一开始提到的,我们每个人都绕不开的生死问题。
书中说:“如果说佛学能对‘死亡恐惧’或‘死亡焦虑’提出什么样的解决思路,那么就是它从根源上看到‘死亡’这一概念的荒谬,而这种荒谬来自人的巨大的‘无明’。”
我们的死亡焦虑来自哪呢?成庆老师说,其实就来自我们形成的“我执”。我们从“我”这个概念出发,切割出了我们与宇宙、自然之间的界限,并生成一种独立和自洽的生命自我想象。这种“我执”一旦建立,它就会面临一个赤裸裸的真相,那就是在这个无常的世界,“我”是没法永恒的。我们抗拒这个事实,但又无能为力,因此会产生巨大的缺憾感。因为有了这样的观念,所以我们才有了死亡的说法,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死亡的焦虑。
而在当代,我们又似乎很避讳去谈论死亡。我们会利用现代消费社会所提供的便利,不断地通过感官欲望的满足,来转移这种深层的存在焦虑,也就是所谓的“娱乐至死”。但是,我们越想用欲望的伸张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也就是所谓的生,其背面就越显现出对死的畏惧。
那么,佛学又是如何去论述死亡的呢?在《大涅槃经》中,佛陀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说出了他的最后法偈:“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成庆老师说,这就是涅槃最为深层的内涵:“死亡不过是世间的一个生灭现象而已,所谓的生与死,不过是我们的幻觉,一切事物,说到底,也只是缘起缘灭,没有一个崭新的生,也没有一个老旧的死。”
也许,死亡焦虑并非一个人们与生俱来且注定逃脱不了的“魔咒”。
在书中,成庆老师讲述了他曾经参与了一场土家族的丧礼。他清楚地记得,那一天的堂屋里,歌声缭绕,十分热闹,村民手里拿着圆盆,绕着棺材载歌载舞,一派喜乐的气氛。这样一场“另类”的丧礼,让他想起了庄子的“鼓盆而歌”:生命源于自然,又复归自然,生生不息,有何悲苦?
他还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小的时候他曾经得了一场重病,在患病的过程当中,他持续高烧,甚至产生了种种幻觉,比如说看到金色的鲤鱼在身边游来游去。不过,那时候的他好像并没有产生任何对死亡的恐惧,只是感觉到在医院里,针头扎进血管会很痛,那种居高不下的体温会让人感到很难受,但除此之外,他并没有想到死亡,那当然就更不会感到害怕了。他说,回想一下,如果那个时候他自己就因病夭折了,家人可能会因此而痛苦,但他自己却可能只是感觉像玩了一次人生的“快闪”而已。
他还记得,他儿时在老家参与一场葬礼的过程。他记得当时他和小伙伴在旁边嬉戏打闹,完全没有感受到死者和堂屋中摆着那口漆黑的棺材所带来的恐惧感。他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他所感受到的葬礼跟春节时候的家庭聚会一样,没什么差别。
他说,这也许体现的是一种生命最初的直观认知特色,这个世界就是这么运作而已。那个时候,死亡的观念还没有在他的头脑里登堂入室。所以,就更无所谓“死亡焦虑”了。
好,这本《人生解忧》就为你介绍到这儿。
在书的末尾,成庆老师还提醒我们,获得精神的安宁与自由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人生目标,但也是一次危机四伏的心灵冒险,需要我们谨慎前行。他引用了《金刚经》当中的一句重要教导:“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以上就是我为你分享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对书中其他内容还有兴趣,也建议你去阅读原书。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
“无常”只是对这个世界的一种客观描述,它意味着一切都在变化。
-
“无我”并不否定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一连串的身心作用,它所强调的,是没有一个“本质的我”。
-
“空”不是抹杀和否定,而是洞察与透视,让我们在经验的当下去看清事物的无本质性。
-
我们的死亡焦虑来自哪呢?成庆老师说,其实就来自我们形成的“我执”。
-
获得精神的安宁与自由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人生目标,但也是一次危机四伏的心灵冒险,需要我们谨慎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