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央华戏剧&莫言《鳄鱼》·王可然专访:什么是当代人需要的戏剧?
【终版】王可然鳄鱼.MP3
正在进行的话剧《鳄鱼》全国巡演是一起文学、戏剧和音乐交织的文艺事件。
莫言本人在 2022 年春节完稿时,对本剧的期许是“写罢《锦衣》写《鳄鱼》,半生郁闷数行书。莎翁故里曾盟誓,开笔香烧二月初”,以之为平生的重要文学事业。
他选择王可然作为这部戏的导演,由央华戏剧将《鳄鱼》搬上舞台。而王可然在完成戏剧构作后,组建了赵文瑄、张凯丽、邓萃雯、么红这个既理所当然又有些出人意料的演员班底,请著名音乐家、王家卫的合作伙伴梅林茂创作音乐。
除了大师名家的碰撞,我们还会在全国各地的剧院里看见什么?
我为此访问了王可然。
我眼中的王可然至少有两个侧面。一个是从法国驻华大使手中领取法兰西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时的王可然。十几年间,他将央华这个民间戏剧团体带上了国际舞台,被称为“拓展中国戏剧世界格局的领航者”。同时,央华创造了艺术戏剧的市场生存奇迹——本来,我称之为是罕见的,在这次访谈中证实:可以说是唯一的,而且是世界范围内的唯一。那个王可然意气风发,是众人的焦点。
另一个是彷徨、痛苦中的王可然。他在喝彩声中隐入幕后,时常在深夜逼问自己:戏剧有用吗?我做的戏剧能帮助我的观众吗?现在的观众需要看什么样的戏剧?
除了请前一个王可然为你讲述《鳄鱼》是如何搬上舞台的,我也略有不安地请你来听听这后一个王可然。
王可然,央华戏剧创始人、艺术总监
01:44 可然老师为什么选择《鳄鱼》这出戏?
02:45 从戏剧制作人到直接下场做导演
05:42 先来了解下莫言老师的剧作《鳄鱼》
08:06 莫言老师看到这部戏剧时的感受
10:21 每次演出都做了哪些调整?
12:35 这出戏的演员是怎样确定下来的?
18:43 可然老师如何理解《鳄鱼》
25:06 剧作中的女性角色塑造
33:58 “我做的戏剧能帮助到我的观众吗?”
39:07 做戏剧,一定要相信你的“光”
43:41 央华戏剧,可然老师,为什么能成功?
50:09 作为观众,我们该怎样看一部戏剧?
52:58 戏剧的本位究竟是什么?
56:34 接下来还有哪些演出计划?
划重点
-
“鳄鱼”其实是存在于我们体内的某种欲望,人是活在“鳄鱼”里面的。
-
究竟是人被欲望吞噬,还是欲望被人吞噬?
-
对于一部好的戏剧作品,最好的感受方法就是去到剧场里,而不是用语言或文字去描述它。文字和语言的想象力和剧场行动所构建出来的空间感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
舞台剧有一个特点,就是在一致的表达中不断变化。而好的舞台剧就应该给观众这样的想象空间和吸引力。
-
人既容易被欲望控制,也容易被恐惧控制。
-
我们对待爱情的不同观点,实际上都是对待内心欲望的投射。
-
我们看似是被动接受了某种命运,而实际上,很可能是我们自己设计并选择了这样的命运,我们是自己选择成为“鳄鱼”的。
-
“《鳄鱼》是一个我二十多年戏剧从业经历中极其难得碰到的好剧本,是一部具有极其复杂而精妙的‘行动性’的剧作。剧中有一个表面上若有似无,内核却极其强劲深刻的‘主人公’,那便是——光,每一个角色心里都在追着这个‘光’,所有的救赎没有这个‘光’便不可能存在。”——王可然
-
迎着欲望,你就进入黑暗;你恐慌,你不愿意进入黑暗,你可以选择控制,这就是“光”。
-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事情已经到了你需要把它的相对物遥远地悬置起来,你才能够去面对的地步了。
-
我们走一条路也好,甚至是我们经历一个人生阶段也好,仔细去回顾它、理解它,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行动。戏剧只是把它凝练到了一个固定的场域里面,让你在其中能够加倍强烈地感悟自己,你可以把这个行动和自己人生的行动参照起来。这可能就是戏剧能够带给我们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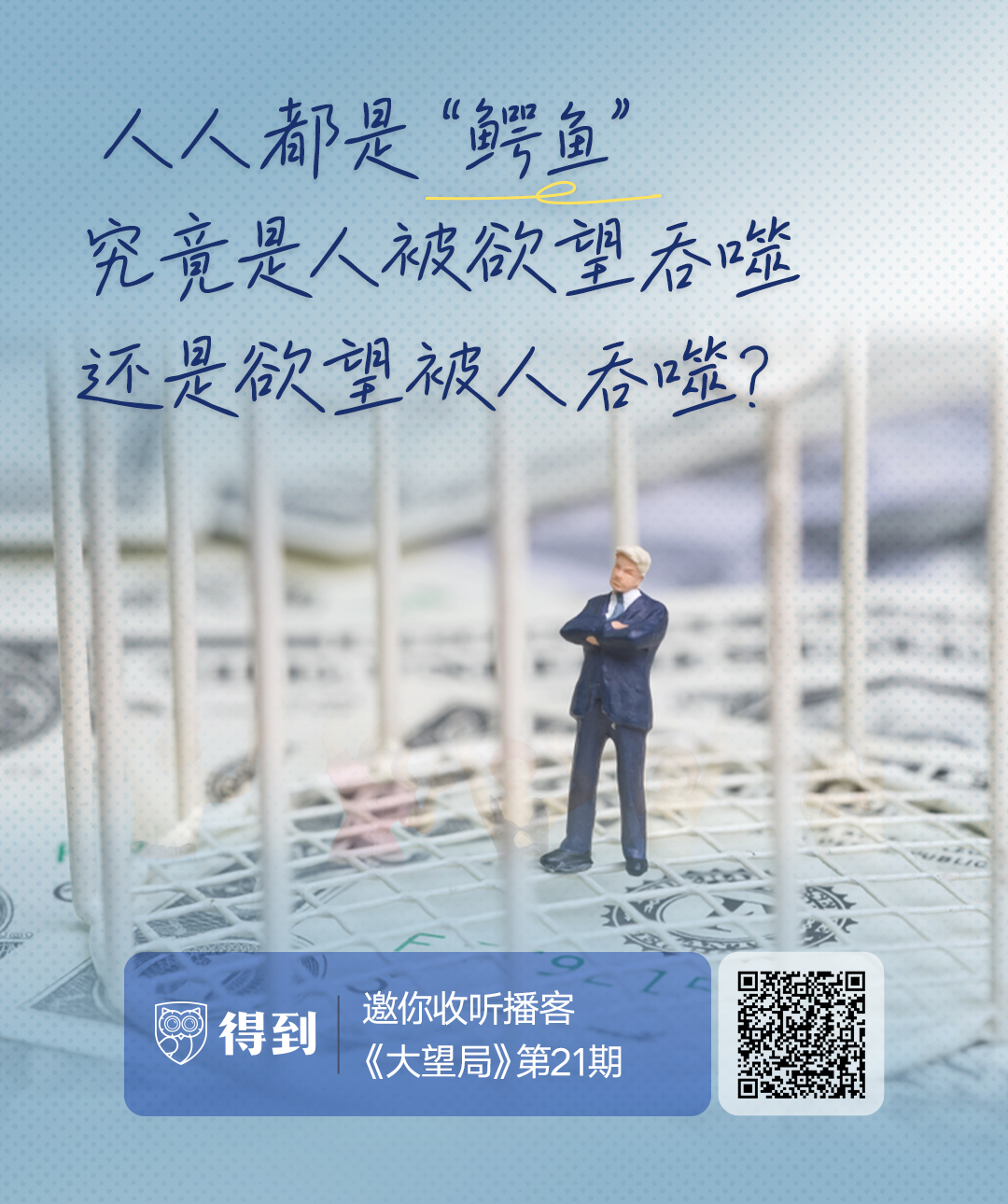
- 为什么说“人人都是鳄鱼”?
王可然:
第二次看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当时在高铁上。我坐在那儿看了一半,我看不下去。我把剧本放在座位上,在高铁的车厢里来回走。我当时感受到就是,这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鳄鱼”,而又那么无能为力,明知自己是鳄鱼,却又一如既往地向着膨胀和毁灭走,让我感觉撕心裂肺。
因为我在很长的人生岁月和时间里,看到的都是“鳄鱼”所带来的破灭感,毁灭人的、不可控的伤心。但是我这里看到了我们的伤的根源是如此形象地体现在这样一个作品里,它尖锐、魔幻、深刻。所以我当时就有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贾行家:
那个时候你也就下决心要把这部戏做出来了。
王可然:
我下决心去跟莫言老师表达我的这种感受,看看能否得到莫言老师的认同。如果认同,那我当然就特别期待自己能去创作这部作品。后来第二天,我和莫言老师沟通了这件事,莫言老师表示认同这个主题,每个人都是“鳄鱼”,而且是我们文化背景下的这种欲望特质。
贾行家:
关于这个意向,我在这给大家稍微做个脱敏。每个人都是“鳄鱼”,这句话听上去很惊人,甚至你可能不太容易接受,但事实上它是一个客观的结果。
你生来是个人,你就带着这样的一个东西来的。我们再回到生物学,提到人脑的进化,人脑最里面的这一层结构和大鳄鱼的脑结构是一样的。它只有吃和繁衍这两种最基本的系统。人类进化了很多年,才进化出一个哺乳动物的脑结构。到这个时候,人类才有一点社会性的功能,摆脱了这个鳄鱼。这也就是为什么说这个意向不是老虎,而是鳄鱼。
再进化了很多年,我们人类才有了文明的一面,我们的前额叶里才有了今天复杂的人性。但是人最里边的东西是割舍不掉的,甚至它是你一切行动的最原始的东西。
所以人人都是“鳄鱼”,这是个事实,你得先认下来。
王可然:
对,人人都是“鳄鱼”,但是你能不能控制它?
贾行家:
包括是一种对恐惧的回应,恐惧这件事情太容易控制我们了。
王可然:
对,你在恐惧什么?它太容易成为我们放大欲望的理由。
贾行家:
其实剧作里的这些人就是“鳄鱼”,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回应恐惧的方式。刚才说到欲望这个概念,我想到就是说鳄鱼它会本能性地逃避,或者说它的攻击也是由恐惧所触发的,而人其实也是这样,人既容易被欲望控制,也容易被恐惧控制,而恐惧本身可能也来自于“生”的欲望。
那你该怎么处理?剧作里的这些人都是聪明人,但是每一个人也都没有处理好这两件事情。
王可然: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人都很难处理好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这个戏并不在于批判某一个人。我们都很难清醒、理智、精准地控制自己的欲望。这是我们很多人生苦恼的源头,我们很多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矛盾往往都源自于我们内心的各类欲望,不节制或是不自知。
包括您刚才说的恐惧。其实人除了恐惧死亡之外,还有很多恐惧啊。我恐惧别人超越自己,你当了优秀分子,我没有当上,这是最简单的例子。还有家庭里的情感纷争,也是源于恐惧自己和别人的关系。
但是这些恐惧,不过是对另外一种愿望、要求的无度。所有这些欲望和恐惧,都是我们从生下来开始渐渐成长起来的,但是当你成长起来之后,又不能够做到对这些成长后的情绪做好管理,或者是做好自我警惕。这些都是“鳄鱼”的寓意和象征。
- 做戏剧,一定要相信你的“光”
贾行家:
我想谈论的是有一个夜晚,那天可然给我打电话,找了几个朋友去吃饭,其实那天已经很晚了,然后我们会认为他有一个很紧急的项目要谈一谈,听听大家的意见,结果发现他没有任何着急的事情。他吃着吃着,突然长叹一声说,你知道为什么要把你们几个找来吗?因为我感到极其的痛苦,我现在不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戏来帮到今天的观众了,我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了。
我那一刻才是真的很感动,一个事业有成的、要为一个组织和文化品牌负责的人,他居然最痛苦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一刻我才觉得,那是一个美丽的北京的夜晚,在一种巨大的空虚感之下,让你看到一个人对戏剧虔诚的夜晚。
那我现在其实要问的就是,你现在觉得如何?你现在知道要做什么来帮助今天的观众了吗?这个《鳄鱼》是你的答案吗?
王可然:
行家,你问的问题好尖锐啊。
贾行家:
因为你看,很多中年人一直在忙,但他们其实没想过我究竟要干什么呢?所以你在那个时候想到这个问题,是一种超越。
王可然:
行家是我的好朋友,那就还是说吧,也没什么可遮掩的。那个时候的想法,在我当时的处境下非常真实,就是生活本身的戏剧性远远高于我们戏剧模拟出来的状态了。
贾行家:
所有写小说的人也经常这样感慨的。
王可然:
问题就是在于,在自己感到非常彷徨的时候,我该从哪里去寻找改变彷徨的支柱呢?我自己找不到。并不是说做戏剧的人他天然就有那种力量。做戏剧的时候应该有更多的敏感,就是你要相信“光”,然后你才愿意把这个“光”放到你的作品中。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你刚才问的我,心里满是苦笑。我的戏剧观是有一点变化的。
贾行家:
什么样的变化?你得先说一下你之前的戏剧观是什么样子。
王可然:
我觉得艺术家和医生是两种同样的职业,一个是灵魂的医生,一个是肉体的医生。可是现在我绝不会再这么堂而皇之地说,做戏剧是做灵魂的医生了。我没这个自信了,或是说我没这个资格了。
做《鳄鱼》这出戏,我是力图把生活中本向的欲望这部分呈现给大家看。如果还有一点“医生”存在的话,那是观众,是每个人自己。我的职责是把莫言老师文本中刻画的如此之深刻的人物戏,用戏剧的行动手段呈现在舞台上,让享受剧场的每一个人看到人性的万千色相,从而去对照自己、感受自己该怎么办。
我现在认为我如果能做到真实地把病人给展现出来就不得了了。能救人的只有他自己或是别人能救,但我没这个资格,甚至以后也不可能有这个资格。以前的我,说好听点是天真,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太狂妄。
贾行家:
我给你打打气啊,可然。我之前也不太了解怎么去思考医学的概念,然后一位医生告诉我,他说医疗的意义就是用治疗手段帮你抵御到你自己的自我修复能力、免疫能力能够重新起作用。医疗不可能从外部给你植入一个东西,人类现在的医疗手段还达不到这个水平。我们都不知道病是怎么来的,我们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好的,我们只是帮你用药顶到你自己的免疫系统重新开始工作。那么你看,要是用这种谦逊的、来自于医学家的说法,戏剧不也可以这样吗?
王可然:
可能别的戏剧家会认为自己可以做到,而我做不到。我觉得我最大的努力就是刻画、模拟万千生命本来的状态,尽量去靠近它,用戏剧的手段把它表达出来,让进入剧场的观众享受以真实为蓝本的梦境。至于未来怎么选择是他们的事情。
贾行家:
那你排练《悲惨世界》,包括这一年多以来你做的几个戏。你自己又做了一个新版的《犹太城》,讲的就是一群即使生命只剩下几个月的人,依然在追寻,像人一样活着,你不觉得那都是在帮助大家去重建“光”的样子吗?包括你在某次发布会上强调“鳄鱼”的时候,你特意去强调“光”,当时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有点迷茫,大家会觉得这个戏难道不是一直在讲黑暗里的人吗?那你在强调这个“光”的时候,你在强调的是什么?
王可然:
我解释一下所谓的“光”。在舞台上我们的光都是行动的,都是对舞台的过程的需求。那个拟人化的“光”没有出来过,但是把让我恐慌的欲望形象化地表达出来给观众看,这是戏剧的责任和职责。而我对于欲望的恐慌,我更愿意把它描述为我在大千生命中走向的抵抗。
迎着欲望,你就进入黑暗;你恐慌,你不愿意进入黑暗,你可以选择控制,这就是“光”。那为什么你会选择控制呢?是因为有一种理性,或者是有另外一种与欲望给你带来的无限享乐背道而驰的东西,它可能是真,可能是善,可能是美。
你是在作品里自然地迎着欲望走,或者是自然地嘲弄自己,还是表现对欲望的抵抗和控制?这个是“光”。
如果没有这个“光”,我觉得就不是我的戏剧。在《鳄鱼》这个作品里,“光”一直在。你看莫言老师写的这些人物最后的毁灭,为什么会毁灭啊?就是因为茫茫的世间里,那道“光”在,他才会写到毁灭。“光”可以说是价值观,这太抽象了,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准则,这就是我的职业准则。
贾行家:
我也看过一些写得很“聪明”的剧,排演的水平也不错。但是我总有那么点遗憾,人家问我遗憾什么,我说我觉得他缺少戏剧应该提供的一种东西。他说那是啥?我说可不可以叫“赞美性”?然后人家就说,你的意思是一定要给你一个光明的结尾,我说不是这样的,比方说我们想给别人传递一个理想、一个超越的观念,它可以有很多种方式,比如我可以在夜里把唯一的路灯敲碎了,让你自己摸索一下,你就会知道光明的缺失是什么,用毁灭光明来证明光明的存在的价值。这就是一种赞美性。
刚才可然说的“光”,就是我们可以在一个剧里看不到一个所谓的高尚的人像,但是你仍然知道它一定要有那样一个东西在,你活着一次、存在一次,才能够获得一个解释。我不敢谈论意义,但才能获得一个解释,而且我们得演这一出戏才会有一个理由,否则的话你就告诉我漆黑到底,这件事情不需要讲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事情已经到了你需要把它的相对物遥远地悬置起来,你才能够去面对的地步了。
而央华的戏剧,我感觉就是这样。大家说央华为什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爆发成为中国戏剧界的首屈一指,既获得了商业成功,又获得戏剧界的肯定。我觉得这个“光”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王可然:
它极其重要,甚至是根本的理由。
贾行家:
央华可以演喜剧,可以演悲剧,可以演残酷的东西,但是每一部戏里他都给你了一个真实的“光”。有些戏剧的“光”做的太虚假了,它就是给了你一个廉价结局。
王可然:
是故作真诚。那个不是“光”,人不会被假的“光”欺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