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子芝麻茶》 杨以赛解读
《豆子芝麻茶》| 杨以赛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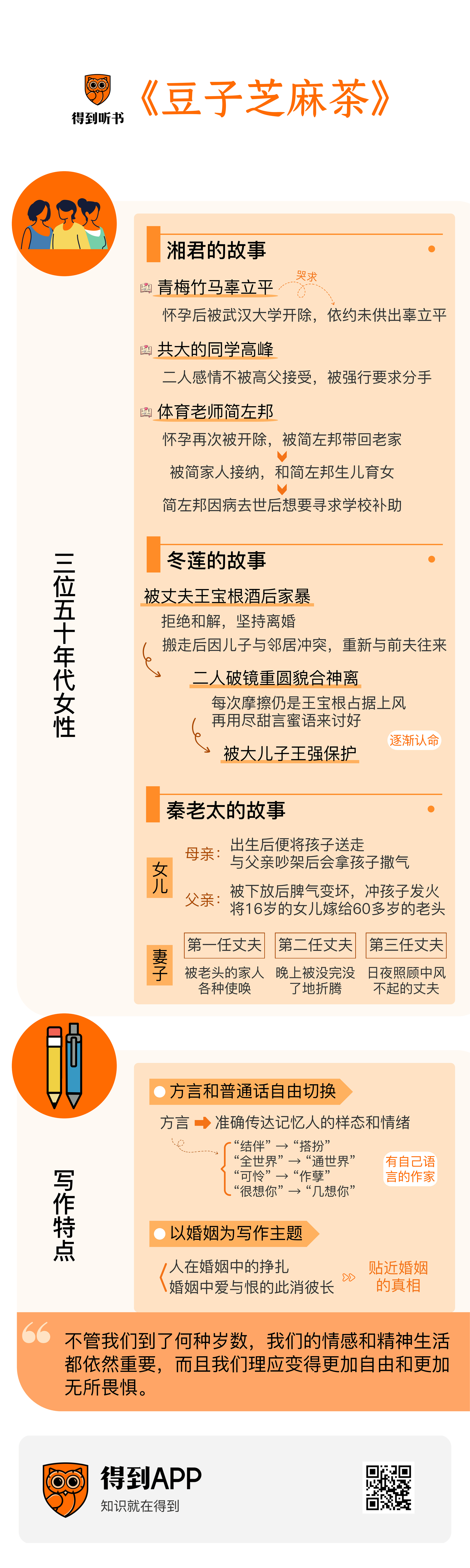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豆子芝麻茶》。这是作家杨本芬在2023年出版的一本小说集。
杨本芬1940年生于湖南湘阴,大半辈子都在一家汽车运输公司工作,没受过任何写作训练,60岁才真正开始写作。2003年杨本芬写下自己母亲的故事,发在了天涯论坛上,意外收获很多关注。但尽管反响很好,却一直没有机会出版,直到2019年,出版人涂志刚看到了这些文字。就这样,杨本芬在80岁这一年,以作家身份出道了。她的第一本书《秋园》在豆瓣被9万多人打出了9.0的高分。之后她每年出一本书,2021年出版了讲述她家人和乡亲故事的《浮木》,这本书荣获“豆瓣2021年度中国文学”。2022年出版讲述自己婚姻故事的《我本芬芳》,继续荣获“豆瓣2022年度中国文学”。《秋园》和《我本芬芳》,“得到听书”此前已经解读过了,今天我们要解读的《豆子芝麻茶》,同样获得了众多好评,荣登了2023年的豆瓣年度图书榜单。
书名里的“豆子芝麻茶”是湘阴人待客时会用到的一款茶,用杨本芬自己的话来说,“湖南人,就算饭不吃,豆子芝麻那是一定要备好的”。她以此为书名,是想说她笔下的人和事就像豆子芝麻茶一样平凡,但也恰恰因为平凡,她想将其打捞记录。这本书收录了3篇小说和两篇散文,3篇小说都写的是和杨本芬同时代的女性,杨本芬在后记中说:“这些女性在现实生活中很容易被忽略,小说家也不怎么留意她们,但我想写她们,她们也是这个天空底下活跃强韧的生命。”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逐一认识一下书中的三位上世纪50年代的女性,她们分别是湘君、冬莲和秦老太。我会一边为你讲述她们的故事,一边分析杨本芬写作的特点和主题。
我们先来听湘君的故事。杨本芬用第一人称写下了这个故事,叙述者“我”显然是她自己的化身,这里我们为了方便叙述,就将文中的“我”称之为芬吧。芬19岁在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读书时认识了湘君,那时候,爱美的女孩子夏天都穿浅色衣服,但湘君只穿深色衣服,这让她浑身上下透着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而且湘君很安静,几乎不主动说话,课间就坐在课桌前自顾自地吹口哨。有时上课了,老师还没进来,教室里吵得不行,湘君就开始吹口哨,她悠扬的口哨能让教室立刻安静下来。
湘君还经常能收到信,一周至少一封,信封上还有“武汉大学”的字样,这让周围的同学羡慕不已,但湘君自己却根本不看,连拆都不拆,随手就扔在了床上。后来芬忍不住问湘君为什么不读信,湘君直接回了一句那你替我念。芬迟疑地接过信,第一句便是“亲爱的妻子”,这让她大吃一惊。写信的人叫辜立平,信中他不断向湘君道歉,他说,“我知道因我要上大学,使我们的爱情结晶夭折了,这是我的罪过,我对不起你,只能等我毕业了,再加倍报答你,让你过上幸福的生活……”
原来,湘君在来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之前,被一所大学开除了,开除原因是怀孕,她怀了辜立平的孩子。她和辜立平是一条街上斜对面的街邻,他俩同岁,小时候经常一起玩,初中高中都在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班,是真正的青梅竹马。所有人都认为他们是顺理成章的一对,包括他们的父母。高中毕业后,两人都去了武汉大学,大一寒假,为了节省路费,两人没有回家,住在了学校。寒假过去,开学三个月后,湘君发现自己怀孕了。当时学校把这作为严重的作风问题,辜立平在湘君面前痛哭流涕,请求湘君不要说出他的名字。湘君按他的要求做了,心中的爱情也随之消失了。之后她被武汉大学开除,想换个环境,就来了江西,入读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共大”,创办于1958年,响应了当时“要把大学办到农村去,办到山上去”的号召。在“共大”,劳动是学生生活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学生们有时会到一个叫做青铜岭的深山砍毛竹。他们先要爬上山,砍倒一根根粗大的毛竹,然后运下山,再扎成竹排,让河水把毛竹运到下游。有一次劳动,班上一个叫做高峰的男生不小心把自己左脚大拇指盖砍掉了三分之一,伤处鲜血淋漓,幸亏带了药箱。湘君帮高峰清洗了创口,敷上了药膏,每天换药的时候,高峰疼得哎哟哎哟叫,湘君这时就会吹起口哨,试图用口哨声帮他平复疼痛。等劳动结束后回到校园,湘君和高峰就谈起了恋爱。
但好景不长,高峰的父亲是镇上的一名官员,对高峰很严格,他完全不能接受自己儿子跟一个比自己大了两岁的女生在一起,强行要两人分手。高峰没有办法,只好与湘君分手了,据说分手当天,湘君凶悍得像一只母豹子,对高峰吼道:“你要听你爸爸的,就滚走吧。”
表面上湘君并未受此事影响,她照常吹着她的口哨,在体育课上飞奔。而这时期,芬也遇到了麻烦。学校要调查全体师生的家庭出身,并以此决定下放农村的师生名单。芬上了名单,大学生活就此止步,她对美好生活的幻想“像肥皂泡一样瞬间破灭了”。正是在这时,她听到了湘君被开除的消息,这次的开除理由是与教师恋爱,但芬没有心思再去找她问个究竟了,挑了一个宿舍没人的时候,拿着一点简单的行李,悄悄离开了这个学校。
再见到湘君是20多年后了。80年代初,芬在一家汽车运输公司的仓库上班,一天同事说有人找她,她出去一看,是一个身条粗壮的农村大妈,辨认了好一会儿才认出是湘君。芬拉起湘君的手,对她说:“你去了哪里,一点消息也没有,晓得我有几想你哦。”
“晓得我有几想你”是湖南方言表述,“几想你”就是“很想你”的意思。普通话和方言自由转换,是杨本芬写作的一个特色。她觉得有些话只有用方言讲出来,才能准确传达出来她记忆中人的样态和情绪。有时候一些方言很难用汉字表述,她也不愿放弃,就凭着音节找最接近的字,组出一个词来,比如她的书里,不说“结伴”,说“搭扮”,不说“全世界”,说“通世界”,不说“可怜”,说“作孽”。正因这一点,挖掘了杨本芬的出版人涂志刚形容她是“有自己语言的作家”。
见到湘君后,芬得知了她这些年的全部经历。湘君在与高峰分手后,十分难过,她把她的难过讲给了体育老师简左邦听,简左邦理解她也同情她,两人逐渐发展出了感情。而湘君当时之所以被开除,是因为她怀上了简左邦的孩子,不过不同于第一次开除时湘君承担了全部责任,这次简左邦主动站出来,承担了所有过错。他带着湘君回了老家。
简左邦父母六十好几了,对湘君很是疼爱,什么活都不让她干。而简左邦为了让湘君过上好日子,披星戴月地耕田、种菜、砍柴,农闲时就去县城搬砖运沙。结婚七个月后,湘君有了女儿,后来她又生了两个儿子,一大家子,八个人吃饭,简左邦的负担更重了。再后来简左邦生病了,家人叫他去看病,他总说歇一歇就好,拖了快一年,他整个人越来越没力气,实在不行了才去看医生,诊断出了肝炎。全家人都慌了,所有钱都用来给他治病,连大女儿出嫁的彩礼钱也立马当成了药钱。但病并没有治好,简左邦的肚子后来肿得“像一个待产的孕妇”。
一日,简左邦精神好一些,他抓着湘君的手说,“湘君,不用怕,已经这样了,就这样吧,人只能顺应形势,我这一生值得,因为我们在一起了,不容易啊。”这之后没多久,简左邦就去世了。湘君说,年轻时的两段分手,让她对感情失去了信心,“那么多的海誓山盟,只是上嘴唇碰下嘴唇的事情”,在终于又重拾起一份感情的时候,却又那么的短暂。简左邦去世后,湘君一人拉扯孩子,两个儿子都很顽劣,只读了初中,毕业后在家务农,她找上芬就是想打听能不能去共大找领导,作为教师遗孀拿一点补助。芬告诉湘君学校早撤销了。湘君不说话,笑起来,笑得让人不知所措。芬接着又问湘君要不要去见一下高峰。这时已是农妇模样的湘君脸上又露出了她昔日的骄傲,她毫不犹豫地说:“不去见了”。
故事就在这里戛然而止了。湘君之后怎么样了,芬自己又怎样了,我们不得而知,初看这个结尾可能会觉得有些随意,但细想或许这样正合乎了这本书“豆子芝麻茶”的题中之义。就着一杯待客的茶,随口讲起一些故人的故事,这些故人来来去去,分别又重逢,因此他们的故事也断断续续,甚至有头无尾。在湘君故事的最后,杨本芬只能暗自感叹一句:“如今又是四十多年过去了,不知湘君是否还在人世。”
杨本芬自己17岁上的中专,从湘阴乡下到岳阳求学,离毕业只3个月,学校倒闭了,找不到工作,她于是又只身跑到江西,入读半工半读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但没读多久,又被下放农村。她在接受“谷雨实验室”的采访时说自己在关键时刻“总是运命不好”。但当在书中回忆求学这段岁月,她回忆的重点却全不是这些,而是几段爱情。这可能也是杨本芬写作一以贯之的一个特点,那些历史和命运固然重要,但她更加关心一个女人的情感,即使这份情感失败了,即使这份情感在多年以后已经被冲刷干净、变得根本不值一提。如果湘君出现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可能只注意到她是一个农妇,但杨本芬要写出这个农妇脸上一闪而过的骄傲,以此提示我们她也曾有过爱情。
好,讲完湘君的故事,接下来我们来讲讲冬莲的故事。冬莲35岁,结了婚,有了家庭,婚姻和家庭是她绕不开的两座大山。
芬第一次见到冬莲,是她来科里报到上班,中等个子,白皮肤,穿得干干净净,“一看就是个很会过日子的人”。她丈夫王宝根也陪她来了。王宝根一米七八的个头,因为当过几年兵,走起路来,昂首挺胸,很有军人风范。他跟大家说自己是个钳工,让大家以后有需要修理的东西,尽管找他,这一番让大家对他印象都很好。
但两个月后的一天,冬莲鼻青脸肿地来上班了,一问是头天晚上王宝根打的。王宝根的两个弟弟来冬莲家了,他们一个月至少来一次,一来就是好几天,而王宝根作为哥哥打肿脸充胖子,总是好吃好喝招待,甚至还借了钱让弟弟带回家去。苦就苦了冬莲,连蔬菜都只能拣最便宜的买。头天晚上,王宝根和弟弟喝了酒,吹完了一番牛,带着一身酒气回房睡觉,一躺下就吐个不停。冬莲一边收拾,一边忍不住抱怨了一句,“喝那么多,喝得去死啊”。就这一句惹火了王宝根,他将冬莲打得滚下了楼梯。冬莲说像这样的挨打多得都数不清了,起初为了两个儿子,她尽量忍着,想将日子安安稳稳过下去,但如今看不行了。这天后,冬莲决定离婚。
王宝根自然不同意,冬莲铁了心,她请了假,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以绝食相逼。几天后,冬莲母亲来了,试图劝和,她跟冬莲说:“这次宝根是真心要改……以前的事就算了,即使离了婚,吃亏的还是女人,更何况有两个儿子,你这年龄大不大,小不小,再找也难。”这样的话,冬莲母亲说过很多次,冬莲又一次听从了母亲。结果很容易想见,王宝根哪里能改掉呢。他很快就又继续喝酒,并继续在酒后家暴冬莲。冬莲只能又提出离婚,这次她终于把王宝根拉到了办事处。两人在离婚手续上签了字,拿到了离婚证,她死死攥着这本本子,心情无比地轻松。
回到家,冬莲跟儿子交代了一切,然后找了辆车子,将自己的东西都打包运走了。刚好单位上有同事调走,腾出来一间旧房子,她便暂时搬了进去。新日子就这样开始了。她上班,买菜做饭给自己吃,闲时和几个朋友打打牌,冬莲说:“都说无债一身轻,我是无老公一身轻。”但这样一身轻的日子,冬莲只过了一年。
第二年,冬莲的小儿子王滔和邻居春面的儿子张亮打闹,张亮不知怎么绊了一跤,哇哇大哭,很快春面拉着张亮来冬莲这里告状。冬莲一边道歉,一边用一根有酒杯口那么粗的棍子狠抽王滔。但尽管如此,两家之间还是有了间隙,不再往来。有一次冬莲早起做饭,发现锅子里被人倒了一盆尿,她很清楚应该是春面家干的,但她不想再惹是非,选择了忍下。可儿子王滔不能忍,一个晚上他冲去春面家里,对着春面的脸一阵挠,在春面的脸上留下一道道口子。春面这下怎么都不肯罢休,最后是王宝根出面,赔了一百元作为医药费和营养费,这才让春面收手作罢。
因为儿子,冬莲和王宝根不得不又来往起来。王宝根开始日日缠着冬莲要复婚,一天很晚了,王宝根不断敲冬莲的门,大声喊着要冬莲原谅,之后一连数日,每晚他都来敲门。冬莲备受困扰,可坚持不搭理他。可王宝根的招数越来越多,让儿子来递信,买菜来冬莲家做饭给她吃,还有一次王宝根拿来一条金项链,执意让冬莲收下。结婚那么多年,冬莲从没有过首饰,她望着项链心软了。她想着王宝根似乎是真的要悔过了,两个人似乎真的还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但与此同时她又想,自己真是鬼迷心窍了,难道受的苦还不够多,难道有了这根项链,就能改变自己命运,就能幸福了。冬莲自己也厘不清自己的想法,但她逐渐和王宝根又走在了一起。
两个人虽然破镜重圆,但貌合神离。每一次的摩擦,还是王宝根占上风,冬莲占下风,王宝根占了上风后,又会用尽甜言蜜语来讨好冬莲。日子就这么循环往复下去,杨本芬写道,“树木绿了黄,黄了又绿,春夏秋冬循环往复,一年四季由你怎么也改变不了”。而冬莲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认命。到大儿子王强长到十六岁,一日王宝根做生意亏了,醉醺醺回家,没和冬莲说几句话,就伸出巴掌准备向冬莲扇去。但这时儿子王强拿着一把菜刀冲上来,他对着王宝根大喊,“从今以后,你再碰我妈半根毫毛,只要我知道了,我就用这把菜刀把你砍得粉身碎骨。”王宝根脸色由红转白,他尴尬一笑,然后回了房,栽倒在床上。而冬莲望着儿子,眼泪流了一脸。故事就结束在冬莲的眼泪上了。她还会做什么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吗,以及生活和命运又还会以怎样的方式套牢这名女性,我们不得而知了。
婚姻是杨本芬写作中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她在她上一本书《我本芬芳》中有讲到自己的婚姻。她是在江西共大读书时,认识了后来的老公章医生。两人很快相恋,很快结婚,有了孩子。章医生不抽烟,不喝酒,不乱花钱,在邻里眼中为人敦厚,在孩子面前是好父亲。可杨本芬觉得他很少体谅和怜惜她,更谈不上理解和爱她。她曾在媒体的采访中提到说,丈夫平生只提过一次她的名字,是在一封家信上写“杨本芬同志”,其余时候他都是以“嘿”和“喂”称呼她。
冬莲的婚姻故事显然要比杨本芬自己的故事心惊胆战得多,但在心惊胆战中,杨本芬依然花了很大的笔墨在写冬莲内心的犹豫、疑惑,以及她的反反复复。她并没有站在一个外人的角度盖棺定论地说这是一段怎样的婚姻,也没有试图指导在这样婚姻中的人到底该如何做。她很坦诚地说,关于婚姻,她自己仍是迷惑的。她一度不满意上本书《我本芬芳》这个书名,就是因为觉得这句话太笃定了,她原来想把这本书叫作《解惑》,想说自己到了八十多岁,好多事仍不明白,仍需要解惑。所以她写婚姻,写的不是简单的失败和成功、幸福与不幸,她写的是人在其中的挣扎,写当中爱与恨的此消彼长,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贴近婚姻的真相。
好,冬莲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位叫作秦老太的女性。相比于湘君和冬莲,秦老太66岁,算得上是一位老年女性了。站在66岁这个节点,她面临怎样的处境,以及又会有怎样的人生感悟呢?
秦老太一年四季风雨无阻在各个小区捡垃圾,芬总是在遛狗的时候遇见她,夏天的时候,她剪着比许多男人还要短的短发,穿花里胡哨又很短的套头汗衫,一弯腰就露出一截背。小区里除了芬没人会和她打招呼或聊天,她也因此对芬格外热情。有一次她还邀请芬去自己的工作室。
她的工作室其实就是一个废弃车库,靠墙码着她剪来的纸壳,一捆一捆码得十分整齐。她的老伴一个月前去世了,秦老太直言死得好。老伴癌症病重,大小便失禁,全靠秦老太服侍,他去世对秦老太来说是一种解脱。秦老太说:“我只要我的小孩答应我一件事,我死了千万不要和老东西埋在一块,我再也不要和男的一起过日子了,哪个都不要。在阳世算脱了身,在阴间千万莫搞在一起。就让我自己过自己的日子,谁我都不麻烦。”
秦老太就此跟芬讲了自己的故事。为了方便叙述,我们将“秦老太”称作“秦”。秦的老家在浙江嘉兴,父亲是家里唯一的男丁,很受重视。父亲读了大学,毕业后分到山东临沂师范学院教书。秦的母亲是父亲的学生,怀孕后不能继续上学,因此一直觉得是女儿耽误了自己前程。秦一出生,母亲便把她送到了其他亲戚这里,几年后才接回来。自秦有记忆起,父亲和母亲便一直在吵架,吵完架的母亲还会把气撒在秦身上,对她一顿打骂。后来父母离了婚,父亲没多久后被划为右派,秦跟随父亲被下放到了安徽一个偏僻村子里。父亲因为下放,脾气变得很坏,在外面对人点头哈腰,回到屋里就总要发一顿火。那时秦经常躺在阁楼楼板上,看灰尘在光柱里飞扬,想了又想,母亲怎么会一生下来就不要我,以及现在我又为什么会在乡下面对一个暴戾的父亲。
到了16岁那一年,秦的父亲开始急着想把秦嫁出去,秦不断恳求父亲别这么做,但父亲只说“不去也要去,去也要去”。没多久就有人把秦带到了一户人家,一进家门,那户人家就使唤秦做饭,之后日日如此。两年后,秦18岁,生下了大女儿,女儿三个月大的时候,她带着女儿逃跑了。杨本芬在书中说:“三月的早晨依然很冷啊!寒风凛冽,像巴掌一样扇在我脸上,我在灰蒙蒙的天空下抱着女儿踽踽独行。后来天大亮了,我站在大路上,天又大又空,自己渺小薄脆,前路不晓得在哪里。”
几经周折,秦去找了自己母亲,但母亲一见是她,就飞快关上了门,连门都没让她进。后来她经人介绍,做了奶妈。一年后她嫁了第二任丈夫。这人看上去很斯文,做事慢慢悠悠的,但住到一起后,本性显出来,晚上总是没完没了折腾秦。忍了两年,秦只能再一次逃跑。
她用自己的一点钱买了张火车票到江西,找自己二姨,但二姨日子过得也不好,她不忍心连累她,于是又在二姨的介绍下,嫁了第三任丈夫。第三任丈夫比秦大了十岁,是个老实人,有工作,对秦还算好,可没多久就得癌了,再过了几年又中风痴呆,卧床不起。秦日日夜夜照顾他,也是在这个时候,她开始出门捡废品。卧床三年后,丈夫走了。秦说,“我这才真正有了自己生活。”
这之后,秦老太早晨睡到几点就几点起来,吃过早饭,有太阳就坐在阳台上晒太阳,阴天或下雨,就窝在沙发上看电视,吃过午饭又睡一觉,吃了晚饭,看看电视,然后洗洗上床。芬有一次问秦老太,你寂寞吗?秦老太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不寂寞。她还随口念出了一首诗: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有一次秦老太邀请芬去她家里坐。她的房子是厂里分的,六十多平方米,家里很杂乱,但唯有阳台扫得一尘不染。杨本芬在书中描述说:“(阳台)前面没有房子挡着,太阳铺开在地面上,白得透明的阳光几乎能用手捧起来。”秦老太最爱在阳台上晒太阳。当天,她走到阳台,突然当着芬的面把上衣脱掉了,让整个上半身裸露在阳光下,然后她用手不断搓弄着身体。芬惊呆了,问秦老太,你不怕被人看见吗。秦老太满脸笑意,显然她一点也不害怕了。
这就是秦老太的故事了。这个故事是书中三个故事中最完整的一个,而且不同于前两个故事的苦涩,这个故事读到最后几乎是令人振奋的。秦老太一无所有,在外人看来她过得堪称悲惨,但她却抵达了某种自由。阳台上脱掉上衣的秦老太,在杨本芬的笔下显得很崇高,她似乎提示出,当一个女性挣脱开女儿、妻子、母亲这些身份,变得只为自己而活的时候,力量是非凡的。
杨本芬是在80多岁的时候写下了秦老太,可能正是她的年龄让她的写作具备了一种洒脱的力量。出版人涂志刚陪伴了杨本芬四本书的出版,他在接受采访时说,眼下杨本芬的写作变得更加自由和无所畏惧了。涂志刚说:“在人生接近终点时,她凝视死亡,一种横扫一切的力量向她迫近,给她带来了自由。”当然,杨本芬本人可能意识不到这些,她只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写。她曾在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时感叹说:原来我写出来的东西这么有深度,我自己感觉不到,我只是想把我看到的事实好好写出来。
好,到这里,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完了。我们再来回顾总结一下。
杨本芬在这本《豆子芝麻茶》中,写下了三位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平凡女性,她们是在爱情中颠沛流离的湘君,在婚姻中不断反复的冬莲,以及一无所有、靠拾荒为生,但却意外收获了自由的秦老太。杨本芬在这本书中延续了她过往写作的特点,借用方言,构造朴素、鲜活,又极具力量的场景和人物。与此同时,她始终关注女性的情感和境遇,书中三位女性的人生受限于时代,她们面前没有今天女性所拥有的选择和机会,但杨本芬仍然写出了她们的坚韧和力量,她用她的写作向我们显示,不管我们到了何种岁数,我们的情感和精神生活都依然重要,而且我们理应变得更加自由和更加无所畏惧。
还必须一提的是,除了这三篇小说,杨本芬还在这本书中用两篇散文悼念了她已经去世的母亲和哥哥,同样写得极为真挚和动人,非常推荐你翻开原书读读看。在后记中,杨本芬还提到,她已经开始了第五本书的写作,这次她将要写一写衰老和疼痛。她说:“写下衰老的滋味和疼痛的感觉,是一种与它们对抗的方式,这又是我不自量力地与命运抗争。这个抗争的结果,人注定是失败的那方,但人的价值、人的意志就体现在这抗争中。我是《老人与海》中的那个渔夫,我最终将穿越我的大海,拖回只剩骨架的大鱼。”我们也期待她接下来的写作。
好,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
杨本芬在这本书中延续了她过往写作的特点,借用方言,构造朴素、鲜活,又极具力量的场景和人物。与此同时,她始终关注女性的情感和境遇。
-
书中三位女性的人生受限于时代,她们面前没有今天女性所拥有的选择和机会,但杨本芬仍然写出了她们的坚韧和力量,她用她的写作向我们显示,不管我们到了何种岁数,我们的情感和精神生活都依然重要,而且我们理应变得更加自由和更加无所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