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斯到来时》 杨以赛解读
《缪斯到来时》| 杨以赛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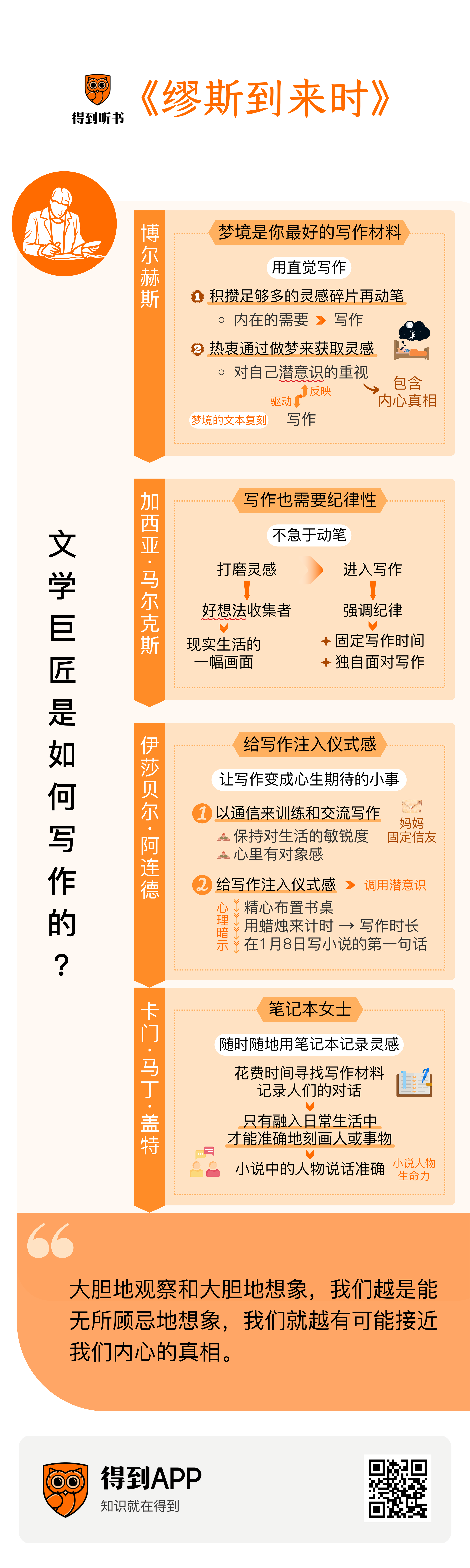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缪斯到来时》,副标题是“文学巨匠是如何写作的”。
很显然,这又是一本教我们如何写作的书。市面上有很多这一类的书,“得到听书”此前也解读过不少了,但今天这本书的不同在于,它重点关注的不是写作理念和技巧,它关注的是文学巨匠们独特的写作流程和写作习惯。理念和技巧,往往得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创作实践才能得以领悟,但流程和习惯,却是我们能够立即尝试,并立马能体会效果的。从这个层面来说,这本《缪斯到来时》或许是一本能让我们立马上手的写作教材。
这本书的作者有两位,一位叫劳尔·克莱马德斯,他在西班牙马拉加大学教授文学及语言类课程,另一位叫安赫尔·埃斯特万,他在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教授美洲文学。这两位作者在这本书中借助采访和扎实的资料梳理,为我们揭开了16位西、葡语文学巨匠的创作历程。你可能会问了,只讲西班牙和拉美的作家会不会存在局限呢?这确实是一个局限,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拉美文学可以说是最天马行空的一类文学,拉美作家可以说是脑洞最大、写作最“飞”的一批作家了,所以向他们学习如何捕捉灵感和管理灵感,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
接下来,我将分四个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我从书中16位文学巨匠中挑选了四位,其中有三位是拉美文学的领军人物:博尔赫斯、马尔克斯,以及伊莎贝尔·阿连德,这三位是谈到拉美文学绕不开的作家。再有一位是西班牙作家卡门·马丁·盖特,她是西班牙语世界很重要的一位作家,中国读者可能对她会比较陌生,但也正因为陌生,才格外值得介绍。此外选择这四位作家还有一个理由是,他们充分展现了写作是一项感性与理性并重的事业,对于如何既挥洒感性又调动理性,他们向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好,话不多说,我们先来看第一位:博尔赫斯。
博尔赫斯是最有声望的拉美作家之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彻曾评价说,博尔赫斯为整整一代拉美文学小说家开创了道路。博尔赫斯生于1899年,他来自一个有着欧洲和美洲血统、具有古老家族传统的家庭。他的祖先是推动阿根廷独立进程的最初的几代人,博尔赫斯钦佩他祖辈的勇气,渴望能过一种战斗的生活,他曾感叹说:“人们都说战争是可怕的,这是肯定的,但生活也是如此,或许死在战场上更好一些。”
博尔赫斯自幼喜欢阅读,整日泡在父亲的图书馆里,他曾说“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大约9岁的时候,他就读完了英文版的《堂·吉诃德》和《一千零一夜》,后者对他影响深远,他尤为喜欢冒险、幻想、神话类的书籍。他的妻子玛丽亚·儿玉说,博尔赫斯不仅是一位优秀的作者,更是一位优秀的读者,“他享受他所读的东西,并且清楚地知道他读的作品是好是坏。他不抄袭任何人的作品,但是他知道有些内容在影响着他。”
15岁的时候,少年博尔赫斯因家庭原因前往日内瓦,在那里他对欧洲文化产生了兴趣,他借助一本字典学会了德语,并由此读了大量的德国表现主义诗歌。这类诗歌打破传统,强调个性与主观表现,以大量的隐喻,描绘最赤裸裸的情感。上世纪20年代初期,欧洲战事结束,博尔赫斯将这些全新的诗歌创作理念带回到阿根廷,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热情》。到30年代初期,他从诗歌转向小说,1935年他出版了《恶棍列传》,之后在40年代他又接连出版了《小径分叉的花园》《虚构集》《阿莱夫》,这三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让他的短篇小说创作达到高峰。1961年,博尔赫斯获得了国际出版家协会的福门托奖,这让他有了国际声誉。与此同时,他眼睛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最后彻底失明。这之后他必须依靠别人帮助来阅读和创作,起初是他的母亲,后来是他的妻子、学生和朋友,他以口述的方式整理出版了一系列稿件。博尔赫斯说:“失明是封闭状态,但也是解放,是有利于创作的孤寂。”同样也由于失明,博尔赫斯从外在世界退出,转而进入深遂的记忆世界,他的作品大多关于记忆,关于一个人在记忆中迷失,又在记忆中重建。
有关博尔赫斯的生平和作品,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得到听书”此前解读过《博尔赫斯大传》与他最负盛名的作品《小径分叉的花园》,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听听看,今天我们会更多聚焦于博尔赫斯的写作过程:他从何寻找灵感,又如何将灵感落到纸面。
博尔赫斯从来不会对着空白的稿纸发愁。有一次,有一位年轻的作家对他说:“老师,我每天早上都感到绝望,因为当我坐下来面对白纸的时候,我什么都写不出来。”博尔赫斯略带讽刺地回了他一句:“那你为什么要坐下来呢?”所以来自博尔赫斯的第一条写作建议就是:任何人都不应该在着手写作的时候等着灵感找上门来,而是应该反过来,得有一种内在的需要,这才会让一个想要写作的人并不感到焦虑,因为他有话要说。
具体怎么做呢?博尔赫斯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写作场所,但他喜欢去咖啡馆和酒馆里把想法写下来。他经常用零星的纸、餐巾纸还有酒店的信笺写作。上世纪30年代末期的时候,他常常会爬到他当时工作的米盖尔·加内图书馆的天台,然后在一个印着小方格的线圈本上写作。后来失明之后,他总是会和朋友、学生聊很长时间的天,他们会给他讲国际报纸上的新闻,如果有什么激发他灵感了,他就会离开一会儿,把灵感的内容记下来。只有当这些碎片的灵感足够多了,用博尔赫斯的话来说是“灵感一再催促你了”,他才会动笔。博尔赫斯的妻子儿玉在接受本书作者采访时说:“(博尔赫斯后期靠口述写作),他口述的方式很特殊,他像一只猫一样全身放松,看起来像是没有骨头一样。他靠在单人沙发上,一条腿搭在扶手上,斜着身子,不断默念重复以进行思考,手指在空中比画着,然后就会开始口述出一首诗。”只有在充分酝酿的情况下,创作才会如此放松,写作才会变得像说话一样容易。
此外,博尔赫斯的另一个写作习惯是,他热衷通过做梦来获取灵感,甚至有些时候他的写作只是忠实地记下他做的一个梦,博尔赫斯说过他很多小说就是他“梦境的文本复刻”。比如他的小说《敌人》,这篇小说就源于他的一个梦,梦里他在一个房子的客厅里,透过窗户看见一个敌人正朝他走来,敌人掏出左轮手枪对着他,说要杀了他,情急之下他意识到只有一个方法可以救此刻的自己,他告诉敌人:“叫醒我”。博尔赫斯醒来后把这个梦迅速地记在了一张纸上,他完全没考虑任何行文上的东西,只要求自己如实记下这个梦,这最终成就了这篇小说。这样的写作过程体现的其实是博尔赫斯对自己潜意识的重视,用潜意识驱动写作,用写作反映潜意识,因为往往潜意识里会包含更多的内心真相。有很多的小说家都曾提到过这一点,比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丽丝·门罗也曾说:“(在写作中)我越努力表达,我就距离真实越远。”所以我们不妨也试着像记日记一样记下自己的梦境,在这个过程中训练自己调动潜意识的能力。正如博尔赫斯提醒说,当我们能够用潜意识写作或者说用直觉写作的时候,我们才能写得更容易,也写得更好。
好,博尔赫斯的写作我们就讲到这儿,我们接下来看另一位大作家,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加西亚·马尔克斯。马尔克斯可能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拉美作家之一了,他1927年出生于哥伦比亚一个叫作阿拉卡塔卡的小镇,一直跟他的外祖父母生活,他的外祖父是一名上校,外祖母则是一个对拉美传统神话非常熟悉的农妇。1947年,马尔克斯考入哥伦比亚国立大学学习法律,但第二年就因为哥伦比亚内战而辍学了,之后他进入报界,成为一名记者。1955年,他担任了《观察家报》驻欧洲记者,也是在这一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小说《枯枝败叶》。
马尔克斯曾说,他是因为海明威坚定了作家梦想。1957年春天的时候,马尔克斯在法国圣米歇尔大街上,远远看到了他一直以来的文学偶像海明威。马尔克斯说他当时想要过去搭个话,但又想到自己英语不行,西班牙语也不行,所以迟迟不敢上前,最后他双手做喇叭状,朝着人行道对面的海明威大喊了一句:“大师——”海明威听见了,他举起手朝马尔克斯喊了一句:“再见——”马克尔斯说他当时一直在记者和作家这两种职业身份之间摇摆不定,但这天的经历使他坚定了他要做一名作家。
在写小说这件事上,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一样,都认为不应该急于动笔。马尔克斯认为他一直扮演着好想法收集者的角色,他把这些想法保存起来,然后反复思索他们的可能性,以及呈现它们的方式,从打磨灵感到写作,这个过程有时候长达十几年。马尔克斯说:“我从来不会对一个没有经受过多年冷落的想法产生兴趣。如果一个想法好到可以忍受《百年孤独》的18年等待,《族长的秋天》的17年,以及《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的30年等待,那我就只好把它写出来了。”
那这些想法来自什么呢?对马尔克斯来说,往往是现实生活中的一幅画面。比如《礼拜二午睡时刻》,这篇被视为他最好的短篇小说,灵感来源于马尔克斯看到了一个女人和一个女孩身着黑衣,在一个酷暑难耐的天气里打着一把黑色的伞走在一个无人的村庄里的画面。《枯枝败叶》这部小说则起源于一个男人带着他的孙子前往墓地的画面。《百年孤独》则要复杂一点,它是马尔克斯童年时期很多个生活场景的集合。要讲述这些童年场景的想法在马尔克斯脑子里盘旋了十几年,但他迟迟没有动笔,一直不断在丰富这个想法,直到1965年1月,他本来要去度假,但路上他突然停下车对他妻子说,“我知道要怎么写了,我要像我外祖母给我讲鬼故事那样,面无表情地讲这些神奇的故事。”然后他折返回家了,他凑了5000美元,决定用这5000美元支撑他闭关写作。他将这本书视为一次冒险,他说,“要么我通过这本书一战成名,要么就彻底完蛋”。18个月后,这本书写出来了,再之后的事我们都知道了,《百年孤独》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引发巨大反响,它甚至重新定义了“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文学流派。
不过,灵感可以慢慢积累,慢慢打磨,但一旦进入写作,马尔克斯认为就该强调纪律了。在写第一本书的时候,马尔克斯总是晚上写作,因为白天他要完成记者的工作,那时候他写得很快,有时一个晚上能写出十页纸的内容。而且他那时在任何地方都能写作,他甚至习惯在周围满是噪音的环境中写作,安静反而会让他分心。但后来他开始全职写作后,他就要求自己规律起来了,他会准时从早上9点写到下午3点。在这一方面他向海明威学习了很多,比如海明威总是站着写作,以及他会把每天的工作进程,也就是写了多少字记录在一张大表格上,以此来督促自己。此外,海明威总是在预感到接下来要写什么的时候就果断停笔,留待第二天再接着写,这样能让自己对第二天的写作有期待,同时又省去了第二天启动写作的时间。马尔克斯还有一点很特别,他觉得在写作的时候,把你想要写的东西讲给身边人听一听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讲述的过程会帮助你理清思路,另一方面是这会帮助发现你写作中的薄弱环节。但马尔克斯愿意讲,却不愿意在写作彻底完成前就给别人看稿,他认为作家必须独自面对写作,过早地让别人参与你的写作,只会让你松懈下来,或者是对你构成干扰。他说:“作家的工作总是在绝对的孤独中完成的,面对着纸张、机器或者电脑,像一个身在大海中的遇难者一般。”
1999年夏天,马尔克斯被诊断出了淋巴癌,大病之后,他开始更有计划地写作。他那时候打算写一套回忆录,计划写六卷,每卷大约400页,他还写了一些短篇和长篇小说,其中一篇讲了一个男人要在写完他最后一篇小说最后一句话时死去的事。2014年,马尔克斯因肺炎在墨西哥城去世。他的一生或许刚好印证了海明威的那句话:“一旦写作变成最主要的嗜好和最大的欢乐,那就只有死亡可以终结它。”
好,说完我们相对熟悉的博尔赫斯和马尔克斯,接下来我们要来给大家介绍两位可能会相对陌生,但又绝对不容忽视的作家。一位叫伊莎贝尔·阿连德,另一位叫卡门·马丁·盖特。
我们先来看伊莎贝尔·阿连德,拉美文学阵营以男作家居多,甚至“魔幻现实主义”很长时间被认为是属于男性的文体,但伊莎贝尔·阿连德打破了这一点。她1942年出生于智利的一个名门世家,她的堂伯父萨尔瓦多·阿连德曾在1970年至1973年间担任智利总统。1973年,智利发生流血政变,伊莎贝尔·阿连德随家人踏上了流亡之路。流亡期间,她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幽灵之家》,这本讲述智利大家族的书被翻译成了几十种语言出版,为阿连德带来了巨大的声誉,文学界开始将她与马尔克斯相提并论。2004年,阿连德入选美国艺术暨文学学会,2010年又获得了智利国家文学奖,她的小说在全世界的销售量超过7700万册,她因此被称为:“最广为人知的西班牙语作家之一”。
阿连德的写作有两个突出的习惯,一个是她以通信来训练和交流写作。阿连德保持通信的习惯很多年了,她的一个固定的信友是她的妈妈。她曾说:“这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我们这样持续了35年,每天清晨我开始给她写信,我打开电脑,梳理前一天发生的事情并将之写下来,一封信就这样诞生了。我知道,即便是我把所有事情都忘了,在智利老家中还有一个柜子,里面保存着35年来我给妈妈的所有信件,或者说我的生活是真实存在的。”写信让她保持对生活的敏锐度,同时写信也让她心里有对象感。她的第一部作品就是在她妈妈的陪伴下完成的,她的妈妈在信件那头充当着她的第一位读者和永远的文学顾问。对阿连德来说,在心里有一个明确的写作对象是很重要的,当你知道你要写给谁看的时候,你的情感和语言自然就会不一样起来。
阿连德的另一个习惯是她喜欢给写作注入一些仪式感。阿连德常说:“我在写小说的时候,人物不是被我创造出来的,他们本就是存在于另一个时空中的生灵,等待着有人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中来。我作为作家只是一个工具,就好比一台收音机,如果我把收音机的波段调到合适的频率,或许那些人物就会现身并向我讲述他们的生活。”这一点和博尔赫斯有些相像,实际就是调用潜意识或直觉写作,博尔赫斯以梦境入手来做这件事,而阿连德则是通过仪式。
阿连德的书桌上总会摆上鲜花和香薰,她的电脑下面会垫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勃罗·聂鲁达的作品全集,以期他能带来灵感。阿连德不用手表,她用蜡烛来计时,一根蜡烛会燃烧六到七个小时,这也就是每天她的写作时长。此外,阿连德还坚持总是在1月8日写她小说的第一句话,因为她的第一本小说《幽灵之家》就是在1月8日开始写的,所以她将1月8日视为她的幸运日期。她说:“那一天我会试着长时间一个人安静地待着,我需要很多时间把我自己从街上的嘈杂声中抽离出来,并从繁杂的生活中整理出头绪。”
这些说起来可能会显得有些迷信,但它本质上都是一种心理暗示,鼓励自己坐下来去面对漫长、艰难且孤独的写作。而且仪式本身也能构成一种纪律性,它让写作融入一套固定的流程之中,让写作变成日常生活中会让你心生期待的小事,也让自己不至于总是面对白纸,无处下手。所以我们或许也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些写作仪式,在仪式中等待灵感上门。
好,伊莎贝尔·阿连德我们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一位西班牙女作家,她叫做卡门·马丁·盖特。马丁·盖特1925年生于西班牙萨拉曼卡,毕业于萨拉曼卡大学哲学与文学系,她1955年发表了自己首部长篇小说《温泉疗养地》,自此走上文学创作道路。这部小说获得了西班牙最有声望的小说奖“希洪咖啡奖”,这之后她写了很多不同类型的小说、剧本和散文,1994年她获得了西班牙“国家文学奖”。她最负盛名的一本小说叫《曼哈顿的小红帽》,这本书出版于1990年,被誉为是“西班牙语世界的《小王子》”,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很畅销。
在《缪斯到来时》这本书中,两位作者称马丁·盖特是“笔记本女士”,因为在她的写作中,笔记本是她最重要的工具。据马丁·盖特的妹妹说,马丁·盖特在离世前还特别叮嘱家人要把她的笔记本带到医院,她是抱着笔记本离开人世的,这是她去向另一个世界的唯一行李。
马丁·盖特喜欢在路上写作,她每天都花很多个小时寻找材料,她到街头、图书馆、咖啡馆,一旦看到什么激发灵感的事物,她就会拿出笔记本记下来。她的笔记本是一些小开本本子,她没有特别的笔记方法,就是想到什么就记什么。有时候一张纸上,最上面是某部长篇小说的开头,往后是某篇短篇小说的笔记,再往后是对某篇报刊文章的摘抄。信息时代到来后,出版社要求作家提交电子文档,马丁·盖特因此买来一台电脑,但她从来没用过,因为她没法带着电脑出门。
马丁·盖特相信只有融入日常生活中,才能准确地刻画人或事物。她曾说:“我的一项挑战是,如何让我笔下的人物说话时显得真实可信。每个人物的个性都不同,说话的方式也该各不相同。”因此马丁·盖特的笔记中有一部分内容就是她在街头、公交车、地铁、咖啡馆听来的各种对话,这让她小说中的人物说话总是很准确,会让你觉得这就该是他说出来的话。马丁·盖特认为小说人物的生命力就来源于此。
在这一点上,前面我们讲到的博尔赫斯也有相同看法,但他还强调了一点:观察不只是用眼睛看、用耳朵听,还得调用自身经验去感受和想象,所以笔记不能只是记下你的所见所闻,还要记下你在那一刻的所思所想。博尔赫斯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一个学生找他签署一份基金申请函,学生说他要写一部加利福尼亚的小说,需要去实地调研。这让博尔赫斯很诧异,他问学生,你为什么不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去想象加利福尼亚呢?你可以从一个物件、一句话,或是一则报纸上的简报去想象加利福尼亚,并由此构造一个故事,这才是小说家能力的体现。
很多写作者会有这样的执念,认为自己必须亲眼所见、亲身体验,或者收集与内容相关的所有素材后,才能开始写作,甚至有很多写作课都会提倡这个方法。但博尔赫斯完全不这样认为,他觉得正是这样的一种执念,让很多小说看起来像是博士论文或历史散文。小说不是复刻体验,而是要创造体验,因此我们要关注和留心日常,但也要练习去挖掘隐藏在日常之下的故事和情感,甚至借助想象超越日常。“幻想”是拉美文学的一大特征,博尔赫斯甚至直接说过他写的就是一种幻想文学,马尔克斯则说“想象反而是发掘现实的最好方法”,所以如果说拉美文学给我们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大胆地观察和大胆地想象,我们越是能无所顾忌地想象,我们就越有可能接近我们内心的真相。
好,到这里,这本书就为你介绍完了,我们再来回顾总结一下。
劳尔·克莱马德斯和安赫尔·埃斯特万两位作者在这本书中为我们揭开了16位西、葡语文学巨匠的写作过程。我们今天讲到了其中四位,这四位作家都有各自独特的写作习惯,但这些习惯的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让自己能灵活调动感性与理性。博尔赫斯极为重视梦境,梦境是他灵感的来源,也是他调动自己潜意识的方法。伊莎贝尔·阿连德则注重仪式,她在仪式中等待笔下的人物主动开口说话,由此开启直觉写作。马尔克斯则强调了写作的纪律性,他以一种近乎苦行的方式写作,认为作家必须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之中,等待茅塞顿开的瞬间。卡门·马丁·盖特也有她的纪律性,她用一个又一个的笔记本捕获和管理她的灵感,绝不放过任何一个转瞬即逝的灵感。
最后必须一提的是,除了这四位作家,书中还介绍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智利著名诗人聂鲁达,他说诗人的职业与船工很像,既要懂得让船随波逐流,但又要懂得随时把握方向。以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他认为重写是写作中最有趣的环节。此外还有拉斐尔·阿尔贝蒂、布埃罗·巴列霍、卡夫雷拉·因凡特等,如果对他们感兴趣的话,可以翻看原书读读看。其实每个作家的创作流程各不相同,这背后是他们不同的创作理念,我们可以不断尝试,在这个过程中寻找适合我们自身自己的一套创作流程。
好,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
理念和技巧,往往得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创作实践才能得以领悟,但流程和习惯,却是我们能够立即尝试,并立马能体会效果的。
-
每个作家的创作流程各不相同,这背后是他们不同的创作理念,我们可以不断尝试,在这个过程中寻找适合我们自身自己的一套创作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