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 黄昱宁工作室解读
《繁花》| 黄昱宁工作室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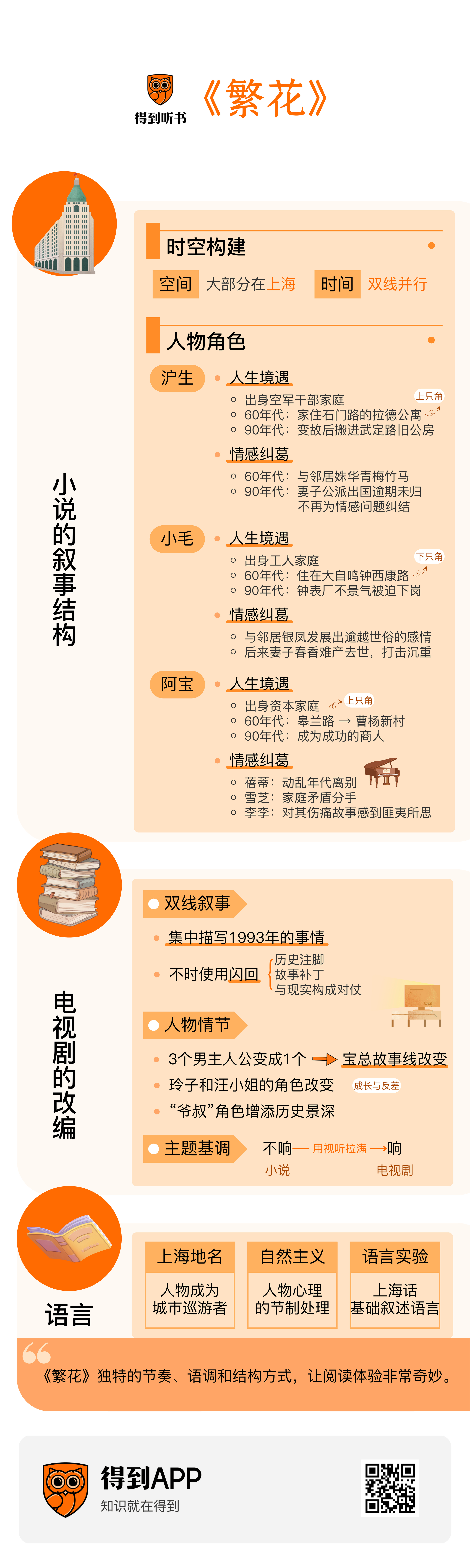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黄昱宁。今天为你解读的是2024年一开年就创造了文化现象的电视剧《繁花》的小说原著《繁花》。
很多人是被屏幕里王家卫的光影游戏深深吸引的,其实,这部电视剧所依托的小说的深厚文学基础更值得我们关注。恰好,我对这部小说有一点“近水楼台”的认知,一方面是因为《繁花》写的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书里写到的一景一物、一草一木都牵动着我数十年的日常生活经验;另一方面,我与小说作者金宇澄老师同在上海文化圈,本职工作也都是编辑,我们不时能在会场、饭桌、剧场和展览馆里碰面,因此我对《繁花》的文本难免平添几分亲切。追完三十集电视剧之后,我趁着余温又重读了小说原著,一边读一边与最近忙忙碌碌的金宇澄老师就小说文本作了一番简短而深入的探讨。我希望能站在一个读者的角度,描述和解读这部小说独特的面貌和气质,说说在我心目中,小说《繁花》的魅力究竟在哪里。
追溯《繁花》这部小说的创作背景,要从十几年前讲起。在2012年之前,上海作家金宇澄的履历表上,主要的轨迹是这样的:上海人,“50后”,青春时代被“上山下乡”的时代洪流带到黑龙江农场,一待就是七年。上世纪70年代回到上海以后,金老师用十来年的时间走上文学道路,发表多篇小说,1988年正式调入《上海文学》编辑部,至今都是这本老牌期刊的主编。
在金老师的多次讲述中,命运的齿轮是在2011年的上海街头开始转动的:一张似曾相识却分明青春已逝的女性的面孔从老金眼前闪过,她正在冬天的黄昏里摆摊。没有戏剧性的相认,老金在沉默中与她擦肩而过,但是那些与这张脸相关的旧时光,触发了他身上的某个开关。那些无名无姓的市井往事,那些无处安放的情绪,似乎唯有写下来,才能纾解。恰巧那时,熟悉的朋友开了一个只有百来个会员的上海话网站“弄堂网”,金老师就用“独上阁楼”的网名,开始了在“弄堂网”上每天连载“网文”的时光。这些文字最终成为长篇小说《繁花》的初稿。
这一段如今被老金形容为“昏睡”的梦幻时光,我当时也是有幸见证的。因为圈里的口口相传,我也到弄堂网里潜水,围观过老金那时文思泉涌、如有神助的状态。对一位彼时已年近六十,以往从未涉足网文的作家而言,网友的“催更”就像台下不时给出热烈反响的观众那样,对他的表演程式乃至“舞台”上的人物塑造甚至情节走向,都产生了直接影响。随着故事的推进,金老师也渐渐意识到他正在写的是一部篇幅不小的小说,所以一边写一边调整,搭建起长篇的结构。即便如此,即便后来真正出版前又经过不少修改,但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繁花》,仍然能在很多细节里读出某些专属于“网络”的特点:那些直击人心的笔触,鲜明而珍贵的表达欲望,以及能让观众产生强烈代入感的氛围。弄堂网的独特属性,也给《繁花》具有浓厚方言特色的表达,提供了合适的平台。
2013年,三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繁花》正式出版,反响远远超过作者的预期,口碑、销量与奖项同时怒放,厚积薄发的老金收获了一路繁花。2015年,小说获得了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荣誉——“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而在这之前,王家卫也已经获得了《繁花》的影视改编权。在我的印象中,中国原创文坛上,像《繁花》这样的现象似乎是绝无仅有的:一位曾经默默无闻,从未写过长篇小说的当代作家,完全从无心插柳开始,创作出一部影响力巨大、成为中国文学当代经典的作品,而这奇迹般的“繁花”效应又在十年之后借着影视的影响进一步放大。
不过,从我这个旁观者的角度看来,面对纷至沓来的荣誉,作者的态度始终是淡定的,充满了阅历积淀之后的大智慧。作为他的读者,我们也不妨静下心来,翻开书本,到文本中寻找答案,让我们依次了解一下小说的故事情节、小说和电视剧的风格有何区别、小说的语言风格以及作者金宇澄要传达给我们什么样的文化信息。
我们先来捋一捋结构,建立一下故事的时空坐标。小说《繁花》的故事空间大部分在上海,书中刻画的场景只有一两次在上海之外,比如几位重要人物曾到江苏常熟旅行,并且发生了影响情节走向的事件。《繁花》的时间要比空间复杂得多,由始至终,都采用双线并行的叙事方式,通过时间顺序把整个文本结构搭建得格外工整。
具体地说,正文部分一共31章,每章分成几个小段落。小说前28章,奇数章节的章节号都用大写的汉字,里面涉及的情节都发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那个特殊时期,人物的命运随动荡的时代载沉载浮,因此情节相对是比较跌宕的;偶数章节的章节号用小写的汉字,故事基本发生在90年代——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定义,这段时间正处在中国,尤其是上海的“改革开放”进入高速发展的时期。从第29到31章,过去与现在渐渐交叠在一起。这末尾三章,连同本书的引子和结尾,都在90年代的语境中展开,最终把这个故事构建完整。从一个身处21世纪的读者的角度看,整本书基本上都是在两个时间段互相交织、互相映射的过程中进行的,总体上的时间跨度从60年代到90年代,跳过了真正发生历史巨变的80年代。也就是说,我们没有看到那些激烈转折发生的进行时态;我们看到的,是转折前的过去时态,和转折后的完成时态。上海的两种时代风貌,在小说中构成了直接的、强烈的对照。
时空构建完整后,我们来看看人物。小说里有三个男主人公,沪生、小毛和阿宝。60年代正值他们的青春期。他们于年少相识,友谊深厚,在小说中各自展开一条情节线,牵出许多故事,而这些故事又往往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而若即若离地交缠在一起。这三个人物的身份显然也是精心选择的,彼此之间形成一定的反差,合并在一起则较为完整地反映出上海不同阶层的日常生活。下面我分别简要地讲述一下这三条线的大致情节。
先说沪生的故事线。
沪生出身于一个空军干部家庭,家住石门路的拉德公寓,这块地方大致属于上海传统上的“上只角”区域。我们想象一下,在60年代的氛围中,这样的家庭出身是具有一定的优势地位的。因此,至少在前半部分的《繁花》中,我们看到的沪生总体上是三个主人公里精神面貌最为积极的。不过,沪生的心地纯正,年少的友情也是真诚实在的。除了有时候会把“我不禁要问”这样具有时代气息的语言挂在嘴上,他和小伙伴们一样对周遭世界充满好奇与同情。沪生与邻居姝华青梅竹马,但姝华在上山下乡潮中去了吉林务农,半年以后来了一封信,这封信在《繁花》出版后触动了无数读者的心弦。姝华说:“我们不必再联系了,年纪越长,越觉得孤独,是正常的,独立出生,独立去死。人和人,无法相通,人间的佳恶情态,已经不值一笑,人生是一次荒凉的旅行。”而此时沪生的人生际遇也发生了逆转,起因是“1971年一架飞机失事”,数年后,牵连到沪生父母,被双双隔离审查。随后,沪生与沪民兄弟两人,被指定搬进了上海武定路的一间旧公房里,与原来的英式公寓,可谓“天地有别”。
在小说中,沪生与姝华后来有一次重逢,那时姝华已经在吉林嫁了人,生了三个孩子,忽然情绪异常,离家出走,回到上海正巧被沪生撞上,沪生把她一路护送到娘家。最终,一份加急电报把姝华催回吉林,于是这场短暂而伤感的重逢戛然而止。到了90年代,已经当上律师的沪生似乎不再为情感问题纠结,他的妻子白萍在1989年公派出国,逾期五年多不归,丈人一家对他格外冷淡,反而让他还清白萍临走时留下的两万多元的借据。沪生还了钱,心如止水。他不再等待妻子归来,却也懒得想办法离婚,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小说结尾。
第二条线的主人公是小毛。
小毛是典型的工人家庭,家里人在上钢八厂上班,60年代住在大自鸣钟西康路,尽管跟沪生家不算很远,但这个位置就属于老上海所谓的“下只角”。关于小毛的居住环境,小说有一段精彩的描述:“老虎窗外,日光铺满黑瓦,附近一带,烟囱冒烟,厂家密布……西面牙膏厂,如果西风,‘留兰香’味道,西北风,三官堂桥造纸厂烂稻草气味刮来,腐臭里带了碱气,辣喉咙的酸气,家家关窗。”
小毛的邻居银凤的丈夫是海员,常年不在家。银凤既深陷孤独,又受到流氓的纠缠,她与小毛渐渐发展出逾越世俗界线的情感,轰轰烈烈一时,却注定惨淡收场。这件事也成为小毛一生的阴影,甚至因为一场与银凤有关的误会,与好朋友沪生和阿宝都断了联络。到了90年代,小毛本来工作的钟表厂不景气,他只能黯然下岗。给他造成更惨痛打击的是妻子春香的难产。在春香弥留之际,“小毛眼看原本多少鲜珑活跳的春香,最后平淡下来,像一张白纸头。此时,苏州河来了一阵风,春香一点一点,飘离了面前的世界。”小毛记得她最后的一句话是:“老公要答应我,不可以忘记自家的老朋友。”然而,当小毛真的有机会再见到少年时的老朋友沪生和阿宝时,他自己也到了病入膏肓之时。在小说的末尾,小说里的主要人物聚拢在他床头,目送他气如游丝、满面冷汗地走向人生的终局。
第三条情节线是阿宝的故事,我会用稍长的篇幅重点讲一讲。
阿宝是小说中相对着墨最多的,也是电视剧在小说的三条主线中唯一借用的原型。沪生和小毛在电视剧里都没有出现,而阿宝的人生轨迹在剧中也有了大刀阔斧的改造。我们不妨来看看小说里的阿宝究竟有什么样的经历。
阿宝的祖父是旧上海的资本家,原先有几家大厂,到50年代公私合营之后赋闲。他把到工商联出头露面的事交给大伯,每月靠定息就足以应付思南路独栋公寓一大家子的开销。阿宝的父亲年轻时投身革命,曾与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当过地下党,蹲过汪伪的监狱,与浙江地主家庭的小姐结婚,60年代这个小家庭居住在同样属于“上只角”的皋兰路,那是他们在解放前就租下的房子。祖父和父亲之间虽然有过决裂,但解放后也互有往来照应。与沪生和小毛相比,阿宝的童年生活条件显然最为精致和优渥。
到了60年代,以阿宝家的情况,当然不可能置身于风暴之外。所有的家族成员都搬出了原来的“好地段”,阿宝在一夜之间住进了上海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在那里,“室外野草蔓生,室内灰尘蜘蛛网”。过惯养尊处优生活的大伯跑来诉苦,落魄颓丧的样子让阿宝一家无言以对,然而,后来落实政策,实施赔偿方案,大伯又第一个跳出来想独揽家产,宣称“房契,产证,名字只许写我一个人”。一时间,家族里鸡飞狗跳,叔伯姑妈都嚷着要打官司。繁花落尽之后,阿宝看到了一地鸡毛。
90年代的阿宝成了宝总,当上了一名看起来颇为成功的商人。不过,小说不像电视剧那样在商战情节上浓墨重彩,书中只是简略提到宝总与外贸公司的汪小姐做过业务。按照沪生的讲法,阿宝“只做正经生意,不考虑越轨投资”,因此小说里的宝总似乎并未介入资本市场,更没有在股市上与“深圳帮”展开惊心动魄的大战。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小说中阿宝的情感经历占据了不少篇幅,也叙述得相当动人,而这些故事主要发生在60年代。
阿宝童年的玩伴是邻居蓓蒂,小说第一章的第一句就是写十岁的阿宝和六岁的蓓蒂从上海老房子的假三层爬上屋顶,眼里是半个卢湾区。蓓蒂的每次出场,或是在和阿宝爬屋顶、看电影,或是听她的保姆绍兴阿婆讲过去的故事,或是与她心爱的钢琴在一起。
在小说中,钢琴显然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它既是动乱年代稀缺、奢侈的艺术品,又与蓓蒂的成长以及蓓蒂阿宝之间朦胧的情感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小说中有一段神来之笔,写蓓蒂的钢琴,像“一匹懂事的高头黑马,稳重,沧桑,旧缎子一样的暗光……蓓蒂小时,马身特别高,发出陌生的气味,大几岁,马就矮一点……待到难得的少女时代,黑马背脊,适合蓓蒂骑骋,也就一两年的状态,刚柔并济,黑琴白裙”,然后作者笔锋一转,说这只是想象,“因为现在,钢琴的位置上,只剩一块空白墙壁,地板留下四条拖痕。阿婆与蓓蒂离开的一刻,钢琴移动僵硬的马蹄,像一匹马一样消失了。地板上四条伤口,深深蹄印,已无法愈合。”
这里说到的蓓蒂和阿婆离开,是突然发生的,原因当然与当时已经混乱不堪的局面有关。有人打着抄家的名义来把琴拖走,可能是拿去卖了。作者在此前的描述中已经暗示了“人琴合一”的意象,琴在,人才在。因此,接踵而至的情节便是人与人的离别。在这里,作者故意偏离写实的轨道,将这一段处理得颇有魔幻色彩:阿宝先是回头,见阿婆为蓓蒂梳头,嘴里念念有词;等阿宝再回头,两道光掠过,闪进水池里。阿宝一揩眼睛,视觉模糊,眼前,只是昏暗房子、树、一辆脚踏车经过,一切如常。几天以后,阿宝收到了姝华的信,告诉他,就是这夜之后,阿婆和蓓蒂失踪,小说没有再交代他们的下落。日后,蓓蒂在阿宝的想象中就成了一条隐入池水中的金鱼。你可以把这看成是一场悲剧,也可以从里面读出任何艰难的岁月里都难以泯灭的对自由与美的向往——而无论是阿宝也好,还是作者也好,对此都不加判断,给予读者广阔的留白。
出现在阿宝生命中的第二段感情是雪芝带来的。书中的雪芝,“苗条身材,梳两根辫子,朝阳格衬衫,文雅曼妙。”她是一个小资本家的女儿,五个哥哥姐姐全部下乡,留她一人在上海过着一体两面的生活:平时还保持着隐秘的大小姐派头,临帖,打棋谱,集邮票;她同时有一份售票员的工作,一卖电车票,就马上换了一副“武腔”,敲台板,摇小红旗子。那时的阿宝在曹杨的集体所有制小企业里当机修工,与雪芝的全民所有制单位之间有一段不小的差距。阿宝开始有点自卑,但雪芝告诉他没有关系。在纷乱扰攘的世界里,两人之间温暖的情愫在慢慢滋长。但乱世并不放过他们。雪芝的这场恋爱触发了家庭矛盾,下乡的哥哥姐姐在外面受苦,听说此事顿时五味杂陈,一致写信反对。阿宝只好不响,恋情无疾而终。
90年代,宝总在生意场上碰到至真园老板娘李李,在推杯换盏中窥探对方坚硬外壳下的累累伤痕。李李不是上海人,当年离开省模特训练班南下到广州、深圳的酒店,先是受到领班压榨,再是被小姐妹陷害,卖到了澳门夜总会,受尽凌辱,直到碰上一位江湖上的“大佬”才逃出生天。这段传奇故事,李李说来字字血泪,阿宝听来匪夷所思。在那一刻,他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有些伤痛是无法用时间抹平的。
在小说的结尾,李李看破红尘,通知宝总见证她的剃度仪式。她的归宿在上海郊区的一家尼姑庵,她说:“一脚跨进庵里,从此天下太平。”宝总为之愕然,却也无可奈何——他知道自己还没到从红尘中解脱的时候。在《繁花》的最后一段,阿宝仍然在这说荒凉也荒凉、说温存也温存的尘世中挣扎:“他接到一个陌生电话,一个女声说,喂喂。阿宝说,我是阿宝。女声说,我雪芝呀。阿宝嗯了一声,回忆涌上心头。阿宝低声说,现在不方便,再讲好吧,再联系。阿宝挂了电话。夜风凉爽,他闷头走路,听见一家超市里,传来黄安《新鸳鸯蝴蝶梦》的悠扬歌声。”
刚才,我们已经把小说《繁花》的情节大致顺了一遍。如果你看过电视剧,一定听得出,小说与电视剧有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小说的双线叙事在电视剧里被精简了一大半,电视剧集中描写的是1993这一年里发生的事情,但故事在行进的过程中不时闪回到更早的时间点:1992年,1990年,1987年,甚至1978年。这样的闪回通常被剪接得很灵动也很细碎,不做刻意的影调区分,时间标志也设置得十分简洁,趋近于无。有时候,它们是历史的注脚,有时候是故事的补丁,有时候又与现实构成对仗。通常意义上的时间线,在王家卫的蒙太奇调度下,成了多个时间切面的重叠,过去、现在和未来互相映射,最终融为一体,营造出某种共时性的幻觉,而这种在时间维度上自由穿梭的感觉,我们也能在小说《繁花》的文本中体会到。可以说,在这一点上,两者有时候是异曲同工的。
第二点,在电视剧中,三个男主人公变成了一个,而宝总的故事线以其商业上的发展为主轴,与小说刻意淡化重大叙事、着力表现日常生活的方式大不相同。相应地,在小说中与宝总几乎无关的玲子和汪小姐,在电视剧中就成了与宝总一起成长的战友和对手,李李的性格也比书中更为杀伐决断——这样的改动使得电视剧里的女性形象更能呼应当下的时代需求。
第三点,在主题基调上,小说是沉着而低回的,对人生和世情的参悟是深刻而通透的,小说中的阿宝、沪生和小毛都在很大程度上承受着时代的重负,两个年代之间的剧烈反差也让其中的很多人物都产生迷惘与失重的感觉——小说对此没有加上任何价值判断,只是不动声色地加以白描,让读者自行体会。而电视剧集中表现的是90年代,透过人物的悲欢离合,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因此基调就显得更为积极和昂扬。
据说王家卫第一次见到金宇澄时,就直截了当地说:“你的小说并没有影视倾向。”金宇澄告诉我,他认为王导这样说是对他的小说风格的表扬。结合《繁花》的结构,我们可以发现,这部小说没有传统意义上那种从头说到尾、起承转合特别清晰的故事,表面上看,它几乎是不可能被影视化的。所以编导常常只能反其道而行之。比方说,原著中出现的一千多个“不响”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在不同的语境下,这个沪语词汇有不同的解释,有时是抗拒,有时是默认,有时是反讽,有时仅仅是节奏上的微妙停顿。对于文字的这种简洁而多变的表现力,电视剧很难用镜头再现。最终,编导做出了果断的决策:把文学最强大的那一面完完整整地保存在小说里,电视剧只取一瓢原浆,另开一桌盛宴——直奔“不响”的反面,把“响”拉满。他们知道,唯有把视听做到极致,才是影像艺术的优势和本分。所以,我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是镜头语言在王家卫的调度之下,“不响”成了“响”,小响成了大响,单薄的响变成讲究而丰富的响,响出了风格化的审美价值。
关于电视剧的这种大幅度的改编,我也请教了金宇澄老师的看法。金老师是在电视剧开播之前一周用三天时间集中看完全剧的。在他看来,蒙太奇的时空拼贴,就好像在一步三回头地讲一个不断生长的故事。游本昌饰演的“爷叔”在小说里是没有的,他刚出场的时候,金老师还以为这也是像孔祥东、陈逸鸣那样的客串角色,没想到这个人物本身就构成了一条坚硬的主线,浓缩了上海的过往,给这部本来在时间维度上特别集中的故事增添了历史景深,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作者原本的意图,让他颇为惊喜。女性角色中,让金老师印象最深的是跟原著截然不同的汪小姐,刚开始的吵吵闹闹和后来的变化与成长形成强烈反差,让人很难忘。
“电视剧有电视剧的语言,”金老师说,“那些频繁的快切,那些特殊的镜头处理,那些强烈的画面,注定会让这片子刚出来的时候广受争论,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它的特别之处啊。就像我们写小说的,一定要找到自己特定的语言,要有自己的辨识度。这片子你一看就知道是王家卫。哪怕抹掉那个名字,透过音乐,透过他的镜头语言,你还是可以找到他。”
这话说出了文艺作品最重要的特质。从我这个读者和观众的角度看,“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辨识度”,确实是王家卫和金宇澄共同的追求。
在今天解读的最后一部分,我们不妨回到《繁花》的小说文本,来稍稍探究一下这部作品独一无二的“语言”和“辨识度”。
我们在概述《繁花》的情节时,已经提请大家注意在小说里出现的大量上海地名。小说里的空间结构不像电视剧那样充满华丽绚烂的色彩,而是深入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的肌理和褶皱,在老式公寓、新式里弄和工人新村的边边角角捕捉细微的样貌和独特的气味。对我这个上海人而言,老金笔下的上海,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魔力。跟着他的人物在我熟悉的地方兜圈子,比如跟着阿宝和雪芝乘上电车从曹家渡到提篮桥,兜了一圈又一圈,身上就像凭空长出一根线来,时不时地,被牵动起某一片神经末梢,于是,皮肤上掠过微微的痒,或者微微的疼。
《繁花》中的人物,常常充当“城市巡游者”的角色。也就是说,在作者笔下,人物在城市里经过的建筑、看到的物件、走过的路线,跟人物本身的悲欢离合和事件的起承转合,享有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地位。用金宇澄自己的说法,“小说就像一座超市,我希望读者进去以后可以随便选取东西,我不会刻意、主动地向你推销什么,那样会把你吓跑。” 这种被作家阿城称作“自然主义”的写法在《繁花》中贯彻得十分彻底,但它又跟西方传统中的“自然主义”有微妙的不同,因为在涉及人物心理时,金宇澄下笔比大部分西方小说都更为节制。在《繁花》中,你几乎看不到阿宝是怎么考虑的,沪生是怎么思索的,你只能透过人物的动作和语言揣摩他们在想什么。在金宇澄看来,中国当代小说的发展基本上跳过了自然主义阶段,直接进入“批判现实主义”,导致这样的“批判”和“现实”整体上过于生硬。于是,金宇澄试图另走一条路,做一个中文小说的新实验。
实验的内容之一,就是使用极具地方特色的语言来叙述《繁花》。这种语言以上海话的词汇和句式为基础,同时又要保证将许多上海人只能说、不会写的字“翻译”成其他地方的人都能看懂的文字。这样一来,你可以用眼睛看懂《繁花》,但如果想把它朗读出来,就只能用上海方言。在读这样一部小说时,我很庆幸自己是上海人。当我把作者精心挑选的汉字一一还原成沪语的音调时,上海市井的强韧活力,那些不会被时代变迁摧毁的声音,就活灵活现地浮现在我的耳边。就像金宇澄说的那样:“我写的是上海的市民阶层,那些被人忽视的上海的声音,最终组成了这样一部小说。”
在今天解读的最后,我想特别说明一点。
这一次重读《繁花》,最让我着迷的是这部小说特殊的节奏、语调和结构方式。《繁花》里充满各色人物的对话,但是一般小说和戏剧里的对话功能不外乎塑造人物、推动情节发展,常常通过对话刻意凸显人物不同的性格和背景。但《繁花》的人物,大部分是淡化这种区别的。所有对话都如流水般融为一体,分不大清是你说的还是我说的。而且,大部分对话其实都是在讲故事。人物讲自己的故事、别人的故事、听来的故事,两个以上的讲述者你一言我一语地互相补充,共同把故事构建完整。所以有人说看《繁花》,就好像看一万个故事同时进行。这话不算太夸张。多少人的生死,多少惊心动魄的瞬间,就潜入这些故事深处,一不小心就会滑过去。这种阅读体验是非常奇妙的。别的小说有一个或者几个叙述视角,《繁花》凭借这种方式获得了几十个、上百个叙述视角——人人都是叙述者,同时人人都活在别人讲述的故事中。当我把这感受与老金交流时,老金不响。良久,他说:“小说再也不只是大树了,它也可以是一丛丛灌木。密密麻麻,短小的,连在一起的,分开的,它们同样有强健的生命力。”
《繁花》的语言魅力,是需要通过朗读来传达与感受的。最后就请你听听上海广播电视台的播音员,为你用“沪语”朗读的《繁花》小说“引子”中最精彩的那段文字。
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阿飞正传》结尾,梁朝伟骑马觅马,英雄暗老,电灯下面数钞票,数清一沓,放进西装内袋,再数一沓,拿出一副扑克牌,捻开细看,再摸出一副。接下来梳头,三七分头,对镜子梳齐,全身笔挺,骨子里疏慢,最后,关灯。否极泰来,这半分钟,是上海味道。
如果不相信,头伸出老虎窗,啊夜,层层叠叠屋顶,“本滩”的哭腔,霓虹养眼,骨碌碌转光珠,软红十丈,万花如海。六十年代广播,是纶音玉诏,奉命维谨,澹雅胜繁华,之后再现“市光”的上海夜,风里一丝丝苏州河潮气,咸菜大汤黄鱼味道,氤氲四缭,听到音乐里反复一句女声,和你一起去巴黎呀一起去巴黎呀去巴黎呀。对面有了新房客了,窗口挂的小衣裳,眼生的,黑瓦片上面,几支白翅膀飘动。
八十年代,上海人聪明,新开小饭店,挖地三尺,店面多一层,阁楼延伸。这个阶段,乍浦路黄河路等等,常见这类两层结构,进贤路也是一样,进店不便抬头,栏杆里几条玉腿,或丰子恺所谓“肉腿”高悬,听得见楼上讲张,加上通风不良的油镬气,男人觉得莺声燕语,吃酒就无心思。
古罗马诗人有言,不亵则不能使人欢笑。
好,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
有人说看《繁花》,就好像看一万个故事同时进行。多少人的生死,多少惊心动魄的瞬间,潜入这些故事深处,一不小心就会滑过去。这种阅读体验是非常奇妙的。
-
小说《繁花》的故事空间大部分在上海,《繁花》的时间要比空间复杂得多,由始至终,都采用双线并行的叙事方式,通过时间顺序把整个文本结构搭建得格外工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