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鱼》 杨以赛解读
《猫鱼》|杨以赛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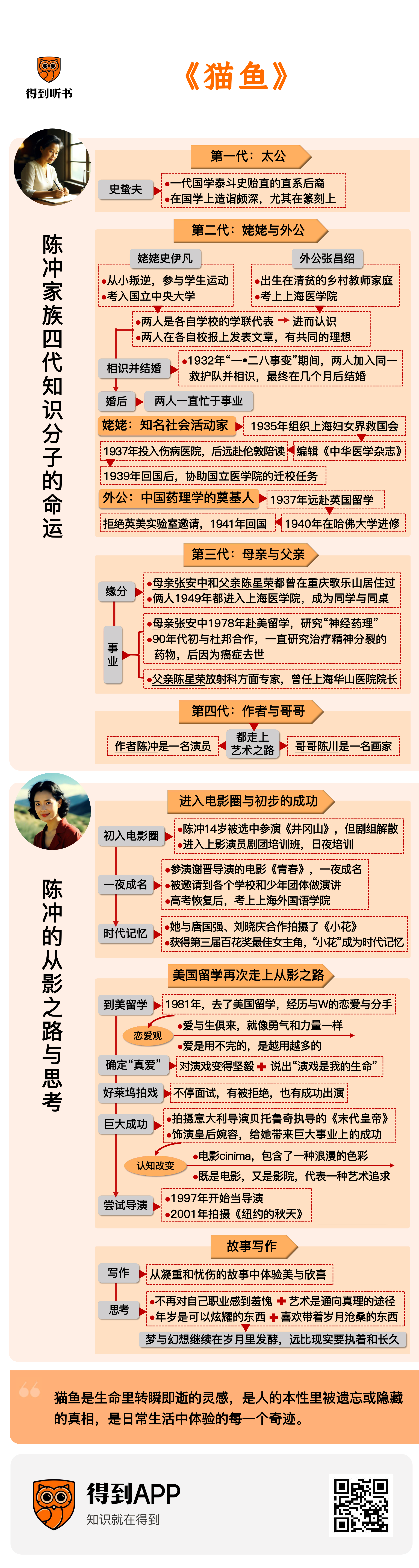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猫鱼》,这是电影人陈冲的一本自传体散文集。
陈冲是著名的演员、导演,主演过一代人时代记忆的电影《小花》,以及拿下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的《末代皇帝》。她出生在一个上海知识分子家庭,偶然走上电影的道路,她在上世纪70年代凭借小花一角获百花奖最佳女主角,80年代赴美,闯荡好莱坞,她是少有的在中美两国的电影产业中都留下经典角色的演员。她能写、能演、能导,不仅拿过最佳女演员奖项,还拿过最佳剧本,以及也是第一个执导好莱坞A级大制作的华人女导演。
《猫鱼》是陈冲的第一本书,但第一本书就入选了2024豆瓣年度图书。在这本书中,陈冲回望她祖辈的命运,写下了一个由四代知识分子组成的家庭故事,作家金宇澄称陈冲笔下这几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填补了文学上海的叙事空白”。她还回顾了她的职业生涯,讲述一部部电影的幕后故事,并从中叩问艺术的本质,但这些都只是这本书的一部分。这本书叫《猫鱼》,“猫鱼”是一种菜场里出售的实该漏网的小鱼,上海人家会买来喂猫。有一年冬天陈冲的哥哥拿回家一条这样的小鱼,但不忍心将它喂猫,找个大碗养着了,可没过多久碗里的水结成冰,鱼成了冰中的化石,但傍晚时候冰化了,这条小鱼竟然还活着,像一个奇迹一般生动如初。陈冲说,“猫鱼是生命里转瞬即逝的灵感,是人的本性里被遗忘或隐藏的真相,是日常生活中体验的每一个奇迹”,“猫鱼”提醒我们,有些东西并不会随岁月流逝,相反它会在岁月的打磨下更显光亮、纯净,充满生命的气息。
接下来,我会分两个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第一部分我们来讲述陈冲的家庭,回望四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命运。第二部分我们来讲陈冲的从影之路,她对于电影艺术,以及对于自我和人生有怎样的思考?
陈冲从小跟姥姥(外婆)长大,她姥姥原名史人范,1908年生于江苏,长大后她觉得为人模范太累,于是自己改名为史伊凡。姥姥的父亲史蛰夫是一代国学泰斗史贻直的直系后裔,史蛰夫同样在国学上造诣颇深,尤其在篆刻上,瞿秋白就曾追随他学习篆刻,是他的得意门生。史蛰夫治家严厉,但陈冲讲姥姥史伊凡从小叛逆,1922年入苏州女子师范,卷入学生运动,高举反封建旗帜,曾三次在报上宣告与父亲脱离父女关系。1926年史伊凡从苏州出走,投奔北伐,被分配到国民党总政治部秘书长王昆仑手下办事,但因感到国民党内部风气不正,就离开了,1927年考入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文学院,也就是后来的国立中央大学。
1930年,陈冲的姥姥作为学联代表认识了上海医学院的学联代表张昌绍,这个人后来成为陈冲的外公。陈冲在书中考据式地回顾了她外公和姥姥在相识前的经历,当外公在他学校的校报上发表《平民教育与平民生计在今日孰为重要》的时候,姥姥则在她学校的校报上发表了《群众运动之动机》,陈冲写道:“这两位素不相识的少年,在同时感受和思考着时代与自身所带来的困境,寻找着更理想的生存方式,向往着更正义与平等的社会。”1928年两人分别赴南京上学,其间并无交集,直到1932年“一·二八事变”,两人都报名参加了上海医学院组织的第四救护队,他们就此相识,先是前线救援队的战友,而后成为恋人,“一·二八事变”几个月后,两人结婚了。
陈冲的外公张昌绍是中国药理学的奠基人,1937年他以全中国庚款留学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赴英国留学,先在伦敦大学,后又赴牛津大学进修,1939年他获得医学博士与哲学博士学位,1940年他又赴哈佛大学进修,当时有不少英美实验室邀请他担任要职,但他毅然在1941年回国。他颇具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风范,渊博,同时刻苦。陈冲在书中提到,她的外公出生在一个清贫的乡村教师家庭,他的气质和人格完全来自他不断地学习和提高。他一生自学了好几门外语,大学期间掌握了英文和日文,毕业后自学德文和法文,1950年代又自学俄文,组织翻译了苏联的药理学专著。逝世之后,家人还在他的床头柜里发现了意大利文的笔记。
有了家庭后,无论是外公,还是姥姥,都没有放下自己的志向。陈冲在书中讲到,1935年北京发生一·二九学运,当时怀着身孕的姥姥与史良等人组织了上海妇女界救国会,后发展为中华救国会。生下陈冲二姨后,她把婴儿留在了上海红十字会,立马投入《中华医学杂志》的编辑工作中。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她又全身心投入伤兵医院。年底战事失败,她丢下两个孩子,远赴伦敦陪读,陈冲直言,这件事给她的母亲和二姨带来了久远的心理阴影。1939年回国后,她仍未回到孩子身边,又马不停蹄协助国立医学院的迁校任务,他们经轮船和铁路迁至云南昆明郊区,后又跋山涉水前往重庆。
陈冲在书中讲起当年姥姥陪她一起读《简·爱》,《简·爱》中有一段写道:“我没有办法,我的个性中有一种骚动不安的东西,有时它搅得我很痛苦……一般人都认为女人应当平平静静,但女人跟男人一样的有感觉。她们需要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且也像兄弟们一样需要有用武之地。”陈冲说她能想象姥姥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个女人,“她一定也向往去发现外面更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完善和证实自己,并从中找到生存的意义”,于是她做了选择,这个选择有其代价,那就是她成了女儿眼中失败的母亲。但陈冲说,姥姥绝非不爱自己的女儿。她向来不重视物质财富,家里传下来的钻戒和图章,她一时高兴就会转手送人,但两封女儿写给她的信,她却一直用心保存着,跟着她到伦敦、到云南、到缅甸、到重庆,再到上海。信上的内容很普通,写的是:“妈妈大人,我接到你的信,心里很快乐,我身体很好,现在胖多了,脸色也红了,晚上不踢被子了。”
陈冲母亲张安中生于1933年,10岁那年她终于与母亲团聚,一家住进重庆歌乐山一间竹篾糊泥巴的房子。在战争的大后方,他们过了几年艰苦的日子,但精神上却很充实。当时陈冲外公日日等待那些从国外寄来的书籍包裹,一到手便迫不及待阅读,在这样的条件下写出了当时国内十分稀缺的医学书籍,并在国外著名的科学杂志上发布了不少论文。而陈冲母亲入读英国教会办的圣光中学,她跟同学读书,唱歌,上树下河,有时也得躲日本飞机的轰炸,她们有句口号:“一个灯笼不用跑,两个灯笼慢慢跑,三个灯笼飞快跑。”也是那几年,一个叫作陈星荣的男孩举家迁至歌乐山,但当时他并不知道这里有一个叫张安中的上海女孩,他也不知道他们后来会结识,成为夫妻,并生下女儿陈冲。
陈星荣家中都是医生,他父亲,也就是陈冲的爷爷毕业于湘雅医学院,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重庆宽仁医院的外科主任。而陈星荣先是考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1949年后,又重新考至上海医学院。这一年,陈冲母亲张安中随家里迁回上海,随后也入读上海医学院。陈星荣和张安中在这里成为同班同学,还分在同一个八人自习小组,坐在了同一个桌角。陈冲在书中写道:“岁月的后镜仿佛一台神奇的织布机,千丝万缕地为我编织出两个人命运的图案——错综、美丽、不可思议。细想想,人的存在真是十分偶然的奇迹,你的父母如果没有遇见,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你了。”
1978年,陈冲母亲张安中参加了派遣出国留学考试,医学界一共录取了三位,她是其中一位。陈冲外公张昌绍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提出吗啡在脑内作用的高度选择性,很可能是针对某种高度选择性、专一性的细胞组织的作用,并预测那将是药物作用原理的核心。十年后,西方科学家发现了内源性吗啡受体,验证了张昌绍的预测,而这时张昌绍已经自杀去世了。张安中接过了父亲的班,继续研究神经药理,陈冲在书中说留学资格对母亲意义重大,她在时代和环境中失去和消耗了太多,包括亲人、年华、机会,这一刻她终于有希望去继承她父亲“未酬的壮志”。
张安中后来去了位于纽约的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进修。陈冲回忆,母亲有一度在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做研究。这家医院在南北战争时期曾是军队的医院和墓地,最高峰的时候,这里有八千多个精神病人。陈冲母亲在的1981年,刺杀里根总统的约翰·辛克利就关在这里。陈冲在书中写道:“走廊上偶尔会有穿着束缚衣的病人,被高大的男性护士领着走过,夜里偶尔会传来病人野兽般的叫喊,令人毛骨悚然”,而母亲全身心沉浸在工作和学习中。陈冲还提及在圣诞长假前的一晚,母亲请了实验室的同事,在医院走廊里开晚会,他们吃比萨,喝饮料,听当时风靡一时的摇滚歌曲《中国女孩》,有人还带来一只迪斯科舞灯挂了起来,所有人在五颜六色的炫光里跳舞。
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张安中应邀与杜邦公司合作,研究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这成为她后半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陈冲记得有一天,母亲带着她所有的行李出现在她洛杉矶的家中,那时她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可能就源于工作压力。她对这款药物寄予很大希望,一次次尝试,一次次失败,一直到她去世,这款药物也没能制成。在去世前,她坦然地跟陈冲说:“科学虽然是掌握知识最好的工具和途径,但它只能发现自然规律,不能改变自然的规律。”
研究了一辈子的神经药理,张安中在人生的最后几年却对自己的大脑毫无办法,她患癌,失忆,她向陈冲感叹:“我的脑子要比我的心脏先走了。”2021年12月,张安中在上海去世,陈冲没能赶到,她写道:“此生第一个爱我的人,也是我第一个爱的人在水深火热中受难,我却没有在她身边,人怎么可能从这样的遗憾中走出来。”陈冲在书中深情地怀念了母亲,她说:“英语里的bereavement——丧亲之痛——是一个词,也意味着一段无法绕过的时间,也许我写母亲的故事是为了度过它;也许悲伤是黑镜中的美,看到了美,就能瞥见更深远的东西。”
陈冲所记述的这个由四代知识分子组成的家庭,每一个名字其实都如雷贯耳,太公史蛰夫是国学泰斗,外公张昌绍是中国药理学奠基人,外婆史伊凡是知名社会活动家,母亲张安中是著名的神经药理学家,培养了一批著名学者,父亲陈星荣是放射科方面专家,曾任上海华山医院院长,这当中每一个人都能连通海量的家国历史。但在陈冲的写作中,这些被一笔带过了,她似乎更注重打捞这些人生命中的一刻,尤其这一刻中的情感。这似乎是陈冲独特的体悟人生的方式,她在一个对谈活动中讲道:“我觉得可能记忆是一个个碎片的画面。你们闭上眼睛,想一个遥远的事情,肯定是一个个记忆的碎片,然后从碎片当中寻找到某一场景。这本书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回忆录,它是我对记忆的模样的一种寻找,我想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什么形状的,什么滋味的。”
所以她写她姥姥,她尤为要写下的是当年她从美国回国探亲,别人从美国回家,都要带一台电视机或者冰箱什么的,她问姥姥要什么,姥姥请她买“一个有波浪的假发套,一个前扣式文胸,一支眉笔和一块羊奶芝士”,等她把这些东西一件一件递到姥姥手上的时候,“(姥姥)笑得眼睛眯起来,好像所有的贪婪都得到了满足”。她写外公,她来到外公曾待过的一栋老楼,她想象外公在楼上楼下忙着倒痰盂、扫地、搓棉签,夜里回到带老虎窗的阁楼里刻苦学习中学课程,她说这里承载了一个少年无尽的辛劳、激情和梦想,离别的时候她依依不舍,她写道:“离开了这个少年的影子,像一个母亲永别了她的孩子。”她写母亲在病中的呓语,写父亲因为她没赶上母亲的临终而责怪她,她说:“父亲的悲哀是一座无声的孤岛,令我为他心痛,但是我与他都没有能力跨越这道无形的深渊,去抚慰对方。”
陈冲打捞的这些记忆是美的、深情的,同时又是复杂的,甚至也有残忍的部分,相比于其他的回忆录,它显得没有那么具象,像是一幅幅细腻敏感的抽象画。但这可能正是陈冲的目的所在,也是她作为写作者的天赋所在,她在采访中说:有形的东西会消逝,比如一张相片会褪色开裂,但无形的东西可能反倒是无限的,“把整个人生的画面变成一种无形的东西,让它无限,我觉得回望的意义正在于此”。
出生在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但陈冲和她的哥哥却相继都走上了艺术的道路,哥哥陈川是一名画家,而她成了一名演员。在多个媒体采访中,陈冲都坦言,在家庭的影响下,她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觉得演戏是一个正当职业,她甚至为此常常觉得自己浅薄无知。但到今天,她已经作为一名电影人工作了半个世纪之久,这个她曾经认为的“青春饭”成了她毕生的事业,也是她由衷热爱的事业。在《猫鱼》中,她也回顾了自己的从影生涯,接下来我们来讲讲她的电影之路。
陈冲参与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是《井冈山》,那时她14岁,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导演来她爷爷奶奶家吃饭,有了这一面的几天后,这位导演通知陈冲来上影厂面试。陈冲去了,就这样被选中去演电影《井冈山》里的小游击队员。摄制组去学校借调她的时候,还顺便看了他们班上其他女孩子,陈冲说她突然感觉到了威胁,她写道:“那时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个职业给我造成的自卑感。我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是伪劣品……回头看,我一生的努力都是企图把自己从伪劣品变成真货。”
《井冈山》后来没能拍下去,剧组解散了,但陈冲由此又有了机会去上影演员剧团培训班,她和18个男生、6个女生一起进了剧团,开始日日夜夜的培训。当年来教他们的老师都是曾经光彩夺目的明星,但当年陈冲毫无概念,只觉得他们是一群无所事事的老人。陈冲记得有一次剧团排演节目,无论男女老少一律画上红脸蛋、红嘴唇,当时有一位叫孙栋光的演员看见她,拿油彩笔给她画了一条乌黑的眼线,还教她,要画得贴近睫毛,越近越好,这样的一条眼线在1970年代的中国是很前卫的。陈冲后来才知道这位演员的父亲叫孙瑜,1920年代留学美国,翻译过杰克伦敦的小说,是中国最杰出的导演和编剧之一。陈冲意识到,孙栋光一定是从他父亲那里耳濡目染到了这样的审美感觉。
1976年,谢晋导演邀请陈冲主演他的电影《青春》,陈冲因为这部电影一夜成名。她在书中讲说那个年代拍戏周期长,一部电影可以拍上十个月一年,因此有足够的时间去体验生活和排练。拍摄《青春》的时候,她害怕谢晋导演,总觉得他会在开拍前觉悟过来,发现她不可调教,然后换掉她。《青春》上映后,她被邀请到各个学校和少年团体做讲座,这让父母非常担忧。那一年,刚好高考恢复,家里让她必须复习功课,参加高考,母亲想让她学医,甚至直接问她:“你想做电影厂里中等好看的,还是科学院里最好看的?”但考虑到此前没上几年学,数理化水平差同龄人太多,要考上医学院实在太难,最后决定考外语学院。她外语底子好,这些年来一直没有中断跟着无线电学习英文,后来在复习了一个夏天后,她成功考上了上海外国语学院。刚刚开启的演员生涯似乎由此转向。
学校的生活单调且纪律严明,令陈冲很不适应。她总是怀念剧组的生活,她形容剧组的人像一群吉普赛人,摄制组就是一辆大篷车,“吉普赛人带着锅碗瓢盆和乐器,在大篷车里生活,大篷车到哪里,他们的世界和家就在哪里。”但这种快乐有时也令她感到空虚,觉得不能如此长久下去,因此想要离开。陈冲在书中写道:“这份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这份灵魂深处的不安,在舒适的时候,放逐我去陌生的险境,在枯萎的时候,逼迫我生出新枝嫩芽,在迷失的时候,提醒我观照命运的轨迹。”在《青春》一夜成名后,她马上离开去做了大学生,后来她与唐国强、刘晓庆合作拍了《小花》,凭借小花这个角色,她一举拿下第三届百花奖最佳女主角。这部影片后来在各种单位礼堂、学校操场反复播放,“小花”成了一代人的时代记忆,可陈冲在拍完《小花》后又再一次决定离开,1981年,她去了美国留学。
在美国,陈冲入读纽约州立大学新帕尔茨分校,她参演学校的话剧,演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中的芥末仙女。她还在中餐厅打工,以及恋爱。当时她与一位被她化名为W的男士处在热恋中,这段恋情后来以她发现W出轨而告终。陈冲说她悲伤到“胃痛,冲到厕所去吐”,并且一度觉得自己不再值得被爱。陈冲在书中以近乎赤裸的坦诚,讲了自己的多段恋爱,上海时期的M,后来的W,美国的N,还有汤姆和彼得,她在这些恋爱中兴奋、疯狂、受伤,而后这些恋爱成为她的养料,她从中成长。陈冲在书中提到朋友说给她的一句话:“人必须经历两次死亡才能成熟——一是理想的死亡,二是爱情的死亡,成熟是死亡后的重生”。所以陈冲不断在书中鼓励人勇敢去爱,她说,她以前觉得爱情是神圣的,而且一生只有一次,用完就没有了,但后来她懂得,爱与生俱来,而且就像勇气和力量一样,它是用不完的,是越用越多的。
在与W分手之后,陈冲对于演戏这件事突然变得坚毅起来,她甚至第一次说出了“它是我的生命”这样的话。她去面试了好莱坞唯一代理亚裔演员的公司,开始在好莱坞拍戏。陈冲说当年好莱坞电影里没什么亚裔可发挥的人物,但竞争依然激烈,无数亚裔女孩挤在接待室,面试一个小角色,她们被拒绝过无数次了,所以已经对拒绝这件事习以为常。但陈冲说:“我却永远无法习惯,也永远不想习惯,被拒绝的可能性让我心悸脉动,其实是被某种恐惧所擒,肾上腺素突然大量分泌,求生欲被激发出来。”
她不停面试,与很多角色失之交臂,也拿下来一些角色,演上了一些电影,其中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给她带来了巨大事业上的成功,她饰演的婉容是她在小花之后又一个经典角色。2018年贝托鲁奇去世,陈冲在缅怀文章中回忆当年的拍摄,她写道:“回想起来,《末代皇帝》的制作像是一场八个月的婚礼,庞大热闹而混乱,而我做了八个月的新娘。”
《末代皇帝》上映后在全球好评如潮,这部在故宫拍摄,讲述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传记电影收获奥斯卡金像奖9项提名,并最终将这9项都收入囊中。贝托鲁奇拿下最佳导演奖,他在获奖感言中感谢了中国人民,以及他的男女主角——尊龙与陈冲。陈冲在书中说,后来她演过很多电影,都没法跟《末代皇帝》相提并论,她写道:“(我和贝托鲁奇)在紫禁城里交错的时刻,是他的导演生涯和我演艺生涯光芒最盛的一刻,(之后我们一直)在这余晖的笼罩下……我们永远拥有紫禁城里的那些晨曦和暮色。”
贝托鲁奇也像一个启蒙者一样,再造了陈冲对于电影的认知。她在书中提到,贝托鲁奇聊电影的时候永远只说cinema,而不是movie或者film,cinema这个字包含了一种浪漫的色彩,它既是电影,又是影院,它是两者的统合。所以cinema代表一种艺术追求,它追求一种只能在影院呈现的电影,一种其他任何艺术方式都难以替代的电影。陈冲写道:“在今天这个数码多媒体的世界,电影如要生存,它必须是cinema,并且挖掘和发明新的形态,而走进电影的人们,就像走进大教堂的信徒,在那里共享同一个梦想。”
上世纪90年代末,陈冲对很多电影感到失望,觉得它们“既得不到视听上的感官刺激,也得不到思想上的冲击、颠覆或心灵的升华”,她由此萌生了当导演的想法。她先是在1997年回中国拍摄了一个发生在青藏高原上的故事,叫《天浴》,由李小璐主演,之后2001年她又在美国拍摄《纽约的秋天》。她也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了中美两国电影产业的不同。在中国,导演是剧组的中心,导演主导所有决策。而在美国,制片人有更大的权力,他们委任导演并监督导演,当对导演不满意的时候,他们会随时换掉导演。在拍摄《纽约的秋天》的时候,制片公司派了五位制片人到片场盯拍摄,陈冲每拍完一个镜头,他们就会问,为什么这样拍不那样拍,双方闹得很不愉快。《纽约的秋天》上映后,评价并不好,这极大打击了陈冲,她说就好像我一贯对自己的怀疑终于被证实了,“我是个庸才、冒牌货,真相终于败露了”。在书中,陈冲反复提到她对自己的不满意,她说她看自己的任何一部电影,往往只看到自己的瑕疵,总觉得自己的能力远不及自己的雄心。但她永远记得她年轻时看的一部讲述舞者玛莎·葛兰姆的传记,当中玛莎说:“艺术家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满足感,唯有一种神赐的不满和幸福的骚动,驱使我们继续前进,也让我们比其他人更有活力。”
到今天,陈冲一直在创作,她手里还在写着很多故事。她说她发现自己喜欢写那些凝重和忧伤的故事,她总是从凝重和忧伤的故事中体验到美与欣喜。这是她的一种感受方式,在一个采访中她讲道:“没有任何美是可以独立存在的,你越懂得残忍,越懂得恐惧,你就会越向往美,越知道爱是什么。”而且在从业接近半个世纪的时候,她终于不再对这份职业感到羞愧,她在书中说:年轻时,我总觉得把自己跟艺术连在一起是一件自命不凡、大言不惭的事,但到了现在这个年龄,我大可不必羞涩与扭捏,艺术是通向真理的途径,在“现实”背后有一个更真实的“现实”,你唯有通过艺术才能接收,“我想接收从那里传来的暗示。”
陈冲如今63岁了,人生已到后半程,她在书中也写到自己的衰老:失眠更厉害了,到嘴边的人名卡在那出不来了,穿高跟鞋走不了路了,阅读也比以前慢了。以前她去一个又一个地方,寄出去一封又一封联络友人、爱人的信,如今她开始写关于缅怀的信。
书中她提到坂本龙一的去世。他们结识于《末代皇帝》时期,坂本龙一负责了这部电影的配乐,他凭借这部电影拿下了奥斯卡最佳配乐奖。《末代皇帝》之后,陈冲与坂本龙一联系就不多了,再联系上时,坂本龙一已与癌症斗争多年,而陈冲母亲也在癌症的后期了。陈冲母亲去世的第二天,陈冲收到一封坂本龙一给她回的邮件,邮件中,坂本龙一祝她“有一个充满正能量的新年”。陈冲说,那几个字令她感触,坂本龙一没有写快乐的新年,因为那时他正在与病魔痛苦地斗争。那之后,他们没再联系,再一次听闻坂本龙一的消息,就是他去世了。陈冲在书中写道:“直到最后,坂本龙一没有失去对艺术的虔诚,没有停止对新生事物的探索与拥抱——新的声音,新的思想,新的感知。他燃尽了,但从未衰老。”陈冲说同代人的死亡反倒提醒了她,年岁的确是可以炫耀的东西,“它好比大树漂亮的年轮”,一圈一圈写下了所有。
陈冲现在与丈夫彼得和两个女儿居住在旧金山,住在一栋陈冲一眼爱上的、建于1905到1911年间的老房子里,她的女儿把这栋房子称作是“你的摇摇欲坠的破房子”。陈冲说她好像就喜欢这些带着岁月沧桑的东西,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她回想起她们一家在上海的老房子,平江路170弄10号,她说她无数次离开这栋房子,出外景、上大学、出国,最终都回那儿了,直到后来他们搬离,再也回不去了,现今这栋房子成了上海街头的网红建筑。陈冲在书的最后写道:“房子的实体从此对我失去意义,而梦与幻想继续在岁月里发酵,远比现实要执着和长久。”这本书正是对岁月的记录,《繁花》的作者金宇澄是督促陈冲写下这本书的人,他一再跟陈冲说:“你把它写下来,别人就偷不走了。”
好,到这里,这本书就为你介绍完了。我们再来回顾总结一下。
陈冲在这本书中回顾了自己家庭的历史,以及自己长达半个世纪的从影生涯。这本书610页,包含25篇散文,很难用一个主题概括这本书,但如果一定要概括的话,我想这本书是关于爱的,是爱维系了一个家庭,也是爱支撑着一个女孩远走他乡,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园。陈冲曾在这本书的一个分享会中讲道:“是什么能让你生活得好?我觉得真的就是爱,你去爱别人,也允许别人来爱你。从中认识到某一种责任,你对你所爱的人有某一种责任。哪怕这份爱是沉重的,哪怕不是每一分钟都快乐,但这样的爱对我来说都是滋养。”
好,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本书中还有很多故事,碍于篇幅,我们没能全部展开,感兴趣的话,非常推荐你阅读原书。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1.有形的东西会消逝,比如一张相片会褪色开裂,但无形的东西可能反倒是无限的,“把整个人生的画面变成一种无形的东西,让它无限,我觉得回望的意义正在于此”。
2.爱与生俱来,而且就像勇气和力量一样,它是用不完的,是越用越多的。
3.没有任何美是可以独立存在的,你越懂得残忍,越懂得恐惧,你就会越向往美,越知道爱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