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段义孚自传》 邓一丁解读
《我是谁?段义孚自传》| 邓一丁解读.mp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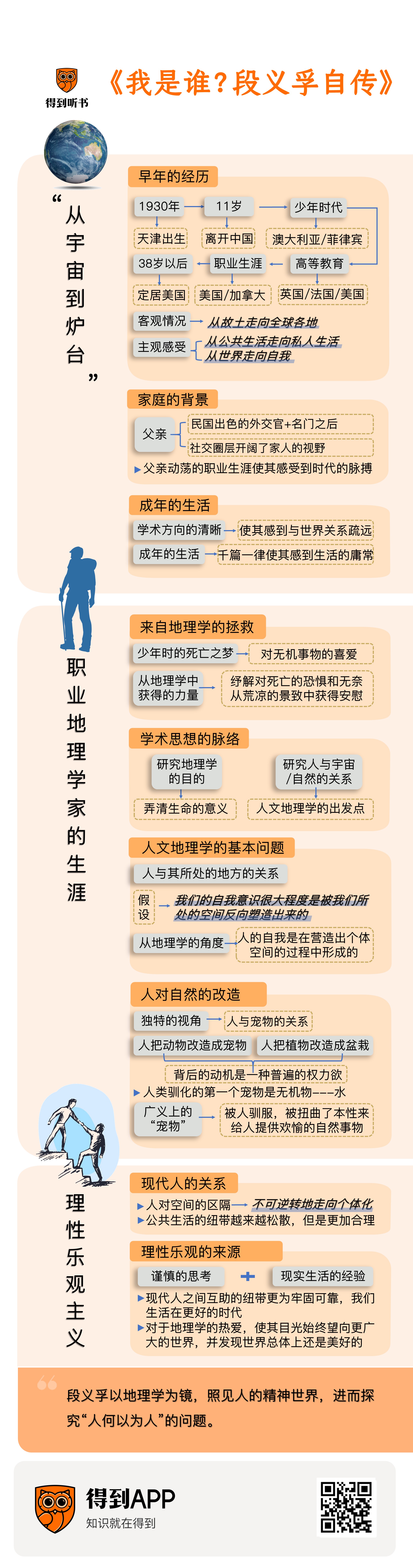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邓一丁。
今天我们来读一本自传,传主是国际知名的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
地理学界的最高荣誉是每年秋天在法国颁发的瓦特林·路德国际地理学奖。2012年,这个奖颁给了段义孚先生。其实早在获奖前,段先生已经是国际地理学界灯塔般的存在了。他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和英国皇家科学院的双料院士,开创了重要的学术分支,人文主义地理学,而在获得瓦特林·路德奖后,他又多了一个有趣的头衔。当年的评委会把他称作地理学的“小王子”。
这里说的“小王子”正是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的那本风靡全球的故事书《小王子》中的主角。熟悉段义孚先生的朋友听到这个说法大概会会心一笑,意识到这两个人之间微妙的联系。和那位从外星落入我们这个世界的小王子一样,段先生也是个内心敏感天真的人,也在反复的内省中度过了孤单却丰富的一生。在地理学的考察工作中,段先生也曾多次像小王子那样,头顶夜空,行走在无人的沙漠上,在无边的寂静里感受过自己和脚下这颗星球的关系。
说来惭愧,在读到段先生的书以前,我对地理学的认识还停留在中学课本上的季风、洋流、等高线和黄赤交角。只是在初步了解了由他开创的人文主义地理学以后,我才知道地理学家的学术视野竟然如此广阔。段先生的思考路径和传统的地理学家不同,并不限于纯物质的山川水文,而是在更偏重精神性的层面上探讨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换句话说,他是把地理当作一面镜子,用它来照见人的精神世界,进而回答“人何以为人”的问题。具体来说,这些问题包括,人是出于怎样的心理动机来改造自然的?人如何在不同的空间里感受自身?怎样的景观会让人感到恐惧或安慰?良好的生活应当在怎样的环境中展开?你听得出来,这些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通常认知中的地理学的范畴,延伸到了心理学家、伦理学家和美学家关心的领域。
用一生的时间思考这些问题的段义孚先生有着怎样的经历?他是个怎样的人?为何会将地理学作为自己毕生的志业?又为何会对人的心灵有如此深刻的兴趣和深入的洞见?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他的自传来了解这位学者的人生。段先生的这本自传在传记体裁的书籍里显得很特别。他无意谈及自己那些耀眼的学术成就,而是对生活中一些看似寻常的琐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似乎在他看来,那些记忆深处不可磨灭的日常的碎片才是映照出他内心世界的镜面,也才能真正回答他在书的标题里提出的“我是谁”的问题。这是一部真诚的心灵史,阅读的过程也是跟随一位老人走回生命原点的过程。
接下来,我们就从段先生早年间的经历说起。
在回顾人生时,段先生在书里多次简短地概括道,自己是个无根之人。
他有这样的感受,和他早年间的经历有关。在38岁以前,段先生从未在任何地方停驻过五年以上的时间。他1930年生在天津,此后随家人辗转迁移到南京、上海、昆明、重庆,11岁那年就离开了中国。从那以后,段先生又在澳大利亚的堪培拉、悉尼和菲律宾的马尼拉度过了少年时代,在英国的伦敦、牛津,法国的巴黎,美国的伯克利完成了高等教育,之后居住过的地方还有美国的布卢明顿、芝加哥、阿尔伯克基和加拿大的多伦多。直到38岁以后,段先生才先后在美国的两所高校中取得了稳定的教职,在明尼阿波利斯和麦迪逊各住了十四年。在写作自传时,段先生已年近古稀,当他历数自己生活过的地方,也只好承认,或许只有在他工作过的两所高校里,他才能找到一点地理上的归属感。
从客观的情况来看,段先生显然是从故土走向了全球各地。但很奇妙的是,他的主观感受却刚好相反。他感到自己是从公共生活走向了私人生活,从世界走向了自我,或者用他的话说,从“宇宙”走向了“炉台”。在他的记忆里,童年时在中国度过的几年和他日后的生活相比,更有世界主义的氛围。究其原因,大致有两点:其一,1930年代的中国正在世界历史的浪潮中载沉载浮,那个年代有见识的中国人都时时关注着世界局势;其二,段先生的父亲是一位知识精英,他平日里接触的圈层让家人们感到世上的大事就发生在自己身边。
段先生的父亲段茂澜是民国时的一位外交官,祖籍安徽银山。安徽段氏另有一个支脉居住在合肥,出了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段祺瑞。段义孚先生回忆,他父亲所属的银山段氏不算富裕,而合肥段氏家财万贯,段祺瑞作为家族的主事人,还曾给他父亲段茂澜的学业提供过资助。出身寒门的段茂澜也没辜负家族的期望,读书非常刻苦,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升入了清华大学,后来又出国留学,在美国的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一路读到博士,钻研过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掌握了英、法、德、俄、日、西等多国语言。
这样的人才回到国内,当然立即就受到了重用。段茂澜先后在南开大学做老师,在北京电报局做经理,后来做了外交官。在段义孚先生童年的记忆里,父亲每天至少用四国语言和世界各地的使者侃侃而谈,家里的客厅也时常接待一些重要的客人。客人们对幼小的段义孚都很亲切,抚摸他的头顶,还送他玩具。后来他才知道,这些人都是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其中有一位还是世界性的伟人。
段先生所说的这位伟人,正是我们的开国总理周恩来。段先生的父亲段茂澜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和同学周恩来一起办校刊,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1930年代末,两位中学时代的好友在重庆共事,周恩来还时常来段家拜访。段义孚记得有一回,父亲在客厅里和周恩来掰手腕。周恩来的手臂受过伤,段茂澜是在帮老朋友检查他的力气有没有恢复。段义孚还记得父亲和周恩来谈话的一些细节。他们两人的价值观十分契合,都深切地同情弱小,主张人人平等。这些谈话在幼小的段义孚心中留下了一抹光明的印记。
不过这也是段义孚在中国生活的最后时光了。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间,段茂澜先后被派驻澳大利亚、菲律宾和英国处理外交事务。段义孚也就跟随家人辗转世界各地。1946年,他在菲律宾读中学时见证了该国的独立。当年晚些时候,他乘坐的航班在飞往伦敦的途中突然迫降马耳他岛,原来是后来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正赶去伦敦办理印度的独立事务,临时征用了他们的飞机。在他十几岁的年纪上,世界大事就这样从他的身边呼啸而过,这让段义孚真切地感到自己置身于世界历史的中心,感受着时代的脉搏。
而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间,当他的生活逐渐稳定下来,学术的方向逐渐清晰起来,他却感到自己和世界的关系变得疏远了。他在英国的牛津大学读完了本科,进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继续进修,终于成为一名地理学者。1963年,他在美国西南部的阿尔伯克基任教。一天晚上,他看完一场电影出来,看到一束探照灯的光束扫过天空。那一刻,所有关于战争的童年记忆苏醒过来,段先生下意识地判断是有人发动了空袭,可是当他紧张地循着探照灯的方向望去,却发现那束灯光来自附近的圆形剧场,原来那里正在举办汽车展。段先生这才放下心来,可是释然过后,他竟然感到一丝失落。他的生活曾被时代的洪流冲刷过,而今已变得平静,甚至庸常。少年时代的他曾为了家国大事茶饭不思,而到了三十多岁的年纪,他却身处异国偏僻的小城,在灯光的诱惑下茫然地走进一场汽车展,绞尽脑汁盘算着该买一辆福特还是雪佛兰。
不知你会怎么看待段先生在自传里记下的这件小事?我感到的是一丝生活的荒诞。多年以后,段先生发现身边退休的同事们陆续写起了家史,这些美国人大多会将家族的起源追溯到欧洲,写他们的祖先如何横渡大西洋,如何在东部新兴的城市里站稳脚跟,又如何在中西部的农场里开枝散叶,可是写到自己这一代,写完童年的经历,突然就讲不出什么故事了。明明对自己的人生最为了解,为什么写到自己反倒搁笔了呢?段先生猜想,这大概是因为:“故土的生活可能充满浪漫色彩,漂洋过海的经历可能是史诗般的,在新世界里筚路蓝缕可能富有英雄气概,幼年时受到的教育可能带有恋旧情结;相比而言,成年后的经历总是千篇一律,无非是家庭琐事、更换工作、任职升迁等等。”段先生在说他的同事,但也是在说他自己。
就这样,在三十多岁的年纪上,段先生的生活逐渐平稳下来,他作为职业地理学家的生涯也由此展开。虽然他在自传里略带遗憾地写道,自己的视野从广袤的世界缩进了象牙塔内,他的思想却转向了更加沉静和精深的方向。回顾数十年来的学术生涯,段先生说,是地理学拯救了自己。
段先生是个早慧的孩子。约莫在12岁的年纪,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了自己的死亡。从梦中醒来,段先生无比清晰地意识到,凡人终究是难逃一死的。这个挥之不去的逻辑令他感到恐惧,却又无可奈何。从那以后,他发觉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发生了变化。那些由无机的矿物组成的景观对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吸引力。
在晚年回想起来,段先生认为,他对无机事物的喜爱大概是与生俱来的,只是在那个关于死亡的梦后被唤醒了。他对这个世界最早的记忆发生在他三岁那一年的冬天。那时他住在天津,午睡醒来会感到心情沮丧,容易哭闹。他的奶妈想出了一个主意。她用一只烟灰缸盛满水,放在窗外,水在寒冷的空气里结成冰。等到段先生快醒来时,奶妈就拿来烟灰缸,翻转过来,用刀柄轻轻一敲,一个晶莹剔透的冰雕就掉在床前的桌上。在年幼的段先生看来,这整件事就像魔法般美妙。在写作自传时,段先生环顾家里的陈设,发现他只买过一件完全没有功能性的东西,那是一只玻璃制成的苹果,放在客厅的桌上。每当傍晚时分,阳光斜照,玻璃苹果就变成了一颗五彩缤纷的光球。每当这时,段先生凝视着这只苹果,醉心于它的美丽,心里安慰地想着,世上美好的事物并非都注定会朽坏。
这正是地理学能给段先生带来抚慰的原因。他在那些不会腐败的纯净的矿物中看到了一种永恒的力量,这种力量帮他纾解了从少年时起就如影随形的对于死亡的恐惧和无奈。出于这样的理由,段先生深深喜爱着在常人看来荒凉的景致。他在书里写下了青年时代一次在荒漠中露营时看到的景象:
“美丽的月色让我难以入眠。我想,命运的安排就是这样无可抗拒。……一眼望去,谷地西侧的整片坡地展现在面前,坡面被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照得微微发亮,像星光映在广阔的海面上,像一丛丛紫色的花,像洒下的一片片金粉。山谷底部的盐碱地,以及四处耸立的光秃秃的岩石,看起来也像是异界之物。但更不可思议的是那种安宁和静谧。我对这种景象非常好奇,估计别人也会如此。但令我困惑的是,为什么我不仅感到好奇,还感到一种醉人的幸福。”
从这段动情的文字里,你能感受到地理学带给段先生的那种宿命般的归属感。
多年以后,当他已经是个成熟的学者,段先生仍然时常被问起,为何会选择成为一名地理学家。面对这个问题,他通常会简单地敷衍过去,说自己在年少时就跟随家人四处旅行,由此产生了对地理学的兴趣。而真正潜藏在他心底的那个答案是很深刻、很抽象,又难以解释的。通过研究地理学,他真正想要弄清楚的是,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哲学问题。但激发段先生思考这个问题的,却是一个地理学上的事实:在我们这颗星球上,乃至整个宇宙中,没有生命又不会朽坏的无机物质是绝对的多数。那么,我们这些拥有生命,却注定要在短暂的时间后归于尘土的存在,究竟为什么存在?我们和无机世界的关系如何?这些关系又反映了人类怎样的本质呢?
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构成了段先生学术思想的脉络。在这些思考中,居于核心位置的是人,这便是人文主义地理学这门独特学科的出发点。接下来,我们就通过段先生的几本代表性的著作,来了解一下他主要的学术观点。
人文主义地理学处理的基本问题之一,是人与其所处的地方的关系。这也是段先生在他1982年发表的著作《分隔的世界与自我》中集中探讨的问题。从少年时代起,他就旅居世界各地,身处异文化的包围之下,在和周遭环境的对比中产生了强烈的自我意识。这引发了他的思考:人的自我意识,和他所处的空间有什么关系吗?
段先生的假设是,我们的自我意识,很大程度上是被我们所处的空间反向塑造出来的。具体来说,远古时代的人生活在开阔的平原上,或群居在山洞里,他们的生活空间也彼此重叠,不存在隐私和区隔。而时间越接近现代,个人就越要求拥有独立的生活空间。在数万年前,我们的祖先曾经终日在部落里同伴们的注视之下生活,由此获得安全感。而如今的我们待在自己的房间里,锁好门,将自我从世界上孤立出来,反而会感到安全。我们也会精心地布置属于自己的空间,就好像那是自我的延伸。
从地理学的角度,段先生相信,人的自我正是在营造出个体空间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个观点在人类学和历史学那里都能找到支撑的例证。人类学家多萝西·李研究过一群北美的原住民。这群原住民生活在开放的空间里,日常起居混杂在一起,没有专属于个人的空间。相应的,他们使用的语言中也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他们不会说“你和我”,只会说“我们”。当人类学家请他们讲述关于自己的故事,他们也表现得有点迷茫。和段先生的那些退休的美国同事一样,这些原住民首先会连篇累牍地讲述自己的家族和祖先的故事,只在故事的结尾才稍稍提到自己。在他们的世界观里,个体的边界是模糊的,脱离了家族的序列,断开与他人的关系,他们的自我也就无处安放了。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多久呢?根据段先生的研究,欧洲人直到19世纪末才逐渐摆脱了这种不分彼此的生活状态。我们不谈那些拥有大量房间的城堡和宫殿,欧洲大多数的民居直到19世纪末才划分出具有明确功能,或专属于特定家庭成员的房间。在这以前,到了饭点,一所房子里的人聚在开阔的厅堂甚至是户外,用公用的餐具吃着大锅饭。所有人的活动都暴露在其余众人的视野之下,人们的自我意识和隐私观念也都不像今天这样明确。
段先生的这些观察给现代人的自我反思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他的另一项研究则启发了后来的许多学者思考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和主流的地理学家一样,段先生也关注人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但他选择的视角却非常独特,他考察的是人与宠物的关系。
谈到人对自然的改造,主流的地理学者通常会从经济学的角度给出解释,批判人为了经济利益而破坏自然环境,但段先生的兴趣则更多地集中在人的心理上。在他看来,人将动物改造成宠物,将植物改造成盆栽,这些行为背后的动机是一种普遍的权力欲。
在这里,我想请喜欢宠物和盆栽的朋友不要生气,段先生的分析并不指向道德上的批判。他只是在人对自然的改造中观察人,试图找到一些人性底层的成分。在他发表于1984年的《制造宠物》这本书中,段先生提到的人类驯化的第一个宠物也不是动物或植物,而是一种无机物,水。
把水称作“宠物”,这种说法可能会让你意外。段先生的解释是,那些被人驯服,被扭曲了本性来给人提供欢愉的自然事物,都属于广义上的“宠物”。当人们从遥远的沟渠里把水引到室内,用复杂的工程技术打造出一池喷泉,让水以规则的几何形态从喷泉的各个孔洞里喷涌而出,人就完成了水的“宠物化”。从16到18世纪,喷泉一直是欧洲王室的宫廷里最重要的宠物,满足着权势阶层炫耀权力和财富的欲望。
听起来,段先生对人类的本性似乎有些悲观吗?说实话,读完他写的《制造宠物》,我是感觉人类的权力欲有点无药可救了。可是在读完段先生的自传后,我却意外地发现,他是个理性乐观主义者。
我们前面提到,从人对空间的区隔来看,现代人正在不可逆转地走向个体化。常年生活在崇尚个人主义的西方社会,段先生的体感也是公共生活的纽带越来越松散。可是他却相信,和人们因为匮乏而不得不彼此依赖的古代社会相比,现代人之间的关系是更加合理的。
他的这种乐观既来自谨慎的思考,也来自现实生活的经验。有一次,段先生在乘坐飞机时目睹了一场意外,一位女乘客突然被食物卡住了气管,无法呼吸。这时机上刚好有位实习医生,他对这位女乘客实施了必要的急救。飞机临时降落在附近的机场,实习医生护送女乘客下机治疗。当他终于回到飞机上,被迫等待的乘客们却无一怨言,而是纷纷欢呼起来,欢迎这位年轻的英雄回到他们中间。段先生明白,在这趟航班起飞前和降落后,机上的乘客都只是陌生人,可是在短暂的航程中,他们却因为一场意外,结成了温暖的共同体。这让段先生感到心安。在他看来,那位实习医生和许许多多现代社会里的专业人士一样,都是当代文明的缩影。他们的行为或许不像古代的英雄那样慷慨激昂,或许也并非出于针对个人的善意,但现代人之间互助的纽带却更为牢固可靠。人们当然会怀念那些在历史上为他人做出重大牺牲的英雄,但现代社会的繁荣富足更加不要求人们做出重大的牺牲。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确实生活在更好的时代。
段先生也是出于这样的体悟,写下了“地理学拯救了我”这一章的标题。在他看来,西方社科学界盛行的对现实的批判或许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光明也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假如没有从事地理研究,段先生这样内心敏感的人或许会更加沉溺于无尽的自省。可是幸好有地理学,他的目光始终望向更广大的世界,并且发现,“尽管有那么多惊骇可怖和虚空无益的事物,但这个世界总体上还是美好灿烂的”。
段义孚先生的这本自传,我就为你介绍到这里。就像我在前言里提到的,这不是一本典型的传记,段先生也没有过多地涉及自己治学的经历。它更像是一位智慧的老人在真诚地和读者对谈,讲述他看待世界和自我的方式。我想,关于“我是谁”这个问题,段先生在提笔时心中也没有答案,而写作的过程也正是他向内心深处探寻的过程。
在这本书里,段先生还有一个反复提到的主题,这就是孤单。段先生终生未婚,而身边的朋友大多组建了家庭。当他孤身一人行走在学术的路上,尽管获得了学界的喝彩,但在生活上,他却始终感到自己难以追赶身边人的步伐。他在自传的结尾写下了一个简短的故事:
那是许多年以前,他独自驾车行驶在内布拉斯加州疏落的景观里。他对自己的驾驶技术一直不太自信,在夜晚的高速路上更是感到心慌。幸好前面不远处有辆车的尾灯若隐若现。段先生很感激有那辆车的陪伴,可是就在他渐渐习惯了前方的灯光时,那辆车却礼貌地打起了转向灯,在不远处的路口驶离了高速路。于是,黑暗的路上就只有段先生一人了。他的车灯只能照亮前方很短的一段路,而在更远处,一切都没入了黑暗。
这无疑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当69岁的段先生在1999年完成这部自传时,他或许也对无人陪伴的晚年感到悲观。但值得庆幸的是,自传的结尾还远不是他人生的结尾。在接下来的二十三年里,段先生的人生发生了不少变化。他收养了一个孩子,以这种方式成立了自己的家庭。他栽培的学生们也纷纷成为学界的栋梁,时常回到他身边。在晚年和友人的合影中,段先生的表情幸福而恬淡。当他在2022年8月10日离开这个世界时,他大概也不会感到自己将堕入无边的黑暗。
除了咱们前面提到的《分隔的世界与自我》和《制造宠物》,段义孚先生的代表作还有《浪漫地理学》《恐惧景观》《恋地情结》《空间与地方》以及《人文主义地理学》。这些著作在近年来都已陆续被翻译成中文,感兴趣的话,欢迎你阅读这些作品。当然,也欢迎你阅读段先生的这本自传《我是谁?》。
以上就是本期听书的全部内容。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1.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开创者段义孚被称为地理学的“小王子”。他以地理学为镜,反观人类的精神世界,从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中解析人性的本质。
2.在段义孚看来,人的自我意识很大程度上是在营造个体空间的过程中生成的。
3.段义孚将人驯化自然事物,扭曲其本性来满足自身欢愉的活动称为“宠物化”,在他看来,宠物化是人性底层的权力欲的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