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牧场》 杨以赛解读
《冬牧场》|杨以赛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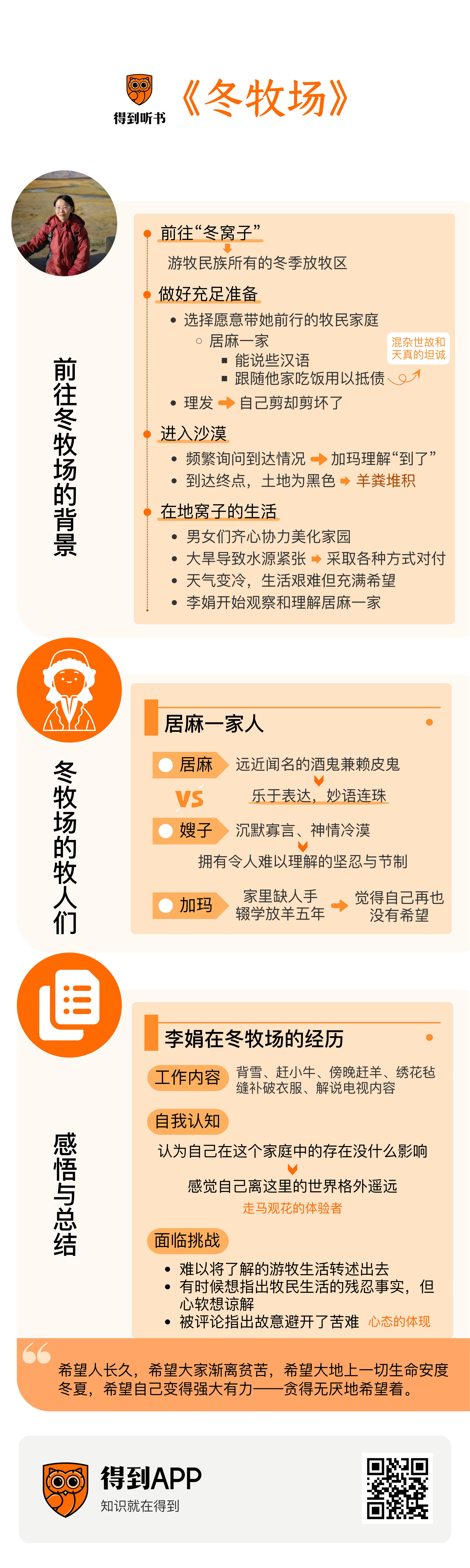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冬牧场》。这是一部讲述哈萨克游牧民族生活的长篇纪实散文。
书的作者是新疆作家李娟。 李娟1979年出生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高中辍学毕业后,跟随母亲到了阿勒泰,帮母亲经营着一家杂货店和裁缝铺。她也曾去乌鲁木齐打工,做过一年多流水线工人。二十岁出头的时候,李娟开始在网络上的一些文学论坛活动,在网友的互相推荐下,她开始发表作品。她没有受过系统的文学训练,但作家王安忆评价她说:“有些人的文字你看一百遍也记不住,有些人的文字看一遍就难以忘怀,(李娟毫无疑问是后者)。”截止到目前,李娟一共出版了11本书,大多是与她自身生活相关的纪实散文,她凭借这些作品先后获得了“人民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鲁迅文学奖”等颇有分量的文学奖项。
《冬牧场》是李娟出版的第五本书,李娟曾说,这本书至今仍是她写作上的最大自信,如果让她选一本书作为“代表作”的话,她觉得非《冬牧场》莫属。自2012年出版以来,这本书不仅受到了文学界的关注,也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在豆瓣有三万八千多人为它打出了9.2的高分,它还长年位列当当的畅销图书榜单,已是当之无愧的长销书籍。
在这本书中,李娟记录了自己在2010年冬天,跟随一户哈萨克牧民家庭深入阿勒泰南部的冬季牧场,并在那儿度过一整个冬季的前后经过。我们可以借由这本书回到广阔的荒野,去了解和感受一种原始、古老、如今已越来越罕见的生活和生存方式。同时我们也可以借由这本书,跟随李娟在荒野之中重新思考人生,以及思考我们眼前的生活。
好,接下来我将分三个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我会一边为你讲述李娟在冬牧场的经历,一边讨论李娟的写作特点和主题。第一部分,我们来了解李娟前往冬牧场的背景,以及她初至冬牧场的经过。第二部分,我们聚焦冬牧场的牧人们,他们是一群怎样的人,有着怎样的生活,我们还将就李娟对这群人的书写,聊到散文写作的核心。第三部分,我们来看李娟对这段经历的感悟和总结,这其实也即是本书的主题。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2010年,李娟决定要前往冬牧场。那一年,她已经出版了几本书,可她却一点不像个作家,还是整天在村里蓬头垢面地赶鸭子。在她所在的阿克哈拉村,村民们对她有四个疑点,一不结婚,二不工作,三不串门,四不体面。这让她的母亲都倍感受辱。这个冬天,李娟决定要改变这一现状,她打笑说,“我终于要像模像样地做一件作家才做的事情了”。她要跟着迁徙的羊群进入乌伦古河南面广阔的荒野深处,观察并记录牧民们的冬季生活。用当地的话来说,她要进“冬窝子”了。
所谓“冬窝子”,不是指具体的某一个地方,而是游牧民族所有的冬季放牧区,广阔且与世隔绝。母亲为李娟挑了一圈愿意带她前行的牧民家庭。李娟最后选择了居麻一家,一是因为居麻能说一些汉语,二是居麻欠了李娟家好多钱,看样子还不上了,按母亲的意思,不如就跟着去他家吃几个月,把钱全吃回来。李娟把这两个原因一五一十写进了书里,这种混杂着世故和天真的坦诚是她写作的一个特色,或者说招牌,直到今天也依然如此。
李娟为这次出行做了充分的准备。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是理发,因为未来几个月很有可能都洗不了头了。她打算剪一个接近光头的短发,但没料到的是经营着村里唯一一家理发店的姑娘玛依拉正在谈恋爱,整天神出鬼没,不好好做生意了,她的店去十次有八次是关着的。李娟干脆自己剪了一个,结果剪坏了,李娟说:“于是乎,此后的日子里,每当面对客人或出门做客时,头发是最伤我自尊心的东西。”
出发的日子终于来临。清晨七点,李娟和队伍上路了。这一路得走三天,李娟和居麻家19岁的女儿加玛负责管理骆驼队,居麻在牧场的邻居新什别克和另一个牧场的牧羊人胡伦别克则负责管理500多只羊和上百头牛和马。居麻和妻子则要在三天后才雇汽车赶来,这三天他们得为这个冬天准备成吨的粮食、饲料和作饮用水的冰块。
李娟是这么形容他们这一路上的景况的:“眼前起伏的大地空空荡荡,只有痕迹微弱的一条土路。太阳刚升起不久,蓝天空旷。走了这么久还不见停歇,使得队伍有些不安。绵羊紧跟着山羊,孩子紧跟着母亲。马群不愿和牛群走在一起,牛群非要和马群走在一起——追来躲去,时不时出现小混乱......我戴着口罩,围着围巾,笼着围脖,还扣了顶有护耳的大帽子。越来越冷,就调整口罩和帽子,整个脸部只露出眼睛那儿的一道半指宽的缝,看出去的世界狭窄又压抑,却很安全。”
头一个晚上,四人住在一个临时搭建的帐篷里。两个男人得轮值守护畜群,提防狼的袭击,于是打着手电,不停地烧水喝茶。李娟熬不住,穿着短羽绒衣和棉裤钻进了被窝,她形容被窝里的自己就像“小鸡在母鸡翅膀下一样安全又舒适”。凌晨三点,李娟被推醒,这时又得起床赶路了。因为前一天的良好表现,这一天李娟被分到了一些新任务,比如赶一赶牛群。一路上队伍喝的都是化开的雪水,前一天李娟还对两个小伙子猛喝冰水感到诧异,结果这天她赶完牛群回来,嗓子直冒烟,喝得比他们还要猛。
到第三天,队伍开始真正进入沙漠,到沙漠那种四顾茫茫的感觉就更明显了。这几天,一到下午,李娟就会频频问加玛到了吗。加玛的汉语水平一般,一开始并不知道“到了”是什么意思,在李娟每次一到驻地就会欢呼“到了”,这才有所领悟。后来李娟再问她这个问题的时候,她会回答说,“不是‘到了’”,意思是还早,或者是“‘到了’的有”,意思是快了。第三天下午三点半,李娟爬过一个山丘后,惊讶地发现沙丘另一面是一块黑色的土地,然后她便听见加玛大喊,“到了李娟,今天的到了,明天的不走啦,明天的明天也不走啦。”这是说,他们到达终点了。
这块地之所以是黑色的,其实是羊的功劳,羊在这里度过了很多个冬天,羊粪一年年堆积下来,就把这块弹丸之地涂抹成了黑色。对牧民来说,羊粪的作用可太大了。软的羊粪经晾晒之后是冬天最好的燃料。而堆积风干后的硬羊粪,则是荒野里最重要的建筑材料。在冬牧场,牧民们会在地上挖一个两米深的大坑,坑墙四周垒上羊粪块,然后坑口搭上几根木头,铺上干草束算作屋顶,这就成了一个房子,当地叫“地窝子”。“地窝子”里的床榻也是用羊粪块砌起来的,所以李娟打笑说:“我们根本就生活在羊粪堆里嘛。”
到达冬牧场后,第一件事是收拾地窝子,因为人得睡觉,第二件事是清理羊圈,因为羊也得睡觉。居麻夫妇也坐车赶来了,召集大家拿起铁锹干活。从早上一直干到下午,每个人的腰都痛得不行。接着李娟见居麻的妻子,她叫她嫂子,她从口袋里掏出一长串塑封的止痛片,然后像分糖豆一样给每个人分了两粒,大家也像嚼糖豆一样嚼嚼吞了。李娟沉默了。她在书中感叹长年艰辛动荡的游牧生活让牧民们都有一颗寂寞又坚强的心。她写道:“春天,牧人们追逐着逐步融化的雪线北上,秋天又被大雪驱逐着渐次南下。不停地出发,不停地告别。春天接羔,夏天催膘,秋天配种,冬天孕育。羊的一生是牧人的一年,牧人的一生呢?这绵延千里的家园,这些大地最隐秘微小的褶皱,这每一处最狭小脆弱的栖身之地……青春啊,财富啊,爱情啊,希望啊,全都默默无声。”
刚到地窝子的时候,里面黑乎乎的,天窗也塌了,入口处的台阶下积满流沙,凄凉极了。李娟说,“这算是个什么家啊!连我的马都很不满意,只探头看了一眼就立刻偏过脸去。”可两天之后就大不一样了,男人们三下两下修好了所有破损之处,女人们则竭尽所能地美化这个家。加玛对此尤为上心,她在床榻靠着的三面墙壁上都挂上了壁毯和漂亮柔软的布料,还给一切露在外面的家什披上绣着花的盖头。每天早上,每个人都不愿离开热被窝。嫂子会一遍一遍叫起床,但无人答应,最终嫂子只好叹口气也钻回被窝。而到了晚上,则无人想睡觉,加玛会就着昏黄的太阳灯绣花,居麻则为大家朗读旧的哈萨克文报纸,李娟则在一边看书和做笔记,就这么一直到很晚。李娟说,地窝子并不牢固,也没有体面的家私,附近也没有便利的生活,但家人在这边,牛、马、骆驼也在这边,所以对牧民来说,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家。
在地窝子,唯一的水源来自雪。出发前,李娟妈妈羡慕地对李娟说,“这个冬天你可以喝到最好的水了”,李娟一度很期待,但没成想这年大旱,没几场像样的雪,只在沙丘的洼陷处及草根处残留一些积雪,收集半个小时的雪,化开后的水还不够洗一双袜子。因为这样的情况,李娟只能决定这个冬天都不洗澡,以及也不再换洗衣服。但不洗澡身上发痒,李娟说她就“挠挠着”对付,挠不到的地方就靠在柱子上蹭,为此居麻笑话李娟,“跟牛一样,跟羊一样,跟猫一样。”好在12月底,终于连着下了三场雪,积了十厘米厚,李娟立马兴冲冲去扛雪,不到半小时,扛了三袋子回家,全化开后,她和居麻夫妇三人各自关起门大洗了一通。
但雪多了,也意味着天气越来越冷了。每天一早一晚,温度计的红色液体柱都停在零下三十五摄氏度左右,这是这支温度计所能显示的最低刻度。以前晚上大家都喝茶,但这下无论怎么劝茶都不喝了,生怕起夜上厕所。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到一月中旬,再往后随着白昼的增长,气温又会升上来。用居麻的话说,“一切总会过去”。李娟写道:“是的,‘一切总会过去’。人之所以能够感到“幸福”,不是因为生活得舒适,而是因为生活得有希望。”
随着在冬牧场的生活逐渐安定,李娟也对她所在的居麻一家有了更多的观察和理解。这本书第二章的章节名叫做《荒野主人》,李娟在这一章中开始将目光从自然转向身边的人,她在书中为他们留下了一幅幅动人的肖像。接下来的第二部分,我们来更深入认识一下居麻一家。但在此之前,我们要先来谈一谈李娟的写作。
李娟一直写的是散文。散文可以说是一种我们熟悉又陌生的文体。我们常说的“古文”,实际上就是说的古代散文。高考语文考试中的记叙文毫无疑问也是一种散文。我们大部分人的日记同样也是散文。所以我们其实经常读,也经常写散文。但说起散文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文体,什么样的散文是好的散文,我们却又不一定说得上来。著名的小说家王安忆写过一篇讨论散文的文章叫做《情感的生命——我看散文》,当中她说散文没什么特征,我们往往只能用它不是什么来说明它是什么,比如它肯定不像小说一样是虚构的,散文在情节上是真实的,它也不像诗一样有某种格律,散文的语言就是我们日常说话的语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安忆认为散文堪称是最难写的一种文体,看上去是你想怎么写怎么写,想怎么说怎么说,但正因为无所限制,所以也就没了任何抓手,用王安忆的话说,“你处在一个漫无边际的境地,举目望去,没有一点标记可做方向的参照。”
在散文中,作者无法躲在语言和情节的背后,他必须直面读者,他的真实所感和真实所想直接决定了散文的质量。所以王安忆称散文为“情感的试金石”,一个人情感的深度和广度,瞒不过散文。《我与地坛》是公认的高质量的散文,贾行家老师评论此书说史铁生的文字中有一种罕见的神性,这种神性来源于不断面对、审视和挖掘自己的内心,哪怕是当中最隐秘、最想要隐藏的部分,这恐怕是一个好的散文作家的必经之路。
李娟的写作毫无疑问是极其真诚的,她的几乎所有书都有关她和她的生活,以至于一些读者在聊起她的时候就像在聊起一个自己的老朋友。李娟自己也曾说,真诚是她对自己写作最大的要求。她在一些访谈中反思过自己早年的写作,认为自己作为一个汉族人去写哈萨克族的生活,自己和他们的生活和情感方式实际有很大差异,但有时候为了把故事写得更美好、更有意思一些,或是让文字更顺畅一些,会除掉这种差异,李娟觉得这其实是自己不够真诚。现在她已经不能接受这样的写作,她希望自己很诚实地写,不要忸怩作态。另外,李娟还提到过一点,人们经常用“天然”“纯洁”这样的字眼概括她的写作,但这可能是对她写作的一种简化。首先李娟文字的天然感实际是她精心打磨的结果,她曾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讲到过她的写作过程,她说她的写作很少是一气呵成,总要经过很多的修改,要一遍遍改掉那些不顺畅的句子、不准确的表达、不稳定的结构、拖沓的节奏、轻浮的态度,甚至改到最后文章已经远离或背离了最初的想法,但她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才打造出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天然纯粹。其次,李娟直言,“写作是表现复杂世界和矛盾世界的行为,太纯洁的人恐怕写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她这里所说的“纯洁”指的不是天真单纯,而是一种对情感的简单和迟钝。一个好的散文写作者必须带着一颗极其敏感的心去体验、理解,并最终用语言描述人类最幽深复杂的情感。接下来我们就借李娟对居麻一家的书写,来看一看她对于复杂情感的捕捉。
先说居麻,居麻快五十岁了,头发花白,身高一米八五,体重一百一十公斤,走起路来惊天动地。居麻是远近闻名的酒鬼兼赖皮鬼,但大家还是乐于与他相处,因为他乐于表达,妙语连珠,经他散播出去的笑话,能流传很长时间。李娟写道:“大约这样的世界里,天大地大,牧人们分散独居,日子寂静单调,生活艰难且封闭,极少与外界交流,人们大多是忍耐而沉默的。于是居麻的出现给大家带来了多少快乐与释放啊。这个人总是能痛快流利地指出一切,总是能说到人心坎儿上,总是寥寥数语就能轻易解开任凭怎样的蛮力也解不开的困结。”
居麻说得满口汉语,这是因为他小时候生活在县郊的生产队,他跟着邻居学了很多汉语。后来赶上阿克哈拉这边的人民公社缺一个赶马车的,他的爸爸揽下这份活计,带着全家人迁过来安了家。再后来公社解散,他们一家就成了牧民。居麻有一次跟李娟说,要是他们一家留在县郊,他会继续上学、工作,可能就成城里人了,但现在他却只是个放羊的。李娟写居麻是“骄傲又敏感的”。
李娟进冬窝子前,最担心就是居麻会天天喝酒,后来这担心放下了一些,因为居麻只带了三瓶酒。可这三瓶酒也足够他闯两到三次祸了。每次闯祸,无非就是大叫大嚷,吵得大家一夜睡不好觉。其次就是扔碗砸东西,但值得安慰的是,地窝子是泥沙地面,所以他扔了那么多碗,从来没碎过一个。李娟用了很多的笔墨写居麻的闹腾,他要不停地擦靴子、要把所有变形的锅盖复原,然后要一会儿骚扰这个人,一会儿招惹那个人,然后他的膝关节和踝关节都有问题,天气一变,他就嚷嚷浑身疼,把阿斯匹林当饭吃,让所有人看着都心惊胆战。但写完这些闹腾后,李娟笔锋一转,写了一笔没事干了的居麻。她写道:“他一个人登上东北面的沙丘,站在最高处,站在明亮广阔的天光下,久久遥望羊群的动向。长时间一动不动。”这一笔寂静,让居麻这个人一下子深邃起来。李娟说,很多时候看到居麻突然而至的快乐,心里一动,会感到难受,又会立刻随之一同欢喜起来。他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人。
居麻的妻子和居麻完全相反,她是一个沉默寡言、神情冷漠的女人,李娟一直管她叫嫂子。有一次在炸一种叫做包尔沙克的当地小吃的时候,嫂子惊叫了一声,李娟扭头看过去,原来是她被溅起的滚油烫着了,李娟正想起身去看看是否严重的时候,她又恢复平静,继续打捞锅里的包尔沙克了。李娟心想可能无大碍吧,但等全部炸完后,嫂子卷起袖子,李娟这才发现她的烫伤很严重。要是当时立刻浇冷水,伤势也许会缓和很多,可嫂子却一身不吭。李娟写道:“好像受伤这件事的严重性远远排名在几只炸煳的油饼之后。又好像表现出对病痛的重视会是多么丢脸的事!这真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坚忍与节制。”
嫂子出生在距离阿克哈拉三十多公里外的恰库图小镇。居麻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眼光很高,结识好几个姑娘都没成,直到有一年他在恰库图的一个舞会上认识了嫂子,自此之后他就三天两头往恰库图跑,就这样把嫂子追到手。居麻显然对这场婚姻很满意,但嫂子满不满意,我们就不知道了,李娟说,聊起婚姻话题的时候,嫂子不怎么说话,只在一旁端着茶碗抿茶,神态安然。有一次结束一场辛苦的劳动后,两口子回到家,疲惫又茫然,居麻一时不知道该干什么,便一把搂住了嫂子,他以为这样会吓嫂子一跳,但没想到嫂子这时立刻反手搂住了他,两人如此这般在炉子前勾肩搭背地站了好一会儿,亲热得让一旁的李娟都看不下去了,直到李娟取出相机,这两人立刻撒手了。
居麻夫妇有四个孩子,加玛排行第二。2010年的时候她19岁,一米七的个子,体型苗条。头发有些稀薄细软,但是柔顺又明亮。李娟说,加玛虽然长个娃娃脸,但顾盼间颇有几分动人的女性美。在冬窝子,很少见姑娘放羊,哈萨克族有句谚语,说姑娘是家里的客人,意思是姑娘只在这个家里出生、成长,总有一天会嫁为人妇,成为别的家庭的一员,因此要善待女儿,给予客人般的尊重,让女儿像男孩子一样干活是很不像样的。但加玛自初中一年级辍学,已经放了五年羊了。当时的情况是加玛的姐姐乔里潘想去伊犁的师范学校学画画,乔里潘一直是这个家庭的骄傲,从小心灵手巧,看到什么图案都能依样临摹,大家都不忍中断她的梦想,但牧场缺人手,家里唯一的男孩扎达未满十岁,妹妹也还小,于是加玛就辍了学,开始跟着居麻放羊。对此加玛的确有些伤心,虽然已经离开学校五年了,她还能大段大段背诵当年的课文,但加玛毫无怨言,说起姐姐弟弟妹妹的时候,她会滔滔不绝地讲他们的优点:“姐姐画画儿好,跳舞跳得好;妹妹莎拉古丽歌唱得好,学习也好;弟弟最聪明,摩托车都会修,而自己什么也不行,所以只能放羊。”
有一天傍晚,结束完牛棚的工作,李娟和加玛坐在没点灯的家中等待羊群回来。黑暗中,加玛突然唱起歌来,她的嗓音不是很明亮,但却真挚又动人。后来两人出了地窝子,走到星空下赶羊,加玛还是没停止歌声。李娟觉得加玛有些情绪,正如她所料,加玛告诉她说她听说了卡西要去阿勒泰上学的消息。卡西和加玛一样,也是辍学后放了好几年的羊,一直跟家里嚷嚷着要上学,争取了好几年,家里终于同意了。加玛显然非常羡慕,李娟写道,“我不知该对加玛说些什么好。一个姑娘实现了梦想,另一个则再也没有希望一般。”对加玛而言,结束放羊的道路可能就只有结婚了。她跟李娟也提到过结婚的事,来提亲的人家不多,而且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加玛说起这些的时候显得很迷茫。
居麻对加玛是有愧疚的,他一直在说,等到明年夏天,说什么也不让加玛放羊了。他打算给加玛投资一笔钱,让她开个小杂货店。居麻还说把李娟也安排进去,李娟负责进货,加码负责卖货。但说是这么说,加玛其实心知肚明,除了她,这个家中没有另外能放羊的人了。加玛跟李娟透露过她的想法,李娟将之称为加玛“小小的、忧伤的野心”,她想去县里打工,学点手艺,并认为一个月只要有500块的工资就够了,只要能够离开荒野。
在冬窝子刚安定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加玛突然得回定居点,因为奶奶生病了,家里的奶牛和山羊没人照料。李娟想到加玛要走,感到一阵寂寞。但加玛感到很高兴,大约因为“(定居点)有年轻人的世界,有可能前来的爱情,有打工的机遇,有改变生活的可能性”。加玛走后,她托兽医捎来过一封信,居麻认真给李娟翻译了,开头第一句说,“冬窝子里的爸爸妈妈,还有李娟,你们好吗?身体好吗?”李娟写道:“只这一句,就让人想落泪。”
关于荒野里的人,我们就讲到这里。书中李娟不仅记录了居麻一家,还讲到了一些邻居和访客,同样很精彩,碍于篇幅,我们就不展开了,感兴趣的话,可以翻开原书读一读。接下来的第三部分,我们来聊一聊,在广阔的荒野度过一个冬天后,李娟有何感受和收获,她会如何总结这段经历呢?
先来回顾一下李娟在冬牧场做了什么吧:背雪、赶小牛、傍晚赶羊、绣花毡、缝补破衣服、解说电视内容……李娟说,其实通通都不是非我不可的,像她这样的人,在这里多了不多,少了不少,其存在对这个家几乎没什么影响。但反之,李娟觉得自己却受了这个家庭很大的影响。最直接的就是说话时开始不自觉地使用哈萨克语的语法和表达习惯。把吃饭说成“饭的吃”,请人帮忙说成“一个帮忙给下”,没看到羊说成“羊的不看”。
李娟最初来就是带着了解游牧民族的生活,并要借助写作转述这种生活的目的,但这件事远比她想象中的要难。居麻汉语不错,与之交流不成问题,李娟说要是不怕麻烦,坚持刨根问底的话,几乎能了解到一切。但恰恰就是怕麻烦,游牧的生活本就辛苦,还要来个外人整天在耳根子边不停聒噪,李娟没法这样做,所以就还是只能靠自己慢慢体会、慢慢懂得。她一直小心翼翼地观察这里的生活,很多时候她感到自己身在此处,但却离这里的世界格外遥远。比如有一次她和加玛背雪回家,远远看到一支正在休息的骆驼队,两人放下雪袋看了一会儿,加玛突然说这是两家人的驼队,李娟完全不知道她是怎么看出来的,紧接着加玛又说有两个骑马的,还有两个骑摩托车的,李娟还是不知道她怎么看出来的,她既没看到马,也没看到摩托车,又过了一会儿,加玛又说有一个骑马的是姑娘,李娟就更不明白了。就是在这种时候,李娟会意识到自己终归是这个世界的外人。李娟写道:“我和别的‘体验生活’者有什么不同呢?大家要么体验一个星期,要么体验一个月。看上去我好像比他们强了一点,完整地体验了一个冬天。可我也只不过多走了五十步而已……我只不过也是走马观花的一个。”
这还只是了解,将了解到的转述出去就更难了。李娟说有时候你隐隐觉得自己看到了牧人和荒野的命运,但写起来的时候你仍张口结舌、着急又混乱。有时候你很想指出关于牧民生活残忍的事实,但你又忍不住心软,想转过身,想谅解人心所向。有不少评论讲到李娟的散文时,会说她故意避开了苦难,李娟解释说当你真正投身苦难,和苦难的现实产生依存关系,你会本能地调整心态,甚至自我欺骗,积极面对一切,否则活不下去,她的文字是她这种心态的体现。她说,有时候真恨自己的懦弱,但又毫无办法。所以到头来,李娟在这本书记录下的是一段没有答案的生活。如今我们频繁提及“远方”,我们急于想去远方寻找一种慰藉、意义,以及对眼前生活的答案。但李娟揭示的是,远方的生活可能仍然没有答案,生活乃是一个一直寻找答案的过程。
李娟在冬窝子待到2月下旬,赶上学校开学,几个孩子要回定居点,李娟和居麻商量了一下,决定和他们一起回去。出发的头两天,她整顿了一下自己的行李,把一件毛衣和一条围巾送给了加玛,再把经历一个冬天后变得破烂不堪的裤子烧了,早早地穿上了唯一的一条好裤子。居麻联系了司机,说好了这两天能来,但结果等了一个星期,一直到2月底,李娟才坐上车,启程回家了。汽车一路往北开,越往北,雪越大,经过一处又一处被大雪覆盖的村庄、田地、树林,李娟到了家。她写道:“眼下的世界仍被大雪严密地封堵着,白茫茫直到天边,但对我来说,这个冬天已经结束了。之前觉得漫长难捱,如今猛然觉得,竟是那么地匆忙、草率、不知所措。”
到这里,这本书就为你介绍完了,我们再来回顾总结一下。
作者李娟在这本书中记述了自己在阿勒泰冬牧场一整个冬天的前后经过。她用轻盈的笔触记下了动荡、艰辛、寂寞,但同时又温馨、可爱、浪漫的游牧生活,她也记下了一群形形色色,但无一不勇敢坚韧的哈萨克牧民。李娟极尽诚实地书写她体验到的世界和情感,她笔下的“远方”或许没有我们想要的答案,但却给我传递出要去寻找答案的力量,只要一步一步坚定往前走,我们定能找到那个答案。
最后我想为大家送上李娟写在序言中的祝语:“希望人长久,希望大家渐离贫苦,希望大地上一切生命安度冬夏,希望自己变得强大有力——贪得无厌地希望着。”
好,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在散文中,作者无法躲在语言和情节的背后,他必须直面读者,他的真实所感和真实所想直接决定了散文的质量。
如今我们频繁提及“远方”,我们急于想去远方寻找一种慰藉、意义,以及对眼前生活的答案。但李娟揭示的是,远方的生活可能仍然没有答案,生活乃是一个一直寻找答案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