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 杨以赛解读
《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 杨以赛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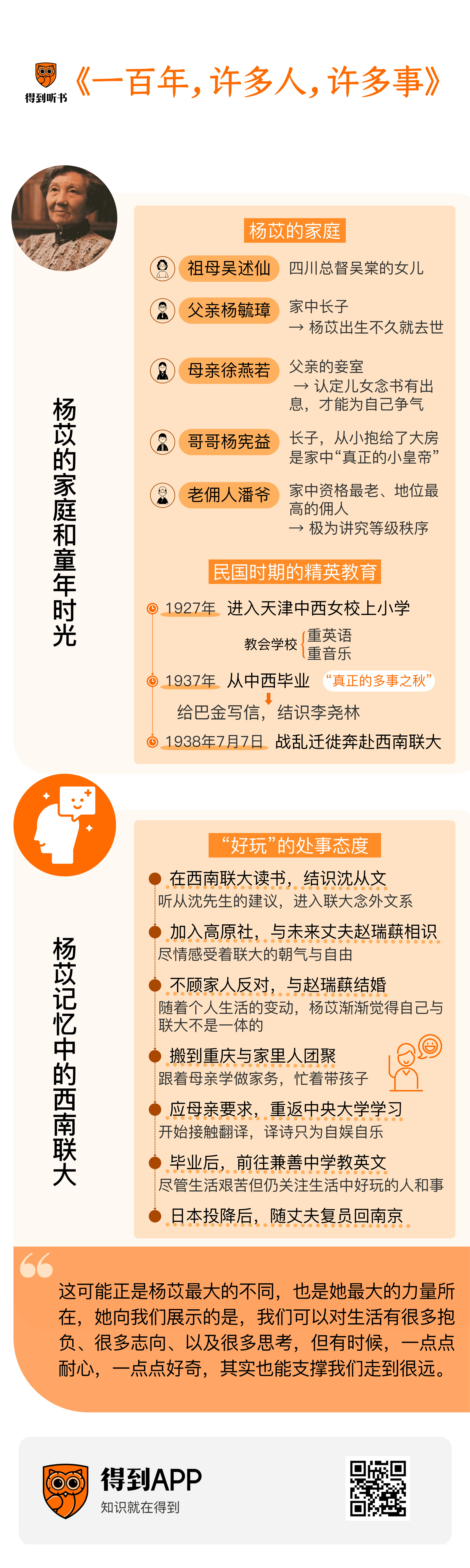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这本书是翻译名家杨苡的口述传记。杨苡生于1919年,历经中国百年的历史变迁,她的传记,既有关时代中的人,也有关人所造就的时代。所以,如果你想要了解人生和时代的话,或许能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杨苡原名杨静如,是中国著名的翻译家、作家。她曾翻译过英国作家埃米莉·勃朗特的 Wuthering Heights,梁实秋先生曾将这一书名翻译为“咆哮山庄”,但杨苡不满意这版翻译,她将之译成了更为传神的“呼啸山庄”,这是公认的佳译。她的家世显赫,祖母是四川总督的女儿,祖父是杭州知府,父亲是北洋政府的高级官员、天津中国银行的首任行长,兄长杨宪益是著名的文学家和翻译家,曾任外文出版社翻译专家,负责了包括《红楼梦》在内的多本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工作。杨苡先生于2023年1月27日逝世,享年104岁。这本《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是她唯一的一本传记 。
本书作者余斌是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张爱玲传》《周作人传》等。余斌在南大结识了杨苡先生,常去她家作客,杨苡善聊,记忆力也极佳,兴致高的时候,聊上一两个小时,不在话下。聊得次数多了,余斌觉得这些内容,实在应该记下来与人分享,就有了做一本口述实录的想法。2019年,杨苡先生跨入百岁,那年年底她生了一场大病,病后她正式提出说,有生之年的一件大事,就是完成这本口述实录 。
这本书的书名里写“一百年”,但实际上书中只讲了1919年到1946年这27年间的内容。余斌将这些内容按时间顺序分为四章:“家族旧事”“中西十年”“从联大到中大(上)”和“从联大到中大(下)”。余斌说,这本书确实只能算作一部分,后续的内容还在整理,而之所以要先出版这一部分,是希望杨先生还在世的时候,能看到一些实际的成果 。这本书在2023年1月出版,余斌在采访中提到说,杨先生拿到书的时候,很激动,还说,“怎么我就随便说说,就做成了这么厚的一本书,只是可惜母亲看不到了。 ”
阅读这本书,可以说是重新了解一段近代历史,只不过它不像其他历史书那般严肃,它是私人视角的,充满了细节和温度的。比如北洋政府总理颜惠庆,民国外交的风云人物,但在杨先生的记忆里,却是小时候在他家玩捉迷藏。再比如文学家沈从文先生,杨先生首先记起的却是他在众人面前讲话,棉袄袖子里掉出棉絮的画面。刘勃老师读完这本书后说,杨先生让我们对历史的感受更具体和更亲切了,“更像是一个人和人的交流,而不是一个人和概念的交流了,这就是这本书不可取代的价值”。除此之外,阅读这本书,也是了解一段人生故事。杨先生虽是出身世家,但在她的叙述中,身份和成就是她最不看重的,她看重的是她的家,她的友情、爱情,她所经历的人和事。余斌说,“杨先生的一生,说平常也平常。然而也正因其平常的一面,也许就更能让读者产生共鸣,传递出‘普遍的人生的回声’ ”。
好,话不多说,接下来我将分两个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第一部分,我们跟随杨苡的叙述回顾她的家庭和童年时光。第二部分,我们则聚焦杨先生成年之后,她一路从天津前往昆明,然后又奔赴重庆,最后安定在南京。这是中国长达八年的抗战史,而对杨先生来说,也是她的漂泊史和成长史。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部分。关于家庭,杨苡从祖母讲起。杨苡祖母吴述仙是四川总督吴棠的女儿。吴棠的发迹之路可谓传奇,据说他早年做县令的时候,有位故交的儿子走水路回原籍安葬父亲,从他那儿经过,吴棠派了仆人送三百两银子过去,结果仆人送错了,送到了另一条灵船上。吴棠知道后,觉得没有讨回来的理,只好又拿了三百两银子送过去。到河边,误领银子的一船人对着吴棠一番道谢,他们是安徽皖南道员惠征的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后来进宫,成了慈禧太后。慈禧一直念及吴棠的这份恩情,入宫掌权后,一有机会就提拔他,吴棠从此官运好得不得了。吴棠的女儿嫁给杨家的长子杨士燮,杨家自然跟着沾光,以至于杨苡的父亲一辈,字里都有个“川”字,就是为了感念做四川总督的吴棠 。
杨苡父亲杨毓璋是家里长子,从日本留学回来后,被安排进了沈阳电话电报局做局长,之后又去到天津,做中国银行的行长。杨毓璋把银行办得有声有色,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还曾送了对联来感谢他对政府的资助 。杨苡在书中说,杨家不少后人,都是靠祖产生活,整天什么事也不干,她父亲要算他那一辈里最能为杨家光宗耀祖的了。
旧式家庭,三妻四妾是常事。杨毓璋有三个夫人,其中杨苡的母亲徐燕若是父亲纳的妾。徐燕若家是在天津开车行的,不算富裕,为了供儿子读书,就把女儿卖给了杨家做妾。徐燕若为此记恨了她父亲一辈子,哪怕后来父亲病重,也不愿再见他。但她仍然为徐家操持了很多,弟弟妹妹读书都是她供的。杨苡在书中说,她舅舅高中毕业,母亲想供他上燕京大学,但舅舅不愿意,写信说不想再花姐姐卖身的钱念书。杨苡母亲听了直落泪,一来心疼舅舅懂事,二来这又勾起了卖身的事,戳到了痛处。妾室在家中地位不高,万事都得低头,杨苡说这个不平等的帽子一辈子也摘不掉。所以,徐燕若认定自己儿女非念书不可,念书才能有出息,有出息才能为她争口气 。
杨苡1919年在天津出生,没几个月,父亲就去世了。起因是一场风寒,本不是什么难治的病,但家里人多,主意也多,加之又有钱,各种治疗方案都想试试,一会儿中医,一会儿西医,最后反而病情加重,没得治了。父亲去世后,杨家随之败落。杨苡在书里总结说,一是没了父亲作主心骨,家中出了不少乱子,比如管钱的七叔挪用家产贩私盐,结果盐船翻了,一大笔家产就此没了;二是父亲太过信任银行,资产大多都存在了银行,后来日本人打过来,强令将中国银行的钱变成储备券,这些钱便不再值钱了 。但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再怎么败落,大户人家的派头也还是在的。
杨苡在书中提到比她大五岁的哥哥杨宪益,杨宪益也是徐燕若所生,只不过作为家中的第一个儿子,从小就抱给了大房,称大房为娘,称亲生母亲为姆妈。用杨苡的话说,他在家中是“真正的小皇帝”。从小吃饭到穿衣,什么都有人伺候,哪怕系个鞋带,也是脚往鞋里一伸,等着用人给系。杨苡小时候爱跟哥哥去逛街,看中什么东西了,只要拉一拉哥哥的衣服,哥哥就吩咐用人付钱去了。有一次逛完街回来,杨苡见哥哥坐着发愣,还眼泪汪汪的,立即大喊了一句“哥哭了”。就这一句,顿时全家大乱,男女老少用人全跑来问是怎么不高兴了。杨苡只好把下午逛街的事一五一十说了一遍,去了哪儿,在哪儿停过,看了一些什么,讲到哥哥把玩过一个手电筒,老仆人潘爷连忙坐家里的黄包车出去,把手电筒买回来了,递到哥哥跟前,谁知哥哥说,太重了,我才不要呢。接着再回想,哥哥还询问过一只小狗。老仆人潘爷又去买狗,买回来后,哥哥说,这是母狗,不喜欢母狗。时隔多年,杨苡回想这件事,她觉得哥哥可能只是太累了,打过哈欠,所以才“眼泪汪汪”,但他的一个哈欠,放家里也是不得了的大事了 。
相对于哥哥姐姐,杨苡笑称,她的“地位是最低的”。母亲认定哥姐是能读书的,但杨苡是笨头笨脑的。母亲从不教哥姐家务活,因为觉得他们用不上,但却要求杨苡必须学。母亲还最要杨苡守规矩,比如吃饭,只吃面前盘子里的菜,不许乱伸筷子,别人夹菜过来,都得让回去,如此一来,杨苡常常觉得没吃饱。她和家中的用人关系好,就是因为他们常给她东西吃。
书中,杨苡也记述了家中的几位用人。比如潘爷,潘爷是家里资格最老、地位最高的用人。杨苡最为记得每当家里来客了,潘爷就会撩起长袍下摆,一路小跑,一路高喊谁谁来了。家里一些关键时刻,都会用上潘爷,比如长房女儿,杨苡称“大公主”,在广州闹离婚,还被人威胁了,家里就派的是潘爷去解围,接回了“大公主”。潘爷极为讲究等级秩序,用杨苡的话说,挺势利的。每每有来客,他都会从上到下把人打量一番,那些他不太看得上的客人,就不往里带,门房聊几句便给打发了。完了还不忘叮嘱杨苡,像这样的人就不要来往了。天津解放后,杨苡带孩子回天津,离开时是潘爷给送到火车站的。母亲特地叮嘱要给潘爷赏钱,到了火车站,杨苡把钱拿出来,潘爷立马单膝跪地说“谢谢六姑娘”,仍是过去的那一套 。
杨苡八岁的时候进到中西女校上小学。天津中西女子中学,简称“中西”,是美国的基督教会“美以美会”创办的一所教会学校。“美以美会”在中国办了不少学校,像赫赫有名的金陵大学和燕京大学 。杨苡在书中说,她很烦总有人拿“贵族”说事儿,但中西女校倒确实是一所比较贵族化的学校。“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的女儿、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颜惠庆的女儿,还有北洋政府交通部总长朱启钤的女儿,都念的是中西 。中西女校每学期的学费要八十几大洋,要知道当时家里女用人的工钱每个月才两元钱,所以普通家庭,是不可能供得起的 。书中,杨苡详细讲述了这民国时期的精英教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教会学校和别的学校最大不同是重英文,小学的时候就用英语授课了,数学、物理、化学都用的是英文课本,文学、古希腊史就更不用说了。除此之外,就是重音乐。杨苡在书中说,“从入校直到毕业,没有一天不唱,在‘歌声’中成长这句话,对我们来说,一点都不夸张。”音乐教育本质是一种情感教育,它教人感受和抒发情感。杨苡特别记得有次朝会,学校里有教员去世了,她们唱起《渡过死海》,歌词里说“这番辞行,我好扬帆,辞别时间空间,远远随了潮头”,一群小孩子,自然不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但唱起歌来,都觉得难过 。
杨苡初中快毕业的时候,国民政府出台了新政策,要求所有学校在“教育部”立案,教会学校也不例外。“教育部”还借此规定,校长必须由中国人担任,并且要提高中文授课的比例,自此之后,像数理化之类的课,就都用中文教了。杨苡在书中着重提及了她的语文老师,其中一位叫范绍韩。范先生对学生很严格,要求学生每周写一篇命题作文,文言和白话轮着来,此外还要求每周至少交两篇周记。范先生常说的是要讲真话,“你怎么想就怎么写,骨鲠在喉,一吐为快”。学生们因此什么都往周记里写,无论快乐还是烦恼,范先生看得很仔细,但从不把这些内容往外说,权当“悄悄话”。有一次杨苡在周记写说觉得自己太笨,不会有什么成就。范先生批了八个字,“不问收获,只管耕耘”。杨苡说,她“后来喜欢写作,爱写长信,多少都和范先生最初给的鼓励有关系” 。
中西的生活完全是象牙塔里的生活,杨苡自己就说,当时对外面的世界、民间的疾苦,真是一无所知的。而实际上,那是很动荡的年代,军阀混战,各派势力打作一团。杨苡记得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学校忽然让学生赶快回家,说是有败兵经过天津。学校顿时大乱,校工们用铁丝网把学校围了起来,还说这铁丝网一会儿是要通电的。杨苡稀里糊涂地跟着姐姐跑到校门口,接人的车停在那儿,乱作一团,喇叭叫个不停,有马被惊到了,拖着车一顿狂奔,很是吓人。但其实当时杨苡自己完全不知道事态的严重性,还在担心当天带到学校的蚕宝宝会不会饿死。
杨苡从中西毕业是1937年,她形容说是“真正的多事之秋” 。7月初毕业,紧接着就是七七事变,中西为了保护校产,在学校里挂起了美国国旗。但杨苡的生活倒是没受多大影响,办了隆重的毕业礼,收到很多礼物,学起了踢踏舞,母亲还因为她成年了开始按月给她零花钱,但她心里却总是感到苦闷的。她在书中说,“我觉得自己和那些参加抗日活动的同学过的完全是两种生活,在这样的大时代里过一种贵族小姐式的生活,我觉得很‘醉生梦死’。”正是在这种苦闷中,杨苡开始给巴金写信。
杨苡一直很崇拜巴金,她觉得巴金在《家》这本小说里写的,和她家简直一模一样。那时很多人在给巴金写信,在那个动荡的岁月,他们都想在大作家巴金这里寻求一份理解、支持,还有指引。杨苡对巴金无话不说,她甚至会仔细描述她夜里做过的梦,最长的一封信有十七页纸。巴金在回信里安慰她,说要把书念好,要有耐心。杨苡说,当时家中与她要好的哥哥出国留学了,巴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她的兄长。巴金还曾在回信里说,在天津可以找他哥哥李尧林,他或许能给一些帮助。杨苡就此结识了李尧林。
李尧林是巴金的亲哥哥,那时在南开中学教英语,后来因为日本人轰炸,炸到南开的教室宿舍,他没地方住了,借住在了一个学生家,顺便就当家教了。杨苡与李尧林见了一面,之后就通上信了。她称巴金为李先生,李尧林比巴金大,她就称他“大李先生”。两人通了有四十多封信,吃了什么,去了哪儿玩,见了什么人,反正什么都说。但两人见面很少,只一起散了几次步。但只是这样,就已经有了一些风言风语。杨苡一直受的家庭教育是男女授受不亲,她当时不太说得清楚她对大李先生的感受,在当时给巴金的信里,她只说,“这怎么谈得上是love呢”。但每当收到大李先生的信,她总是很开心,她在书中说:“甚至不只是开心,是欣喜,因为守着一个秘密,兴奋是翻了倍的,你也可以说,那就是一种幸福感吧。”
有一次,杨苡和几个同学在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开场她就见大李先生坐在后排。散场后,她不自觉就往大李先生那边走,也不敢叫他,只是跟在他身后。出了影院,大李先生才站下等她,然后说要带她去一个地方。他把杨苡带去了海河边,这是杨苡此前从未来过的一个地方。杨苡在书中记述说,“我们站在海河码头一带的岸上,看见远处一艘白色的大轮船缓缓地驶去,一点点变小,最后消失,这景象带给我一种说不出来的新鲜感受。”大李先生那时说,“你就会坐这样的轮船离开你的家乡。”杨苡问,“那你呢。”大李先生回说,“我迟早也是要走的。”
分别的日子很快来临。1938年7月7日,杨苡要就读的南开大学因抗战迁往昆明,她要随学校奔赴西南。那天上午,她背着家人,悄悄和大李先生见了一面。大李先生当时从口袋里掏出一堆碎纸片,那是杨苡写给他的信,他解释说他主张信是不必保存的,随后他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把这些碎纸片抛掉了。两人约好要在昆明再相见,大李先生还在杨苡的纪念册上写下:“虽然离别就在眼前,但是相信不久我们就会见面,希望我们见面时都比现在健壮。”但实际上,那天就是两人的最后一面了 。
那天之后,杨苡踏上了前往昆明的道路。1937年,北平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天津的南开大学南迁至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战争再度逼近,三所大学又迁往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无论在战争史,还是教育史上,西南联大都是不折不扣的传奇。用作家李海鹏的话说,当年这条迁往西南的道路,“是男孩们成为男人们的道路,是中国珍贵又脆弱的大学传统的保存骨血之路,是既在逃难也在进军之路,也是20世纪中国知识阶层的苏生之路。 ”接下来的第二部分,我们跟随杨苡的叙述,来看一看她记忆中的西南联大。
杨苡7月7日上船 ,经上海、香港、越南的海防,然后又转铁路,奔波20多天后,到了大后方昆明。到了后,先住在南屏大旅社。旅社老板说是一位军长的遗孀,叫刘太太,她非常爱国,对流亡西南的大学生特别好,住那儿的头天不收钱。当时昆明不够现代化,房子很老旧,也没有高楼大厦,但杨苡却立马迷恋上了那里的云、树、山、水,她说滇池“平滑得像缎子一样的涟漪是可以直接入画的,直到老年了都还会梦见”。
杨苡先是在蒲草田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又租住在了青云街的一个大院里。当时这个大院住了不少名人,像是沈从文先生,还有民国初年为父报仇刺杀孙传芳的施剑翘 。杨苡住的房间不过四五平方米,屋里只有一张床、一条长凳、一张小破桌。墙是竹篱笆做的,每逢下大雨,雨水从屋檐上泻下来,很容易就进到屋里。但杨苡完全不担心,甚至巴不得被淹一次,她还会不由地唱起在中西学的和雨有关的歌,一边唱一边扭。杨苡说:“到现在当时的情形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当然是因为看到雨‘触景生情’,更突出的却是那时的心境,那时真是年轻。 ”
在青云街住久了,杨苡和沈从文也熟了起来。她回忆沈从文总是一副容易害羞的样子,一口湖南话很绵软。沈从文极为用功,杨苡记得几乎每个晚上,她都会看到沈先生在糊纸的窗后伏案写作,直到深夜才举着灯进卧室。有时沈先生会问杨苡,昨晚写了什么,看了什么,叮嘱她不要犯懒贪玩。杨苡在书中说,沈先生都是笑着说这些话,但其实是很认真的教诲,只是自己一直做不到。杨苡进联大念的外文系,也是沈先生拿的主意。他的意思是,在教会学校学了那么多年外语,扔掉实在是太可惜了 。沈从文有时还会给杨苡抱来一堆世界名著,叫她做读书笔记。杨苡在书中说,沈先生平时低声细语,动不动就脸红,但他其实有自己很倔强的一面。
联大开学定在十月 ,可就在快开学时,日军飞机轰炸昆明,把学校那一带炸得一塌糊涂。其实从九月起,日军就一直在轰炸了,每有日军飞机飞来,城门楼上就会挂起一只红色的气球,警示大家要躲起来。那一阵,所有人早上起来,头一件事就是往城门楼上看,一旦升了气球,就得扛着衣物往郊外山沟里跑,待到天黑再回来。
后来,总不开学也不是事,联大就在轰炸声中开学了。联大的校舍分散在好几个地方,都是借来的,学生每天早上起来,在各处之间跑着上课。老师们都是名家,杨苡印象最深的是大一国文,教课的有陈梦家、朱自清、闻一多、刘文典等,没有教材,他们各自讲各自的研究。有时上着课,警报声响起,学生们就得带上书出城,一点也不慌张。用巴金的话来说,这是“强迫我们游山”。
杨苡在书中说,说实在的我读书不太用功,但联大好就好在它是允许你不用功的。联大气氛宽松,特别自由,去不去上课,根本没人管,只要头一次把听课证给交了,之后一个学期不露面也没事。杨苡的一个同学一个学期找不到人,后来知道是到缅甸跑单去了。杨苡因此参加了不少课外活动。联大学生社团很多,也很活跃,杨苡加入了高原社,这是一个文学社团,当时的团员有后来成为现代诗歌大家的穆旦,以及后来成为杨苡丈夫的赵瑞蕻。
杨苡在书中细致回忆了她与赵瑞蕻相识相交的过程,令人惊讶的是,这个过程一点也不浪漫,也不美满,相反杨苡毫不避讳地流露出一种悔意。作者余斌在采访中说,议论杨先生的时候,经常说到她天真,这天真有时候就表现为别人很忌讳的事情,她却能直接说出来。这背后隐含着的其实是我们对真实的接纳程度,很多人会回避真实,但杨苡不回避 。
杨苡说那时赵瑞蕻一直追她,没心没肺的。杨苡上哪儿,赵瑞蕻就跟到哪儿,连吃饭也跟着,而且最后还是杨苡付钱。有一次两人在小馆吃饭,有人从那儿过,大喊说有个男同学专吃女同学的,赵瑞蕻并不在乎,但杨苡却窘坏了。还有一次赵瑞蕻约杨苡去学校后门的一个偏僻地方,遇上了一个云南兵,云南兵对着他们一通骂,还让拿钱消灾。但他们都没带钱,杨苡说可以拿折子去银行取,云南兵不准两人都去,结果赵瑞蕻去了,留下杨苡在那儿当人质。后来赵瑞蕻回来,只问了一句他们没把你怎么样吧。杨苡很生气,她在书中说,这事我是一直不原谅他的 。
而且那时杨苡其实还在和大李先生通信。大李先生在一封信中说过,他已经买了来昆明的船票。这之后杨苡一直在等,但后来又收到一封信,大李先生说把船票退了,退票原因等见面了再说。杨苡不免有些生气,后来还从朋友口中听到大李先生晚上常和一个人去溜冰,就更生气了。要到很后来,杨苡晚年了,才知道这其实是一个误会,大李先生退票可能只是经济上的原因,他当时的情况,连买双皮鞋都要犹豫再三。杨苡对大李先生,一直是有自卑的,不敢表露这份感情,只说是崇拜,她后来觉得她只顾自己自卑了,没想过大李先生可能也有他的自卑,他也会因为他的年龄和家境,在爱情上选择退缩 。总之,两人就此错过了。杨苡当时把赵瑞蕻对她的追求一五一十跟大李先生讲了,信里还曾用到“纠缠不休”这个词。大李先生回信说,我一向关心你的幸福,希望你早日得到它,既然赵瑞蕻这样追求,你为什么不接受他的爱呢。杨苡当时心想,那你让我接受,我就接受吧。后来大李先生曾跟友人说杨苡结婚是跟他赌气,这是句玩笑话,但杨苡在书里说,他也许是说中了。
杨苡和赵瑞蕻的婚事,家里是很不满意的,但无奈当时杨苡怀孕了。两人没办婚礼,就在昆明西山上订了个旅馆,招待了一些朋友。杨苡在书中很坦诚地说,关于昆明,关于联大,她的记忆有两个部分,头两年,她尽情感受着联大的朝气与自由,但后来随着个人生活的变动,事情不那么愉快了,她渐渐觉得自己与联大不是一体的了,也就不愿再回想了。她和赵瑞蕻,搬过好几次家,一边躲轰炸,一边抚养刚出生的女儿赵苡,日子过得很难。沈从文有一次来看杨苡,他对她就这样结婚是不满意的,但还是各种帮忙,还叮嘱杨苡,不能有了孩子就什么都放弃了,还是要做事。
而另一边,杨苡家里人也因战争迁往西南大后方,到了重庆,母亲一直来信让杨苡来重庆。杨苡是犹豫的,一方面她还想完成学业,另一方面又实在想换个环境,不想老和赵瑞蕻在一起。后来母亲见她迟迟不来,干脆托人买了机票,送到了杨苡手中,杨苡闷头去了重庆 。
在重庆,她和母亲、姐姐住在了姐夫租来的一处院子里。母亲对赵瑞蕻不满意,起初看了孙女赵苡的照片,也不满意,但真的见到的时候,又喜欢得不行。那一阵,杨苡就跟着母亲学做家务,忙着带孩子,她在书中说,“我是真正当家庭妇女了”。两个月后,赵瑞蕻也从昆明来了重庆,他到了一所中学教书,后又去了中央大学柏溪分校当助教。而杨苡则开始在南开中学代课。不过只教了一个学期就停了,因为当时杨苡还没拿到大学文凭。这事刺激了母亲,她要求杨苡回学校上课,孩子就交给她来带。回联大是不可能了,但好在当时各校之间的学分是互认的,在中央大学借读,修满学分,也可以拿联大的文凭。杨苡于是又考进了中央大学,重新开始了学生生活。
按理说,时隔一年回学校,重新过集体过生活,会有些不适应,但杨苡说她一点也没有,甚至还很兴奋。中央大学与西南联大是两所很不一样的学校。两所都是当时国内最有名的大学,但联大宽松自由,没什么禁忌,学生自由散漫,而中大则有不少规章制度,比如每天早上要吹号叫学生起床,中大的学生会更用功,更在乎考试和成绩。但杨苡倒是没怎么改变自己的作风,她说,“在联大我不是好学生,在中大也还是不用功”,她甚至因为花太多时间泡茶馆,而被同学告状到了系主任那儿,说这个样子,考试怎么能过呢。
大四那一年,杨苡上了一门课叫“维多利亚时期的诗歌和散文”,她尤为喜欢勃朗宁的诗,逐渐就做了一些翻译。不过她说,她当时译诗就像她写诗一样,纯粹是自娱自乐,没想过要发表的事。与此同时,丈夫赵瑞蕻也在着手翻译《红与黑》,他比杨苡用功,一直不停地在写、在翻。杨苡说在翻译这件事情上,她与赵瑞蕻可以说是“志同道不合”,从对诗歌的喜好,到翻译的方法、习惯,再到这背后人的性格和教养,差别都很大 。有一阵儿,杨苡想过要不要与赵瑞蕻离婚,她还去问了母亲。母亲说,你结婚的时候不来问我,这时候来问我了,我不管。在离婚这件事上,杨苡也就只是想了想,她担心这会影响孩子,后来她又有了二女儿赵蘅,离婚就更不可能了。
中央大学毕业后,杨苡去了兼善中学教英文 ,这时抗战快到尾声了,但谁也不知道究竟还要多少年,日子依然是有些艰苦的,心情也有很多的苦闷的时候。但杨苡在书中没太讲这些,她依然在讲的是生活中好玩的人和事。比如她讲重庆很大一只的老鼠,讲她是怎么用老鼠来吓唬女儿,让女儿听话;她还讲她去排话剧,从母亲这儿求来了一件银狐大衣去当戏服。作者余斌在本书的后记里说,杨苡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就是“好玩”,“好玩影响到她的记忆和对记忆的筛选,这后面未尝没有一种观人观世的态度”。甚至可能这种“好玩”的处世态度,支撑着杨苡走过了外在和内在的种种动荡 。
1945年,日本终于投降。8月15日当天,街头卖报的一路高喊“日本鬼子投降了”,所有人都跑到外头,到处都是欢呼声和鞭炮声。但紧接着,对普通人来说,他们要考虑的是回家问题。杨苡在书中回忆说,八年流落他乡,一时之间,所有人都在寻找回乡的法子。这可不是说走就走的,要抢交通工具,要处理这八年的家当。那一阵儿,重庆街头到处都是摆地摊卖东西的,杨苡也拿着不要的毛衣旗袍去卖了 。
赵瑞蕻当时在中央大学任助教,要随中央大学复员回南京。中央大学包了一艘大轮船回去,但教职工本就多,再加上各自的家属,根本安顿不下。杨苡一家只能是睡在甲板上。甲板上用粉笔画好了,一家一块地方,也就一米来宽。刮风下雨了,没处躲,就拿准备好的雨布盖在身上。一家人就这么到了南京。杨苡在书中记述说,“船是下午到的南京,一看见下关码头,船上的人就激动起来。船上有许多是南京本地人,南京是他们的家,九年了,有家不能回,这时见了家乡,大哭起来,好多人一起哭,泪流满面。我想起三八年从越南那边入关的情形,当时大家见着国旗,兴奋得又哭又跳。那时我十九岁,现在人到中年,有了两个孩子,没有那样的兴奋了。不是南京人,我对这里是陌生的,只是想,船上的日子结束了,流亡的日子总算结束了,生活该安定下来了吧。”
本书就在这里戛然而止了。这之后,无论家里还是家外,还发生了很多事情,动荡的程度,一点不比战时少。杨苡也逐步走向了翻译的道路,她先是在南京的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担任翻译工作,翻译了《罗马帝国衰亡史》和《马可波罗游记》 。1954年,她开始了《呼啸山庄》的翻译工作,她曾在一次采访中回忆说,当年翻译这本书,窗外狂风大作,她嘴里不断念着这本书的英文书名,Wuthering Heights,突然就想到了“呼啸山庄”这个名字。她说:“我告诉你呀,这就是种玩法,我一直觉得翻译就是好玩。”
晚年的杨苡,依然爱看电影,也爱写信,103岁接受采访时,也依然是神采奕奕、兴致勃勃的。她后来常提到《基督山伯爵》结尾的一句话,这句话在她17岁写信给巴金的时候就已经用上了,那就是“等待和希望(Wait and hope )”。我们再回望杨苡的一生,从显赫的旧式家庭,到军阀混战时期的中西女校,再到昆明的西南联大、重庆的中央大学,最后再定居南京,贯穿始终的不正是这句话吗——“等待和希望” 。
余斌在杨苡去世后,写了一篇纪念的文章,当中他说,杨苡的等待不灰暗、不怀疑、不焦虑,也不虚妄,相反是充满人情和温暖的。从前面的这些内容,你应该也能感受到,在杨苡的叙述中,她注重的是自己的所见所闻,和当下那一刻的真实感受,其中思考和启示一类的东西很少,她讲的就是她的生活本身。这可能正是杨苡最大的不同,也是她最大的力量所在,她向我们展示的是,我们可以对生活有很多抱负、很多志向,以及很多思考,但有时候,一点点耐心,一点点好奇,其实也能支撑我们走到很远。余斌在那篇纪念文章的最后写道:“未来对于杨苡先生和对于我们一样,没有剧透,我相信如果历史早晚会成为故事的话,她会有好奇心和我们一起听下去,听下回的分解。她会以她的乐观、达观陪伴着我们,等待,并且不放弃希望。”
好,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
杨苡生于1919年,历经中国百年的历史变迁,她的传记,既有关时代中的人,也有关人所造就的时代。
-
“杨先生的一生,说平常也平常。然而也正因其平常的一面,也许就更能让读者产生共鸣,传递出‘普遍的人生的回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