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传染效应》 王朝解读
《行为传染效应》| 王朝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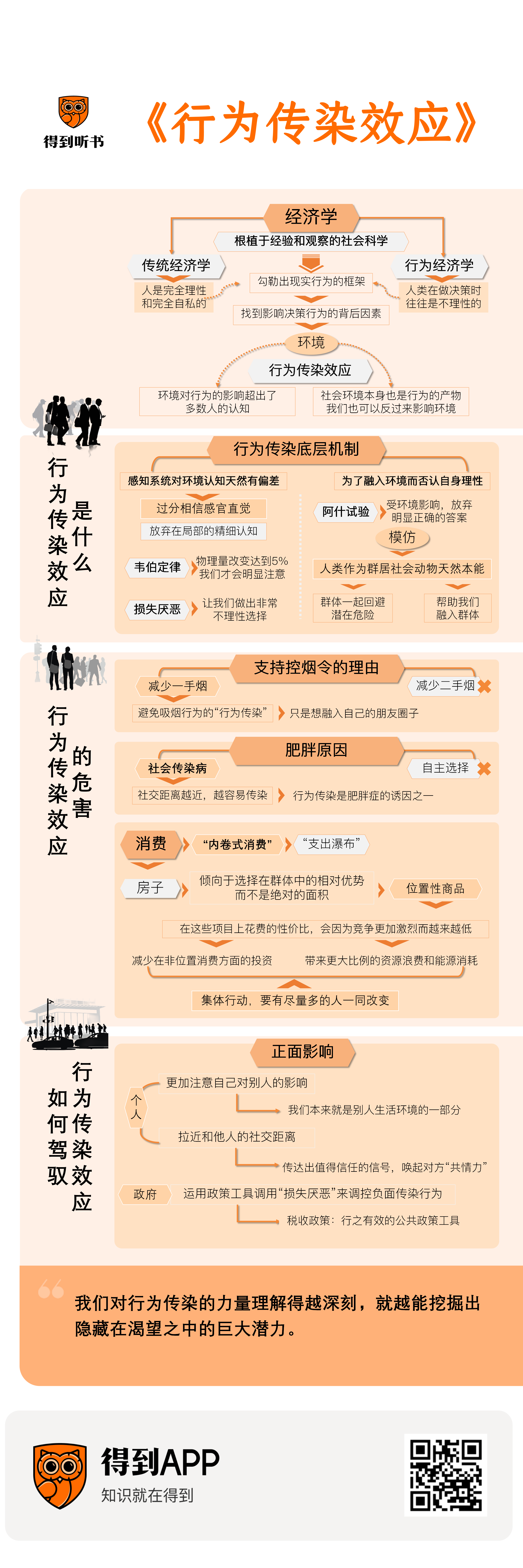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以前有过一个新闻,说很多网红店排队时间动辄要几个小时,其实是他们专门花钱找人来自己的店门口排队,形成一种生意火爆、门庭若市的“假象”。我以前就产生过疑问,这是什么原理?为什么人们只要看到有排长龙的地方,就会去“凑热闹”一起排队?
其实这个现象背后的原理,就是“行为传染效应”,也就是今天这本书的标题。这本书里,也提到了一个中国的实际案例。创办新东方的俞敏洪曾经说过,当初新东方也有招生难的问题,但是他发现,最关键的是最先报名的那十个人,如果已有十个人报名,后面招生就会容易得多。如果有三十个人报名,那后面再报名的人来了就交钱,不会再有什么其他的疑问。中国也有一句古话,“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些只是经验性的总结,而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特别是行为经济学领域,这些现象受到了相当的重视,已经有非常多的研究成果来描述、解释、利用这种效应,这本书就是为你介绍这个我们习以为常的小现象,背后还有什么样的大智慧。
这本书的作者罗伯特·弗兰克,是一名行为经济学家,担任康奈尔大学约翰逊管理学院经济学和管理学教授,也是《纽约时报》的特约评论员,而且他还特别擅长把深奥晦涩的经济学理论变成通俗的大白话。他与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合著的《宏观经济学原理》和《微观经济学原理》,曾经被评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经济学教材”。你可能还听说过他的另一本畅销书《牛奶可乐经济学》,那是他在课堂上要求学生用经济学原理解释身边的日常现象的作业,然后他再把其中的优秀课题结集成书。而这本《行为传染效应》,按照他在书中说的,自己年岁已大,所以这本书很可能会是他的封笔之作。因此,在这本书中,既有弗兰克作为一个学者的深刻洞察,也有他对解决气候变化等社会问题的热切呼吁。
弗兰克认为,经济学不能只是以数学为核心的硬科学,要分析真实的社会运转,经济学还得是一门根植于经验和观察的社会科学。弗兰克所研究的行为经济学挑战了传统经济学的“理性行为者”模型,这种模型会在分析的时候把个人看作是完全理性和完全自私的,而行为经济学则认为这并不符合现实中的人类心理,他们借用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大量使用了实验方法,观测人类在真实环境中的反应。书中说,社会心理学家认为,当人们试图解读一个人的行为时,经常过度关注其能力、个性等内在因素,却忽视了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社会心理学家称之为“基本归因误差”。行为经济学家们据此认为,人类在做决策时其实往往都是不理性的,而他们的目标就是在这些理性和不理性交织形成的复杂现实中,勾勒出现实行为的框架,找到那些影响决策行为的背后因素。
其中,环境对决策影响最突出的一个效应,就是行为传染效应,也就是我们会不自觉地模仿别人的行为,也就是被“传染”。他在这本书中反复强调行为传染效应有两层意义,第一层,是“环境对我们行为的影响超出了多数人的认知,这种影响有时是正面的,但更多的时候是负面的”。第二层,则是要意识到社会环境本身也是行为的产物,“那些影响我们选择的环境本身是一个由多个个体选择组成的集合”,所以我们也可以反过来影响环境。
接下来,我们就先谈谈“行为传染”到底说的是什么,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然后,我们再顺着作者的思路,看看我们如何能够反过来影响环境,应对这个时代的挑战。
好,首先我们先来讲讲“行为传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实际上就是要说清楚,我们的行为,是如何被环境、被他人所影响,而我们还不自知的。行为传染的底层,其实是几个机制,第一,是我们的感知系统对环境的认知天然就有偏差,会因为环境的不同而改变参照物;第二,是我们为了融入环境而否认自身的理性,去模仿别人。
先来讲第一个机制,就是我们的感知系统存在偏差,而我们经常过分相信我们的感官直觉。这个偏差的核心是人类的感官和大脑对整体变化、相对变化更加敏感,而经常会放弃在局部的精细认知。相信你肯定见过很多那种视错觉图,比如左右各有一个同样大小的圆形,但是左边的圆被一圈比它更大的圆包围住,而右边的则被更小的圆包围,我们的大脑就会认为左边那个圆形要小一些,右边那个要更大一些。对我们的大脑来说,我们并不是单独地认知一个一个圆形,而是把每张图上的圆形都作为一个整体来认知,所以两个一样的圆形就会因为参照物的差别而显得大小不一。
那么局部的细微差距大概到多少才会被我们的感官系统捕捉到呢?在心理学上还真有这么一个“韦伯定律”,用来表示感觉的下限。简单来说,只有一个物理量的改变达到5%,我们才会明显注意到。比如说,如果一个灯泡的功率为100瓦特,另一个灯泡为101瓦特,绝大多数人是说不上来哪一个更亮的,而如果另一个灯泡是105瓦特,才会让人明显注意到更亮了。从这个定律可以得知,比九五折更少的折扣就是无效打折。而韦伯定律还有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区分不同的外界刺激之间的细微差别的能力,会随着刺激的加强而下降。再举个例子,现在一个筐里有十个鸡蛋,另一个筐里有二十个鸡蛋,你很容易看出来哪一个鸡蛋更多。但如果一个筐里有100个鸡蛋,而另一个筐里有110个,虽然也是十个鸡蛋的差距,但想要判断哪个筐里的鸡蛋更多,就变得困难了很多。有学者推测,我们的感知系统之所以有这种特征,还是源于人类祖先求生时的需求,“知道你面前的狮子有5只还是3只,比知道你正在追逐的鹿群是100只还是98只更重要。”
除了这种整体认知带来的模糊感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偏差,就是人类对损失更加敏感。弗兰克说:“相比努力去获得尚未拥有的东西,人们更愿意花更多的精力去保护他们已经拥有的东西。我们把这种非对称性称为损失厌恶。”
这种损失厌恶会让我们做出非常不理性的选择。有一个实验,假设现在出现了一种流行病,如果不采取措施,将会造成600人病死。研究人员把被试人员分为两组,其中第1组被告知有这样两个方案:
1.如果采纳A方案,将有200人的生命获得挽救。
2.如果采纳B方案,将有1/3的概率挽救600人的生命,但也有2/3的概率没有任何人获救。
结果,第1组被试有72%的人选择A方案,28%的人选择B方案。也就是说,为了避免那三分之二一个人都救不了的概率,他们宁愿直接放弃400个人的生命,选择确定的200人获救。
而在第2组,实验人员给出了如下两个选项:
1.如果采纳C方案,400人将会死去;
2.如果采纳D方案,有1/3的概率可以拯救所有人,但也有2/3的概率600人都会死。
结果,22%的人选择了C方案,剩下78%的人选择了D方案,也就是冒着全军覆没的危险尝试拯救所有人,避免400个人的确定死亡。仔细想想,A方案和C方案是完全一样的,而B方案和D方案也是一样的,甚至四个方案的数学期望全都是一样的,区别只是在于B和D有风险概率,而且第二组的选项描述整体强调的是损失。这就是“损失厌恶”对我们的决策过程的干扰,因为想要避免损失,反而丧失了对环境中风险的理性判断。
刚才讲的是对感官的过分自信,再讲第二个机制,也就是融入环境而放弃理性,甚至连自己的感官都不再相信,这里我们可以了解一个经典的“阿什实验”。这个实验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社会心理学先驱阿什教授所做的。实验内容很简单,就是找几个人来看两张图,第一张图上有一条线段,而第二张图有长短不一的三条线段,被试者需要从第二张图当中,找到和第一张图的线段一样长的那一条。听起来这好像是一个比拼眼力的实验,实际上,第二张图里的长短非常明显,只要一眼就能看出正确答案。有趣的地方来了,阿什在这里埋了一个陷阱,被试者并不知道,和自己同组的其他所有人,看起来和自己一样都是来参加实验的被试人员,其实都是阿什安排的演员,按照阿什的安排一致选择了另一个错误答案。没错,阿什设计这些实验的初衷,就是评估外部的环境因素会在多大程度上让人们忽视自己独立感知到的,而且有明确依据的答案。
中国俗语说“三人成虎”,在这个实验里足足有六个。想象一下,原本非常简单的问题,突然出现了好几个和你不同的答案,而且还非常一致,你还会坚持认为自己的答案是对的吗?可能很多朋友会很自信,“我的眼睛就是尺”,觉得自己会排除别人的影响,坚持正确答案。但实验的结果,可能会让你惊讶。如果没有那几个“猪队友”在旁边,独立决策的被试者回答正确率超过了99%,这是非常正常的。但加上了这几个演员,就会有37%的人选择否定自己的眼睛和理智,一起选择错误答案。而在后续的访问中,很多人甚至坦承自己知道这是错误答案,仅仅是为了与同组人保持一致,才做出随大流的选择。就连有标准、明确的正确答案的问题,还能有这么高比例的人会被传染,可想而知其他场合得有多少人都会被环境所动摇,模仿别人。
这种模仿,其实并不是一种缺点,而是人类作为群居动物、社会动物的一种天然本能。一方面,模仿帮助我们和群体一起回避潜在危险,在当年那个危机四伏的自然环境中,如果看到身边的人都开始拔腿狂奔,最好跟着一起狂奔,谁知道后面跟着的是什么东西?另一方面,模仿能够帮助我们融入群体。曾有一个心理学实验发现,在合作任务中,人们会对模仿自己行为的伙伴产生更多好感。这种模仿本能深深印刻在我们的神经系统中,大脑里专门形成了一个脑镜像神经元系统,实时记录我们与其他人互动时对方的一切活动,并且随时准备调动我们的神经系统来模仿,打哈欠的“传染”,就和这个系统有关。
这就是所谓“理性行为者”的真实情况。不仅我们对周围环境的具体感知并不精准,对相对变化和损失更敏感,而且就算我们的感觉精准,也可能会被环境“带跑”。即便是在正确答案很清楚的情况下,如果当身边的人都选择明显的错误答案时,竟然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会被带偏,放弃理性的选择。
我们的“理性”如此脆弱,实际上我们的生活中到处都是行为传染效应。就比如开头说过的网红店,因为人们会更喜欢选择本来人就很多的餐厅,而不是没有人的新店,所以店家不惜要雇人来排队,吸引人们跟风。但我们刚刚讲到,我们人类对损失更加敏感,所以这里我们先来讲讲环境对我们的负面影响。
比如书里反复解释的抽烟的传染。以往解释控烟令,我们一般都是说,因为公共场合的二手烟会对周围人群造成防不胜防的伤害。但作为一名14岁就开始抽烟的行为经济学家,弗兰克说这并不应该是禁烟的最大理由。
他反驳说,数据显示,在美国,肺癌导致死亡的病例中,有85%的人可以归因为主动吸烟,而剩下的死亡案例中也仅有非常小的比例与二手烟相关。因此,就实际效果而言,这些控烟措施对保护吸烟者免受自身伤害的作用远大于保护暴露于二手烟环境中的无辜民众。同时,由于吸一手烟对身体的巨大危害,吸烟者日后可能因为吸烟患上各种疾病,会给医疗系统带来更大负担,挤压不吸烟者的医疗资源。
所以在弗兰克看来,支持控烟的最合理理由不是减少了二手烟,而是减少了一手烟,是因为这样能够避免吸烟行为的“行为传染”。他说,“一旦一个人决定成为吸烟者,他周围的人吸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这才是吸烟最大的危害。”这一点也有数据支持。由两个美国经济学家做过一个全国统计,他们发现某个青少年周围同学的吸烟率每提高10%,该青少年吸烟的概率就会提高3%。而且关系更加亲密的朋友的影响比同学更高,如果是亲密朋友的吸烟率提高10%,那么该青少年吸烟的概率就会增加5%。我们可以想象一个100人的群体,吸烟人数如果提高10%,从10人变成20人,那么吸烟人数就会额外再增加5%,变成25人,而因为总体吸烟率又提高了5%,这又会传染另外2.5%,以此类推,就像滚雪球一样,经过一个简单的极限计算,最终我们会发现最终增加的吸烟者数量将是初始增量的两倍。如果没有外部压力,会有越来越多人因为行为传染效应而不断卷入吸烟,而他们抽烟时可能根本没有想过自己日后需要付出什么样的健康代价,只是想融入自己的朋友圈子。
事实上,不少研究都表明,绝大多数烟民都曾希望戒烟,或多或少都后悔染上烟瘾,但是九成烟民都会遭遇戒烟失败。欧盟还有一个调查,发现七成的吸烟者都支持增加吸烟有害健康的标识。更有意思的是,在2005年的一项研究中,哈佛大学的经济学者乔纳森·格鲁伯发现,吸烟倾向强烈的人更喜欢在烟草税更高的地区生活,这些人很有可能也是想要通过环境的力量帮助自己戒烟。
我查询了一些数据,在通过烟草税、公共场合禁烟等等手段,提高吸烟消费的门槛之后,美国的吸烟人口比例逐年下降,从20世纪60年代的超过40%,到了2023年就只有12%了。如果我们仅仅用“控烟能够减少二手烟”来解释控烟的好处,就忽略了这方面的成功。就像弗兰克,因为他周围的同学早就开始吸烟,所以他14岁就成为烟民,但因为整体吸烟率的下降,他的四个孩子没有一个吸烟的。
类似的情况还包括肥胖。在书中,弗兰克引用了一个2007年的开创性医学研究,这个研究的数据来自在1971—2003年期间对12000多人的心脏病跟踪研究,其中包括了受访者历年的BMI指数,也就是用一个人的体重(以千克为单位)除以身高(以米为单位)的平方得到的商,超过25就属于超重,再超过30就是肥胖范畴了。同时,数据记录也包括受访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这使得研究者可以观察到一个人体重的增加与他的朋友、兄弟姐妹、配偶和邻居们体重增加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虽然肥胖看起来是一个自主选择,但实际上却是一种“传染病”。假设小王和小陈原来都不胖,而小王认为小陈是自己的朋友,那么一旦小陈成为肥胖者,小王变成肥胖者的概率会增加57%。如果小王和小陈互相视为朋友,那么这个效应会显著放大,小王变成肥胖者的概率会增加171%。
而且这种效应也会发生在夫妻之间,如果丈夫变成肥胖者,那么妻子发胖的概率会增加44%;妻子变胖也有类似的效果,即丈夫发胖的概率会因此增加37%。但是,一个人体重的增加不会受到隔壁邻居体重增加的影响,而朋友之间的影响不会因为地理距离而衰减。换句话说,肥胖是一种社会传染病,社交距离越近,越容易传染。
研究者得出结论,“如果某个人的社会关系网中有肥胖者,他对肥胖的容忍度,以及他对某些具体行为(比如吸烟、饮食和锻炼)的接受度都可能会受到影响。除了这种严格的社交传导机制之外,还可能出现心理上的模仿:观察到别人做出的进食等行为,会刺激大脑中与之相关联的某些区域。因此,推导出行为传染是肥胖症的诱因之一的结论,是有一定依据的。”
除了抽烟、肥胖,饮酒其实也有类似的传染效应,这里就不重复了。接下来要讲的是,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身体损伤的风险:消费。你会发现,我们有很多消费是“内卷式消费”,或者用书中的术语,叫“支出瀑布”。
我们先来尝试回答一个问题:选项A是:你和家人住的房子面积为200平方米,同小区其他所有的房子都有450平方米那么大。
选项B是:你和家人的房子面积为150平方米的街区里,同小区其他所有的房子都只有75平方米那么大。
你会选择哪一个?相信大多数人都会选择B。
经济学家发现,在房子这种商品上,我们更倾向于选择在群体中的相对优势,而不是绝对的面积。英国经济学家弗雷德·赫希创造了一个术语,叫“位置性商品”,意思就是这种商品的价值来自相对的稀缺性,而非绝对的价值,或者说,它们的价值主要取决于与同类商品比较的结果,越是显眼、容易被观察到的消费项目,越容易拥有“位置性”。弗兰克说,为了维持相对优势,行为传染效应会极大放大位置性商品在我们心中的价值,导致我们在“位置性商品”上的开销不成比例地增加。
比如房屋,美国建造的房子的面积中位数,由1973年的140平方米,增长到2020年的230平方米;并且因为现在中位数的房子里的居住人数更少,所以目前平均每个人的居住面积几乎是1973年的2倍。但是不是美国人的平均生活质量变高了呢?恐怕并没有,美国经济学家已经发现,在夫妇中只需要一人养家糊口的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家庭都能在预算范围之内过上舒适的生活,而在20世纪90年代,双职工成为普遍现象之后,反而有许多家庭变得入不敷出。
为什么会这样呢?简而言之,美国顶级收入阶层的高消费,改变了下一级收入阶层的人群对于“足够”的参照系的定义。由于美国占据最高位置的巨富阶层的财富增长更快,房子面积不断增长,所以同等面积房子的相对位置感在不断下降,而中产阶级为了维持和更高层的距离,害怕被甩得太远,就被卷入了“支出瀑布”,跟着前面的消费者一同不断提高房屋的支出。弗兰克指出,在美国,最富有的1‰的那部分人和其他人相比,同一时期内的收入总额增加了6倍以上。比如美国最大企业的CEO们,2016年,他们的收入是普通工人的347倍,而在1980年仅仅为42倍。
其他位置性消费领域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更华丽的婚礼、更豪华的汽车、更精致的生日派对等等。并不是说,这些不能给我们带来快乐,而是说,我们在这些项目上花费的性价比,会因为竞争更加激烈而越来越低。你可以把这理解为“位置性军备竞赛”。弗兰克担心,当我们在这些方面花费过多的钱,超出了理性娱乐的限度,就势必减少在非位置消费方面的投资——比如健康,比如公共投资。而且,它也势必会带来更大比例的资源浪费和能源消耗,对环境造成威胁。
位置性商品的支出瀑布影响极其普遍,不仅发生在家庭消费。比如赫希解释说,“我的教育对我的价值,取决于和我竞争同一份工作,但排在我前面的人的受教育程度。”这其实就是现在普遍学历内卷的一大原因,随着求职者不断提升学历,学历的价值其实反而在不断下降,为了克服这种下降,求职者只好追求更高的学历,恢复自身学历的价值。
就像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军备竞赛无法通过单个国家实现一样,阻止社会陷入支出瀑布的内卷,也需要集体行动,要有尽量多的人一同改变,那么最后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如何驾驭行为传染效应,对环境施加正面影响。
好,讲了这么多环境对我们的负面影响,我们最后看看自己能给环境带来哪些正面影响。
就像书里说的,行为传染效应既是问题,又是答案。首先,最容易理解的一点是,我们要更加注意自己对别人的影响,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别人生活环境的一部分。就像前面所说的吸烟、肥胖和饮酒的传染,自己就会成为某一个链条的起点。所以古话说“勿以善小而不为”,此时就找到了行为经济学的原理支撑。弗兰克希望,有读者可以成为社区里第一个放弃大排量汽车、改用清洁能源汽车的家庭,或者是社区里最注重节能的家庭。
第二,弗兰克还指出,如果我们想增强我们对别人的影响力,就需要拉近和他人的社交距离,也就是要传达出值得信任的信号,唤起对方的“共情力”。此时,更具有传染性的并不是理性解释,而是情绪。就像模仿他人的肢体动作可以唤起对方的好感,和对方共情,也能让对方相信自己不仅仅是在考虑自己的利益,也是在考虑对方的利益,增加自己行为的“传染力”。
第三,也是弗兰克展开大量论述的,是政府可以运用政策工具调用“损失厌恶”来调控负面传染行为。弗兰克指出,税收政策是一项已经在行为经济学上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公共政策工具。他的一些建议已经开始深入讨论和实施,比如对碳排放和高污染征税,也有一些值得进一步讨论,比如用累进税率可以抑制巨富阶层的奢侈和浪费,进而控制支出瀑布,避免普通家庭陷入内卷的浪费之中,提升相对位置提高获得的幸福感。这些举措具有很强的公共意义,是弗兰克作为学者的最后谏言,但是其中也有明显的美国背景,这里就不再展开。
最后,还有一个小问题,我们如何不成为阿什实验里那从众的三分之一呢?在一开头提到过,行为传染效应有两层意义,第一层是我们受到环境影响而不自知,而现在,你已经知道了自己所受到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开始注意自己在哪一些方面是受到环境影响的,最后的决策结果是否合理?然后再到第二层,社会环境本身也是行为的产物,我们要注意,我们和朋友、亲人之间已经建立起信任关系,自己有没有什么可以和大家一起再进步的地方。就像弗兰克最后说的,“我们对行为传染的力量理解得越深刻,就越能挖掘出隐藏在渴望之中的巨大潜力”。
好,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对书中其他内容还有兴趣,也建议你去阅读原书。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1.行为传染效应是指我们会不自觉地模仿他人行为,而环境对我们行为的影响往往超出我们的认知。这背后有两个主要机制:一是我们的感知系统对环境认知存在偏差,更敏感相对变化;二是为了融入环境,我们会放弃理性去模仿他人。
2.行为传染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吸烟、肥胖等不良行为会在人群中迅速蔓延。此外,还会导致消费的内卷,人们为了维持相对优势而过度消费一些“位置性商品造成资源浪费。
3.我们要学会驾驭行为传染效应,发挥它的正面作用。比如注意自己对他人的影响,主动传播正面行为;拉近与他人的社交距离,增强自己行为的“传染力”;政府也可以用税收等政策工具来限制和引导行为的传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