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裂痕生活》 杨以赛解读
《带着裂痕生活》|杨以赛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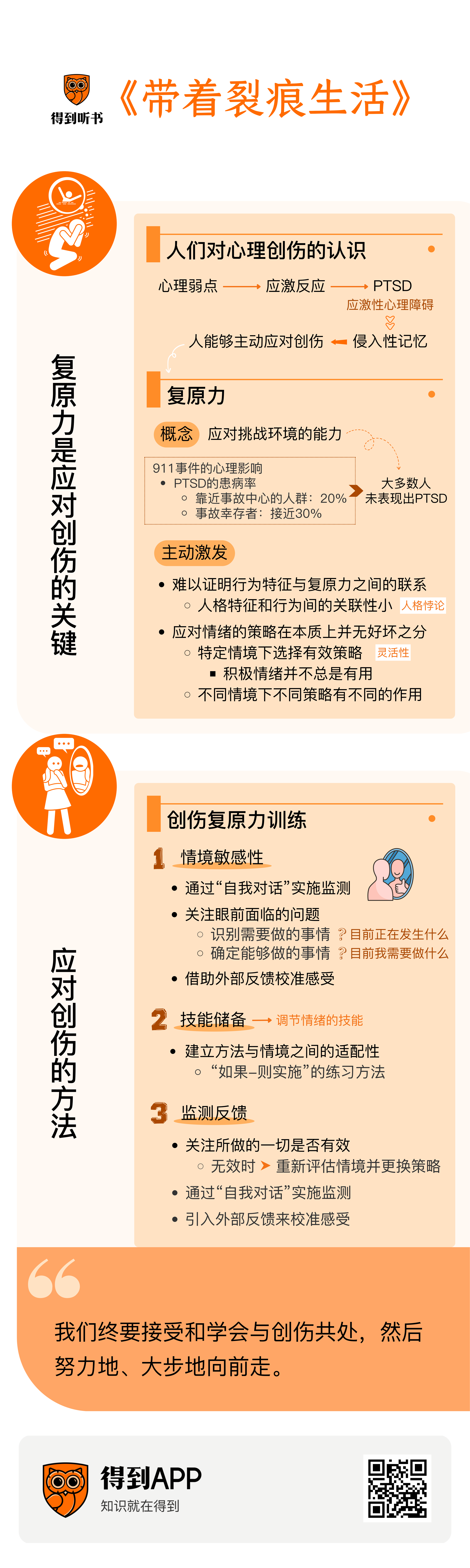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带着裂痕生活》,副标题是“复原力如何帮助我们应对创伤”。
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过创伤经历,心理学自诞生以来就一直试图帮助人类解决创伤问题。这种伤痛不为人所知、一旦刻下就难以消除,并在无形之中不断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究竟要如何理解创伤,以及如何与创伤相处,今天的这本书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这本书的作者叫乔治·博南诺,他是哥伦比亚大学临床心理学教授,是心理咨询和临床心理学系主任,多年来他始终聚焦对丧失和创伤的研究,他也因此在2019年获得了美国心理学会最高荣誉“詹姆斯·卡特尔奖”。
在这本书中,乔治·博南诺梳理了学界对于“心理创伤”的认识及变化,并指出了他认为当中存在的误区,同时他近距离接触了许多创伤事件的幸存者,试图从他们的亲身经历中,找寻一套应对创伤的方法。博南诺试图用这本书来证明和强调:我们的身体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强大。
好,接下来,我将分两个部分来为你解读这本书,第一部分我们来重新认识“心理创伤”这一概念,博南诺对其做了一番细致的考证和辨析,并在此基础上引出了“复原力”这个新概念。在他看来,“复原力”是我们应对创伤的关键。第二部分,我们聚焦书中介绍的实际方法,来看我们具体要如何应对创伤。
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心理创伤实际上是一个近现代才有的概念。根据《牛津英语词典》,“创伤”(trauma)这个词在17世纪就已经流传开来,但那时它只是用来描述身体上的重伤。直到19世纪中期,这个词指涉的范围逐渐扩大,开始不仅用来描述重伤,也描述一种精神或心灵的伤害。那时,工业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随之而来的是工业事故频发,那时的医生为事故幸存者治疗时,偶尔会注意到他们一些奇怪的行为或神秘的、无法解释的症状。比如一名叫作埃里克森的丹麦医生当时提出了“铁路症候群”这个说法,他在治疗一批经历了铁路事故的工人和旅客时,发现他们身体上基本没有明显伤痕,但他们却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记忆力减退、缺乏食欲、做噩梦、感知混乱、焦虑,以及莫名的疲劳和烦躁等症状,他把这称为“铁路症候群”。当时的医学界对此持怀疑态度,就连埃里克森自己也不时怀疑,这些患者是不是为了骗取铁路公司的赔偿,才故意表现出这些症状。但不管是真是假,越来越多的工业事故幸存者开始寻求医生的帮助,讲述自己出现的奇怪症状。1889年,柏林著名的神经学家赫尔曼·奥本海姆出版了一本叫做《创伤性神经症》的书,他在书中首次提出事故幸存者身上出现的奇怪症状是一个心理问题,他也首次在医学上用“创伤”一词来描述这种心理问题。
之后进入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越来越多的人面临创伤问题,这已然变成了一个我们无法再回避的问题。在“二战”时期,关于创伤的观念已略有进步,受到创伤的士兵表现出异样行为不再被视为懦弱,也不再因此受到惩罚,相反他们被视为是需要关照的对象,但当时人们仍不认为创伤是一种疾病,而把它认为是一种人固有的心理弱点,并且认为它是只要稍作休息就能缓解的。再到20世纪60至70年代,一部分从越南战场返回家乡的美国士兵发觉自己难以继续正常生活,或者难以重新融入社会,这逐渐演变为一个社会问题,它促使医疗机构再一次认识创伤,并试图为其寻找解决方案。1980年,《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在美国出版,前两版中它都有谈及创伤,但只将它视为一种应激反应,在第三版中,它开始明确将这种重大事故后的创伤视为疾病,并用PTSD这一术语称呼它,中文叫“应激性心理障碍”。手册指出PTSD的核心症状是侵入性记忆,也就是一种突然的、不由自主的、非常不愉快的记忆不断提醒人们事件发生时的细节和痛苦,它反复地、强行地进入人们的意识之中,由此导致患者处于一种高度的警惕状态,并在不断的循环中让患者筋疲力尽。手册还提出了PTSD的核心诊断标准是患者先前曾暴露于超出人类正常经历范围的、几乎任何人都会感到痛苦的事件,后来随着诊断的普及,这一标准被认为过于狭隘,因为很多对于某些人来说只是轻微的困难和不愉快的事情,对其他人却可能是一种创伤,而这些人也理应得到确切诊断,并可选择是否对其进行治疗。
在这本书中,作者博南诺指出像这样的诊断标准是极其含糊和主观的,这导致了多年来PTSD的诊断范围不断扩大,以至于任何令人不悦的事件都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创伤。到今天,创伤俨然已经走出了医学范畴,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常常谈到创伤,PTSD成为一种流行语汇,当一件事令我们感到困扰,我们可能就会说“这让我PTSD了”。而且在心理学越发流行的当下,越来越多的人学会用“创伤”来理解自我,我们会时常追溯是怎样的创伤让我们成为现在的我。德国哲学家韩炳哲有一句很精辟的话,他说现代人简直是一个创伤的主体,工作有创伤,家庭有创伤,有时候就连空气都带有创伤。他指出的是创伤成为一种现代文化,几乎无孔不入。
但在这本书中,作者博南诺表达了对此的担忧,他说我们现在对于创伤似乎有些矫枉过正了,创伤的种类不断增多,创伤的不良反应也不断增多,对此的研究可以说数不胜数,就好像创伤是一件我们无法避免,而且注定带来持久伤害的事情。博南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丧亲,丧失亲属的人同样面临巨大的痛苦,但博南诺在其中注意到的是人其实会主动应对创伤,人在面对创伤的时候,并不是只会应激,人也有可能产生正常、良好的反应。他自此转向了对人的复原力的研究,而这也是今天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所在。
什么是复原力呢?复原力这个概念最初和人无关,它是关于树木的。20世纪70年代初,环境生态学家开始使用“复原力”这个词来描述森林和其他生态系统如何在受到持续威胁的情况下仍能保持生长。例如,尽管火灾会给森林带来严重的破坏,但火灾也为森林提供了益处,火可以滋养土壤、清除老树和弱树、帮助消灭疾病或害虫,对于一些植物来说,火已然成为其繁殖周期的重要参与者。之后,“复原力”这个概念也出现在有关儿童成长的研究中,关注弱势儿童福祉的研究人员注意到,不少弱势儿童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中,也能够很好地应对生活的动荡,并最终过上正常、健康的生活。
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袭击的规模之大,程度之惨烈,让当时的纽约市卫生专员作出了会出现严重“公共心理健康危机”的预测。纽约市为此做了充足的准备,纽约市政府咨询了全国各地的创伤专家,建立和培训了一支志愿治疗师队伍。袭击发生三天后,著名研究机构兰德对创伤情况进行调查,发现接近一半的被调查者出现了一种或多种应激症状,在距离纽约市100英里范围内的人群中,这个比例更高,达到61%,参照PTSD的诊断标准,研究人员发现在靠近事故中心的人群中,整体的PTSD患病率达到20%,直接经历袭击的人群中,也就是事故幸存者中,PTSD的患病率接近30%。这组数据显示了“911事件“造成创伤的普遍性,但它也同时显示了其实有三分之二的人群并没有发展出PTSD,换言之,直接暴露于这场美国有史以来破坏性最强的恐怖袭击的人之中,大多数人尚未表现出PTSD。而且更令人意外的时候,患病率随时间急剧下降,研究团队在六个月后展开研究,发现事故地纽约曼哈顿的居民中PTSD患病率从最初的7.5%缩减到了不足1%。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为纽约市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免费危机咨询,但很快它们发现,很少有人有咨询需求。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人们在意自身被视为软弱,不好意思去求助吗?还是说在重大事故后,我们除了生成创伤,我们也会生发出对抗创伤的力量,也即复原力。以往我们的目光全被创伤所吸引了,却忽视了我们体内的那股复原力。我们知晓创伤的发生模型,却对复原力的发生模型一无所知。有没有可能有的人会比其他人具备更多的复原力,这些人是怎样来管理情绪和适应创伤后的生活,他们的经验有没有可能被复用,来帮助那些在创伤中挣扎的人。换一句话说,我们有没有可能主动地激发我们的复原力呢。
本书的作者博南诺就此去访问和研究了一批从创伤中走出的人,他近距离地研究他们的经历,试图寻找复原力的运作轨迹。博南诺起初着力寻找与复原力有关行为和特征,他发现那些评估为具备复原力的人一般更能控制自己的感受、能感知自我且留心周围的事物、关注自己身体感觉、有好奇心、有幽默感、有让自己快乐的能力等等。这些行为特征可以列到很长,但令博南诺感到棘手的是他很难证明这当中哪些特征最能激发我们的复原力,它们与复原力之间究竟有何联系。而且早就有研究证实人格特征和行为之间的关联性实际上是非常小的,换一句话说你是何种人格,并不意味你在生活中就会按这一人格行事,这被称为“人格悖论”,比如一个判定为外向人格的人,并不一定在所有事情上都表现为外向。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很难得出复原力强的人就一定会怎么样的结论。
另外,还有研究显示,应对情绪的策略在本质上并无好坏之分,每种策略都有成本和收益,而某个特定的策略只有当它能帮助我们满足特定情况的要求时,才是有效的。比如像喜悦、幸福、自豪和快乐等积极情绪,我们本能会认为它们是良好心理状态的一部分,因此我们需要努力培养这些情绪,但实际上,积极情绪并不总是有用,比如有研究就显示那些热衷于表达积极情绪的人比不善于表达积极情绪的人面临更大的社交成本,因为这种热衷有时候会被视为一种自大或不真诚和不亲切。作者博南诺的一项对遭受过性虐待的女孩的调查研究也显示,那些在讲述性虐待经历的同时表现出积极情绪的女孩,她们的社会适应表现并没有更好,相反更差,最可能的原因是这种积极是一种扭曲的积极。总之,不同的情绪和心理策略在不同的情境下会有不同的作用,不存在一种策略是始终有效的,关键的是我们能否在特定的情境下灵活地选择我们该采取的策略。
在作者博南诺看来,这种灵活性可能才是我们最不可或缺的,他带着对灵活性的认识,重新去访谈那些事故幸存者,最终搭建出来了一套关于“灵活性”的框架。书中,博南诺花了不少篇幅去论证灵活性和复原力之间的关系,碍于篇幅,在这里我们就不展开了,我们主要来看这套框架的内容,其中既包括观念,也包括很实际的方法,它或许能够为我们应对日常生活中的创伤,或其他的精神困境,提供一些启发。
博南诺在书中认为灵活性像任何的思维技能一样,可以在训练中增强。他在书中介绍了一套训练方法,他称之为“灵活性序列”,这个序列包括三步:第一步是情境敏感性,它是指对于所处情境的敏感察觉,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置身何种情境,我们就很难有效地做出反应,所以情境敏感性是一切的基础。第二步是技能储备,我们除了要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我们还要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而这取决于我们所掌握的知识和工具,即我们的技能储备。在之后,就进入了第三步反馈检测,因为我们常常无法避免判断失误,所以我们得通过这一步来重新观察事态,并据此调整和更换策略。接下来我们逐一来讲讲这三个步骤。
首先是情境敏感性,大多数人对情境有一定的敏感性,但与其他任何能力一样,这存在个体间的差异。有研究显示,对情境不敏感的人相对会经历更多的心理挣扎。博南诺曾做过一项研究探讨这个问题,他要求被试者阅读一些假定的情境描述,比如被困在电梯里,或度假回家后发现家中遭遇入室抢劫等,然后请他们对这些情境做出评估。结果显示,个体对情境评估的能力存在很大差异,患有抑郁症或焦虑症的人往往难以确定某种情境是否具有威胁性,因此也不能确定何时需要做出应对。还有一项针对PTSD患者的研究显示,他们持续地认为引发创伤的场景仍在发生,这极大干扰他们对当下情境的判断,由此使他们的心理状况进一步恶化。这一点不难理解,甚至我们其实能感同身受,当情绪裹挟大脑的时候,我们往往容易忽视我们眼前究竟在发生什么,而越是忽视眼前,情绪也就越汹涌,可能不经意间我们就被情绪拽进了黑洞。所以在这种时候,我们要主动地拉住自己,关注眼前。博南诺在书中介绍了一个叫做“自我对话”的练习,来帮助我们提升情境敏感性。这个练习非常简单,其实就是不断向自己提问“目前正在发生什么”和“目前我需要做什么”,甚至你也可以问得更具体,像是“我现在身处在何地”“我与何人相伴”“我听见别人对我说了什么”等,问得越具体,你对于环境的感知可能也就越强烈。而且博南诺还在书中提到,我们可以在问题前加上第二人称代词或是你自己的名字,比如问自己“你在做什么”“你在说什么”,像这样拉开你和你自己的距离,从而凸显你所处的环境。
然后我们看第二步技能储备,这里所说的技能更多是关于调节情绪的技能。我们其实从一出生就在学习如何调节情绪,有研究显示,即使是个婴儿,他也已经知道通过转移注意力来缓解不适,以及利用特定的行为来引起其他人的注意。随着长大,我们会在人际交往中习得越来越多的技能来调节情绪,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得到听书”解读过很多心理方面的书籍,讨论了很多方法,掌握的方法越多自然是一件好事,但在这本书中,作者博南诺一直强调的是每一个方法都有其利弊,重要的是它能否满足特定情境的要求,比如像转移注意力、更改认知、借助运动和娱乐活动,这些方法常常被视为是一种健康的方法,但它们其实也不总是有效的,而像被动接受、躲避或逃离、自欺欺人、靠食物疏解压力等被视为不健康的方法,也并不一定就是百害而无一利的。所以我们要主动储备方法,但同时也要注意结合自身情况,分析这些方法所能适应的情境。博南诺在书中介绍了一个叫做“如果—则实施”的练习方法,这个方法来自一个研究。在这个研究中,研究人员向参与者展示了一些图片,包括不带感情色彩的图片、令人愉快的图片和令人厌恶的图片,像是一些血腥照片,参与者被分为三组,其中一组只是简单地观看照片,另一组被要求在观看的过程中重复完成一个目标,即说服自己不要觉得恶心,还有一组则被要求重复“如果—则实施”的策略,比如告诉自己“我不会感到恶心,如果看到血,我要保持冷静和放松”,这个研究最后显示,只有第三组,即采取了“如果—则实施”策略的参与者,才真正做到了减轻对血腥照片的反应。所以,我们也可以尝试借助这套练习来建立方法与情境之间的适配性,由此让方法能够真正为我们所用。
再来看第三步,监测反馈。如果说前两步关注的问题是我在面临什么、我需要做什么和我能做什么,那这一步关注的问题则是我所做的一切是否有效,如果无效的话,我是否要重新评估情境并更换策略。在面对创伤问题或任何其他精神困境的时候,要看策略是否有效,实际就是看它是否让我们身体感觉好一些了,它是否减少了我们的焦虑、恐惧或悲伤。我们仍然可以借助“自我对话”来实施监测,比如问自己“你现在面对的情况有好转吗”“是什么策略让情况好转了”“你的感受好些了吗”“你还需要做点什么吗”等。但博南诺在书中特别提醒的是,这一步看似简单,但实际很复杂,主要在于我们并不总是能够准确判断我们的身体感受,甚至在很多时候我们会有意或无意地扭曲我们的身体感受,所以博南诺提出说在这一步有必要引入一些来自外部的反馈,比如来自朋友、家人或是医师,我们可以试着通过他们对我们的观察来校准我们的感受。
这三个步骤彼此配合,不断重复,由此训练我们的灵活性,提升我们的复原力。至于它具体是如何实施的,书中讲到了杰德的故事,这是一个动人且给人力量的故事,我也想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杰德是一个在纽约艰难谋生的音乐人,他一边追逐音乐梦想,一边靠在餐厅做服务员来维持生计。有一天杰德上完晚班,凌晨一点半左右,他带上四瓶要给家人当节日礼物的葡萄酒,出门回家了。这天晚上很冷,杰德整个人缩在他的连帽衫里,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一辆垃圾车突然从拐角处快速驶来撞向了杰德。这辆25吨重的垃圾车直接从杰德的腿上碾了过去,他的腿和臀部立马血肉模糊起来。救护车迟迟不来,杰德一直躺在地上,他记得自己没有昏迷,相反他一直在尖叫。不幸中的万幸是当晚的气温很低,杰德躺在冰冷的人行道上,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失血速度。就这样等了有半个小时,救护车终于来了,杰德被送进了手术室。由于伤情过重,要多次手术,医生们决定通过医学手段让杰德进入昏迷状态。杰德后来昏迷了六个星期,在此期间,他接受了近20场手术,除了截肢,他还接受了气管切开术和结肠改道手术。杰德的家人非常担心,不仅是担心手术的安危,也担心杰德在醒来后得知自己被截肢的反应,他要如何应对这场磨难所带来的创伤?
博南诺在书中完整讲述了杰德的康复过程,杰德醒来后自然是崩溃的,但好在他很快地把注意力拉回到他当下面对的情境。他这么描述当时的情境:“第一,我面临的问题是非常清晰的;第二,事故没有明显影响我的认知和思考能力,对我胸部以上的部位没有任何影响,除了始终困扰着我的疼痛。对于‘脑脊液漏’这个手术后出现的新问题,我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治疗方法是什么。我咨询了多位专家,我躺在他们的办公室里,试图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该怎么做。可他们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有些医生说应该马上做手术。有些医生说,不,再等等。我时常置身于迷雾之中,那种感觉痛苦极了。”
紧接着他会去想他能够做什么,杰德一直以来是一个善于社交的人,通过社交他能收获到很多支持,他常常是在这样的支持中走出困境。但此刻他意识到他不想与人打交道,尤其不想在其他人面前强颜欢笑,原来给予他支持的社交在此刻满是痛苦。但好在杰德没有就此止步,他进一步想他还能做什么,他发现如果他把社交范围缩小至家庭核心成员,他似乎能好受很多。自那之后他每时每刻都跟家人待在了一起,也是在这过程中他兴奋地发现瘫在床上也是能做一些事情的,比如他尽力承担了给儿子换尿布的工作。杰德的状态因此有了很大好转,但问题总是随时来临,因为病情变化,杰德又做了几次手术,术后恢复期非常难熬,他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头疼,身体的状况让他不得不放弃了彻底康复以及取得博士学位这样的念头,他不得不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思考:他面对的是什么,他还能怎么做,这么做是否有效,他还能拥有怎样的未来。
博南诺一直在关注杰德的后续人生,他的病情、他的工作、他的家庭都不断地在面临新的情况,而且永远没法预见前面还有什么。但杰德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趋于平静,他接受了生活不会停滞,只能不断地寻求方法、不断地重塑自己、不断地适应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杰德说,虽然他仍在挣扎,但他已将自己的生活拉回正轨,并仍在不断进步。他知道,从某一刻起,无论接下来将发生什么,他总是能够找到一种方法走出困境。
好,到这里,这本书就为你介绍完了,我们再来回顾总结一下。
作者乔治·博南诺在这本书中细致梳理了学界对于创伤的认识及其变化,在他看来,过往的研究在不断扩大创伤的范围,我们对创伤的不良反应知晓颇多,但对于当中正常、良好的反应却知之甚少。博南诺指出创伤其实没有那么可怕,我们的身体有一套应对它的程序和方法,他将此称之为“复原力”。通过走访众多走出创伤的人士,博南诺总结说“复原力”的关键在于灵活性,也就是在特定情境和特定时间下,不断判断并灵活做出行动的能力。他还归纳出了一套他叫做“灵活性序列”的方法,来帮助我们训练和提升灵活性。这套方法包括三步,情境敏感性、技能储备和监测反馈,博南诺相信三个步骤将有效提升我们应对创伤的能力。同时他还不断在书中强调,生活永不停滞,在旧的创伤消退后,新的创伤可能又会来临,这是我们需要花一辈子去面对和处理的问题。正如书中杰德所说,我们终要接受和学会与创伤共处,然后努力地、大步地向前走。
好,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人其实会主动应对创伤,人在面对创伤的时候,并不是只会应激,人也有可能产生正常、良好的反应。
总之,不同的情绪和心理策略在不同的情境下会有不同的作用,不存在一种策略是始终有效的,关键的是我们能否在特定的情境下灵活地选择我们该采取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