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利·波特与魔幻类型电影 谭苗解读
哈利·波特与魔幻类型电影|谭苗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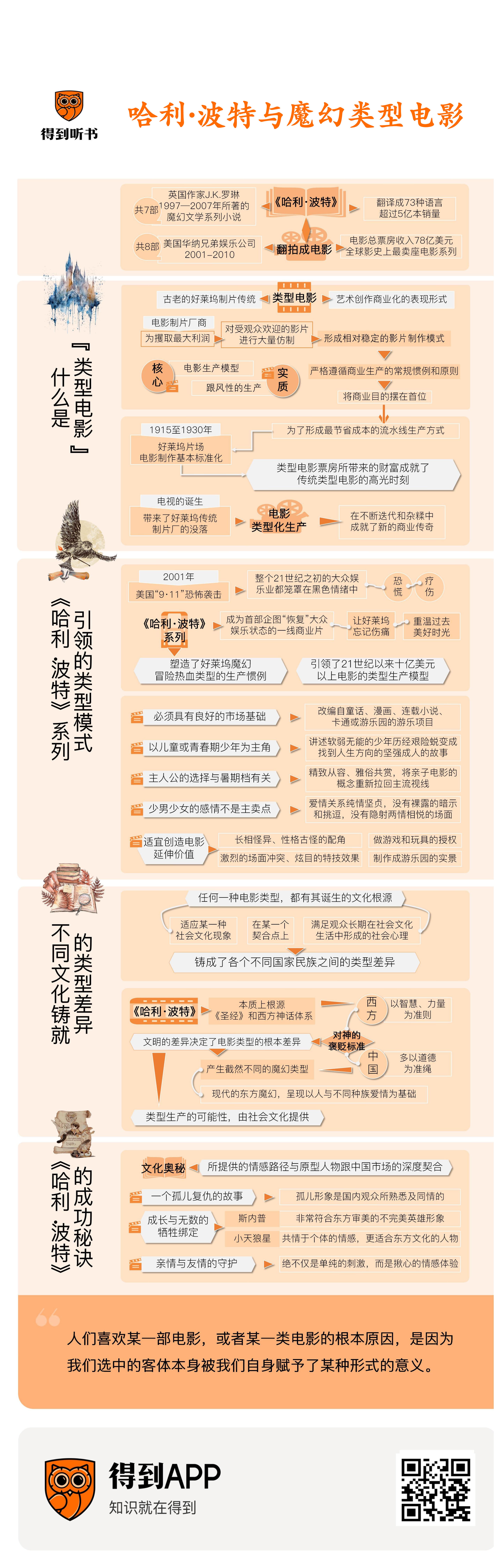
“得到听书”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教授谭苗,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想来跟大家讲一讲类型电影。今天是我们的第一讲,关于《哈利·波特》的类型成功。
《哈利·波特》(Harry Potter)是英国作家J.K.罗琳(J. K. Rowling)于1997—2007年所著的魔幻文学系列小说。这套小说一共7部。
小说的故事开始于1970年,魔法界遭遇重大危机,以伏地魔为首的食死徒势力崛起。伏地魔坚信纯血巫师至上,所以想要推翻麻瓜世界,清除不会魔法的人的麻瓜。为对抗这股邪恶力量,邓布利多成立了凤凰社,双方展开了长达十年的激烈斗争。直到1980年,预知巫师特里劳妮发出了一个将改变整个魔法世界的预言:拥有消灭大魔王能力的人即将出现,他将出生在一个三次对抗大魔王的家庭,生于七月的月尾。大魔王将标记他成为对等劲敌,但是他拥有大魔王所不了解的力量,一个必须死在另一个人手上,因为两人不能同时存活。
食死徒斯内普偷听到了预言的前半段,将预言透露给了伏地魔。虽然邓布利多利用“赤胆忠心咒”保护起了哈利·波特一家,但哈利·波特的教父小天狼星却因为误信叛徒,暴露了哈利·波特一家人的踪迹。哈利·波特的父母都为保护哈利·波特而死,母亲莉莉临死前的主动牺牲的行为触动了一种古老的魔法,保护着哈利。于是当伏地魔对哈利·波特再次发动死亡咒语时,咒语被反弹回去击中了伏地魔。伏地魔残破的主灵魂迸发出碎片,将哈利·波特作为寄生体,并在他额头上留下了闪电疤。
至此,哈利·波特成为孤儿,被邓布利多寄养在姨母家。小天狼星想要为哈利父母报仇结果却被栽赃成了罪魁祸首关进阿兹卡班。斯内普因为深爱着哈利的母亲莉莉,为了死去的爱人而改换阵营,成为潜伏于食死徒中的卧底。
1981年,哈利·波特11岁生日。他终于获知了自己的魔法师身份,并顺利入读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开始了自己的学习与冒险。在这个宏大的魔法世界里,对于邓布利多而言,哈利将是斩杀伏地魔的利器,对斯内普而言哈利那双与莉莉一样的眼睛是他的守护与救赎,对蒙冤入狱12载的小天狼星而言,哈利是他的求生之念。这个11岁的男孩在追寻真相和探究前尘往事的过程中,与自己的好友罗恩、赫敏一起奋力成长,历经十年,终于长大成人,成为守护魔法世界的希望之光。
书籍出版之后,美国华纳兄弟娱乐公司将这7集小说翻拍成8部电影,前6集各一部,第7集分成上下两部。从2001年《哈利·波特与魔法石》暑期上映,到2011年《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下)》上映,横跨了整整十年,观众见证了主演团成员的十年成长。无论是《哈利·波特》小说20年翻译成73种语言超过5亿本的销量,还是《哈利·波特》系列电影总票房收入达78亿美元,夺取全球影史上最卖座的电影系列的桂冠,《哈利·波特》系列都是一个奇迹,是新时代类型电影的成功标杆。
类型电影是一种古老的好莱坞制片传统。电影史从1895年12月28日在巴黎卡普辛路14号大咖啡馆里开始。当时,卢米埃尔兄弟通过公开售票的形式,让观众支付1法郎来观看由1部长度约1分钟的十部影片组成的节目,第一个镜头或许是《工厂大门》,也可能是《火车进站》。总之,这是一个融合了科技、艺术与社会变革的非凡时刻,标志着电影这一新兴媒介的诞生,而这一收费放映活动也预示了电影作为一种新的娱乐方式和文化传播手段的商业潜力。
虽然电影的商业性很少在电影课程上被提及,但其实,电影与文学、音乐、绘画这些早期艺术形态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电影这种艺术形式从它出现的第一天开始,就是以营利为目的而进行的生产。
而类型电影就是艺术创作商业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当时的电影制片厂商为攫取最大利润,对一些受观众欢迎的影片进行大量仿制,久而久之就形成一些相对稳定的影片制作模式。
也就是说,类型电影的实质是一种电影生产模型,其核心是一种跟风性的生产。类型电影的生产严格遵循商业生产的常规惯例和原则,是将商业目的摆在首位的电影生产模式。在类型生产的片场制度下,电影艺术家与精明的商人相互博弈彼此依靠,在电影作者努力提高艺术水准的同时,制片人则进一步发掘这种形势下可能蕴含的商业潜力。
1915至1930年之间,好莱坞片场为了形成最节省成本的流水线生产方式,基本上将电影制作的方方面面都标准化了。这种成熟模式带来了每年400至700部的巨大产量以及非常高的市场占有率。而按照这种生产模式生产出来的电影,由于其中有着流水线的生产规则,在主人公、情节以及视觉表现形式上的范式化,被称为类型电影。在好莱坞制片厂的鼎盛时期,米高梅1个月就可以推出一部剧情片,B级片甚至一个礼拜就可以完成。这些类型电影票房所带来的财富成就了传统类型电影的高光时刻。
随后电视的诞生带来了好莱坞传统制片厂的没落。随着六大片场纷纷进行合并出售。电影对于逐渐扩张的各大媒体集团的财务版图而言,其占的比例已经微乎其微。但是电影类型化生产却在不断迭代和杂糅中,成就了新的商业传奇。从商业角度而言,《哈利·波特》系列所取得的全球化成功,足够让电影制片商趋之若鹜并以此为标杆形成全新的当代电影类型。
2001年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这场袭击让整个21世纪之初的大众娱乐业都笼罩在一片黑色的情绪中。那时的好莱坞充斥着一种“恐慌”“疗伤”的情绪。《哈利·波特》成为首部企图“恢复”大众娱乐状态的一线商业片。小说中奇幻的空间历险,光怪陆离的魔幻世界里一个小男孩的故事让好莱坞忘记了伤痛,重温了过去的美好时光。
迄今为止,《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依然是《哈利·波特》系列电影中,北美票房最高、海外市场收益最强的一部电影。该片在北美3672家影院上映,打破了《碟中谍》3653家影院的上映纪录,一举创造了放映院数最高纪录,轰动好莱坞。《哈利·波特与魔法石》最终的单日、首周票房都创造了影史纪录,并分别夺得当年北美年度票房第一和全球年度票房第一的宝座,并在当时全年票房尚未超过五亿的中国电影市场获得了5700万票房佳绩。之后,《纳尼亚传奇》《魔戒》等影片开始跟风生产,这一系列营收超过十亿美元的魔幻电影为类型电影迎来了全新的时代。
《哈利·波特》系列的成功已然塑造了好莱坞魔幻冒险热血类型的生产惯例,并引领了21世纪以来十亿美元以上电影的类型生产模型。
首先,这类影片一般选材改编自童话、漫画、连载小说、卡通或者游乐园的游乐项目,必须具有良好的市场基础。比如《哈利·波特》系列和《纳尼亚传奇》系列、《星球大战》系列都在早期具有畅销小说基础。这也是最初IP的兴起之源。
其次,这类影片以儿童或青春期的少年为主角,嵌入童话般的剧情,讲述一个软弱或无能的少年历经艰险蜕变成为找到人生方向的坚强的成人的故事。《哈利·波特》中的角色,如哈利、赫敏、罗恩等,都经历了显著的成长和变化,这些变化通过丰富的剧情得以展现。而其后的《纳尼亚传奇》《魔戒》也都毫无意外地聚焦了少年成长。
而且,这种类型电影中主人公的选择还跟该类型电影选择暑期档有关。毕竟,在《哈利·波特》出现之前的好莱坞,以儿童/青少年为主导的主流商业片,都是一些搞笑粗糙电影。以2001年为例,最卖座的儿童/青少年电影,是被影评人集体视为“脑残”的《间谍小子》和裤裆思维的《美国派2》,虽然两片票房双双过亿,但都难登大雅之堂。而此时《哈利·波特》的精致从容、雅俗共赏,一改儿童片的简单粗暴,在9·11的阴霾之后将亲子电影的概念重新拉回主流视线。
另一个明显的类型特征是:该类型电影中爱情关系纯情坚贞,没有裸露的暗示和挑逗,没有隐射两情相悦的场面。这种类型特征来源自日本的少年热血片,也是所有少年热血漫画的主特征。大家也许有印象,2005年,逐渐长大的哈利在《哈利·波特与凤凰社》这一集中情窦初开,并在镜头前与张秋轻轻一吻,不仅是对原著经典情节的忠实再现,也成为影片中的一抹亮色。该片在中国上映第二周,片中新角色张秋的扮演者梁凯蒂还来到北京为影片做宣传,这波操作让该片在中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种镜头表现已经是这类影片中的限制级,更多是基于对原著情节的尊重、对电影营销策略,以及前四部电影累积的良好口碑与观众基础的考量。毋庸置疑的是,少男少女的感情始终不是这类型电影的主卖点。所以我们在同类影片《纳尼亚传奇》和《魔戒》中,并没有看到类似的镜头。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类型影片中都有长相怪异、性格古怪的配角,非常适合做游戏和玩具的授权。激烈的场面冲突,炫目的特技效果也非常适宜制作成游乐园的实景。2007年的3D还远远不像现在这么普及,但《哈利·波特与凤凰社》为了吸引观众,在影片高潮部分的20分钟狂砸2000万美元耍起了3D影像。《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由于技术上的全面升级,让投资成本迅速突破了1.5亿美元,从而带动起了好莱坞挥金如土的3D风潮。而大家如果去过北京环球影城应该对哈利·波特城堡里的“禁忌之旅”项目留有印象。坐上这个整个园区最受欢迎的游乐项目,游客将穿越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走廊和教室,亲历5D的魔法世界,并与哈利·波特和他的朋友们一同经历一场沉浸式的魁地奇比赛。制片厂当年花在影片制作上的经费,在电影落幕十年之后依然以游乐园票价的方式持续回收。这种投资方式成为当代制片商们的最高追求。以至于国内华谊兄弟、方特等多家制片方纷纷效法,火速开启了国产影视的乐园时代。
毕竟,对于制片厂来说,电影作为追逐利益的产品,无论在任何一个电影时期,都会迅速寻找可复制的成功道路用于流水线生产。《哈利·波特》系列为好莱坞世界带来了类型的新时代。至此,类型电影并没有随着老制片厂分崩离析而陷入诸神的黄昏,反而扩展了自己的类型版图,在迪士尼动画之外开启了另一方魔幻的疆界。
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果将《哈利·波特》系列的成功视为新的类型时代到来,那么,《哈利·波特》系列之后,好莱坞的魔幻传奇为什么没能无限复制,尤其是中国为什么并没有跟风生产出《哈利·波特》类型的魔幻题材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类型电影除了其商业本能之外的另一个文化特征。那就是,任何一种电影类型,都有其诞生的文化根源,是适应某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某一个契合点上,满足了观众长期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形成的社会心理产生的。
文化成就了类型,也铸成了各个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类型差异。而任何一种电影类型都可以从接受美学以及观众心理入手,发掘出文化共识。这种文化共识是通过集体无意识达成的,是电影类型能够实现类型化,并随着社会发展实现类型转化与融合的基本所在。
《哈利·波特》作为魔幻题材,像所有的西方魔幻一样,其本质上根源于《圣经》和西方神话体系。以古希腊神话为例,天神都是世袭的,讲究血统,只要是天神的子女多半可以成神;凡人通过与天神婚配有机会使得子女成神,而自己不行。西方人永远是上帝的子民,耶稣的羔羊。但翻开中国上古神话,一个圣贤的世界扑面而来。尽管中国神话没有十分完整的情节,神话人物也没有系统的神系家谱,但它们却有着鲜明的东方文化特色,其中尤为显著的是它的尚德精神。希腊神话中,对神的褒贬标准多以智慧、力量为准则,而中国上古神话对神的褒贬则多以道德为准绳。这种思维方式深深地注入中国的文化心理之中。几千年来,中国古代神话的这种尚德精神影响着人们对历史人物的品评与现实人物的期望,决定着社会对人们进行教育的内容与目的,甚至也影响着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明的走向。
正是这种文明的差异,决定了电影类型的根本差异。毕竟,对于电影生产者来说:其生产依据都是与观众的需求所达成的共识,而其成就的原因依然是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因素的综合平衡所致。
中西方文化的不同注定我们会产生截然不同的魔幻类型。2008年,中国地区《画皮》上映,获得了2.32亿的票房成绩。这部取材于《聊斋》的东方魔幻,其与《哈利·波特》系列的对比已经充分说明同一个类型在不同文化视域下的截然不同形态。
《画皮》系列与《捉妖记》系列都是东方魔幻类型的成功范例,虽然同样是魔幻题材,但相比较于世界范围内的“少年热血”类型,国内始终没有较为成功的少年成长型影片,而往往聚焦于爱情和亲情。
这是不同的国情和文化对于同样一个原型模式的重新理解。虽然中国的传统神话中,后羿、夸父这样的英雄与普罗米修斯一样,但是在儒家思想等一系列哲学思想兴起之后,东方的智慧就转化为七仙女以及牛郎织女这样的浪漫情怀,神仙不再为全人类的福祉而做出个人牺牲。吸引人界与仙界达成共通的,是人类美好的情感。而正是这种集体意识基础,使得现代的东方魔幻,呈现出《聊斋》风格,以人与不同种族的爱情为基础的。而像《哈利·波特》那样的故事,虽然在全球取得了非凡的票房成绩,但是在制作上而言,并不是中国商业电影所效法的道路。要知道,虽然类型生产是由商业生产的需求性所奠定的,但类型生产的可能性,却由社会文化提供。
尽管我们承认不同的文化将最终导致电影在类型生产上的截然不同,但奇怪的是,虽然国内没有生长西方魔幻类型的文化土壤,但《哈利·波特》依然在国内取得了票房佳绩,而相比之下,同样成为北美票房前十的《纳尼亚传奇》系列和《魔戒》系列却在国内稍显逊色。
《哈利·波特》系列在全球市场上取得了一种近似于跨越文化的巨大成功。这让我们不得不将目光再次聚焦在其故事本身。也许其作为一种类型成功的代表,有着自己更深层次的文化奥秘。这种奥秘就是其所提供的情感路径与原型人物跟中国市场的深度契合。
首先,《哈利·波特》是一个孤儿复仇的故事。传统中国故事里的《赵氏孤儿》,以及《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都是这种孤儿型的典型人物。这种孤儿形象是国内观众所熟悉及同情的,也就是主人公不能是简单的父母双亡,不能是仅仅有着孤儿院长大的背景,这种类型的孤儿应该出身名门世家,如果不是因为一场浩劫,原本是出生在罗马,过着幸福的生活。但偏偏他的父母遭受了灭顶之灾,可能是出于冤情,也可能是被人陷害,总之,他们父母的亡故成为他们人生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一旦观众对其父母的死耿耿于怀,对这个孩子遭遇的一切充满了意难平和惋惜,那么他们必然将对这个孩子的未来充满期待。哈利·波特仿若西方版赵氏孤儿,在观众万众期待中长大。
《赵氏孤儿》里,程婴为了救赵武子主动牺牲了自己的孩子。哈利·波特的成长更是跟无数的牺牲绑定。其中,最动人的是“混血王子斯内普”和“阿兹卡班的囚徒小天狼星”。
西弗勒斯·斯内普是一个痴情于哈利·波特母亲莉莉的悲剧人物。从小被校园霸凌的他一开始是食死徒阵营中的人。《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中,斯内普也是第一个被怀疑的反派。童年的斯内普父母不和,到学校与詹姆等人争斗,并被自己唯一的朋友莉莉抛弃。童年的经历让他成为麻瓜及麻瓜出身歧视者,却始终没有遇见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于是成年后误入歧途为伏地魔卖命。直至莉莉为了保护哈利死在伏地魔手上,斯内普才幡然醒悟。电影对斯内普进行了堪称完美的改编。原著中,斯内普无法控制狭隘的私欲,想要通过惩罚哈利来报詹姆当年之仇。小说里的斯内普是一个小心眼,有着明显性格缺陷,永远活在阴暗中的人。甚至电影中点睛之笔“他有着与莉莉一样的眼睛”是邓布利多用来提醒斯内普不要被仇恨所蒙蔽的最后防线。但在电影的呈现中,他强忍着对哈利的厌恶,将自己置身于最危险的境地,默默承受一切的误会,甚至承担着杀害邓布利多撕碎自己灵魂的风险,只为履行着自己的承诺,最终为哈利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体现出了忠贞爱意的最高境界。
电影中的斯内普是一个非常符合东方审美的不完美英雄形象。这个角色有着一种东方阴郁,像极了一个忍受千般痛苦为胜利潜伏到生命最后一刻的谍战英雄。相比之下,《纳尼亚传奇》《魔戒》系列中,明显没有这种亲近东方文化的人物角色。这些剧集中的主人公,因为缺少悲惨的身世,没有承担巨大的牺牲而很难让中国观众共情。我们承认《魔戒》中甘道夫的死亡也很感人,但甘道夫的死是为了大义,而不是单纯为了主人公个人。斯内普最终虽然是为正义献身,但邓布利多那句“他有着和莉莉一样的眼睛”贯穿了斯内普整个人物的始终。中国观众共情于个体的情感,而与痴情且勇敢的斯内普相比,“阿兹卡班的囚徒小天狼星”更适合东方文化的人物。
保护教子的信念支撑着小天狼星成为第一个成功越狱阿兹卡班的人。哈利的这位教父跟他一样有着不幸的童年,两人同为格兰芬多学院,都是扣分大王,冲动体质,也同样都是校园风云人物,总是登上报纸头条。命运的相逢让小天狼星想尽一切办法,冒着被通缉的危险,陪伴哈利。电影中,小天狼星的饰演者以大反派的人设出场,却完成了剧情的极地逆转,一个有着摇滚气质的英国男星加里·奥德曼,狠狠拿捏了反转版暖心教父的人设,将疯狂与优雅、绅士与不羁、睿智与敏感都表达得恰到好处。原著中“小天狼星之死”成为电影最让人意难平的情节。
小说中,伏地魔得知了小天狼星和哈利之间的情感连接,用梦境设下陷阱,制造了刑讯小天狼星的假象,引诱哈利进入。哈利果然中计,被食死徒瓮中捉鳖。危难时刻,小天狼星冒着被通缉的危险带着凤凰社成员赶到。这是小天狼星的一场必死之局。原著章节“帷幔那边”写道:小天狼星躲过贝拉射出的一道红光,他大声嘲笑她:“来吧,这不是你的水平。”他喊道,声音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第二道红光正中他的胸膛。笑容还没从他脸上完全消失,他的眼睛惊愕地瞪圆。小天狼星坠落的过程似乎十分缓慢。他的身体弯成一个优雅的弧线,向后跌入了挂在拱门上的破烂的帷幔。哈利看见,他的教父坠入那道古老的拱门时,那张曾经英俊、现已消瘦憔悴的脸上混杂着恐惧和惊讶。他消失在了帷幔的后面。帷幔像被大风吹着一样摇摆片刻,又恢复了原样。
电影中将这段情节改编成了小天狼星与哈利父子联手,合力击倒了卢修斯,但是被贝拉偷袭。一道绿光击中小天狼星,他倒入拱门,跌入帷幔。拱门连接生死,帷幔分隔阴阳。在某个瞬间,小天狼星甚至将哈利看成了自己的挚友詹姆·波特。他带着对詹姆以及哈利的深情缓慢地跌入了帷幔,消失在帷幔后面。这个瞬间让无数中国影迷为之泪目。
斯内普和小天狼星的牺牲,其实就是《哈利·波特》拿下中国市场,至今依然成为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的根源。因为有着这样义无反顾的牺牲,《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在18年后再次修复上映,依然在中国取得了1.7亿的票房。因为有着这样的亲情与友情的守护,使得环球影城里,哈利·波特园区永远是最火爆的场景。
单纯的奇遇和冒险、夸张的视觉奇观,也许永远无法在中国市场获得巨大的成功,诸如《哈利·波特》同类型题材《黄金罗盘》等片甚至票房惨败。因为对于中国观众而言,让他们所钟情于电影等所有文化产品的,绝不仅仅是单纯的刺激,而是揪心的情感体验。
文化是人类在历史中创造的,所想与所做的综合产物。我们在观察和分析文化现象时,往往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无意识或下意识的行为理解为文化行为的一部分。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人们喜欢某一部电影,或者某一类电影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们选中的客体本身被我们自身赋予了某种形式的意义。那些使我们娱乐的东西,其背后有着我们为何因此而娱乐的深层内涵。为什么我们谈起《哪吒》与《封神1》,这些能够在国内电影市场票房占据一席之地的魔幻题材,我们谈论的话题是哪吒中的“父母之爱”,是对抗命运的“我命有我不由天”,是伯邑考为了父亲的视死如归,甚至是他带去朝歌的那匹老马。制片厂聚焦中国市场的电影类型之旅只能在情感上更加共情同理,而非单纯依靠选材与制片模型。而这些深藏于类型电影背后深层的文化内涵,也许才是我们此时讨论类型电影的终极意义所在。
好,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哈利·波特》的电子书链接我已经为你附在文稿末尾,感兴趣不妨阅读一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1.类型电影的实质是一种电影生产模型,其核心是一种跟风性的生产。类型电影的生产严格遵循商业生产的常规惯例和原则,是将商业目的摆在首位的电影生产模式。
2.任何一种电影类型,都有其诞生的文化根源,是适应某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某一个契合点上,满足了观众长期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形成的社会心理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