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西狩丛谈》 张笑宇解读
《庚子西狩丛谈》| 张笑宇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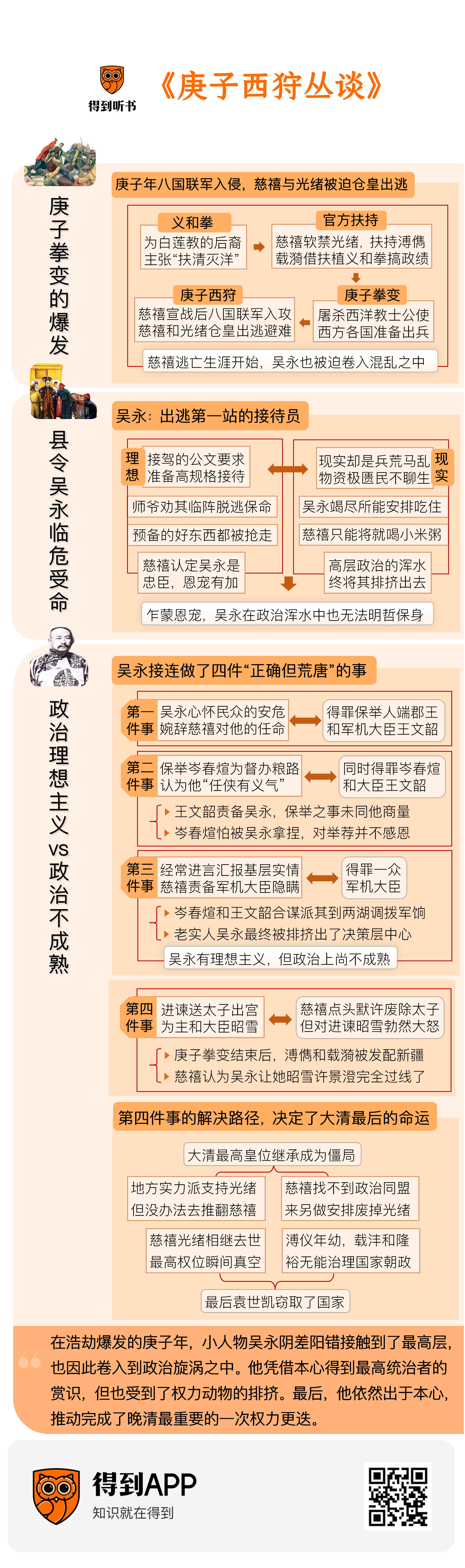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张笑宇。今天我要给你介绍的这本书叫《庚子西狩丛谈》。
庚子就是庚子年,1900年。我们都知道那一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被迫出逃,一路走到陕西西安去避难。但是清王朝要为尊者讳,不能用“出逃”这个词,只能换一个词叫“西狩”,意思是去西边打猎了,不是出逃。这本书讲的就是一个慈禧太后出逃的亲眼见证者所经历的一切。
这本《庚子西狩丛谈》很有意思,我们读的版本是2009年由中华书局整理再版的,而它最初的作者竟然是一百多年前清代的一个普通县令,叫吴永。这本书是由他口述,后由曾经担任光绪年间京师大学堂教授的刘治襄记录出版。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吴永正在今天河北张家口怀来县做县令,是慈禧太后出逃的第一站接待员,所以亲眼见证了很多历史细节。要说这个吴永,也不是一般人物。他的出身基本是一个中产家庭,读过一些诗书,但他本人应该是非常有才华的,因为他娶了曾纪泽的女儿。曾纪泽是曾国藩的儿子,做过大清驻英、法、俄的大使,是权势滔天的人物。这个吴永肯定是读书为人有过人之处,所以才能被曾纪泽看中做女婿。
那这个吴永走上仕途以后,先是在直隶做试用知县,办理洋务,受到洋务派名臣张荫桓的赏识。这个张荫桓曾经做过户部侍郎,大清驻美公使,后来因为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跟戊戌六君子一起被抓,流放到新疆,1900年庚子事变后又被处死,也是一个有才华的悲剧人物。那当然吴永被张荫桓赏识的时候,张荫桓还没出事。他很欣赏吴永对洋务的理解,于是把他调到了怀来做知县。吴永接待慈禧太后出逃,就是他在怀来任知县时发生的。这也就是《庚子西狩丛谈》这本书所以诞生的缘分。
但是吴永写这本书,倒也不只是说要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他还是想讲清楚前因后果,为后世作一些借鉴。所以他一开始讲述的,是他对“庚子拳变”始末的理解。所谓“庚子拳变”,“拳”就是义和拳,又叫义和团。吴永说,义和团是白莲教的后裔,嘉庆末年演化为八卦教,因为西洋来的耶教,也就是天主教在中国往往受到官府的偏袒,民众恨之入骨,所以就加入八卦教与其抗衡。而八卦教也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旗号,试图得到官方的支持。他们也没有什么正经的教义,就是从民间流行的《西游记》《封神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这类小说中摘一些神来拜,自称是沙和尚、猪八戒、孙悟空、二郎神附体。他们中有一派是从练拳开始修行的,以武入道,这一派就叫做义和拳。
吴永认为,义和拳之所以得到官方扶持,其实跟清朝高层内斗有关。我们知道戊戌政变之后,慈禧软禁了光绪,从皇室里给他找了一个十三岁的少年叫溥儁的做干儿子,并且立做大阿哥,其实就是打算把光绪废掉,改立溥儁做皇帝。那么溥儁的生父是端郡王载漪,他一下子权势滔天,就想借机搞一些政绩,树立威信。这个载漪选的政绩,就是扶植义和团,称赞他们扶清灭洋。你可以想象,未来皇帝的亲爹开口发话了,下面的大臣一定是极力逢迎。慈禧太后也被他们说服了,这就导致义和拳一发不可收拾。
但是这批义和拳民能不能救大清呢?在吴永看来,那是毫无可能。他们吹嘘自己有神通法术,其实都是骗人的把戏。他们名义上说是要打洋人,其实也就是敢去欺负一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教士信徒,而且他们残虐自己同胞的本事,要比对抗洋人大得多。义和拳管洋人叫“老毛子”,管教民,也就是信天主教的中国人叫二毛子,你家里凡是有西洋器具,都不用说西洋家具电器什么的,就是有洋火,也就是火柴,那也算二毛子,该杀。所以当他们进北京城之后,在前门一带,包括珠宝市、大栅栏、煤市街,那是到处放火、任意屠掠。百姓们哭声响彻天地,可以说饱经劫难。
义和拳进入北京,屠杀西洋教士公使。西方各国质问大清政府还能不能遵守国际公法,保护侨民,如果不能,那我们就要出兵了。这个时候,慈禧太后拿不定主意,召集大臣开会,讨论要不要对西方开战。八国联军侵华是一场侵略战争,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国际政治的底层是实力关系,打不过贸然去打,不讲方法策略,会引发一连串大问题,祸及自身。这个道理其实不难解释,但是在载漪等最高层营造的政治氛围里,绝大部分大臣还是想明哲保身,不敢说实话。
吴永说,当时光绪皇帝想要劝阻慈禧太后开战,但又不敢自己站出来。他在人群中看到总理大臣许景澄,亲自下座拉着他的手,哭着说,许景澄,你在总署干了很多年了,你是熟悉洋务的。你说,这个仗到底能不能打?“国命安危,在此一举”,你可要说实话啊!许景澄也痛哭流涕说,决不能打。但是端郡王载漪害怕风向一变,自己就被夺了权,站出来指着许和其他支持议和的大臣说,老佛爷你看,这个样子,成什么体统!结果会议就此结束。第二天,主张议和的三个大臣就都被处死了。
我们前面讲到过,吴永踏入仕途的知遇恩人张荫桓,也是在这个时候被处死的。只不过吴永解释他为什么被处死跟别人不同。他说,张荫桓亲口跟他解释过,他得罪了慈禧身边的太监李莲英。清朝宫中的潜规则是,所有京外大员要给皇上送礼,必须经过李莲英的手,所以他们也要为李莲英准备一份礼物。但是张荫桓出使英国回国的时候,采购了两颗宝石,一颗是红披霞,一颗是祖母绿,两颗分别进献给东宫和西宫太后,但是没给李莲英预备礼物。那么张荫桓把价值更贵重的祖母绿献给了慈禧,慈禧本来也很开心,结果李莲英在旁边来了一句:“难为他如此分别得明白,难道咱们这边就不配用红的么?”
这句话一说,张荫桓就完了。因为古代中国妻妾等级严格分明,正室才能穿红,侧室只能穿绿。慈禧是西宫太后,不是正室,对这个事情一直耿耿于怀。李莲英一句话,搞得她恼羞成怒,把这个礼物当即就退回去了。张荫桓就这样被发配新疆了。
很多历史研究者觉得吴永这个话夸张了。他们觉得张荫桓被贬,肯定不会是一颗宝石的事,而是因为他卷入了戊戌变法。但其实我倒觉得,吴永的说法反而更淋漓尽致地揭示了清王朝皇权专制的本质。马基雅维利的好朋友,意大利历史学家圭恰蒂尼就说过一句话:“你在理解君主的意图时,不能用理性去判断,而是要从他的习惯和天性去判断。”在古代皇权社会,人上人的权力不受丝毫约束,清朝高层随意的一句话、一个念头,就可以定夺千万人的生死。哪怕你是官阶再高的大臣,在他看来也不过是个家奴而已,说杀了就杀了。张荫桓对自己遭遇的这个解释,其实反倒符合那个时代的实情。
我们言归正传。总而言之,慈禧赞同主战派的大臣,决定对洋人宣战。慈禧宣战后,各国军舰集结。六月十九日,大沽炮台失陷。七月十七日,天津失陷。八月,八国联军攻入紫禁城,慈禧的逃亡生涯正式开始,而吴永也被卷入了这场混乱之中。
刚才讲过,吴永只是一个怀来县令。按清代官制,这只是个正七品。他上面还有通判、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巡抚、总督等一堆大官,接驾这个活绝对排不到他。就算是真接驾,他最多也就是有资格排在最后面,远远地跪着,只能看到前面上司撅起来的屁股。况且,那个时候兵荒马乱,义和拳进了北京,全国各地的流民地痞都在冒充自己是义和拳,会法术,假借神仙附体敲诈勒索,连县官也不放过。吴永在怀来任职,离京津都很近,还会遇上前线溃退下来的士兵扰民。他每天忙这些事都已经焦头烂额,又完全不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只能与幕僚一道借酒消愁。
所以在这个节骨眼,当他接到一封要求他接驾的公文,你可以想象他完全是蒙的。那这封公文上面写的是什么呢?它上面盖的印是延庆州公印,印是真的,所以肯定是官方文件。但它的内容你可能想破头也想不到,它写的是一堆接待规格:要求吴永给皇上和皇太后准备满汉全席,给下面的王爷、军机大臣准备一品锅,简单说就是用鸡鸭猪蹄海参煮出来的大杂烩。再给随架的神机营、虎神营准备军需粮草。你看这个事多么大清特色,对吧?国家都要亡了,这个公文上还要求按接待规格准备满汉全席呢。
吴永接了这个公文他蒙了啊,他只能跟师爷商量。师爷一看这文件,一拍大腿:咱跑吧,官也不要了。这兵荒马乱的,上哪去准备这满汉全席一品锅去?你要是准备不好,你这是杀头的罪名。但是这个吴永毕竟是读书世家,觉得还是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我自己尽心尽力做到力所能及最好了,你要杀我我也没辙了。于是他就开始筹备接驾,搜罗些老弱病残,负责给太后和皇上抬轿的、做饭的、护卫的,有什么人用什么人吧。满汉全席是不可能了,一品锅也别想了。当时县里大部分富豪都逃亡了,他派厨子去采购的食品,半路也被义和拳跟散兵游勇抢走了。最后张罗到三口锅,杀了三头猪,炖点白菜粉条子,咱们民间版本大乱炖凑合一下吧。
吴永这筹备了半天,圣驾一行人就这么到了。他第一个见到的是军机赵大人。这个人叫赵舒翘,投靠载漪和刚毅,支持义和拳杀洋人,后来被西方列为战犯,被慈禧太后赐死。这个人身体倍儿棒,什么吞黄金、吞鸦片、吞砒霜都上了,被赐死了十几个小时都没死,最后是被士兵用湿纸糊在口鼻上憋死的。当然这是后话。在怀来县,他已经是吴永一辈子仰望不可及的高官了。
赵舒翘一见吴永,先问有没有住处。吴永惴惴不安,说预备了公馆,就是事出仓促,准备不周。赵说有个住处就行了,咱们两宫太后已经两天没吃没睡了,你快去迎驾。吴永接着又遇到肃亲王,以及慈禧身边的二号太监崔玉桂。据他回忆,崔太监声音锐利,跟京剧《法门寺》里的唱腔一模一样。
在崔玉桂的引见下,吴永终于见到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慈禧一开始先问了他姓名籍贯家常,问着问着就哭起来,说她跟皇帝连日走了几百里,路上一个百姓官员都没见到。如今到了怀来,你居然衣冠齐整来迎驾了,你是我的忠臣啊!“我不料大局坏到如此。我今见尔,犹不失地方官礼数,难道本朝江山尚安全无恙耶?”说罢放声大哭。吴永也陪着她哭。这个时候的慈禧边哭边讲路上的惨状:她想喝水,派太监去井里打水,结果井里浮着个人头,没办法,只能跟皇帝一起嚼高粱秆,吸里面的汁解渴。她想睡觉,但是没床,昨晚上跟皇帝挤在一个板凳上,背贴着背靠到天明,完全变成一个乡下老太太了。皇帝已经两天没吃饭了,你这儿有饭没?
吴永说,本来预备了点好东西,都被溃兵抢走了,这儿三锅小米绿豆粥,刚才已经被随行士兵抢了两锅,还剩一锅,怕您嫌弃。慈禧说,有小米粥,甚好甚好,可速进。患难中有这个不错了。但是没筷子啊,不能拿手捧着喝啊。还好这个吴永有个满人的习惯,因为满人是渔猎民族,随身带着小刀牙筷预备打猎割肉吃,于是就把自己随身带的筷子献给慈禧,别人就只能撅根高粱秆凑合了。这小米粥一上,可见两宫真是饿坏了。吴永没资格陪太后吃饭,只能跪在院子泥地里等,听见屋里人抢着喝,还砸巴嘴呢。
这小米粥喝完,李莲英出来发话了,说你办差办得好,但是老佛爷喝了粥,又想吃点鸡蛋,有法子没?吴永只能说,我去试试。去到一家主人已经逃窜的空屋,抽屉里找到五个鸡蛋,如获至宝,自己烧了锅水煮熟了,配了点盐。这五个蛋,老佛爷一人吃了仨,又想抽水烟。吴永找来烟纸,伺候着抽完水烟,又问有没有衣服。吴永把自己太太和母亲的衣服献上,又问有没有轿夫。一切伺候完毕,陪着皇驾轿子到了地方。太监看过住处,十分高兴,北京话都蹦出来了:“咱们今日已算是到了地头了。”
到这一步,吴永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其实从这些细节里,我们不光可以感受到历史鲜活的一面,也可以窥见清朝官府运作系统。你想想,前面州府给吴永发公文,要求的还是满汉全席和一品锅呢,后边太后和皇帝到了,也就不装了,小米粥也行,鸡蛋也行。如此前倨后恭,引人发笑。但笑完之后我们仔细一想,这就是清朝官僚体制的运作方式。
太后本人不可能直接越级给吴永下命令,对吧?她可能连吴永是谁都不认识,她只能通过州府交代下级去办。而州府给吴永下命令,明知道他不可能真弄来满汉全席,但公文也必须这样写。因为清朝官员是对上负责而不是对下负责的,他们只要按照流程操作,就可以做到自己的责任最小化。具体任务能不能完成,那就成了吴永这些基层官员的责任。而要是他们真的为基层考虑了实情,请求上面宽限基层,那背锅的人就变成他们了。但基层官员要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最佳选择是什么呢?最佳选择只能是装傻充愣,比如推脱说公文寄丢了没收到,甚至就像吴永的师爷出的主意一样,干脆弃官逃跑了事。毕竟要是治世的时候还有仨瓜俩枣的俸禄可图,这是乱世,我有什么可图的呢?也就是慈禧和光绪运气好,遇上了吴永这个老实人,真的还认他们。要是碰上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估计还得多饿几顿。
这整件事看起来十分荒唐,但细想之下,却是清朝官僚机制下容易发生的事。清朝统治者权力不是来自人民,而是来自人上人,他们的官员不对百姓负责,而只是对上负责。所以这些祸乱朝政、推诿责任,亡国之际还发公文要求准备满汉全席的事情就一定会发生。
让我们言归正传。慈禧作为一位政治家,自己心里也清楚,吴永是个老实人,是个忠臣。所以吴永接驾以后,她对吴永可以说是恩宠有加。
照一般人的想法,吴永一介小小县令,机缘巧合伺候了太后,那后面一定是平步青云、提拔高升了。可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我们前面反复说过,吴永是个老实人,他做县令保境安民,那可以说是尽忠职守、造福一方。可他乍蒙恩宠,实心办事,却没想到清朝高层政治是一汪说不清道不明的浑水。得到慈禧眷顾之后,他接连做了四件自己看起来正确,但其实在高层权臣看起来荒唐的事情,最终也被排挤出了慈禧身边。
我们一件一件来解释这四件事,第一件是他婉辞慈禧对他的任命;第二件事是他为保举岑春煊而同时得罪了岑春煊和军机大臣王文韶;第三件事是他进言基层实情又得罪了其他军机大臣;第四件事则是他进谏废除太子而触怒了慈禧。
第一件事关系到他的提拔。按常理说,提拔应该是好事,可为什么吴永要拒绝呢?慈禧提拔他做的官是“办理前路粮台”,说白了就是看他伺候得体,让他做慈禧出逃的大管家,一路安排接待供给。这个活虽然是伺候人的活,但也很考验一个人协调各方面的能力,再者伺候的是太后,办事得力,未来前途一片光明。可吴永是个老实人,担心自己一走,怀来县的民众无人照管,会被拳民溃兵骚扰,所以拒绝。他这一拒绝不要紧,就把那些保举了他的人,包括当时的端郡王和军机大臣王文韶给得罪了。其实像吴永这样的基层官员,一朝得宠爆红,但根基浅薄,对高层构不成威胁,反而可以成为拉拢对象。可吴永这么一拒绝,端郡王和王文韶以为他是不想跟自己站到一队,态度马上就有了变化。
第二件事跟晚清两个政治人物有关,一个是岑春煊,一个是王文韶。岑春煊是个官二代,年轻时放荡不羁,名列“京城三恶少”之一。1900年庚子拳变那年,他在甘肃做按察使,听说慈禧和光绪出逃,他马上带了两千人赶到怀来救驾。后来他成为晚清立宪派的领袖,又跟袁世凯权斗失败,改投梁启超的革命党。当然这是后话。他赶来救驾的时候,吴永本人是大为感动的,觉得他“任侠有义气”,又比较有从政经验,所以上书慈禧,请求把自己督办粮路的职位让给岑春煊,自己改为会办,也就是任副职协同办理。他这一陈奏,慈禧觉得很好,可没想到又把王文韶给得罪了一层。
这个王文韶早年是得到左宗棠、李鸿章共同赏识推荐的,明白洋务,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时,他也是唯一跟在慈禧身边的军机大臣。但是他为人十分圆滑,外号叫“琉璃蛋”,那意思就是滑不留手。他本人是看不起岑春煊这种二代子弟的,知道这件事后,就来责骂吴永,说你举荐岑三,也不跟我商量一下。这小子野性不改,将来你一定会遭殃,到时候可别来找我。果然不幸被王文韶一语言中:那吴永举荐了岑春煊,岑春煊并不感恩,反而觉得吴永一定是要用这个人情拿捏他,所以处处欺负吴永。
第三件事则又是吴永作为地方官员,太过理想主义了。他得到慈禧恩宠之后,经常向慈禧陈奏外界的实情,像地方利弊、民间疾苦,一陈奏就是一两个小时。结果有一天,李莲英过来跟他咬耳朵,说你闹出大乱子了。怎么回事呢?你昨天跟老佛爷禀报的事情,老佛爷今天召见军机大臣,大发雷霆,说这些外界实情我一概不知,你们是不是要故意蒙蔽我和皇上?所以吴永本来是想着尽忠办事,可又把这些军机大臣得罪了。后来王文韶出面,更改了汇报规矩,每天军机大臣先汇报,然后才是外臣。最后,岑春煊和王文韶一同合谋,把他派去了两湖调拨军饷,虽然是升官,但也把他排挤出了决策层中心。
在这三件事上,其实可以说吴永既有理想主义的一面,也有政治不成熟的一面。理想主义在于,他是基层官员,一直以来直面问题,所以他办事的思路就是解决问题,一切有利于问题解决的办法都是正当的。但他政治不成熟的一面在于,在当时清朝高层看来,所有的问题都是技术细节,唯有人和人之间的权力分配才是根本要务。你吴永跟谁不跟谁,才是最关键的。吴永的悲剧,就在于他并没有深刻理解这一点。当然,反过来说,如果他理解了这一点,他也可能被异化成一个纯粹的权力动物,丧失了理想主义的本色。所谓福兮祸兮,谁又能说他的选择一定是错的而不是对的呢?
最后一件事,就是吴永进言废除大阿哥。这件事虽然触怒了慈禧,但老实说,这确实关系到晚清最重大的权力斗争之一。
我们来详细解释一下来龙去脉:吴永到两湖之后,跟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推心置腹。张之洞跟他有次聊天时提到,说这一波庚子拳乱啊,归根结底,是因为大阿哥溥儁和他爹载漪作乱。现在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要是不把大阿哥废掉,天下人心不平。这个事,你吴永现在受恩宠这么深,你得为国家担起来。你回去之后,要对太后上奏这件事,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吴永听张之洞这么说,那是豪气顿起,说:“既是关系重要,誓必冒死言之。”
当然,经历了王文韶、岑春煊等一系列政治斗争之后,吴永也成熟了一些。他没有直接进谏慈禧,而是找到荣禄商量了一下。荣禄听完之后,猛猛抽烟,吸完又换,换了又吸,如是三次,十多分钟后才慢慢点头:这个事也可以说,你的地位分寸倒是刚刚好,像我们这种人就不便开口。但你得格外慎重,不要鲁莽。
那么吴永就跟太后上奏了,说这是张之洞的意见,希望把大阿哥送出宫,才好跟洋人签合约。慈禧点头说我知道了,等圣驾回汴梁时自有办法。吴永知道这个事大概十有八九了,于是又壮起胆子,希望太后为当时因为主和而遭处死的许景澄等人昭雪。没想到,太后勃然大怒:吴永,连你也这么说?!吴永吓得马上下跪叩头。太后稍稍平息怒气,又说,你不知道当时情形。皇帝(就是光绪)现在在这里,你问他。当时许景澄哄着皇帝下来,拉着衣袖说,许景澄你救我,然后抱头痛哭,你说这还有什么体统?这是宫里的事,你是外臣,不知道,今后不要说了。
到这里,晚清最后一次重大权力斗争落下帷幕。
我们稍微复盘一下。张之洞要吴永进言太后,请大阿哥出宫,这个事表面上是大阿哥的废立,但本质上其实是慈禧和光绪的关系。因为光绪没有自己的儿子,如果溥儁是大阿哥,那么慈禧废光绪,立溥儁,这就是很顺畅的事。但如果把溥儁废了,其实就等于堵上了慈禧废光绪的路。往深了说,张之洞此举牵涉到否定戊戌政变以来慈禧软禁光绪等一系列的政治安排,是最高级别的生死层面的政治斗争。
张之洞知道这整件事背后的意味,但还是发难了。这是因为,就算你是太后,这个事归根结底也是你办砸了。你引发了八国联军侵华,差点把天下给亡了。现在你要把这个政治责任担起来,承受后果,废掉载漪这个派系,这是我们地方实力派的意愿。那荣禄允许吴永上奏这个事,其实就代表他也知道这件事,他也站在了地方实力派一边。但他们自己没有出头,而是把吴永当枪使,这就是还为慈禧留了一点面子。就是我们没有逼宫,我们找了你信得过的人来传话,你自己可以决定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体面地办,大家都有台阶下。
其实慈禧自己也接受了这个安排,毕竟她是个成熟的政治家,知道输了要担责,不能耍赖。我们知道庚子拳变结束后,溥儁和载漪父子俩也被发配新疆。代表她认可了这一安排。但吴永让她昭雪许景澄,在她看来这就是完全过线了,是打了她的脸。我把大阿哥废掉,里子已经给你们了,你们难道要把我的面子也拿走?当然吴永很快用行动证明,这件事不是张之洞和荣禄的谋划,是他个人的自发行为。所以慈禧最后也没有发难,还解释了一番,就此了事。
这件事的解决路径,其实决定了大清最后的命运。自此以后,大清最高皇位的继承就成了一个僵局:地方实力派当然是支持光绪的,但他们并没有办法推翻慈禧;反过来,慈禧也找不到政治同盟来另做安排,废掉光绪。双方的僵持一直持续到1908年,慈禧自知命不久矣,派人毒死光绪皇帝,第二天自己也紧随其后去世。她的这一安排,导致大清最高权位瞬间进入真空:即位的溥仪只有三岁,他的父母载沣和隆裕太后又完全没有治国才能,而当时唯一能依靠的封疆大吏张之洞也在次年去世,最后是袁世凯得到了机会,窃取了国家。
这就是吴永的故事。在那个浩劫爆发的庚子年,他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却阴差阳错进入到最高层,也因此卷入到政治旋涡之中。他毫无经验、战战兢兢,做事只能因凭自己的本心。他本心中那一点知识人理想主义的坚持让他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但也让他被“权力动物”所排挤。最后,他依然出于本心,甘愿给封疆大吏做枪,推动完成了晚清最重要的一次权力更迭,然后又回到了他普通的人生轨迹之中。
我不想总结你能在这个故事里面学到什么关于权力斗争,抑或为人处世的技巧学问。我只想给你展现一个风云际会中的小人物,因为坚持本心而与大人物发生过的一段缘分。
历史不是什么教科书,也不是什么成功学宝典,历史就是一面镜子,它从中折射出我们不同选择的后果。然而有时候我们作出选择不是因为我们知道后果怎样,而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那样的人,像吴永一样,想改也改不了,如是而已。
好,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对书中其他内容还有兴趣,也建议你去阅读原书。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1.意大利历史学家圭恰蒂尼就说过一句话:“你在理解君主的意图时,不能用理性去判断,而是要从他的习惯和天性去判断。”
2.历史不是什么教科书,也不是什么成功学宝典,历史就是一面镜子,它从中折射出我们不同选择的后果。然而有时候我们作出选择不是因为我们知道后果怎样,而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那样的人,如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