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文集》 刘文飞解读
《契诃夫文集》|刘文飞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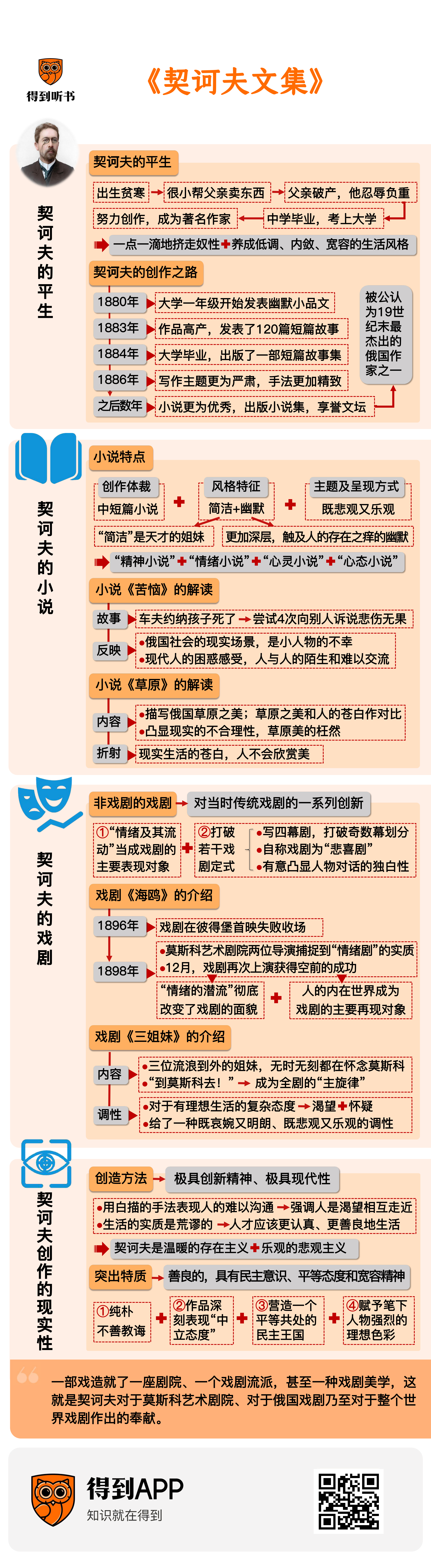
得到听书的朋友,你好!今天是我们“俄国文学名著”系列节目的最后一讲,我们来讲19世纪俄国文学中的最后一位大家,也就是契诃夫。契诃夫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也还是一位杰出的剧作家。因此,我们今天借由《契诃夫文集》这套书,来比较概括地来介绍一下他的小说和戏剧创作。
和大多数贵族出身的19世纪俄国大作家相比,契诃夫的出身是比较贫寒的。他1860年年初出生在俄国南部亚速海边的一座港口城市塔甘罗格,他的父亲是一家杂货铺的老板。契诃夫从小就是一个孝子,后来一生都是一个善良的人。他是家中的第三个孩子,上面有两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契诃夫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帮父亲站柜台卖东西,因为个子太矮,他常常要站在一个小板凳上,才能和顾客进行交易。后来,他的父亲生意破产,为了躲债逃往莫斯科。还在上中学的契诃夫独自一人留在塔甘罗格,寄人篱下,实际上是父亲留给债主的“变相的人质”。但是在三年多的时间里,这位中学生忍辱负重,自食其力,给人当家教,甚至还寄钱给在莫斯科的家人。三年之后,契诃夫中学毕业,考上了莫斯科大学的医学系,从此离开了故乡。
1889年,已经成为一位著名作家的契诃夫,在给他的朋友苏沃林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贵族作家们天生免费得到的东西,平民知识分子们却要以青春为代价去购买。你写一个短篇小说吧,讲一位青年,一个农奴的后代,他当过小店员和唱诗班歌手,上过中学和大学,受的教育是要尊重长官,要亲吻神父的手,要崇拜他人的思想,要为每一片面包道谢。他经常挨打,外出做家教的时候,连一双套鞋也没有……您写吧,写这个青年怎样从自己的身上一点一滴地挤走奴性,怎样在一个美妙的早晨,一觉醒来的时候感觉到,他的血管里流淌的已经不再是奴隶的血,而是一个真正的人的血……”契诃夫建议苏沃林描写的这个“青年”,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契诃夫自己。艰难的成长环境往往会使人愤世嫉俗,敌视一切存在,但有的时候却相反,会使人养成低调、内敛和宽容的生活风格。在契诃夫身上发生的,当然是后一种情况。
1880年,还是莫斯科大学一年级学生的契诃夫就开始在一些讽刺幽默杂志上发表小品文。由于这些作品都是搞笑故事,契诃夫在发表它们的时候常常使用各种笔名,他用的最多的署名是“契洪特”,这是契诃夫在上中学的时候他的老师给他起的外号,是对契诃夫姓氏的一种有意的变音,有调侃、搞笑,甚至贬损的意味。可是很有幽默感的契诃夫却把它拿来当成笔名,后来,他这个时期的创作也就被研究者们称为“契洪特时期”。契诃夫当年写作这些幽默故事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赚稿费,补贴家用,据说他用第一笔稿费给过生日的妈妈买了一个大蛋糕。这个时期,契诃夫的创作力十分旺盛,据统计,他在1883年一年之内就发表了120个短篇故事,平均三天写成一篇。契诃夫的早期短篇大多是一些幽默故事,但是其中也不乏后来流传于世的名作,比如《变色龙》和《万卡》等等。在契诃夫1884年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已经出版了一部短篇故事集。
1886年,当时俄国文坛的一位重要的作家叫格里戈罗维奇,他在读到契诃夫的小说之后,给契诃夫写了一封信。他在肯定契诃夫的天赋和才华的同时,也对契诃夫过于热衷搞笑、写作过于匆忙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建议契诃夫转向“严肃的写作”。契诃夫读了这封信之后,很受触动,他之后的创作也的确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虽然还在继续写作短篇故事,继续幽默的调性,但主题更加严肃了,手法也更加精致了。他在数年时间里写出了许多俄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最优秀的短篇小说,比如《苦恼》《草原》等等,他相继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杂色故事》和《在昏暗中》也引起了轰动。契诃夫从此享誉文坛,被公认为19世纪最杰出的俄国作家之一,他的地位似乎仅次于如日中天的托尔斯泰。
契诃夫的小说创作只有一种体裁,这就是中短篇小说。他篇幅最大的中篇译成中文也不过三四万字,简洁是他最大的小说创作特征,这首先就体现在中短篇小说这样的体裁上。纳博科夫曾经开玩笑地说:契诃夫是文学界的短跑选手,而不是一位有耐力的长跑运动员。契诃夫自己说过这样一句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姐妹。”他的短篇小说的另一个突出的风格特征,就是幽默;但除了他早期的一些作品之外,他小说中的幽默绝不是搞笑,甚至也不完全是果戈理式的“含泪的笑”,而是一种更加深层的、触及人的“存在之痒”的幽默。契诃夫的小说是所谓的“精神小说”“情绪小说”“心灵小说”和“心态小说”,表面上不写心理,但通过白描式的手法,却恰恰写出了主人公,乃至作者自己的深层心理和感受。契诃夫一生写了数百篇小说,放在一起有十几卷,我们在这里选择其中两个中短篇,来尝试着做一些解读和赏析。
第一篇是《苦恼》。这篇小说的前面有一个题词,也就是:“我向谁诉说我的苦恼?”这句话引自俄国的民间圣歌,这句题词就奠定了整篇小说的基调。小说里写到,车夫约纳的孩子死了,死了已经快一个星期了,他很想向别人诉说一下自己的悲伤,并先后四次做了尝试。他想对他的第一位乘客、一位急着去赶约会的军官说,但是却遭到了对方的冷遇。他好几次转过身去看那位乘客,却发现人家已经闭上了眼睛,显然不愿意再听下去。一个小时之后,他拉上了三位喝了酒的年轻人,他对三位年轻人说:“我的……那个……我的儿子这个星期死了!”乘客却回答说:“大家都要死的……得了,赶你的车吧,赶你的车吧!”其中一位乘客还嫌约纳赶车赶得慢,还对着约纳的后脑勺来了一巴掌。第三次,约纳想对自己的同行、另一位车夫说,这位车夫与约纳一起在等乘客,他似乎很愿意听约纳讲他的故事。可是听着听着,这位车夫也睡着了。小说中写道:
约纳又孤身一人了,寂静又向他侵袭过来……他的苦恼刚淡忘不久,如今重又出现,更有力地撕扯着他的胸膛。约纳的眼睛不安而痛苦地打量着街道两旁川流不息的人群:在这成千上万的人当中,究竟有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倾诉衷曲呢?然而人群奔走不停,谁都没有注意到他,更没有注意到他的苦恼……这种苦恼是广大无垠的。如果约纳的胸膛在此时裂开,那种苦恼滚滚地涌出来,那么它仿佛就会淹没整个世界。可是话虽如此,他的苦恼却是人们看不见的。这种苦恼竟包藏在这么一个渺小的躯壳里,就连白天打着火把也看不见……
最后,车夫约纳决定把自己的“苦恼”说给他那匹拉车的小母马听。“那匹瘦马嚼着草料,听着,向它主人的手上呵气。约纳讲得入了迷,就把他心里的话统统对这匹马讲了……”约纳的痛苦无处倾诉,这或许是当时俄国社会的现实场景,是小人物的不幸。但是,这同时也象征着现代人的困顿感受,人与人之间的存在主义状态,所谓“他人皆地狱”,人与人之间的陌生和难以交流是普遍的,无处不在的。
我们再介绍一下契诃夫的第二篇作品,它的题目叫《草原》。这部作品与其说是一个短篇小说,不如说是一首长篇散文诗。这部作品没有清晰的故事线索,通篇都是契诃夫关于俄国草原之美的描写。与此同时,契诃夫却拿草原的美和人的苍白作对比,以此来凸显现实的不合理性,这有些像我们在前面谈到的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的写法。契诃夫在这部作品中间写道:
你在路上碰见一所沉默的古墓或者一块人形的石头,上帝才知道那块石头是在什么时候,由谁的手立在那儿的。夜鸟无声无息地飞过大地。渐渐地,你回想起草原的传说、旅客们的故事、久居草原的保姆所讲的神话,以及凡是你的灵魂能够想象和能够了解的种种事情。于是,在唧唧的虫声中,在可疑的人影上,在古墓里,在蔚蓝的天空中,在月光里,在夜鸟的飞翔中,在你看见而且听见的一切东西里,你开始感到美的胜利、青春的朝气、力量的壮大和求生的热望。灵魂响应着美丽而严峻的故土的呼唤,一心想随着夜鸟一块儿在草原上空翱翔。在美的胜利中,在幸福的洋溢中,透露着紧张和愁苦,仿佛草原知道自己的孤独,知道自己的财富和灵感对这世界来说白白地荒废了,没有人用歌曲称颂它,也没有人需要它。在欢乐的闹声中,人们听见草原悲凉而又无望地呼喊着:歌手啊!歌手啊!
让契诃夫感叹的,不仅有草原的美,而且还有草原的美的枉然,似乎草原“白白荒废了自己的美丽”!美丽的草原是孤独的,美的白白荒废,其实折射的是人心的苍白,折射的是现实生活的苍白。人不会欣赏美,可能是在生活的重压之下无暇欣赏,也可能是在庸俗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们已经失去了对美的感受能力。
用最为简洁的形式来表达关于人类生活的存在主义感受,用黑色幽默般的态度来面对生活中的庸俗或庸俗的生活,用对人内心的诗意本质和生活中点滴的美的细心发现,来冲淡现实中无处不在的“苦恼”和“忧伤”,既悲观又乐观:这可能就是契诃夫中短篇小说总的主题以及它的呈现方式。用英国作家伍尔夫的话说,契诃夫创作的主题就是“灵魂得病了,灵魂被治愈了,灵魂还没有被治愈”。从伍尔夫的这个评价我们不难感觉到,契诃夫的小说其实写得很现代。他作为一位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家,可是他的小说却被后面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和读者反复阅读,并不断做出新的阐释。契诃夫的创作在他同时代的作家中间无疑是超前的。
契诃夫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也是一位伟大的剧作家,他戏剧创作的成就和影响丝毫不亚于他的短篇小说。契诃夫最重要的剧作有《普拉东诺夫》《海鸥》《三姐妹》和《樱桃园》等等,我在这里就简单地介绍一下《海鸥》和《三姐妹》这两部剧作。
1896年,契诃夫精心创作的剧作《海鸥》在彼得堡首演。剧中的女主角尼娜向往艺术,向往着理想的艺术家生活。她怀着想当演员的愿望,置身在乡间的农庄,面对一汪湖水,与身边的两个青年艺术家交往和对话。她说:“我被这片湖水牢牢地吸引着,就像一只海鸥。”《海鸥》全剧没有什么激烈的冲突,情节发展很缓慢,几个准艺术家在台上走来走去,说着一些前言不搭后语、相互缺乏关联的抒情的独白。当时的观众看不懂这样的戏,这次演出以失败收场,演出现场哄笑声不断。在现场观看的契诃夫半途退场,心情十分沮丧。演出结束之后,报纸上登出了这样的剧评,说:“这不是海鸥,而是一只野鸭!”但是两年过后,联手创建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琴科却苦苦哀求契诃夫,让他们重新排演此剧。因为这出戏剧的“情绪剧”的实质被这两位大导演敏锐地捕捉到了,也就是说,让人物的情绪取代传统的戏剧冲突,成为舞台上的主角。1898年12月,《海鸥》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的上演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从《海鸥》开始,人们对“舞台真实”产生了新的理解。舞台上的真实并不意味着生活中的真实,人的内在世界成为戏剧的主要再现对象,所谓“情绪的潜流”彻底改变了戏剧的面貌。在今天的莫斯科艺术剧院老剧场入口处的门楣上,有一个巨大的海鸥雕像,一只飞翔在海浪之上的海鸥图案也成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院徽,被绣在舞台的幕布上,印在每次演出的节目单上。人们在用这样的方式昭示契诃夫和他的《海鸥》一剧的不朽。一部戏造就了一座剧院、一个戏剧流派,甚至一种戏剧美学,这就是契诃夫对于莫斯科艺术剧院、对于俄国戏剧,乃至对于整个世界戏剧作出的奉献。
《三姐妹》一剧写三位流落到外省去的姐妹,在无聊的生活和失败的爱情中,无时无刻不在怀念莫斯科。“到莫斯科去!”这就成为了她们的心声和时刻挂在嘴边的台词,成为全剧的“主旋律”,“莫斯科”似乎就等于《等待戈多》中的“戈多”。对于有理想的生活,契诃夫表现出了一种复杂的态度。一方面,他认为人不能过没有任何理想的生活;另一方面,理想的生活究竟是否可能,也往往是令人怀疑的。因此,他在剧中给了我们一种既哀婉又明朗、既悲观又乐观的调性。就像他的短篇小说《出诊》中的主人公科罗廖夫说过的一段话,说:“过了50年,生活一定会美好;可惜我们又活不到那个时候。要是能够知道一点那个时候的生活,那才有意思呢。”在小说《在故乡》中也有一段抒情的独白,契诃夫是这样写的:“要知道,更好的生活是没有的!美丽的大自然、幻想、音乐告诉我们的是一回事,现实生活告诉我们的却是另一回事。显然,幸福和真理存在于生活之外的某个地方。”幸福在明天,但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却并不十分牢靠,也不十分确定,似乎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是,如果连希望也不具有,岂不是更糟糕?这是生活永恒的难题,每个有意识、有思想的人在一生当中或迟或早、或多或少都会遇到过。契诃夫不过以一种更为直接、更为尖锐,也更为艺术、更为美学的方式把它摆到了我们面前。在《三姐妹》的剧终,三位姐妹轮流独白,她们的话无疑是这部剧作的主题,乃至契诃夫整个世界观的集中体现。在这出戏的最后,三姐妹中的大姐奥尔嘉说道:
音乐演奏得多么欢乐,多么振奋,真想生活!哦,我的上帝!总有一天,我们会永远地离去,人们会忘记我们,忘记我们的脸庞、声音和我们的年纪。但是,我们的痛苦却会转化为后代人的欢乐,幸福和安宁将降临大地,如今生活着的人们将获得祝福。哦,亲爱的妹妹,我们的生活还没有结束。我们将生活下去!音乐演奏得多么欢乐,多么欢快,似乎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因为什么而生活,因为什么而痛苦……如果能知道的话,如果能知道的话!
俄国文学史家米尔斯基把契诃夫的戏剧定义为“非戏剧化的戏剧”。这种“非戏剧化”,其实就可以理解为对当时传统戏剧的一系列创新。契诃夫戏剧的“非戏剧化”,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把“情绪及其流动”当成戏剧的主要表现对象,用平淡的现实生活场景来屏蔽激烈的戏剧冲突,与生活拉近距离。用契诃夫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舞台上的一切应该像生活中的一切一样复杂,一样简单。人们吃饭,就是吃饭。但与此同时,要么他们的幸福正在形成,要么他们的生活正在断裂。”在契诃夫的戏剧中没有传统的戏剧冲突,比如决斗、错杀、揭开谜底、抖落包袱等奇情剧的元素,人物的心理、心境、内心生活、内心世界成为舞台上的主角。其次,为了服务于这样的戏剧表现对象,契诃夫有意地打破了若干戏剧定式。比如,他喜欢写四幕剧,故意打破奇数幕的划分,目的就是淡化戏剧的高潮。因为如果是三幕剧或者是五幕剧,戏剧情节的起伏就会显得更强烈一些,就更方便把戏剧高潮设计在剧中或者剧末。而两幕剧、四幕剧就结构自身而言就会显得平淡一些,稳重一些。比如,契诃夫从来不愿意界定他的戏剧究竟是悲剧还是喜剧,他自称是“悲喜剧”,也就是悲剧和喜剧的相互融合。看到有导演把他的戏当成了悲剧,他就说他的戏是喜剧;但是在导演们把他的戏处理成纯粹的喜剧的时候,他又心有不甘,又说他的戏是悲剧。一个大学生在看了契诃夫的戏之后,写信给契诃夫,说他是“流着泪看完的”。契诃夫在回信中间不以为然地说:“我只不过想告诉你们,看看你们的生活,你们的生活多么糟糕呀,我们生活得多么糟糕呀!这有什么好哭的呢?!”再比如,契诃夫有意凸显剧中人物对话的独白性,不让剧中人物的交流过于流畅,让剧中的人物常常是环顾左右而言他,或者是词不达意、言不由衷。契诃夫以此来表达人的交流障碍和理解困难,以此来构成戏剧中的复调效果。这样的戏剧设置是服务于剧作者独特的主观立场的,契诃夫把戏剧的冲突从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转变成人与环境之间的冲突,他的戏剧也由此成为一种体现人类存在荒诞性的哲理剧。契诃夫是世界范围内剧作上演频率最高的现代剧作家,与莎士比亚并列;莎士比亚是被上演频率最高的古典剧作家。
在19世纪的俄国作家中,契诃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可能是最具现代性的作家。契诃夫是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最后一位世界级大作家。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发展在这个时候已经达到了顶峰,它自觉或不自觉地都会发生某种变化。在契诃夫创作晚期,俄国文学的“白银时代”已经开始。以象征主义诗歌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已经开始,印象派、表现主义等艺术方面的现代派也已经成为时尚,这些都注定会对契诃夫产生影响。
从具体的创作方法上来看,契诃夫是极具创新精神,极具现代性的。在我们前面关于契诃夫的小说和戏剧创作的讨论中间,已经谈到了契诃夫一些独特的创作方法,比如“精神小说”“心态小说”的存在主义主题,他的小说用白描的手法表现人的难以沟通,难以相互理解,但又强调人是渴望相互走近的。生活的实质是荒诞的、无意义的,但是正因为人生的荒诞和无意义,人才应该更认真地生活,更善良、更优美地生活。契诃夫是温暖的存在主义,也是乐观的悲观主义。纳博科夫说:“契诃夫把一切传统小说的写法都打破了。”这句话出自纳博科夫这样一位以小说形式创新著称的作家之口,应该更能让我们感觉到其中的分量。
契诃夫的善良,他的民主意识、平等态度和宽容精神,在他同时代的作家们中间显得十分突出。他的妻子克尼碧尔,后来在回忆录中间这样写到她和契诃夫的第一次见面,她写道:“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第一次站在契诃夫面前的那一刹那。我们都深深地感觉到了他人性的魅力,他的纯朴,他的不善于‘教诲’和‘指导’……”打动克尼碧尔的是契诃夫的“纯朴”和“不善教诲”。契诃夫的“中立态度”,更深刻地体现在他的创作中。契诃夫对他笔下的主人公是充满爱意的,即便对于那些“反派”人物,契诃夫也是不带恶意和敌视的。甚至面对“变色龙”“套中人”这样的典型,契诃夫的态度也不是居高临下和毫不留情的。契诃夫试图在他的创作中营造一个各色文学人物平等共处的“民主王国”,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他的作品中间“既没有恶棍,也没有天使……我不谴责任何人,也不为任何人辩护”。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对人的信赖和关于人的信念。他始终赋予其笔下的人物以强烈的理想色彩,而且,越到他创作的后期,这种“相信人的未来”的大善良就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充分。
听众朋友,在这一讲中我们分别谈了契诃夫的生平,他的小说和他的戏剧创作,以及他的创作所具有的现代意义。
讲完了契诃夫,我们关于19世纪八部俄国文学名著的介绍也就告一段落了。我们从普希金一直讲到契诃夫,这几位作家跨越的正是俄国文学的“黄金世纪”。之后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尝试再讲一讲俄国文学的“白银时代”,以及20世纪的俄苏文学,甚至是当代的俄罗斯文学。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白银时代”,在独具特色的苏联文学时代,在20世纪中叶的“解冻”时期,在苏联解体前后,都出现过“文学天才成群诞生”的壮观景象,也涌现出了一批举世闻名的文学名著,它们都值得介绍给你。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希望我们有机会再见!
好,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方的“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一共由十六卷构成的这部《契诃夫文集》,它的电子书已在“得到”上架,感兴趣不妨阅读一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再见。
划重点
1.契诃夫的小说是所谓的“精神小说”“情绪小说”“心灵小说”和“心态小说”,表面上不写心理,但通过白描式的手法,却恰恰写出了主人公,乃至作者自己的深层心理和感受。
2.契诃夫把戏剧的冲突从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转变成人与环境之间的冲突,他的戏剧也由此成为一种体现人类存在荒诞性的哲理剧。
3.契诃夫的作品中“既没有恶棍,也没有天使……我不谴责任何人,也不为任何人辩护”。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放弃他对人的信赖和关于人的信念,而始终赋予其笔下的人物以强烈的理想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