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原版)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 1968 刘怡解读
(英文原版)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 1968| 刘怡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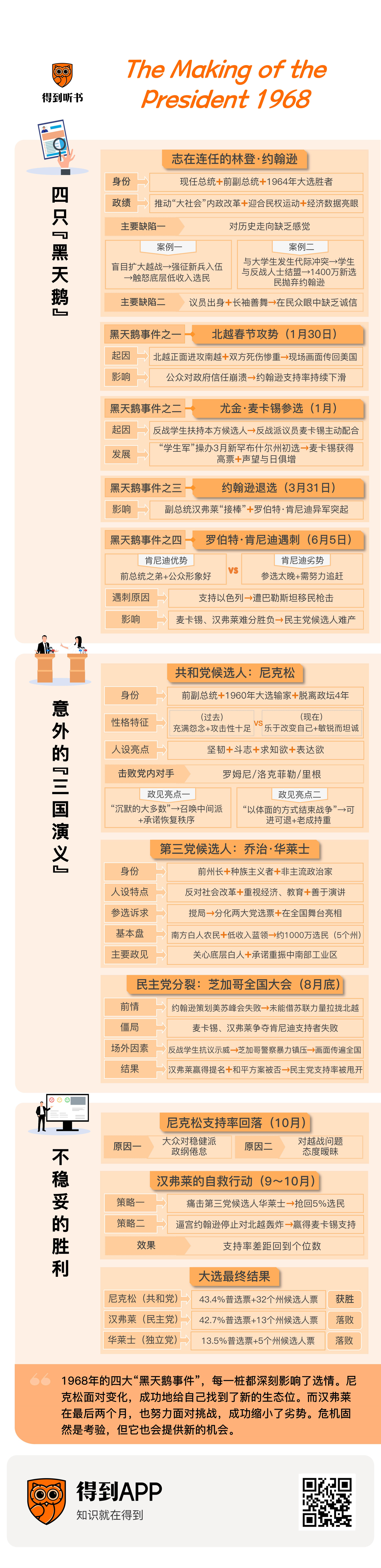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刘怡。今天我要为你讲的书,叫做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 1968,直译过来就是“美国总统的诞生1968”。顾名思义,它讲的是1968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故事。2024年又是美国的大选年,关心国际局势的朋友,对这个话题想必做了不少功课。问题是,1968年距离2024年,可是隔了整整56年。别说美国社会了,就连提名规则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那为什么我还要推荐你了解这段陈年往事呢?别急,咱们先猜个谜语。
话说有这么一年,美国面临总统大选,但社会气氛极为紧张。大学生为了抗议对外政策失当,发起了一系列静坐示威。通胀问题和种族议题也在持续发酵,报纸上每天都有坏消息。在任的民主党总统,原本希望争取第二个任期,没承想初选开始了几个月,他的支持率始终很低迷。结果,总统只能咬咬牙,宣布放弃连任,让副总统顶上。但对手共和党方面呢,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因为他们征召的候选人,从前就输过一次大选,公众形象还不太好。于是,整个选战开始走向混乱。有人开枪暗杀候选人,震惊了世界。还有人别出心裁,把白人里的低收入群体变成了自己的票仓,成为政坛“黑马”。民主党把自己的全国大会定在8月下旬,地点在芝加哥。但到那时为止,谁胜谁败依旧看不出头绪。激烈的角逐一直持续到了最后几个星期,民调结果频繁波动,谁都不敢打包票说自己有必胜的把握。
听到这儿,你是不是以为我在说2024年这场大选?那你就错了。其实,这些都是1968年大选的戏码;主要“演员”不是拜登、哈里斯、特朗普,而是约翰逊、汉弗莱和尼克松。2024年发生的一切,像是政治极化、临阵换将,包括暗杀,在1968年已经预演过一次了。虽然历史不能简单类比,也不会100%重复过去,但了解1968年大选的经过,还是可以为你理解当下的美国政治,乃至许多复杂的政治现象,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你会发现,当整个社会经历深刻的经济和代际变化时,过往的成功经验,以及固化的传统思维,是会被颠覆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将主导事态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那些敢于面对不确定性,并从中发现潜藏机会的人,才有可能开创出全新的局面。
本书作者白修德,是美国传奇政治记者,职业生涯长达近半个世纪。早在“二战”时期,他就以《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的身份,撰写关于中国抗战的现场报道,因此声名鹊起。20世纪50年代,白修德转向报道美国政治。他从1960年开始,每隔四年就深度采访美国总统大选,再集结成书,形成了“美国总统的诞生”这个书系。在采访过程中,白修德不仅会还原大选之年,美国社会和舆论的核心关注点,他还会跟主要候选人直接交谈,记录他们的选战策略和性格特质。像1968年这一回,白修德就采访了退选的约翰逊总统和最后的胜利者尼克松,并用生动的文笔呈现出来。这种观察和记录模式,深刻影响了整个美国新闻业。《纽约客》杂志在1978年盛赞说,白修德的“美国总统的诞生”书系,是“新闻行业的一座丰碑”。“得到听书”此前解读过这个书系的第一部《美国总统的诞生1960》,本书则是第三部,精彩程度丝毫不减。相信它也会让你大有收获。
接下来,我就分三部分,为你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1968年大选为什么发展成了乱战,执政的民主党遇上了哪些麻烦。在第二部分里,我会为你分析,几位主要候选人都采取了哪些选战策略,实际效果又是如何。最后,我再为你总结一下,大选的最终赢家尼克松,做对了哪些事,他的胜利又有多少偶然性。
全书一开篇,作者白修德首先把我们带回1968年1月的美国。到那时为止,林登·约翰逊总统顺利连任,似乎还是理所当然的事。这里简单介绍一下约翰逊:1963年肯尼迪遇刺后,约翰逊以副总统身份递补继任,干完了肯尼迪剩下的一年任期。1964年,他又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自己第一场独立的总统大选。如果单看纸面成绩,约翰逊这位民主党总统干得相当出色。他发起了著名的“大社会”内政改革,在消除贫困、医疗保障和改善基建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成效显著。他顺应黑人民权运动的呼声,给了有色人种平等的投票、就业和住房机会,备受好评。美国的经济呢,虽然遇上了通胀,但失业率很低,GDP增长率接近5%。这让约翰逊本人异常自信,觉得连任已经十拿九稳了。
可作者白修德却说,当总统不光需要治国才能,还得会捕捉社会情绪的变化趋势,得对历史的走向有感觉。1932年的罗斯福,还有1960年的肯尼迪,都是在这种历史感的加持下,才当上了总统。但约翰逊就缺乏这种感觉。有两件深刻影响美国社会的大事,没有引起他的重视。第一件事是越南战争。1964年北部湾事件之后,越战开始全面升级。约翰逊政府在短短3年内,把派驻越南的美军从1万多人增加到了52万。这些军人里,有1/3是强制征召的义务兵,特别是家境贫寒、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底层年轻人。像电影《阿甘正传》的主角,就属于这种类型。在拙劣的指挥下,美军在越南战场的伤亡率高达1/7,却还在源源不断地投入人力物力。这让底层民众形成了一股怨气,他们觉得,约翰逊是要用万里之外的战争,变相消灭美国的低收入群体。这就形成了第一股反对总统连任的力量。
底层青年充满愤怒,大学生也好不到哪儿去:这是约翰逊忽视的第二件大事。“二战”结束后,美国的高等教育系统迎来了一波扩张,在校学生人数从135万人一路上升到了690万。这些年轻学生和他们的父辈不大相同,他们更关注社会公平和外交政策,这就和反战人士形成了天然的同盟。更重要的是,大学生群体的行动力非常强。他们在1967年发起了“抛弃约翰逊”的宣传活动,还跟黑人民权运动中的激进派公开结盟。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这其实是一种代际冲突,是“二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世代美国人,对上一辈人的反叛。代际冲突追求的不是多么具体的目标,而是在情感和价值观上被接纳。但约翰逊就不明白这一点,他认为,打仗是政治家和军人的事。至于种族问题吗,政府已经通过了那么多改革法案,难道还不够吗?这就把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
要知道,在1968年,有1400万美国人是第一次获得投票权。他们中有200万是黑人,1200万是大学生和刚成年的年轻人。约翰逊对他们的诉求置之不理,约等于得罪了1/8的选民。更要命的是,约翰逊的个人形象也很糟糕。他是资深国会议员出身,最擅长的不是面对公众,而是玩弄权术,推动自己的法案在国会顺利过堂。美剧《纸牌屋》的主人公安德伍德总统,原型之一就是约翰逊。在议会政治中,长袖善舞、转换立场是很常见的事,也是必要的政治技巧。但当了总统,还搞这一套,给人的感觉就不好了。1968年的情况就是这样:1月初,约翰逊让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对公众放话,说北越军队已经失去了战斗意志,美国在年底之前就能打赢越南这场仗。不料就在1月30日深夜,北越出动10多万大军,对南越的六大主要城市发动了正面进攻。这就是越战历史上著名的“春节攻势”。
从军事角度看,春节攻势是一场彻彻底底的失败。北越军队的总伤亡超过5万人,没能拿下任何一座大城市。但美军同样蒙受了重大伤亡,南越首都西贡的美国大使馆还遭到围攻,现场画面通过电视新闻,迅速传回了美国。这样一来,公众对约翰逊的不信任情绪被彻底点燃了。对手都打到南越首都了,约翰逊你还有脸说美国马上就能赢?撒谎!于是,“春节攻势”就成了1968年大选的第一个“黑天鹅事件”。约翰逊开始被社会舆论反复“拷打”,变得焦头烂额。
当然,要是民主党内部没有出现公开的挑战者,约翰逊也许还能咬咬牙,挺过这一关。问题是,第二个“黑天鹅事件”很快就来了。1967年,两位年轻的反战活动家——纽约城市大学教授洛文斯坦和哈佛大学研究员山姆·布朗提出了一项愿景。他们认为,既然美国年轻人如此讨厌约翰逊这种老政客,那他们应该扶持自己心仪的候选人,把他选进白宫。洛文斯坦和布朗挑中的,是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参议员尤金·麦卡锡。这位麦卡锡和“冷战”初期的反共急先锋麦卡锡不是一个人,他当过大学教授,沉默寡言,在国会里不是一个多醒目的角色。但麦卡锡公开反对越战,还以清廉著称,在青年群体里有很强的号召力。他清楚,以自己在民主党内的资历、声望,根本不可能跟约翰逊正面对抗。但麦卡锡的内心也有抱负,也想站上擂台试一试。因此,他把自己的竞选活动直接“外包”给了反战的大学生。
不得不说,1968年参与选战的这批美国大学生,虽然缺乏经验,眼光和行动力却是一流的。1968年1月麦卡锡正式报名参选后,他的“学生军”马上就意识到:麦卡锡的影响力局限在北方的几个州,他在全国层面名气还不够大。但要是先集中力量,在党内初选中拿下几个州,麦卡锡这个名字就会传遍全国,到时就有了进一步操作的空间。按照惯例,第一场党内初选定在3月上旬,地点是新罕布什尔州。约翰逊总统对自己信心十足,没有做任何针对性部署。而支持麦卡锡的3000多位大学生,1月份就赶到了当地。他们缺少资金支持,就以小额捐赠的形式募款,为麦卡锡购买电台广告时段。课本上教授的民调和宣传技巧,被他们直接用在了这场特殊的社会实践中。他们还挨家挨户敲门,拜访了4万多个当地家庭,记录他们的诉求,向他们发放传单。而1月底“春节攻势”开始后,约翰逊在全国的人望一下掉到了谷底。此消彼长之中,支持麦卡锡的呼声开始在民主党内部浮现。两个“黑天鹅事件”合流了。
3月12日,第一场初选结果揭晓。约翰逊拿到了49%的支持票,但麦卡锡也有42%,这给约翰逊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当时,“春节攻势”引发的负面舆论已经彻底发酵,CBS电视台的民调显示,有63%的美国人反对政府的越战政策。一批退休高官开始对总统“逼宫”,他们暗示:要是约翰逊没有必胜的把握,那就应该把党派利益置于个人之上,让位给形象更好的候选人。作者白修德在3月下旬拜访了约翰逊,他注意到,总统心力交瘁,显得疲惫而孤独。紧接着,3月31日,约翰逊在全国电视讲话中突然宣布:他决定放弃连任,改为支持副总统休·汉弗莱。另外,他继续承诺,将在1968年之内,通过与北越正式谈判的方式结束战争。这样一来,第三个“黑天鹅事件”也出现了。
然而,约翰逊退选的最大受益者,既不是汉弗莱,也不是刚刚崭露头角的麦卡锡。因为就在3月16日,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弟弟、前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也加入了民主党的混战。这位肯尼迪和他的哥哥一样,形象出众,能言善辩。他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越南问题,又亲近民权运动,这就分化了麦卡锡的基本盘。约翰逊退选之后,肯尼迪一下成了中间派民主党人的宠儿。但他参选太晚,整个4月都在忙着建立选战班底,麦卡锡的强势也就多维持了一个月。不过,进入5月,肯尼迪的明星效应开始彰显。他在印第安纳、内布拉斯加等几个州,都以明显优势击败了麦卡锡。民主党内部,现在形成了麦卡锡、汉弗莱、肯尼迪三人并驾齐驱的局面,其中肯尼迪的后劲似乎是最足的。
但1968年这场大选,乱就乱在,意外事件总是层出不穷。4月4日,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美国随后爆发了大规模黑人骚乱。这个事件显示,极端情绪和暴力活动在美国民间已经普遍存在,并且将直接影响顶层政治。然而,肯尼迪对此并不在意。他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参选太晚,一定要抓紧时间多跑几个州,多办几场拉票活动,才能尽快逼退麦卡锡,与汉弗莱正面对决。因此,6月4日拿下加州初选后,肯尼迪在洛杉矶多待了一天,对当地支持者发表演讲。6月5日凌晨,当他离开集会的酒店,从厨房小门借道时,一位24岁的巴勒斯坦移民对他开了四枪,肯尼迪当场身亡。刺客供认说,他是要抗议肯尼迪在中东战争中,公开支持以色列。关于这起案件的真相,美国民间一直众说纷纭。但无论如何,它成了影响选情的第四个“黑天鹅事件”。最强势的“黑马”意外身亡,麦卡锡和汉弗莱还没有分出胜负。这时距离投票日,只剩下不到5个月了,民主党要派谁出战,依旧没有任何头绪。
好,刚刚我们回顾了1968年上半年,影响选战的四个“黑天鹅事件”。它们涉及的主要是民主党阵营。那共和党当时在干什么呢?答案就一个字:在“等”。因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早就确定了,那就是曾在1960年落败的尼克松。
尼克松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位美国政治家。白修德在《美国总统的诞生1960》中,也分析过他当年败给约翰·肯尼迪的原因。但你可能不知道,尼克松在1962年还参加了加州州长选举,而且又输了,这让他暂时离开了政坛。从1963年开始,尼克松以闲云野鹤的姿态,在纽约当了4年律师,但这反而治愈了他的人生。作者白修德分析说,尼克松是一位出身贫寒,依靠个人奋斗走上巅峰的政治家。他在50岁之前,面对肯尼迪这种出身名门、光芒四射的对手时,内心有很强的嫉妒感。美国公众眼里的尼克松,也总是充满怨念,攻击性十足,给人的印象很不沉稳。但在蛰伏的四年岁月里,尼克松开始尝试改变自己。他的收入很高,买了新房子,有大把的时间读书、听音乐,还系统学习了历史。他和年轻学者来往,修正了刚愎自用的性格,变得敏锐而坦诚。有一回,白修德在飞机上偶遇尼克松,后者一本正经地和他谈论起了,最近在读什么书,记者有哪些采访技巧,美国的政治问题该怎么解决。白修德当即意识到,面前这个尼克松,既有当初的坚韧和斗志,又多了几分求知欲和表达欲。他的人设出现了新亮点。
当然,要想在1968年赢得共和党的提名,尼克松也有几个竞争对手。但这几个人,各有各的缺点。排名第一的是密歇根州州长乔治·罗姆尼,他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和老派政治家,但对外交政策缺乏主见。问题是,越战是1968年最热门的话题,候选人不能不发声。罗姆尼每发表一次看法,就引起一片哗然,最终在2月份退选了。排名第二的是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他是共和党里的进步派,但过于喜爱内斗,政治形象不好。洛克菲勒希望排名第三的政坛新星里根先顶上,去和尼克松竞争,等他们两败俱伤了,自己再坐收渔利。问题是,里根也是这么想的,他在党内初选中也没有尽全力。这样一来,充了四年“电”的尼克松就在初选中一马当先,拿下了共和党的提名资格。
那尼克松要怎样回应,美国在1968年面临的种种问题呢?答案是一个著名的概念,叫“沉默的大多数”。尼克松认为,民主党在过去两届大选中,打的都是“改革牌”。种族议题和反战问题,就是被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和宽松的舆论环境炒热的。问题是,黑人和激进的年轻选民,加起来只有1400万,美国选民的总数却有1.2亿。剩下那1亿人,大部分属于郊区中产阶级、高级蓝领和“二战”老兵。他们未必赞成越战,但也不喜欢年轻人的反叛,更不喜欢暴力和社会冲突。只不过,媒体平时不关注这个面目模糊的群体,无形中放大了年轻人的声音。而尼克松要做的,就是把这个“沉默的大多数”召唤出来,告诉他们:自己会恢复社会秩序,制止暴力,让美国重新回到正轨。对越战问题,尼克松用了一个含糊的说法,叫“以体面的方式结束战争”。换句话说,他既不宣扬扩大越战,也不承诺马上展开和谈,进退都说得过去。这种老成持重的论调,可谓滴水不漏,很快吸引了一大批中年人,构成了他的基本盘。
这样说来,尼克松是不是稳了?并没有。1968年的独特之处在于,选情每个月都有新变数。夏天还没过完,一个意外的新人就冒了出来,那就是亚拉巴马州前州长乔治·华莱士。华莱士是个奇人:他是个公开的种族主义者,反对一切社会改革。但他对发展经济和教育,又很热心,也取得过不错的地方政绩。在个人形象上,华莱士善于演讲,极富个人魅力。他其实非常清楚,自己那些耸人听闻的言论,既得不到两大党中任何一派的支持,也不是美国社会的主流。于是,华莱士另起炉灶,组建了美国独立党,以第三方身份加入选战。两党争雄就这样变成了“三国演义”。
那华莱士的诉求是什么呢?两个字:搅局。他的支持者,主要是美国南方的白人农民和低收入蓝领。这些选民分布在5个小州,加起来只有1000多万,肯定不足以把他选进白宫。但要是他能“吃定”这5个州,民主党跟共和党又打成平手,那大选结果会被提交国会裁断。到时候另外两方都要拉拢他,他会获得在全国舞台上亮相的机会。于是,华莱士在美国中南部组织了一系列巡回演讲。他告诉自己的支持者,南方白人之所以生计艰难,是因为民主党政府把新的工作机会都给了大城市。只有他关心农村底层白人的处境。对蓝领工人,华莱士的论调是:黑人和移民正在夺走美国的就业岗位,如果他当选,一定会重振中南部工业区。你听听,这些说法是不是很熟悉?是不是很像2016年以来,美国一些政治家的话术?它的始作俑者就是乔治·华莱士。而华莱士在1968年的舆论场中,还真的掀起了一些波澜。他在全国的支持率一度高达20%,直到10月份才大幅回落。由此看来,当时的美国社会是分裂的。
和美国社会一起陷入分裂的,还有民主党阵营。6月肯尼迪遇刺之后,麦卡锡和汉弗莱依旧没能分出高下,民主党需要召开全国大会,来决定候选人归属。为了把肯尼迪的支持者收入囊中,麦卡锡和汉弗莱在场外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偏偏已经退选的约翰逊总统,也跳出来给自己“加戏”。他秘密联络了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准备在8月份举行美苏首脑峰会,借助苏联的力量让北越同意对美和谈。这次峰会定在8月下旬,约翰逊认为,只有等他从苏联人那里带回了好消息,民主党的选情才会有起色。因此他坚持要求,把全国大会定在8月底,地点选在“铁腕市长”戴利管理的芝加哥市。巧的是,2024年民主党全国大会,也是在芝加哥召开的。历史中总是充满了意外的巧合。
那1968年这次大会的结果怎么样呢?很不幸,从头到尾都是一片混乱。8月20日,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美苏峰会取消了,约翰逊的承诺也落空了。8月26日,芝加哥大会刚刚开幕,就陷入了僵局。肯尼迪的支持者既不想要麦卡锡,也不支持汉弗莱,他们打算再推出一个候选人。大会被迫暂停。没事可干的记者们听说,有几千名支持麦卡锡的反战学生,从全国各地涌进了芝加哥,正在会场外面抗议,于是带着器材过去拍摄。他们震惊地发现,戴利市长派出的11000名警察,正在殴打这些示威者,空气里到处都是催泪瓦斯的烟雾,连大会会场都被灌进了浓烟。这场冲突持续了整整四天四夜,有1100多名示威者和100多名警察被打伤,还有600多人被捕,这才勉强平息。
不夸张地说,芝加哥的这场骚乱,彻底毁掉了民主党的整个选战。有8900万美国人通过电视画面,看到了警察殴打示威者的镜头。反战人士对此自然深恶痛绝,他们即使不会支持尼克松,也下决心绝不投票给民主党人。保守派则认为,正是民主党政府对青年群体的长期纵容,造成了这场骚乱。要是尼克松当选,秩序就会恢复,不会出现这种乱象。大会闭幕那天,尼克松在民调中的领先比例,一度高达22%。这是自选战开始以来,双方差距的峰值。
当然,我们也得交代一下这次大会的结果。8月29日,汉弗莱在约翰逊和戴利的支持下,终于艰难地说服了一部分肯尼迪派,拿到了提名资格。但在约翰逊的压力下,汉弗莱提出的在越南立即停火,加速实现和平的方案,被大会否决了。更糟的是,大会闭幕的第二天,一群芝加哥警察为了搜捕反战人士,闯进了代表们下榻的酒店,甚至用警棍殴打了几位国会议员。义愤填膺的麦卡锡当场宣布:虽然他没能拿到提名权,但他的支持者也不会拥护汉弗莱。这样一来,汉弗莱的形象,就和已经声名狼藉的约翰逊彻底绑定了。一切都在朝着不利于民主党人的方向发展。
好,刚刚我们回顾了1968年选战中期,“三国演义”格局的形成。到8月底为止,尼克松的选情都是一片大好。但在最后8个星期,事情又起了变化。汉弗莱奋起反击,一度把支持率的差值追到了个位数。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尼克松的竞选策略有一个重大缺陷,那就是讲不出新故事。8月份的时候,他呼吁“恢复秩序”,还有人听的进去;到了10月份,他还是那一套,大众就有点倦怠了。另外,尼克松对越战问题的态度,是“少说少错”,尽量不表态。这让一些中间派选民认为,他是一个不敢担责任的人,内心产生了犹疑。而一直被看衰的汉弗莱,恰恰在这个时候,展开了自救行动。整个9月,汉弗莱一直追着最弱的华莱士猛打。他动员了美国中西部的左翼工会和妇女团体,针对华莱士的极端言论展开痛击,成功夺回了全国5%的选民。在这一战果鼓舞下,汉弗莱又对约翰逊发起“逼宫”,要求立即停止对北越的轰炸,推动双方达成和平协议。9月30日,约翰逊被迫松口。同一天,坚定反战的麦卡锡呼吁自己的支持者投票给汉弗莱。美国选举史上多次出现的“10月奇迹”,差一点就在1968年重演了。
那尼克松是怎么应对的呢?他做了一件不太光彩的事,就是派自己的私人朋友去游说越战的另一个当事方——南越政府,让他们破坏和谈。这使得汉弗莱的和平倡议,没有立即结出硕果。但在投票前48小时,两个主要党派的支持率已经非常接近。盖洛普民调测算的结果是:尼克松将以2%的微弱优势获胜。这也是盖洛普声名鹊起的开始。
事实是,尼克松确实赢了,但赢得并不稳妥。他最终拿下了43.4%的普选票,成功赢得32个州。汉弗莱拿下42.7%的普选票,赢得13个州和首都华盛顿。双方在全国的差距只有51万票,其中三个州的得票率差距,更是不足3%。第三党候选人华莱士赢下了南方5个州,但未能成功搅局。这种犬牙交错、难解难分的局面,正是美国社会在20世纪60年代,剧烈变动的结果。而选民的代际变化,政治极化的出现,乃至社会议题的升温,并不会随着1968年大选的结束而落幕。它们将继续影响美国政治,直到今天。
好了,关于这本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 1968的主要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1968年总统大选,在美国政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正是因为初选阶段出现的一系列混乱,美国两党从1969年开始,确立了新的选举规则。只有正式报名参加初选的候选人,才有资格得到全国大会的提名。现任总统如果中途退选,竞选资金只能转给原来的搭档。拜登退选、哈里斯“接棒”,就是根据这套规则完成的。
但比规则变化更重要的遗产,是应对重大变局的能力。1968年的四大“黑天鹅事件”,每一桩都深刻影响了选情。尼克松面对这些变化,成功地给自己找到了新的生态位,最终胜出。而汉弗莱在最后两个月,也努力面对挑战,成功缩小了劣势。危机固然是考验,但它也会提供新的机会。这个道理对政治以外的问题同样适用。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此外,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1.当总统不光需要治国才能,还得会捕捉社会情绪的变化趋势,得对历史的走向有感觉。约翰逊就是因为缺乏这种感觉,在越战问题上出现重大误判,才黯然退选。
2.尼克松在选战期间,提出了“沉默的大多数”这一著名概念。他承诺会恢复社会秩序,制止暴力,让美国重新回到正轨。这些口号对中产阶级选民很有吸引力。
3.乔治·华莱士早在1968年,就注意到了美国南方农民和白人蓝领群体的贫困状况,并用煽动性的言论,把他们变成了自己的票仓。这是政治极化的先兆。
4.1968年的四大“黑天鹅事件”,每一桩都深刻影响了选情。尼克松面对这些变化,成功地给自己找到了新的生态位,最终胜出。而汉弗莱在最后两个月,也努力面对挑战,成功缩小了劣势。危机固然是考验,但它也会提供新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