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原版)The Last Kings of Shanghai 吴晨解读
(英文原版)The Last Kings of Shanghai | 吴晨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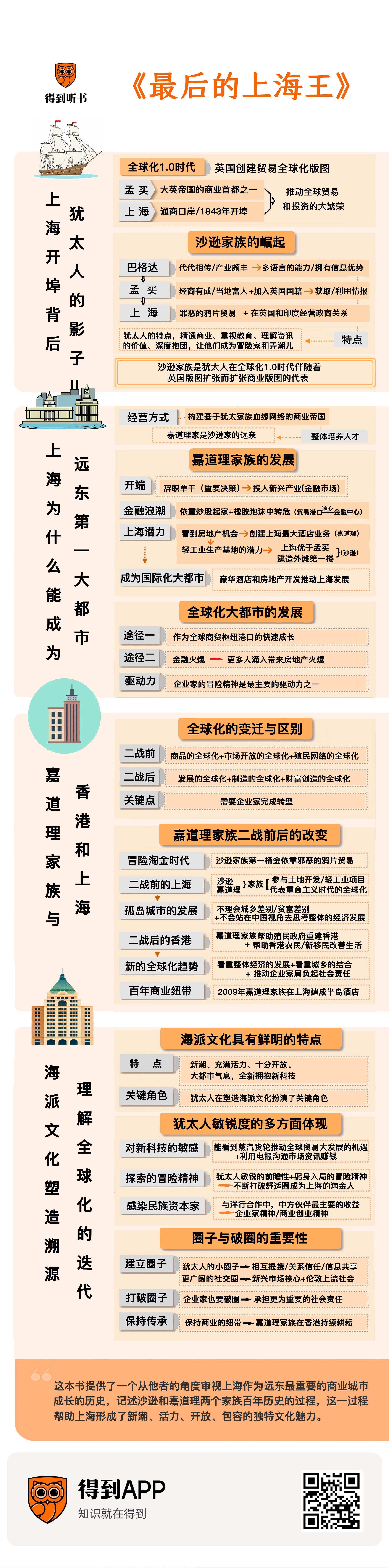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一本2021年在美国出版的书。它的名字叫做The Last Kings of Shanghai。我们可以叫它《最后的上海王》。它的副标题是可以翻译为“犹太家族之间的竞争帮助创建现代中国”。
2023年电视剧《繁花》热映,让中国人得以追忆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的繁华。但这本书告诉我们,其实,早在100年前,海派文化就已经风靡世界。
海派文化有着明确的特点:新潮、充满活力、十分开放、大都市气息,全新拥抱新科技。很多人可能想不到,1895年上海就有了有轨电车体系和供气系统,与伦敦是同时的。1930年,上海的天际线已经堪比芝加哥,摩天大楼可以与全球任何一座顶尖大城市比肩。可以说,100年前的上海已经是远东最具全球特色的大都市。
在全球化1.0时代,为什么开放的上海不仅能够成为远东第一大都会,成为亚洲最重要的经济与商业中心,也能形成非常有鲜明特色的文化?这本书告诉我们,犹太家族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有人说,犹太人是智慧社会中的盐,带来心智上的刺激。在我们讲述上海开埠181年历史的时候,离不开犹太商人在这个远东冒险家乐园所留下的印记,尤以沙逊家族和嘉道理家族为甚,这也是为什么《Last Kings of Shanghai》(最后的上海王)把这两个家族的兴衰与上海的故事串联在一起讲述。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个故事。
我们知道,今天上海特别流行City Walk(城市漫步)。如果在外滩的建筑博物馆漫步,肯定不会错过两栋跨越时空的建筑,一座是建于1929年的和平饭店,另一座则是比邻苏州河外白渡桥的新建筑,也是外滩唯一一栋新建筑,建于2009年的半岛酒店。两座酒店把上海的历史与在上海滩闯荡的犹太家族联系了起来。和平饭店是沙逊家族的杰作,而半岛酒店则是嘉道理家族与中国大陆持续保持联系的结晶。
有人戏称上海是中国的“孟买”,那是不懂得全球化的历史,对孟买也显得不够尊重。早在1843年上海开埠以前,孟买就已经成为大英帝国的商业首都之一。在上海淘金的沙逊和嘉道理两大家族,如果溯源的话,都是经过孟买洗礼的来自巴格达的犹太人。从他们的身世上我们就不难看出全球化与贸易和冒险精神。在上海1843年开埠之前,英国人已经在印度的孟买经营多年,与中东的经贸往来频密,善于经商的犹太人更是在英国创建的贸易全球化版图中如鱼得水。换句话说,英国为全球化1.0提供了“英国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ica),并据此推动了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大繁荣。
先来讲讲沙逊家族的创业故事。
沙逊家的鼻祖要溯源到1829年逃离巴格达的大卫·沙逊。沙逊家在巴格达产业颇丰,但到了十九世纪初,统治巴格达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已经感受到以大英帝国为代表的海洋帝国崛起带来的压力,开始横征暴敛。作为沙逊家的传人,大卫为了躲避灾祸而逃到孟买。十多年后,大卫在孟买经商有成,成为当地的富人,并选择加入英国国籍。
大卫是会多种语言的能人,在前信息时代,识字是成功商人的必须,而会多种语言则一定带来巨大的信息优势。犹太人恰恰是识字率极高的族群,而像沙逊这样中东的商人世家,天然就会操用多种语言。
大卫·沙逊早年为了跟官府打交道,跟巴格达的土耳其人讲土耳其语,跟阿拉伯商人说阿拉伯语,与穿梭在海上的水手和船长说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在家里说希伯来语。这种多语言的能力在一个信息闭塞的世界,使得他拥有了巨大的信息优势。到了孟买,沙逊的英文突飞猛进,相比较英国商人和孟买本地的土著,多语言的信息优势也是碾压式的。
举一个例子,1850年代,沙逊从船长口中了解到英国棉布生产旺盛,从而推断出从印度出口棉花的生意即将火爆,开始下注棉花贸易。到了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美军掐断了美国南方棉花对英国的出口,沙逊在印度到英国的棉花贸易上赚了大钱。
能够获取情报并及时利用情报的价值只是沙逊家族崛起的推手之一,让他能够看到大宗商品的商业机会。同样,沙逊也也充分意识到技术变革带来的机会,比如蒸汽船给全球贸易带来的巨大改变,或者电报让资讯传递变得更为迅捷,也让捕捉商机变得更加重要。随着英国的扩张,沙逊也在不断扩大自己的商业版图。1843年上海开埠之后,大卫就派二儿子进驻上海,开拓中国市场。
在这里我们需要特别强调一个历史大背景。上海是在鸦片战争结束之后《南京条约》要求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鸦片在中国的贸易合法化,许多英国商人都靠肮脏的鸦片贸易赚取了第一桶金,沙逊家族也不例外。我们对此必须要有清晰的认知。
沙逊家之所以能成为上海滩的弄潮儿,主要依靠的是不正当的鸦片贸易,以及在英国和印度经营的政商关系。不要天真地以为这些冒险家都是靠冒险挣钱的,近乎垄断且高暴利的鸦片生意才是沙逊家发达的主要原因。
1860年代之后,沙逊的二儿子在上海主要经营的生意是鸦片贸易。大儿子则在孟买与总督建立深厚联系,因为孟买的收入三分之一来自鸦片税收,总督也要问问沙逊未来十二个月鸦片的行情。犹太人做生意,善于利用情报。他们是最早使用电报传递情报的企业,上海到孟买的第一封电报就是沙逊家族拍发的关于鸦片供求关系信息的加密电报。
政商关系也非常重要。大卫的几个小儿子在伦敦开辟办公室,帮助沙逊家族打入伦敦的上流圈子。全球化初期的伦敦也是一个阶层波动剧烈,各色人等横流的社会,传统的土地贵族有土地、有爵位和地位,却缺少现金,因而至少在表面上对在全球化淘金中致富的新富们保持开放的态度。英国旧贵族迎娶美国富翁的女儿继而继承一部分新富财产就是常见的做法,比如丘吉尔的母亲就是美国来的新贵之女。沙逊这样孟买的犹太商人则是另一种,赚取第一通金之后,他们马上申请英国国籍,进而挤入英国高层的圈子,一方面给自己的家世镀金,另一方面也希望谋求商机,虽然骨子里,英国上流社会始终有一种“反犹”的情绪存在。
沙逊家花精力笼络最多的是维多利亚女王的王储——俗称Bernie的爱德华七世。有趣的是,这位爱德华七世与当今英国国王查理三世可谓难兄难弟,都因为女王高寿,几乎在王储威尔士亲王位子上望穿秋水。
爱德华七世这位做了近六十年王储的威尔士亲王生活奢华,绯闻不断,也需要大量金钱,沙逊家成了招待威尔士亲王的大金主。增加了未来国王的体面,沙逊家希望增加对王室乃至对英国政治的影响力,目的是维持暴利的鸦片贸易。
在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让沙逊家族暴富的鸦片贸易是极为不正当的。鸦片在中国贸易合法化后,沙逊家族因为几乎垄断了在印度的鸦片种植,进而垄断了对华鸦片的贸易。参与鸦片贸易让沙逊家族赚取暴利,他们却对鸦片给中国人带来的伤害不闻不问,这一点也需要谴责。罪恶的鸦片贸易是暴利行业,毛利高达三成到五成,沙逊家族在鸦片贸易中赚了1.4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的27亿美元,换算成现在的美元超过上千亿。
总结一下,沙逊家族是犹太人在全球化1.0时代伴随着英国版图扩张而扩张商业版图的代表。他们从巴格达到孟买,最后来到上海。从沙逊家族的崛起不难看出全球化1.0时代的三个特点:
1、 英国在全球不断扩张的殖民地网络和开放港口给了从事贸易的冒险家巨大的机遇
2、 犹太人的特点,精通商业、重视教育、理解资讯的价值、深度抱团,让他们更容易成为冒险家和弄潮儿
3、罪恶的鸦片贸易帮助冒险家在上海挖到了第一桶金,这一点我们特别需要谴责。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犹太家族是如何助力100年前的上海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的。
经商有成的大卫·沙逊,接着就着手培养自己的八个儿子构建基于家族血缘网络的商业大帝国。如果你读过著名犹太金融家族罗斯查尔德家族的传记,你就会知道这种基于血缘网络的犹太家族经营方式很普遍。罗斯查尔德从德国起家,却让自己的儿子分别在法国和英国建立自己的领地,靠血缘网络构建金融帝国,依靠犹太人的资讯优势在市场上时有斩获,当年罗斯查尔德家族因为早一天知道滑铁卢战役中拿破仑战败的消息,在伦敦市场上购买英国国债赚了大钱。
大卫·沙逊也是如此。他给自己的八个儿子每人优渥的薪水,分配他们到不同地方打拼,有时候还会轮岗,丰富他们的经验和阅历,但他们并不会因为血缘关系就直接成为公司的合伙人。想要接班,必须证明自己的能力。
有趣的是,大卫·沙逊看不起罗斯查尔德家族,并不喜欢被人称之为东方的罗斯查尔德,因为罗斯查尔德家族是一代暴富的犹太人,但他们自认代代相传的富人,巴格达的富裕的犹太人聚居区在沙逊移居孟买之前已经传承了八百年。
大卫·沙逊有一套自己管理的模式,他制定了一套整体培养人才的方案,从巴格达和中东东亚其他地方的犹太人群中筛选年轻人来孟买学习、成为学徒,学成之后加入沙逊家族的企业,嘉道理家好几个孩子都是从到沙逊家做学徒开始。
嘉道理家是沙逊家在伊拉克巴格达的远亲,曾经是巴格达生活优渥的商业银行家,但因为父亲早逝,家道中落,寡母决定把六个儿子都送到沙逊家在孟买开办的学徒学校,原本几个孩子就在法国犹太人开设的学校学习法文、英文等,在沙逊家族学校中如鱼得水。语言的优势在全球化1.0的商场中大有用武之地。
埃利·嘉道理是嘉道理家第五个儿子,被派到香港、后来又去了威海卫,他对沙逊家族漠视中国人苦难的态度不满,辞职单干。按照嘉道理家族的叙事,这次辞职是嘉道理家族未来发展最重要的决策。从辈分上讲,埃利是大卫的子侄辈,他创业的生意不再依赖沙逊家的鸦片业务,而是投入到当时更加新兴的产业之中——金融市场。
埃利·嘉道理在香港从哥哥借了500港币炒股起家。在二十世纪初马来西亚的橡胶热潮中,他从渣打银行借钱炒股,1910年马来西亚橡胶泡沫破裂,渣打银行要求尽快还钱。焦急之际,埃利得到了汇丰银行的资助,并且在汇丰银行的帮助下参与了马来西亚香蕉园的资产重组,转危为机,之后在上海开启了自己的更大的冒险。
埃利·嘉道理家族关注的是上海作为新兴市场涌现出来的新机会,特别是房地产的机会。埃利·嘉道理创建了香港上海大酒店公司,到了1924年已经拥有上海最豪华的三家饭店,尤其以新建成的大华饭店为最。同年建成的嘉道理私宅号称小凡尔赛的“大理石宫”,更是沪上犹太富商的瑰宝。嘉道理也开始与沙逊和哈同家族一起并称沪上犹太富商之冠。
豪华酒店和房地产开发真正推动了上海成为国际化大都市,被好莱坞认为是全球五大大都市之一。沙逊家族也把投资放在了房地产开发之上。
维克多·沙逊是沙逊家族的第三代,他出生于英国,受亲属邀请返回亚洲打理沙逊在亚洲的业务。他有政客的敏锐度,也有着商人的精明,在上世纪20年代与孟买的商人打交道的时候,他就意识到甘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潜力,意识到英国的治权摇摇欲坠,而自己的商业帝国也会遭殃,因此他决定全面退出印度市场,将清盘的1.4亿美元全部投入到上海。在他看来,上海作为“开放的国际都市”,其发展潜力优于孟买。
维克多·沙逊敏锐地观察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崛起的潜力,一方面是公共租界作为“开放的国际都市”的冒险者乐园的地位,监管少,税收低廉,有巨大的投机潜力,一度因为炒家云集,上海房价超过纽约和伦敦;另一方面中国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上海背靠庞大地中国内地市场,已经初现轻工业生产基地的面貌,面粉厂和纺纱厂不断崛起。换句话说,维克多·沙逊赌上了上海的未来。
1929年,维克多·沙逊在外滩建造的华懋酒店(后改名为和平饭店)成为外滩的地标,因为现代和奢华为世人瞩目。国民政府三十年代计划在附近建造中国银行大厦,高33层,超越和平饭店成为外滩最高的建筑。沙逊家在租界工部局七位董事席位中占据永久一席,维克多旧利用工部局市政监管的权力,以“技术”问题否决了中国银行的设计方案,确保和平饭店外滩第一楼的地位。
怎么理解一百年前的上海?当时的上海仍是开放的国际城市,是外国冒险家的乐园,与中国本土之间的联系并没有那么紧密,这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城市,一个快速致富的城市,一个可以享受奢华的城市。犹太人推动了上海作为“开放的国际大都市”。上海租界里有5万欧美人,100万华人;华界里还有200万华人。一开始,租界仍然对华人有不少的限制,但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当埃利·嘉道理和维克多·沙逊大笔投资房地产,尤其是酒店业务的时候,上海已经成为华洋共处的国际化大都市。
简单小结一下,100年前的上海成为国际化大都市,部分原因是像沙逊和嘉道理这样的家族在上海深耕的结果。与沙逊家不同,嘉道理是依靠炒股积累了第一桶金,一百多年前马拉西亚的香蕉泡沫是整个远东最大的一次金融浪潮,突显了香港和上海从初创的全球化贸易港口变成更为重要的金融中心的演变。虽然埃利·嘉道理因为汇丰银行的帮助而在金融海啸中毫发未损,但他也及时转向,看到了上海作为“开放的国际化大都市”的机会,尤其是房地产开发的机会,创建了上海最大的酒店业务,也推动了上海成为华洋共处的国际化大都市。沙逊家族的第三代维克多·沙逊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也看到了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房地产发展的机会,以及上海作为辐射中国内地轻工业生产基地的潜力,在印度和上海之间选择了上海。
从沙逊和嘉道理两个家族在上海几代人的经营,不难看出全球化大都市的发展途径:首先是作为全球商贸枢纽港口的快速成长,然后是金融的火爆,随之而来的是更多人的涌入带来的房地产的持续火爆。以此来对照改革开放后的上海复兴,贸易、金融、城镇化的次第展开的机会,不得不说历史是不断重复的。当然,企业家的冒险精神是这一历史进程中最主要的驱动力之一。
咱们再来重点说说,嘉道理家族与香港和上海的情缘。埃利·嘉道理并没有像维克多·沙逊那样全部下注上海,他反而把自己的大儿子罗兰士派到了香港,在上海和香港两地发展,并在广东发展实业。嘉道理家族在上海鼎盛的同期,罗兰在九龙建设了当时亚洲最豪华的酒店之一半岛酒店,还在九龙内地建设了自己的物业,在新界修建自己的别墅。这也是后来香港人常说的伊拉克富商的物业。
经历了日本侵华战争的掠夺之后,嘉道理家族将香港选择成为重生之地。香港作为下一个快速成长的繁华都市,吸引到了10万多南来的资本家和百万新移民,迅速从日本人占领的废墟中走出来,并在二战之后的繁荣中迅速崛起,成为取代上海的亚洲国际大都市。
在日本侵华期间,嘉道理家族被关进了集中营,埃利·嘉道理没有坚持到1945年大战胜利就去世了。而他的两个儿子在日据时期集中营中的经历让他们对未来以及对企业家的角色有了深入的思考,父亲的悲惨死亡也让他们对企业家责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虽然沙逊和嘉道理两个家族是上海滩上最著名的犹太家族,在中国赚了大钱,也为上海的成长做出了卓越贡献,但和许多前来淘金的海外家族一样,他们对中国本土并没有那么明确的认知,也没有与中国社会有真实深入的接触。两大家族都没有学习汉语,在他们的小圈子里面没有华人存在的空间。很显然,他们有着根深蒂固居高临下去俯视中国的这种姿态。对他们而言,中国和上海只是赚钱的地方。
举个例子,1930年的一年里,公共租界在街头收埋的尸体超过5000具,要么是冻死饿死街头的,要么是病死了家人没有钱收殓的。上海的贫富差距以这种极端的方式展现出来,但根本进不了沙逊和嘉道理家族的眼帘。
战争的毁灭,集中营的经历,父亲的惨死,都让嘉道理兄弟意识到除了赚钱之外,还有更重要的责任需要企业家去承担。
哥哥罗兰士考虑的如何帮助英国殖民政府重建香港,在香港推广了一个小版的“罗斯福新政”,强调政府在重建城市时扮演的角色。罗兰士参与二战之后香港治理制度的设计,强调低税收、少监管、清廉政府、法治和重商。这些政策一定程度调和了劳资关系,推动香港经济整体发展,提高了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因为这些成绩,罗兰士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被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推举加入英国上院。
弟弟贺理士在二战期间参与了上海对超过15000逃难来的犹太人的保护工作,更能体会中下层老百姓的苦难。到了香港之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帮助香港农民和南下的新移民改善生活上。当时的香港并不是现在大多数人印象当中的国际化大都市,新界广大土地拥有大量农地,而新移民不少也选择务农为生,贺理士就从为这些人提供帮助入手,推出农业试验推广农场,为农户提供小额贷款,让他们能够购买耕地,种植、养殖、并未他们修建道路,提供电力,提供种植和养殖方面的科技服务。
贺理士的利民措施卓有成效,以至于受益的当地人说:贺理士对养猪样样都懂行,除了味道不知罢了。这么说是因为贺理士认为养猪是农民致富的捷径,尤其当香港日益繁荣,人口激增,对猪肉的需求也同样激增。但贺理士是犹太人,不吃猪肉。
嘉道理家族串联起上海和香港两座城市,演绎出一段传奇。改革开放之后,2004年嘉道理家族重返上海,在寸土寸金的外滩修建了全新的半岛酒店,2009年建成,体现了一种保持百年商业纽带关系的力量。
简单小结一下,从嘉道理家族二战前后的改变,不难看出全球化的变迁。二战前与二战之后的全球化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商品的全球化,市场开放的全球化,殖民网络的全球化;后者是发展的全球化,制造的全球化,财富创造的全球化。这就需要企业家完成转型。冒险淘金时代的沙逊家族第一桶金依靠邪恶的鸦片贸易。二战前的沙逊和嘉道理家族参与棉花、面粉、土地开发等项目,代表的仍然是一种重商主义时代的全球化,带来的仍然是上海这样孤岛城市的发展,并不理会城乡差别和贫富差距,也不会站在更广阔中国市场的视角去思考整体的经济发展。
嘉道理家族二战之后在香港的经营体现了一种全新的全球化趋势和企业家责任的转型,这种全球化看重整体经济的发展,看重城乡的结合,也推动企业家肩负起更多社会责任。
《最后的上海王》(Last Kings of Shanghai)不仅讲述了沙逊和嘉道理两个家族跨越百年的故事,也从侧面帮助我们理解上海的发展和上海文化的形成。接下来我们就重点说说百年前的犹太家族是如何促进“海派文化”的形成的。
海派文化具有鲜明的特点:新潮、充满活力、十分开放、大都市气息,全新拥抱新科技。
犹太人在塑造海派文化上扮演关键的角色。犹太人的敏锐度体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他们对新科技特别敏感,能看到蒸汽货轮推动全球贸易大发展的机遇,也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首先利用电报沟通市场资讯赚钱。作为全球贸易枢纽港口和快速发展的大都市,上海可以与伦敦、纽约、芝加哥几乎在同一时间享受到最新的科技,比如电灯、电话、自来水、下水道、有轨电车和摩天大楼也就不为奇怪了。
其次,他们拥有在新市场中探索的冒险精神。现在很多人比较上海和孟买,对孟买有这样那样看不上,也有人把上海戏称为中国的孟买。但是要记住,在1860年从孟买的视角去看上海,当地的英国商人会有百般看不上,但犹太商人有敏锐的嗅觉和前瞻性,能感受到上海之于庞大中国市场的区位优势,以及上海开埠之后巨大的发展潜力。更重要的是这种冒险精神需要他们躬身入局,不断打破自己的舒适圈。1860年孟买的上流社会舒适度远远高于刚刚开埠的上海,但必须有行动力才能真正成为淘金人。
最后,犹太商人的冒险精神和企业家精神也感染到了随后崛起的中国民族资本家。100年前,中国100多万家工厂中,有50万创建在上海。在与洋行合作过程中,中方伙伴最主要的收益是企业家精神,商业创业的精神。是这些受到感染的民族资本家真正开始利用起中国巨大的劳动力市场,棉纺行业就是一个例子。
从犹太人在上海的成功经历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圈子与破圈的重要性,依赖基于信任的稳固圈子发展,融入当地社交圈,同时又敢于在当地破圈,这样的经验对于中国企业未来出海也有着很强的借鉴作用。
犹太人是一个小圈子,来自巴格达的沙逊和嘉道理家族更是如此,他们相互提携,有信任关系,且信息共享,他们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身份构建了一种认同感,也构建了一种在全球化中能够有所创建有所发展的行为准则。
商场上光有基于信任的小圈子还不够,还得在更大的码头上去混圈子,而沙逊和嘉道理两个家族都成为了更广阔社交圈的核心。上海滩沙逊家华懋饭店(后来的和平酒店)的舞会和嘉道理家大理石宫的宴席就构建了这种更广阔的社交圈。想要成为新兴市场的弄潮儿,能进入什么圈子,认识什么人,从他们那里又能得到什么样的帮助,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沙逊家族选择回伦敦上流社会混圈子,甚至与王室打得火热,也是因为当时政商关系对做生意的重要性。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企业家也需要破圈,承担更为重要的社会责任。香港战后的发展,嘉道理兄弟扮演重要角色。他们很清晰地认识到,一个只是以洋人为主角的洋场不可能持续发展,更为包容的经济发展需要让所有人都能够参与经济发展的机会,同时不断减少贫富差距。
作为传承几代人的商业家族,保持商业的纽带也至关重要。嘉道理家族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重返上海,在寸土寸金的外滩修建了全新的半岛酒店,就是因为他们在中国香港的持续耕耘。
最后简单小结一下。《最后的上海王》这本书提供了一个从他者的角度审视上海作为远东最重要的商业城市成长的历史,在记述沙逊和嘉道理两个家族百年历史的过程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国自1843年以来经济发展的历史,以及上海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一过程帮助上海形成了新潮、活力、开放、包容的独特文化魅力。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1、犹太商人的崛起,不能简单归因于他们的智慧和勤奋,而是要看到英国主导的全球化1.0时代殖民地网络扩张给他们带来的机遇。
2、嘉道理家族在香港的发展,不是简单复制战前在上海的模式,而是顺应战后全球化趋势的转变,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3、沙逊和嘉道理两个家族百年历史的过程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国自1843年以来经济发展的历史,以及上海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一过程帮助上海形成了新潮、活力、开放、包容的独特文化魅力。
4、犹太商人的成功,不能只归功于他们内部团结的小圈子,而在于他们善于融入当地社交圈,建立广泛的人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