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资本》 裴鹏程解读
《青铜资本》| 裴鹏程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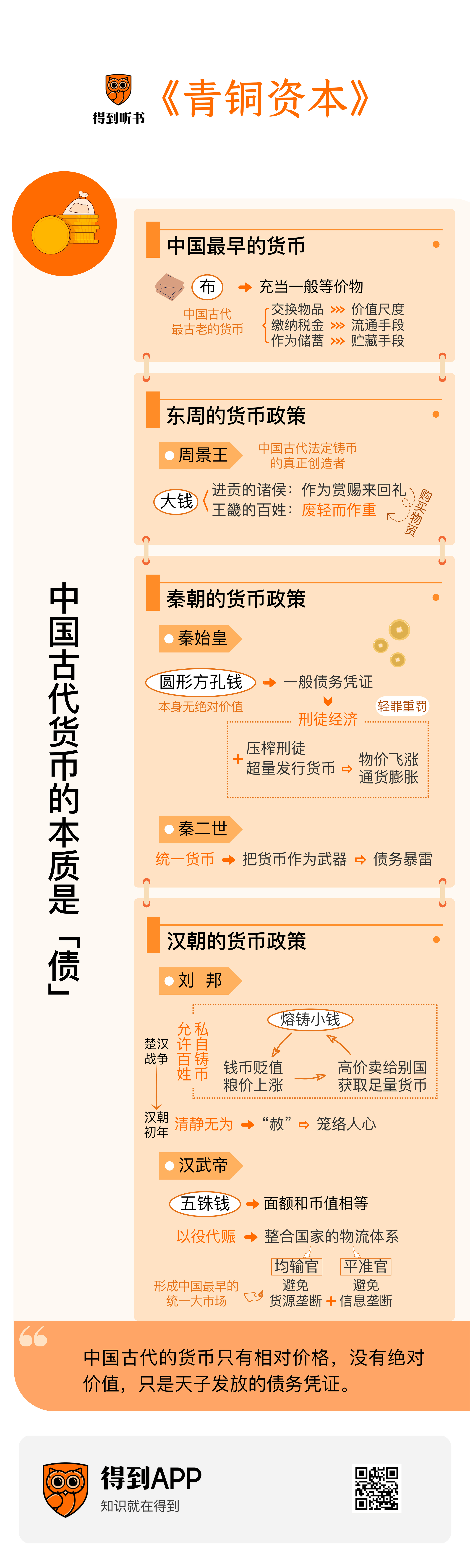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介绍的是《青铜资本》,这本书要为我们破解一个谜题。
马克思说过一句我们耳熟能详的话:“货币天然是金银”。货币要流通,而金银的优点很突出,外形美观,储量稀有,不容易生锈,切割起来很方便,是理想的货币。既然“货币天然是金银”,为什么中国最早的金属铸币不是金银币,而是铜币呢?为什么白银货币化直到明朝中后期才完成?
2017年,德国经济学家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翻译到国内,迅速走红,这本书回应了,为什么白银在明代大量涌入中国?但没有回答问题的另一半,为什么中国人执着地使用铜钱两千多年?而且,尽管白银在明代成了法定货币金属,但明清政府都没有铸造银币,广大民众用的还是铜钱,民间流通的白银,都是称重的散碎银块儿,这个状态一直持续到了民国时期。
《青铜资本》这本书,从题目上看隐隐约约是要呼应《白银资本》。实际内容也确实是这样,它要破解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谜题,为什么中国古代铸币是青铜?中国古代的青铜铸币,和金银铸币有什么不一样呢?
破解这个谜题的,是本书作者,历史研究者刘三解老师,“解”是解读、解密的“解”字。他的作品数量不多,但反响都很好。他的书有两个特点,一是考据非常扎实,每本书都不下四五百页,除了传世文献和学者研究,他还会直接使用很多出土材料,以及钱币学、统计学研究成果,在学界内评价很高。第二个特点是,视角切入很巧妙,比如他的成名作《秦砖:大秦帝国兴亡启示录》以及姊妹篇《汉瓦:西汉王朝洪业启示录》,听得出来是以秦砖和汉瓦这两种文物“四两拨千斤”,然后不断抽丝剥茧,让读者在兴致盎然的阅读中突然一激灵,哦,原来秦汉政治经济居然有这样的一面。
就比如这本《青铜资本》,它有一条线索是青铜铸币的诞生和演化。作者用了大量篇幅介绍周代、战国、秦国和汉初的历史,当你沉浸在周景王穷疯了变着法子要钱、商鞅变法后的秦国用没价值的货币竟然统一了天下、秦始皇和秦二世父子俩花式赖账、刘邦用流氓经济手段战胜项羽、汉武帝专挑大灾之年发动战争时,当你沉浸在书中,全书竟然在汉武帝的时候戛然而止了。因为,作者认为,正是从东周到汉武帝,这四百年左右的历史已经奠定了中国古代两千年的经济格局。
所以,接下来我们了解这四百年的货币史,颇有点正本清源的感觉。
先来想一下,中国最早的货币是什么样的呢?
要当货币,这类物资一定不能太多,得稀有。不过太少也不行,那就没法流通了。
中国一直以来都缺少黄金,尤其是在周代,周王室居住在陕西关中,黄金出产在几千里以外的地方。在周天子眼里,黄金跟珍珠、美玉没什么区别,都是奢侈品,是地位的象征。就像今天的我们不会拿着LV皮包换油条一样,在周代,过于稀有的黄金也承担不了流通手段、价值尺度的功能,它当不了货币。
中国古代最古老的货币,说起来你可能不太会相信,其实是作为纺织品的布。《诗经·氓》这篇当中有一句“氓之蚩蚩,抱布贸丝”,说一个老实忠厚的人,抱着布匹来换丝织品。
凭什么说这里的“布”是货币,而不是故事主人公在以物易物呢?
在周代的王畿,也就是周天子直接管理控制的区域,布是可以充当一般等价物的,不仅能换东西,能缴税,还能当财富存起来,你看这就体现了货币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的功能。而且,“布”这种货币,几乎所有的先秦文献中像《诗经》《左传》《周礼》《韩非子》,都记载了,甚至布不再作为货币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名称、货币单位仍然叫“布”。
不过,布作为货币并没有持续下去,也没有推广开来,甚至我们今天都忘记了布竟然还当过货币。青铜铸币是怎么取代“布”,成为货币的呢?
我们要说到两件事,一个是水上物流升级,还有一个是周王室变穷了。
我们现在经常用到一个词“沟通”,它其实反映了春秋后期,水上物流升级的历史。“沟通”这个词出自《左传·哀公九年》,讲吴王夫差战胜越王后飘了,觉得自己强大到可以当中原霸主,于是他打算从今天江苏南部挥师北上。为了提高行军和运粮速度,他做了一件事,把长江和淮河下游地区沟通起来。这就是“沟通”的故事。
沟通大江大河的,不只东南的吴王在干,别人也在干。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也是想要北上角逐,在长江中游开凿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条运河。
当然吴王夫差和楚庄王开凿运河是为了打仗,但副作用是,水网陆陆续续连接起来,贸易变多了,财富也增加了,这就会间接影响到周代的货币。
原本在西周时期,周天子住在陕西关中,他直接管理下的“王畿”地区,贸易活动并不多。这个时候,前面说的“布”就是本地不错的货币,因为人们生活离不开布,家家户户都可以织布,而且几乎没有对外联系,不用担心,今天本地来了一批外地的便宜布匹,会扰乱物价。但到东周,各地联系紧密了,如果还是把布当作货币,它的购买力就会大幅波动,周天子必须选择一种新的货币。
这就要说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位主角,周景王。
他曾为我们贡献了一个成语,“数典忘祖”。这个成语就跟青铜铸币的诞生有关系。
原本周天子的王畿在陕西关中,由于西方戎人入侵,周王室被迫东迁,从富饶开阔的关中迁到了狭窄的洛阳一带。当初,周王室靠着富饶的关中土地活得很滋润,诸侯国偶尔进贡一些土特产,算是锦上添花。但是迁到洛阳后,没有那么多土地和百姓供养自己了,于是周天子打算问诸侯要。
一次,周景王问到了晋国头上,我们把《左传》相关记载大致转述一下。周景王质问晋国使者:各诸侯国都为我准备了器物,怎么你们晋国就没有呢?晋国使者编瞎话搪塞:那是因为几百年前,晋国受封的时候,周天子没有赏赐礼物,而且最近晋国忙着帮周天子对付戎狄,所以没有进贡。周景王立刻找来典籍,列数当初周王室赐给晋的土地器物,反驳晋国使者,你这分明是“数典而忘其祖”。
第一次听到“数典忘祖”的故事,我们未必会觉得晋国失礼,反倒会觉得周景王蹭吃蹭喝,有点丢人。继续了解周景王,我们对他的认识会更深刻一些。
史料记载,周景王临终前几年,忙着铸造一种叫“大钱”的东西。这是一种青铜钱币。诸侯进贡,天子需要回礼,在西周时期,周天子家大业大,进贡和赏赐是对等的。东周时期,周天子过得实在困难,只想从发迹的诸侯身上揩油。但程序得走嘛,所以诸侯进贡后,周天子就把青铜大钱作为赏赐来回礼。
当然,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周天子是“一视同仁”的。除了富起来的诸侯们,周天子也要关照一下王畿本地纳税的民众。虽然洛阳的土地和人口比不上当初的关中,但蚂蚱再小也是肉。所以,周景王下诏“废轻而作重”,这里的“轻”指的是布币,“重”指的是青铜铸币,也就是告诉王畿的百姓们,传统得变一变了,麻布我就不再要了,以后王畿都流通青铜铸造的“大钱”。
如果只是周景王在自嗨,青铜铸币只能在王畿流通,在其他诸侯国地界上未必能推行得开。我们不确定周景王是不是真那么深谋远虑,总之事实是,“大钱”慢慢成了真正的货币。怎么回事呢?
诸侯们进贡了物品,却换到青铜大钱,他们也嫌弃,但直接扔掉,就赔了,不如原汤化原食,就在周天子直接管辖的王畿购买物资。结果是,这反而促进了大钱的流通。
咱也不用替王畿的贵族和百姓担心,亏都让他们吃了。因为交通发达了,王畿的居民有机会带着大钱在外地换取物品,如此一来,大钱更成为实实在在的货币了。
以后,当我们再听到周景王这个名称,除了“数典忘祖”的成语,别忘了,他很可能还是中国古代法定铸币的真正创造者。
各诸侯国也许并不愿意接纳周天子的大钱,但这给他们带来启发,我是不是也可以在我本地铸造金属货币呢?于是青铜铸币登上了历史舞台。
刚才提到“青铜铸币”的时候,不知道你的脑海里会浮现什么样的画面?
你想到的很可能是我们在书中插图、在博物馆看到的圆形方孔钱,毕竟这种“天圆地方”的货币样式,我们用了两千多年。其实,最初的铸币五花八门,有的像一把刀,有的像个小铲子,最终是秦朝统一了货币,在全国推行圆形方孔钱。
而秦朝统一货币,前提是统一了六国,而秦能统一六国,除了秦国成功实施变法外,青铜铸币本身也发挥了关键作用。
湖北省博物馆有一套镇馆之宝,叫《睡虎地秦简》,记录了战国晚期的秦国法律规定,是我国所有法律从业者心中最珍贵文物之一。其中一条规定,很奇怪:“贾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择行钱、布。”翻译过来就是,在秦国的市场交易中,无论你是买卖人还是当官的,都不允许拒收、挑选秦国的货币。
不允许民众拒收秦国货币可以理解,国家统一推行嘛。不允许挑选是什么意思?我卖东西,顾客拿来两枚铜钱,一枚是完整的,一枚有缺损不足值,我当然要选择完好的那一枚。不仅我不吃亏,也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维护市场稳定,怎么秦国政府还反对呢?
作者告诉我们,是劣币还是良币,秦国统治者根本不在乎。
因为秦国的货币跟我们今天的货币有本质不同。对现代人来说,货币天然是金银,金银本身是有价值的,所以现代货币也是有价值的。但在秦朝,货币是统治者决定的,它本身没有绝对价值。秦国百姓手里一枚完整的钱币和一枚缺损的钱币,在秦王看来都是一样的。
作者有个关键论点,会让我们眼前一亮。其实,秦国货币是“一般债务凭证”。秦王发行货币,就是在向社会借债。秦王通过货币,向民众借来物资充实国库,把民众雇来充当士兵,以此发动战争,推动秦国扩张。而秦国人拿到的货币,就是秦王借钱的债务凭证。
既然是凭证,就像我借你钱,写了借据。过几年这个借据皱了一点,甚至撕了一角,都不影响它记录着我曾向你借钱的事实。所以秦国货币有所损伤并不妨碍它“一般债务凭证”的功能,秦王自然不允许民众挑选拒收货币。
这就有个问题,既然秦国发行货币是借债,借债得还,秦王怎么还钱呢?
秦国留给后人一个突出标签,就是轻罪重刑。犯小错受重罚,这是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基本国策,而这正是秦王还钱的策略。
秦国刑法的严酷程度超乎常人的想象,最著名的就是“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种地的田亩宽度超过六尺就处罚,把灰烬丢弃在道路上要受刑。结果是,民众动不动就会触犯刑法,沦为刑徒。但对秦国来说,刑徒正好能缓解经济危机。因为刑徒跟自由劳动力不一样,秦王可以随意驱使他们干活,就像韭菜一样,不断收割。
秦国有当时最残酷的刑法,制造了当时最多的刑徒。这个规模非常庞大,甚至到了秦朝末期,天下揭竿而起,吴广带领起义军向咸阳进发,当时的秦国四面受敌,眼看着起义军直捣咸阳,章邯只是率领了在骊山修建秦始皇陵的刑徒就击溃了起义军,仅这一支刑徒军队就有70万人。
你看,我们说商鞅变法意义重大,在众多意义中,最实际的一个结果是,轻罪重罚创造了源源不断的刑徒,这些刑徒是秦王手中免费的劳作大军,他们能为秦国发动对外战争提供财政支持,这就是秦国非常奇特的“刑徒经济” 。
但这种经济模式是无法持续的,秦国得天下归功于“刑徒经济”,失天下同样也是因为“刑徒经济”。
下面,咱们聊聊秦始皇和秦二世父子俩“赖账”,结果亡国的事情。
商鞅变法是在公元前356年,秦始皇统一全国是在公元前221年,也就是说,刑徒经济大概支撑了秦国一百多年的快速扩张。
到秦始皇手里,“刑徒经济”支撑的秦国国库已经捉襟见肘了,因为开支变大了。粗算一下,为了鼓励士兵英勇杀敌,秦国推出“军功爵制”,作战有功就有相应赏赐,这是第一笔巨大开支。为了能维持刑徒经济的稳定运转,秦王要养一支忠于自己的官僚队伍,管理成本是第二笔巨额开支。统一全国是从未有过的,即使兼并了六国,秦始皇还要保持足够军队,防范六国民众造反,这是第三笔开支。还有,著名的《阿房宫赋》开篇一句是“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秦始皇热衷于移山填海,建设大型工程,毕竟他做成了三皇五帝都做不到的事情,放纵一下怎么了,但这无疑是让秦国经济雪上加霜的第四笔开支。
钱从哪儿来呢?
《阿房宫赋》还有一句“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朝歌夜弦,为秦宫人”,一句话概括,就是把六国的人口转移到秦国的统治核心区。你可能说,这讲的是上层贵族。下层更是如此,有关秦国历史的记叙中,有很多人口流动的桥段,比如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时,他俩的身份就是负责押送劳工的“屯长”。刘邦担任沛县的亭长,类似于派出所所长,他任务之一就把本地的劳工送到骊山给秦始皇修建陵墓。
过去看这些内容,我们会说这是秦始皇个人的暴政,现在你会知道,秦始皇只不过是顺着一百前年变法后的惯性,维持“刑徒经济”运转。
秦始皇一方面压榨刑徒,同时也在继续超量发行秦国货币,说得客气点就是向秦国百姓借更多的钱。但滥发货币,一定会造成物价飞涨。
看一个案例,为了避免民众不用秦国货币,秦国法律规定了粮食的价格,前面提到的《睡虎地秦简》就记录了官方米价。《睡虎地秦简》是秦国一位从事法律行业的小官记录的,他在秦始皇三十年过世时下葬,竹简是陪葬品。也就是说,竹简记录的是,秦始皇三十年这年的米价,是一石三十钱。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录了第二年发生的一件事。这年,闲不住的秦始皇带着四个武士微服出行离开了都城,结果路上被盗贼围攻,当然盗贼这个事情不重要,我们要说的是司马迁在这里交代了一个细节,当时米价上涨到了一石一千六百钱。也就是说不超过两年时间,米价上涨了50多倍,相应地秦国民众手里的也贬值了50多倍。价格时有波动,但不到两年贬值五十倍,这样的通货膨胀,实在是吓人。
问题来了,秦国的“刑徒经济”运转一百多年都没事,秦始皇统一全国刚开始也没事,为什么到中后期出现这么严重的通货膨胀呢?
因为早期的秦国在扩张中,会不断占领更多耕地、俘获更多人口、夺取更多财宝,消化秦国内部的债务问题。但这种以战养战,说白了是拆东墙补西墙。当六国统一,秦国没有新的土地可征,财政窟窿就无处填补了。
当然秦始皇倒没有太多担心这个事情,一是因为他在历史惯性中,或许并不能觉察到什么,二是当经济危机爆发后,没过几年他就撒手人寰了。接手的,是后人口中所谓阴谋夺权的篡位小人、残害手足的不义之徒、二世而亡的无能之辈,每当后人咒骂昏君就一定会被拖出来反复鞭尸的,秦二世。
秦二世这么差,但统一货币这个我们眼中的千秋功业,恰恰是秦二世这位昏君干的,而且是一上台就立刻推进。统一货币,这可是跟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一同被写入教科书的必背知识点。
但接着前面的话题,你再琢磨秦二世统一货币这个事情,估计就得皱皱眉头了。秦始皇撒手人寰,秦二世接过来的是一个财政窟窿如黑洞般的王朝,实在是没法堵了,因为“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几世几年,剽掠其人,倚叠如山”,六国的各种资源早就被亲爱的父皇拿去补窟窿了。
现在怎么办?秦二世决定把货币当作武器。他要赖账了!
秦国货币最初在本国流行,统一六国后,各国原本都有自己的货币,货币一度混乱。不过这倒不是个严重的问题。因为统一王朝的疆域过于辽阔,而中国古人以种地为生,哪怕距今一百年前,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不会离开自己的村子,所以赵国故地继续用赵国钱币,秦国本土还是用秦国货币,倒也不影响。
但这次,秦二世统一货币了,原本收购商贩物资,用金银珠宝这些贵重物品置换,现在发钱;原本付给劳工的报酬,也是口粮或贵金属,现在也发钱。秦国的经济大厦崩塌了。
受伤害最严重的,当然是给秦二世干活最多、使用钱币频率最高的首都民众。书中有句话,读来令人唏嘘:在这场大崩溃中,首当其冲的是拱卫帝都咸阳的“故地”秦民,曾经以胜利者的姿态肆意羞辱被征服者的他们,仅仅在天下一统11年后,竟然挨饿了。
秦朝快速灭亡,看似亡于苛政,其实亡于秦二世的“债务暴雷”。
公元前207年秦朝二世而亡,接下来是汉朝,不过汉朝再次统一全国是五年后的公元前202年。这几年里,角力的是刘邦和项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三对主角。
刚开始,项羽的实力最强大,因此他有能力分封各路诸侯。但过去我一直有个疑惑,项羽把自己封在了江淮地区,他提防着刘邦反而把刘邦封在了秦国故地。稍稍熟悉地理和军事知识的朋友就会觉得欠妥,秦国故地有很多天险,而项羽的地盘多是平原丘陵,真要打起来是无险可守的,项羽身经百战,这点常识都没有吗?
《青铜资本》给出了答案,经济因素会决定一个政权的存续,而交通对于经济发展很重要。我们看项羽的西楚国,水网密布、耕地连绵,他占尽了当年楚国和魏国的黄金区域。再看秦国故地重山叠嶂,往好了说这是易守难攻,往坏了说就是缺少了经济发展潜力,别忘了,秦国故都曾被一把火烧光了。项羽毕竟经历了秦国统一和灭亡的全过程,他的取舍是非常理智的。
既然西楚国这么富庶,刘邦的汉国那么贫瘠,为什么结果是“汉兵盛食多,项王兵罢食绝”呢?物流发达、资源丰富的项羽一方竟然完败?
这在于刘邦发动了货币战,他的具体策略是,允许百姓私自铸币。
听起来这又是一个自掘坟墓的想法,秦二世榨取百姓财富好歹还是把铸币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现在刘邦让百姓自己造钱,流通的货币如歪瓜裂枣,劣币是一定会驱逐良币的,这对刘邦有什么好处呢?
对于一个处于和平时期的统一王朝来说,允许百姓私自铸币是不能碰的雷区,但在列国竞争阶段,是一种“我不好你也别想好”的拖你下水策略。
刘邦是这么干的,他下令,在他的受封地域里,把一枚标准的“八铢半两钱”熔化后,铸成8枚小钱,但名义还是当八铢半两用,1个变8个,这就是7倍暴利。钱不值钱了,商品价格,尤其是粮价就会暴涨,其他诸侯国的商人得知刘邦的汉国物价高,商品就会涌入,尤其是最为富庶的西楚国,各类物资也会流向汉国。
我们看楚汉相争,刘邦的帮手越来越多,而项羽越来越孤立。过去从人性角度解释,刘邦老谋深算,懂得分享利益广交朋友;项羽吝啬猜忌,结果失道寡助。
成年人世界里,朋友多,一定是因为你能给很多人带来利益。刚才讲刘邦发动货币战争,铸造劣质的钱,他的粮食变多了,其实,除项羽外其他诸侯王在刘邦的地界也能获益不少。比如各诸侯王可以把本国黄金珠宝带到汉国售卖,假设一串珠宝一千钱,带到汉国卖就可以坐地起价,比如卖到一万钱。
要注意,咱们现在是以上帝视角聊这个话题,所以你知道刘邦铸造的劣质货币与标准货币的比值大致是8:1。两千多年前,交通依然不便,能够往返不同经济区的,只有诸侯王这样的贵族。他们可以靠着信息差,把自家的金库装得满满的。结果,这些人吃刘邦的嘴软,自然愿意和刘邦往来,这就是所谓的“得道多助”。
你看,在货币战中,刘邦不断降低自己的下限,导致财富像水一样,从最富庶,标准最高的西楚流向这里,因此短短两年多时间“汉兵盛食多,项王兵罢食绝”,项羽败了。
当然,在这场货币战争中受伤的,除了项羽,还有广大普通民众。如果仅从经济行为的结果看,刘邦和当初的秦二世或许并没有那么大的区别。
你可能会说,刘邦和秦二世还是大不相同的,秦国当初实行的是“刑徒经济”,这刘邦就没做。但事实上,刘邦在基本统一天下后立刻就重启了刑徒生产线,原因不难想到,因为他通过发行劣质货币打败了项羽,在他统一天下后,社会流通的货币十分混乱,前面说了,这对于和平时期的统一王朝来说,是十分糟糕的,刘邦当初种下的种子,结出了恶果。
于是,刘邦汉承秦制,打起了奴隶的主意,只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这是因为刘邦做得很巧,他下诏,明确要求释放一部分奴婢,给人留下不同于秦代的宽和形象。同时,刘邦瞄准了另一群不被关注的人,那些没有申报户籍的人。他下令,要求指令下达县一级后,没申报户籍的人如果三十天内还没履行申报义务,就要被剃去鬓发胡须,罚为官家奴隶。看起来这是刘邦在推动户籍管理,但问题就出在期限上了,三十天,在信息传达异常缓慢的古代,过于短了。
如果刘邦真的重启了刑徒经济发动机,汉朝或许会成为另一个秦朝。幸好,这一切没有发生。
原因是一个字“赦”,大赦天下的“赦”,让罪犯或奴隶回归自由身。“赦”是一种笼络人心的方式,比如攻占敌人的城池,可以赦罪人;立太子,可以赦罪人;尊长过世,皇帝也可以大赦天下。其实,“赦”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是,经过秦末战争、楚汉战争,社会上的人口实在太少了,运转不起来了。所以,刘邦在位期间各种“赦”达10次,之后汉惠帝继位,在位不到七年驾崩,吕后临朝称制,母子执政15年间“赦天下”5次。
刑徒经济是需要大量罪犯和奴隶的,本来常年战争打下来,刑徒就不多了,这一次次大赦,更是让“刑徒经济”无法重现。
汉朝同秦朝一样,疆域辽阔,国家规模相差不多,没有刑徒,怎么行呢?
从汉惠帝、吕后母子俩开始,汉朝接受了秦朝的教训,转而实行“清静无为”的政策,不再利用国家强大的组织力反复征用民力,人们受到的干扰减少了。许多被赦免的劳动力重新回到社会。民众有了更多生产和生活自由,所以汉代国家规模跟秦朝差不多,但费用支出不多,不用养那么多军队、那么多官僚,财富慢慢滋长,“刑徒经济”便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还有一个深层次问题没有解决,这就是从东周的周景王、商鞅后的历代秦王、刘邦早期曾经使用过的铸币问题。尤其是,汉代休养生息,的确社会财富在增加,但地方铸币甚至私人铸币的行为泛滥起来了。这个问题不解决,经济崩溃还会重演。
我们要迎来今天的最后一位主角,汉武帝。一般来说,讲完汉初休养生息,再提到汉武帝的时候,就会说他四处征战,掏空国库了。
没错,但我们要讲到一个关键细节,这就是汉武帝总在灾荒之年征伐匈奴。
“武帝元光六年夏,大旱……四将军征匈奴”“元朔五年春,大旱,刘将军众十余万征匈奴”,几乎所有的征匈奴的时间,国家都发生旱灾或水灾。这听起来很反常,大灾之年正是用钱的时候,况且社会也会不稳定,为什么还要对外大动刀兵呢?
其实汉武帝的军事行动,也是一种经济行为,他有个雄心勃勃的计划。
发生灾荒,必然产生大量流民,如果像上古典籍里写的那样,国家开放仓库赈济灾民,国家是吃不消的;如果像秦国那样动不动就把流民变成奴隶,押往边境戍边做苦工,组织难度太大了,更费钱。
汉武帝的策略用金融术语叫“转移支付”。某个地方发生灾荒,受灾百姓可以在当地服劳役,比如为国家开荒种田,创造经济价值。作为交换,政府会出面安置发送赈灾钱粮,这就是“以役代赈”。而创造的财富,汉武帝就可以拿去打仗了。
请注意,这个行为背后汉武帝在下一盘大棋。回顾前面讲的,周景王发行大钱来敛财、秦二世统一货币补窟窿、刘邦铸造劣质货币冲击西楚的经济,都是因为当时全国的市场是割裂的,存在巨大信息差。物资方面,不能根据市场需要流转,货币方面,手里的钱到底值多少,只有少数人有数。于是苦了广大百姓,富了像周景王、秦二世、刘邦这些少数统治者。但结果是,市场会崩溃,然后统治崩盘。
而汉武帝这种“以役代赈”的背后,是他在整合国家的物流体系。这个体系里有两个重要角色,一个是均输官,他们在基层工作,负责采购各地物产,输送到都城长安,或洛阳这样的大城市,这就避免了货源垄断。而在长安,汉武帝设置了平准官,平准就是“公平准确”,他的职责是统计各地的物价信息,这就避免了信息垄断。打破货源垄断、物流垄断、信息垄断,全国各个独立经济区域终于被连缀起来。中国最早的统一大市场形成了。
这时,青铜铸币的流通,这个让统治者头疼的难题就可以解决了。周景王的大钱被弃用,是因为不足值;秦国铸币被弃用,是因为秦国缺少稳定的金融支撑。汉武帝最终推出五铢钱,面额和币值相等,都是五铢。靠着全国统一大市场,五铢钱一直使用到唐初,直到著名的“开元通宝”的出现。后来尽管开元通宝替代了五铢钱,但圆形方孔的样式、国家依靠大市场统一发行的原则,一直被延续了下去。
本书的故事,到此结束。
回到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问题。
为什么中国古人选择了铜,没有选择金呢?既然选择了铜钱,为什么我们依然能看到金银流通呢?
作者给我们的答案是这样的,西方和中国古代的货币思想不一样。西方主流的货币理念源于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公平交换,所以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本身必须得有价值,这一点是根本。但对中国古人来说,货币是什么,那是天子说了算的事情,也就是王权决定货币。货币只有相对价格,没有绝对价值,只是国家发放的债务凭证。底层逻辑不同,导致西方选择了金银贵金属,而中国古代选择了青铜。
不过,黄金白银是有实际价值的,这一点所有人都清楚。其实,青铜资本是中国古代货币史的明线,背后还有一条暗线。铜钱一直都在下层民众间流通,它主导着各地域内部的流通,它的本质是国家发放的债;而金银除了在上层贵族间的流通外,它还主导着地域间的大额流通。这种双线并行的情况,直到明清时期,美洲白银大量涌入中国,才逐渐发生变化。
好,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
秦国货币是“一般债务凭证”。秦王发行货币,是在向社会借债,以此发动战争,推动秦国扩张。
-
中国古代的铜钱主要在下层民众间流通,它主导着各地域内部的流通;金银主要在上层贵族间流通,同时它还主导着地域间的大额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