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与帝国》 王朝解读
《茶叶与帝国》| 王朝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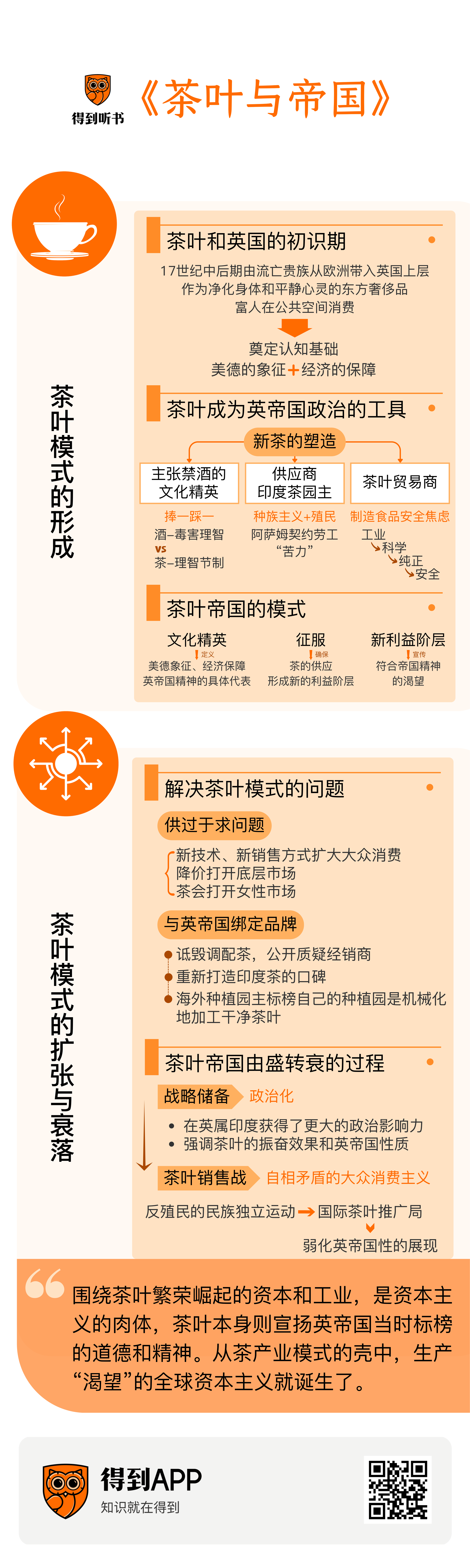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介绍的是《茶叶与帝国》,副标题是“口味如何塑造现代世界”。
你可能在社交网络上看过一个印度面孔用粤语大声宣布:“三点几了,饮茶先!”意思是“三点多了,先喝茶!”听了今天的这本书,你会发现这个略显滑稽的视频,恰好浓缩了茶叶与帝国的复杂历史。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慢慢跟你展开:这个人叫哥迪普·辛格,是在马来西亚出生的印度裔码头工人,他的祖先是被英国人带到马六甲海峡的苦力工人,他奶茶里的茶叶也很有可能是来自印度的红茶。至于三点喝茶,则是源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劳工习惯:劳累的工人下午歇一会儿,吃点高热量食品补充精力,狠狠喝几大杯振奋精神的热红茶。很奇怪吧?中国人看来是镇静放松的茶,在那个时代的英国人看来,竟然是一种兴奋剂。
我们知道,英国人酷爱喝茶,以至于英语里有“我的一杯茶”的说法来形容对某样事物的喜爱。我们也知道,英国人普遍爱喝的是红茶,特别是大吉岭、锡兰、阿萨姆等等南亚地区出产的茶叶,还喜欢往茶里加奶、加糖。那你有没有想过,英国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么喜欢喝茶的?其实,在英国最开始引入茶叶的时候,人们并没有一下就被这种来自东方的神奇树叶给迷住。那些耳熟能详的英国习俗,都是后来在茶叶逐渐成为英帝国必需品的过程中,才慢慢养成的。茶要成为一种国民饮料,除了老生常谈的物质供应,精神的需求也不可或缺。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在精神上形成对茶叶的普遍积极认知,就不会产生需求,物质上的茶叶供应也就可有可无。
这本《茶叶与帝国》要告诉你,茶可不只是提神醒脑的健康饮料,它还是一种模式。这种模式种植的不是茶叶,而是“渴望”,它是我们现代商品营销的鼻祖级模式。今天我要讲的不是茶叶产业发展史记,而是茶叶如何联系起大英帝国和全球的各个领域;也不是单纯的商品交易,而是塑造现代消费社会的力量。
茶叶的产业化历程和帝国主义的发展,的确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种利用帝国的权力和资源进行广告和政治游说的商品。得到听书有一本《棉花帝国》,也是用物品的全球流动展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的著作。它就描述了棉花通过“战争资本主义”打开贸易渠道和争夺原料产地来扩大产业,茶叶和棉花在这一角度上很类似。但茶叶与棉花不同,英帝国主义还用茶叶象征自己高人一等,这样就可以从认知上先开始建立不平等秩序,然后借此倾销产品。茶叶产业形成独立的利益团体,反过来利用英帝国的权力征服了更多人的味蕾。要知道,想讲清楚这些交织的故事,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本书作者埃里卡·拉帕波特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历史学教授,为了这本书花了十数年,寻访了八个国家的无数档案馆,上到大英博物馆,下到企业私有档案,终于整理出茶叶帝国的多面历史。
那么接下来,我就分两部分为你介绍本书。我会先讲讲为什么茶叶从一杯饮料被发明成为一种模式。这里面有那个年代的食品安全焦虑,还有“捧一踩一”的跨国商战,最终茶超越了社会阶层和种族差异,成为庞大殖民帝国的文化纽带。而第二部分,我们会看到这种模式怎么借着英帝国的力量扩散到全球,又因为帝国主义精神结构的内在矛盾逐渐衰落,茶和英国都让位给了新的饮料和新的帝国。
好,我们先来看看英国和茶叶的故事是从哪开始的。
你可能听说过罗伊·莫克塞姆的《茶:嗜好,开拓与帝国》,莫克塞姆自己就有在英国非洲殖民地种茶的经验,很熟悉英国的茶叶产业。莫克塞姆对英国人如何在19世纪从中国清王朝夺得了茶叶的贸易主导权做了回顾,我们的听书解读为他总结,叫“嗜好产生商机,开拓成就帝国”。但是这本书没有解决一个第一动力的问题——英国人的嗜好是怎么产生的?
奇怪的是,英国人在17世纪后期,也就是清朝初年才最早接触到茶叶,而且既不是在英国也不是在中国,甚至可能也不是从中国人那里得到的。总的来说,茶从中国传出,基本上通过两条路线,一条走陆路,从西域跨过中亚的崇山峻岭和浩荡沙海,大致在元代以前就沿丝绸之路向外传播,另一条则是顺着洋流和海风,在明清以后从中国东南沿海贸易逐渐散播开来。这儿,我还可以教给你一个小窍门,可以辨别一个国家是从哪条路线接触到茶叶的。如果一个国家是从陆路先接触到茶叶,那么他们的语言中茶的名字就会听起来像“茶”的读音,比如俄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如果走东南沿海的贸易路线,卖茶的就是说闽南语的人,而在闽南语中茶的读音类似普通话“爹”,他们的买家就有样学样,比如东南亚的爪哇语、东非的斯瓦西里语、欧洲的荷兰语。现在,你听英语单词“tea”的读音,能猜到英国人是哪条路线的买家了吗?没错,tea其实就是闽南语的变音。
福建的茶,是在17世纪中后期才途经荷兰在东南亚和台湾的贸易点传入欧洲,成为贵族之间流行的外国奢侈品,但当时很多人不太能接受茶味,比如一位法国夫人说茶喝起来像“干草和粪便”。至于此时的英国,还正在经历漫长的内战,无暇顾及品尝东方怪味饮料,反而是保王党的人逃到欧洲后能尝尝鲜。1660年,随着斯图亚特王朝的查理二世复辟,一些被茶迷住的贵族悄悄把茶装在包袱里带回了英国,闽南语的读音也一同传入英语。还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说法,说查理二世的欧洲老婆爱好喝茶,把茶会的风尚带给了英国上层。
讲到这里,我终于要为你解答,那时英国人到底是怎么看待茶的?当时英国有一位溜须拍马的文人为那位爱喝茶的王后献上了一首题为《论茶》的祝寿诗,歌颂“最好的王后、最好的药草”,感谢她借助这种东方的神秘力量平静头脑和心灵。
还记得最开始说的英国工人把茶当成兴奋剂吗?和《论茶》的观念一对比,你就会发现最开始的英国茶是被贵族用来镇静精神的,这倒是跟我们中国人很相似了。对于中国人来说,大约在宋朝以后,随着理学发展,物质世界和道德秩序相统一的观念越来越流行,茶被赋予了高雅和净化的属性。到明朝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茶性寒,可以降火,“火为百病,火降则上清矣”,几乎等于说茶包治百病。于是,茶就这样作为能够净化身体和平静心灵的药品被卖到了欧洲。在当时的英国,贩卖茶叶的咖啡馆中的广告宣传“所有医生都认可的中国饮料”,说茶叶有男性减肥、治疗头痛等等的疗效。拉帕波特认为,对当时的英国人来说,即便对疗效半信半疑,也可以炫耀自己能够消费东方奢侈品,可以摄入高雅、品尝文明、提升道德、改善健康。
在欧洲的启蒙时代,欧洲人认为中国国力胜于西方,都把中国视为更加文明开化的“天朝上国”,各国贵族争相模仿他们想象中的外国文化,让自己显得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 。你可能会想,这么好的东西,那不得在英国大卖特卖?看起来是这样的。从17世纪50年代开始,英国富人开始在新诞生的公共空间里消费新航路带来的新奇商品,比如咖啡馆、游乐花园等等。现在非常著名的茶叶品牌“川宁”的创始人,托马斯·川宁发现在咖啡馆里喝茶的都是谈生意的男性商人,于是就想为何不自己做批发,再开一个专门卖茶的商店,卖给更多人?1717年,他在伦敦开办了第一家专门卖茶的小茶馆并因此发家致富。这种零售模式令茶叶消费变得更大众,堪称茶叶的“零售革命”。
在喝茶王后到来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涉足茶叶贸易,与更早和中国人展开贸易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等等其他欧洲公司抢市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年进口额从最开始的数百磅逐渐增长,到1757年已经达到了1200万磅,足有五千多吨。
这就是茶叶和英国的初识期,这一阶段奠定了英国人对茶的认知基础。从英国人的角度来看,来自东方的茶有益身心,但只限于有钱人能够享受。由于当时茶叶只产自中国,高达110%的惩罚性关税和运输成本让茶叶价格居高不下,阻止了茶叶消费的扩大,还造成了大规模的走私。这样一来,茶叶消费在英国只能局限在一些交通运输发达的富裕地方,比如伦敦、北美殖民地等地。那么,茶叶帝国要怎么样突破这个瓶颈呢?
作者认为,由于英国在与法国的七年战争中战事吃紧,故而维持极高的关税,却不得不更依靠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力量,为后来的让步埋下了伏笔。 在川宁家族为首的合法批发商游说下,英国议会于1784年通过法案,将茶叶关税下调到了12.5%,为东印度公司解决了走私问题,还让茶叶消费量大涨了50%。后来推动此事的理查德·川宁在1793年被选为东印度公司的董事。
注意了,从这个时期开始,茶叶就开始和英帝国政治紧紧地咬合在了一起,逐渐成为英帝国的工具,并利用着英帝国的政治。茶叶模式的重新发明也在此开始了,他们需要给英国公众重新打造一个全新的茶叶品牌。新茶的塑造有三个主要玩家:第一个是禁酒团体代表的文化精英,第二个是供应端的印度茶园主,还有第三个是茶叶的贸易商,他们都参与了茶叶形象的重塑。
在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开始,大量工人承担着远超过去的劳动强度。资本主义开始有了“劳动力”的概念,人的身体被视为某种需要保养和维护的有机机械,因此,社会越来越关注怎么保护劳动力。酒、咖啡、茶之类的被认为对身体有影响的饮料,马上被道德化,被放入基督教的道德模型。当时活跃的禁酒团体成员地位很高,不仅有富商家族,还有议会议员,这些精英推动了政府取消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让更多自由贸易商为普罗大众供应茶叶。
为什么禁酒团体要这么做呢?当时英国的基督教禁酒团体主张控制欲望,主张用“道德的茶壶替换不道德的酒壶”。特别是对劳累的工人来说,酒毒害身体和理智,而茶让他们理智又节制。这些禁酒团体大办茶会盛宴,吸引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前来消费茶而不是去喝酒。比如1836年英国普雷斯顿办了一次1200到1300人的大茶会,连当地市长一家人都亲临现场。禁酒者强调,只要培养健康的消费习惯,也就是喝茶,懒散和不受控的工人不仅会转变为模范劳动力,还能成为社会经济的引擎。原本的堕落欲望会被茶引导到“衣服、美食、生活中所有舒适的享受,总之可以很好地报答种植者和制造商”。这种大众的“推广文化”选择性地合理化一种消费习惯,而贬低另一种,创造出商品之间的道德差异,是现代营销活动的雏形。
在禁酒团体的茶会中,英国各个阶级被团结在了茶周围,茶叶为新的工业英帝国赋予了高尚的灵魂。新生的工人阶级获得了丰富的饮料和食品,也逐渐相信禁酒能够带来家庭幸福、社会进步,为未来进一步争取政治公民权做准备。小茶馆店主相信自己可以借机跟酒馆抢利润,还能够蹭一蹭那些“体面人”的热度。而大厂商和贸易商则相信这样能够创造出清醒健康的劳动力队伍,说不定还能以此为筹码跟中国谈下更好的贸易协定。
说到中国,角色也很重要。时间到了19世纪,清朝由盛转衰,启蒙时代的“中国热”退潮,随着英国重商主义兴起和中英关系交恶,茶叶的中国属性反而变成了负资产。 他们眼中的清王朝不再是天朝,而是一个腐败、落后、野蛮的国家。有英国人担心中国的文明代表了阴柔和女性化,喝中国来的茶有损英国工人的阳刚性。还有人担忧英国人又爱喝茶又不产茶,长此以往,英国的财富会流失到中国。于是英国为了逆转白银外流的趋势,开始出口印度产的鸦片。结果清朝和英国的关系更加恶化,茶叶还真的变成了外交武器。林则徐在广州禁烟的时候,认为英国人不喝茶就会死,给皇帝提议禁止向英国出口茶叶:“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意思就是,外国野蛮人喝不到茶叶,就活不下去,所以他建议用茶叶禁运让英国人中止鸦片贸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英国人的方案很简单粗暴,和禁酒运动的“捧一踩一”思路非常相似,把茶叶变成英国货,再贬低中国人的茶叶,让茶叶的消费在英帝国内“闭环”。
荷兰人当时其实也有类似想法,他们从中国偷走了茶种,1828年开始在现在的印尼区域种茶树,这让英国人更加着急。但英国一个苦寒之地,哪儿去找能产茶的地方?巧合的是,在19世纪初英国逐渐控制印度的孟加拉地区后,殖民者的下一阶段目标瞄准了连接中国和印度的中间地带。我们现在熟知的茶叶产区阿萨姆,就在这条连接带上。现在,我们就要看第二个玩家:作为供应商的印度种植园主。
在英国1826年从缅甸王国夺走阿萨姆时,并不知道这里有野生茶树。直到1831年,才开始有阿萨姆出产茶树的探险报告。此后,在1834年,正好是东印度公司被废除垄断权的第二年,英属印度的茶叶委员会宣布阿萨姆的的确确产茶。1838年,东印度公司为维多利亚女王献上了英国人自己产的茶叶,并获得了英国社会各界的追捧。1839年,阿萨姆公司在伦敦成立,开始投资阿萨姆的茶园事业,似乎英国终于能结束对中国的依赖。
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些事情:当地的景颇人对英国人的到来和统治非常反感,开垦丛林也绝非易事,想要把印度变成英帝国的茶叶工厂,最后实现与清朝茶叶彻底“脱钩”,靠的不是乐观主义,而是残忍的帝国主义。
这里,我就要讲讲英国茶叶的黑暗面了。英国人在阿萨姆大规模生产茶,靠的是复制糖和咖啡的种植园制度。然而他们很快发现当地人根本不愿意为英国人工作,只想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主导开垦的阿萨姆公司可以说是虚伪而无知,总把自己碰到的问题说成刻板的种族问题,比如土著人不愿意来就嫌弃他们懒、华人要开高工资就说他们贪得无厌。 英国人为了让本地人乖乖进种植园当奴工,就像用印度种植的鸦片来弥补和中国茶叶贸易中的白银流失一样,也用鸦片诱惑了阿萨姆的原住民。据19世纪30年代后期时任总督的代表估计,可能有三分之二阿萨姆人对鸦片成瘾,他们因为毒瘾而不能成为合格劳动力。这就造成了阿萨姆有茶没人种的劳动力问题。
从1836年到1847年,主导开垦种植园的阿萨姆公司面临着原住民和劳工起义的威胁,无法有效填补劳动力短缺问题。眼看阿萨姆的投资就要打水漂,1854年英国改变拓垦规定,免费租用的土地不能低于500亩。也就是说,低于这个面积的小茶园必须缴付额外租金。这个新规定鼓励了种植园的土地兼并和扩张,还恰好碰上1851年阿萨姆茶叶在万国博览会上获奖,吸引了新的种植园主。他们争抢别人无力管理的土地,维持了垦荒的上升势头。种植园规模的扩大加剧了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于是私人种植园引进了大量俗称“苦力”的契约劳工。说是引进,其实多多少少是被苦力公司坑蒙拐骗,从印度贫困的乡下强行征募来的。更有甚者,英国还颁布法令,允许种植园主自行逮捕逃离的劳工,并随意惩罚。由于恶劣的工作环境和茶园主的残酷虐待,一些种植园劳工死亡率高达50%。
不幸的是,这种血腥的方式让英国人尝到了甜头。1860—1947年间,超过三百万苦力被运输到阿萨姆工作,他们生产的阿萨姆茶叶很快成为英帝国急需的本土茶叶。英国人又在锡金的大吉岭、锡兰,也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非洲等等地方复制了这一模式,满足英帝国茶叶种植国产化的渴望。各个殖民地里的新种植园主阶层一边自诩文明开化,穿着礼服在豪宅里进餐,另一方面也孤身在偏远的边疆艰难经营着。作者拉帕波特认为,英国殖民地种植园主的这种焦虑感促使他们变得更加种族主义和暴力,还驱动他们在英帝国内部寻找更多的盟友。
说到这里,这个把茶叶重塑为英国特产的大局中,我们来看最后一个玩家,那就是贸易商们。
对于贸易商来说,当务之急是让人们认可自己的茶叶比别人的茶叶更好。那到底用什么办法呢?他们找到的“痛点”是“纯正”和“安全”。食品在全球化和工业化的起步年代,不像以前一样能够直接看到供应过程。要进嘴的东西脱离了熟悉的生活圈子,人们更容易担心安全和质量。随着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手段声称能够检测食品成分。19世纪50年代,也有一位“打假使徒”亚瑟·希尔·哈索尔,号称用显微镜发现市面上几乎所有的食品都掺了假 ,或者按我们的说法就是“科技和狠活”。
茶叶在这种大规模的食品安全焦虑中,并不是例外。不仅如此,英国社会公众还相信,自从英国和清王朝展开自由贸易以后,越来越多不懂行的英国商人去进口茶叶时会被卖家欺骗。英国人还相信,英国和清王朝连续打了两次鸦片战争,他们觉得是清朝人怀恨在心,往茶叶里面下了毒!如果你在当时的英国卖茶,面对这些对茶叶的诋毁,会怎么做?
有位基督教贵格会成员、禁酒主义者、茶叶经销商约翰·霍尼曼的角色特别值得讲讲。这位霍尼曼发明了封装茶叶的销售方式,在1826年开始事先把称好重量的茶叶密封包装。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在报纸广告上解释,因为清朝人卖给英国人的绿茶都是假货,用有毒物质染过色,而他的茶叶绝对纯正。虽然在当时,广告不是一种非常流行的宣传做法,霍尼曼却坚持花大价钱在《泰晤士报》等当时流行的报纸上做广告,宣传自己的纯正产品能够保护消费者,呼吁家庭妇女为了保护英国人的身体购买他们的纯茶。他甚至专门请哈索尔之类的打假科学家,来赞美他的包装茶纯正无污染。这和现代的广告思路,是不是一模一样?
总而言之,在19世纪中期的英国,倡导纯正的科学家、文化精英和茶商一同宣传建立了一种科学的健康观念:纯正就是好的,科学的就是纯正的,工业的就是科学的。而清朝的绿茶是落后的、不纯的、不健康的。这些种族化的观念完全忽略了一个简单事实——为了在竞争激烈的茶叶贸易中赚取更高利润,英国人也掺假。只是,在英国茶叶本身就变成一种卖点以后,拥有英帝国灵魂的茶叶掺点假,有谁还在乎?
茶叶就这样,从东方的养生饮料,变成了代表英帝国的万能灵药。
到这里,我们来总结一下茶叶帝国的模式:首先,茶通过英帝国文化精英被定义为美德的象征、经济的保障,成为英帝国精神的具体代表。然后,帝国通过征服确保茶的供应,这个过程会生成新的利益阶层,影响帝国决策向他们倾斜。最后,新的利益阶层通过广告、宣传影响大众文化,制造符合英帝国精神的新“渴望”,把英帝国变为自己的促销工具。帝国种下渴望,从消费中收获模范公民、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等等好处,而茶的从业者则从渴望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利润。这就是作者所说的茶叶和英国的双轨帝国。
我们初步了解了茶叶模式,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模式如何扩张。
茶叶模式在19世纪中期初见雏形后,很快表现出极强的适应力,经历了很多次重大考验。
我刚刚讲到,很多地方都复制了阿萨姆的血汗模式,随之而来的就是供过于求的危机在1865—1866年大爆发,大量公司和种植园倒闭。刚刚起步的茶叶帝国这笔学费交得早,很快就着手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
除了有利于所有食品产业的运输和储藏的技术革新,连锁店、合作社等等新的各类销售方式促进了大众市场的普遍扩大。你一定听说过一个品牌“立顿”,它就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立顿创始人托马斯·立顿在1890年开始收购锡兰的种植园,靠低价获得商业成功。不断降低的税收推动了茶价格一路走低,立顿这样的品牌才能够通过定价战略,一举打进底层市场。同时,商家们在广告上更多标榜自己的茶适合女性口味,迎合当时的下午茶会风俗。这么一来,茶不仅卖给急需提神的英国工人和自我标榜的新兴中产阶级,还能卖给他们的妻子。最后英国商人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大家就是觉得不好喝,怎么办?
从1838年维多利亚女王尝到阿萨姆茶叶开始,英帝国的茶已经种了几十年,市场为什么还是不够大?关键还是它们的“人”设没有完全立住,对茶的渴望没有被完全导向它们。尽管之前说过,阿萨姆茶叶有维多利亚女王本人亲自背书,但是印度茶叶的品牌还是没有打响。它们被认为味道太浓,不算好喝,更别提背后还是一大堆以虐待劳工闻名的种植园主,让人觉得有损道德。新茶要完全和新帝国适配,还需要迭代几个版本。于是,海外种植园主们结合起来形成了产业组织和贸易协会,去扮演以前文化精英的角色,有意识地影响英帝国政府和英国公众的看法。
首先,英国当时流行调配茶,把不同比例的不同地区产的茶混在一起,形成独特风味,不利于建立对印度茶的认知。品牌化的调配茶会让消费者始终无法分辨自己的茶是来自哪的,也让种植园主没法更好地营销自己的茶叶。
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第一,是诋毁调配茶,他们公开质疑经销商让消费者没有办法支持“大英帝国辛勤劳动的同胞”。二是更重要的,要重新打造印度茶的口碑,和大英帝国再捆绑得深一点。种植园主的品牌焦虑实在是太明显了,有些广告按今天的眼光来看实在硬得不能再硬。书上有个例子,是一份1881年的广告,我念给你听听:“印度茶叶更纯正。印度茶叶更芳香。印度茶叶更浓郁。印度茶叶更便宜。印度茶叶更有益健康,因此在各个方面,都比中国茶叶好”。打广告的供应商嫌不够,又加上了一句“全体盎格鲁-撒克逊人,心怀我们种族的繁荣的人……尝试着喝印度茶叶吧!”他们很聪明地利用这些争论让印度茶叶的消费变成了一种对英帝国忠诚的表现。
接下来,种植园主还标榜自己已经蜕变,残酷剥削的种植园模式已经过去了,现在的种植园非常文明,机械化地加工干净茶叶,不像中国人要赤脚碾压树叶。经销商和供应商找上了在女性之间流行的下午茶会,让茶叶消费变得更女性化、更柔和、更时髦,以贴近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中产阶级喜好。同时,比如立顿这样的品牌还用低价和浓郁的味道攻占了英国工人的味蕾,为英属印度的茶叶获得了更大的市场份额。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也就是清朝光绪时代,在伦敦到处都能见到印度茶更工业、更便宜、更符合英国爱国精神的广告,最后这一系列的努力的确收获颇丰。到1887年,印度种植园主们把印度茶叶抵达英格兰五十周年和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五十周年捆绑营销,宣称印度和锡兰的年度茶叶合计进口量在这个年份终于超过了中国。英国社会各界赞美茶叶是“把种植园主和祖国连接起来的无处不在的强大纽带”,把这一成就作为更现代、更文明、更工业的英国战胜中国的象征,更把这次“胜利”解释为两国种族性的差异,他们宣称中国人更懒、更保守,所以喜欢掺假、没有走上工业化。 这说明,海外种植园主还真把印度茶忽悠成为英帝国的象征。小心,可不要被他们骗了。其实印度的茶叶到19世纪末都没有实现普遍机械化,而且掺假问题仍然没有根除。
但茶叶和英国两个帝国就这样绑定到了一起,从此以后,茶叶帝国的浮沉起落和大英帝国保持了高度一致。
在一战期间,具有调节和振奋效果的茶被英国政府当作战略储备,女性化的下午茶成了浪费和堕落的象征,反而是英国工人和士兵被优先供应,喝茶更加政治化了。种植园主们顺势在印度获得了更大的政治影响力,他们可以让整个英属印度都为他们卖茶。同时茶商的广告也变得更阳刚,更强调茶叶的振奋效果和英帝国性质。茶叶搭上“购买英国货”的便车,英帝国各地的种植园主和茶商挂着在他们眼中象征文明的米字旗,打开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等殖民地的市场,试图让不同种族和阶层的英帝国臣民都变成新的茶叶消费者,将他们提升到英国人觉得更文明的境界,帮助英帝国在殖民地营造均一、和平的社会秩序。1931年,英国对茶叶的控制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根据英国皇家经济委员会的说法,“70%以上的出口茶叶是在帝国生产的,近70%的茶叶都是由帝国所消费的。2/3以上的茶叶生产资本由帝国提供。印度和锡兰使用的所有机器都来自帝国,而60%用于茶叶运输的箱子是从帝国各地进口而来的。”
我们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茶叶帝国达到了巅峰期,也正是那个喂养了茶叶产业帝国和大英帝国的印度,亲手拉开了帝国由盛转衰的序幕。英国人主导的茶叶市场在印度的推广遭遇了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广泛抵制,当时农民喊出了“喝茶就是喝我同胞的血”的口号。面对民族化的抵制运动,种植园主们诉诸最纯粹的帝国主义强硬镇压,维护英帝国的不平等秩序。拉帕波特说,茶叶销售战反映了英帝国主义的核心矛盾:“他们相信消费主义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同时又拥有提倡差异的种族和民族意识形态”。 这种自相矛盾的大众消费主义,虽然维持了一百年的虚假团结,但不可避免地在英帝国各个角落孕育了反殖民的民族独立运动。
到了30年代,英帝国权势式微,英国和荷兰的种植园主团结在一起,于1933年建立了国际茶叶推广局。此时,英帝国性对茶叶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国际茶叶推广局在推销时弱化了英帝国性的展现,重新强调对身体有活化作用,选用了茶壶卡通形象和“茶叶让你精神焕发”的广告语作为主要推广手段。再随着二战后各地的去殖民化,英帝国已经不再需要帝国精神的象征,茶叶的帝国也无法继续维持自己。
取而代之的是新的资本主义帝国:美国和它的可口可乐,标榜自由的神奇快乐水。
好了,这本《茶叶与帝国》的主要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你可能还会问,那中国、日本、荷兰都曾经在茶叶领域与英国竞争,也有自己的故事,而且也有咖啡、糖、棉花之类的商品,为什么就得讲茶叶,就得讲英国?这里就得提一下,这本书的原名可以直译为“帝国的渴望”,作者玩了个小双关。这个渴望,既是说想要喝茶的渴,也代表帝国扩张的望。而标题里的帝国,既是说支配世界的大英帝国,也是风靡全球的茶业帝国。这有两个帝国,他们的边界有时会相互重合,但却并不完全相同。这是什么意思呢?
一方面,在英国人眼中源于遥远东方的茶在19世纪的英国被重新发明,成为健康、文明、工业等等代表大英帝国的概念象征,成体系的茶叶产业在英帝国疆域内被生产、流通、消费,从业者们用各式各样的广告和游说手段催动英帝国的政治力量帮助自己扩张,这是常常重合的方面。另一方面,当单纯的“茶叶”演变成了茶的产业,资本主义的力量就驱动着新生的产业向外辐射,将自己传播到了英帝国的边界以外。面对新的风土、新的资本、新的欲望,茶的产业帝国已经不是英帝国的工具,会有不同变体,这是不重合的方面。
不管是实体的英国,还是无形的茶产业,帝国的扩张总是面对着竞争和抵抗。以茶叶帝国在美国的遭遇为例,美国人当初就是因为茶叶代表了英帝国特权才一怒之下搞出了波士顿倾茶事件,夸张一点说,不喝英国茶是写在美国人的基因里的。就连日不落英帝国鼎盛期的20世纪初,美国人都把茶当作娘娘腔的英国老奶奶饮料。在别处卖爆茶叶的英帝国性,在美国正好是它的命门。至于抵抗,日不落英帝国土崩瓦解后,独立的印度、斯里兰卡、肯尼亚等等都想围绕着茶叶建立新的英帝国,但旧的英国资本还是控制着很大比例的产业。这些新生的国家于是重建了茶叶产业和民族独立的关系,抵抗着外国资本的控制,例如印度最古老的英国种植园公司之一,詹姆斯·芬利集团在2000年被印度的塔塔茶叶公司取得控股权。
我们要看到,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茶叶,创造了一种用经济产业把大众消费和英帝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模式。作者认为,围绕茶叶繁荣崛起的资本和工业,是资本主义的肉体,茶叶本身则宣扬英帝国当时标榜的道德和精神。从茶产业模式的壳中,生产“渴望”的全球资本主义就诞生了。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看全文和脑图,也欢迎你点击右上角的“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
茶不只是提神醒脑的健康饮料,它还是一种模式。
-
围绕茶叶繁荣崛起的资本和工业,是资本主义的肉体,茶叶本身则宣扬英帝国当时标榜的道德和精神。从茶产业模式的壳中,生产“渴望”的全球资本主义就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