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与太阳》 裴鹏程解读
《英雄与太阳》| 裴鹏程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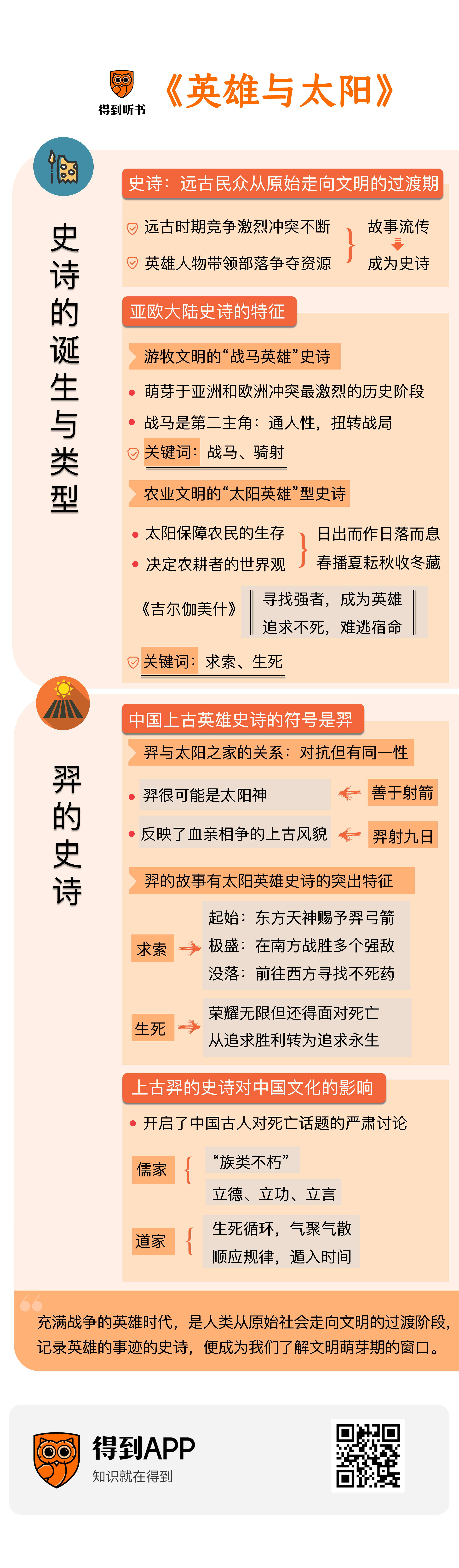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介绍的是《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原型重构》。
“史诗”这个词你应该听过,一些背景设定宏大、人物众多、情节复杂的小说、电影、戏剧,常被人称为“史诗巨作”。不过,史诗并不是字面上“历史诗歌”的意思,这个表述是从西方来的,简单说史诗就是“古代英雄故事”。它可能是神话、传说,也可能是民间故事 。过去的英雄故事是口口相传的,节奏明快、情绪饱满,因此在中文中被称为“史诗”。古印度的《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是史诗,古希腊《伊利亚特》《奥德赛》的故事文本也是史诗,在中国,藏民至今传唱的《格萨尔王传》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
中国中原地区以前有史诗吗?很多人认为,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就诞生了史学,人们更关注现实世界,再加上儒家提倡“敬鬼神而远之”,所以,充满神话色彩的英雄史诗即使最初出现过,也未能流传下来。但今天这本《英雄与太阳》提出了不一样的观点,尽管中国中原地区缺少完整的长篇英雄史诗,但“史诗思维”是中国古人曾有的,我们依然可以在古代历史文献中找到属于中国古人的史诗原型。
西方历史哲学之父维柯曾把人类文化发展历程分为三个时代: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人的历史。本书作者叶舒宪教授沿着这个思路,搜集了大量史料,做了扎实的研究。他提出,史诗反映的是人类历史的第二个阶段“英雄的时代”。世界上许多文明都经历了从原始向文明的过渡,因此理论上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英雄史诗。中国上古时期最主要的史诗之一是“羿”的史诗,“后羿”的“羿”。关于“羿”,有人主张古代有两个“羿”,我们熟悉的“后羿”是传说中夏王朝东部的一个部落首领;而射了太阳、娶了嫦娥的那个叫“大羿”。这些说法都有浓重的传说色彩,真假难辨。我们可以做的,是深入传说背后分析中国古人是怎么思考问题的。与古希腊史诗不一样,“羿”的史诗属于农耕定居文明,在中国各地,甚至是古埃及、古巴比伦等古老的农耕区都可以找到同伴。尽管“羿”的史诗记载早已零落成泥,但它对中国文化、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方式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借着这本书,我们不仅有机会对世界上的“史诗”有个初步了解,也为我们观察中华文明的萌芽期打开了一扇窗。介绍一下作者叶舒宪教授,他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同时担任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会长。听书曾解读过他的《中国神话哲学》《玉石神话信仰与华夏精神》。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就在研究并写作“神话与史诗”的课题,这本《英雄与太阳》是他研究上古史诗的学术论文集 。
下面,我们就跟随叶舒宪教授走入史诗的世界。第一部分,我们从世界角度整体了解一下,史诗是怎么诞生的,有什么类型?第二部分,我们走入羿的史诗,它有什么特点,对中华文化产生了什么影响?
我们首先看,史诗是怎么产生的?
作者结合维柯的观点提出,与史诗对应的是“英雄的时代”,史诗反映的是一个民族从原始社会走向文明的过渡期。
最初,人们生活在茹毛饮血的蒙昧状态,后来,一些规模较大的社会组织开始形成,就像金字塔,顶部是部落大首领,在他下面有许多小的首领,最下层是被统领的民众。这类组织的出现,少不了部落内部的权力变动,部落之间的资源争夺。所以战争成为那个时代的主要事件 。一个部落能否有幸存活、野蛮生长,很大程度仰仗部落首领。于是,一些能征善战、智谋过人的英雄人物涌现出来了,他们带领民众保护部落安全,并争夺到更多资源。因此,作者把那个血雨腥风的时代称为“英雄的时代”。英雄的故事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文化遗产,流传至今,便是史诗。
如今现存的史诗,多是在亚欧大陆发现的,作者认为这与战争有关。远古时期,撒哈拉以南非洲、美洲以及大洋洲,人口较少而且分散,少有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因此缺乏长篇英雄史诗诞生的土壤 。
亚欧大陆的史诗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作者提到,英雄时代正在走出原始社会,人们对神的崇拜习惯没有消散,所以人们认识世界会带着浓重的神话色彩。史诗中的敌人们总是邪恶丑陋的妖魔,这反映了人们与其他族群的对抗;史诗中洪水、大火、地震也常化身为鬼怪,这反映了人们与自然灾害的对抗。不论如何,英雄最终带领大家战胜了它们,维护了本部族的生存与发展。
而且,史诗诞生时文字或许还没有普及,所以需要靠吟唱的方式口口相传。作者引用了别的学者研究,史诗最初的演唱者并不是游吟诗人、民间艺人,而是兼有宗教身份的巫师或祭司。他们的工作,说白了就是把故事讲好,让部落的民众相信并听从统治者。
另外,演唱史诗需要在特定场合配合特定仪式。演唱史诗并不是为了欣赏和娱乐,而是为了鼓舞士气。为了尽可能鼓舞战士们效法先辈英勇杀敌,史诗演唱常伴有庄重的宗教气氛。甚至演唱者还会“通灵”,假装神灵下降到他的身上,然后借他的口对将士们发表一番演讲。
亚欧大陆上诞生了很多史诗。作者认为,这些史诗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游牧文明的“战马英雄”史诗,一类是农业文明的“太阳英雄”史诗。
先看“战马英雄”史诗。从广阔的中亚草原到欧洲,都属于“战马英雄”史诗流传的区域。特别说一下,尽管欧洲不是一望无际的草原,但从古代到中世纪,亚洲腹地游牧民族常常冲击这里,因此为欧洲文明植入了有关“战马”的文化基因。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认为,欧洲文明史其实是亚洲历史的一部分,他的解释是,欧洲古代和中世纪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结果” 。
所以,很多史诗都萌芽于亚洲草原和欧洲冲突最激烈的历史阶段。早在公元前14世纪,以游牧为生的一支雅利安人向南迁徙,经伊朗高原到达了南亚,经过一系列征服后建立了国家,著名的《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等史诗就诞生于这块土壤 。名气更大的《荷马史诗》,故事背景是著名的特洛伊战争,冲突双方分别是古希腊人和西亚地区的民族。
直到中世纪仍然如此。公元4、5世纪后,一波又一波游牧民族逼近欧洲,一些史学家称之为“蛮族大迁徙”。在匈奴人的冲击下,日耳曼民族孕育了《尼伯龙根之歌》等史诗;几百年后在突厥人的冲击下,法国出现了《罗兰之歌》,西班牙诞生了《熙德之歌》,俄罗斯则有《伊戈尔远征记》。
在这些史诗中,马从来都不只是一种运输工具,更是精神纽带。有了战马,原本分散、独立、弱小的小群体可以聚拢起来,变成来去如风、规模庞大的战斗集团。如果看具体的战斗,战马是英雄战斗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如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的主人公玛纳斯的名言:“要是徒步行走,我便成了一条不能直立的狗” 。
因此,战马往往是这些英雄史诗中的第二主角。它们通人性,会对主人提出忠告,会在生死攸关时刻,救主人的命,进而使战局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北亚地区的《阿拉坦沙盖夫史诗》中讲到,英雄去世后,坐骑把他的尸体带到安全地带,藏在一个山洞里,然后跑到大汗的女儿那里,逼迫她为自己的主人施展起死回生术。在我国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主人公的坐骑是马头神的化身,身体各部位栖息着许多神灵,尾巴栖息着“克敌制胜的愤怒的众神”;牙齿隐藏着“减轻病痛,平息恶魔的众神”;它的双耳上端是“洞察一切的众神”等等 。
在我们熟知的史诗中,这样的战马英雄史诗占了绝大多数。甚至,提到史诗,战马、英雄、搭弓射箭、长途奔袭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但叶舒宪教授提醒我们,世界上还有另一类史诗,这就是农耕文明的“太阳英雄”型史诗。
对于农耕定居民族来说,有了太阳的光和热,农作物才能生长,农民生存才有保障。除此以外,太阳还决定了农耕者认识世界的方式 。太阳有东升西落的规律,为定居的农夫们提供了时间和方位观念尺度,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播夏耘秋收冬藏;建造房屋的时候,门窗朝向太阳,储存食物的时候,要选择背阴的地方。民族考古学专家宋兆麟老师提到,我国很多民族都是先知道东西方向,后来才有南北方向的知识。生活在云南一带的景颇族将东方称为“背脱”,意思是日出的方向,将西方称为“背冈”,意思是日落的方向。汉字繁体字的“東”,你仔细看是一个“日”落在一个“木”上,这个“木”正是扶桑神木,是日出处;汉字“西”,是个象形字,象征着飞鸟落在巢中 。
更进一步讲,太阳还是个坐标符号,人类认识宇宙秩序,给自然万物编码分类离不开它。比如中国古人把地上的政治区域划分为若干组成部分,以便和天上的星宿对应。在古老的农耕区两河流域,也就是今天伊拉克一带,也有类似的“十二分野制” 。除了古代中国、两河流域,像北非的埃及、东非的埃塞俄比亚、南美的安第斯山区、印度南部的农耕定居区,太阳都在原始先民的生产生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定居农耕区与游牧区,生产生活方式不一样,因此,这里诞生的史诗并不是把战马简单替换为太阳,内部逻辑也与战马史诗不一样。
我们具体以两河流域的《吉尔伽美什》史诗为例。19世纪以前,西方学者把古希腊《荷马史诗》当作史诗的始祖和楷模,但在19世纪70年代的考古发现中,一部被遗忘数千年的古老英雄史诗重新展现在人们面前,这就是《吉尔伽美什》 。
在西亚的两河流域,公元前4000年就有了人类最早的文字,公元前3500年出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城邦国家,凭借高度发达的灌溉农业系统,发展起繁荣的文明。后来曾有许多入侵者占领过这个富饶的农耕区,公元前19世纪,围绕巴比伦城又一个新国家出现了,《吉尔伽美什》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历经一千多年形成的 。
《吉尔伽美什》的主要情节是这样的,有个城名为乌鲁克,统治者吉尔伽美什是位英雄,但他十分残暴,于是,天神创造了一位气力非凡的英雄恩起都与他交战,结果胜负未分,两人不打不相识,结为好友,一起挑战更强大的对手。后来,恩起都受诅咒死了,吉尔伽美什伤心之余开始远游,寻找生命之草,寻求长生不死,但就在他成功返回时,意外被一条蛇叼走了生命之草,追求不死的希望最终还是落空了 。
吉尔伽美什的故事中有个关键词“求索” ,最初他求索强者,与之战斗,因为只有挑战强者,才能成为英雄;后来他追求不死,但英雄也难逃死亡的宿命。
作者认为,“太阳英雄”史诗的核心结构就是“求索”。太阳东升西落,仿佛在锲而不舍地追逐着什么,日出时,古人看到了光明是兴奋的;中午时,太阳当空是极盛;到傍晚,尽管人们恐惧黑暗,但太阳依然一去不复返。这样的观念深入农耕定居区先民的感受和思想里。反映在史诗中,吉尔伽美什也在追求胜利,追求永生,他也曾战无不胜,如日中天,但也要遭受朋友离世的悲伤,以及必将一死的恐惧。他努力寻找不死的方法,尽管拼尽全力,最终还是如必然西落的太阳一样,与不死失之交臂 。求索与生死,这是太阳英雄史诗的关键词。
介绍了两河流域农耕定居区的《吉尔伽美什》史诗,中国上古的史诗是什么样的呢?
翻看中国古代汉民族的典籍,我们找不到像《吉尔伽美什》那样的长诗。有人说,中国古代的史诗散落在《诗经》中。《诗经》的《大雅》部分有五篇介绍周人开国创业的历史作品,但不少人反对,即使把五篇诗凑在一起,字数仍然很少 。
叶舒宪教授提出新的思考角度,与西方史诗、古希腊戏剧相比,中国古人更注重对现实的历史记录,因此上古时期的中国叙事文学并不发达,成熟的小说类叙事作品出现在唐代以后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先民没有史诗创作,我们依然可以在纷繁的先秦史料中,找到太阳英雄史诗的蛛丝马迹。
开头已经提到,中国上古英雄史诗的符号应该是羿。为什么用“符号”这个词呢?作者提到,由于中国古代缺少长篇史诗文本,有关“羿”的记录散落在许多文献中,许多“羿”的故事是断裂、矛盾的,但如果将这些碎片拼接起来综合分析,我们会有不一样的发现。
羿最著名的故事是“后羿射日”,天上有十个太阳炙烤着大地,民不聊生,英雄后羿为民除害,射掉九个。关于这个故事,过去的学者倾向从人类与自然的对立角度分析我国神话的特点。比如,中国神话传说中的英雄面对大灾害的时候都不是束手无策,而是想尽办法去克服它们,除了后羿射日,女娲补天也是这样。而且,这些英雄人物的命运不是由神安排的,而是它们自己的力量决定的,它们往往和神处在对抗地位,而不是神的顺从者 。
但作者认为,羿与太阳之间的关系,并不只有对抗,还有同一性 。注意,这是我们理解“羿”史诗的关键。
我们先把作者的假设抛出,再逐步分析。作者认为,羿很可能是一位太阳神,但他因为杀害兄长而失去神的身份,落入凡间,后来他在人间为民除害,希望恢复不死之身 。
听起来有点天马行空,不着急,我们先看作者的第一项假设,羿可能是太阳神。
叶舒宪教授提到一个有趣的洞见,神话的本质在于先民对事物的象征性解释。由于他们不掌握抽象的词汇、繁复的逻辑,所以需要用想象来完成解释,最常用的方法是类比。类比是神话创造的原则,也是语言创造的原则 。
在现代汉语中,我们把光线叫作“射线”,把光照治疗叫作“放射”治疗。但我们知道光并不是一根一根的,把光线称作“射线”是个古老的记忆遗存,反映了中国古人认识世界的方式。
说回“后羿射日”,试着看“羿”这个字,它就像两支并列着的箭,后有箭羽,箭头向下。羿作为受人敬仰的英雄,最突出的特点是擅长射箭,在《左传》《论语》《孟子》《韩非子》等很多上古典籍中,羿都是神箭手。
善于射箭,这是上古很多太阳神共同的特点。比如古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太阳光就是他的金箭,可以置人死地。古巴比伦神话中,太阳神马杜克的主要武器也是弓和箭 。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认为,把太阳光类比为箭,这个原始观念甚至要比神话本身的产生年代还要早。前些年,人们在我国云南仓源发现一幅原始岩画,画的主体是个太阳,太阳中有个人张开双臂,一手持弓,一手持箭,这体现了太阳、人、弓箭的相互统一 。
但我们想,如果说羿是古人心中的太阳神,为什么羿要射日,这不会矛盾吗?
我们接着看作者的第二项假设,“羿射九日”反映了血亲相争的上古历史。
《山海经·大荒南经》讲到,天神帝俊和妻子羲和生下十个孩子,由于羲和是女性太阳神,所以十个孩子便是十位小太阳神 。结合前面作者分析的,后羿、射箭、太阳之间的统一关系。作者提到,在古人观念中,后羿是帝俊和羲和的十个太阳神之子中的小儿子,被他射落的九个太阳,应该是他的九位兄长。
听起来是一场惨烈的血亲相争,实际上隐约透露了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讲的“幼子继承制度”。古代大多数父权制社会组织,实施长子继承制。在更早的原始社会,则是由更年幼的子女继承家庭遗产。人类学家弗雷泽的解释是,幼子之所以继承遗产,是因为哥哥姐姐离开家庭后,只有幼子与父母同住,自然负担起奉养的义务,也就拥有了继承权利。这种继承制度除了南亚、非洲的某些原始部落,在大多数文明社会已经不存在了。不过,由于这种制度起源古老,在上古神话传说、史诗以及后代的民间故事、童话中,印记仍然难以磨灭 。
只是前面这些内容,羿与太阳对立统一的逻辑关系还是不够牢固。如果羿的故事对于中国古代的影响力足够大,应该还有更多证据。
作者提到,汉民族周边族群中大多有射日传说,只不过主人公不叫“羿”或“后羿”,取而代之是本族群的英雄。作者列举了非常多的例子,像纳西族的桑吉达布鲁射日、布依族的翁戛射日、黎族有万家射日、傈僳族是一对兄妹射日等等。其实,到底是谁影响了谁,并不重要,这也很难追溯。比较确切的是,英雄与太阳的统一对立关系在中国各地上古先民的思想中很普遍。
我们接着说。前面讨论两河流域的《吉尔伽美什》时提到,太阳英雄史诗有两个突出特征,“求索”与“生死”。羿的故事碎片能满足这一点吗?
如果把有羿的故事拼接起来,我们也能看到像吉尔伽美什一样的“求索”路径。
羿的生命历程是从东方开始的,古代典籍对于这个问题基本统一。比如《山海经》记述他是东方天神帝俊的儿子。闻一多先生也说:“羿为夷族,本居东方”,这里“夷族”是古人口中“东夷西戎”的“夷” 。前面提到,羿射九日掀起了家族内部斗争。《山海经·海内经》的描述是,东方的天神帝俊赐予后羿弓箭,让他下凡 。作者分析,这是羿因为自己的暴行而被帝俊逐出天庭,贬降尘世,成为凡人。
羿最终是在南方成为英雄的。《淮南子》提到,尧帝让羿在畴华这个地方杀死凿齿。畴华是传说中南方一处水泽地带的名称,凿齿是生活在南方的猛兽。另外,羿还在洞庭杀死了大蛇。我们都知道洞庭湖,站在中原看,洞庭也在南方。在南方这些壮举,是羿的高光时刻,他因此成为光彩夺目的英雄。
尽管成了英雄,但羿还有一件心心念念的事情,这就是恢复不死之身。这就有了我们熟悉的,后羿前往西北方向的昆仑山求取长生不老药的故事。与《吉尔伽美什》的情节很相似,尽管后羿拿到了仙药,但嫦娥偷药导致他还是与不死失之交臂 。
从东方开始,在南方极盛,最终没落于西方,这跟我们看到的太阳的轨迹是吻合的。羿先通过战斗成为英雄,尽管荣耀无限但还是得面对死亡的威胁,于是从追求胜利转为追求永生,这正是“太阳英雄”史诗的基本逻辑。
说了这么多,上古羿的史诗对中国文化有什么影响吗?
读中国上古神话,你是否发现,“后羿和嫦娥”几乎是唯一一个直接讨论生死的故事。嫦娥急于吞服仙药,反映了中国古人对死亡的恐惧。叶舒宪教授认为,羿的史诗开启了中国古人对死亡话题的严肃讨论 。
面对死亡意识的巨大威胁,中国儒家拿出的方案是“族类不朽”。人类社会的基层组织有三类:家族,这是血缘类;乡亲,这是地缘类;同行从业者,这是业缘类。三类中,血缘类组织是最原始、最基础的。古人总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光宗耀祖”“光耀门楣”。作者认为,这正是儒家对死亡话题的回应 。既然个人的肉体无法永生,那就努力让家族永恒绵延,让有限的个人生命融入无限的与天地同寿的社会进程中。
不过,这种思路还是粗糙了些,人们恐惧的生命终点还是会到来。有什么办法能让个人生命独立地实现永恒绵延呢?儒家提出另外的方法是,立德、立功、立言 。立德,只有尧舜那样的圣人才能做到;立功,也得是治水的大禹那样的英雄才配得上;相对比较容易的,或许是立言。
很多人都能背得出“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成一家之言”是很多中国古人的追求。也因此,中国成为世界上保存文字记载最丰富的国家,原因便是历代知识分子对“立言”不朽境界的不懈追求。
虽说留下文字能让后人记住自己,但是面对肉体的死亡,我们还是会恐惧的。
于是道家提出了循环生命观。道家的“道” 含义之一是“规律”,道家认为,生死循环、气聚气散,这是宇宙规律,我们应该顺应规律,遁入时间中。
道家会先对古人进行一番精神按摩。庄子讲过一个故事,一次他见到一具骷髅,就问骷髅生前因何而死,然后枕着骷髅睡下。随后骷髅托梦:“纠结因何而死,这是你们活人才有的烦恼。让我讲讲死的快乐吧,死后就没有君臣礼法,没有饥寒病痛,无忧无虑与天地自然共存” 。
缓解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紧接着道家还要解释人的肉体消亡后,将向何处。道家有个说法叫“尸解”,蝉会脱壳,蛇会蜕皮,道家认为人也可以摆脱肉身束缚,开始新的生命 ,化入周而复始的无限时间中。这与太阳的东升西落,周而复始,不可谓不一致。
关于这本《英雄与太阳》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我们跟随作者叶舒宪教授了解了世界上的史诗。充满战争的“英雄时代”,是人类从原始社会走向文明的过渡阶段,因此记录英雄事迹的史诗,便成为我们了解文明萌芽期的窗口。
作者把世界上的史诗分为“战马英雄”类和“太阳英雄”类。上古中国属于农耕定居区,因此孕育了“太阳英雄”史诗。由于中国人倾向记录现实历史,如今并没有完整的史诗留存下来。但我们仍然可以在中原地区以及周边许多农耕区找到史诗的碎片,这关键的就是有关“英雄射日”的传说。这些传说不仅留下了精彩的故事,也启发了古人对生死这个终极命题的思考与解答。
今天我们多次提到神话传说。很多时候,我们会把神话和天马行空的想象联系在一起,或许它反映了一些古代史实,但一定不多。做了数十年神话学研究的叶舒宪教授有一番心得,也许能启发我们对神话的看法:神话讲述活动大大早于文字的起源,它先是伴随最初的口传文化,文字起源后成为书面最早记录的重要内容。神话并不是文学的一个子类,而是文史哲、宗教、政治、艺术的共同源头,也是我们追寻文明的“婴孩时代”首选的路径。
好,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
史诗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游牧文明的“战马英雄”史诗,一类是农业文明的“太阳英雄”史诗。
-
神话讲述活动大大早于文字的起源,它并不是文学的一个子类,而是文史哲、宗教、政治、艺术的共同源头,也是我们追寻文明的“婴孩时代”首选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