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锦的香港往事》 杨以赛解读
《素锦的香港往事》| 杨以赛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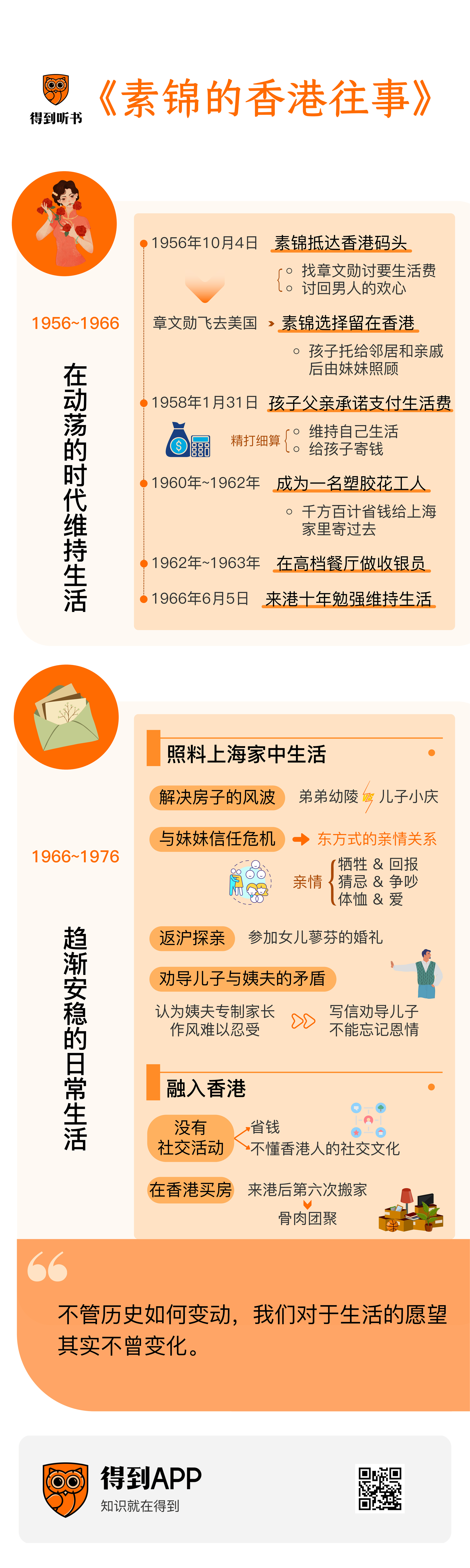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素锦的香港往事》。
这本书起源于收藏家刘涛在上海文庙淘到的一沓书信。这沓书信一共482封,内容是一个叫素锦的女人从香港写给上海家人的信,以及她妹妹给她的回信,时间从1956年10月5日开始,到1976年12月12日结束。刘涛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这些书信既是素锦这个女人的个人生命史,让我们看到她在香港地区二十年的日常起居、生活琐事,以及她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除此之外,这些书信也是研究香港和上海城市史的文献资料,我们可以由此看到上海和香港在1956至1976年间的历史变迁。
2021年,刘涛和作家百合以这些书信为基础,完成《素锦的香港往事》一文,发表在了《读库2202》上,受到了很多关注和好评,并荣获了2022年《收获》文学榜非虚构类第二名。今天的这本书出版于2023年8月,是由文章扩写而来,既丰富了素锦在香港二十年间的生活细节,也更进一步展现了沪港两地二十年间的沧桑变化。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罗新教授评价这本书说,这是一本蕴含着深刻时代内容的个人生命史。
接下来,我将分两个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第一部分,我们来看素锦在1956至1966年间的生活,她是如何在一系列时代动荡下,维系一个家和一份生活的。第二部分,我们来看素锦在1966至1976年间的生活,在生活渐趋安稳,回到日常之中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又会呈现何种面貌,以及走向何方?
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1956年10月4日,素锦抵达香港码头。她此行有两个目的,一是要到男人的钱,二是讨回男人的欢心,把孩子们都接来与父亲团聚。
这个男人叫做章文勋,素锦是在上海舞场认识的他。当时素锦因家庭生活困难,进到舞场做伴舞,遇到章文勋后,章愿负担她一家生活,素锦于是与他同居,后育有子女三人。章文勋本有家庭,1950年他抛下素锦去了香港,承诺说每月会汇来生活费。但自1953年起,汇款经常拖欠,1953年11月之后更是一分也没有了。素锦实在没了办法,只能赴港找寻章文勋,以解决子女生活问题。
她从上海出发,经广州转澳门,再从澳门到香港,这明显是绕了远路。作者百合推测这可能和当时的边境政策有关,从1951年2月15日起,来往香港地区的旅客一律需要公安机关签发的通行证才能通行,因此,赴港人数锐减九成,素锦八成是没有搞到通行证,于是不得不绕了一大圈才到香港。
第一晚,素锦在她的一位小姑姑家住下,洗了澡,吃了饭,逛了马路,素锦在信件中写这里“真是热闹......东西都甚便宜,五光十色”。第二天天一亮,素锦在小姑姑的陪同下,开始按地址找人,但去了两次都没见到。上午十一点半的时候,章文勋出现了。他样子没怎么变,但明显手抖得厉害,面对这个被自己遗落下的女人,章文勋感到的是惊吓。他直言自己生活负担重,无法再负担素锦和子女的生活。素锦对这番话有心理准备,她知道章文勋没钱,但再没钱也不能让三个小孩饿肚子吧。章让素锦先回上海,他会汇生活费回去。但素锦怕这是章的缓兵之计,她告诉章自己不打算回去了,孩子也都要接过来。章又说,自己手头的生意刚开始,要等六个月才能看出好坏。素锦不松口说,那我就等你六个月。当天给妹妹的信件里,素锦写:这个男的除了和当初一样胖,其他方面都变了,简直是个混蛋。但在给女儿的信里,素锦却没说章文勋一句坏话,她说:“你爸爸确实环境不良,受很重的刺激,他很不得意,我们也不怪他了,因为他实在是这样。”
九天之后,章文勋飞去美国了,没留一分钱给素锦,只留一句口信说:九龙闹事,适逢宵禁,街上封锁,没条件见面,也没法出门借钱,飞机票是提前买好了,不能改期。他所说的九龙闹事,是指1956年10月10日的“九龙暴动”事件,这是香港地区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暴动。医院记录伤病数四百四十三人,其中五十九人死亡,三百八十四人受伤。此事件又称“双十暴动”。
素锦听闻街上惨状,瑟瑟发抖,一方面觉得章文勋确实迫于无奈,另一方面又担心他这一走又是金蝉脱壳。以及,眼下香港地区是这般情形,她真要留在这儿吗,要不要回去上海呢。素锦的小姑姑劝素锦再留一段时间,耐下性子磨一磨章文勋。
素锦在上海的三个儿女,大女儿蓼芬和儿子小庆,托给了邻居和妹妹素美照顾,小女儿小芬则寄养在苏州亲戚家。此外,素锦还有两个弟弟分别叫元陵和幼陵。幼陵一直催素锦回上海,而元陵身在台湾,得知姐姐的窘状后,则一直劝她不要着急做决定,对章再观察观察,并说他这个当舅舅的有一日在世,即当全力以赴照顾三个孩子。
素锦于是在香港留了下来,夜里想孩子想得睡不着,就爬起来给孩子写信,写的都是一些琐事,像是:“你们时常要留心冷热,保护身体,最好的就是身体健康,因为妈妈不能照顾你们,你们早晨要漱口、刷牙,晚上要洗脚、洗面,手一定要清爽,这种习惯一定要养成,否则别人看来就是不懂规矩和不礼貌,整洁也是要紧的。”
素锦等了快有一年,章文勋才回来。这次回来章的态度好了一些,大概因为在港上海人的圈子就这么大,他一个生意人,多少也要顾及自己的声誉。他会时不时来小姑姑家看素锦了,有时候也约她出去走走,吃个饭或看个电影什么的。不过章文勋确实拮据。上世纪50年代的香港市场繁荣而高度饱和,外来移民很难再分到一杯羹,章文勋打拼一年多,一个写作间都没打拼到。另外,章文勋妻妾成群,算下来有十二个子女要养,负担不重才怪。所以他态度虽然好了,但现实问题却一个也不能解决。
1957年7月,上海的邻居来信给素锦,说已经吃不消再帮她照料孩子。原先一直给她寄钱的弟弟元陵这时也来信说要辞职上学了,没法再像以前那般寄钱了。雪上加霜的还有上海房东要求素锦退房。各种压力之下,素锦病了,早年开过刀的左颈淋巴结硬核复发,但她没钱看病,只能拖着。
好在还有妹妹素美,她帮素锦办理了房屋续租手续,又和邻居谈妥了延期照顾孩子事宜。这一时期,素锦对妹妹的付出十分感激,信件中她将对妹妹的称呼从“你”换成了“您”。她说:“我是非常记挂您的身体的,像您的体质和性格沉静,会思虑,终是不会十分强健……希望保重为要。”
到1958年1月31日,素锦来港后的第三个年头,章文勋终于给了素锦两百港币。素锦第二天就兴冲冲地给妹妹寄了一百元,另一百元留给自己用。但也因为给了钱,章文勋有了底气,对素锦开始不闻不问起来。素锦在给妹妹的信中说:“我知道我现在是忍受的时候,那是应该忍耐的,有什么别的方法的,除非我自己有本事能自力更生,经济独立。”
素锦不是没试过工作,年少时她在纺纱厂做工,为人母后又去了托儿所做工,但都因收入实在太过微薄而作罢。据1939年《上海生活》杂志统计,上海女职员工资多则二三十元,少则几元,这点钱维持她们个人开支都不够,更谈不到维持家庭了。于是那个时代大多数女性只能选择一个男人,将后半生“牢牢焊死在他身上”。作者百合就此说,“单纯批评旧式妇女主观上‘不独立’,这太过片面和太冤枉她们了。这实在是时代造成的悲剧。”
1958年,素锦开始筹划将孩子接到香港生活。章文勋见她铁了心不回上海,有点松动,答应说先接到澳门居住,那边生活费低一些。素锦同意了,她信里说:“随便,住澳门也好,新界也好,元朗沙田哪里都好,只要他能负担生活。”
到这时,素锦已经在小姑姑家住了快两年时间,随时间越来越长,小姑姑对素锦的态度也有变化,难免流露出一些不耐烦。1958年九十月间,章文勋的生意好做了,公司扩充,甚至准备要办厂了,这时他终于给素锦租了一间小房子单住。章文勋每月给二百五十块生活费,素锦小心计算着,想把每一分钱用到刀刃上。她把本用来买衣服的钱买成了棉布,做了床单和被子,预备孩子们来了用。用作者百合的话说,素锦是像“耗子偷米”一般,每月零零碎碎买点生活用品,想给孩子们拼凑一个像样的家。素锦在这一点上颇以为傲,她在信件中说:香港这地方,人容易被花花世界带偏,但自己如果头脑清楚有定力,就不会轻易被同化......现在我知道善于处理经济也是一种学问,能精打细算,同时耐心、冷静,不能冲动......我有信心,我有勇气,我相信我们是会好的,快乐些吧!
可就过了半年,素锦又陷入了困顿。1960年7月,妹妹素美给素锦写信说,她的丈夫(也就是素锦的妹夫)路临轩想要继续读书,完成大学课程。可一旦录取,每个月六十五元的工资便没了,家庭全部开支落到妹妹一人头上,她估计很难再替素锦照料孩子,但她承诺再替素锦撑一年。也是这一时期,章文勋开办制衣厂的计划泡汤,又开始拖欠生活费,没多久还去了越南首都西贡,也就是后来的胡志明市,留下素锦一人,身无分文。素锦这下认识到,必须自谋生路。
摆在素锦面前的生路,无非两条,一是找工作谋生,二是找男人,借谋爱而谋生。素锦两条都走了。素锦去了一家塑胶花厂打工。1957年,还处在困顿中的李嘉诚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说欧美市场对塑胶花有巨大需求,于是他前往意大利打工,学习塑胶花制造工艺,回香港地区后组织人生产,出口海外,他正是借此赚到了自己创业以来的第一桶金。而后香港市民也逐渐喜欢用逼真低廉的塑胶花来装饰房子,本土需求增大,塑胶花生产规模也随之扩大,素锦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成了一名塑胶花工人。这份工作她做到大约1961年底至1962年初。
也是在塑胶花厂,她认识了一位张先生。在1961年的一封信中,素锦称这位张先生“热心热肠,照顾我实际,帮助我实际”。1961年间,素锦被房东赶出来,她四处寻一个小房子,本在郊外找到一处,但张先生说这房子在塑胶厂上面,一旦着火,插翅难逃,他让素锦再找一处,钱不够来找他。后来在张先生的帮助下,素锦搬到了香港北角的一处大厦里。但张先生毕竟只是个小商人,只帮得了一时,没多久他就去东南亚了。
1962年,素锦又去做了高档餐厅的收银员。素锦在信中兴奋地告诉妹妹,“不得不说我运气真是太好了”。她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1962年这一年约有15万人涌入香港,用工市场竞争十分激烈。素锦既没有学历,又没有工作经验,年龄还偏大,能找到一份工作,实属幸运了。
素锦每月薪水加小费一共有两百元左右,房租就要用去一百一十五元,再买点生活用品便所剩无几了,但她还是千方百计省出钱来,给上海的家里寄过去。当时内地的食品供应非常紧张,购物得凭票。当时国家为了争取更多外汇收入,规定寄来的外汇可以领到同样金额的物资购销凭证,俗称侨汇券。素锦把钱寄给素美,素美再把钱兑成侨汇券,然后再用侨汇券去兑换物资,就这样把生活张罗起来了。
1962年底到1963年,香港整整九个月没下过雨。香港三面环海,不缺海水,但却很缺淡水,9个月的干旱更是加重了这一情况。那时候香港水务署制定了极为严苛的供水时间限制,学校为了让学生少洗澡,甚至都停了体育课。张学友曾回忆那一时期说,水龙头里的水一滴接着一滴,想装满一个漱口杯都困难。正是这次干旱,才有了东江引流入港的工程计划,简称“东深供水工程”。
素锦一边应对着恼人的缺水状况,一边又失去了工作。因为难以忍受老板娘的无端羞辱,素锦辞了职。在这个节骨眼上,章文勋回来了。越南的生意不好做,他是一无所获地回来的,拿不出一分钱来不说,每次出门,还得素锦付账。
更让素锦焦灼的是上海来信说,女儿蓼芬和儿子小庆被动员作为知识青年去新疆参与开发建设。收到信的素锦舍不得孩子去新疆,但又没办法把他们接来香港。但素锦没想到的是儿子小庆很积极地响应了下乡的号召,素锦自然担心,但也只能由他去了。小庆一走,女儿就不用走了,被安排了一个上海的工作。但不久又传来消息,小庆没去成,被调到了上海周边崇明岛上的国营农场。一波三折,素锦不断地接受这些结果,她在信里感叹说:想到做不到的事,世上实在太多了。
无助的时候,素锦会找张先生求助。张先生在1965年给过素锦一百元。其实本可以再给多一点,但恰逢香港银行危机事件,民众恐慌银行无力支付现金而发生挤兑,于是当时有限令,中外银行一律每户每日限提现金一百元港币。一起本来看似离生活很远的事情,却不动声色地影响到了每一个人的生活,这可能就是时代的“魔力”。作者百合说,没有人可以旁观这个时代,“风所过之处,人渺小如草叶,根本不可能纹丝不动。”
1966年6月5日,儿子小庆生日,素锦寄回港币二百多,并叮嘱妹妹素美,如果孩子在上海,记得给他下碗面吃。之后整整四个月,他们没再通信,直至10月24日,素锦写了一封只有四五行的信,信里只问是否安好。这一年风云突变,素锦所能说的也只有这句是否安好了。这一年,也是素锦来港的第十年,用她信里的话来说,这十年“打了一仗又一仗,有时失败,有时成功”。但也因为这一刻不停的“战斗”,素锦维持住了一份生活。如果说头一个十年是在动荡的时局下维持生活,那后一个十年,随着时局逐渐平稳,人的视野逐渐打开,生活也逐渐有了一些选择,那这个时候,素锦的生活又会走向何处呢。接下来的第二部分,我们来讲讲素锦的下一个十年。
上世纪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好转,香港地区经济随之好转。章文勋做起了玉石生意,也终于挣到了一点钱。1956年到1966年,从信件里所提及的现金数字统计,素锦一共给上海家里寄去两千六百三十二元港币。而1967年到1976年,素锦共计寄回三万三千九百元港币,折合人民币一万两千元。
这一期间的信件里聊得最多的是生活物件:素锦买了心心念念的裁缝机,素美又给几个孩子做了棉袄。大女儿想要一辆自行车,儿子想要一块瑞士摩纹表。女儿甚至与素锦在信里就买衣服的事争论起来,女儿说,“如果做姑娘的时候不穿些,难道老了之后再打扮吗?”素锦回她说,“欲无止境,做人是应该克制不能任性,养成了习惯苦的还是你们自己,一旦经济有了问题时,我看你们怎办?”但唠叨完,她还是寄了钱让女儿买衣服。
女儿蓼芬和男朋友谈了一年多,除了衣服,还得给她置办嫁妆。当时的上海,姑娘结婚的嫁妆需要四条被子、两对枕头、两条床单。素锦特地给寄了几个孩子的结婚储备金,素美用这些钱一件一件地置办起嫁妆。
在照料上海家中生活的同时,素锦也在一点一点地融入香港这个城市。70年代的香港,物质大大丰富,素锦在信中不厌其烦地描述香港食品的物价,一毫钱可以买到三块腐乳或一根油条。此外香港的公共交通也在这一时期便捷了很多,但当时的交通状况让人不敢恭维,一是经常拥堵,二是车从来不让人,素锦在信里打比方说,“过马路好像充军,要奔得快”。素锦最大的支出还是房租。70年代,香港房地产业空前繁荣,素锦在信里抱怨:“那些做房地产的人是舒服了,一层楼要卖到六七万到十几万,房地产涨价,比前二年涨一半。”
素锦在香港基本没什么社交活动,一是为了省钱,二是她不懂香港人的社交文化。比如她始终不习惯香港人的“AA制”付账,她觉得这过于现实了。此外,素锦一直对自己的妾室身份有所介怀,这令她觉得自己不宜结交朋友,她在信里说:“所谓自重,免辱也。”
1971年底,素锦的儿子小庆由崇明抽调来上海,被分配到铁路局蚌浦东站工作。素美好好为他庆祝了一番,但小庆回来也引发了一些争端。素锦离开上海前,留有一套住房,后来给了弟弟幼陵居住。但这下小庆回了,素美意识到小庆马上面临结婚成家,便提出幼陵该把房子还给小庆。幼陵因此与素美大吵一架,幼陵说素美偏心,只因得了大姐每月寄钱的好处,所以向着外甥,欺负他这个弟弟。素美说姐姐当年为了他们这些弟弟妹妹不饿死,牺牲了自己的名节,现在就该好好报答。最后只能素锦来信劝说:请幼陵替我想想,他自己也有儿子了,如果换了他又会怎样呢?望他们早日分配到房屋,叫他眼光放远点。等我将来条件好转,有能力会寄钱给他的。
房子的风波还未散去,素锦与妹妹素美之间也爆发了一场信任危机,这件事发生在1973年春节。起因是小庆向素锦去信说素美夫妇苛待了他。素锦本就对素美用钱方式有不满,看信后十分震怒,立马去信向素美发出了一连串诘问:“为什么每次寄来的合影不见小庆身影?为什么每次家庭聚餐他鲜有参加?小庆要的手表、自行车,我钱都寄给你们了,为什么还不给他买?”以及,“为什么我始终不能见到孩子的来信,述及自己的情形?究竟是他们自己不愿意来信,还是有别种阻力呢,我不明白,你们是抱有什么意思。我头脑比你们清醒,看法也有一定的见解,勿以为我麻糊不知。”
素美收到信后伤心不已,整整两夜没有合眼,极度委屈又极度愤怒。素美这么多年来之所以无怨无悔为素锦照料三个孩子,是因为素锦于她有过大恩大德。幼时家里贫困,素美被母亲送去做童养媳,是姐姐出面,上门把她领了回来,她从那时就下定决心要努力读书,将来报答姐姐。素美在给素锦的回信中,一一回应了姐姐的诘问,澄清了事实。她说:“我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地,中不愧于人,我呕尽心血为你们的子女服务了十六年,全部的金钱全部都是花在大家用上......我可以说一声我是取之于你们,用之于你们的子女。”
素锦收到信后,为了平息妹妹怒火,又回了一封长信,也是在这封信中,她第一次说到她的前半生。父亲去世那一年,她十二岁,此时元陵八岁,素美四岁,最小的弟弟幼陵才六个月大。她流着泪答应父亲要把三个弟妹抚养成人,于是她十三岁就出门打工挣钱。母亲起初狠心把元陵送进了孤儿院,之后又送走素美和幼陵,她把他们全接回来,对母亲说一家人不能分开。之后她就去做了舞女。当时很多贫寒之家的上海女儿都选了这条路。正因为做了舞女,素锦才会遇见章文勋,才有了后来的一系列遭遇,她在信里说,“如果换了现在,我肯定不会选择他”,但那时候她认命。
姐妹两人在一来一往的两封信中和解了,她们的矛盾并不大,也不特殊,甚至可以说每一个中国家庭都有过类似矛盾,它的背后是一种十分东方式的亲情关系:有不断的牺牲与回报,不断的猜忌与争吵,但同时也有不断的体恤和爱,所有的这些东西掺杂在一起,构成了我们的亲情。
1973年还不得不提的一件事是香港股灾,股市跌幅高达91.5%,历时21个月之久。那年数以万计的香港小市民因此破产,甚至自杀,当时流传一个段子说,香港精神病院里也设有证券交易所,专为因炒股票发了神经的人而设。素锦也在股市中亏了一笔,亏钱后她夜夜失眠到凌晨四点,她向女儿去信说:“没有一个不做大闸蟹,被股票绑死了”。好不容易把1973年熬过去了,谁知道又马上迎来1974年中东石油危机,香港地区原油价格两个月内上涨了四倍,石油荒导致百业废。素锦由此不得不进一步压缩生活开支,但哪怕如此,素锦也还坚持每月给家里寄钱,并且会因寄回的数目减少而连连道歉。其实她大可不必如此付出,子女都已长大成人,妹妹妹夫也都有工作,完全不需要她的接济,作者百合分析,素锦此举其实是出于一种歉意,她想尽力补偿,即使后来女儿和儿子结婚成家,她也没有停止寄钱。
1975年9月26日,素锦终于得以返沪探亲。而此行的一件大事是女儿蓼芬结婚,来之前她特地在香港地区找了算命先生,选了良辰吉日,她信里说:“我们虽以不迷信,故冲喜也为佳。”来年春天,也就是1976年4月,素锦又再次回内地,邀请妹妹和两个女儿在广州相见,好好玩了几天。
1976年3月14日,儿子小庆结婚,素锦这次没能返沪。婚前小庆与姨父闹了矛盾,他认为姨父的专制家长式作风难以忍受。素锦来信劝导说:“你要知道,在你十岁那年,我离开上海时只有数百元人民币交给他,以后有六七年没有汇过钱,你父亲失业破产已久,这段日子是最痛苦的日子。你们姐弟三人所用所吃所穿,姨父母尽了最大的努力......所以我受恩于他们,不能忘记他们,这些恩情不是我们后来好转了,寄点钱所能补偿的。”小庆收到信后很惭愧,给素锦回信说,“我的确有自私之心.......我以后再也不提以前之事。”
1976年,还有一件大事是素锦买房了。素锦早有此打算,但此前因为想让孩子们过得舒服一点,一有钱就往上海寄,于是迟迟未能买房。但眼见着自己心仪的房子从两万涨到五万,再不买恐怕一辈子都买不起了,素锦咬了咬牙付了首付,五年内分期付款还清。1976年8月28日,素锦搬进了新房子,这是她来港后第六次搬家,也是最后一次搬家。这之后素锦唯一的愿望就是骨肉团聚了。可这件事仍然不容易,这场仗她已经打了二十年,还要继续打下去。妹妹素美来信激励素锦,引用了《基督山伯爵》里的一段话,这段话是这么说的:“在抱有希望的前提下,应该有所等待。一位先哲曾告诉我们:人类的所有智慧,就是集中在‘等待’二个字,世上最最伟大的,最最坚强的,特别是最最敏慧的,就是知道怎样有所等待的人。”
素锦的信件在1976年12月戛然而止,此后的信件已无处可寻。她后来过得怎么样?她的孩子们如愿赴港了吗?她在哪一年去世?是留在了香港还是回了上海?这些我们都无从知晓了。作者百合在书的最后说,“(我们)唯一可预知的,是生活不可能一帆风顺,但总要继续,它有它的轨迹。隔着一百年的尘烟,(我们)祝福她和她的家人们。”
好,到这里,今天的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完了。
作者百合基于收藏家刘涛淘到的482封信件,勾勒出一个叫素锦的女人在1956至1976年这20年间的生活轨迹,以及沪港两地在这20年间的历史变迁。当把个人的命运与历史放置到一起,我们会发现无人能够置身于历史之外。正如作者百合在书的最后所说,“历史进程中每一次变动,都可能引起渺小个体巨大的辗转动荡。无论方向还是步伐,哪怕轻微的调整,对于被裹挟其中的普通人而言,都意味着变数,意味着不可预知也无法把控的悲欢离合,人的命运由此而成为一门玄学。”
但就算如此,素锦面对生活一刻也没气馁过。她在信中说,“(我心中)一直有一种信心,我一定要到达愿望,决不气馁”。她算不上一个大人物或传奇人物,作为一个普通人面对生活,凭靠的可能正是这点勇气和信心,这一点到今天也是如此。
好,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
当把个人的命运与历史放置到一起,我们会发现无人能够置身于历史之外。
-
作为一个普通人面对生活,凭靠的可能正是勇气和信心,这一点到今天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