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工匠》 朱步冲解读
《秦汉工匠》| 朱步冲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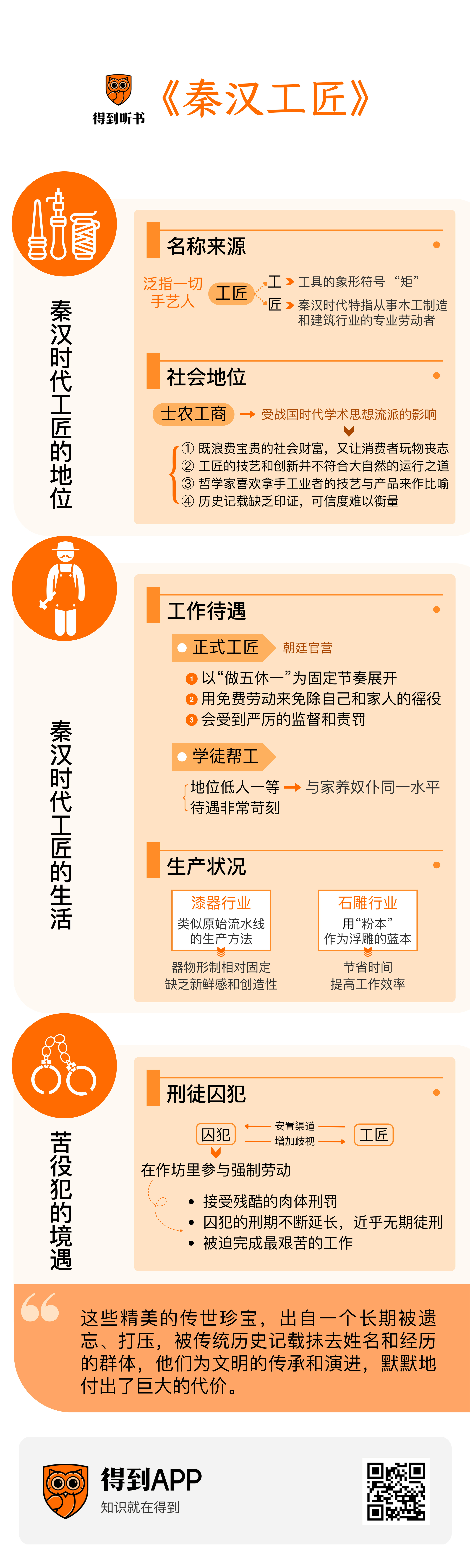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要为你讲述的书,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李安敦的《秦汉工匠》。
由于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在今天中国各地的博物馆和历史遗址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可胜数的珍贵文物与艺术瑰宝。当我们在博物馆或者田野遗址里凝视这些文物珍品时,往往会感觉到自己与中国古老的传统,或者旧日的祖先,产生了难以形容的共振与连接。
秦与两汉,被称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第一帝国时代”,统一带来了社会的稳定与和平,极大促进了古代中国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许多堪称中国文化符号象征的珍贵文物,就诞生在这个年代。在今天,我们还能在各地的博物馆中看到它们。
我们都知道,文物的使命,是承载历史,但我们现在能够接收到的历史信息,很明显是不完整的。如果我们仔细推敲,就会发现,单纯地陈列和观赏,并不能让我们完整接收到这些文物承载的信息。作者李安敦解释说,这是因为两个原因,首先,文物脱离了它原本所处的,生动而现实的生活场景;其次,我们对这些器物或者艺术品背后的故事知之甚少:它是被谁,用什么样的技术和工艺造出来的?又是如何辗转流传到使用和购买者的手上?
著名历史学者胡鸿曾说:“历史学家在关注宏大时代脉络之余,驻足体味一下那些远离历史舞台中心的普通人的人生,或许能对遥远的时代增加一份了解之同情。”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了解这些传世珍宝真正制造者的生平故事,他们运用的技术,以及在大时代中的命运,才能对这些器物所携带的历史密码,与传承的文明精神,有更加全面和透彻的了解。
在本书中,李安敦曾动情地对读者说,当我们凝视着一片汉代画像石的拓片,应该在为它描绘的传奇故事或者生动的场景赞叹之余,想到那些挥汗如雨,挥动着铁锤和凿子劳作的石匠,以及那些在噪音和粉尘里坚持作画,迅速在石碑表面勾勒出形象的画师。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各类资料的丰富,总有一天,我们能够更细致地了解这些文化遗产创造者的生活与经历。
正是在这种愿景的带动下,作者李安敦花费数年时间,完成了这部厚重的著作。他综合运用历史学、考古文献学与艺术鉴赏美学研究方法,努力还原并探讨了这些传世珍宝背后的工匠、手工业者的故事。他告诉我们,工匠,不应该被看作是默默无闻、毫无创造力,只会批量复制模仿的无名者群体,而是一个个有着自己独特经历,活生生的历史个体。
接下来,我就分三部分,为你大致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看看,工匠这个群体,在秦汉时代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其次,我们再追随着作者李安敦的叙述,以漆器和石雕两个行业为案例,来近距离观察下,秦汉时代工匠的日常生活与劳作。最后,在第三部分中,我们来关注下秦汉工匠中,因为失去自由,而境遇悲惨的刑徒,也就是苦役犯。
在本书一开始,李安敦就以一件稀世文物的身世,展开了他的叙述。这就是1968年,在满城汉墓中发现的长信宫灯。上世纪80年代初,它曾被送往美国,在大都会博物馆等展览。这座高48厘米的青铜鎏金雕塑,呈现的是一位手持灯盏,呈跪坐姿态的宫女。这位宫女神态静谧安详,左手持灯盘,右手扶着灯盏,身穿厚厚的曲裾深衣,也就是一种当时的女性正装,特点是通身紧窄,长度拖地,衣襟围绕身体盘绕,系于腰部。这位宫女的长发,则挽成发髻,以方巾包裹。
如果想了解这座艺术奇珍的身世,就需要从各种蛛丝马迹中去拼凑真相。所幸的是,负责铸造它的工匠和监管的官员,在长信宫灯上留下了九处铭文,根据铭文的信息,我们大体上能够勾勒出,它的诞生经过和使用者的信息。这盏青铜灯具,在西汉最为繁荣的时代,也就是文景之治中诞生,首先被放置在长安皇城里的长信宫里,这里居住着当时的皇后与皇太后。到了公元前150年,它又被汉景帝,或者母亲窦太后,赐给了景帝的大女儿阳信长公主,几年后,又辗转送到了公主的兄弟,中山靖王刘胜手中,最终,这盏精美的铜灯被当做随葬品,放入刘胜的妻子窦绾的墓室,并于1968年被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土。
在长信宫灯烛台的上部,有一处不起眼的铭文,是一个数字“百八十九”,作者李安敦说,这个数字可能代表某种库存或者生产序号。在当时工匠制作的上百件同款宫灯中,只有这一盏足够幸运,完整地穿越了历史漫长而幽暗的隧道。
然而,在精美的外形和无法估算的价值之外,长信宫灯的诞生,是许多工匠和奴隶付出的血汗代价。铸造它的原料,很可能来自南方的铜矿,矿坑里的矿工,大部分是毫无自由的劳动力,包括罪犯和被征发来的农民。而在长安的皇家作坊里,拥有人身自由的工匠和出身奴隶的苦工并肩劳动,最终完成了这件杰作。他们的工作环境可能并不舒适,甚至充满了危险: 例如,为青铜制品表面鎏金的工人,被称为“黄涂工”。由于金箔需要和液态水银混合在一起,涂抹到青铜器表面,再放置于低温环境下烘烤,所以肯定有相当数量的工人,都会因为水银中毒而短寿。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手工业的从业者,常常简称为“工”,工这个汉字的起源,是工具的象形符号,很可能是木匠手中的曲尺,叫“矩”,“规矩”的那个矩。 另外,匠这个字的起源,则是一把放在容器中的斧头。作者李安敦考据说,匠这个字,在秦汉时代,特指从事木工制造和建筑行业的专业劳动者,而如果把工和匠连在一起使用,那么“工匠”,就是泛指一切手艺人,这个用法一直沿用到今天。
那么,在秦汉时代,辛勤劳作,不断为整个社会制造各类生产消费品的工匠,他们的社会地位是怎样的呢?可能大家也听过一种说法,一种按照身份等级从高到低的排行,叫“士农工商”。什么意思呢?就是除去尊贵的皇室贵族和官员,以及低贱的囚犯和奴隶之外,那些拥有自由身份的平民百姓,按照他们的职业,被分成了这样四个等级。出身贵族或者富裕之家,但由于身处家族旁系,只能通过努力读书,出人头地,去担任官职的男性,就是士;接下来分别是在土地上辛苦劳作的农民、从事手工业的工匠,以及商人。
为什么工匠地位相对低贱?原因有很多。其中可能包括战国“百家争鸣”时代,一些学术思想流派的影响。比如无论儒家还是法家,都坚持认为,农业是社会稳定与存在的基础,因为它关系着全体社会成员的口粮供应,也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而且,从事农业,也可以把人牢牢固定在土地上,便于行政管理;所以,农业人口越多,国家的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就越有保障。
反过来说,从事手工业的工匠,他们的形象,总是与迁徙和城市密切相关,而城市,固然一方面意味着经济的繁荣,但同时也表明,脱离农业生产和国家税收系统的人口在悄然增长;更重要的是,受到高额利润驱动的工匠,会不惜时间工本制造各种精巧昂贵的奢侈品,既浪费了宝贵的社会财富,又让消费者,尤其是皇帝和贵族穷奢极侈,玩物丧志。比如,东汉著名思想家、文学家王符就提出,任何行业,都有各自的“本”“末”,具体来说,工匠之本,在于为老百姓制造物美价廉的生活生产必需用品,那些材料昂贵、工艺繁复、实用性不大的器物,只能是“末”。
为了证明这一点,作者李安敦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我们也许听说过,在古代,技艺高超的工匠,有时也会被称为“巧匠”,但巧这个字,同时含有褒义和贬义。首先,巧代表了技艺的高超、聪慧的心灵,以及创新发明的能力;但同时,巧也可以用来形容利用诡诈的手段和言语,来实行欺骗和操控的能力,比如成语中的“花言巧语”和“巧言令色”。甚至,道家哲学的创始人老子,直接把这两种能力看做一个硬币的两面,声称,工匠的技艺和创新并不符合大自然的运行之道,如果人人都对它加以追求崇拜,那么人内心淳朴的道德就会被破坏。
然而,有趣的是,战国到秦汉时代,诸子百家中的许多哲学家,在讨论政治、哲学、宇宙之道时,却非常喜欢拿手工业者的技艺与产品来作比喻,比如庄子的庖丁解牛、韩非子的自相矛盾等等。
当然,在当时的官僚与士大夫中,尊重商品经济规律,思想开明的人也并不是没有。比如《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就提出,农工商各个行业,在社会经济运转中相辅相成,只有分工的不同。手工业和商业,是贫困的普通老百姓能够改善自身经济状况的重要途径。 比如《西京杂记》里就记载一条逸闻,说西汉中期,河北钜鹿有个纺织巧匠陈宝光,把他的技术传给了自己的妻子。后来,陈宝光之妻因为手艺精湛,被当时的大将军霍光招揽到自己的府邸里,六十天就可以织好一匹精美的绫,价值能卖到一万枚铜钱。
在普通人看来,提到中国古代的工匠,想到的往往只是一个面目模糊的群体,他们勤劳智慧,富于想象力,仅此而已。确实,由于工匠的社会地位不高,所以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凭借登峰造极的成就和手艺,在历史典籍中留下只言片语的记载。然而,这些记载由于过分零散,缺乏印证,又掺杂了民间传说,可信度难以衡量。比如,汉代曾经有一位大师级别的能工巧匠,叫丁缓,据说他曾经营造了长安皇宫中壮丽的大殿,昭阳殿;流传到今天的汉代珍宝,未央宫博山炉,据说也出于丁缓之手。丁缓最天才的发明,据说是一件神奇的“被中香炉”,这种香炉可以放在被褥中,但无论如何转动,都可以直立不倒,原理可能是有一个复杂的平衡吊环装置,被放在香炉内部。
根据作者的推测,丁缓可能供职于汉代宫廷中两个和工程与奢侈品制造相关的部门,黄门或者尚方。黄门的原意,是皇城中通向皇帝后宫私密区域的大门,由宦官掌管,宫廷里的乐队、舞蹈杂耍艺人,以及御用诗人和画家,都属于这个部门。而尚方,则是皇城内的宫廷作坊,位于皇城的西北区域,同时负责为宫廷制造精美的奢侈品,以及管理从事巫术占卜的术士。
然而,记载丁缓事迹的文献,是诸如《西京杂记》这样的笔记小说,内容有很多夸大和想象。甚至连丁缓生活的年代都无法统一,一会儿说他活跃在西汉汉武帝时期,一会儿又说他活跃在东汉时期;不仅如此,他的名字一会儿被写作丁媛,一会儿被写作丁护或者丁绶,这很可能是早期文献在持续的传抄中,造成的失误。
那么,秦汉时期的普通工匠们,他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呢?由于历史的久远,和文献资料的欠缺,我们只能通过壁画、浮雕和墓葬中的陶土模型来想象。比如,在洛阳附近的一座东汉墓葬里,发现过一件酿酒作坊的陶土模型,这间作坊三面有墙,临街的一面敞开,方便交易。作坊里摆满了桌案、酒壶、水罐,用来加工材料的臼与杵等工具。在秦汉时代,私人手工作坊逐渐集中在城镇繁荣的商业区,比如在秦朝首都咸阳出土的陶器上,有制造作坊盖的戳记,就多达40种,标明作坊的位置和制造人的姓名,其中多数都显示,这些作坊的位置,都集中在咸阳市区中的某个“里”,也就是街区。
一般来说,如果某个人,立志想成为工匠,那么他首先要进入朝廷官营或者私营的手工作坊当学徒。根据当时的法律,学徒的培训期长达两年,掌握所需的技艺,产量达到了熟练工的标准,才能获得正式的工匠资格。
虽然在秦汉文学家和官员的批评中,手工业是一份清闲又赚钱的职业。但实际上,作坊里的工匠和他手下的学徒、帮工,和田野里的农民一样忙碌。秦汉时期,管理官办作坊的官员,和朝廷中的其他同僚一样,每工作五天就会休息一天,所以我们也可以进行推测,官办作坊里的工匠的日常生活,也以“做五休一”为固定节奏展开。
由于季节变化带来的日照时间不同,工匠每天的工作时间也会按照时令有所调整。比如,冬季每天的工作时间就会明显少于夏季。而在私营作坊里,由于营利的压力,工匠们的工作时间就可能更长,不过,根据秦汉法律,商业贩卖活动必须等到晌午才开始,所以从晌午到日落,才是他们工作量饱和的高峰时段。
官营作坊里的工匠,很多是来自民间的从业者,根据秦汉两朝法律规定,有特殊手艺才能的工匠,每年可以通过在官方作坊里劳动,或者把一部分产品贡献给国家,来免除自己和家人的徭役。作者计算说,每年12个月里,秦汉两朝的工匠们都大概要为朝廷免费工作一个月。
在官营手工作坊里,工匠的工作不仅繁重,还会受到严厉的监督和责罚,例如,根据秦代法律,如果产品抽检时不合格,那么负责的官员和工匠都要被处以沉重的罚款,负责人要承担的罚款,相当于一套盔甲,副手和工头承担的罚款,约等于一面盾牌,工匠的罚款相当于20条络组,也就是甲胄上用于缀连甲片的带子。千万不要觉得这笔钱是个小数目,根据战国末期至秦代的物价与购买力,一副甲胄的价格是1344枚铜钱,而一面盾牌的价格是384个铜钱,分别是一户普通人家一年和一个季度的净收入。
比起正式的工匠,秦汉时代作坊里的帮工和学徒的待遇如何呢?虽然没有具体的文献资料,但是根据后世,唐宋至明清时代的法律规定,帮工和学徒的待遇,应该与家养的奴仆处于同一水平,地位低人一等,待遇非常苛刻。例如,有个叫窦广国的少年,由于家庭负债,儿童时期就沦为了债务奴隶,在山里的烧炭作坊中起早贪黑地辛勤劳作。有一天夜晚,山里暴发了泥石流,瞬间吞没了工地上的所有人,只有他逃出生天。当然,窦广国之所以能在历史文献中留下这些记录,是因为在此之后,他的命运发生了180度的改变:窦广国的姐姐,成为汉文帝的皇后,而自己也一步登天,被封为章武侯;据说,即使在成为贵族之后,窦广国也依旧没有忘记早年的辛酸记忆,常常规劝皇帝,要爱惜民力,轻徭薄赋。
说到这里,就让我们跟随作者李安敦的描述,来到秦汉时期的重要手工业产业,漆器行业和石雕行业,来看看当时手工业者的日常生产状况。之所以选择这两个行业,是因为有相当丰富的漆器与石雕文物存留到今天,从而能够让我们相对了解它们的制作工艺和从业者生活状况。
所谓漆器,就是以软木或者层叠的麻布为胎体,层层涂上漆料,表面描绘纹彩而制成的日常生活用具,比如杯、盘、碗等等,由于工艺复杂、费时费力,所以在当时是上层贵族才能使用的奢侈品。
首先,工匠们要在胎体上涂抹一层比较厚的黑漆做底,然后再抹上几层薄薄的清漆,为表面的彩绘做准备,一般,器物内侧的涂色是红色,而外部的底色是黑色。最后,彩绘工匠会在底色上绘制各种各样的图案作为装饰,一些名贵的作品还会在手柄等部位安装鎏金或者鎏银的青铜镶边。
由于秦汉时代的繁荣,社会对漆器的需求迅速增加,所以我们聪明的老祖先,就发明了一种类似原始流水线的生产方法,那就是在制造器物时,每个工匠只负责处理某一道固定的工序,这样不仅能保证器物的形制相对固定,形成比较高的生产率,还能保证,那些数量有限的熟练工匠,能够把全部精力用来干他们最拿手的事情,比如画图案。
在秦汉时期的官营作坊里,为了满足质量检测标准,所有的漆器纹样都趋于标准化,然而副作用就是,官营作坊制造的器具,图案一成不变,甚至逐渐呆板,缺乏新鲜感和创造性。
1981年,在湖北云梦县,一批秦汉之交年代的古墓被发掘出土,文物中包括几十件漆器,根据器具上的铭文,它们都来自遥远的秦国首都咸阳,而其中相当一部分,则出于一位名叫“骜”的女工。
骜的全称,叫“大女子骜”。在秦国法律中,所谓“大女子”,就是指15岁以上的女工,她的工作应该是在漆器表面描绘图案。在所有“骜”负责制作的器物中,有一部分具有官方作坊的印章,这说明,骜自己平时可能在一处私营作坊里工作,而在每年的固定时段里,还要被征调到朝廷下属的官办作坊里服徭役。正如刺绣一样,在漆器表面绘画是一项复杂而精细的工作,在当时的人眼里,细致耐心,手指更纤细灵活的女性,似乎更适合做这项工作,所以漆器工坊里的女性,比其他行业比例都要高。
不过,秦汉时代作坊里的女性,并不是只能从事这种繁重的体力工作。根据出土漆器的铭文显示,在公元前85年,四川的一处官办漆器作坊里,出现了一位女性管理层。这位叫“母夷”的妇女,在作坊中担任“令史”,用今天的话说,负责公文誊写和会计事务,需要很高的读写能力;作者推断说,“母夷”可能在作坊里担任工匠多年,最终因为经验丰富,还学会了读写,而最终被提拔到这个位置上,而这,已经是漆器行业中女性能够达到的职场天花板了。
说完了漆器,我们再来看看石雕,由于汉代经济繁荣,社会文化生活丰富,崇尚厚葬,所以有大量精美的建筑石碑和墓葬石雕传世。在石材从采石场抵达建筑现场的作坊之后,工人会借助木工的曲尺,把它切成一块块的方形,并开始打磨表面。随后,画师会用笔墨在石材表面划分区域,并勾勒出图像的基本轮廓,石匠就沿着画师的草图,把图像和边缘装饰刻成浅浮雕,最后再加深一次浮雕上人物和其他器物的轮廓。最后,当这些浮雕石砖被安放进墓室后,负责上色的工匠会把这些浮雕涂上鲜艳的色彩,就算大功告成。
为了节省时间,石匠和画师往往会使用已经设计好的套图,来作为浮雕的蓝本,这种套图被称为“粉本”,在后世中国的传统美术设计里,粉本也被用来快捷地绘制壁画和其他建筑纹样。
不过,最不幸的,是作坊里参与强制劳动的罪犯,也叫刑徒。一旦产品出现质量问题,直接遭遇的是残酷的肉体刑罚,杖责50到100下。
在本书中,作者李安敦告诉我们,秦汉时期,手工业从业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失去自由的囚犯。这个群体的存在,和工匠社会地位的低下,形成了某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也许正是因为工匠是一种相对低贱的职业,所以成为安置囚犯,榨取其劳动力的渠道。反过来说,由于手工业中充斥着奴隶和囚犯,所以让整个从业者阶层,也都在秦汉时代,受到了歧视。
秦朝统一后,所谓的“秦政”,也就是法家思想主导的君主专制,很快就暴露了它空前的残酷性:尤其体现在刑罚的滥用,以及对民众劳动力资源的榨取上。根据统计,秦朝初年,人口大约是两千万,但其中被征发、参军戍边、强制劳动的,就多达三百万,其中因触犯律法而沦为苦役犯的,也有将近百万之多。
众多的刑徒囚犯,等待他们的是多达数年,乃至十年以上的沉重体力劳动。包括手工作物、土木建筑、放牧牲畜,而他们配给的衣食物资,质量粗劣,数量稀少。比如,根据秦朝法律规定,从事强迫劳动的男性成年囚犯,每餐的粮食供应是三分之一斗,换算成今天的度量衡,只不过折合小米0.6公斤左右,这点粮食在去壳后,大约只能剩下原重量的60%。在没有其他辅食的情况下,这些粮食提供的营养,根本不能支撑人完成日复一日的强体力劳动。
更糟糕的是,囚犯自己身上的囚服,也要自己负担。根据秦代法律规定,囚犯每天劳动报酬为六个铜钱,春夏天的单衣,每人要55个铜钱,冬天的冬服,每人110个铜钱。从而导致这些苦役犯不得不向官府赊账贷款购买囚服遮体,这些欠款也必须用更多的苦役劳动来偿还,从而让许多囚犯的刑期不断延长,近乎无期徒刑。
当然,理论上,刑徒或者奴隶也可以通过在战场上立功而摆脱这种苦难的命运:比如,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竹简中,就记载着这样一条法律,如果一位奴隶工匠想获得自由之身,可以通过参军并斩获一个敌人的首级来实现,或者由参军的家人或者朋友通过把自己的斩首军功转让给他。
很多人以为,西汉建立后,这种骇人听闻的状况得到了改善,理由是刘邦进入关中地区后,和老百姓“约法三章”,彻底废除了秦代苛刻而繁复的法律条文,然而真实情况并不是这样。根据统计,汉代的法典“汉律”中,记载了超过1800多种罪名,而苦役劳动,依旧是最常见的处罚,刑期依旧在四到六年之间。和秦代一样,这些刑徒会遭受剃去头发、脸上刺字、套上铁枷锁的待遇,去从事修造宫殿和皇帝陵墓,开采铜铁矿、铸造铁器、煮盐等繁重劳动,日常饮食待遇,也和秦朝没什么区别。
在今天河南郑州郊外,散布着许多汉代铁矿开采和冶炼工厂的遗址。这里最艰苦的工作都是由刑徒来完成,比如向熔炉里倾倒矿石和木炭,鼓动风箱,确保熔炉的温度,最后再把沉重的铸铁块搬运到指定地点准备加工,甚至要冒着危险的高温,进入损坏的高炉内部,取出附着在内壁上的铁块。
这种漫长而痛苦的强制劳动,让大部分刑徒陷入绝望的境地。根据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孔融的奏折,在服刑期间,刑徒的死亡率可能高达10%。在绝望中,很多刑徒选择拼命祈祷,希望皇帝能够大赦天下,让自己获得自由,至少缩短刑期。作为证据,在郑州冶铁工坊出土的陶器上,可以看到使用它们的刑徒悄悄刻下的铭文,其中经常出现的,就有“大赦”两个字。
好了,这本《秦汉工匠》的基本内容,就大致为你介绍到这里。作者李安敦从一件件秦汉时代传世的珍宝为切入点,通过解读镌刻在器物上的铭文,以及相关文献资料,努力一点点拼凑出2000年前,秦汉时代手工业从业者的真实生存与劳动状况。
通过叙述,我们知道,这些用自己的天分和汗水制造出各类生活生产必需品和传世瑰宝的匠人,由于传统中国社会以农为本思想的偏见,在秦汉时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都受到了极为不公正的歧视和打压。由于脱离了土地与农业生产,他们被统治阶层认为是不安定因素,助长了奢侈浮华,以及投机取巧等社会不良风气。更有甚者,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阶层,手工匠人们都被官方历史文献记录有意识地遗忘、忽略,导致今天的我们,只能依托传世器物上的少数铭文和各种只字片语的记载,才能拼凑出少部分资料,来了解他们的故事和经历。
秦汉时代的统一和繁荣,对手工业技术的发展和繁荣,毫无疑问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然而,一些负面因素,也在这种兴盛的局面中悄悄酝酿。作者李安敦在书中说,秦汉官僚帝国成立后,加强了对底层人民的管制,手工业者再也不能像春秋战国时代那样,自由地迁移游历,这就极大妨碍了技术的传播与交流。同时,官营手工业处于垄断地位,对各种产品提出了繁复而死板的标准,让工艺的改良从此逐渐陷入停滞。
不仅如此,手工业者还面临着沉重的赋税,税额明显高于其他阶层,这同时进一步妨碍了资本的积累,多数私营手工业者难以通过积累资本而扩大生产,始终处于一种朝不保夕的地位,难以承受经营风险。而中国古代传统的家族继承制,又让技术与手艺的传承变得非常脆弱:事实上,我们从典籍记载中可以发现,无数精巧的技术曾经失传,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部分会幸运地被后人再次发明或者发现,例如丁缓的平衡香炉,据说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被另一位巧匠“房风”发明过,所以丁缓的成就严格来说,是“重新发明”。这种周期性的损失,也严重减缓了技术积累与进步的速度。
所以,作者李安敦在本书结语中说,在知晓了这些故事之后,希望读到这本书的人,在博物馆里,能够把目光放远到物质之外,能够意识到,这些精美的传世珍宝,出自一个长期被遗忘、打压,被传统历史记载抹去姓名和经历的群体,他们为文明的传承和演进,默默地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此外,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
当我们凝视着一片汉代画像石的拓片,应该在为它描绘的传奇故事或者生动的场景赞叹之余,想到那些挥汗如雨,挥动着铁锤和凿子劳作的石匠,以及那些在噪音和粉尘里坚持作画,迅速在石碑表面勾勒出形象的画师。
-
作者李安敦在本书结语中说,在知晓了这些故事之后,希望读到这本书的人,在博物馆里,能够把目光放远到物质之外,能够意识到,这些精美的传世珍宝,出自一个长期被遗忘、打压,被传统历史记载抹去姓名和经历的群体,他们为文明的传承和演进,默默地付出了巨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