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铁卢》 朱步冲解读
《滑铁卢》| 朱步冲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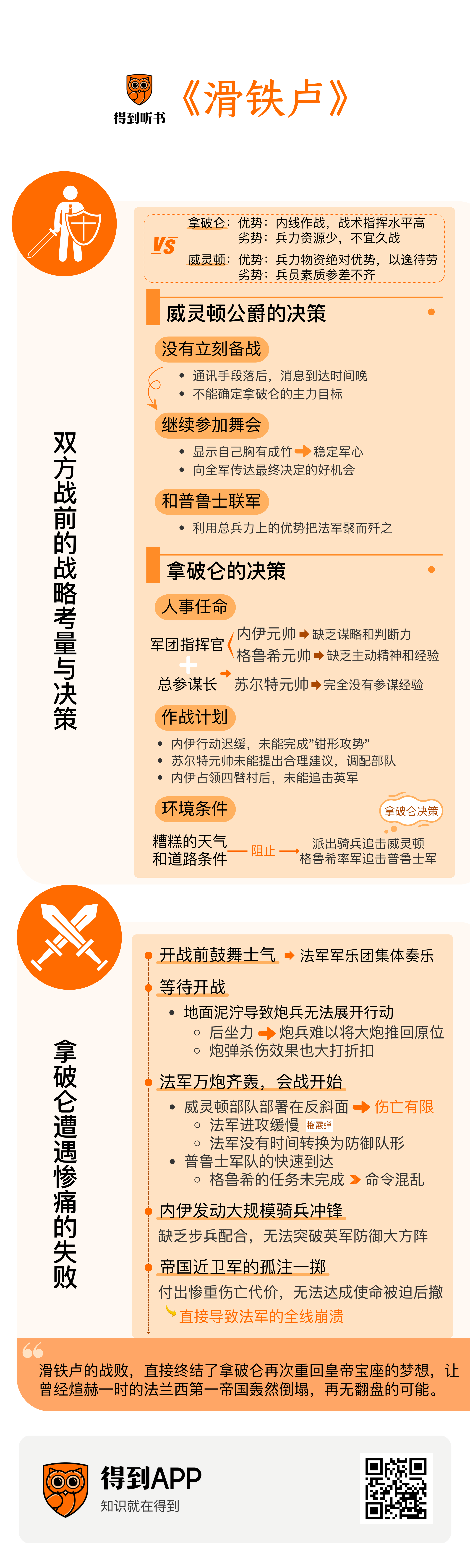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要为你讲述的书,是英国历史学家与文学作家伯纳德·康沃尔的《滑铁卢》,副标题叫“四天、三支大军和三场战役的历史”。
一看这个标题,爱好历史和军事题材的朋友估计就知道,这是一本关于拿破仑生平最后一战,滑铁卢战役的著作。滑铁卢战役是军事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战役之一,它彻底终结了拿破仑征服欧洲的梦想,欧洲各强国自此进入了一个保守势力复辟,互相制衡,但大体和平的时代。而维持这种制衡与和平的外交政治体系,也来源于欧洲各大国为了反对拿破仑而组织的政治军事联盟,史称“维也纳会议体系”。
甚至,“滑铁卢”这个地名都已经破圈,变成了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专用名词。当我们在媒体上看到“遭遇了滑铁卢”这样的标题时,就能立刻明白,某个人物、公司或者产品技术等等,遭遇了“惨痛的失败”,“功亏一篑”。
关于滑铁卢之战,拿破仑的军事政治生涯,乃至他创立的法兰西第一帝国对于欧洲,以及世界的冲击与影响,相关的研究著作已经不可胜数。但是,今天为什么我们还要读一本关于拿破仑和这场战役的著作呢?我个人觉得有两个理由:首先,作者康沃尔把历史学家的严谨,资料收集能力,和作家细腻观察,塑造戏剧冲突的天赋结合在了一起。在他的笔下,从拿破仑、威灵顿公爵这样的历史大人物,到参战的各军将领,乃至普通一兵,都是有血有肉的个体;他们的一举一动和思绪,被康沃尔一一复活,然后摆上舞台,供我们鉴赏。
其次,拿破仑的失败,既要归咎于历史的必然性,也是双方每一个具体决策和行动积累导致的结果。由于本书的时间跨度,被限定在滑铁卢战役短短的四天之内,所以,我们可以像用放大镜一样,近距离观察拿破仑、威灵顿公爵这样雄才大略的军事家、政治领袖的每一个“微操作”。这对今天我们提升认知思维能力有什么用处呢?我自己觉得,今天的互联网社会,是一个形势瞬息万变,各种信息数据向我们奔流而来的环境;如何排除信息噪音和自己内心的认知偏差,同时兼顾局部和长期决策最优,是一项长期任务。我们今天需要做出的决断,一点不比二百年前的拿破仑、威灵顿公爵简单多少;所谓“以史为鉴”,说白了就是,复盘以往的经典案例,修正我们今天的策略。在接下来的讲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被誉为百年一遇的天才统帅拿破仑,是如何在极度自信和路径依赖中,犯下了一个又一个决策失误,最终迎来了毁灭性的失败的。
接下来,我就分两部分,为你介绍本书的大致内容:首先,我们来看看,拿破仑指挥的法军,以及威灵顿公爵指挥的反法同盟联军,双方在战前的态势、战略考量与决策。其次,我再顺着作者康沃尔的叙述,带大家走进1815年6月18日,滑铁卢战役发生的当天,来目睹拿破仑如何遭遇了一生中最为惨痛的失败。
本书作者康沃尔的叙述,开始于1815年春天:随着拿破仑宣布退位,被流放到地中海的厄尔巴岛,欧洲大陆似乎恢复了和平。此时,一位在欧洲军界享有盛誉的英国贵族,受命出任英国驻法国大使,他叫阿瑟·韦斯利,被封为威灵顿公爵。在漫长的拿破仑战争中,公爵曾经率领反法同盟的军队,在西班牙和法军交战多年。随着1814年反法同盟联军的胜利,威灵顿公爵也有了解甲归田的心思,不过本着强烈的责任感,他依旧决定前往巴黎上任。
在欧洲大陆登岸后,公爵一行穿越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准备进入法国国境,沿途的地形平缓开阔,风景美不胜收。不过,威灵顿公爵出于职业军人的本能,在行进中,依旧在用军事地理学专业眼光,打量着眼前的一切。
在今天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以南,约15公里的地方,威灵顿公爵注意到了一片特殊的地形,在法国通向布鲁塞尔的必经之路,尼维尔公路上,横亘着一道山岭,被称为圣约翰山,周围是麦田和风车磨坊。在圣约翰山南边的山脚附近,从西到东,有两座农庄和一个小村落;两个农庄的名字,分别叫乌古蒙和拉艾圣,它们都有坚固高耸的石墙,房屋也是用坚固的条状石头砌成的。于是公爵立刻想到,如果有朝一日,战火再起,法军从南面直扑布鲁塞尔,那么这道山岭就是最好的防御阵地,两个农庄也可以被改造为阵地外围的据点,互相支援,如同一个三角形。在越过圣约翰山之后,威灵顿公爵一行来到了一座繁华的小镇,这里有巍峨的教堂,还有很多家热情好客的客栈,为了记住这个地点,公爵曾打发下人向当地居民询问,得知,这里叫滑铁卢。
写到这里,作者康沃尔充满诗意地说,威灵顿公爵肯定想不到,这个小村庄会把自己送上历史舞台的巅峰,也会永远留在自己的记忆里。
3月1日,不甘心蜗居小岛的拿破仑率领1000名士兵,从法国东南部的儒昂湾悄然登陆,20天后就兵不血刃地顺利抵达了首都巴黎。
拿破仑违背协议,重返欧洲政治舞台,瞬间让所有反对者摒弃前嫌,重组了反法同盟。还在维也纳开会,构思欧洲未来政治秩序的英国、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代表,迅速达成共识,各自出兵十五万,彻底打败拿破仑;而在会议现场列席的威灵顿公爵,则临危受命,迅速前往比利时,指挥那里的英国与荷兰联军。各国政治领袖,都把公爵看作打败拿破仑的绝佳人选,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甚至直白地对他说:现在,就指望阁下拯救世界了!
拿破仑深刻了解,自己的统治地位是否稳固,完全取决于自己能否在战场上赢得胜利。法国民众对依靠外国军队复辟的路易十八,没有什么感情,但也不会接受一个打败仗的自己。于是,拿破仑看着地图,迅速开始了评估:自己有内线作战的优势,可以对反法同盟的联军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俄国和奥地利两国虽然已经出兵42万,但是动作迟缓,尚在莱茵河地区,距离法国东部边境还远;而且由于通信技术落后,没办法彼此呼应,协调行动。但是,反法同盟,在毗邻法国北部边境的比利时,还有两支大军:在威灵顿公爵麾下,是9万多英国、荷兰、比利时联军;而另外一支,是布吕歇尔元帅统领的12万普鲁士陆军。所以,拿破仑的理想战略,就是兵贵神速,首先北进,杀入比利时境内,先把英国与普鲁士军队分割开,各个击破,再回头慢慢和俄军、奥军周旋。
然而,拿破仑心里也清楚,自己必须胜利,而且要速胜,因为自己的劣势也很明显,毕竟兵力和资源严重不足:虽然拿破仑在回国后,迅速整军备战,恢复了义务征兵制,同时要求在自己麾下服役的老兵重新入伍报到,但能够跟随自己进入比利时作战的士兵,也不过12.5万人。
兵力和物资处于劣势,已经让拿破仑头疼;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那些随着拿破仑20多年,东征西讨的名帅猛将,许多已经离自己而去;有一些已经战死于沙场,比如忠心耿耿,英勇的拉纳元帅,在1809年的阿斯佩恩·艾斯林会战中牺牲;冷静,擅长指挥骑兵的贝西埃元帅,1813年在吕岑战役前夕阵亡;而另一些拿破仑倚仗的高级指挥官,则因政见不同,拒绝为他效力:例如,还在当打之年的乌迪诺与麦克唐纳元帅,他们认为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偷偷潜回法国复辟,是背信弃义之举。
然而,其中最惨痛的损失,当属法军曾经的总参谋长贝尔蒂埃。贝尔蒂埃虽然不是果断的战场指挥官,但他精细、稳妥,能够迅速理解拿破仑的意图,把拿破仑的只言片语,转化为优质而详细的作战计划。拿破仑登陆后,贝尔蒂埃却没有前来投靠,而是选择跟随路易十八一起流亡。随后,这位天才的战术大师,在1815年6月1日,也就是滑铁卢之战开战前17天,在自己的庄园里不慎坠楼,当场去世。有谣言说,贝尔蒂埃当时又起了追随拿破仑的心思,所以被法国保王党狂热分子暗杀,伪装成事故。无论如何,据说拿破仑在兵败滑铁卢后,曾感叹:如果贝尔蒂埃依旧在自己身边,那么这次惨败就不会发生。
所以,拿破仑在指挥自己的12.5万大军扑向比利时的时候,他发现,为了有效作战,自己需要至少两位独立的军团指挥官,分别对付英军和普鲁士军队,以及一位统筹协调全局的总参谋长。无奈之中,拿破仑任命苏尔特元帅作为总参谋长,内伊和格鲁希元帅,分别为法军左翼和右翼指挥官。很多军事历史学家评论说:拿破仑在滑铁卢的失败,是由一系列战场内外的错误决策积累而成的,而这个人事任命,首当其冲。
苏尔特元帅,虽然是个一流的战场指挥官,但完全没有参谋经验,直接导致法军内部的情报处理和军令传递,变得混乱而迟缓。而内伊和格鲁希呢,也不合适被提拔到这个位置。内伊因为勇气超群,被誉为“勇士中的勇士”,但他缺乏谋略和判断力,不适合出任独当一面的指挥官;而格鲁希呢,是新近被晋升为元帅的,没有大兵团的指挥经验;在指挥风格上也比较保守,缺乏主动精神。
不过,拿破仑当时虽然缺兵少将,其实还没有沦落到“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的地步。比如,法军元帅里,被认为综合能力排名第一的猛将,达武元帅还在。但是,拿破仑却没有让他加入大军,一起北上,而是任命达武当战争部长,替自己坐镇巴黎。明智的达武曾苦劝拿破仑,说巴黎,乃至法国的局势稳不稳,全看拿破仑在战场上是否能获胜,谁在巴黎坐镇当代理人,其实不太重要。然而,拿破仑并没有接纳达武的意见;另外,法军中还有一位名将,絮歇元帅,他又有参谋和行政管理经验,又曾长期独当一面;但此刻,拿破仑却任命他去当法国东南部地区的军事总指挥,应对俄罗斯、奥地利的威胁。一些军事历史学家说,拿破仑其实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如果让絮歇担任总参谋长,再让达武和苏尔特分别担任两翼指挥官,拿破仑自己带着预备队坐镇在后,那么单独一场滑铁卢战役的胜负,真的是还未可知。
让我们再把目光,投回到1815年6月15日的比利时:在布鲁塞尔,威灵顿公爵和麾下的盟军军官,以及当地的名流显贵,在当天晚上,参加了一场盛大奢华的舞会。军官们笔挺的制服,华丽的勋章和绶带,与女士的珠宝晚礼服,交相辉映。然而许多人不知道,仅仅24小时后,一场血战就将来临,他们中间的不少人,也将喋血沙场。因为当天早些时候,兵贵神速的拿破仑已经率领大军,渡过了法国和比利时边境的桑布尔河,直指布鲁塞尔而来。
看到这里,你肯定会问,威灵顿公爵怎么还在花天酒地,不认真备战?实际上,由于通信手段落后,法军进入比利时的情报,到了15日下午才送到威灵顿公爵手里。威灵顿公爵之所以没有立刻召集将领开会,集结兵力,是因为他还不能判定,拿破仑的主力,到底剑指何处;另外,继续参加舞会,还有两个好处,首先显得自己胸有成竹,可以稳定军心;其次,大多数高级军官都会参加舞会,所以反而是个向全军直接传达自己最终决定的好机会。
说到这里,想提醒大家的是,19世纪初打仗,由于没有机械化的交通工具,一支军队的行军路线,必须严格沿着现有的道路网前进;毕竟大炮和辎重补给前进,都靠马车,离开了公路可以说寸步难行;所以两军对阵,谁抢占了重要的交通枢纽和附近的有利地形,谁的赢面就大。于是,拿破仑、威灵顿公爵和布吕歇尔,三位主将摊开地图一看,心里已经对彼此的作战计划有了大概的了解:拿破仑要想打赢,就必须把英普两军分割开来,各个击破;反过来呢,威灵顿公爵和布吕歇尔,一心想的是赶紧“抱团”,连成一片,这样就可以利用自己总兵力上的优势,把法军聚而歼之。
为了达成各自的目标,小镇滑铁卢和圣约翰山以南的两个小村庄,西边的四臂村和东边的利尼村,就成了双方的必争之地。因为这两个村子,都是几条关键道路的交叉口,威灵顿公爵指挥的英军,要想去支援位于自己东南边的普鲁士军队,必须经过四臂村;同样,如果普鲁士军队失去利尼村,那么再想和滑铁卢一带的英军会师,就必须向东北方向绕一个大圈子,从而暂时远离战场,让英军承受大部分压力。所以,从6月16日到17日这两天,法国军队的左翼和右翼,分别在这两个小村子,与英军普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这两场战斗,可以被看作是6月18日滑铁卢之战的序幕。
表面上看,法军在这两场战斗中,都获得了胜利,英普两军遭受的人员和装备损失,也比法军大。但是,拿破仑作战计划中的一些重要目标,并没有达到,而且还为18日的最后决战,埋下了致命的隐患。
首先,左翼法军指挥官内伊,行动迟缓,没有果断出击,导致英军能够向四臂村不断派出援兵,内伊在这里被拖住了几乎一整天。然而,按照先前的作战计划,内伊如果迅速占领了四臂村,就应该率兵赶紧增援右翼的格鲁希,双方合兵一处,把利尼村的普鲁士军队打垮。所以,内伊拖拉的结果就是,拿破仑苦心设计的“钳形攻势”没有完成,普鲁士军队虽然遭遇重创,但并没有分崩离析,而是从容撤退北上,去和威灵顿公爵的英军会合了。
其次,苏尔特元帅领导的参谋部,本该从战场全局出发,向拿破仑提出合理的建议,调配部队,但他没有做到。在战斗当天,法军一支主力部队,埃尔隆伯爵的第一军,在四臂村和利尼村之间来回折腾,根本没能投入任何一边的战斗;这是因为,埃尔隆伯爵不断接到了来自拿破仑和内伊自相矛盾的命令,都要第一军去支援自己。
最糟糕的是,内伊好不容易占领四臂村之后,居然决定全军休整,眼睁睁地看着打了败仗的威灵顿公爵带领英军从容撤退。作者康沃尔在书中写道:6月17日,当拿破仑赶到四臂村,发现内伊居然按兵不动时,他生气地咆哮说:“你毁掉了法国!”
耽误到这个份上,拿破仑也只能亡羊补牢了,他派出骑兵追击威灵顿公爵,同时命令格鲁希率领3.3万人,也就是自己全部兵力的三分之一,去追击普鲁士军,阻止他们和威灵顿公爵会合。然而,天公不作美,下起了倾盆大雨,整个滑铁卢周边地区变成了一片泥泞的海洋。糟糕的天气和道路条件,有效地阻止了法军的追击行动,同时也为滑铁卢战役的胜负,再布下了一枚决定性的棋子。
17日深夜,拿破仑从自己的侦察兵那里得到消息,威灵顿公爵并没有逃往布鲁塞尔,而是在北面远处的圣约翰山重新布阵;于是,拿破仑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决定在第二天,也就是6月18日,在这里打一场决定性的会战,歼灭英军。毕竟,在反法同盟里,英国是领袖,还是最大的金主;一场战场上的惨败,可能就会让当时的强硬派英国内阁倒台,同意接受外交谈判,直接导致反法同盟土崩瓦解。
当6月18日的太阳冉冉升起时,以圣约翰山为中心,大约8平方公里的地区内,15万大军在此集结,准备决一死战;这是战争史上重大会战中,战场面积最为狭小的一场。拿破仑麾下的法军有大约7.8万人,246门大炮;而威灵顿公爵麾下的英国、荷兰、比利时和德意志联军大约有7.3万人,157门大炮。
对于很多联军士兵来说,法军即使已经屡遭失败,但依旧是那支曾经横扫欧陆的王者之师,而眼前的敌人在进入战场时,更是军容威武,令人恐惧。作者康沃尔在书中,援引了一位英国骑兵迪克森的日记,是这样说的:
透过散乱的树篱和山毛榉树丛,我看到在距离我们不到1英里的地方,法军重兵云集:有雄壮的步兵纵队,一个中队接一个中队的胸甲骑兵、红色军装的龙骑兵、褐色军装的骠骑兵,以及穿蓝色制服的枪骑兵。阳光照在他们的武器和盔甲上,闪闪发亮,凡是看过的人,都会永生不忘。
为了鼓舞士气,在接近敌人时,法军的军乐团开始集体奏乐,首先是军鼓手密集而响亮的鼓点,然后是《胜利属于我们》等雄壮的进行曲。英军中一些刚刚入伍的新兵,面对这种阵势,吓得脸色苍白,手指颤抖。在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个有趣的小插曲,一名英军炮兵连长说,身骑白马的拿破仑在将领的簇拥下,正在自己的部队前列奔驰巡视,鼓舞士气,应该在自己的大炮射程之内;所以,他请求威灵顿公爵允许自己开炮,来个“斩首行动”。这个请求被威灵顿公爵客气地拒绝了,威灵顿公爵的意思是,对于拿破仑这个篡夺法国皇位,试图独霸欧洲的罪魁祸首,最好的办法是在战场上堂堂正正地打败他,然后让他接受维也纳会议的审判和制裁。
两军阵势摆好之后,拿破仑却迟迟没有开战。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头一天的瓢泼大雨,让地面泥泞无比,从而让炮兵无法展开行动:大炮每发射一次,后坐力就会把它从炮位上向后推;对于炮兵来说,在泥地里不断地把大炮推回原位,可是件苦差事。另外,泥泞的土地,会让炮弹的杀伤效果,也大打折扣。所以,炮兵军官出身,极度依赖大炮的拿破仑,就决定,等土地干燥一点再进攻。为此,苏尔特元帅警告说,时间宝贵,而且对防守的威灵顿公爵有利,因为每拖延一分钟开战,普鲁士军队前来增援的可能性就多一分,但拿破仑不为所动。
终于,到了中午十一点半,拿破仑觉得地面状况差不多了,于是一声令下,法军万炮齐轰,宣告会战开始。根据另一位军事历史学家阿德金的统计,在半个小时的炮火准备中,拿破仑的炮兵就向英军阵地发射了4000枚炮弹。拿破仑信心百倍地对身边的将领说,到了下午茶时间,这场战斗就能结束。
然而,法军的情况从一开始就不顺利。擅长防守,了解拿破仑战术的威灵顿公爵,没有把自己部队全部部署在圣约翰山的高地上;很大一部分英军士兵,是待在高地后方,敌人看不见的山坡上;在军事专业术语中,这叫“反斜面”。这样,法军的大炮没办法直接瞄准,自己部队的调动,也能在隐蔽的情况下进行。所以,拿破仑一开始的炮轰虽然惊天动地,但是造成的伤亡却十分有限。
另外,按照拿破仑的作战计划,法军的左翼,先要猛攻山脚附近,位于英军右翼的据点,乌古蒙农庄,但目的不是占领它,而是吸引威灵顿公爵增兵来救,为自己的主力部队实行中央突破创造条件。没想到,乌古蒙农庄本来就坚固无比,又被英军改造了一天,变成了一块难啃的骨头,非但不能吸引山顶上的英军主力来救援,反而让法军不断投入更多的兵力,可谓弄巧成拙。当然,这个局面,主要是拿破仑的弟弟,热罗姆亲王的责任。他依靠裙带关系当上了师长,负责攻击农庄,结果一心只想着立功,丝毫没有考虑到全局。
随后,拿破仑按照自己的既定计划,派出了自己手下的生力军,埃尔隆伯爵的第一军,试图占领英军阵地左翼:1.8万名法国步兵,开始缓缓向圣约翰山的山顶移动。由于道路泥泞,还需要爬坡,法军的进攻非常缓慢,导致英军的炮兵和步兵有充分的时间展开轮番射击。英国炮兵掌握的一种秘密武器,榴霰弹,发挥了致命的威力。
所谓榴霰弹,就是一种内部中空,同时装填了火药和无数小弹丸的炮弹。炮弹在半空中爆炸后,炮弹外壳碎片和小弹丸会向四面飞溅,杀伤敌人。作者康沃尔说,这些可怕的炮弹,像镰刀割草一样把法军士兵扫倒在地,麦田和草丛里躺满了刚刚死亡,还在抽搐的士兵遗体。

当法军的前锋好不容易攀上了圣约翰山的顶峰时,又遭到了处于反斜面位置英军步兵的排枪射击,伤亡惨重;随后,英军事先布置好的骑兵团,又冲进混乱中的法军步兵方阵,由于他们来得太快,法军根本没有时间转换为防御队形,于是战斗变成了屠杀。其中,最为勇猛的是苏格兰高地灰色龙骑兵团:他们统一头戴高耸的熊皮军帽,身穿耀眼的红色制服,手持重剑,坐骑一律为灰色战马,他们一鼓作气,把惊慌失措的法军一直赶回山脚。
看到志在必得的主攻遭遇挫折,拿破仑的心情顿时变得烦躁焦虑。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副官贝尔纳风尘仆仆,带来了一个更坏的消息:普鲁士人来了!而且比预想得要快。原来,贝尔纳原本带着一群轻骑兵,在战场周边侦察警戒。在距离滑铁卢战场不远,东北方向的拉恩河边,贝尔纳看到了普军前锋部队,头戴普鲁士陆军标准的黑色筒形军帽,身穿深蓝色制服。作者康沃尔说,如果拿破仑是一个谨慎的统帅,那么肯定会收拢部队,向南撤退,寻找下一个分割敌人的机会。但是拿破仑是“艺高人胆大”,还是觉得自己会赢,只要抓紧时间打败眼前的威灵顿公爵就行,他亲口对身边的苏尔特元帅说:“如果早晨我们的胜算是90%,那现在我们还有60%。”
为什么普鲁士军队来得如此之快?作者康沃尔在书中利用获取的各种资料,给读者做了详尽的解释:首先,普鲁士统帅布吕歇尔从利尼村撤退时,就下定决心,坚决和威灵顿公爵会合,再和拿破仑一决雌雄。其次,格鲁希没能完成自己的任务。
很多军事历史爱好者都说,滑铁卢战败的第一责任人,是奉命追击普鲁士军的格鲁希,他应该直奔主战场和拿破仑会合。不过,这也不能怪他,因为这一天多来格鲁希收到的命令,都是混乱、自相矛盾的,一会儿说首要任务是追击布吕歇尔,一会儿说希望他见机行事,向滑铁卢主战场靠拢;性格刻板、缺乏主动性的格鲁希压根不会结合瞬息万变的形势,去理解拿破仑的真正意图。当然,这个乌龙事件的第一责任人,还是苏尔特元帅的参谋部,没有把拿破仑断断续续的口头指示翻译为清晰、合理、可执行的命令。
另外,康沃尔告诉我们,格鲁希比普鲁士军队更加远离滑铁卢主战场,所以哪怕是立刻动身,也来不及赶上6月18日的会战。最终,自以为尽职的格鲁希,在滑铁卢主战场以东,和普鲁士军负责断后的部队纠缠在了一起,打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小胜仗,可以说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一转眼,时间到了下午四点左右。内伊元帅通过望远镜发现,部分英军官兵似乎正在撤离圣约翰山的顶部,所以他鲁莽地判断说,英军顶不住了。于是,他命令发动一次大规模骑兵冲锋,自己也身先士卒,拔剑上阵。整个滑铁卢之战的高潮到来了,法军投入了包括胸甲骑兵、卡宾枪骑兵等等各兵种在内的骑兵主力,向圣约翰山顶发起了一次又一次凶猛的冲击。法国胸甲骑兵和卡宾枪骑兵,头戴闪耀的金属头盔,头盔上耸立着红色或者黑色的马毛装饰,胸前是闪闪发光的金属护甲,看上去仿佛人马合一的怪物,威风凛凛;但是,由于缺乏步兵的配合,法国骑兵虽然来势汹汹,但无法突破英军刺刀林立,不断射击的防御大方阵。
为什么此时没有法军步兵去配合骑兵呢,这并不是拿破仑的疏忽,而是他发现,自己没兵可派了!首先是山下两个据点,乌古蒙和拉艾圣还在英军手里,牵制了大量法国步兵;其次,普鲁士军队的前锋,已经抵达了法军右翼的外围,逼得拿破仑被迫分兵抵挡,手头根本没有富裕的步兵,去支援自己的爱将内伊。
同时,在圣约翰山顶上的威灵顿公爵,日子也不好过,防线上各部队的求援,像雪片一样飞来。晚上六点,坚持了一天的据点拉艾圣,也落入了法军之手,法国炮兵可以把大炮推到山脚下,进行精确的近距离射击,打得英军死伤惨重。根据他身边的副官回忆,一向镇定,喜怒不形于色的威灵顿公爵,也开始在马背上碎碎念,一会儿抱怨“拿破仑快把咱家每根骨头都打碎了”,一会儿又开始绝望地祈祷:“黑夜或者普鲁士人,给我其中一个就行!”
到了晚上七点左右,法军的战线已经被正面的英军和不断赶来的普鲁士军压缩成了一个马蹄形。拿破仑终于像一个输红眼的赌徒一样,坐不住了,他决定孤注一掷:拿出了自己最后的预备队,也是整支法军里,最精锐的帝国近卫军,共计4000人:它的成员,都是拿破仑麾下身经百战的老兵,头戴高耸的熊皮军帽,军帽上有黄铜装饰牌和红色羽毛装饰,身穿特制的蓝色燕尾制服。

拿破仑给近卫军的任务简单直接:向圣约翰山上的英军防线做最后的冲击,占领制高点,迫使威灵顿公爵撤退,好让自己腾出手来对付普鲁士人。法国近卫军在血红的夕阳下,踩着层层叠叠的尸体,冒着猛烈的炮火冲上了圣约翰山的山脊。然而,威灵顿公爵也带领着自己战斗力最强的英国步兵近卫旅抵达了这里;最终,近卫军即使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也无法达成使命,被迫后撤。
近卫军的后撤,直接导致法军的全线崩溃。前一刻还在各处奋战的法国官兵,如同洪水一样,纷纷掉头后撤,嘴里呼喊着:“全完了!”“大家赶快逃命!”看到此情此景,威灵顿公爵果断摘下了自己的黑色三角军帽,举过头顶,挥舞了三次,发出了“全军向前推进,追击敌人”的信号。大约晚上九点半,乘胜追击的威灵顿公爵,和前来增援的布吕歇尔元帅,在一个小农庄,佳姻庄园门口相遇,这里是头一天拿破仑设立的司令部。两位统帅在马上握手拥抱。面对来之不易的胜利和尸横遍野的战场,布吕歇尔对威灵顿公爵感叹道:“亲爱的朋友,多么厉害的一仗啊!”
好了,这本《滑铁卢》的主要内容,就为你大致介绍到这里。本书作者康沃尔利用自己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资料,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上至拿破仑、威灵顿公爵等载入史册的伟人,下至战场上普通一兵,他们的遭遇和内心的波澜,都在书中被描绘得细致入微。如果你是一位军事历史爱好者,相信你会和我一样,一旦捧起这本30万字篇幅的巨著,会有手不释卷,一气读完的冲动,丝毫不会感到枯燥与畏惧。
滑铁卢的战败,直接终结了拿破仑再次重回皇帝宝座的梦想,让曾经煊赫一时的法兰西第一帝国轰然倒塌,再无翻盘的可能。仅仅半个月后,他就被迫宣布再次退位,接受了英国对他的处置,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一个炎热、荒僻的南大西洋小岛。6年后,拿破仑在岛上病故。
从本质上说,虽然长达12年的拿破仑战争,在欧洲传播了民族主义与启蒙思想,加速了近代民族国家的诞生,但这是一种明显的“破坏型创新”:根据统计,在战场上,共计有250万到350万人死亡 ,整个欧洲都无法容忍如此持续的振荡与破坏。法国作家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曾诗意地描述道:那些公墓中的尸体、战场上的鲜血和孤儿寡母的哭泣,最终变成了对巨人拿破仑的控诉,惹怒了上帝。
正如著名国际政治学研究家保罗·肯尼迪所说,滑铁卢战役,是拿破仑政治和军事生涯中最后一次“胆大妄为”。即使他依靠自己的天赋和侥幸,能够在滑铁卢获胜,他也难以抵挡反法同盟后续的军事和外交行动。在滑铁卢战场的废墟上,直接催生了一种全新的欧洲政治体系:维也纳会议体系,它维系了日后欧洲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与稳定。
实际上,自从1814年拿破仑第一次退位后,组建反法同盟的四个欧洲大国,英国、奥地利、俄罗斯与普鲁士就在维也纳持续召开会议,构思未来如何维持欧洲的和平与政治稳定。英国自16世纪以来,一直主张的欧洲势力均衡,被参加会议的各国基本接受:也就是说,坚决不允许再出现任何拿破仑,或者法兰西第一帝国这样,试图建立霸权,统治欧洲的野心家与超级大国。一旦有类似的苗头出现,这些欧洲主要强国就有责任义务再度建立类似“反法同盟”这样的政治联盟,合力把它扼杀在摇篮里。
另外,由于拿破仑战争一口气打了十几年,欧洲大陆满目疮痍,参战各国都元气大伤,唯一没有被战火波及,还拥有雄厚资金和强大海军的英国,在欧洲政治舞台上,赢得了核心地位。同时,为了限制未来法国再次称霸的企图,维也纳会议的参加国,也达成共识,中欧各国,尤其是当时尚未统一的德意志各邦,必须加以扶持,作为抑制法国扩张的保险。这也为半个世纪后,德国的统一与崛起,打下了最初的伏笔。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此外,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1.拿破仑的失败,归根结底,在于拿破仑战争,是法国大革命的后续,但传播的启蒙思想与民族主义观念,与拿破仑的征服扩张行动产生了严重的矛盾。
2.滑铁卢战役的结局,是双方统帅所有决策叠加累计的结果;拿破仑同时追求达成多个目标,资源不占有,时间窗口更狭窄,再加上用人不当,失败是意料中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