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与东亚世界》 朱步冲解读
《汉文与东亚世界》| 朱步冲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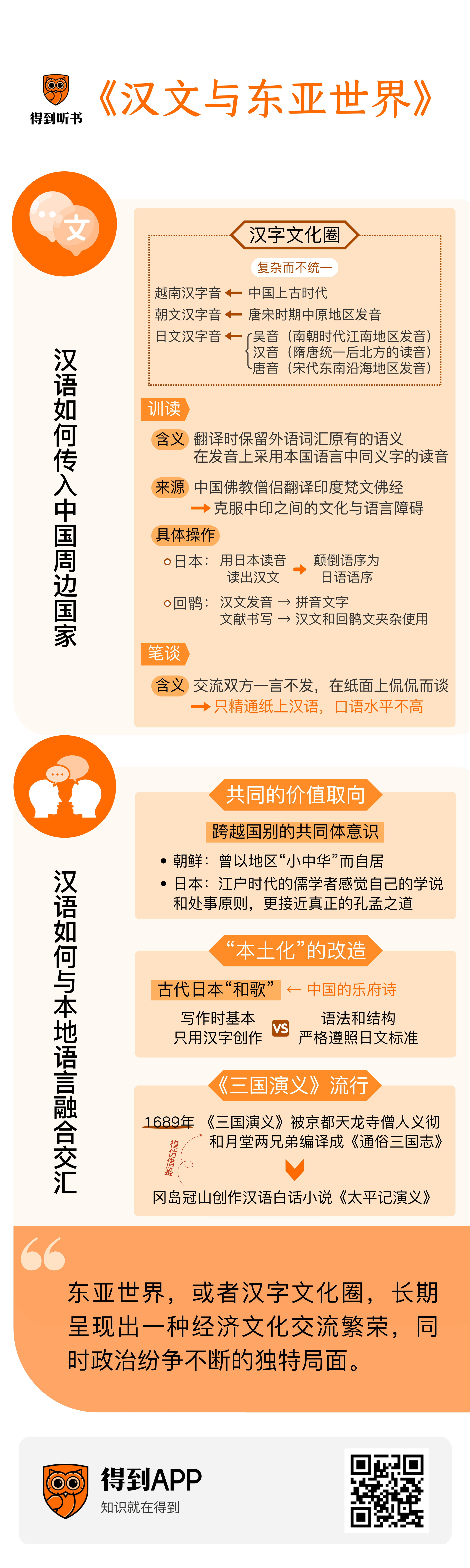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韩国语言研究学者金文京的《汉文与东亚世界》。
猛一看,这本书的名字有点抽象艰涩,但它讲述的,却是一个重要而有趣的历史现象:汉语,曾经在一千多年前,就是东亚地区通用的交流语言,以汉语为载体的中国文明,在长时间内支撑和推动了东亚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东亚汉字文化圈”,而它的影响,一直保留到今日,绵延不绝。比如,作者金文京就举例说直到今天,日韩两国的大学生,能够背诵秦汉唐宋等中国历代王朝名称和序列的,或者对《三国演义》中人物、故事如数家珍的,大有人在。
同时,日韩等国,在吸收汉语的同时,也对它进行了持续的改造与消化,最终把汉语变成了自身语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和中国难以斩断的文化共同基因,在全球化时代,也许会为东亚地区进一步的政治经济文化合作,提供基础和契机。
在本书开头,金文京就讲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来让我们快速理解,汉语在东亚地区的长期使用,以及在不同国家的独立变化。金文京说,近年来,去日本旅游的中国游客越来越多,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印象,那就是,在日本,汉字可以说随处可见,不用通晓日语,有时能够单凭这些汉字,就能了解这些信息大致的意思。不过这种望文生义的理解,也往往会导致张冠李戴、南辕北辙的结果。
比如,在日本火车站或者地铁站,自动售票机上会有日文汉字:“券売(卖)機”(kenbaiki),这个勉强还能理解:券,应该就是指车票,卖就是出售,机就是机器,按照日语宾语在前,动词在后的语法,卖票机,就变成了票卖机。但是,如果继续往里走呢?你就会遇到“改札口”,日文读作kaisatsuguchi,虽然三个汉字咱们都认识,但连起来一理解,就有云里雾里的感觉。实际上改札口,就是检票口,“改”这个汉字,在流传到日本之后,逐渐衍生出检查的意思 。没有学习过日语,单靠“望文生义”来理解的普通中国游客,自然会难以理解。
那么,为什么日文汉字,会让我们中国人产生这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呢?在古代,汉语为什么能够跨越文化与语言障碍,流行于东亚?为了解答这两个问题,我就分两部分为大家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简单回溯下,从南北朝末期到隋唐,汉语如何传入日韩等中国周边国家;以及,在传播过程中,这些国家的精英阶层,如何利用汉字音意结合的特质,发明了“训读”和“笔谈”这两种独特的汉语翻译和交流手段,降低了汉语学习和传播的难度,推动了汉语在东亚地区的普及。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再来看看,汉语在被日韩等东亚国家接受后,如何与本地语言融合交汇,生长变化,滋养了一个高度发达的东亚汉字文化圈。
首先,金文京就开宗明义地表示,在遥远的古代,中国曾经是东亚地区的中心大国,向周边源源不断地输出服饰、艺术、制度、饮食、器物等产品、技术与文化,作为交流符号的汉字,由于其音形分离的特性,所以即使抛开字音,依旧可理解内容,从而导致虽然东亚各国语言文化风俗各异,但符号化地书写汉字,依旧能够成为东亚地区的通用交流语言,进而形成了独特的东亚汉字文化圈,也进一步奠定了古代中国东亚文化中心的地位。
汉字文化圈这个名词,本身就是日本著名语言学家河野六郎,于1963年创造的,主要包括今天的中日韩三国,以及越南 。
刚才在序言中提到过,汉字是一种独特的方块文字,每个汉字同时具备表音与表意功能,不过由于中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同一个字,会因为时间流变和地域之隔,发音大不相同。由此,在汉字文化圈中就演变出了一种有趣的现象,就是中越日韩等国虽然语言中都有汉字,但它们的发音却是多种多样,大相径庭,越南汉字音,多来自中国上古时代;朝文汉字音,则基本是唐宋时期中原地区发音;而日文中很多汉字的读音则同时有吴音、汉音、唐音三个版本,分别是来自南朝时代的江南地区发音、隋唐统一后北方的读音,以及宋代东南沿海地区的发音 。本来,汉语独特的语言结构和语法,就已经让学习者望而生畏,再加上如此繁复多变的读音,实在是令人头疼。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复杂而不统一的情况呢?作者金文京就在书里解释说,古代日本人最早接触的是从朝鲜半岛传来的吴音;到了隋朝统一中国以后,日本为了政治交往和学习先进文化技术,接连派了遣隋使与遣唐使前往中国,结果使团和留学生抵达了首都长安,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熟悉掌握的吴音,并不是隋唐王朝北方统治使用、推行的汉语发音,于是赶紧下令禁止吴音,鼓励改用汉音,但是语言的发音并不是说改就改的,无奈之下,就形成了吴音与汉音并用的局面。一般来说,在日本汉语里,有关佛教的词汇和常用词继续用吴音,其他新词和儒家经典相关的词汇,则基本上用汉音 。
所以,在汉语的对外传播中,日韩越南等周边国家,为了迅速领会和传播汉字文献承载的信息,就放弃了大规模推行汉语发音的歧途,转而发明了一种独特的汉语学习与翻译方式,称为“训读”,训练的训,阅读的读。
所谓训读,就是在翻译书写外语的时候,保留外语词汇原有的语义,但在发音上,却采用本国语言中同义字的读音。作者金文京举例说,比如汉文“山”字,变成日文汉字后,字形和意思不变,但读音却变成了日文中山峰的读音:“yama”。 以日本为例,对汉语进行训读的具体操作方法是,首先把汉文中的每个字,按照日文对应的词语读出 ,再把语序不同于日语的地方,颠倒改为日语语序并做出标记 。
实际上,训读的发明者,是中国的佛教僧侣。他们在翻译印度传来的梵文佛经时,为了省事,克服中印之间的文化与语言障碍,就采用了这种方法。具体过程为,首先由印度僧人朗读经文,由通晓汉语与梵文的僧人先根据读音,用谐音汉字做记录,再根据词义翻译成能够读懂的汉语经文,最终再由官员加以润色,变得优美简练 。
作者金文京说,这种训读翻译法,很可能经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从六世纪下半叶开始,日本开始和朝鲜,以及中国开展了频繁的经济与文化交流。来自中国的儒学与佛教经典,以及陶瓷、金属锻造、驯马、灌溉等技术,就以朝鲜半岛为中转站,逐渐传入日本,而在这个过程中,由朝鲜文人士大夫发明的汉语训读法,也随着这些技术与产品,一起传入。 同时,日本、韩国前来中国访问学习的使团和留学生里,佛教僧侣为数不少,很多人也曾亲临佛经翻译现场,对训读翻译的流程非常熟悉,从而也利用这种方法来翻译汉语佛教经典 。
在隋唐时期,兴盛于中国北方的强大草原骑马民族回鹘,也根据汉语发音,草创了自己的拼音文字,而在书写文献的时候,汉文和回鹘文经常夹杂使用。为了吸收唐王朝的文化成果,回鹘人也曾大量收集唐代文献书籍,利用训读法进行翻译阅读。作者金文京就在书中举例说,比如儿童读物《千字文》,其中一句“云腾致雨,露结为霜”,用回鹘语音来读,就是“yun tin u yu,lu ker vi o”,而这一句如果按照回鹘语语义来直接翻译,意思就是平实直白的“云升了,雨就下了;露水降了,霜就冻了 ”。
汉语训读法在当时的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普及后,它们的文人或者外交官员再遇到中国同行,就可以在纸上书写汉语,来克服语言发音差异,进行实时交流。这种方法,被称为“笔谈”,在中日韩三国今天摄制的一些古装历史剧中,时常可见来自不同国家的宾主双方,进行笔谈的场面。
具体来说,笔谈的方法就是,交流双方对面而坐,各执笔墨,中间摊开一张纸,一方先写字句,完成后交给另一方,另一方阅读后,继续在纸上写下回应再交还。虽然在整个过程中,双方都一言不发,但实际上已经在纸面上侃侃而谈。如果其中某人写下了什么隽语妙言,令对方赞叹,双方也会在阅读后相视而笑,表示心意相通。日本高僧圆仁,曾于公元839年来中国研习密宗佛教,他在归国后,写了一部游记,叫《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其中有一段就记载说,圆仁刚到中国,跟扬州开元寺的僧人元昱,就进行了一场生动的笔谈,圆仁向元昱请教的是唐代中国的风土人情,最后双方还互赠礼物表示感谢 。
当然,这种一言不发的笔谈,也导致,东亚汉字文化圈形成初期,日韩等国的文人与官僚,精通的只是纸上汉语,口语水平不高。例如世纪初 ,有一位出身贵族的日本留学生橘逸势,跟随日本遣唐使团队,前来唐朝学习交流两年 ,当时前来中国学习,是日本贵族子弟在仕途上获得升迁的捷径。不过当时唐王朝针对留学生的汉语教育,在语言发音方面,逐渐从日本人比较熟悉的我国江南沿海地区的发音,也就是“吴音”,转变为关中北方地区的发音,“汉音”,这样一来,日本留学生学习汉语的难度,就明显增加了。
橘逸势,算是这一批遣唐使留学生中的后进差生,在中国待了两年,中文口语水平还是入门级,但是他的汉文书法,却写得有模有样,不仅被唐朝文人士大夫起了一个“橘秀才”的绰号,还因书法飘逸出众,与同时代的高僧空海,以及嵯峨天皇一起,被日本后世尊称为“三笔” ,也就是当时最为出众的三位书法大家。
和橘逸势同期在华的另一位日本贵族留学生善道真贞,在长安一口气苦学了十七年,据说成为研究《春秋》和《周礼》等儒家重要经典的大学问家,回到日本后担任了大学寮博士。大学寮,是当时平安时代日本朝廷效仿唐代建立的,面向贵族官僚子弟传授儒家经典的官方教育机构。但是根据史料记载,即使是留学了十七年的善道真贞,汉语口语水平也并不好,无法以纯汉语来给学生授课,只能用训读夹杂口语的办法解决。 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通过训读和笔谈,来继续学习唐代中国的文学创作,以及制度法律和科技。
到了江户时代末期,也就是十八到十九世纪,日本人通过一千多年不断的汉文学习,精英阶级的汉语造诣,终于达到了跟中国士大夫差不多的水平,多数人已不必依靠训读,就能直接读懂汉语作品原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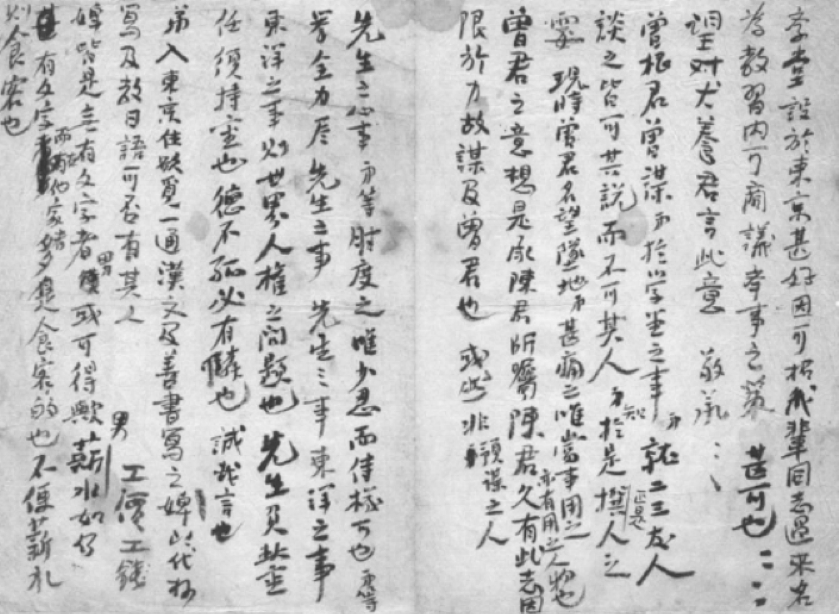
但是,由于中国本土的汉语发音与语言习惯日新月异,而口语白话文逐渐流行,这让习惯于汉语文言的日本人感到无所适从,所以笔谈这种交流模式,依旧长期存在。例如,1897年,孙中山抵达横滨,与日本民间志士宫崎滔天一见如故, 但宫崎滔天汉语口语水平不高,而孙中山当时的日语也不好,所以交流还是只能依靠笔谈。在一份记录中,孙中山曾问宫崎,沙俄正在虎视眈眈,试图占据中国东三省,万一得逞,则西方列强恐怕就会群起仿效,瓜分中国,情况危急,该如何是好呢?宫崎写下的回答是:“瓜分之机已兆,则我辈须静观清政府之所为如何,暗结日、英两国为后劲。我同志之士相率潜入内地,收揽所在之英雄。先据有一二省为根本,以为割据之势。而后张势威于四方,奠定大局也 。”
好了,刚才我们顺着作者金文京的介绍,基本了解了从隋唐到近代,东亚各国如何利用汉字音形同体的特征,利用“训读”和“笔谈”这两种独创的方法,来学习汉语,并进行交流的故事。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汉语在被日韩等东亚国家接受后,如何与本地语言融合交汇,生长变化,滋养了一个高度发达的东亚汉字文化圈。
为了具体说明,广泛普及的汉字,让东亚各国的文人艺术家不仅有了共同的创造载体,更让他们实现了跨越时空的共情。在书里,作者金文京特地一口气为我们列举了三首汉文诗歌:
第一首:水国秋光暮,惊寒雁阵高。忧心辗转夜,残月照弓刀。
第二首:叶声落如雨,月色白似霜。夜深方独卧,谁为拂尘床。
第三首:楼头秋雨暗,楼下暮潮寒。泽国何萧索,愁人独倚栏。
读完了,作者金文京就向读者发问,这三首汉诗,都写得意境深远,行文优美,但是这里面,只有一首是中国人写的,大家能辨别得出吗?这道选择题的难度,显然是五星级的。实际上,第一首,叫《闲山岛夜吟》,是16世纪著名朝鲜抗日名将李舜臣的作品;第三首,叫《游子吟》,是19世纪日本著名文学家夏目漱石所作;而只有第二首《秋夕》,是出自我国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手笔 。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有一句名言,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形式。从南北朝末期到20世纪初,一千多年来,汉语在整个东亚世界不仅是通用的交流工具,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神积淀、价值观,以及浩繁的人物典故,都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形式,植入了日韩越南等国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的意识。
例如,生在17至18世纪之交的朝鲜名臣李天辅,就写过一篇《武侯论》,评论三国时期蜀汉名臣诸葛亮 。这篇文章写得纵横流利,对中国历史的兴衰成败,提出了自己的洞见,压根看不出是出自外国人之手。李天辅在文章里说了,春秋时代,越国之所以能消灭吴国,是因为勾践善于用人,有文种负责内政,范蠡负责练兵。同理,汉高祖刘邦能够消灭项羽,建立汉朝,也是内有萧何搞行政后勤,外有韩信率领大军作战;而蜀汉呢,人才凋零,只有一个诸葛亮,其他都是庸碌之才,搞得诸葛亮恨不得把自己一个掰成两个来用,搞内政的时候变成萧何文种,领兵作战的时候又要充当范蠡韩信,实在是分身乏术,所以说纵然诸葛亮鞠躬尽瘁,蜀汉的复兴大业也难以成功 。
实际上,由于汉字成为东亚地区的通用语言,中国文化精神,变成了东亚地区精英的共同价值取向,比如朝鲜曾以地区“小中华”而自居,日本江户时代的儒学者,也感觉自己的学说和处事原则,更接近真正的孔孟之道:这种价值观上的趋同,也让东亚地区的精英,萌发出一种跨越国别的共同体意识:例如,明代万历二十五年,也就是1597年,朝鲜外交官李睟光,在北京遇到了越南使节冯克宽,两人一见如故,以汉语笔谈的形式聊了几天,临别之际,还以笔谈形式,作诗互赠。从现存文献记录来看,李睟光这几首可以说写得意境十足,不仅平仄、韵脚都很工整,内容里对中华文化中的各种典故,也是运用自如。在这里,我就随便给大家念其中的四句,大家来听一听:
万里来从瘴疠乡,远凭重译谒君王。
提封汉代新铜柱,贡献周家旧越裳。
这四句,可以被看作是李睟光对冯克宽的客气夸奖,大体可以翻译为:阁下克服了语言不通,路途遥远等重重障碍,从环境恶劣的远方来到中国,拜见明朝的天子,我实在是钦佩之至。阁下此行的重要意义,堪比古代遥远的越裳国前来朝拜西周;当时越裳国向周公奉上珍贵白雉鸟 的举动,依旧历历在目。我祝愿阁下此行能获得外交上的巨大成功,而你的功绩,则如同汉代的伏波将军马援一样不朽。
同时,这些中国周边国家的精英阶层,在利用汉语创作文学作品和各类文献的同时,也在按照本民族的语言习惯,对汉语的字义、语法,进行“本土化”改造,变成了自身文化的一部分,例如古代日本独有的诗歌体裁“和歌”。实际上,早期日本和歌的体裁,来源于中国的乐府诗,写作时也基本只用汉字创作,但是这些和歌,虽然是由汉字写成,但是语法和结构,却是严格遵照日文标准,如果我们中国人直接按照字面来读,就会产生一种难以理解的感觉。作者金文京举例说,在成书于公元8世纪的日本和歌作品集《万叶集》里,就有一首日本女贵族,额田女王写给自己前夫大海人皇子的汉文和歌 :“茜草指,武良前野逝,标野行,野守者不见哉,君之袖布流。”
这首和歌,是额田女王在天皇举行皇家狩猎活动时写的。当时大海人皇子虽然和额田女王离了婚,但是感觉旧情未了,在打猎的时候,向女王挥手致意;但女王却很傲娇,没好气地写了这首和歌来调侃自己的前夫。如果翻译成我们能理解的现代汉语,这首和歌的意思就是:来到这茜草茵茵的紫野猎场,你跟我这挥衣袖套近乎,猎场的守卫都看见了!收敛点吧!
当然,在普通民众与通俗文化方面,日本汉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三国演义》系列故事的流行。
元禄二年(1689年),《三国演义》被京都天龙寺的僧人义彻和月堂两兄弟编译成《通俗三国志》,正式登上日本文学舞台。可能是为了代表对中国文化的倾慕,这两兄弟还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湖南文山”。1836年,以图文夹杂形式来讲述三国故事的《绘本通俗三国志》出版,负责绘制插图的,是浮世绘名画家葛饰北斋的弟子葛饰戴斗;作品问世之后,在日本民众中迅速普及,受到追捧 。
《三国演义》之所以在日本迅速受到热捧,首先是因为江户时代的日本,市民文化蓬勃兴旺,对英雄传奇、精怪鬼神、浪漫爱情等题材的文化作品需求极大,有限的日本本土故事传说已经被改编得差不多了,急需新鲜素材。生活在17到18世纪,曾经将《水浒传》翻译成日文的日本汉语研究家,小说家冈岛冠山曾这样解释《三国演义》在日本的流行:说《三国演义》,因为发生在一衣带水,同文之国的中国,再加上描写的是类似日本战国时代的东汉末年乱世,所以能够被日本人迅速接受。不仅如此,《三国演义》的故事,发生在一片面积数倍于日本的国土上,故事中豪杰并起,猛将如云,这是日本本土的英雄传说所望尘莫及的;而书中展现的如奇想天来一般的权谋术数,以及战争规模场面的壮雄辽阔,都让日本读者为之热血沸腾,拍案而起。
不仅如此,冈岛还模仿借鉴《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创作了汉语白话小说《太平记演义》。“太平记”故事的主角,日本南北朝时代忠于天皇的武将楠木正成,在当时的日本民众心中,和《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可以说是十分相似,互为镜像,都是符合传统道德,值得崇拜的忠臣典范。
好了,这本《汉文与东亚世界》的基本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里。作者金文京用自己渊博的语言研究和历史学识,以汉语的传播和使用为切入点,为我们讲述了一部生动而有趣的东亚文化交流史。
汉字,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和载体,直到今日,也是全球范围内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 。其实,早在距今大约1700年前,随着中国逐渐向周边国家地区系统输出文化与技术,增强经济与政治交流,东亚地区,就逐渐形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东亚汉字文化圈”。正如日本历史学家气贺泽保归所说的那样,当时的东亚,作为一个地理单元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有四大共同元素:汉字、儒学、律令制国家体系,以及中国佛教。
在这种文化交流中,汉字,由于自身可以实现音意分离的特性,从而降低了使用与学习难度,迅速成为东亚地区文化交流的基本工具与载体。
当然,汉字与中国文化的输入,既构建了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共同体,也让中国周边地区的民族国家和民族意识,在经济文化发展繁荣的同时,开始萌芽;从而导致,一方面周边各国与民族,都渴望学习与吸收中国发达先进的文化,另一方面又要保持自身政治独立与文化独特性。所以,东亚世界,或者说汉字文化圈,长期呈现出一种经济文化交流繁荣,同时政治纷争不断的独特局面。
到了19世纪末,整个东亚世界也被西方列强逐渐纳入全球化经济和政治体系,东亚各国的知识分子和有志之士,都在急切探索独立救国之道;其中一些人,比如梁启超和福泽谕吉,都曾认为,欧洲除了先进的科技与政治经济制度,就连它的表音字母式文字也更加便捷精确,容易学习记忆,优于汉字方块字,于是都在本国提倡文字改革运动,绵延了上千年的东亚汉字文化圈,由此受到极大冲击。 日本、韩国、越南等国,都不同程度地发起了语言革新运动,例如韩国,曾经几次尝试彻底弃用汉字,但由于东亚汉字文化圈形成已久,许多汉字与汉字发音名词已经约定俗成,嵌入了韩国语言文化与习俗的底层逻辑,所以只能作罢。
在本书结尾,作者金文京自己也很坦率地承认,在全球化时代,曾经的东亚汉字共同体究竟该何去何从,他自己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判断和倾向。我个人感觉,金文京在本书中,不断呼吁新一代东亚人,应该好好回首往事,了解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兴衰过往。这种潜台词中,依旧包括一种对于东亚各国再度形成文化与经济共同体,和谐共处,扶持发展的憧憬和希望 。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原书的电子版已经为你附在最后,欢迎你进行拓展阅读。此外,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
回首往事,了解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兴衰过往。这种潜台词中,依旧包括一种对于东亚各国再度形成文化与经济共同体,和谐共处,扶持发展的憧憬和希望 。
-
东亚世界,或者汉字文化圈,长期呈现出一种经济文化交流繁荣,同时政治纷争不断的独特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