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下的大明》 陈章鱼解读
《显微镜下的大明》| 陈章鱼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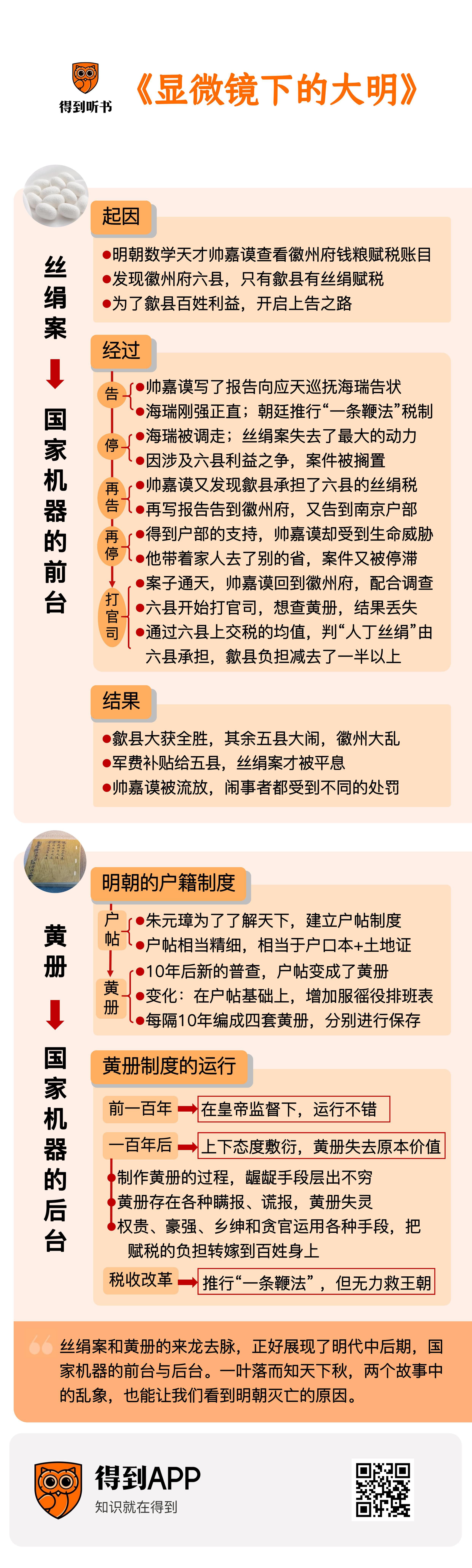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陈章鱼。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显微镜下的大明》,作者是著名的历史作家马伯庸。
马伯庸可以说是得到听书的老朋友了,之前为你解读过他的小说《两京十五日》《长安的荔枝》《大医·破晓篇》。不过,今天这本《显微镜下的大明》有一些特殊,它不是一本小说,这本书记录的,是明代六个真实的历史事件。虽然是历史,但是读起来并不枯燥,就在我正在写这段文稿的这天,由这本历史著作改编的电视剧刚刚开播,这也证明这本书中记录的故事有多曲折离奇。
马伯庸从历史文献中,挖出这六段往事,给我们展示了明代的许多真实细节,尤其是基层百姓的生活状态。从这些细节中,我们又能以小见大,看到明代兴起和灭亡的种种原因。就像是一台显微镜,通过检验一滴血、一个细胞,来判断一个人的健康程度。这就是为什么,马伯庸把这本书取名叫《显微镜下的大明》。
半个小时的时间,我肯定没法把六个故事都讲给你听,我从书中选择了两个最曲折的故事。而且这两个故事之间,还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如果把明朝的政治系统比喻成一个电脑程序的话,那么这两个故事正好展现了程序的前台和后台。
我们先来看前台的这个故事。
这一年是公元1569年,大明朝已经开国二百零一年,还有七十五年就要灭亡。此时在位的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八世孙隆庆皇帝。大明王朝的国都早已经从南京搬到了北京,不过南京依然有着副首都的地位。北京以及周边一大片土地统称为“北直隶”,南京以及周边一大片土地统称为“南直隶”,这是明朝的两个省级区划,当时并称“两京”。南直隶下边有一个徽州府,徽州府下边管着六个县,其中最富裕的是歙县。今天依然有歙县,隶属于安徽省黄山市。
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歙县。故事要从一个普通人讲起,他叫帅嘉谟。
帅嘉谟文武都很一般,唯独有一个特长,对数学很敏感。要是放到今天,帅嘉谟肯定不愁找工作,去IT行业、金融行业都是前途无量。可惜在明朝,朝廷重视的是诗文,不重视算学,帅嘉谟最好的就业方向,就是争取去官府当个管钱粮税赋的小官吏。这个岗位需要做大量的计算来练习,但是那个年代既没有教辅书,也没有习题集,上哪去练习呢?帅嘉谟想到,歙县因为富裕,所以是附郭县,也就是徽州府的衙门也在这个县,所以歙县的库房里,存着整个徽州府历年的钱粮赋税账目。帅嘉谟想办法接触到官府账册,拿往年的账目当成应用题来练习。
练着练着,帅嘉谟在账目上看出问题了。他发现徽州府每年上交的税赋中,在正税之外还有一笔税叫“人丁丝绢”,每年要缴纳八千多匹丝绢。可是再查阅徽州府下边六个县的账目时,发现其他五个县都没有“人丁丝绢”这笔支出,只有歙县的账目上有记录。
八千多匹丝绢不是小数目。南直隶下边管着十几个府,每年总共要上交的丝绢是四万多匹,相当于徽州一府就承担了五分之一。徽州府管着六个县,这八千多匹的丝绢税却让歙县一个县承担,这就不够意思了。
帅嘉谟又查阅了大量资料,想要搞清楚这笔税的来龙去脉,一查不要紧,这笔税的历史可太长了。早在公元1365年,明朝还没有建立时,徽州就已经是朱元璋的地盘。这一年在征税时一算账,朱元璋发现徽州府的六个县交粮食交少了,于是加了一笔税,让各县用等价的丝绢补齐,这个欠款和“人丁丝绢”的数量刚好一致。
当年六个县一起欠了债,不知道为什么,如今却让歙县自己去还钱。更可怕的是,徽州并不养蚕,不产丝绢,为了交这笔税,歙县的老百姓必须先把粮食卖成银子,再用银子从别处购买蚕丝用来交税,无形中让成本翻了一倍。大明开国才二百零一年,歙县的老百姓却当了二百零四年的冤大头。
这让帅嘉谟非常气愤,他决定去告状,替歙县的老百姓讨个说法。他没有向徽州府告状,而是直接告到了徽州府的顶头上司、整个南直隶的管理者应天巡抚那里。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时的应天巡抚,他叫海瑞。这可是铁面无私、刚强正直的海青天,帅嘉谟相信,只要引起海青天的注意,就一定能解决问题。
不仅如此,当时的政治形势对于翻案也非常有利。隆庆年间,朝廷正在江南推行“一条鞭法”,简单来说就是税制改革。明朝之前的税收制度比较复杂,你看单单一项“人丁丝绢”税,就涉及交粮食、交蚕丝、交银子。“一条鞭法”的核心就是简化税收种类,粮食之外的那些实物税,统一改成用银子交税。这样能简化税收程序,减少中间操纵的空间,可以更公平。所以一条鞭法的口号是“均平赋役,苏解民困”。
朝廷有政策,省里有青天,这让帅嘉谟觉得很有希望。他写了一份报告,开篇就是“天下之道,贵乎均平,故物有不得其平则鸣。歙县久偏重赋,民困已极,躬遇仁明在位,备陈情款,恳乞均平。”翻译过来就是:天下的道理,最重要的就是公平,遇到不公平的事情,就应该发出声音。歙县长期以来,独自承担如此重的赋税,百姓苦不堪言,现在遇到您仁慈又贤明的官员,我向您详细说明情况,恳请您给歙县老百姓一个公平。
不得不说,帅嘉谟写报告还有挺有水平的。一上来调子就定得很准,既符合朝廷推行的新政策,又指出了百姓的困苦,用两个角度打动海瑞的心。后边详细说明自己的查考过程,指出这笔“人丁丝绢”让歙县一县承担,使得百姓苦不堪言,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数学才能,数字翔实,层层推导,极有说服力。最后,帅嘉谟还贴心地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这笔钱六县分摊,可以按照人口数量分摊,也可以按照耕地面积分摊。方案都做好了,就等着海大人批准,不论按哪种方案分摊,歙县至少都能减少一半负担。
这一份报告递上去,效果立竿见影,海瑞很快给出批示,让徽州府好好查清楚,向省里汇报。徽州知府不敢怠慢,迅速召集下边六个县的官吏乡绅过来商议。
这样看来,丝绢案翻案有望。但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事情有了变数,海瑞被朝廷调走了。海瑞一走,丝绢案失去了最大的动力。
你可能会问,这么大个南直隶,不能只有海瑞一个官吧?无非是几个县的纠纷,别说省里的官员了,就是徽州知府应该也能处理,怎么海瑞一走,事情就不好推进了呢?
你要知道,徽州不比别的地方,这里的读书人多,考中的进士多,所以做官的人就多。徽州府下边六个县,几乎每个县都出过总督、巡抚、尚书、侍郎这样的高官,这些高官和家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结成了一个个的利益集团。帅嘉谟要减轻歙县的负担,也就增加了其他五个县的负担。丝绢案的核心,是六县的利益之争,那些高官很可能会站出来为自己这一县说话。这帮大佬们个个手眼通天,那可不是好惹的。刚直的海瑞不会在乎这些,毕竟他还是个六品小官时,就敢直接写奏折批评皇帝。可是其他官员就没这么大胆子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管这个案子,朝廷收的税也不会少,管这个案子,指不定会给自己管出什么麻烦来。
于是海瑞一走,这个案子马上就被搁置了。大家就像商量好了一样,都是一个字——拖。帅嘉谟急了,事情走到这一步,怎么能让你们给拖黄了呢?他又重新查阅账目,准备上交一份更详细的报告。
这一查,还真查出了新的问题。
帅嘉谟翻出了户部给徽州开的收据,上边写得很明白,收到了徽州府的“人丁丝绢”,但是徽州府发给六县的公文中,“人丁丝绢”这个项目没有了,只有歙县多了一个项目,叫“夏税生丝”。这个“夏税生丝”就是前边所说的,二百多年前为了补交粮食欠款上交的生丝。
这就清楚了。当年“夏税生丝”这笔欠款其实早就没了,别的五个县早都不交了。后来朝廷又给徽州府加了一笔“人丁丝绢”的税,有人移花接木,继续以旧的名义从歙县收税,再以新的名义向朝廷交税。这样,原本需要六县均摊的丝绢税,神不知鬼不觉地压到歙县一个县的头上。
原本以为当年账算错了,所以歙县吃了亏。现在看来,人家就是故意的,就是要让歙县把其他五县的税也给交了。这就是欺负人了。
帅嘉谟又写了一篇报告,讲述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他先是把报告递到了徽州府,可是徽州府一点回应都没有。帅嘉谟一想,海瑞一走,估计自己在省里也得不到支持,干脆进京上访,接着往上告!
这里说的“进京”不是去北京,而是去南京。前边咱们说过,大明有南北二京,北京的六部这些政府机构,在南京也有一套备份。虽然权力远不及北京的大,但是对于南直隶这片区域还是有发言权的。钱粮税赋方面,南京户部就相当于南直隶的顶头上司。
帅嘉谟就把官司打到了南京户部。很快,南京户部给出了意见,也是让徽州府查明情况,然后向户部汇报,而且特别提出几个问题:丝绢税是从哪年开始征收的?为什么只让歙县出?其他县有没有出过钱?如果没有,接下来徽州府打算怎么解决问题?
虽然都是疑问句,但是我们能看出来,南京户部也觉得这么收税是有问题的,对歙县不公平。这一次得到户部的支持,按说应该解决问题了。没有想到,事情又有了变数。
因为史料没有记载,我们今天已经不知道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帅嘉谟去南京上访之后,没有再回徽州,而是带着家人去了别的省。最可能的原因是,帅嘉谟此时遇到了死亡的威胁。眼看官司就要打赢,这笔税也要压在其他五个县头上,断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既然解决不了问题,干脆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帅嘉谟这一逃,丝绢案又一次陷入停滞,原告都没了,官司还怎么打?户部日理万机,不可能一直盯着徽州。这个案子也就没了下文。日子一年一年过去,这中间连皇帝都换了一回,隆庆皇帝驾崩,万历皇帝继位,似乎丝绢案就要彻底被人遗忘了。
意外的是,就在六年后,这个案子又被翻出来,而且这一次会震惊朝野。
这个案子之所以被翻出来,是徽州知府突然向歙县发了一道逮捕令,要求火速捉拿帅嘉谟,给出来的理由也很牵强,你帅嘉谟有本事去告状,为什么不留在歙县配合调查?现在想找你找不到,躲在外头一定是有问题,把他逮回来。
歙县一点也不热心,拖了半个月后才向徽州府报告,我们了解到帅嘉谟现在在别的省,我们是没有权力去别的省抓人的。又过了半个月,徽州知府居然收到了帅嘉谟的信。帅嘉谟在信中说,当年从南京回来有人要害他,他这才躲到外地。现在他愿意为了这个案子,快马加鞭赶回来。信里又附上一份报告,提供了这些年他查到的新线索。
这里边的细节很有意思,帅嘉谟躲到了将近一千里以外的江夏县,从歙县知道帅嘉谟的下落,到徽州知府收到帅嘉谟的信,前后只过去了十几天。这要是歙县派人通知帅嘉谟,一来一回两千里,这也太有效率了吧?更有可能的是,歙县其实一直都和帅嘉谟有联系,向他通报徽州的动态,帅嘉谟早就知道徽州知府要找自己,于是早就准备好了报告。这也好理解,帅嘉谟为了歙县的利益家都回不来,歙县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很有可能私下里为帅嘉谟提供帮助。
等到帅嘉谟回到徽州府,徽州府马上下令,详查丝绢案。为什么徽州府这么着急呢?因为早在那一年的年初,南京户部下发了一道文书,责问徽州府丝绢案到底查得怎么样了。更吓人的是,这封文书的前头有三个字“奉圣旨”。这个案子通天了。
再想拖是不可能了,再想压也压不下去,只能打官司了。于是,围绕这笔丝绢税,徽州六个县进行了一场大辩论。
正方选手当然是歙县。以前都是帅嘉谟单枪匹马,而这一次,歙县的知县亲自下场写了一份报告。帅嘉谟写报告时,有些话不能说得太直白,知县大人就直接多了,表示有人篡改收税种类,使得六个县的税让歙县自己承担了。而且他还指出,徽州府这么多年,管财务的官吏没有歙县人,都是其他五个县的。这就相当于指着鼻子骂其他五个县,黑了心算计歙县。
这位知县大人怎么如此硬气呢?因为他的报告,找了几位本地的乡贤一起署名。这些人说是乡贤,其实都是退休官员,品级最小的是三品。这回清楚了,很有可能就是歙县本地这些大佬把案子捅到了朝廷,给徽州府巨大的压力,必须把案子查清楚。
其他五个县只能应战,各自向徽州府上交报告,以各种理由反驳,每个县也都学歙县,拉上本地的退休官员一起署名。这一年的徽州热闹非凡,六个县的报告雪片一般往上递,各县的乡绅们暗自斗法较劲,后来连当地百姓都惊动了。你帅嘉谟一介平民能进京上访,我们县的老百姓就不能告状吗?以至于后来,南直隶下发的公文里,除了催徽州府赶紧拿出结论,还反复强调,让徽州府管住老百姓,不要再来省里告状了。
可是徽州府哪里敢拿出结论?上边有大佬们神仙斗法,下边是百姓民意汹汹,哪边也得罪不起。后来,徽州府想了个相对公允的办法,和下边六县向南京户部打了一份报告,要求查阅黄册。
什么叫黄册呢?后边我会详细讲,这里你可以简单把它理解为国家历年收税的档案。地方的记录有可能被篡改,国家的档案是权威的,孰是孰非一看就清楚。
黄册存放在南京,是朝廷机密文件,之前各县都曾经偷偷去申请查询黄册,结果都被拒绝。这次徽州府的报告得到了批准,徽州组成了一个调查团,前往南京查看黄册。没有想到的是,年深日久,当年的记录没了!所有人听到这个消息,都傻眼了。六县人民都望眼欲穿,指望黄册来主持公道,现在档案丢失,死无对证,谁也说不清楚当年是怎么回事了。
消息传回徽州,歙县和其余五县从辩论升级成了人身攻击,几乎到了开战的边缘。
眼看这个案子越来越乱,南京户部看不下去了,迅速下发一道公文,请徽州府统计一下各县上交的各种税,加上这笔“人丁丝绢”一块算算,如果符合平均数,那就说明丝绢税是歙县分内的。如果算出来不平均,那么就让各县负担。
六个县人口田地都不一样,直接算平均实在是有些粗暴。不过,这不是南京户部糊涂,他们下发的公文中,有一个词反复出现:“均平”。
你可能还记得,当年帅嘉谟第一次写报告时,就用这个词引起了海瑞的注意,当时朝廷正在江南试行一条鞭法,如今,朝廷正在酝酿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核心就是减少税收种类,实现“均平”。甚至有人猜想,朝廷把丝绢案翻出来,就是要利用丝绢案引发一场大辩论,凸显旧税法的弊端,为推行一条鞭法引导舆论。南京户部的解决方案看似粗暴,实际上最适合向朝廷交差。
在这个算法下,歙县的赋税已经超过了各县平均,徽州府给出结论,以后丝绢税应该六县承担。最终计算的结果是,以后五县一起负担54%,歙县负担46%,减少了一半以上。这个方案被一路报到了朝廷,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准,下发圣旨。
歙县人民欣喜若狂,此时距离帅嘉谟第一次告状,已经过去了八年,终于大获全胜。帅嘉谟在歙县被当做英雄,他给自己弄了一副冠带,相当于今天的大红花,在百姓的簇拥下游街庆祝。
歙县这边是锣鼓喧天,那边其余五个县的老百姓牙都快咬碎了,你们歙县能闹,我们也能闹。老百姓堵住县衙、府衙,截住官道,阻拦官员,非要讨个说法。
最夸张的是婺源县,这时正好赶上婺源知县离职,趁着权力真空期,秀才程任卿联合大族乡绅成立议事局,俨然要自治了。正好婺源县里有一批驻军,带头的军官是歙县人,他连夜带兵撤出婺源直奔歙县,沿途散布消息,婺源要造反!
婺源人听到歙县人污蔑他们造反,勃然大怒,马上也派人散布消息,说真正造反的是歙县人。隔壁休宁县听说这个事情,表示你们玩得不够狠,看我们来个大的。休宁人直接占领了县衙,挟持了知县,然后以休宁知县的名义,给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省发去文书,说歙县现在出了上万叛军。
休宁玩得确实够狠,那几个省接到文书都吓傻了,按说歙县出了乱子,休宁县应该先上报徽州府,再上报南直隶,如今休宁的文书既越级又跨省,难道叛军都打到南京了?
乱了,这回是真的乱了。江南震动,各省哗然。南直隶和徽州府赶紧派兵,该弹压的弹压,该安抚的安抚,这才把乱局压下来。但是这一次动乱让大家看到,丝绢税的方案必须修改,不然徽州还得乱。
但是事情已经闹到这一步,六个县哪一方都没法让步了,五县的负担要往下减,歙县也不会多出钱,否则百姓还会闹起来。最后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是个非常黑色幽默的结果。不知道哪位高人指出来,徽州府每年要交的赋税里,有一笔军费其实被重复征收了两遍,只是多年以来一直这么操作,就成了惯例,不如和当地军队商量一下,从军费里拿出钱来,补贴给其余五县。军队那边很痛快地答应了,大概是因为他们算计着,要是再闹出民变,还得军队收拾这个烂摊子,不如少拿点钱,买个省事。
就这样,因为一笔糊涂账引发的徽州丝绢案,又因为另一笔糊涂账而被平息下来。从这里就能看出,大家这么纠结这些税目数字,不是因为他们热爱诉讼,大明的正税不多,但是各种隐性税却无比繁重,很多临时征收的税赋,执行几年后就固定下来,之后不断有临时税变成固定税。百姓的负担越来越重。从徽州丝绢案这两笔小小税赋,就能以小见大,看到明朝灭亡的原因。
说回这个案子,这场案子前后持续了将近十年,最后终于拿出一个大家都能满意的解决方案,上上下下的官员都松了一口气。然后,他们把目光看向了帅嘉谟,要是没有你生事,哪来这十年的乱子?该秋后算账了。
帅嘉谟被判刑的理由竟然是,他给自己弄的冠带,用的是歙县老百姓捐给他的钱,这就算挪用公款,假公济私。最终给帅嘉谟定的处罚是,流放三千里充军。当然我们知道,在官老爷们看来,帅嘉谟只有一个罪名:你给我们找事了。帅嘉谟踏上了充军之路,他之后的人生是什么样,历史上再无记载。值得欣慰的是,歙县民众没有忘记他,他被收录在县志的义士传里。
受到惩罚的不止帅嘉谟一人,徽州大乱中各县站出来闹事的人,其实大多不是坏人,都只是想为当地百姓减轻一点赋税,不过在官府眼中,这些人都必须处理,给他们安的罪名各不相同,处罚从杖责、下狱到流放充军都有。
那位在婺源县成立议事局的秀才程任卿处罚最重,在官府看来,他的所作所为已经接近谋反,所以他被判处斩监候,相当于死缓。程任卿不是一般人,他在监狱里听到这个消息,没有哭闹,而是详细引用法律条文,上书为自己辩护。在很多有心人的保护下,程任卿的死缓就一直缓了下来。在监狱里待久了,程任卿决定做一件事情,他要编一本书。他联络徽州官吏和各县的朋友,把这十年来围绕丝绢案的各种资料汇集起来,从朝廷圣旨到乡绅书信,一共137篇文书,他都客观保留下来,这本书叫《丝绢全书》。
程任卿在牢里一待就是二十年,后来,有同乡当了高官,为他喊冤,这才改判充军,发配边疆。程任卿还真有本事,在边疆立下军功,成了一名军官,最终荣归故里。婺源百姓也在县志的义士传里给他留了个位置。而那本《丝绢全书》也流传至今,生动地向我们展现了四百多年前的这段历史。
丝绢案说完了,这个案子可以当做一个样本,展现明代政治系统的“前台”。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故事,正好可以展现“后台”。
你发现没有,在丝绢案中有个关键变量——黄册。各方都相信只要查阅黄册,就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明白,等到大家发现黄册的记录遗失,整个徽州就彻底乱了。黄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权威呢?这就是《显微镜下的大明》中另一篇浓墨重彩的内容了。
这要从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说起。朱元璋打下了天下,建立了明朝,作为皇帝,接下来他就要治理天下了。然后他发现,治理天下真的是个技术活。
治理天下有个前置条件,那就是了解天下。不是说天下有多少地,这些地就自然而然成为帝国的粮仓,朝廷永远只能管理自己知道的人口和田地。对于皇帝,这天下就像是被一团迷雾笼罩,你能吹散多少迷雾,实际上你才拥有多大的天下。
那怎么了解天下呢?有的朝代能占一点前朝的便宜,比如刘邦攻陷咸阳后,萧何马上接管了秦朝的户籍档案,靠着这批档案,刘邦迅速了解了天下的情形,在和项羽争霸的时候占据了优势,建立汉朝之后,也能参考秦朝的户籍制度,建立起有效的管理体系。
可是朱元璋没有这样的运气,在他前边是元朝,元朝的户籍制度实在太乱,根本没有办法全盘继承。朱元璋只能另起炉灶,自己搞一套制度。
这套制度的第一版叫做“户帖”,相当于明朝版的户口本。
在那个年代,户帖可以说相当精细,每一户都要写明籍贯、人数、名字、年龄、住址、田产等等信息,所有的经手官员,上至知县下至乡里的里保,每个人都要签名。一式两份,一份存在百姓手中,一份交给官府留底,两份中间盖一个骑缝章,防止任何一方伪造篡改。
各地统计好户口之后,层层上报,逐级汇总到朝廷。这样,朱元璋手里就有了一份全国总报告。全国一共有多少人口,有多少耕地,一目了然。有了这个东西,天下在朱元璋面前就变得透明了。
为了防止官吏谎报瞒报,朱元璋还搞了核查制度,直接派军队下去抽查。哪一级数字和实际不符,哪一级官员就要掉脑袋。
这一次大普查,搞了整整一年,虽然原始记录并没有留到今天,但是历史学家根据种种记载推测,全国总注册人口在五千五百万以上。这就是朝廷可以实际控制的人口,只要愿意,可以追查到具体任何一户的情况。这一年是明朝建立的第四年,公元1371年,经过了宋朝末年和元朝的混乱管理,一百多年后,皇帝第一次如此清晰地了解天下。
但是这种管理不是静态的,人口会增长,土地会变化,于是朱元璋下令,从此之后,每十年各地都要更新一轮数据。他要靠制度让天下一直透明下去。
十年后,新一轮普查开始,这一次朱元璋又把制度进行了一次升级,从户帖变成了黄册。有什么变化呢?一个最重要的变化,是把徭役的统计也加了进去。在古代,百姓除了交税还要服徭役,也就是给朝廷打工,朱元璋规定,一百一十户百姓是一个里,每年这个里当中有十一户要去服徭役,十年一轮。黄册里边就有一张大表格,记录了哪一年都有哪几户应该去服徭役。
简单来说,之前的户帖是户口本加土地证,现在的黄册,是户口本加土地证再加排班表,这样,全国有多少人口,有多少土地,能上交多少税,又能出多少劳力,就变得清清楚楚。
为了防止谎报瞒报,朱元璋又创造性地设计了一个制度。黄册中的数字不能只写现在的数字。比如说人口,要写清楚上次造册时的数量,这十年间增加了多少,减少了多少,现在又有多少。这样,就从户帖的静态统计,变成了动态管理。你想作弊,想把这一次的数字改了,官府调出从前的档案一对,就能看出问题。这么一来,朝廷不只掌握了每一户的现状,还控制住了过去和未来。
朱元璋规定,每隔十年,各地的数据统计好之后,要编成四套黄册,县里、府里、省里、朝廷各留一份。于是各地的黄册纷纷运往当时的首都,今天的南京。朱元璋把黄册存放在今天的南京玄武湖,这里四面环水,既不用担心火灾,也不怕别人闯入。二百多年来,玄武湖就成了明朝的数据中心。
说到这里你就明白,为什么在丝绢案里,大家都想要去查阅黄册,因为这个王朝从开国以来的人口、田地、赋税、徭役,那些最详细真实的数据,都记录在黄册中。这一套制度,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可以说已经非常完善了。
只可惜,再好的制度,也需要有人来执行。明朝的前一百年,在朱元璋、朱棣这些认真皇帝的监督下,黄册的制度运行得不错。但越往后,上上下下的态度就越来越敷衍,龌龊手段层出不穷。有些地方在制作黄册时,会选择粗制滥造的纸张,甚至特意在纸张里掺甘蔗汁和蜜水。这样的黄册在库房里,不是化成粉末,就是被虫子咬破,之前的记录就会荡然无存。
到了发生丝绢案的隆庆、万历年间,黄册制度已经是病入膏肓。在各种瞒报、谎报之下,黄册已经根本没有办法反映基层的真实情况。举个例子,隆庆年间,福建省福宁州的户口数比朱元璋的时候减少了三分之二。其实,这个地方这些年一不打仗二不闹灾,人口一直在增长,只不过当地的大户通过各种手段,把增长数藏了起来。
到后来,地方官员根本不把黄册当回事,他们自己又搞了一套统计制度,里边记录了当地真实的土地和人口,当然也是他们能力范围内的“真实”。这套制度叫做“白册”,朝廷曾经反复向地方索要白册,甚至动过以白册替代黄册的心思,但是地方上坚决不合作,这件事情一直没成。
这个时候,上上下下谁都知道,黄册已经沦为一堆废纸。黄册一旦失灵,对于朝廷来说,天下就不再透明。长此以往,权贵、豪强、乡绅和贪官,他们会运用各种手段,将赋税的负担转嫁到百姓身上,甚至还会为了私利,自己进行摊派。这样下去,是要亡国的。
说到这里你就明白,为什么隆庆、万历年间,朝廷对一条鞭法非常重视。利用推行新税的过程,就有机会绕过黄册,建立一个新的统计制度,让天下重新变得透明。
只可惜,从丝绢案我们就能看出来,那时的明朝已经是积重难返,一条鞭法为明朝延续了一段时间的生命,却没能彻底拯救这个王朝。黄册也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延续了下来。
黄册的结局让人唏嘘。清朝占领南京后迅速封存了黄册库,顺治皇帝打算找到一些有用的档案,为清朝的统治提供帮助。他指派户部尚书来负责黄册的整理。后来,顺治皇帝问户部尚书,在这些黄册中有没有找到有价值的资料?户部尚书苦笑着说,他发现一些地方在崇祯年间制作的黄册,里边的户口和数字竟然和朱元璋时代一模一样。这些官员已经连基本的户籍调查都懒得做了,抄几份老档案就算应付差事。
更让人震惊的是,在地方的库房里,户部尚书还找到了崇祯二十四年的黄册,可是大明到了崇祯十七年就已经亡国了。这说明地方官府已经懒得每十年制作一次黄册了,反正也是假的,反正也是抄作业,不如一下多抄几批,到时候交上去就行了。
这本应该在崇祯二十四年上交的黄册,成了大明王朝一件充满讽刺意味的死亡物证。
到这里,这本马伯庸的《显微镜下的大明》,我就为你解读完了。
丝绢案和黄册的来龙去脉,正好展现了明代中后期,国家机器的前台与后台。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两个故事中的乱象,能让我们对明代的历史中的问题,有更直观的感受。
最后,想和你分享一个有趣的事情。《显微镜下的大明》这本书,其实和得到App还有一些渊源。
当年,马伯庸从朋友那里听说了历史上有个徽州丝绢案,又找到了那本《丝绢全书》,他就萌生了要把这个故事写出来的想法。可是,当他自己动笔写时,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故事涉及太多专业的历史知识,很多政治和赋税的问题,马伯庸感觉自己没有弄明白。于是他找来许多论文研读,历史学者的研究成果,帮助马伯庸最终完成了一篇三万字的文章。一次偶然的机会,马伯庸把案子讲给了和菜头,和菜头又把这篇文章推荐给了罗胖。2016年,得到App做了一件很不一样的事情:用十万元买下这篇文章,免费发放给得到的用户。
后来,马伯庸没有留下这十万元,而是把钱分给了他参考最多的四篇历史论文的作者。可能是第一次有人因为读了论文要给自己送钱,几乎每位作者都不相信这是真的,总以为是一种新型的诈骗,中间的过程既曲折又搞笑,推荐你去看马伯庸自己写的公众号文章《四起几乎未遂的学术“诈骗”案始末》。
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恰恰是当年这个活动最想传达的理念:“知识应该是有价的,智慧结晶理应得到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尊重。”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按钮,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我在文稿末尾还附上了电子书的链接,推荐你去进行拓展阅读。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1.《显微镜下的大明》记录了明代六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作者马伯庸希望从这些细节以小见大,讲述明代兴起和灭亡的种种原因。就像是一台显微镜,通过检验一滴血、一个细胞,来判断一个人的健康程度。
2.从“徽州丝绢案”,我们能看出明代隐性税繁重,临时税逐渐变成固定税,给百姓造成巨大负担,这是明代走向衰亡的一大原因。
3.朱元璋建立的黄册制度,其存储之巨、信息之丰、分列之细,是全世界档案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