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礼议》 陈子昂解读
《大礼议》| 陈子昂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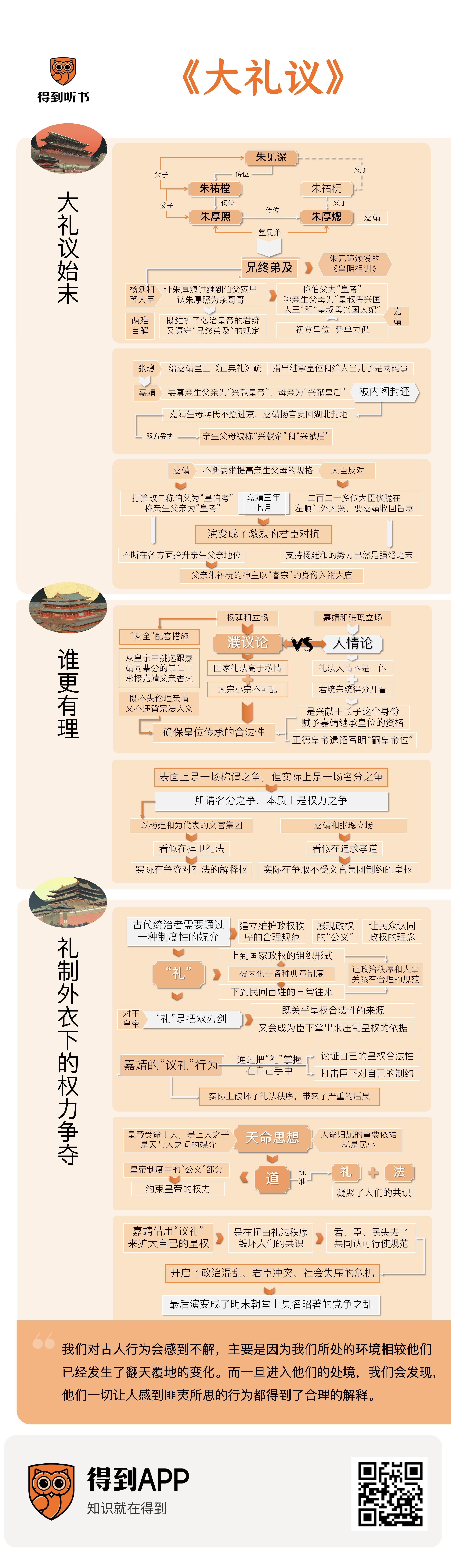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陈子昂。
读历史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古人会做出很多让我们当代人感到难以理解的“迷惑行为”。
比如,你能想象吗?在明朝,曾经有一群大臣,他们群情激愤,跪在紫禁城的左顺门前痛哭流涕,就只为了一件事儿:阻止嘉靖皇帝朱厚熜做一件看似平常的事——管自己的亲生父亲叫“爹”。
站在我们当代人的立场,这件事就显得很莫名其妙。首先,喊自己的亲生父亲一声“爹”,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怎么还成了一种忌讳了呢?凭什么人家皇帝不能管自己的亲生父亲叫“爹”?其次,这是一件嘉靖他们家里的私事,至少表面看起来,跟国家治理一点关系都没有,认了自己的亲生父亲作“爹”,难道会带来什么实际的政治恶果吗?这些臣子,是不是管得也太宽了?
然而,就是这么一件看似荒谬的事儿,却在明朝嘉靖年间引发了一场漫长且激烈的争论,在这场争论当中,有的大臣得罪了皇帝,丢了官,有的大臣还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就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大礼议”事件。
咱今天这期听书,就借由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尤淑君老师的这本《大礼议》,来仔细聊聊这件事。
“大礼议”最让人困惑的点,就在于:为什么一件在我们今天看起来无足轻重的小事,在当时的人们眼中,却是性命攸关的原则问题?一群饱读诗书的聪明人,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称呼问题上拼个你死我活?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更深入一层,来看看这个表面上的称呼之争,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对古人行为会感到不解,主要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相比较他们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一旦进入他们的处境,我们会发现,他们一切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行为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块回到当时的历史现场,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来聊聊嘉靖皇帝是如何上位的,大臣们反对他管亲生父亲叫“爹”的理由是什么,嘉靖又是通过何种手段与大臣进行斗争的,以及,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最终给明朝带来了什么。
时间回到正德十六年。
这年,年纪轻轻的正德皇帝朱厚照突然驾崩。由于正德皇帝不但没有子嗣,而且没有兄弟,因此,谁来继承这个皇位,就成了一个重大的问题。
当时,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暂时掌管了政权。通过与正德皇帝的母亲昭圣皇太后商议,内阁最终决定由正德皇帝朱厚照的堂弟,兴献王朱祐杬的长子朱厚熜来继任皇帝,是为嘉靖皇帝。
到这里,我先跟你梳理一下嘉靖皇帝朱厚熜他们家的情况。
朱厚熜的爷爷朱见深是皇帝,伯父朱祐樘是皇帝,堂哥朱厚照是皇帝,但他爸朱祐杬不是皇帝。也就是说,本来皇位应该是在他伯父朱祐樘、堂哥朱厚照这一支传下去的,跟他这一支没有关系。不过,朱厚熜的伯父弘治皇帝朱祐樘只有一个儿子,就是他堂哥正德皇帝朱厚照,而朱厚照没有儿子,因此,在正德皇帝朱厚照驾崩之后,皇位在他们这一支传不下去了,这才轮到朱厚熜来继承这个皇位。
那么,为什么是朱厚熜,而不是其他的皇亲来继承皇位呢?杨廷和搬出了由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颁发的《皇明祖训》,里头有一条规矩,叫“兄终弟及”。也就是说,皇位可以由兄长传给自己的弟弟。
但是,严格来讲,朱厚熜只能算是朱厚照的堂弟,而不是亲弟弟。那怎么办呢?杨廷和他们想出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那就让朱厚熜认正德皇帝朱厚照做哥哥呗!也就是说,让朱厚熜过继到他伯父家里,认他伯父作父亲,认伯母作母亲,认堂哥作哥哥,如此一来,“兄终弟及”名正言顺,这问题不就得到完美的解决了吗?
在杨廷和他们眼中,这可是他们几位忠臣煞费苦心的安排,改认父亲,两难自解,既维护了弘治皇帝的君统,又遵守了“兄终弟及”的规定。但是,到了嘉靖皇帝这儿,味儿就变了:什么?我伯父是我爸,那我爸是谁?大臣告诉他,那当然就是叔父、叔母啦!
杨廷和指示吏部尚书毛澄告诉嘉靖,按照规矩,你应该称你的伯父为“皇考”,“考”就是死去的父亲的意思,至于亲生父母,应该分别称为“皇叔考兴国大王”和“皇叔母兴国太妃”。在毛澄他们看来,允许嘉靖的亲生父亲在“王”面前加个“大”字,就已经很够意思了,所谓“尊荣至极”。
为了防止有人有异议,杨廷和一开始就放出狠话,说:“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把这事儿给上纲上线了。如此一来,朝堂上就形成了一面倒的局势。而此时的嘉靖,虽然贵为皇帝,但也没法跟看上去铁板一块的文官集团叫板。一方面,是因为他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很多东西他还没有完全搞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势单力孤,自己从封地带来的也就那么几个人,而且素质也不怎么高,很难给他提供有效的指导和帮助。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慢慢起了变化。原来,杨廷和虽然用他的威胁震慑了朝臣,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朝臣都因此跟杨廷和一条心了。更何况,嘉靖这边又一直对杨廷和的这个安排意见很大,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于是,渐渐地,反对嘉靖改认父亲的声音也开始冒了出来。
转机出现在一个小人物身上。当时,礼部有一名刚考上进士不久,正处于实习试用期的官员,叫张璁,他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给嘉靖呈上了《正典礼》疏,里头详细批驳了杨廷和他们的论述,并且指出继承皇位和给人当儿子是两码事,一码归一码,怎么可以混为一谈呢?
嘉靖看到张璁这些说法,十分兴奋,说:“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随后,嘉靖决定要尊自己的亲生父亲为“兴献皇帝”,母亲为“兴献皇后”。结果,内阁是一点面子也不给,直接封还了嘉靖的手诏。这可把嘉靖给气的。
当时,嘉靖本人已经在北京即了皇帝位,但他的母亲蒋氏还没到北京。这也可以理解,“国不可一日无君”,正德皇帝去世之后,嘉靖得赶紧赶过来继位;而蒋氏就没有那么着急了,可以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妥当了再出发。
到了九月,蒋氏抵达通州。听说自己的儿子当了皇帝得改认别人当妈之后,蒋氏表示老娘不干了,我不进京了。嘉靖也很绝望,于是开始闹,说这皇帝我不干了,我要跟我妈回湖北封地去。这把内阁搞得很头疼。最终的结果是,双方都各退一步,嘉靖这个皇帝还继续干,不闹了,但他的亲生父母的规格得往上提,称“兴献帝”和“兴献后”。
后来发生的事儿,大概也都是在闹类似的问题。比如嘉靖想给父母再提高一点规格,加个“皇”字,变成“皇帝”和“皇后”,结果这下轮到杨廷和不干了。杨廷和表示,你要这么干,那我辞职,老夫不干了。于是嘉靖只能作罢。但他并没有放弃,而是瞅准机会就反复试探,最后还是成功把这个“皇”字给加上去,并且弄走了杨廷和。
成功把父亲变成“皇帝”后,嘉靖又想确认他们的父子关系,表示要称自己的父亲为“本生皇考”,所谓“本生皇考”,就是说这是生我的那个爸。再后来,嘉靖又想去掉“本生”两个字,他觉得,我爸就是我爸,又怎么还要强调“本生”呢?一个人只能有一个爸,生我的这个就是我爸,我伯父就是我伯父,不能是我爸。于是,他又打算改口称自己的伯父为“皇伯考”,称亲生父亲为“皇考”。
但是,嘉靖皇帝的这一系列举动,让很多支持杨廷和观点的大臣十分愤慨。他们强调:“本生二字,上干宗庙,内干宫闱,事体重大。”随后,就发生了咱开头讲到的那一幕。
嘉靖三年七月,一帮刚下早朝的官员振臂高呼:“万世瞻仰,在此一举,今日有不力争者,当共击之!”杨廷和的儿子杨慎此时也在其中,他呼吁道:“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于是,在杨慎等人的鼓动下,二百二十多位大臣一起伏跪在左顺门外,放声大哭,要嘉靖收回旨意。这件事儿最后演变成了激烈的君臣对抗,结局是八名带头的大臣被捕,四品以上的官员停薪,其余一百八十多位官员遭廷杖,其中有十七人直接被打死。
经此事件之后,支持杨廷和的势力已然是强弩之末。而在后续二十年的时间里,嘉靖仍然不断地在各个方面去抬升他亲生父亲的地位,最终让他父亲的神主以“睿宗”的身份入袝太庙。至此,我们可以说,嘉靖的父亲朱祐杬虽然在生前没有当过一天皇帝,却在死后获得了无异于皇帝的待遇。
这场“大礼议”,最终以嘉靖皇帝的大获全胜落幕。
听完了“大礼议”事件的完整经过,不知道你会觉得哪一方更占理呢?
如果按照我们最朴素的直觉,不允许一个人叫自己的父亲为父亲,这本身就是一个很不合人情的行为。
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的场景,站在杨廷和的立场,要求嘉靖认伯父为父亲,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首先,国家礼法高于私情。杨廷和认为,作为一名君主,国家的礼法肯定要放在个人私情的前头的,不能只顾私情,不顾正统大义。这话说得大义凛然,没毛病吧。
其次,大宗小宗不可乱。按照宗法制度,嘉靖的伯父弘治皇帝这一脉是“大宗”,是皇位正统,而他爸这一脉是“小宗”,是藩王支系。因此,嘉靖只有接续上弘治皇帝这边的宗统,才能确保皇位传承的合法性。
杨廷和他们迎立少年朱厚熜来当皇帝,有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皇明祖训》。而《皇明祖训》当中明明白白规定的是“兄终弟及”,是同母弟才能继承哥哥的皇位,显然,嘉靖并不是正德皇帝的同母弟。只有当他过继给了伯父家,成了弘治皇帝的儿子,正德皇帝的弟弟,这样一来,他当皇帝,才能算是符合所谓“兄终弟及”的规定。
再次,像嘉靖皇帝这样,过继给之前的皇帝当儿子,之后继承人家皇位的,历史上是有先例的。比如说,北宋的宋英宗,他的亲生父亲是濮王,但由于他过继给了宋仁宗当儿子,于是他就继承了宋仁宗的皇位。当了皇帝之后,宋英宗认的父亲是宋仁宗,至于他的亲生父亲,他也只能叫伯父了。当时,宋英宗还为他亲爹争过名分,但没有什么结果,后来也就接受了既定事实,历史上把这件事称为“濮议之争”。所以,杨廷和他们的论述,也被称为“濮议论”。说白了,嘉靖不能“既要又要”。
最后,杨廷和他们也想好了“两全”的配套措施。原来,嘉靖是他父亲的独子,这就意味着,如果嘉靖过继给了他伯父,那他爸这一支将绝后。但杨廷和他们把这事儿也给想到了,他们从皇亲当中挑选一位跟嘉靖同辈分的崇仁王,让他来承接嘉靖父亲的香火,而且,嘉靖未来如果有了多位孩子,也可以过继一些来承接他爸这边的宗脉。
在杨廷和看来,这样的安排简直完美,既不失伦理亲情,又不违背宗法大义,天理人情都顾全了!你嘉靖怎么就不能明白我们老臣的良苦用心,而要去听那些小人的谗言呢?
但是,你要是反观嘉靖和张璁的说法,你也会觉得他们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首先,礼法人情本是一体。按照《礼记》里的说法,礼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底冒出来的,而是根据人情来制定的。“圣人缘人情以制礼”,礼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得根据现实人情和血缘伦理,作出适当的调整。就像咱刚刚说的,以咱最朴素的道德直觉,逼着一个人不认自己的父母,本身就是一件违背人性、不合情理的事。更何况,“孝亲”本来就是儒家理论的核心。
其次,君统和宗统得分开看。继承皇位和给人当儿子,这是两件事。这就涉及争论双方的一个核心分歧,嘉靖继承的是谁的天下?嘉靖、张璁这一方认为,嘉靖继承的是祖宗的天下,因此,嘉靖接续伯父、堂哥留下来的君统,并不需要成为伯父弘治皇帝的嗣子。
从这个角度,嘉靖这一方对所谓“兄终弟及”也有了自己的解释:“《祖训》兄终弟及,可推之无穷,而施由亲始。先及同父,次及同祖,皆所谓伦序也,非专指同产言也。”按照张璁的说法,在嘉靖堂哥正德皇帝没有子嗣,也没有兄弟的情况下,依照“兄终弟及”的原则,那就得往上追溯,到嘉靖的伯父弘治皇帝这一辈。弘治皇帝有个弟弟,就是嘉靖的生父兴献王,按理讲,兴献王就应该是那个依照“兄终弟及”原则登上皇位的人。但此时,兴献王已经过世,那么,皇位就自然落到了兴献王长子朱厚熜这里了。换言之,嘉靖之所以能够获得皇位,并不是因为他是弘治皇帝的嗣子,而是因为他是兴献王的长子。是兴献王长子这个身份,赋予了他继承皇位的资格。既然如此,他又何必过继给弘治皇帝当儿子呢?
最后,嘉靖一方认为,杨廷和他们推崇的所谓先例,其实一点也站不住脚。毕竟,像宋英宗他们,是早早就被前任皇帝收为养子的,所以,他们继承养父的皇位,自然得继续奉之为父亲。但嘉靖不一样,嘉靖是等到他堂哥过世之后才来继承皇位的,正德皇帝遗诏里明明写的是“嗣皇帝位”,说明朱厚熜就是直接过来当皇帝的,跟所谓先例完全不是一码事。
当然,这场旷日持久的“大礼议”,双方还有很多细碎的论点,咱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总的来讲,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双方都能够从传统的经典当中找到支撑自己论点的论据。
从双方交锋的观点来看,估计你也感受到了,这表面上是一场称谓之争,但实际上是一场名分之争,如果我们再往深一层去探究,还会发现,所谓名分之争,本质上是权力之争。以杨廷和为代表的文官集团,看似在捍卫礼法,实际上是在争夺对礼法的解释权;而嘉靖看似在追求孝道,实际上却是在争夺不受文官集团制约的皇权。
为什么这么说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先来看看“礼”在中国古代社会当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并不是仅仅靠依凭由上至下的暴力。只靠暴力,王朝也持久不了。就好比说秦朝,它虽然借由暴力吞并了六国,但由于难以收服天下人心,最终二世而亡。
因此,古代的统治者会通过一种制度性的媒介,来建立维护政权秩序的合理规范,展现政权的“公义”,让民众能够认同他的政权的理念。
这种媒介,就是我们所说的“礼”。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即军事,也就是咱说前面的暴力;“祀”即祭祀,说的也就是礼。
在古代,“礼”被内化于各种典章制度之中,上到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下到民间百姓的日常往来,都有详细且严格的规范。这样一来,社会就有了一套严格的身份等级,每个人可以按照他的身份被纳入到一套名分礼秩体系之中,社会就能够平稳运行。换句话说,所谓“礼”,并不仅仅是我们表面看到的像叩头跪拜这样的一些礼节或者仪式,它的作用在于,让政治秩序和人事关系有合理的规范。
所以,名分在古代是极其重要的。嘉靖以孝亲之名,不断地抬高自己父亲的地位,实际上达成的效果就是强调了自己的皇权的正当性:他要表明,他不是因为过继给伯父家才得到了这个皇位;而是因为他爸本来就能够接续这个君统,他是名正言顺地继承了皇位。如此一来,他就不用被笼罩在杨廷和他们的权力阴影之下了。确定了这个名分,实际上也是巩固了他的皇权。
这也是为什么嘉靖在明明已经为他爸争到了名分,能够管自己的爸叫爸之后,还非要把让他爸进太庙。事实上,尽管在“大礼议”事件当中,张璁整体上是站在嘉靖这边的,但他同样不支持让嘉靖的父亲朱祐杬进太庙,理由很简单,朱祐杬没做过一天的皇帝。
嘉靖也知道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理亏,但他迂回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他在太庙旁边给朱祐杬建了一个庙,随后,将原本放在一块的明朝历代皇帝神主牌分散放入一个一个小房子里,这样一来,原本祭祀他爸的家庙就与之混在一块了,你要不特别说明,还真看不出来它跟九间太庙有什么区别。再后来,经过很复杂的一番操作之后,嘉靖他爸的神主最终入了太庙,整个过程花了整整24年的时间。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礼”对皇权的制约作用。
在我们传统的印象里,皇帝那得是乾纲独断,尤其是明清时期的皇帝,由于废除了丞相,那更是没人能够制约他们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嘉靖实际上还是受到了礼制的极大束缚的,否则,他也不用花整整24年的时间才能够办成对他如此重要的一件事。
而嘉靖不断地跟臣下讨论经学,调整国家礼制,还弄出了一本《明伦大典》,实际上也是在借由对经典的诠释,来帮助他扩大手中的权力,挣脱“礼”对他的束缚。
对于皇帝来说,“礼”是把双刃剑,它既关乎皇权合法性的来源,又会成为臣下拿出来压制皇权的依据。所以,嘉靖的“议礼”行为,实际上就是通过把“礼”掌握在自己手中,一面论证自己的皇权合法性,一面打击臣下对自己的制约。
但是,这里头有个很微妙的点,按照尤淑君老师的讲法,嘉靖借由“议礼”扩大了皇权,但他的一系列举动又实际上破坏了礼法秩序,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得先来聊聊,在古代,人们是如何理解皇权的合法性的,也就是说,古人为什么认可天下需要一个皇帝。
我们知道,在古代,中国有一种天命思想。所谓天命思想,说的是皇帝受命于天,是上天之子,同时也是天与人之间的媒介。不过,天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归属有个重要的依据,那就是民心。也就是说,天命从来都没有赋予皇帝绝对的权力,相反,它会以所谓“道”来约束皇帝的权力,让皇帝不能自行其是、为所欲为。
而这所谓的“道”,就是皇帝制度当中的“公义”部分。它的要旨是:“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也就是说,皇帝是天下人的代表,应该以民众为念,再执行皇帝的权责。而一旦皇帝违背了公义,必然会遭到上天的抛弃,臣民也可以“从道不从君”。那么,“道”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礼”和“法”。换言之,所谓“礼”,其实本身就带有了“公”的属性,它凝聚了人们的共识。
所以,一旦嘉靖借用“议礼”来扩大自己的皇权,让“礼”为“私”服务时,它其实也是在扭曲礼法秩序,毁坏人们的共识。于是,君、臣、民三方失去了共同认可的行为规范,开始各行其是,故而开启了政治混乱、君臣冲突、社会失序的危机。
在尤老师看来,明末的党争,祸根其实也在嘉靖这儿。本来,很多大臣还抱有“为王者师”的理想,但嘉靖破坏礼法秩序,将礼法从“天下共守的准则”变为“皇权操控的工具”,这种试图将皇权私有化的做法让很多人心灰意冷,最后变得消极顺从,只求明哲保身。
此后,被皇权碾碎的文官集团开始分裂重组,朝堂上的权力平衡被打破。这也催生出了一次又一次的权力之争,在这些斗争过程中,有些大臣为求自保,开始拉拢亲近自己的人搞小团体,私下结党,最后演变成了明末朝堂上臭名昭著的党争。
好,到这儿,这本《大礼议》的主要内容,就为你介绍完了。
听完了前面这些内容,不知道你对“大礼议”这个事件本身,会不会有一些新的看法呢?
咱来对今天的内容做一下归纳。咱今天聊的是明代嘉靖朝的“大礼议”事件,表面上看,这是一个争论皇帝“该不该管自己的父亲叫爹”的口水仗,但实际上,它涉及的是朝堂上的权力之争。
首先,杨廷和等人主张濮议论。虽然他们的观点显得不通人情,但他们坚信,他们的坚持能够确保皇权的公共性质,这样一来,皇权才能被包含在天理纲纪的框架之中,避免绝对的专制。
其次,张璁等人主张人情论。他们基于现实人情的考虑,着眼于每个个体都有亲亲之私的需要,强调不应该把嘉靖皇帝想要尊崇父母的那份孝心当做不正当的私欲。
但是人情论的最终目的,还是在于把皇帝的亲亲之私收入天理纲纪的价值体系之内,而不是要把“私”抬到“公”的上面,更不是支持嘉靖皇帝让自己的父亲入太庙,自创新宗统、取代旧宗统的政治行动。
然而,这样的一些争论,使得礼法在“公”与“私”之间出现了灰色地带,嘉靖借此扩张了皇权,却破坏了国家礼法的基础,朝堂形成了党争不断的政治生态,最终影响了明朝历史的走向。
以上就是我为你分享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对书中其他内容还有兴趣,也建议你去阅读原书。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1.“大礼议”表面上是称谓之争,实际上是名分之争、权力之争。
2.在古代,“礼”并不仅仅是一些表面的礼节或者仪式。它的作用在于,让政治秩序和人事关系有合理的规范。
3.嘉靖借由“大礼议”扩张了皇权,却破坏了国家礼法的基础,朝堂形成了党争不断的政治生态,最终影响了明朝历史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