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极亚洲中的唐朝》 朱步冲解读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 朱步冲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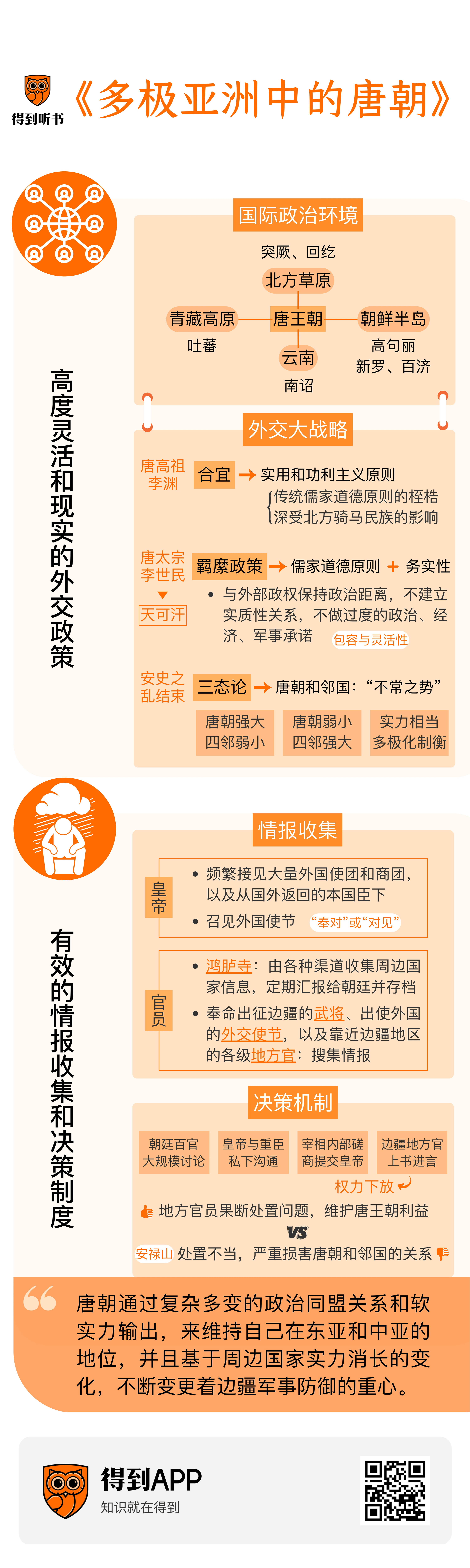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书,是历史学家 王贞平的《多极亚洲中的唐朝》。
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强盛的王朝之一,具备高度的国际与开放性,中国传统文化也在唐和两宋之间,达到辉煌的高峰。著名日本历史学家森安孝夫说,在七到八世纪之间,唐帝国是全世界当之无愧的第一流世界性大帝国,首都长安,更是首屈一指的国际性大都市。唐帝国的影响力从东亚沿海、朝鲜半岛与日本,一直蔓延到今天的中亚各国。丝绸之路,也因唐帝国的存在,而变得畅通繁盛。
为什么唐朝能够在亚洲乃至世界政治舞台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传统历史学家的观点是,唐朝从初期到中叶,凭借强大的武力和发达的经济文化,建立了以自己为绝对中心,以传统朝贡体系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秩序。不过,本书作者王贞平通过多年研究,却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新观念:那就是,哪怕在唐帝国实力和影响力最为鼎盛的时期,它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也更类似今天的世界,呈现出多极化和动态性的特征;而唐王朝的外交政策,也和之后的宋明王朝不同,体现出一种更为现代、务实灵活的价值取向。
在本书中,作者王贞平试图从7到10世纪 ,唐朝与周边国家势力此消彼长,动态博弈的视角,来分析唐王朝的外交政策。他强调,从本质上说,唐与周边政权之间的关系,既不是自己占据绝对支配地位的朝贡关系,也不是简单的零和博弈。而是在相互依存与制约的过程中,维护一种动态平衡。在唐王朝经历安史之乱,军事与政治实力衰落后,历代唐王朝君主也能运用所谓“软实力”:通过自己发达的文化、繁荣的经济、完备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向外输出影响,延缓支配力的衰落,在国际政治中维持对自己相对有利的外交与政治地位 。
接下来,我就分两部分,为你解读本书的内容,首先我们来看看,在当时亚洲多国并立的政治体系中,唐朝务实而灵活的外交政策,是如何形成的。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再来看看,唐朝是如何通过有效的信息收集和决策机制,将自己的外交政策落地,并及时作出调整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唐王朝在存在的将近3个世纪 里,所处的国际政治环境。作者王贞平说,自从周代以来,统治华夏文明区的各个王朝,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如何处理与周边地区国家、政权和民族关系的问题。而唐王朝在建国之初,就发现,自己所处的国际政治地理环境,比往日任何一个朝代都复杂,更具竞争性:在朝鲜半岛上,有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在北方草原上,有强大的骑马民族突厥和回纥 ,在西侧的青藏高原上,有羌民族建立的吐蕃,而在云南,还有新兴的部落国家南诏。所以说,唐王朝要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中生存发展下去,就必须制订一套与之相匹配的外交大战略。
于是,唐高祖李渊,这位唐朝开国君主,就为唐代的外交政策,定下了一个明智的基调:简简单单两个字“合宜”。说到这里,就不得不叹服古汉语的博大精深:“宜”这个字,包含了很多含义,例如准确评估自己和竞争对手,或者敌人的相对实力,以及预测行动后果等一系列运筹帷幄的考量 。作者认为,“合宜”的本质,就是采用一种实用和功利主义的原则, 来指导唐王朝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抛开传统儒家道德原则的桎梏,之所以出现这样独特的状况,也与李渊和唐朝很多开国功臣家族,在出身和血统方面,深受鲜卑突厥等北方骑马民族影响有关。纵观唐代历史文献,一项政策是否“合宜”,往往是皇帝与朝廷百官讨论的中心议题。
早在山西晋阳起兵反隋时,李渊就面临着一次重大的外交路径抉择:就是一旦挥军南下,如何处理和北方骑马民族东突厥的关系。当时,东突厥一直袭扰隋朝的北部边境, 许多其他起兵反隋的割据势力,也向东突厥俯首称臣,以换取军事支持。 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如果处理不当,那么东突厥或者支持的其他反隋势力,可能会趁机出兵,让自己陷入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于是,李渊决定,臣服于东突厥,但只象征性地接受对方少量军事援助, 也就是精锐的突厥骑兵来助战,努力把双方的关系保持在一种借兵助战的军事联盟状态。所以,在起兵时,李渊的唐军军旗,是红白两色 :红色是隋代官方仪仗使用的颜色,而白色,则是突厥部落军旗的主色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就分析说,这一举动体现了李渊与李世民父子娴熟而狡黠的政治手腕,在向其他对手彰显自己忠于隋朝的同时,表明东突厥对自己的支持。
到了唐太宗李世民当政期间,随着唐朝国力的逐渐恢复和统治的巩固,唐朝迎来了一个积极进取、扩充影响力的新阶段。从公元630年到640年,唐太宗部署唐军进行了三次军事行动,分别打败了东突厥、青海地区的吐谷浑,以及位于今天新疆 的高昌国 。644年,唐太宗更御驾亲征,率军讨伐高句丽 。
然而,对唐朝初年的对外扩张政策,在朝廷内部始终有不同声音,很多大臣表示激烈反对。作者王贞平在书中说,这种节制,主要来自唐初的名臣魏征。魏征的核心主张就是,隋炀帝好大喜功,连年对外征战而导致亡国的教训,还历历在目;唐的国力有限,对周边国家和政权,不应该做出过度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承诺,而是要把主要资源和精力用在内部治理上 。此外,即使唐军获胜,也消耗了宝贵的军事实力,更会因为试图控制占领地区,而背上沉重的负担。
实际上,从唐王朝疆域的西部到北部,居住的大多是游牧,或者半游牧民族。他们随着季节变化在草原上迁徙,平时会和华夏农耕文明进行边境贸易换取必需品,但一旦发生气候灾变,牲畜死亡,就会南下劫掠。同时,动荡的内部权力斗争和民族部落之间的战争,又使得失败者往往选择南下,投靠唐朝。
在当时的儒家士大夫看来,这种首鼠两端的行为,实在是令人愤慨。但是,正如前面所说,由于唐朝皇室从出身与文化上,都深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所以能够在制定对外政策时,把儒家的“德”“义”等道德原则,和实际上的务实性结合起来。
魏征提出的一系列政策,被统称为羁縻政策。“羁縻”这个词,最早来自东汉时期的史学大家,《汉书》的作者班固。他提出,全面战争,或者全面和平,都不是有效应对北方草原民族的最佳策略。华夏农耕文明帝国应该和他们保持一种平衡与制约的战略:在军事上常备不懈,能打防御战;同时,在外交政治上,不强行向对方输出制度文化,不给予对方平等地位。但是,如果对方因为文化仰慕和经济需求,前来主动示好,则应该盛情迎接,以礼相待。可以说,班固的思想,是在儒家道德的框架内,对中原与草原关系进行一种务实性的考量,对唐代初期外交战略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但是,魏征强调说,唐朝应该采取的羁縻政策不应照搬汉朝的模式。唐与外部势力的接触应该是有限的。这个政策的核心观念是与外部政权保持政治距离,不建立实质性关系,不做过度的政治、经济、军事承诺,强调包容与灵活性 。听上去很有一些近代国际政治中“离岸平衡与仲裁”的意味,这套政策得到了李延寿、褚遂良等其他开国功臣,以及李世民本人的赞许和支持。
魏征的羁縻政策,构成了唐王朝对外关系的基点。用唐太宗自己的话说,就是“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也就是说,唐帝国是一个对周边民族开放的政治和经济联盟体系,唐朝皇帝,同时是华夏文明区域的皇帝,和周边草原地区的领袖。唐王朝允许那些前来归附,表示友好的邻国,既不必把自己奉为唯一的宗主国,也不必改变自己的风俗习惯。而对于唐朝利用军事力量征服的地区,则尽量扶持原有部落首领进行统治,同时在当地设立都护府,派兵维持秩序。
唐王朝对周边国家政策的成功,可以从一件事上看出:公元630年,唐太宗接受了西域各部落进献的尊号“天可汗” 。可汗,是草原民族部落首领的尊称,而天可汗,则可以被看作是各部落公推的盟主。
贞观二十三年五月 ,也就是公元649年公历七月,李世民突然去世,在长安居住的西北各部落贵族,都非常悲痛,纷纷采用了草原骑马民族的习俗进行哀悼。当然,这些习俗在今天听起来非常野蛮和血腥,比如用刀割掉自己的耳朵,割伤面部,以及剪掉头发,甚至有两位北方草原民族出身的武将,要求按照草原上的惯例,自杀为太宗殉葬。 顺便说一句,即便到了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国力日渐衰微,但西北游牧民族依然尊奉唐朝皇帝为“天可汗”。
当然,从另一方面说,这种合宜的外交指导思想,也意味着根据双方力量对比的消长,随时改变策略,甚至有时要不惜背信弃义。作者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对于在今天蒙古图拉河流域崛起的游牧部落薛延陀,唐朝的外交政策经历了多次反复:从扶植薛延陀对抗东突厥 ,到薛延陀强大后,唐朝又接受东突厥的归顺,反过来限制薛延陀的扩张,防止它在北方一家独大。公元642年,唐太宗准备将新兴公主嫁给薛延陀部落首领夷男,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缓兵之计。第二年,唐太宗就重新评估了局势,决心以武力解决这个心腹大患。 公元645年,夷男病死,薛延陀内部发生权力斗争,唐太宗借机出动大军,并联合突厥、契丹、奚等草原部落,一举消灭了煊赫一时的薛延陀 。
另外,唐代在与邻国的政治博弈中,也特别善于发挥自己的经济、文化制度优势,把这些优势转化为软实力。历代唐朝帝王,都努力利用这种软实力,来维护唐王朝的威望与地位:比如,持续吸收周边各国贵族子弟、移民或者留学生入境,让他们担任唐代中央和地方官职,或者送进国子监学习儒学经典。这样,等他们回到国内执政时,就会形成一个个深切仰慕唐朝制度,倾向于和唐朝保持友善关系的利益集团。同时,唐朝帝王定期举办各种外来使节接见活动并赏赐丰厚的礼物;在与邻国和亲的时候,往往会把大量工匠和丝绸等特色产品作为公主的陪嫁一起送出。这一切都是在向周边邻国展示,唐帝国在各个方面的先进与强大,如果邻国和自己保持友好的关系,那么就可以获取丰厚的利益,共享繁荣。
在安史之乱结束后,唐朝的军事实力和政治权威都有明显下降,变得更加依赖周边邻国,尤其是各骑马民族的军事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唐德宗提出了一个明智的判断,说唐朝应该接受一个全新的现实,就是唐朝和邻国的关系属于“不常之势”,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承认国际关系中,各方地位和彼此关系,始终处于一种流动和变化之中。
公元793年,翰林学士陆贽,写了一份详细的奏折献给朝廷,把德宗的这种思想加以细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三态论”。 说白了,陆贽把唐朝与邻国关系,归结为三种状态 ,分别是:唐朝强大,四邻弱小;四邻强大,唐朝弱小,以及唐朝与邻国实力不相上下,呈现多极化制衡状态。
那么如何针对这三种情况来具体制定唐朝的外交政策呢?陆贽提出,在唐朝整体军事实力和物质资源下降的情况下,只能立足防守,并且要利用周边各国的矛盾,通过外交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 尽量争取“不战而胜”。
比如,唐朝与北方著名游牧民族回纥的关系,就体现了这种实力政治中的持续博弈:从公元747年到841年,多达11位回纥部落首领,接受了唐朝赐给的可汗称号。这是因为,回纥本身是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每一位首领都需要唐朝的支持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但即便如此,双方的关系也不是一帆风顺。在唐初,回纥曾经出兵帮助唐朝攻打突厥 和薛延陀 ;在安史之乱中,回纥支援的精锐骑兵,是唐朝最终能够战胜叛军的关键因素。但是,回纥看到唐朝国力衰败后,就逐渐改变了往日的恭顺态度,要求唐朝为军事援助和政治同盟支付更多的财物,并且开始入侵唐朝边境,烧杀掳掠。
尽管如此,唐朝并没有与回纥决裂 。这是因为,崛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对唐代西部边疆的威胁越来越大。所以,唐朝必须继续借助回纥的军事力量来与之对抗。于是,唐德宗就在著名谋臣李泌的劝说下,通过和亲,挽回了唐与回纥之间濒临破裂的政治同盟 。作为回报,回纥军队持续在西北和吐蕃开战,替唐朝分担吐蕃的军事压力,维持着唐朝与西域各都护府之间的陆路通道 。
8世纪末,回纥部落改名为回鹘,以表示对唐朝的忠诚 。9世纪中期,由于内乱,回鹘政权瓦解,一部分部落贵族率部进入唐朝境内,请求收留。例如,公元842年,回鹘可汗的兄弟嗢没斯 就率部来到天德军,也就是今天内蒙古巴彦淖尔一带。此时,当地的唐朝地方官就觉得对方来者不善,要求用武力将他们驱逐出境。但是,宰相李德裕力排众议 ,说回鹘一直是唐帝国的盟友,而且对方如同走投无路,主动落入怀抱的飞鸟,怎能乘人之危。不仅如此,唐朝此时国力衰弱,兵力有限;驱逐嗢没斯,还要向周边的吐谷浑等部落借兵,万一吐谷浑趁火打劫,唐朝不仅在道德名分上有了缺憾,还会遭受实际损失。
最后,唐武宗明智地接受了李德裕的建议,给嗢没斯发放粮食等后勤物资,还封他做左金吾卫大将军、怀化郡王,赐给他一个汉族名字叫李思忠 。由于唐朝皇室也是李姓,所以这是对嗢没斯的一种优待和笼络。同时,唐朝还在西北各地,让前来归附的回鹘武士建立军事据点和堡垒,充实了唐朝中后期的西北边疆防御。后来,这一批回鹘武士的后代,在唐朝末年平定黄巢起义的军事行动中,也发挥了相当的作用 。
唐朝这种因时而动的灵活外交政策,必须要有一套有效的情报收集和决策制度来作为支撑。在这个方面,比起前代王朝,唐帝国可以说是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与探索。
首先来看看情报收集工作,及时了解周边各国和部落政权的情况,是制定外交战略的基础。作者王贞平在书中说,几乎从历代皇帝本人,到各级中央和地方官员,都广泛、积极主动地参与了这项重要工作,成了唐朝自始至终的基本政策。
首先,由于唐王朝的开放性,皇帝会频繁接见大量外国使团和商团,以及从国外返回的本国臣下,包括军人、使节,以及僧侣等等。例如,公元645年,唐太宗就盛情接待了从印度取经跋涉而归的高僧玄奘,也就是《西游记》里唐僧的原型。在会谈中,唐太宗最感兴趣的,就是玄奘到达过的印度各国,以及喜马拉雅地区的地理、物产和风俗。唐太宗的求知欲,不仅是因为好奇心的驱使,更是因为这些资讯有助于他制定唐朝在西域的外交政治战略 。
作者说,在这种持续的学习了解中,唐太宗对西域的情况,可以说了如指掌;书里特地还举了一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在前一年,唐军远征西域的焉耆国,它的位置,大致位于今天的塔里木盆地。根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根据自己掌握的地理知识,居然能精确推算出唐军抵达焉耆,与攻克城市的日期, 还自言自语地说“如果一切顺利,报捷的使者今天也该回到长安了”,结果唐太宗话音未落,臣下就禀报,使者果然刚刚抵达。
同时,皇帝搜集情报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召见外国使节,这种仪式被称为“奉对”或者“对见”:在翻译的帮助下,宾主双方互致问候,然后皇帝就会提出各种关于使节所代表国家的问题 ;例如672年,唐高宗接见吐蕃使者的时候,就直截了当地向使者提问,包括在位的吐蕃君主,也叫赞普的性格怎么样,他和大臣的关系,以及吐蕃政治制度有什么特点等等 。
当然,由于个人精力,皇帝从这些直接渠道获取的情报,肯定有限,所以他必须更多依赖下属官员收集的相关信息。这个重担,首先落在主持外交礼宾的机构,鸿胪寺的负责人鸿胪卿头上。
在之前解读过的《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这本书里,大家可能听到过一个名字,贾耽 。贾耽曾经身兼宰相和鸿胪卿这两个重要职务,从而让他有机会大量接触各国使节,和出使外国的唐朝官员。博闻强记的贾耽,不仅主持绘制了囊括整个唐朝疆域和周边地区的大型地图《华夷图》 ,还编纂了一部丰富详细,多达40卷的《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 。这本书,可以算是“华夷图”的文字说明材料,汇总了唐朝境内和周边国家的地理交通状况。实际上,鸿胪寺各级官员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把各种渠道得到的周边国家信息,定期汇报给朝廷,并且存档。
另外,奉命出征边疆的历代唐朝武将、出使外国的外交使节,以及靠近边疆地区的各级地方官,也都肩负搜集情报,呈报朝廷的重任。比如,唐代中期的著名政治家,李德裕,就在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时候,用两年时间完成了一部《西南备边录》,详细记载了西南地区各个部落政权的状况,以及这些部落与唐朝发生冲突的细节 。
有了丰富而充足的情报,那么接下来关键性的一步,就要有一个相对高效稳妥的决策机制,迅速、正确地处理各种外交政务。作者王贞平总结说,唐朝历代皇帝在制定对外政策的时候,一般会有四个环节,朝廷百官的大规模讨论,皇帝和少数重臣在非正式场合进行沟通,交换意见,然后,作为官员首脑的宰相,会再进行一轮内部磋商,制定出最终的政策意见提交给皇帝。同时,处在边疆地区,对邻国情况熟悉的唐朝地方官,在处理涉外事务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权,也能通过上书进言,影响唐朝对外政策的制定。
当然,这种“权力下放”的操作是有利有弊。在一些时候,精明干练的地方官员,能够抓住机会,对一些问题进行果断处置,有效维护唐王朝的利益。反过来,在某些时候,一些腐败或好大喜功的地方官员,也会因为处置不当,严重损害唐朝和邻国之间的关系。正反两面的案例,在唐代的历史记载中都有很多:例如,唐朝建立之初,镇守丰州,也就是今天内蒙古河套地区的名将张长逊,就得知了一条情报:当时和唐朝对立的割据势力梁师都和薛举,两个人企图向突厥请求军事援助。由于情况紧急,张长逊没有向朝廷请示,就自己直接拟了一道假的皇帝诏书,送给突厥首领,说唐朝对梁师都和薛举的图谋,已经了如指掌,请突厥不要出兵相助。果然,突厥首领信以为真,拒绝了梁师都和薛举的请求。唐高祖李渊对张长逊的这种自作主张的处置,并没有责怪,反而给了重赏。
反过来说,比如安史之乱的策划者,安禄山,就在自己担任镇守辽宁、河北等地的边军将领期间,多次故意挑起冲突,袭击近邻的契丹、奚等游牧部落,掳掠人口财物,给自己邀功请赏。终于导致在公元745年,契丹和奚,两个游牧部落不堪凌辱,杀掉了唐朝送来的和亲公主,起兵反唐 。
好了,这本《多极亚洲中的唐朝》的基本内容,到这里基本就为你介绍完了。在本书中,作者王贞平详细回溯了唐王朝在将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和北方游牧民族突厥、回纥,朝鲜半岛的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 ,西方的吐蕃,以及南方的南诏等主要邻国的政治交往与博弈。作者指出,即使唐帝国在鼎盛时期,它也不是东亚和中亚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唯一霸主,它和邻国的关系,也不像传统中国历史典籍中所描绘的那样,是一种单纯的主从关系。实际上,如果从宏观角度观察当时欧亚大陆的东半部,就会发现,至少有四大强国,拥有在这个地区称霸的实力和意愿:包括位于东端的唐帝国、北方草原上的突厥以及后继的回鹘、处于青藏高原的吐蕃,以及西部的伊斯兰帝国,它们之间的矛盾,既源于草原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制度冲突,也源于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冲突。唐朝面对的,其实是亚洲政治格局最为动荡的时代。
正因为如此,唐朝从建立开始,就一直保持了一种高度灵活和现实的外交政策,通过复杂多变的政治同盟关系和软实力输出,来维持自己在东亚和中亚的地位,并且基于周边国家实力消长的变化,不断变更着边疆军事防御的重心。
同时,唐帝国本身的命运,也与这种多变复杂的外部环境息息相关。例如,导致唐帝国由盛及衰的安史之乱,也并不是一场单纯的政治内乱:安禄山和史思明所代表的,实际是欧亚大陆草原上的游牧武士集团,和丝绸之路贸易经济力量的结合。这种新生力量在成长到一定程度之后,必然与原本接纳它的唐帝国产生矛盾,甚至产生取而代之的冲动。
历代唐朝帝王和能臣的运筹帷幄,使得唐朝在中后期实力大为削弱的情况下,依旧能够让自己在当时的亚洲政治体系中,维持一个相对重要的地位。然而,在风云诡谲的历史舞台上,这种政治操作的背后,是许多历史当事人无法决定自己命运的悲剧,他们的故事,在今天读来,依旧令人叹息。比如,西安曾经出土过一方墓志,纪念的是一位在公元723年香消玉殒的突厥公主,贤力毗伽公主。 这位公主,在父亲默啜可汗 死后,为了逃避内乱,和兄长丈夫一起投奔唐朝,后来因为丈夫犯罪被牵连,罚入长安皇宫充当奴隶 。
此时在位的唐玄宗,正试图趁突厥内乱之机,联合回鹘、同罗等部落,出兵征讨,铲除这个心腹大患;但联军由于联络不畅,反而被突厥打败。突厥新可汗,趁机向唐朝要求和亲,于是唐玄宗耍了个自以为高明的政治手腕:此时,贤力毗伽公主由于年轻貌美,在皇宫中已经从奴隶变成了妃嫔。玄宗就想将她变成这桩政治联姻的主角 。这样,公主既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也会感恩于自己的收容和恩宠,能够在突厥可汗身边,为双方的政治联盟尽心尽力。
然而,在贤力毗伽公主看来,突厥新可汗是自己的堂兄,这桩婚姻有悖人伦;而且,这位堂兄更是杀害自己亲人的凶手 。根据日本汉学家羽田亨的推测,公主在出嫁前猝然离世,很可能是拒绝充当政治博弈中的棋子,愤而自杀,时年仅有25岁。正因为于此,悲痛的公主兄长,才会让人在她的墓志铭中写下“朝露在阳光下突然散去,疾风吹过松门而发出悲鸣”,这样哀怨伤感的句子。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
本书作者王贞平通过多年研究,却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新观念:那就是,哪怕在唐帝国实力和影响力最为鼎盛的时期,它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也更类似今天的世界,呈现出多极化和动态性的特征;而唐王朝的外交政策,也和之后的宋明王朝不同,体现出一种更为现代、务实灵活的价值取向。
-
唐朝从建立开始,就一直保持了一种高度灵活和现实的外交政策,通过复杂多变的政治同盟关系和软实力输出,来维持自己在东亚和中亚的地位,并且基于周边国家实力消长的变化,不断变更着边疆军事防御的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