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 刘怡解读
《叙利亚》|刘怡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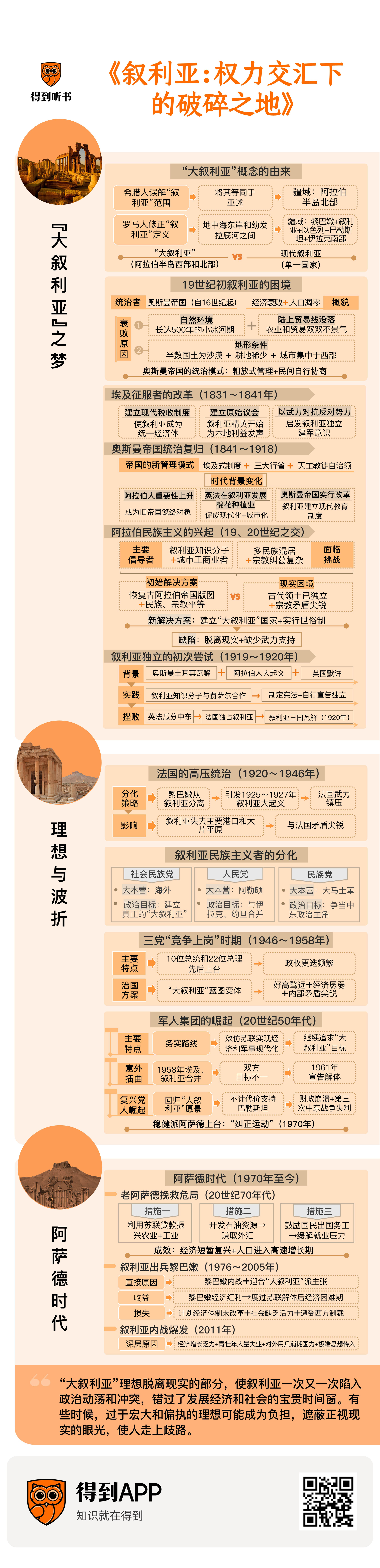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刘怡。今天我要为你讲的书,书名叫《叙利亚》。中文版译者给它加了个副标题,叫“权力交汇下的破碎之地”,其实有点化简为繁了。因为本书的法文原名,直译过来就是《19到21世纪的叙利亚史》。这段历史有什么特殊之处呢?别急,咱们先来说说叙利亚这个国家。
如果我问你,你对叙利亚这个中东国家有什么印象,不同的人或许会有不同的答案。喜欢古代史的朋友多半会说,它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也是早期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播中心。还有朋友可能听说过,叙利亚出产橄榄油和锋利的大马士革钢刀,还出过世界级诗人阿多尼斯。但大多数人对叙利亚的第一印象,多半源自2011年开始的那场惨烈内战。它在十几年时间里,造成60多万人丧生,1300多万人流离失所。内战引发的中东难民危机,深刻影响了欧美各国的国内政治。而席卷整个叙利亚的暴力、民族冲突和大国干涉,直到2024年依旧不曾平息。
我本人对叙利亚,尤其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从2017年起,我曾4次前往叙利亚采访,既踏上过不同势力的控制区,也见证过残酷的交战现场。但接触越多,我对这个国家的感受越是困惑。从国土面积看,叙利亚的大小和中国的湖北省差不多,有一半以上的疆域属于缺水的荒漠,也没有像样的大港口,绝对称不上兵家必争之地。从资源禀赋看,叙利亚虽然有少量石油,但储量还不到邻国伊拉克的2%,从1982年开始人均GDP就持续下降。从社会氛围看,叙利亚自1946年独立以来,一直都是世俗化国家,并不存在激烈的宗教斗争。这样一个“平平无奇”的国家,怎么就会爆发一场撼动整个中东的内战呢?叙利亚的政治能量,和它的经济、社会基础,是不是有点不对等?
而且,这种奇特的不对等状态,还不是从21世纪开始的。早在100多年前,叙利亚就是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的熔炉。“二战”前夕,从黎巴嫩到巴勒斯坦,到处都有叙利亚爱国者在活动,抵抗英法殖民统治。“二战”结束后,叙利亚又参与了5次中东战争中的4次,直到2005年还有海外驻军。它在1958年一度与埃及合并,结成一个新国家,后来又成为阿拉伯复兴主义的倡导者。可以说,在现代中东每一波激进的革命浪潮和军事冲突中,叙利亚都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即使没有后来的内战,它也会向周边地区持续放射能量,扮演超出自身经济和人口规模的国际角色。
要解释这种独特的现象,答案就不能从遥远的古代史里找了。它的奥秘,就藏在本书回顾的19到21世纪叙利亚历史当中。这段时间里,活跃在叙利亚政治舞台上的,不仅有来自奥斯曼帝国和法国的异族征服者,还有形形色色的本地阿拉伯精英。他们为这个新诞生的共和国,规划了好几种发展蓝图,其中既有我们熟悉的苏联式计划经济,也有雄心勃勃的“阿拉伯联邦”。有一个方案,甚至打算把今天的伊拉克、巴勒斯坦、约旦和科威特统统并入叙利亚。不用我说你也能想到,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叙利亚自身的国力上限。正是这种目标和实力的“倒挂”,加上外部因素影响,才使叙利亚陷入了复杂的政治漩涡,并最终引爆了绵延十几年的内战。我们学习本书,除了能搞清楚叙利亚问题的来龙去脉,还可以重新审视政治活动中理想与现实的张力。这对你理解复杂的国际局势会很有帮助。
本书作者马修·雷伊,是法国历史最悠久的学术机构法兰西公学院的历史学副教授,也是法国中东研究所当代研究中心主任。他的学术专长,就是剖析20世纪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政治史,出版过两部相关著作。这本《叙利亚》是雷伊在2018年用法语写成的,2024年翻译成中文。为了撰写本书,雷伊不仅广泛查阅了法国、叙利亚、伊拉克三国政府的解密档案,还在叙利亚住了4年,亲历了内战的爆发。相信这本融入了个人观察的专著,也会让你大有收获。
接下来,我就分三部分,为你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叙利亚在19世纪,是怎样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传播中心的;它的第一次独立,为什么会以失败告终。在第二部分里,我会为你介绍,叙利亚在“二战”前后的政局,特别是它在中东战争中扮演的角色。最后,我再为你概述一下,“冷战”后期叙利亚国家和社会出现的变化,以及2011年内战爆发的深层原因。
开始讲述本书的内容以前,我想先给你讲一段掌故。话说“叙利亚”这个名字,最初其实是源自以讹传讹。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人听说,中东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矗立着一个强大的帝国——亚述帝国。他们就用“亚述”这个词在希腊语中的变体“叙利亚”,统一称呼现在的阿拉伯半岛北部。其实,亚述帝国的核心部分,在今天的伊拉克,跟叙利亚根本就是两个方向。但这个错误的名字,却在古代欧洲流传了好几百年,深入人心。直到公元前1世纪,罗马人登上阿拉伯半岛,才发现了希腊人的错误。他们修改了“叙利亚”这个词的指代范围,把它局限在地中海东岸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相当于今天的黎巴嫩、叙利亚、以色列、巴勒斯坦外加伊拉克南部。这片领土,后来在阿拉伯语中称为“沙姆”,在法语和英语里则叫“黎凡特”。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不管是地理意义上的古叙利亚,还是近代欧洲人口中的黎凡特,它们的疆域都比今天的叙利亚共和国要大好几倍。为了方便区分,欧洲人一般把古叙利亚称为“大叙利亚”或者“天然叙利亚”。可别小看这多出来的一个“大”字,现代中东的许多纷争,都和它有关。这段故事咱们稍后再讲,先回到本书的开篇:19世纪初。
喜欢世界史的朋友都知道,公元7世纪,中东地区一度被纳入阿拉伯帝国的版图。到了16世纪,它们又被奥斯曼帝国所征服,叙利亚也不例外。这个曾经的文明摇篮,经过一系列变故,逐渐变得萧条不堪。原因有两方面:外因是自然环境。从14世纪开始,地中海东岸经历了长达500年的小冰河期,传统的小麦种植业变得极不景气。航海大发现之后,历史悠久的陆上贸易也被海洋取代,加剧了叙利亚在经济上的窘境。内因则是地形条件。如果拿一份今天的叙利亚地图来看,你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全国人口最多的10座城市,有7座分布在西部边境一条狭长的“走廊”上。这是因为,叙利亚东部属于沙漠地带,不适合定居。全国只有28%的土地可以耕种,它们大部分集中在西部这条走廊地带,两侧则是高山。叙利亚传统的农业和陆上贸易,都是在西部这块狭长的平原上展开的。既然这两项产业都不景气,叙利亚也就持续衰败下去。到19世纪初,这里只有两座城市的人口超过10万人。
不过,经济衰败、人口凋零,倒是让奥斯曼帝国的管理工作变得简单了。今天的叙利亚和黎巴嫩,在17世纪被粗略地划分成4个行省。奥斯曼帝国在省城派驻总督和法官,负责收税、征兵,其他事务则交给本地阿拉伯人领袖打理。至于沙漠边缘的游牧部落,他们连税都不用交,偶尔帮忙打打仗就行。叙利亚的宗教和民族问题呢,奥斯曼总督也乐得让大家私下协商。反正这里只是一片贫穷的海外领地,没有多少油水可以压榨,采取放养政策就行了。
然而,1831年却出了一桩大事。过去效忠奥斯曼帝国的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目睹旧帝国摇摇欲坠,生出了个人野心。他指挥大军在地中海东岸登陆,占领了整个叙利亚和大半个巴勒斯坦。奥斯曼帝国直到1841年,才在英俄两国支持下,打败埃及人,夺回了失去的领土。但埃及人的10年统治,却给叙利亚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埃及人把现代税收制度带到了叙利亚。他们重新开垦荒芜的土地,组织农民耕种,并从收成里征税;城市居民也要按人头纳税:这使叙利亚在经济上成为了一个有序的整体。其次,埃及人模仿欧洲,在叙利亚建立了原始的议会制度。一切城乡居民,不分民族、宗教,都可以推举代表进入议会,商讨本地大事。虽然当时的议员,大部分还是过去的部落领袖和富商,但这项新制度,却让他们第一次有了为本地利益发声的使命感。最后,埃及人用武力降伏了不服管束的游牧部落,又用武力让奥斯曼人吃了十年瘪,这让叙利亚人由衷地觉得:要自保,必须拥有武装。
有意思的是,埃及人虽然撤走了,他们留下的税收和议会制度,却被奥斯曼帝国原样继承了。不过,为了实现精细化管理,巴勒斯坦地区被单独划了出去。叙利亚只剩下了3个省,分别是大马士革、阿勒颇和贝鲁特。贝鲁特省,就是今天黎巴嫩的沿海地带。在新体制下,穆斯林和天主教徒享有平等的社会地位,这就带来了新问题。因为叙利亚的绝大多数人口属于穆斯林,他们抗拒这种变化,并在1860年挑起了宗教战争。奥斯曼帝国为了息事宁人,把叙利亚的天主教徒迁移到黎巴嫩山区,给他们单独建了一个自治领。这种安排,一直持续到1914年“一战”爆发。
整个19世纪后半叶,叙利亚在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上,一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离帝国的政治中心君士坦丁堡,是既不近又不远。不近,意味着控制力没那么强;被巴尔干问题深深困扰的旧帝国,不会把太多精力放在叙利亚身上。不远,则方便了叙利亚人成为帝国改革政策的受益者。要知道,在19世纪末奥斯曼帝国的2400万国民里,阿拉伯人占到1/3。作为阿拉伯人聚居区的叙利亚,自然成了笼络对象。巧的是,当时的西欧对棉纺织品有着旺盛的需求。英法两国的企业看到了叙利亚的经济潜力,开始动员本地人大批种植棉花。要出口棉花,就得修筑铁路和公路,港口也要扩建。银行、外贸公司等配套设施,也在叙利亚蓬勃兴起。加上奥斯曼帝国为了表现改革的诚意,开办了一系列实行欧洲学制的中小学,沉寂了数百年的叙利亚,意外迎来了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浪潮。短短40多年间,这里就出现了一个以阿拉伯知识分子和城市工商业者为核心,思想高度激进的新生代精英群体。正是在这个群体里,诞生了近代中东第一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也正是他们,主持制定了叙利亚独立的第一个具体方案。
回看19、20世纪之交的世界史,我们会发现:倡导在民族独立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现代化,是许多被压迫民族的共同选择。中国的辛亥革命,还有欧洲的巴尔干独立运动,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但阿拉伯人的情况,却有点特殊。首先,阿拉伯人定居的中东地区,从几千年前开始,就是一个多民族混居地。像叙利亚的阿勒颇,就住着一大批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他们跟阿拉伯人共同生活,还发生通婚,根本就没有清晰的边界。那阿拉伯民族主义,要不要把这些人也带上?其次,大部分阿拉伯人,和奥斯曼帝国的突厥人一样,信奉伊斯兰教,但其中有许多分裂的小教派。另外,阿拉伯人里还有天主教徒,有东正教徒。怎么处理这些混沌的宗教纠葛,也成了难题。
正是在错综复杂的现实面前,叙利亚的阿拉伯知识分子,走上了一条空想之路。他们认为,阿拉伯民族最辉煌的年代,是公元7到10世纪。那时节,从北非到波斯高原,属于同一个政权;大家不分民族,不分宗教,都是阿拉伯帝国的子民:这样才是理想状态。19世纪的阿拉伯人,也必须朝这个方向努力。按照他们的说法,只要一个人是生活在古代阿拉伯帝国的领土上,那不管他属于哪个人种,信奉哪种宗教,都可以被视为阿拉伯人,都是革命同志。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这当然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且不说古阿拉伯帝国的许多领土,比如埃及和伊朗,早就成为独立国家了。单说宗教矛盾,叙利亚的穆斯林和天主教徒,直到1860年还在互相杀戮,他们怎么可能骤然化敌为友呢?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叙利亚知识分子又提出了一些新主张。他们从历史的尘埃里,打捞出了“大叙利亚”这个概念,并宣传说:阿拉伯半岛的西部和北部,本来就是一个整体。未来的独立国家,至少不能比这个“大叙利亚”再小了。至于宗教矛盾嘛,只要新国家实行世俗制,不偏袒任何一方,好像也能解决。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注意了,我刚刚说的这些理念,全都是19世纪末的叙利亚知识分子,在纸面上凭空设计出来的。它代表的只是一小批城市精英的想法,既脱离现实,又很粗糙。但在当时的中东,这却是唯一一个相对完备的民族独立方案。它被印成传单和小册子,一路扩散到整个中东。本书作者形容说,20世纪初的叙利亚大马士革,就像是大革命年代的法国,到处都是雄心勃勃、激扬文字的阿拉伯知识分子。唯一的问题是,他们没有武装,只能进行“纸上的革命”。
转机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奥斯曼帝国征发阿拉伯人入伍,激化了民族矛盾。英法则扶持圣城麦加的大贵族哈希姆家族,发动了阿拉伯人大起义。这段历史,“得到听书”解读过的《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有过详细的记录,这里不再赘述。我们只说叙利亚的动向。1918年10月,哈希姆家族的费萨尔亲王,指挥阿拉伯起义军开进了大马士革。叙利亚知识分子意识到,实现“大叙利亚”之梦的机会来了。费萨尔有武力,有名声,还是英国的盟友;叙利亚人则有建国方案,双方是天作之合。他们满心以为,只要抓紧时间把政权建立起来,再获得国际承认,叙利亚的独立理想就可以“落地”了。因此,1919年,叙利亚精英在大马士革召开了国民大会,草拟了一部宪法。他们宣布:以历史上的“大叙利亚”边界为基础,成立一个新国家“叙利亚阿拉伯王国”,实行君主立宪制,拥戴费萨尔为国王。
问题是,英法两国早在1916年,就秘密达成了瓜分中东的《赛克斯-皮科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叙利亚将由法国单独占领,他们当然不会容忍叙利亚人自行宣布独立。1920年7月,法国军队开进叙利亚,击败了费萨尔的军队。存在不到一年的叙利亚王国政权就此瓦解。这是“大叙利亚”之梦第一次遭遇挫败,但它的影响绝不会就此消失。
好,刚刚我们回顾了19世纪叙利亚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它在“一战”结束后遭遇的挫败。接下来,我们来看法国统治时期。法国殖民者很清楚,叙利亚民族主义者把他们视为死敌,他们是得不到主流阿拉伯精英的拥护的。但也有一些本地人,对入侵者抱有好感。记不记得,前面提过,1860年宗教冲突中,叙利亚的天主教徒被赶到了山区?他们就愿意跟法国人合作。1920年9月,法国把这批天主教徒迁到地中海东岸,以他们为基干,建立了一个新政权——黎巴嫩国。叙利亚剩下的海岸线,则由一个不太主流的穆斯林派别阿拉维派统治。后来成为叙利亚总统的阿萨德父子,就属于阿拉维派。至于叙利亚的其他部分,法国人允许他们建立议会,但不让他们有武装。理由很简单:假如叙利亚知识分子继续闭门造车,捣鼓一些空想的建国方案,对法国人是没有威胁的,就让他们接着闹好了。
然而,分裂黎巴嫩却捅了一个马蜂窝。前面说过,叙利亚民族主义者的终极梦想,是建立一统中东的阿拉伯国家;最低限度,也要确保“大叙利亚”版图的完整。而黎巴嫩成为独立国家,直接划走了“大叙利亚”最优良的港口贝鲁特,连带还割走了一大块海滨平原。这是他们无法忍受的。既然抗议没有用,那就起来战斗。从1925年到1927年,民族主义者串联部落武装,在整个叙利亚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起义。法军出动飞机、坦克和大批火炮,付出6000人战死的代价,才把起义镇压下去。幸存的起义领导者,潜入中东其他地区,继续从事反对英法殖民统治的斗争。像1936年著名的英属巴勒斯坦大起义,就有大批叙利亚爱国者参与。他们追逐的,依然是那个“大叙利亚”之梦。
不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叙利亚民族主义者也出现了分化。流亡海外的这批抵抗者,是所有党派里最激进的。他们组建了叙利亚社会民族党,追求原生态的“大叙利亚”目标。留在本土的政治活动家呢,有一派以北方的阿勒颇为中心,称为人民党。他们认为,英属中东的政治状况,比法属叙利亚要好。当年叙利亚人拥戴的费萨尔亲王,现在已经是英国人扶持的伊拉克国王了;费萨尔的哥哥阿卜杜拉,也当了约旦国王。既然“大叙利亚”短期内无法实现,是不是可以考虑先跟伊拉克、约旦两国合并,形成一个“中等叙利亚”?反对人民党的政治家,则以大马士革为中心,称为民族党。他们认为,叙利亚才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真正的中心,怎么能给哈希姆家族“抬轿子”呢?就这样,三个党派在论战中,发展成了竞争关系。大家都想掌握法属叙利亚的执政权,然后试一试,谁的方案效果更好。
而法国在叙利亚,一直采取高压统治模式,直到1946年才允许它完全独立。在那之前,天主教人口占微弱多数的黎巴嫩,还宣布不会和叙利亚统一。这样一来,别说“大叙利亚”之梦成了泡影,就连19世纪的传统领土也少了一大块。面对这种情形,叙利亚的三个主要党派开始“竞争上岗”。首先登场的是民族党,它刚刚执政两年,就遇到了一个大麻烦,那就是1948年的巴勒斯坦危机。激进的社会民族党第一个发难,他们表示:巴勒斯坦,那可是“大叙利亚”的一大部分啊,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人民党也跳出来帮腔,说伊拉克和约旦都准备出兵,帮助巴勒斯坦人打以色列,我们总不能干看着吧?民族党的库瓦特里总统,对此非常头疼。他想了一个鸡贼的点子:谁想援助巴勒斯坦,就自己上前线去打仗,我这个政府反正不出全力。叙利亚就在这种各怀异志的情况下,吃到了第一次中东战争的败仗。但大失所望的人民党和社会民族党,反手就发动政变,推翻了民族党政权。叙利亚也进入了彻底的乱世。
从1946年到1958年,叙利亚先后更换了10位总统和22位总理,没有哪届政府能撑过两年。每届政府鼓吹的治国方案,都是“大叙利亚”蓝图的变体。但以叙利亚的经济之弱,内部矛盾之尖锐,哪一个方案都不可能真正成功。库瓦特里总统晚年曾说:“我管理的这个国家,有50%的人认为自己是民族领袖,25%的人认为自己是先知,还有10%的人觉得自己就是真主。只有15%是正常人。”这个说法虽然略显夸张,却也形象地概括了叙利亚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好高骛远,把领土野心置于国家发展之上的心态。而一股新势力——军人集团,就在这种乱象中崛起了。
军人政治,在“二战”后新独立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很常见。不过,叙利亚的军人集团,却极富地方特色。他们依然推崇“大叙利亚”的梦想,只是手段比较务实,希望先实现经济和军事的现代化,再作长远打算。在“二战”后的世界上,要发展经济,只有美苏两个模板。叙利亚军人选择的是苏联。1957年,叙利亚与苏联签订经济合作协议,开始大刀阔斧地实施土地国有化和工业化。然而就在1958年,埃及总统纳赛尔突然提议:与叙利亚合并成一个国家。
站在叙利亚人的角度,埃及虽然不是“大叙利亚”的一部分,但在19世纪初,正是他们给叙利亚带来了最初的现代化,两国关系很近。埃及总统纳赛尔,又是阿拉伯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这和叙利亚军人的短期目标是一致的。他们开始畅想,能不能借埃及人的力量,实现光复“大叙利亚”的终极目标?于是,由埃及和叙利亚结成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就在1958年诞生了。但埃及人的算盘,显然和叙利亚人不大一样。他们把叙利亚人当成跟班和附庸,对他们颐指气使。忍无可忍的叙利亚军人在1961年,再度发动政变,赶走埃及官员,脱离了联合共和国。
而叙利亚的执政权,随后就落到了新生代军人集团——复兴党人手中。复兴党人继续从“大叙利亚”的愿景出发,不计代价地支持巴勒斯坦解放运动,把国家财政弄得一团糟。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轻敌的叙利亚人不仅损失了整个空军,还丢掉了战略要地戈兰高地。这一回,复兴党里的稳健派,自己都忍不下去了。1970年,空军将领哈菲兹·阿萨德发动“纠正运动”,夺取了政权,随后出任总统。叙利亚政治史,从此进入了阿萨德父子的时代。
好,刚刚我们回顾了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叙利亚经历的政治动荡。到哈菲兹·阿萨德,也就是老阿萨德上台执政时,“大叙利亚”之梦已经变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幻影。频繁的战争和政变造成严重通货膨胀,商人、企业家纷纷逃离叙利亚,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为了挽救危局,阿萨德利用苏联贷款,修建了一系列水利设施,提升了叙利亚的农业产量和发电量。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石油资源,虽然储量不大,但在油价进入“牛市”的背景下,也为叙利亚挣到了可观的外汇。老阿萨德还鼓励叙利亚人出国务工,去波斯湾石油富国充当蓝领工人,以此缓解就业压力。经过这番改革,叙利亚在20世纪70年代迎来了短暂的经济复兴,全国人口也从1981年开始,进入了高速增长期。
前面说过,老阿萨德属于阿拉维派穆斯林。这个派别在叙利亚人口中,只占1/10,社会基础并不稳固。为了巩固政权合法性,老阿萨德在稳定局势之后,也开始迎合“大叙利亚”派的口味。只不过,他的胃口没有那么漫无边际,没有想过要合并伊拉克或者巴勒斯坦,只把目光投向了长期孱弱的邻国黎巴嫩。1976年,叙利亚以调停黎巴嫩内战为由,派兵进入这个邻国,随后一直驻军到2005年,其间还和以色列爆发了第五次中东战争。
站在大叙利亚主义者的角度,黎巴嫩本来就是叙利亚的一部分,两者不可分割。而对老阿萨德来说,黎巴嫩这个服务业发达的“窗口”国家,可以解决叙利亚的许多现实问题。有100万叙利亚人前往黎巴嫩打工,黎巴嫩的港口和金融业,也在为叙利亚经济“输血”。正是靠着“黎巴嫩红利”,叙利亚才平安度过了“冷战”结束之初,苏联援助断绝带来的冲击。但它的负面影响也很明显:直到21世纪初,叙利亚实行的依然是刻板的计划经济体制,社会活力极度萎靡。而20世纪80年代人口爆炸期出生的那一代人,到21世纪初恰好面临就业问题,整个国家开始不堪重负。
2000年,老阿萨德去世,次子巴沙尔·阿萨德继任。这一年,叙利亚的人均收入还不到1980年的1/3。2005年,叙利亚最终从黎巴嫩撤军,但欧美国家继续对其实施制裁。增长乏力的经济,大量青壮年失业人口,加上中东整体环境的动荡和极端思想传入,最终在2011年引发了叙利亚内战。这个历经沧桑的国度,如今依然在苦苦支撑。
好了,关于这本《叙利亚》的主要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记得2017年第一次前往叙利亚采访时,我发现,首都大马士革的建筑群,可以清晰地分为三个板块:一是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古建筑,二是法国统治时期的街区,三是苏联式的灰色高楼。这三个建筑群,恰好对应近代叙利亚的三个历史阶段。把它们连结在一起的,则是“大叙利亚”的宏伟理想。但也正是这一理想脱离现实的部分,使叙利亚一次又一次陷入政治动荡和冲突,错过了发展经济和社会的宝贵时间窗。有些时候,过于宏大和偏执的理想可能成为负担,遮蔽正视现实的眼光,使人走上歧路。这样的警示,也是我们在阅读历史时,可以汲取的宝贵教益。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如果你对这个主题感兴趣,非常建议你去阅读原书。此外,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1.19世纪末的叙利亚知识分子,基于对历史的浪漫化想象,重塑了“大叙利亚”这个概念,以之作为争取阿拉伯民族独立的蓝图,影响一路持续至今。
2.“大叙利亚”之梦,是推动叙利亚在“二战”后的中东政治中,持续对外放射能量的深层原因。但由于经济实力贫弱,内部矛盾尖锐,它始终没能变为现实。
3.经济增长乏力,青壮年人口大量失业,对外用兵消耗国力,加上极端思想传入,共同导致了2011年叙利亚内战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