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启蒙》 刘怡解读
《世俗启蒙》|刘怡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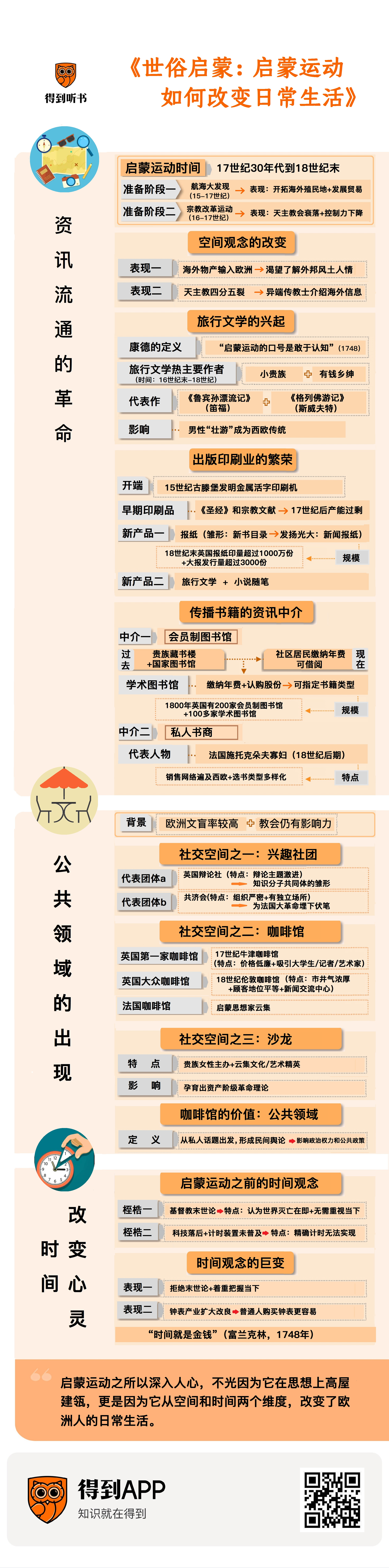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刘怡。今天我要为你讲的书,叫做《世俗启蒙》。中译者给它加了个副标题,叫“启蒙运动如何影响日常生活”,应该说非常贴切。发生在17到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在我们以往的印象里,总是和牛顿、卢梭、康德这些响当当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有时我们会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启蒙运动是由几百个科学家、哲学家和艺术家,在书斋里完成的一场思想革命,是非常阳春白雪的。被启蒙运动直接影响的,似乎主要也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最多再加上受到“冒犯”的神学家和封建贵族,反正肯定不出圈。问题是,这样的印象,真的正确吗?
我们不如来个“穿越”,回到启蒙运动之前的欧洲,感受一下它的真实影响。假设你是一位生活在16世纪末的欧洲平民,不算太穷,也读过几年书,那你的日常生活会非常枯燥。首先,精神消遣是很难找到的,因为你周围的人70%是文盲。市面上的印刷品有一半是宗教文献,另一半里还有不少是拉丁文的古代典籍。公共图书馆还没有出现,百科全书也没有问世。假如你不是生活在印刷业重镇,你可能连一张世界地图都买不到。其次,你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娱乐,因为咖啡在绝大多数国家还被当成药材。啤酒和葡萄酒倒是不难搞到,但大多数酒馆只营业到晚上9点。要是你想在酒馆里玩牌或者搭讪异性,治安官可能会罚你的款,或者拿鞭子抽你。至于常住居民超过10万,社会氛围比较宽松的大城市,整个欧洲只有10座。最后,你连时间都很难掌握,因为机械钟表还没有大规模量产。而你的邻居家多半连本台历都没有,他们只知道某几天是天主教圣徒的生日;至于今年是哪一年,根本没有人会关心。
这样的日子,听着都很绝望吧?但150年过后,18世纪中期,情况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资讯流动变得异常活跃,普通人不仅能读到报纸和小说,还能通过本地的会员制图书馆和书店,接触到国外最新出版的学术著作。长途旅行成为一种时尚,跋山涉水去到异乡的冒险家、小贵族和平民,会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让更多人了解本国以外的世界。在巴黎、伦敦这样的大城市,咖啡馆和沙龙是最时髦的社交场所,小城市也有形形色色的兴趣协会。人们在那里分享文学作品,褒贬各国统治者,丝毫不担心神学家和治安官会破门而入,打断他们的欢聚。更别提,欧洲商人已经把生意做到了遥远的美洲和亚洲。他们争分夺秒,寻找着新市场、新商机。时间成为了重要的盈利变量。
那在中间的一百多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才造成了这样巨大的反差呢?答案就是本书的书名——世俗启蒙。它不仅发生在大学校园和实验室,也出现在街头巷尾的日常生活中。推动世俗启蒙过程的,远不只是牛顿、卢梭这样的大名人。那些默默无闻的跨境商人、书店老板、沙龙主持人,承担了更具体的“打地基”的工作。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普通欧洲人的生活,逐步远离宗教戒律和封建道德的束缚,开始走向世俗化和现代化。当时留下的许多习俗,甚至一路延续到了今天。学习完这本书,你不光能增加历史知识,你还能深刻体会,一种抽象的思想观念,要怎样才能成功“出圈”,实现大众化和普及化。而把这里的想法换成技术和产品,其实就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商业活动。
本书作者玛格丽特·雅各布,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教授,也是英语世界公认的研究启蒙运动的权威学者。由她主编的《西方文明》教科书,是英美许多顶尖文科高校的必备教材,已经发行到第五版。这本《世俗启蒙》是雅各布在2019年撰写的,汇聚了她半个世纪学术生涯的精华,文笔也很风趣幽默。相信它一定会让你大有收获。
接下来,我就分三部分,为你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启蒙运动期间,欧洲人接收和交流资讯的方式,出现了哪些变化。在第二部分里,我会为你介绍当时的城市文化生活,尤其是市民阶层在社交方式上经历的革命。最后,我再为你概述一下,启蒙运动怎样改变了欧洲人的时间观念,并彻底影响了他们的人生哲学。
开始讲述本书的内容以前,我想先给你捋一捋和欧洲启蒙运动有关的时间线。欧美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启蒙运动发生在17世纪30年代到18世纪末之间,但它不是凭空出现的,此前经历了两个重要的准备阶段。第一阶段是著名的航海大发现,它出现在15到17世纪。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为代表的欧洲海洋强国,初步开辟了海外殖民版图,贸易活动的规模与日俱增。第二个准备阶段是16到17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它不仅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教派,颠覆了罗马天主教会对宗教问题的唯一解释权,还引发了法国、西班牙、德意志等地长达200多年的宗教战争。封建君主的权力在这些战争中受到严重冲击,他们对社会的控制力显著下降,这就为启蒙思想的出现创造了可能。
本书作者雅各布认为,航海大发现和宗教改革在精神层面最大的影响,是它们改变了欧洲人对“空间”这个概念的理解。这里说的空间,还不光是地理空间。要知道,15世纪之前,欧洲人虽然也听说过世界上有亚洲,有中国,但感性体验非常少。特别是中世纪时代,奥斯曼帝国阻断了欧亚交通线。除了少数传教士、商人和知识分子,欧洲人根本无法想象,万里之外还存在着其他民族、其他政权,过着完全不受天主教影响的生活。就算是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设想的也只是回到希腊、罗马时代。它的眼界依然局限于欧洲本土,比较狭隘。但航海大发现改变了一切。来自亚洲和美洲的财富、物产,以商人和殖民者为中介,源源不断涌入欧洲市场。欧洲人日常消费的糖、咖啡、烟草、棉花,大部分是从海外进口的。经过100多年感性接触,普通欧洲人已经完全确信,世界上不只有一种文明和一种生活方式。他们渴望了解其他地区的风土人情,和“外邦人”发展商业关系。这就是一种空间上的突破。
那宗教改革,为什么也和空间有关呢?我们知道,第一批登陆美洲和东南亚的西班牙殖民者,尝试过在当地推广天主教。但随着宗教改革运动和宗教战争的爆发,天主教本身变得派系林立,四分五裂。许多奔赴海外的传教士,根本不属于“正统”教派。他们的兴趣早就超出了单纯的宗教教义,变成了最早的人类学家和旅行作家。举个例子:明末清初来到中国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就是由一个不那么主流的教派“耶稣会”派遣的。他们把欧洲的数学和天文知识带到中国,也把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想想看,过去总是一本正经,言必称《圣经》的传教士,现在整天谈论的都是《圣经》里没有记载的陌生地域、陌生文明。这不正是一种思维方式上的“空间革命”吗?
康德在1784年写过这么一段话:“什么是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了自己给自己强加的不成熟状态。什么是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过他人的引导,就没有勇气和决心去运用自己的理智。要敢于认知!这是启蒙运动的口号。”而把认知活动付诸实践的典型,就是旅行作家。前面说过,欧洲最早开始记录异国他乡风土人情的,主要是传教士和殖民探险家。进入16世纪末,许多小贵族和稍有闲钱的乡绅,也兴起了“旅行热”。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到遥远的亚洲、美洲,那就骑马走个一千来公里,到周围的国家游历一番,把沿途的所见所感写下来。《鲁宾孙漂流记》的作者笛福,就是一位商人出身的旅行家,写过不少在英国国内游历的见闻。18世纪初英国的讽刺小说《格列佛游记》,干脆虚构了一位在“小人国”“大人国”“慧骃国”四处游走的航海家,用奇幻的旅行故事来影射社会现实,出版两个月就重印了三次,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著名的“雅虎网”,就是用《格列佛游记》里的物种“雅虎人”命名的。我们今天熟知的旅行手册,也是17世纪在欧洲出现的。到了18世纪,西欧的大小贵族和乡绅,甚至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叫做“壮游”。年满21岁,受过教育的男性,会在家庭教师和仆人陪同下,花费几个月到几年不等的时间,在中南欧游览名胜古迹,见识社会百态。《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吉本,就是在“壮游”期间,产生了撰写罗马通史的想法。
不过,光有旅行家和写作者还不够。要是这些旅行文学,只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小圈子里传播,那它的影响力势必很有限。旅行文学之所以能流传开来,和出版印刷业的繁荣有关。熟悉西方文明史的朋友都知道,15世纪中期发生了一件大事:德意志人古滕堡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机。它制作简便,容易仿制,很快在整个欧洲流行起来。据荷兰历史学家布林估算,光是16世纪,欧洲用古滕堡印刷机印制的书籍就超过了2亿册。像巴黎、罗马、日内瓦,都是当时重要的印刷业中心。不过,早期的印刷品,几乎都是《圣经》和宗教文献,内容比较单一。但进入17世纪,正统天主教的影响力开始下滑,没有那么大的印刷需求了。用今天的话说,欧洲印刷业出现了“产能过剩”。怎么办呢?印刷厂以及它们背后的出版社,开始各显神通。欧洲最早的报纸和通俗出版物,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
说起欧洲早期的报纸,它的雏形是16世纪末,出版业商人为了方便跨境订货,自行印刷的新书目录和简介。进入17世纪,越来越多的商人发现,资讯对商业活动的成败至关重要。他们需要知道,最近哪里发生了战争,哪里有自然灾害,哪位国王去世了,据此来规划自己的生意。新闻报纸因此横空出世。据《不列颠百科全书》记载,18世纪20年代,光是伦敦就有12份全国性报纸和24份地方报在发行,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泰晤士报》。前面说过的作家笛福,就是靠兼职给报纸写稿,在出版业崭露头角的。在识字率较高的英国,全国性报纸一周能出版三期,周报更是欧洲大中城市的标配。当然,那时的报纸并不是由专业人士主持的,它刊登的小道消息和假新闻非常多,订阅价格也不便宜。到18世纪末,英国每年印刷的报纸,总数虽然超过了1000万份,但所谓“大报”每期的发行量也就3000份出头,还是消化不了印刷业的过剩产能。怎么办呢?印刷厂和出版社又开始想辙了。他们意识到,报纸的问题是时效性和地域性太强,无法长期销售。要想提高销量,还是得做书,尤其是那些专业性不强,普通人也能理解和接受的书。旅行文学和各种形式的小说、随笔自然成为首选,这才造就了笛福、斯威夫特等人的一夜爆火。
书是印出来了,靠什么渠道把货铺出去呢?在启蒙时代,有两个资讯中介发挥了关键作用。其一是会员制图书馆。它们跟封建贵族的藏书楼,或者国家建造的大型图书馆不太一样,面向的是自己所在的社区。这种图书馆通常只有几百本藏书,基本都是新书。附近的居民只需要交纳一定的年费,就可以自由借阅书籍。到了18世纪初期,北美独立运动先驱富兰克林提出了更严肃的“学术图书馆”概念。学术图书馆的会员,除了定期缴纳年费,还需要认购股份。作为回报,他们可以指定购买某种题材的书籍,甚至把自己写的书推荐给图书馆。据《剑桥英国史》记载,1800年英国共有200家大众会员制图书馆,还有100多家小众的学术图书馆,几乎覆盖了所有人口过万的城镇。
另一个推广新书的渠道,是私人书商。图书馆虽好,但需要有一定量的会员作为支撑。那些居住在小城镇,或者希望长期收藏图书的读者,就得仰赖走南闯北,神通广大的私人书商了。作者雅各布写了这么一个案例:1771年,法国有位著名的地下书商施托克朵夫寡妇,在巴黎进货时,被宗教裁判所告发,关进巴士底狱坐了两年牢。当时她买进的书籍,既有英国政论家博林布鲁克批判教会的书信集,也有无神论哲学家霍尔巴赫的《自然的体系》,甚至还有色情小说。而这位施托克朵夫寡妇的销售网络,遍布法国、荷兰以及大半个德意志,知名度非常高。雅各布把这位寡妇书商称为“另类唯物主义者”,她自己虽然不是知识分子,却通过销售图书这种商业活动,在客观上推动了启蒙思想的普及。可以说,启蒙运动造就的“空间革命”,首先就表现为资讯流通的革命。它和那些普通的印刷厂老板、报纸出版商、书商、图书馆主理人,以及持续产出新资讯的旅行家和写作者,具有密不可分的关联。
好,刚刚我们回顾了启蒙运动在资讯流通领域造就的革命。不夸张地说,互联网诞生之前,一般人心目中那个喝着咖啡,翻着报纸,阅读国外最新书籍的欧洲知识分子形象,就是这场资讯革命奠定的。但作者雅各布又说,光是一个人游历四方,阅读新书,改变的只是个体的思维方式,影响还不够大。启蒙运动塑造的“空间革命”,还有社交的一面。它在当时的欧洲城市,创造了一个精神上的公共活动空间,深刻影响了整个欧洲社会和后来的欧洲政治。
站在今天的角度,你可能会觉得雅各布的说法有些大惊小怪。读书读报,跟家人、朋友交流时事和新知,这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啊,为什么还要专门强调呢?你得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去看这个问题。17、18世纪的欧洲,虽然初步建立起了近代教育制度,但文盲率还是非常高。18世纪中期,欧洲文化程度最高的英国,男性识字率刚刚突破50%,法国则是48%。至于识字的女性,英国只有40%,法国更是低达27%。不少人接受的所谓“教育”,其实只是在教会学校里抄写和朗读《圣经》。要他们谈论更复杂的话题,他们是做不到的。另外,教会虽然无法再一手遮天,但势力依旧相当可观。要他们像几百年前一样,随便把人绑上十字架,放火烧死,肯定是不可能了。但以“亵渎上帝”为理由,把人关进监狱,或者处以罚款,还是很容易的。这意味着讨论新思想、新观念,不能在大庭广众下进行。
既不能不“出圈”,又不能太肆无忌惮,那该怎么办呢?答案是“兴趣社团”。18世纪初,英国伦敦出现了最早的辩论社“罗宾汉社”。每周一晚上,会有50多个小商人、低级文官、作家和大学生聚在一间酒馆里,针对某个议题轮番发表观点。大贵族和牧师是没法忍受这种平起平坐的氛围的,根本不会参加,所以辩论的主题往往非常激进。有时是“你认为殖民地有独立的权利吗”,有时则是“妇女应不应该享有投票权”。众人轮番发言之后,主席会进行总结。据本书作家雅各布统计,1780年前后,伦敦地区较大的辩论社至少有35个。有一回,罗宾汉社讨论热度最高的税收问题,结果居然来了1200个听众,以至于酒馆干脆卖起了门票。随着辩论的话题越来越宽泛,受过教育的女性也开始参与讨论。不过为了避免受到教会和传统卫道士的抨击,她们通常会戴上化妆舞会的面具,匿名出席辩论会。除了辩论社,闭门读书会也非常流行。这种读书会和前面提到的图书馆结合起来,形成了知识分子共同体的雏形。
在形形色色的兴趣社团里,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共济会。你可能听说过,这个组织非常神秘,只吸纳欧美各行各业的精英,还有一套复杂的等级制度和入会仪式。其实,最早的共济会,是14世纪末欧洲的石匠行业协会,只是到了18世纪,才演化成了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的秘密社团。共济会拥有严密的组织和自己修建的聚会场所,比辩论社更安全,因此吸引了大量反对教会和贵族特权,追求自由、平等的知识精英。18世纪的许多文化名人,比如孟德斯鸠、歌德、莫扎特,都是半公开的共济会成员。法国的共济会甚至在全国有1000多个分会。他们阅读和讨论启蒙思想家的著作,畅想未来的选举制度和政体,为后来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不过,辩论社和读书会,多少有点知识门槛。要是一个人既不想发表长篇大论,也没有读过教会查禁的书籍,他有没有什么消遣的地方可去呢?答案是咖啡馆。其实,咖啡在西欧流行开来的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要晚得多。英国第一家咖啡馆,是1650年才在牛津附近开出来的。当时店家打出的广告是“来自奥斯曼帝国的提神饮料”,主打一个异域风情。进了这家店,只需要交1便士,就可以得到一杯咖啡,还可以免费取阅店里的报纸,因此很快吸引了附近的大学生。紧接着,穷记者们也涌进了咖啡馆。他们在这里交流小道消息,甚至随机读出几段刚写好的稿子,请其他顾客发表看法。紧接着,初出茅庐的本地音乐家也进了咖啡馆,他们一边拉小提琴,一边向顾客们求几个打赏。
当然,并不是所有咖啡馆都像牛津那么学术化。18世纪伦敦的咖啡馆,就相当有市井气。英国历史学家艾通·埃利斯形容说:“这里就像一艘诺亚方舟,不管你是写书的才子、体面的律师、健谈的水手,还是精明的商人,在咖啡馆里都有一席之地。”有意思的是,一些咖啡馆还拟定了自己的顾客守则,比如:平民无须给贵族让座。禁止饮酒或者大声喧哗。凡是出口伤人,冒犯到其他顾客的,必须给对方买一杯咖啡作为道歉。平民会在咖啡馆里交流自己的职业和收入,股票经纪人会在咖啡馆里一坐大半天,研究生意经,有的咖啡馆甚至推出了代办法律执照的业务。当时英国最流行的大众报刊,比如《旁观者》杂志,干脆把新刊铺到了咖啡馆里。杂志上刊登的文章马上就会成为谈资。
1675年前后,英国咖啡馆的数量已经突破了3000家。它的变体也逐步输出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得到听书”解读过的《康德传》曾经提到,18世纪的大哲学家康德,每天会在哥尼斯堡的小酒馆用餐,和其他客人畅谈两个多小时。这种小酒馆,就是英式咖啡馆在德语地区的变体。伴着美食和咖啡,市民阶层基于平起平坐的地位、相似的价值观和相互了解的心理,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共同体。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把这种现象称为“公共领域”。哈贝马斯指出,在18世纪的欧洲,政治权力掌握在贵族和教会手中。平民阶层,尤其是城市平民,看似只能讨论一些私人话题,比如文学、艺术和个人职业。但当咖啡馆里的平民们,交流了足够多的信息之后,他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渴望获得更平等的经济地位和更充分的政治权利,这就形成了民间舆论。西方近代政治体制的变化,正是由此推动的。
说到启蒙时期欧洲的咖啡馆文化,不得不提的还有法国。大思想家伏尔泰、卢梭和狄德罗,都是咖啡馆的常客。据说伏尔泰每天要喝40杯咖啡,还喜欢把融化的巧克力和咖啡掺着喝。法国启蒙学派的代表作《百科全书》,就是在巴黎的普罗科普咖啡馆编写完成的。18世纪的法国还流行文化沙龙。沙龙是意大利语“房间”一词的变体,强调私密性。一些有钱的法国贵族妇女,比如德芳侯爵夫人,会在奢华的宫殿举办社交沙龙,邀请巴黎最出名的文人和艺术家光顾。一些沙龙的女主持人自己就是出过书的小名人。和咖啡馆相比,沙龙当然没那么大众化,但它同样是公共领域的组成部分。沙龙的主办者,往往只是依附大贵族的女性;她们邀请的宾客,则是平民出身的顶尖思想家和艺术家。大家在沙龙里谈论的,除了绘画和音乐,还有自然科学、哲学甚至“异端”的政治思想。正是在这种相对私密又火花四射的沙龙里,法国启蒙思想家孕育出了资产阶级革命理念,最终改变了整个欧洲社会。
好,刚刚我们回顾了启蒙时代公共领域的表现形式。它和资讯革命一样,都属于世俗启蒙的“空间”部分。最后,我们再来简单了解一下,启蒙运动对当时欧洲人的时间观念,有哪些影响。这个话题听起来有点怪:时间有什么可革新的呢?它不就是从古到今,再到未来吗?但17、18世纪的欧洲人,可不是这样想的。作者雅各布注意到,当时的大部分欧洲人,受到两项条件的桎梏。其一是基督教末世论。就连牛顿这样的大科学家都相信,上帝是在公元前4004年创造了地球,而整个人类的存活年限只有6000多年。换句话说,到公元2000年前后,基督将会再临,世间生活则宣告终结。按照这套说法,当时的欧洲人只剩下200多年可活了,当下的时间自然无足轻重,无须在意。
另一项桎梏是技术条件。要知道,启蒙时代的人们还没有经历工业革命,一切都是慢慢吞吞的。在1770年,英国人骑马出行,一小时只能走14公里。坐小帆船从英国多佛尔到法国加莱,32公里的路程,居然要花3个半小时。更要命的是,机械钟表虽然已经出现,但要到18世纪中期才会变得相对精确。在1690年之前,欧洲的机械钟上是没有分针的。这意味着精确计时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人们就在对末世的恐惧中,粗枝大叶地过着日子。
“得到听书”解读过的《万物皆可测量》一书,回顾过启蒙时代前夜欧洲计时装置的变化,这里不再赘述。我们主要来看抽象的时间观念的演变。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深入,普通人对末世论逐渐失去了信心。虽然依旧有人相信,地球会在未来某一天毁灭,但不再有整齐划一的“末世时间表”。人们越来越觉得,与其为了遥远的毁灭而担忧,不如过好当下,把握好眼前的时间。今天我们买到的记事手账本,往往会附带这一年的日历,最后还会留出几页空白,让你填写下一年的计划和期待。这种手账格式,就是17世纪中期在英国和荷兰出现的,它预示着时间观念的变化。
更重要的是,随着钟表产业的扩大和改良,普通人购买计时装置变得越来越容易了。作者雅各布发现,整个18世纪,欧洲怀表的售价下降了75%。到1799年前后,英国人只用花1英镑,就可以买到一只不错的手表,这笔钱只相当于底层工人10天的工资。属于末世论的“宗教时间”成为了过去,立足当下的“世俗时间”变得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精确。1748年,富兰克林说出了那个著名的金句:“时间就是金钱。”人们不再消极等待,而是争分夺秒,为获得世俗幸福而奋斗。至此,世俗启蒙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取得了突破,欧洲近代社会的曙光开始在地平线上浮现了。
好了,关于这本《世俗启蒙》的主要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雅各布的这部专著,篇幅只有25万字,不算鸿篇巨著,但它指出的问题却十分重要。以往我们对启蒙运动的了解,主要是一些名人和他们的思想,比较抽象。而《世俗启蒙》告诉我们:启蒙运动之所以能深入人心,不光因为它在思想上高屋建瓴,更是因为它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改变了欧洲人的日常生活。图书馆、咖啡馆、钟表,都是普通人有需求,并且能影响思想观念和大众心理的事物。不管是一种思想,还是一件产品,只有观照到绝大多数人的日常,才能站稳脚跟,并取得进一步的收益和成效。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如果你对这个主题感兴趣,非常建议你去阅读原书。此外,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1.启蒙运动造就的“空间革命”,首先表现为资讯流通的革命。它和那些普通的印刷厂老板、报纸出版商、书商、图书馆主理人,以及持续产出新资讯的旅行家和写作者,具有密不可分的关联。
2.兴趣社团、咖啡馆和文化沙龙,构成了启蒙运动中的“公共领域”。伴着美食和咖啡,市民阶层基于平起平坐的地位、相似的价值观和相互了解的心理,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共同体。
3.世俗启蒙改变了欧洲人的时间观念。属于末世论的“宗教时间”成为了过去,立足当下的“世俗时间”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不再消极等待,而是争分夺秒,为获得世俗幸福而奋斗。
4.启蒙运动之所以能深入人心,不光因为它在思想上高屋建瓴,更是因为它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改变了欧洲人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