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皆可测量》 王朝解读
《万物皆可测量》| 王朝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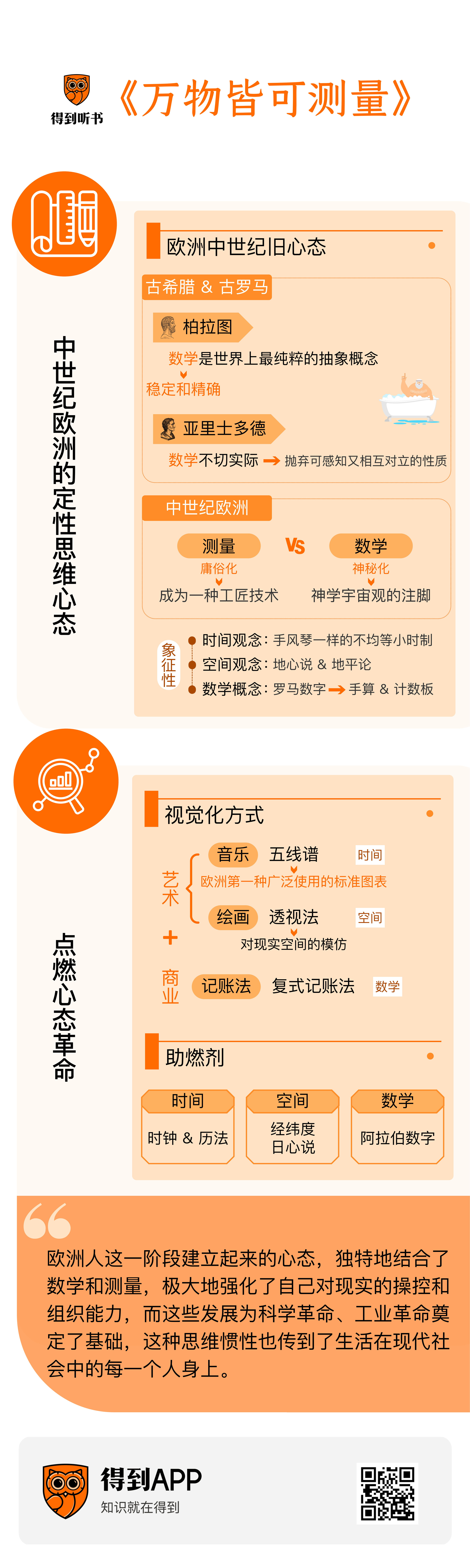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
今天我们要读的书,是《万物皆可测量》。我们对“测量”这个事情,实在是太熟悉了,已经有些理所当然。比如说,想换家具了,要量一下尺寸;月底了,看看KPI完成进度,甚至包括给闹钟定时间、穿衣服看气温等等,我们的每一个小动作,都和对现实的量化有关。你有没有想过,相比那种实际存在的一个一个的物体,什么几厘米、摄氏几度、股市几点等等,这些事如果不用确定的数字和刻度,那要怎么说?我们的世界从什么时候开始,被测量所定义?我们为什么如此痴迷于测量?
我先不回答这个问题,介绍一下本书的作者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你可能还听说过作者的另外两部作品《哥伦布大交换》和《生态帝国主义》,正是这两本书奠定了生态史的基础,还启发了后来贾瑞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克罗斯比在这两本书里描述了在哥伦布之后,新旧大陆之间发生的一系列生物交换,比如玉米、辣椒和土豆传入了欧洲,而甘蔗和咖啡则传入了美洲,改变了世界各地的生态和文化,但同时欧洲人带去了天花,毁灭了原住民文化,带回了梅毒,至今仍然难以摆脱。
写这两本书的时候,克罗斯比想到了一个问题,欧洲人凭借高超的导航技术横渡大西洋,靠着精确的弹道计算指哪打哪,用股份制公司推行殖民扩张,似乎欧洲人总是先人一步,更有效率地组织人力资源和利用物质工具,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传统上,教科书的解释很简单,就是科学和技术。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不是有种循环论证的感觉?这么说就是,科技发展使欧洲走在了科技的尖端,科技先进说明欧洲科技发展很快。促进科技发展的推动力是什么?或者按作者的话,是什么点亮了那根火柴?
这本书给出了他的答案。克罗斯比说,工业文明的“测量癖”源于1250—1600年之间的西方,也就是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在这一期间,西方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变革,逐渐从神秘主义的定性思维转变为精确的量化思维,也正是这一个关键的心态转变,为未来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他称之为“心态革命”。
接下来,我把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先讲欧洲原来的定性思维,在1250年前是一个什么样的认知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要了解心态革命的火柴是怎么点燃的,就要先了解火柴棍上有什么物质。第二部分我们就讲划火柴的那一下,也就是作者说的量化思维的视觉化,以及其他助燃剂,也就是一系列的技术革新,使测量变得可能。
我们要讲清楚这场“心态革命”,先得说说被革掉的那种旧心态。我们要说欧洲逐渐走向量化思维,并不是说在那之前欧洲人不懂什么叫量化,或者不在乎数字。
相反,早在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就把数学作为宇宙秩序的真理。比如柏拉图认为理想国的公民人数应该是5040人,还有零有整的,怎么来的?可能有两个理由。一个呢,是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也说过,一个人不用扩音设备的情况下,同时能听到他声音的最多人数,差不多就是五千人,但是他和柏拉图好像并没有给出任何的证据证明这个人数就是5040。另一个理由更玄妙,因为这是七的阶乘,就是从一乘到七的乘积,也可以被一到十的数整除,反正就是有非常多的数字能整除5040,所以对分组很有好处。
柏拉图为什么那么爱好玩弄数字?因为他认为,真实世界是理念世界的影子,我们以为的现实,只是我们感官系统产生的感觉,所以是不可靠的、变动的,反而抽象的概念才是永恒的。而数学是世界上最纯粹的抽象概念,方啊、圆啊、三角形啊,这种纯粹的理念才是稳定和精确的。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也这么认为,但他是觉得数学不切实际。他说数学家必须抛弃轻重、冷热、软硬等等可感知,又相互对立的性质,才能测量世界的维度。你会不会感到奇怪,他说的这些明明就是可以测量的啊?但那时的欧洲人不这么想。相比现实当中离散的物体,也就是明确一个一个的物体,什么冷热、软硬对他们来说更像是一种连续的状态,而非数量。这些是现实感官可以感应的,所以就很低等。我们现在已经很习惯于把现实都分割为某种均匀的单元,但这种思路在那个时候其实是非常陌生的。
这就是神秘主义数学的一个副作用:真正用来测量现实的实用技术,被认为跟数学关系不大。比如建筑工程、观测和制定历法,以及各种集市里还有称重、量长等等,这些其实都应用了数学,但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和那种“高贵的”数学哲学结合起来。
所以到了中世纪的时候,欧洲人的数学概念和计量已经分离得非常远,虽然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哲学已经衰落,但是他们的数学概念还是传承了下来,测量基本上被当成一种工匠技术,而不是数学应用,而数学基本上变成了神学宇宙观的注脚。
我们先讲讲测量。你会发现那时候的测量单位完全不是根据数学理解创造的,所以很多的古代单位听起来非常具体,到了有点古怪的程度。比如英国长度单位foot,就是英尺,是一只脚的长度,但丈量土地又要用别的单位,比如化朗furlong,也可以翻译成犁沟长,意思是一队牛在不休息的情况下可以犁地的距离。还有中世纪建造哥特式教堂复杂结构的建筑工匠们,他们非常熟悉几何学的方法,但他们都只是清楚如何应用,而没想过构建更深刻的理论。顶多就是指一下某块石头或者木头,然后说“得这么切”,但如果要他指出这个切法里面有什么立体几何原理,他就蒙了。
我们接着来看数学。大约公元5世纪,有一个叫圣奥古斯丁的神学家,他的神学理论被认为是中世纪开始的标志之一,也是早期天主教基本教义的来源。他有一句话,“我们不能轻视数字的科学。”但他怎么做数学呢?他认为上帝6天创世,是因为6这个数字很完美,是自己的三个因数,也就是1、2、3的和。第七天休息,是因为7也很神圣,是第一个奇数3和第一个非质数偶数4的和。后来到了13世纪,这种概念还是很流行。当时有一个大学者叫圣托马斯·阿奎纳,他认为启示录说世界末日只能有144000人得到拯救,是因为这个数很神圣。144是耶稣的12个门徒乘以12个以色列的支派,而1000是10的3次方,3是耶稣受难到复活之间的天数,它们的乘积就很神圣。你会发现那些神学家很有柏拉图的风格,他们认为数学是认知抽象性质的方式,而对感官感受的现实漠不关心。虽然已经有了后来数论的概念,会研究数字和数字能产生什么关联,但他们的重点是每个数的本质与神有关,什么样的关联更神圣、更美,而不是这些数字作为抽象概念之间有什么关系。
这种欧洲中世纪旧心态,是一方面把数学神秘化,另一方面把测量庸俗化,结果两边互不理解的认识。在这种心态中,现实作为上帝的造物,不应该用人类的标准来衡量,万事万物的差异是性质的差异,对事物的认知要从根本性质来理解。这个旧心态产生了一种作者所说的“历史悠久的神圣模型”,这个模型当中,时间和空间是人类的尺度,是根据象征意义确定的相对概念,而不是绝对的、均匀的、可量化的。 作者提醒我们,每个时代的“常识”都不一样,我们的常识,在一千年以前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可能这么说你不好理解,我给你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时间,我们现在都知道一天是24个小时,每个小时和每个小时都是一样的。但是中世纪欧洲人只从《圣经》上学来了中东人的时间观念,知道白天和晚上都应该有12个小时。问题来了,对于欧洲这种高纬度地区来说,一年中绝大多数时间昼夜都跟平分不沾边,那怎么样才能做到白天黑夜都有12个小时呢?欧洲人搞了一个手风琴一样的小时制度,确保每个季节的昼夜都是12小时,但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时间单位小时。那这要怎么判断现在是几点?不用看表,也不是看太阳在天上的位置,而是要听教堂提醒祷告的钟声。按照主流的分法,一天祈祷七次,要敲七次钟,所以人们对“几点”没有概念,而只知道现在是哪两次敲钟之间。至于是什么时候敲的,就不太确定了。在天主教斋戒期间,要在第九小时的祷告之后才能吃东西。这个第九,就是指日出之后的第九个小时。如果按我们的算法日出时间在早上六点,那么第九小时其实应该对应下午三点。但是为了夏季白天饿肚子时间短点,修道士们就开始提前敲钟,慢慢地,原来在下午的小时就变成了中午,表示第九小时的nones变成了英语的中午noon。至于其他小时,无非是往前挤挤、往后让让,纯粹是个操作问题。这种时间观的本质还是把现实的时间往象征性上靠,满足神学系统的需求。
空间观念也类似。当时流行的地心说和地平论,其实不仅仅是一种基于观测的理论,更重要的是符合神学的秩序。地心说认为我们所在的地面是宇宙的中心,诸天像半个鱼缸倒扣在大地上,绕着我们转。最外层的天球上天体都在做完美的圆周运动,因为圆这个概念具有完美的品质。我们所在的地面是最低等的区域,所以这里的运动原则就不是完美的圆,而是低级的直线。大地就像一张大饼,被上帝分成几个区域,对应生长不同的生物。在画地图的时候,中世纪的地图不按上北下南,而是把正东放在地图上方。为什么呢?因为据说伊甸园在东方。当然,当时的地图本质上不是根据几何投影画出来的导航图,而是一种表现主义的风景画,上面会画很多怪物、圣人,充满了象征意味。什么比例尺啊、图例啊,根本不在考虑范围内。
至于数学概念,很长时间之中,欧洲人都不稀罕精确的数字,他们满足于用“少许”“几个月”这样的词。只要我讲讲当时流行的罗马数字,你就知道有多么不利于数学发展了。现在很多手表上还有什么I、V、X这样的字母,这个就是罗马数字。其实罗马数字还有L、C、D、M,分别是50、100、500、1000,把代表更小数字的字母放在大数字的字母前面,就代表是要用大数减去这个小数,放在后面就代表要加上,比如VI就是六,IV就是四。那如果我要表示1549这样的数字怎么办?写作Mcccccxxxxviiij,最后这个j就代表数字结束了。可想而知,这种罗马数字肯定是不适应计算的。因此,那时计算的时候用的是手算和计数板。手算就是靠手指的弯曲和各种造型表示不同的数字,数字再大,还得用上胳膊、手肘,甚至肚脐,比如拇指指着肚脐就是五万。更复杂的计算,一般就要用上计数板。计数板很像我们的算盘,也是用拨动珠子来完成计算。但令人震惊的是,在公元十世纪欧洲教士从西班牙南部的伊斯兰教地区重新引进阿拉伯数字和计数板之前,欧洲已经有五个世纪没有计数板了。
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中世纪欧洲的定性思维心态。在这种旧心态之中,数字拥有道德和情感上的价值,不是纯粹的定量单位,而是有定性的象征意义。在欧洲旧模型观念中,世界上的万物俱有上帝赐予的不同性质,都富有象征意义,妄图用人类的理性标准去测量万物是大逆不道,更何况测量并不方便。
那为什么欧洲后来抛弃了历史悠久的神圣模型?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心态革命的火柴如何燃烧起来。
首先我们讲讲划火柴的那一下,视觉化,它是怎么让“万物皆可测量”成为一种流行思维的。所谓视觉化,就是用眼睛看到的图表、表格等等,以更快更直接的方式传递信息。
比如说文字和语言的使用方式,以前欧洲人阅读都讲究大声阅读,要到15世纪才有图书馆规章制度规定要保持安静。纸、笔、墨的普及加上识字率提升,使欧洲精英不再通过口口相传的福音和史诗获得知识,转而诉诸文字记录,默默阅读成为知识获得的主流方式。就连我们听书的产品,也有脑图和文稿这样的方式,方便你的眼睛快速接收信息。在此之外,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艺术和商业。
艺术上,我们应该很熟悉美术的透视,但我先讲一个不容易想到的视觉化艺术形式——音乐。音乐不是用来听的吗?我一说您就明白了:五线谱。在7世纪的欧洲,虽然有了很多宗教圣咏,但当时的神学家担心音乐会消亡,因为声音“无法被记录下来”,只能靠歌唱者用脑子记。圣咏是天主教祷告文的歌唱版本,早期记谱法没有指定确切的音高,而是用“形状”记录旋律音高是何时上升或下降。到11世纪时,意大利人圭多开始推广使用五线谱,用不同的等距线标记音高的准确变化。圭多用当时流行的圣咏的前几个单词开头命名了不同的音高,你听听熟不熟:ut,re,mi,fa,sol,la,没错,这就是现代通用音阶的雏形。在圭多之后,音乐家开始大胆尝试混合流行音乐和宗教音乐,在圣咏中加入更多的声部,创造了复调音乐。为了记录复杂的声部配合,13世纪的音乐家又发明了节拍的记谱法,节拍将时间切分为均匀的单位,眼睛阅读音符就知道每个音的持续时间。从此,即便是耳聋的贝多芬也能够写出复杂的交响乐了。教会认为,音乐作为传达上帝神性的形式,如今却变成了彰显人类理性能力的工具,人们光顾着夸作曲家厉害,忘了要崇敬神,于1322年教会下令不准用腐化的复调音乐,但是世俗的宫廷和街道上已经处处都是用新型记谱法创作的新音乐。五线谱不仅可能是欧洲第一种广泛使用的标准图表,还向人们展示了人类理性对时间的操控能力。
而空间的表现则当然是绘画。中世纪绘画往往把很多时间的事情画在一起,而且毫无透视,按照人物的意义安排位置和大小。画不反映空间,而只有纯粹的象征性。随着光学和几何学的发展,艺术家们意识到自己有方法表现空间,这就是透视法。虽然题材还是宗教的,但是透视法把绘画变成了对现实空间的模仿。13世纪的大画家乔托就擅长画巨幅壁画,运用透视法让观众可以在画前感受到物理纵深。为了使自己的绘画变得更符合现实视觉的比例,画家们精准地计算人或物在哪个区域画得多大,表示哪个距离。画家们逐渐变成了数学家、几何学大师。
无论是绘画还是音乐,在1250—1600年之间都大量增加了。原因大家都很熟悉,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大量新兴资产阶级,这些资产阶级花钱买心态革命的艺术品,那他们怎么赚钱和心态革命有什么关系呢?这就要说到记账的簿记员了。高度货币化的经济让商品价格记录变得方便了,可是货币价格不断浮动,还有为了应付远距离贸易的汇票、期票等等信用方式打乱了交付和收款的顺序,商人记账变得十分麻烦。以前,记账就得讲一段商品的全流程故事,甚至还能写上一笔中间撞见隔壁老王的聊天。不过,一种全新的记账法出现了,不同时间的经济行为能够呈现在一张图表上:复式记账法,每一笔交易都会分列在对开两页的资产和负债栏目下,两边保持相等。威尼斯作为欧洲最繁忙的港口,那里的商人大量使用了复式记账法,以至于“威尼斯方法”成了复式记账法的代称,这个城市同时开始出现代数的公共讲座其实并不是巧合。后世被誉为会计学之父的帕乔利就是在威尼斯学习的数学,他用数学完善了别人发明的复式记账法。帕乔利是修道士,但他还是数学家,达·芬奇的好友。他写了一本《数学大全》,说建筑、占星术、军事、神学等等,本质全都是数学,当然还有透视和音乐。这本书最实用的是,清晰地讲解了复式记账法如何操作。他建议在一个日子清点财产情况,然后按照备忘录、日记账、分类账三个类别记三本账,还得标上“圣十字”驱赶恶魔。这样的账本仿佛是给一场漫长的风暴拍了一张照片,清晰地展示风暴里每一滴雨滴的位置和方向。不同时间内数量的正与负、物的出和进,最后都能被平衡。资产阶级从复式记账法中学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万物皆可测量,而且万物皆需测量。
从五线谱、透视法、复式记账法三个例子,我们能感受到这些视觉化方式使定量思维逐渐主宰了人们的感官,数学“入侵”了现实,并成为理解现实、控制现实的唯一方法。也就是说,通过数学化的衡量手段,现实的神圣意义逐渐退去,而一目了然的视觉化方法让定量成为操控现实的最流行方案。
欧洲观念的旧模型从1250年左右开始加速转向,定量思维逐渐占了上风。这根火柴的点燃还有很多助燃剂,比如中世纪欧洲的权力并不集中,相对独立的城市和小国为各种思想提供了庇护;还有很多地方出现了最早的大学,集中学者专门从事研究,他们需要整理大量经卷,不得不采用更严谨的方法编排文献。为此他们发明了目录系统、章节标题、页眉标题,把文本变得井井有条而且方便检索。很多经院哲学家发现诗性和象征意义的语言无法满足需求,必须要用严谨的逻辑语言才能理清思绪,于是他们开始用数学描述上帝的造物,定量思维即将从中发芽。
更重要的是,当时商业和贸易越来越发达,欧洲正在进入货币经济时代,但却面临着贵金属硬通货缺乏的难题,这些问题也成为神学家的研究范畴。一个叫奥雷姆的修道士在14世纪发现,只要降低金币的金含量,金币就会变多,于是金币的价值会贬低,人们反而会变穷,也就是通货膨胀和劣币驱逐良币的原理。商人们开始使用“记账货币”的概念,固定了一个理想的衡量尺度,方便在不同的货币之间确定兑换比例。通过货币,每一件商品都开始拥有价格,而价格则来自测量,甚至时间也开始有了价格,也就是利息。
在视觉化和新技术的冲击下,旧模型出现了裂痕:连时间都能被数字衡量的话,还有什么不可以?但是要真正点燃心态革命,需要时间、空间、数学三方面的助燃剂,才让人们有工具能够测量万物。
我们先说时间。欧洲人在这个时期改进了从古罗马继承的儒略历,按照天文时间校准了人类时间,创建了我们现在通用的格里高利历。这次改革的理由其实也不是为了天文学,而是为了复活节。教会规定,复活节是春分后第一个满月的第一个礼拜天,但是由于儒略历对太阳年的估计有偏差,闰年算多了,到1582年的时候,儒略历已经和实际的时间差了11天。教会很苦恼,如果按照教义,就没法在真正的春分之后庆祝复活节了。那一年的时候教皇格里高利十二世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改用校准后的新历法,并直接向前跳了11天,也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公历。很多教徒发现自己很难接受这一改革,时间标准居然是按照天体而不是神学制定的。
不过,更加核心的变化是“小时”。我们刚才说了,中世纪欧洲用钟声标记时间,和中国很像,只不过欧洲的钟声是教堂掌管的,小时是不均等的,一天被按照祈祷时间分成了几段。到了晚上没人敲钟,可是占星家需要记录行星位置变化、修道士要准备晚上的祈祷,怎么办呢?而且如果天阴,看不见日月的位置,他们就很难知道时间了。人们需要一种钟,能够在任何时候都准确地告诉人们神圣时刻到了,该做祈祷了。由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计时工具已经失传,中世纪欧洲人大多用蜡烛、沙漏、水漏,但对修道士来说都不够精确。大约在13世纪,欧洲的某个修道院发明了一个绝妙的方案:机械钟。机械钟的核心装置叫做擒纵器,它能够让机械装置按照固定的节奏运动,比如那种摆钟,就是通过钟摆的固定摆动带动一个锚,左右晃动就会控制齿轮的一收一放,发出嘀嗒声。最早的机械钟大多使用重力驱动,用擒纵器控制重物下坠,所以都修建在高塔上,这也让整个城市都更方便听到钟声。到1335年,在意大利米兰的一个礼拜堂中已经有能够24小时报时的机械钟。第几个小时就敲几下钟,当时的学者夸这个钟“知道不同时候的敲击具体指的是几点,而这对人的所有生活和工作来说是最必要的。”
机械钟还提供了一个对世界的全新理解模式。比如那个发现通货膨胀的奥雷姆,他称赞上帝创造世界的方式就像制作时钟,让钟表跑起来并靠自己持续运动。不仅如此,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竖起了机械装置的钟塔,市民们按照新的钟声来组织生活,擒纵器的嘀嗒声和音乐的节拍一起,让世界均匀、可分的观念流行开来。人文主义之父彼得拉克说:“生活在稳速前进,既没有回头路可走,中间也不会稍作停留。我们勇往直前,无论狂风暴雨。无论这一路是容易还是艰辛,是短还是长,贯穿始终的都是一个恒定的速度。”时间就这样被理性驯服了。
而空间上的革新更缓慢一些,主要有两个重大理论,经纬度和地心说。以前的欧洲地图一般是所谓的TO地图,也就是地图中央有一个T字形水域,上面是亚洲,耶路撒冷在T字交汇点,左下方是欧洲,右下方是非洲,展现的是神学世界观。有了源于东方的指南针,航海的方位确定才变得更简单。也因此,13世纪末的水手们开始使用一种能够表现陆地方向的“波托兰航海图”。这种图主要记录海岸线的轮廓和港口,并用放射状的线条标记方位,有一定的比例尺来反映距离。波托兰航海图的应用区域一般只限于地中海和周围的狭小海域,所以就算制图者不知道地球是曲面,几何偏差也没多大,但如果涉及远洋航行就不准了。1400年左右,古希腊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又从东罗马帝国传回了欧洲,地圆说和网格化地图的概念让水手们恍然大悟,找到了理论和实践偏差的理论依据。制图者从此可以根据天体位置确定坐标,用均匀的网格覆盖地球表面,来标记坐标,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经纬度,并且他们也知道需要应用几何学来修正地球曲面投影到地图平面的偏差,这和画家的透视法是类似的原理。等西班牙和葡萄牙15世纪末开始殖民争霸时,教皇提出两国瓜分地球的边界应该是“佛得角群岛以西370里格的位置,以度数计算”,可见当时已经广泛接受了用经纬度数划分空间的做法。
与此同时,航海业的发展启发了天文观测。聪明的奥雷姆提出,人在船上很难判断另一艘船是不是在动,我们怎么确定地球静止而太阳运动?不过他在14世纪中期提出这种疑问时,他并没有足够的数学知识。到200年后,哥白尼采用精密的数学论证了日心说,将地球从宇宙中心踢开,1543年出版了《天体运行论》。这本书不仅论述了日心说,还是一千年以来欧洲第一次用数学描述天文的著作,他算出了恒星要多远才能在地球运动时看起来保持静止,这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新的、广阔的宇宙观。后来布鲁诺在1600年被烧死,不仅是因为支持哥白尼,还是因为他提出了地球之外是无限的虚空,是均匀的空间。
我们已经说到数学帮助了欧洲人认识绝对的时间和空间,我们再来说说什么数学进展让哥白尼能够写出《天体运行论》,也让复式记账法变得简明易读。还是得说说奥雷姆,他在14世纪就提出来要测量有“连续量”的事物,就得假设有隐形的点、线、面,方便数学化。但是我们也说过,就凭手指和计数板做计算,实在是太为难,更别提得用罗马数字记录了。还好,东方人又来救场了,12世纪时阿拉伯的大数学家花拉子密的著作被翻译为拉丁文,印度-阿拉伯数字传入了欧洲。新数字简单、清晰,无论多大的数都能用10个符号表达,完美适应十进制,但欧洲人还是花了一段时间适应。由于之前没有0的概念,欧洲人以为0只是用来表示进位的符号而不是数字。他们还混用罗马数字,比如MCCCC94,意思是1494。新的运算符号应运而生,比如1489年出现了十字和一横的加减符号,在那之前人们只能用单词或者字母描述运算,还有用字母表示未知数、小数标记等等方法,总之,数学慢慢脱离语言,逐渐符号化了。1就是1,超脱于自然,稳定地存在着。到16世纪末,提出行星运动三定律的开普勒相信上帝按照数学创造宇宙,人类和上帝理解数学所用的是同一种理性。他写道,“除了数字和大小,人类的头脑还能理解什么呢?”
总结一下,在1250—1600年的欧洲,时钟、历法把时间上切分为均匀、可计算的精确线条,经纬度和日心说把空间变为了均匀、可计算的几何形状,新的时空观对应新的音乐和绘画,而阿拉伯数字促进的数学符号化极大地简化了数学,方便了记账,人类的理性思维已经准备好测量万物。
讲到这里,我们大致就对1250—1600年之间欧洲人的“心态革命”有了理解。
我们都知道一句话,“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其实是1748年,美国开国元勋兼大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说的。我们刚刚讲了,金钱是有均匀的单位的,而时间曾经就像个手风琴。使这两者出现一个等式,就是“心态革命”的作用。现实可以被切分成均等的单元,然后被视觉化为一幅图像,按照数学的方法被衡量。宇宙不再意义复杂、高高在上,实用压倒了神圣,越来越多的资产阶级从中获得了世俗的力量。随着古登堡的印刷术越来越普及,人们能读到炮弹的射击目标、远洋大陆的导航路径、人体的肌肉组成等等如何用数学的方法精确地被视觉化呈现。像伽利略说的,宇宙“是由数学的语言写就的,这门语言的字符是各种三角形、圆形和其他几何形状,如果没有这些图形,那么宇宙这本大书,人类一个字也看不懂;没有这些,人们只能在黑暗的迷宫中徘徊。”
欧洲人这一阶段建立起来的心态,独特地结合了数学和测量,极大地强化了自己对现实的操控和组织能力,而这些发展为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这种思维惯性也传到了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身上。下一次听音乐、填excel的时候,你可以想想,自己依然被七百多年前点亮的火柴照亮着。
好,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
在1250—1600年的欧洲,时钟、历法把时间上切分为均匀、可计算的精确线条,经纬度和日心说把空间变为了均匀、可计算的几何形状,新的时空观对应新的音乐和绘画,而阿拉伯数字促进的数学符号化极大地简化了数学,方便了记账,人类的理性思维已经准备好测量万物。
-
欧洲人这一阶段建立起来的心态,独特地结合了数学和测量,极大地强化了自己对现实的操控和组织能力,而这些发展为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这种思维惯性也传到了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