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深重的呼吸》 王朝解读
《每一次深重的呼吸》| 王朝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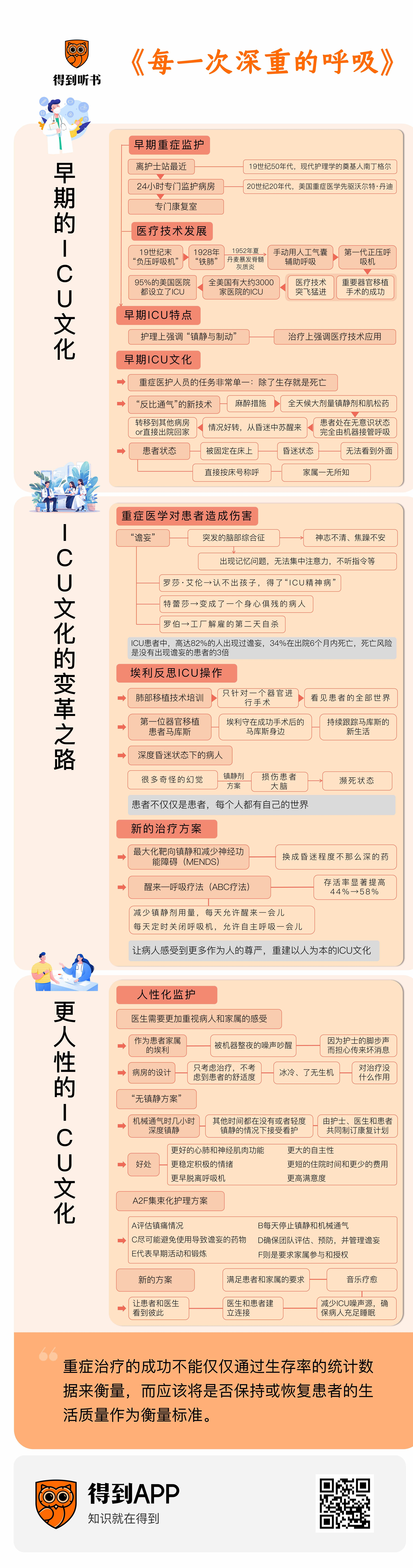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
今天这本《每一次深重的呼吸》,标题听起来就有些沉重,这是一本关于ICU,也就是重症监护病房的书。或许你会想到,只有最危急的病情,才会需要进ICU,门里痛苦的病人,在昂贵而冰冷的大机器辅助下深重地呼吸,门外是焦急的家属等待未知的消息。你可能会进一步觉得,ICU是一个很遥远、很吓人的事情。
这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想要回应的,这本书就是用他的亲身经验,告诉患者和医生们,即便是ICU,即便是离死亡最近的地方,也可以是不那么可怕、不那么令人绝望的地方。
这本书的作者韦斯·埃利是一个美国医生,更是国际知名的重症医学、呼吸科专家,从1989年他第一次在ICU救治患者到今天,他已经有35年的危重症救治经验。在新冠疫情期间,他也仍在一线救治危重症病人。不仅如此,埃利医生还就是那个改变ICU的人。他发现有些ICU虽然挽回了患者的生命,却摧毁了他们的生活,让很多人患上了新的疾病,也就是“ICU后综合征”,出现了谵妄、痴呆、抑郁、认知失调等等问题。
埃利意识到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时流行的ICU文化有多么大的问题。正是在他引领的变革之下,美国医院的ICU变得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强调病人的感受,不但生存率比以前提高了14%,而且有更多康复患者能够回归原先的生活。
因为他的亲历者身份,这本书既包含了他从医几十年来的宝贵思考,也像是一本ICU简史。他也根据自己在最前线和死神搏斗的体验与反思,启发我们思考死亡和生命的价值:什么样的生命是值得过的?如果病情难以逆转,医生和病人应该如何做出更好的选择?
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先看看ICU的起源,看看最开始的ICU救治文化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再从埃利医生经历的病例中,一起体验当时ICU文化存在“只见器官不见人”的问题。最后,我们再来了解变革后的新ICU文化是什么样的,有什么效果。
好,那么我们先来看最早期的ICU是什么样的。
我们现在讲起ICU,都很容易想到那些医疗机器。比如呼吸机、血液透析机,你还可能在新冠救治的新闻中听过ECMO,也就是体外膜肺氧合,也叫叶克膜,或者人工肺。其实,一个标准的现代ICU里可不止这些,还包括全天候计算机监控、多条中央静脉输液管、营养管、导管、超声、磁共振成像和通过泵注系统进行输送的各类药物。这些必不可少的医疗设备不少都成本不菲,一台要几百万。以埃利医生所在的美国为例,ICU的一平方米造价高达二十万到四十万美元,是豪华酒店的五到十倍,一周治疗费用高达十万美元。但贵也有贵的道理,随着危重症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从1988—2012年,重症患者的病死率降低了1/3。
那么,在这些设备出现之前,有ICU吗?如果有,ICU长什么样?
埃利医生说,其实重症医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可追溯的历史仅150多年。最早的重症监护,可以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现代护理学的奠基人南丁格尔要求把病情最严重的患者安置在离护士站最近的地方,这就是重症监护的雏形,但已经包含了ICU的精髓所在:把病情最严重的患者单独安置在一个方便医护人员投入最大精力救治的特定地方。
后来,20世纪20年代的一位美国重症医学先驱沃尔特·丹迪开设了专门的24小时监护病房,专门服务重症康复患者。此后,很多医院都开始为病情最严重的患者设立专门康复室,除了有医生、护士和麻醉师密切看护,配置上并没有太大区别。
现代医学意义上的ICU,不仅是管理模式的变革,还依靠一系列能够维持人体基本生理机能的仪器。而最早的这种维持生命的仪器,就是呼吸机。
早在19世纪末就有人设计出了最早的呼吸机,原理非常简单,就是把患者装进一个封闭的圆桶形装置,外面露出一个头,然后用外部的风箱来抽空里面的空气,牵拉胸腔,形成胸腔内部的负压,辅助肺部吸入空气。这种类型的呼吸机叫“负压呼吸机”,后来不断改进,直到1928年出现“铁肺”,才算是真正意义上能够替代人体器官的机器。“铁肺”就是早期负压呼吸机的铁桶版本,外置的机器泵自动把“铁肺”中的空气吸出,患者的肺被动扩张,吸入新鲜空气,然后“铁肺”中再加压,把肺里的空气压出去。但问题是,“铁肺”太大、太笨重,把人装进铁桶里,只剩头露在外面,医生就很难再为患者做其他治疗了。
1952年的夏天,丹麦暴发了脊髓灰质炎。这个脊髓灰质炎,就是俗称的小儿麻痹症,患者神经会受到攻击,导致无法自主呼吸,“铁肺”在当时挽救了很多人的性命。但问题是,比起急速增长的患者,“铁肺”的数量根本不够。当时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整个城市只有一家医院能够收治脊髓灰质炎病人,而且只有一台“铁肺”,入住的30名患者中,72小时内有27人死亡,医生们必须要想出一个新的治疗方法。
情急之下,麻醉学家比约恩·易卜生提出,把治疗破伤风婴儿的插管术用在脊髓灰质炎的呼吸衰竭患者上。当时一个12岁的小女孩已经四肢瘫痪,喘不过气来,危在旦夕。易卜生先在小女孩的气管上切开一个创口,插入一根管子,然后再在管子上接了一个装满氧气的橡胶气囊,通过手动挤压气囊将氧气输送到她的体内,通过正压将空气送入患者体内,而不是用“铁肺”的负压牵拉肺部。在麻醉药的作用下,小女孩配合完成了气管切开和插管,易卜生一下一下地把空气泵入她的肺中,把她从鬼门关拉了回来。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按照易卜生的设想,要在专门的急救室中,每个病人配一个专门的护理人员,医院找来1500多名哥本哈根大学的医学生,日以继夜地守在气管插管的患者旁边,手动用人工气囊辅助呼吸,患有呼吸衰竭的脊髓灰质炎患者的病死率从87%降至31%。
后来根据易卜生的急救方法,诞生了第一代正压呼吸机,用电泵替代了人力,而易卜生设计的抢救室,也被称为世界上第一个ICU。也是从这里开始,奠定了日后ICU的两大特点:第一个,是由于病情危急,救治手段往往对患者身体的介入程度很深,不得不附加一些额外伤害和风险,比如切开气管。第二个,是因为动用了这些深度介入患者身体的手段,所以护理上强调“镇静与制动”,也就是普遍使用深度麻醉,确保病人配合治疗。
此后几十年间,医疗技术突飞猛进,除了青霉素开始量产,起搏器、人工肾、除颤器、储存血浆等等现在常用于急救的医疗技术都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到七十年代间发明出来的,肝、肺、心脏等重要器官的移植手术也先后在这一时期内取得成功。于是,现代ICU如雨后春笋般在欧美各地涌现,到了1981年,95%的美国医院都设立了ICU。如今,全美国有大约3000家医院的ICU,每天监护着超过10万名濒临死亡的危重症患者,每年有超过六百万患者进入ICU接受治疗,平均每个美国人都会有至少一次重症住院经历。
我们可以这么说,现代ICU的出现,包括两个方面的创新,既有呼吸机为代表的医学技术进步,同样也包含对危重病人护理方式的变革。这两大前提条件,形成了作者所说的“ICU文化”,也就是一整套ICU的治疗和护理观念和实际操作习惯的统称,治疗上强调医疗技术应用,而护理上像前面提到的,强调“镇静与制动”,这就使当时的患者在ICU当中处在极其被动的状态。
好,我们就来看看早期的ICU文化是什么样的,以及在这种ICU文化主导下,ICU是什么样的。
作者说,一大变化就是医学界开始把救活病人作为自己的最高目的,出现了以阻止死亡为唯一目的的重症医学。作者提到,欧美的医生入行前有一段“希波克拉底誓言”要宣誓,包括了作为医生的职业道德和信念,比如首先考虑病人的健康和幸福、尊重病人的自主权和尊严、对任何病人都平等治疗等等,其中并没有要求医生把拯救生命作为唯一目标。在我们中国,医生也需要宣誓,有很重的八个字,“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最重要的是“健康”,而不仅仅是活着。但在ICU当中,除了生存就是死亡,重症医护人员的任务变得非常单一。作者自己就经历了这种思维变化。
当作者开始当医生时,他起初还很喜欢和患者互动,成为他们的伙伴和朋友。然而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进入重症医学领域后,他越来越接受重症医学的思维方式:患者只能分成两种结局,死亡当然是坏的,而活着就是好的。他开始意识到,生与死仅有一线之隔,他作为医生所做的一切能在几分钟内改变患者的整个世界。为了能挽救更多的生命,他选择成为一名呼吸重症领域的医生,因为如果人的肺不能持续呼吸,即便心脏继续跳动,也无法为身体供应足够氧气,人体就会死亡,而当时出现了越来越多更先进的呼吸机,能够让医生越来越精细地、有针对性地管理和治疗患者的肺,埃利医生很自然地选择了他心目中有希望能救治更多人的领域。
在埃利医生最开始到ICU工作时,他开始使用一种叫做“反比通气”的新技术,用来救治那些血氧水平很低的患者。为什么叫反比呢?因为这个呼吸方式和我们自然呼吸的方式完全相反。正常情况下,我们呼吸时呼气时间长,吸气短,时间比例约为一比三,而反比通气中,吸气长,呼气短,比例为二比一。你可以自己试着感受一下,先深吸一口气,保持2秒钟,然后在1秒钟内呼出空气,之后立即深吸一口气,再保持2秒钟,如此循环往复,看看多久以后自己的肺部会开始不舒服,有一种要炸裂的感觉。然后再想想,自己在一整天的时间里都被迫这么呼吸,甚至是一个星期、几个月呢?
站在医生的角度,很多病人不采用反比通气就无法活下来,但可想而知,这种反自然的呼吸方法,病人一定是不舒服的。埃利亲眼目睹过,患者不能适应反比通气,在插上呼吸机之后,因为呼吸机的强制呼吸开始对抗身体习惯,患者会出现呛咳和恐慌。为了让病人能够忍受这种治疗,必须要采取麻醉措施,全天候给患者使用大剂量的镇静剂和肌松药,确保患者一直都处在无意识状态,完全由机器接管呼吸。一到两周后,如果情况好转,医生们将让他们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再将他们转移到其他病房进行康复护理,或者直接出院回家。对于医生来说,任务仿佛到此结束了,埃利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一条生命得救了,这种感觉真好!”
当时的ICU里,空间狭小、昏暗,除了患者无意识的深重呼吸声,就是笨重的医疗机器工作的声音。当时一个医生如此描述ICU里的状态,“这些天我看到的都是处于肌松和深度镇静状态的患者,他们一动不动地躺着,要不是监护仪显示他们还活着,他们看起来就像已经死去了一样。”虽然窗外或许有漂亮的风景,但是患者都被固定在床上,处在昏迷状态,根本无法看到外面,他们也会直接按床号称呼,而不会被叫到名字。此外,家属被抛在一边,对亲人病情和治疗的细节也一无所知。虽然就算做了这么多的努力,还是会有三分之一的机械通气患者无法活下来,但至少还有三分之二活了下来。然而,就在活下来的这三分之二人身上,医生们意想不到的问题逐渐开始浮现。
那么,我们就从埃利医生的案例看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那是埃利医生20世纪90年代开始工作之后,他在维克森林大学医学中心的ICU工作,一个叫罗莎·艾伦的妈妈来到他们医院生孩子,却在几天后患上了产褥期败血症。这是一种分娩后出现的严重感染,会危及生命,很快她就被送到埃利的ICU里抢救。埃利给她插管,接上呼吸机和监护仪。在ICU里,罗莎不再叫罗莎,而叫“7号床的败血症患者”,情急的时候只叫“7号床”,而ICU里总是着急的。
经过十几天的ICU治疗,罗莎逐渐恢复过来,埃利就给她逐渐停药,让她从昏迷中苏醒。护士在天花板上挂了一张照片,罗莎9岁的女儿希望妈妈醒来就能看到新生的弟弟。停药的第二天晚上,埃利和罗莎的妹妹一起探视罗莎,他们给她看宝宝的照片。但是罗莎惊讶地瞪大了眼睛,看起来忘记了自己的孩子,她在床上扭来扭去,说不出话,用笔在埃利医生给她的白板上写下,“这不是我的宝宝”,写了足足两遍。埃利甚至有点气愤,他为了这个宝宝挽救了母亲的生命,可这个母亲居然认不出来自己的孩子。他认为罗莎可能还没有准备好苏醒,而且还得了“ICU精神病”。所谓的ICU精神病,当时认为主要是因为重病导致在ICU中集中出现的各种精神症状,需要重新进入深度镇静,并且增加注射一些精神类药物。又过了两周,罗莎才接受自己的孩子,和他一同回家。
医学上,罗莎所出现的症状也被叫做“谵妄”。谵妄就是指突发的脑部综合征,患者会变得神志不清、焦躁不安,还会出现记忆问题,无法集中注意力,也不听指令等等。而且,在ICU中出现过谵妄的患者,未来患上认知障碍的风险比没有出现谵妄的患者高十倍。有些患者从镇静中苏醒时,会产生幻觉,认为护士在给他们下毒,医生都要害他们,他们就拼命挣扎,抗拒身体约束。而被埃利称为“安静型谵妄”的占比更高,可能达到95%,他们看起来只是有点糊涂,只会用点头和微笑回答问题,这其实也是谵妄的表现。埃利曾经做过一项研究,他的ICU患者中,就有高达82%的人出现过谵妄,而且34%在出院6个月内死亡,死亡风险是那些没有出现谵妄的患者的3倍。这份调查,让埃利突然意识到,ICU挽救了生命,却让他们后来可能死于ICU造成的疾病。
罗莎所受到的伤害并不是孤例,而且有些病例更加可怕。早在1989年,埃利还只是内科实习医生时,他就接诊过一个名叫特蕾莎的患者,她因为自杀未遂而入院,哭着对护士说,她不是真的想死,但她的心、肺、肾等等多个器官都出现了衰竭。长达几周的时间里,埃利都在救治特蕾莎,透析机、胸腔引流等等手段都用上了,特蕾莎才终于脱离危急状态。当特蕾莎终于出院后,埃利想象她会在复查时高兴地感谢他。然而,特蕾莎回来复查时,只剩下了一具躯壳,她无法正常吞咽,无法自行入睡和如厕,不能自己洗澡、穿衣,一次只能走几步,完全无法爬楼梯,而且她变得健忘和胆怯,仿佛变了一个人。由于长期不活动和重度炎症,特蕾莎的关节异常发育,在不是骨骼的地方长出了骨化组织。不仅如此,她的大脑也受到了伤害。他救好了她的器官衰竭,却让她变成了一个身心俱残的病人。在埃利看来,特蕾莎过得比在医院里还糟糕。
还有一位叫做罗伯的患者,原本是一个机械工程师,但在ICU治疗后连小学乘法都感到吃力,由于认知能力下降,他无法回到工作岗位。在被工厂解雇的第二天,罗伯自杀了。
越来越多的病例让埃利医生开始怀疑,“重症医学正在对患者造成伤害”。一位患者对埃利医生说:“我有时觉得我活下来仅仅对医生是一个好结果,虽然我还活着,但我感觉不到自己还活着。”如果仅仅是把拯救生命作为唯一目的,这种重症医学当然完成了任务。但如果再考虑患者康复之后,能不能恢复以往的生活,埃利认为重症医学当时的答卷显然不及格。有近80%的患者后来出现了ICU后综合征,也就是和ICU治疗经验有关的一系列大脑和躯体症状,除了谵妄,包括痴呆、肌肉无力等等,还有三分之一的重症幸存者最后患上了痴呆症。为什么会这样?怎样才能让ICU更好地救治患者?
抱着这样的疑问,从1998年开始,埃利开始反思自己的ICU操作。他逐渐把注意力从肺部移开,开始研究大脑障碍与肺部重症的关系,同时,他也从刚接触的器官移植技术当中获得了启发。
在接受肺部移植的技术培训过程中,埃利惊讶地发现,其他的移植医生能跟他的病人聊家庭、聊爱好,甚至知道病人的孩子即将高中毕业,而这种深度的医患关系在当时的ICU里几乎是绝迹的。对埃利来说,对病人的了解可能仅限一张索引卡,他们只是病床上的7号患者。和ICU的患者不同,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需要进行更多筛查。除了病史,医生还需要知道他们的个性特点、职业背景、生活状况以及家庭支持系统等等。由于器官移植后还可能会出现排斥反应,病人和医生都知道未来会有新的一系列问题要解决,医生也需要确保患者的家庭能一直提供支持。在这种深度和长期的接触后,埃利开始重新看待自己的患者,他们不仅仅是患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
埃利意识到,器官移植虽然只针对一个器官进行手术,却需要看见患者的全部世界。而和器官移植的过程相反,ICU的危重症医生只看见衰竭的器官,看不见完整的病患。埃利说:“作为他们的医生,我一直很关心他们,并希望自己能竭尽所能救治他们,可我却把他们当作是没有生命的对象来对待。”他和患者的关系是人和物品的关系,患者只是“一组要修复的器官和要解决的问题清单”。
他的第一位器官移植患者叫马库斯,马库斯患有一种罕见的先天性疾病,导致血液在心脏的流向不正常,没有流经肺脏获取氧气便直接流往身体各处。由于血氧奇低,仅有65%,马库斯浑身发蓝,颜色像褪色牛仔布。要知道,一般血氧低于90%,医生就会开始进行干预,而马库斯却在过去三十年里,一直这样顽强地生活着。他和妻子一起,来向埃利寻找帮助,而埃利看到马库斯,突然第一次感到自己没有资格为这个人的余生负责,但还是让他们回去等待移植。埃利相信马库斯是他第一次以完整的人来看待的患者。
后来,埃利守在成功手术后的马库斯身边,调整呼吸机参数、血压药物、镇静剂、抗生素和免疫抑制药物的剂量。埃利不再只是想马库斯活下去,他还知道,马库斯一直希望能去山上远足、去跳伞,能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和孩子。他持续跟踪马库斯的新生活,发现让马库斯最开心的事情是那些他以前没有想过的生活琐事,比如和孩子踢足球。
埃利的研究还发现,他们以往认为处在深度昏迷状态下的病人是没有意识的,然而实际上他们会有很多奇怪的幻觉。这些幻觉包括自己被外星人袭击、被蛇群包围、监护器变成了美洲豹等等,这些都造成了之后的谵妄。更严重的是,通过对麻醉患者的脑电检测,发现ICU常用的镇静剂方案对患者大脑可能造成了损伤。有些患者的脑电波水平线,麻醉后变成了一条几乎没有电活动的长线,活动几乎降到了0。换句话说,他们不仅仅是昏迷,而是沉到了意识的海底,也就是濒死状态。病人告诉埃利,“接受机械通气让我以为自己要淹死了。你们要把我沉到水里,把我淹死。”这种感受,实际上就是麻醉造成大脑损伤的反映。医学证实,一个没有脑部疾病的人也可能会患上痴呆,而ICU导致的痴呆,可能就与深度镇静的过度压制脑活动有关。
于是,埃利制定了新的治疗方案,也就是醒来—呼吸疗法,也叫ABC疗法,还有最大化靶向镇静和减少神经功能障碍,也叫MENDS。这两个听起来很吓人,其实原理很简单。ABC疗法,就是减少给患者的镇静剂用量,甚至每天都允许他们醒来一会儿,同时呼吸治疗师也每天定时关闭呼吸机,允许病人自主呼吸一会儿。MENDS,就是改变ICU的常用镇静剂,从镇静效果更猛的药,换成昏迷程度不那么深的药。通过实验后,医学界发现ABC疗法能够显著提高患者的存活率,ICU患者康复出院后一年内的存活率从44%提高到了58%。
从器官移植开始,埃利开始研究到底为什么自己会给病人带来那么多伤害,并且开始走向ICU文化的变革之路。他的变革核心,就是要让病人感受到更多作为人的尊严,重建以人为本的ICU文化,总结起来就是八个字,“遵循科学,发现人性”。
埃利开始注重让病人更舒适,也能让病人的家属参与进救治和康复过程中。这和他女儿入院的经历也有关,当时她的女儿从泳池上跳下,一头撞在泳池边上,他把女儿抱起来时甚至摸到了女儿头骨上的裂口。整个急救流程对他来说无比熟悉,但也无比陌生,他只能静静看着,意识到自己完全无力掌控事情的发展。作为医生的埃利变得遥远,作为患者家属的埃利在病房里陪伴着女儿,会被机器整夜的噪声吵醒,会因为护士的脚步声而担心传来坏消息。他第一次注意到病房的设计只考虑治疗,而不考虑到患者的舒适度,让人觉得冰冷、了无生机。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房间的布置对于治疗没发挥什么作用。
从前他认为医生的责任就是用医学技术挽救生命,他现在从这种技术至上的催眠中醒来,他说,他意识到自己的患者们“很脆弱,很害怕。他们来找我是想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重新拼凑在一起”。医生需要更加重视病人和家属的感受。
后来,他从欧洲学习了“无镇静方案”,也就是除了开始进行机械通气时需要几小时的深度镇静,其他时间都让患者在没有或者轻度镇静的情况下接受看护,由护士、医生和患者共同制订康复计划。病人会下床散步,呼吸机跟在后面,而不是像以前一样等病人能停用呼吸机才下床活动。埃利列举了新方案的好处:“更好的心肺和神经肌肉功能、更大的自主性、更稳定积极的情绪、更早脱离呼吸机、更短的住院时间和更少的费用,还有护士、患者、医生、治疗师和家庭成员的更高满意度。”
在一系列研究基础上,埃利规范化了一整套新的重症监护方案,他从原来的ABC疗法延伸到了字母F,简称A2F集束化护理方案,就是英文的从A到F的意思。A就是要评估镇痛情况,以预防和管理每位患者的疼痛;B是要求每天停止镇静和机械通气,让病人醒来并自主呼吸;C是要尽可能避免使用导致谵妄的药物,选用副作用更小的;D是要确保团队评估、预防,并管理谵妄;E代表早期活动和锻炼,让患者能尽快下床;F则是要求家属参与和授权,开放更多家属探视的机会。埃利认为,这六个部分要一同发挥作用,也就是“集束化”。
他的人性化监护还不仅如此,他开始确保自己每天看见患者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看着对方的眼睛,然后轻轻触摸患者,让患者和医生看到彼此。然后他会和患者聊和疾病没有关系的事情,让自己和他们建立连接。他减少了ICU的噪声源,确保病人能有充足的睡眠。他还引入了音乐疗愈,比如有个患者喜欢电影《指环王》,听到电影中霍比特人家乡的配乐时就会洋溢幸福的微笑。他还会满足患者和家属的要求,即便在病人时日无多时也会满足他们的愿望,比如喝一杯冰啤酒,让狗狗陪一会儿等等。后来的研究证明,这些新的方案也对医护人员有益,比如,那些满足濒死患者的护士感到的痛苦程度较低。
以前,ICU的医生们会抱怨“我没有时间做那些事!我在这里是为了救人!”但是在埃利和包括其他许多医生、患者等有识之士共同推动下,重症医学的成功标准不再仅仅是让人复苏,而也要包括醒来之后的生活。他引用一位医生的话说,“重症治疗的成功不能仅仅通过生存率的统计数据来衡量,而应该将是否保持或恢复患者的生活质量作为衡量标准。”
埃利回忆,有医生说在ICU里“人们被剥夺了个性、过往人生、个人需求乃至价值观。简而言之,就是淡化他们的一切”。这一切正是旧观念造成的假象。
以往,很多人都会对遭受ICU后综合征的患者说,“能活下来就很了不起了”。但其实,这些伤害本来就是可避免的。活下来很重要,但这不意味着为了活下来,付出什么代价都是合理的。
埃利在救治新冠的过程中发现,在大流行的恐惧之中,人性化救护方案又被一些医生遗忘了。埃利研究了疫情早期的14个国家的2000多名新冠病毒感染者,发现过度使用深度镇静药物和病床边家属的陪护不足仍然是导致新冠患者谵妄和死亡的原因之一,令本就严重的病情雪上加霜。
所以,他在一线救治病人时,坚持使用自己提倡的集束化护理方案。埃利反思说,在危重症护理领域有太多决定都是由恐惧引导的,对死亡的恐惧让对患者的护理忽视了人格尊严。但埃利也坦承,最令医学界害怕的是,要承认自己的方法是错误的。曾经,科学的进步和管理的创新,让人类发展出了和死亡对抗的重症医学。然而,太过注重“活下来”本身,而忘记生活质量也是生命尊严的一部分,让活下来的患者变成了缺乏灵魂的躯壳,很多人无法接受自己的改变,甚至自杀。医生和病人应该建立起一种互惠的关系,共同推进医学的进步,才能帮助更多人。
埃利最后回顾自己的从医经历,他说:“当我还是一名年轻医生的时候,如果有人问我认为重症监护领域最重要的方面是什么,我会热切地谈论机械通气和血管活性药物,以及如何让患者摆脱休克并进行生命维持。而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的回答会是无花果,或是汤匙上的蜂蜜,或是一段音乐。面对绝望,我会一如既往地向希望迈进。”
这本书的最后,还附上了一系列的给医护团队、患者、家属的资源,为有需要的人们更细致地讲解谵妄和ICU后综合征,并提供了共同陪护和康复的指南。有需要的话,可以查阅最后的电子书。
好,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
现代ICU的出现,包括两个方面的创新,既有呼吸机为代表的医学技术进步,同样也包含对危重病人护理方式的变革。
-
“重症治疗的成功不能仅仅通过生存率的统计数据来衡量,而应该将是否保持或恢复患者的生活质量作为衡量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