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价高昂的健康》 王兴解读
《代价高昂的健康》| 王兴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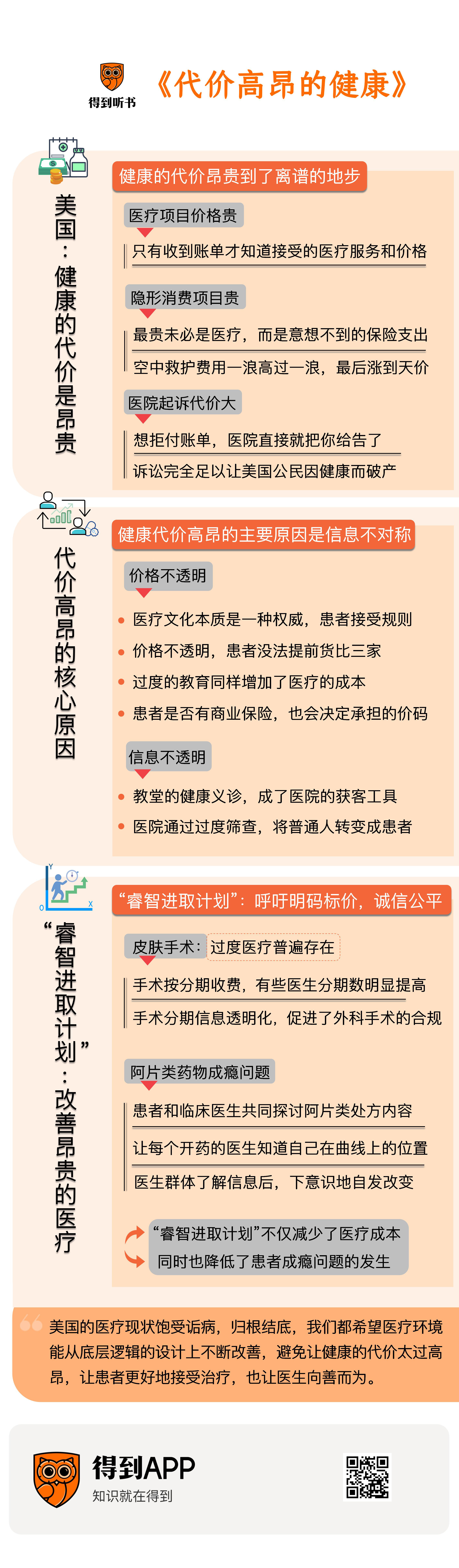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王兴。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书是《代价高昂的健康》。
生活在现代,维持身体健康需付出高昂的代价,这好像是个常识,毕竟“有什么不能有病,没什么不能没钱”。美国医疗是目前世界范围内相对先进的,同样也是最昂贵的,从逻辑来看,似乎没什么问题。但购买健康真的遵循一分钱一分货的规律吗?有这样几个事实分享给你,请体会一下:
假如你要在美国做一台心脏搭桥手术,你调研了不同医院的价格,其中53家愿意透露报价的医院对心脏搭桥手术的最低报价为4.4万美元,最高为44.8万美元,最高最低相差40万美元。奇怪的是,没有任何依据能说明治疗效果有什么差别,也不知道这40万美元的差距到底体现在哪里。
你没挑最贵的,也没挑最便宜的,你选择了的这家医院开价15万美元,而且你凭借灵魂砍价手法,竟然把费用砍到2.5万美元,正当你觉得赚大了的时候,打听一下才发现同样的手术在法国水平相当的医院,只需要1.5万美元。原来,这些医院享有自己定价的权限。
那问题来了,这种医疗价格的霸权在美国是怎么产生的?当下又是怎样影响美国人的生活的?这本《代价高昂的健康》会给你提供一些有效信息。
本书作者马蒂·马卡里,是美国顶尖医学学府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胃肠外科的讲席教授。他不是研究医疗法案的倡导者,不是记者或者评论家,而是个实实在在的局内人,他正是这套“代价高昂的”医疗系统中的环节之一。一位局内人写出这样一本书,揭露美国医疗行业内部一些问题,不得不说需要巨大勇气。而且,这本书并不是单纯吐槽美国健康的昂贵,更重要的是,作者还是个坚定的行动派,他开创了一个组织,用颇有建设性的方案,通过积极行动有效解决了不少问题。
下面,我们就跟随作者一探美国医疗的究竟:在美国,健康的代价到底有多么昂贵?昂贵的核心原因是什么?有什么应对方案吗?
我们先看看,在美国,健康的代价到底昂贵到了多么离谱的地步。
首先是字面意义上的价格贵。
书中列举了大量实例。例如,一个滑雪者因高山反应,被朋友说是高山病,劝他吸一会儿氧气,但他心里不踏实,就去了医院。医生看了看,果然就将其诊断为高山病,让他在医院吸了一会儿氧气,而费用是1.1万美元。再比如,一位女患者在医院急诊室待了两个小时,只做了一次静脉注射和一些常规检查,费用是6.9万美元,账单上会标注这属于必要的安慰和护理工作;一位患者因切除手指上的一个很小的良性赘生物,而被强制进行全麻,费用是1万美元;一次并不复杂的正常分娩,在波士顿的收费从8000美元到4万美元不等,可从医疗治疗上来看,不论是最实惠的医院还是最奢华的医院,都无法证明有任何区别。
很多人会觉得,你觉得贵就换个地方好了,但可惜的是,就诊前你并不知道这次的治疗会有多贵。试想一下,如果你提前知道吸氧这么贵,在急诊室做基础检查也很贵,那你一定会想办法避开。很可惜,医院从不给你这个价目表,你只有收到账单的时候才能想起自己接受了怎样的医疗服务和相应的金额。
除了价格昂贵外,在美国,健康代价高昂还源于医疗账单之外的额外费用。
有人说费用贵是应该的,毕竟医生的服务含金量高,医生的培养也很昂贵,但很多人收到账单的时候发现,其中最贵的项目未必是医疗,而是意想不到的保险支出。其中一项很关键的就是直升机的费用。
对于中国人来说,直升机救援在医疗方面并不常见,但在美国,哪里有繁忙的医院,营利性空中救援公司就涌向哪里,空中救护的费用一浪高过一浪,最后涨到天价。一趟短距离飞行动辄要价数十万美元。仅2007—2016年,一家公司的空中救护平均收费就从1.3万美元蹿升至5万美元,而实际产生的成本可能只要你所支付费用的10%就够了。
有的人会觉得,直升机加入医疗活动,这是健康产业发达的表现,更快的转运速度带来了更有效的救治时机。然而在美国,每年超过50万架次空中救护飞行中的80%都不是紧急任务,而更像常规客运。而且,是选择直升机救助、地面救护车接送,还是患者自行入院,美国医疗系统目前缺乏有效的判定机制。直升机和地面救护车本应该承担的是挽救生命的任务,但美国政府研究发现,有三家大公司控制着业内75%的直升机,他们出于收益考虑,当然要尽可能频繁地出动直升机。也就是说,当急救成了一门不受约束的生意,健康的昂贵就成了一种被人为操纵的结局。
说到这里就想到一句我们很熟悉的英文,“I’m fine, thank you”。请记住,身在美国,当你受伤后,别人问要不要为你叫救护车或者直升机的时候,你可以说出这句话,或许能保护你不会过于破费。
如果说上面所说的价格贵、隐形消费贵,还不足以让你觉得健康的代价有多高昂,那接下来要为你介绍的医院起诉,则完全可以让一位美国公民因健康而破产。
前面介绍了美国医疗的账单很贵,贵到离谱的地步,所以有些人就想拒付账单,或者是会选择和医院砍砍价,这在美国其实是一个合理的操作。但你跟美国医院砍价,跟我们在菜市场的上讨价还价可不一样。我们习惯的讲价是“我一分都不能再多给了,不卖算了”,然后医院会挽留你说“再加两块,赔本卖你了”,但结果是,你觉得你在讲价,医院却完全不想跟你协商或谈判,直接就把你给告了。
有的患者会觉得,那这账单我不服气,我不付钱,你告吧。但在美国,赢了官司的医院会直接从患者的工资里扣钱,甚至扣划美国公民的退休金分红。如果没有钱,也没有可以被医院划走的资产,那么患者的信用体系将被扣分,导致患者在圣诞前给儿子买件礼物都将异常艰难。
不过,从这些美国医院角度来说,我提供服务,患者缴费这是天经地义的,难道医院不告患者,要纵容患者做老赖才合理吗?这倒不是,问题出在,这些医院或许有更合理的做法,比如考虑患者实际的付费能力,使其有机会量力而行,而不是直接将其踩进破产的泥潭。
归根结底,假如患者付费前就知道大概要多少钱,也许会改变自己的医疗决策,很可惜,他们没有这个选项。
接下来我们就重点聊聊这个话题,这也是这本书用最多笔墨所探讨的问题:美国代价高昂的健康产生的核心原因,是价格不透明和信息不透明。
作者举了个非常形象的例子,诠释了美国医疗收费的现状。买家问:“请问这个橙子多少钱?”卖家会说:“得等你吃完了才知道。”
从美国医院的角度出发,他们认为价格是无法确定的,连参考价格都没法有。这也是我们在另一本听书《美国医学的社会变迁》中曾经解读过的,美国的医疗系统是个权力场,医疗文化本质是一种权威,由于患者信服医学权威,因此心甘情愿接受它所制定的规则。
美国医疗价格的不透明,有个突出表现是价格浮动超出了市场价值判断,简单说就是,患者没法提前货比三家。
作者讲了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一个人选择做心脏手术,医生开价15万美元,患者觉得有点贵就多花了点心思,结果查到了法国同样的手术只需要1.5万美元。于是,他回去找了医院说要去法国做,接着就预订了去法国的航班。然而他刚走出房间,就在走廊里被医院代表截住了。医院代表迫切想要做成这笔买卖,拿出了终极报价:“好吧,2.5万美元。”患者被医院的职业道德惊呆了,自己明明陷入了困境,医院却还想着占他们的便宜。
而且,一个患者有没有商业保险,也会决定他收到的价码。作者看到,美国医疗领域经常出现先提价再打折的把戏,也就是医院先把价格提到很高,让你望而生畏,再说明保险可以报销绝大部分,让你又觉得占到了便宜。作者认为,美国的医院和保险公司是一对利益共同体,对于拥有保险无须全额付账的患者,医院最终的要价不会太高,而没有保险的患者会被划分到“网络外”,医院会对他们漫天要价。而可怕的是,没有人能够核算医院的成本究竟有多少。作者反感的正是美国医疗中的生意,这不是生命值多少钱,或者手术要花多少成本,而是商人们觉得自己能让买主出多少钱,标价就是多少钱。
既然有这么多医疗诉讼,本书作者又探访了美国法院,本以为会吃到闭门羹,令作者惊讶的是,法院非常欢迎,因为他们也饱受医疗官司的苦。本书作者探访的这个地区法院95%的官司都来自当地一家医院,在这个镇上,每5个人就有1人曾被本地医院起诉并划走薪水,可见美国的医疗诉讼到了怎样的程度。作者找出的医院起诉患者案件数以千计,而医院基本上就没输过。作者想研究一下细节,看看医院是怎么赢的官司,他查验了一份医疗账单复印件,却发现账单上所有的明细都被涂黑了,定价和实际收费都有涂改。法官看不到明细条目,根本无从判定这些定价是不是合理的。这就意味着,只要医院说是合理的,那就只能是合理的,可见美国医生强大的文化权威。作者越发认为,要从更诚信、更透明、更公平的收费做起,让卫生保健服务重获信任。
作者还亲身体验过一次医疗成本和价格脱钩。外科医生在手术时,经常需要电刀切割患者的有害组织,而切割组织会产生烟雾,可能提高外科医生、护士的肺癌发生率。而当时市场上出现了一款新型电刀,以及一款新型显示器。新型电刀比普通电刀增加了一个真空孔,它可以吸走烧灼组织时产生的有毒烟雾。新型4K显示器也能让手术视野更清晰,手术安全性将会更高。这本是医院设备升级的机会,管理层看着提案却反问,之前的能用吗?能用就不用更新了。这让作者哑口无言。在管理者的角度来看,只要医疗上能凑合用就行,不要增加额外的医疗成本,但这一边看似压低了医疗成本,另一头却还在劝说患者付更高的费用,作者发现,原来美国的医院赚的是两头的差价。
另外,过度的教育也同样增加了医疗的成本。作者本人就是医生,他回顾了自己的医学教育生涯和正在从事的工作,认为当今的医学教育充斥着类似的脱节。在繁重的学习期间,医生不得不记忆一些未来很容易查到的知识,例如多发性内分泌腺瘤病1型和2型分别是什么情况,但在医疗实践中,大多数医生可能永远都不会遇到这种遗传病,即使偶然遇到也可以很快查到相关资料。可是,为了取得资格认证,所有医生必须一遍又一遍地记忆这些罕见、非紧急的疾病和它们特殊的基因突变。
除了价格的不透明,医疗中还有大量的信息不透明。
作者在本书中写到一个关于教堂的故事。他发现教堂的社区活动是健康义诊,开始还觉得挺好的,毕竟是为居民谋福利。去实地考察才发现,这个健康义诊经常筛查出许多周围动脉疾病的患者,并指导他们到医院进行手术治疗。教堂的牧师对此一无所知,他们原本只是需要更多人来教堂活动从而进行传教,并不过问医生会做什么,而在他们的认知中,医生为群众服务不是一件挺好的事情吗?他们却不知道原来健康义诊成了医院的获客工具,医院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过度筛查,甚至进行没有必要的手术。这个健康义诊的筛广告词就是简简单单的一句“你的腿疼吗”。这里有个更好的问题:谁没腿疼过?用赵本山老师的话说,你跺脚你也疼。
所以疾病筛查看似是为了健康,但筛查本身,是可以将普通人转变成患者的。作者认为市面上充斥着太多无效的筛查,它们经常以善意为幌子,以非常小概率发生的疾病故事作为噱头,来扩大筛查的范围。而事实上,大多数疾病的发生是和年龄密切相关的,年纪较轻的人罹患多种疾病的风险都不大,低于某一特定年龄的患者接受过多的筛查试验可能是弊大于利的。对于患者来说,认识到筛查与医疗产业的联合非常重要,这能让许多患者避免成为商业和医疗裹挟下的牺牲者。
上面我们通过一些数据和案例看到了在美国当下,健康的代价之高已经到了非常离谱的地步,并且也探索了其产生的核心原因是价格的不透明,如果只是写到这里,这就只能算是一本普通的社会观察书籍。然而,本书最有价值的一点,其实是介绍了作者如何将理念和行动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非常具有启发性。
作者提到一项计划,叫作“睿智进取计划”,寄希望于改善价格不透明的现状,减少过度医疗的发生。
前面说过,本书作者是一名局内人、改革者,他说:“我自己就是外科医生,对手术室里遍布的金钱诱惑再熟悉不过了。”那么在价格不透明和信息不对等的前提下,作者最先开刀的,就是自己所在的外科。
作者很早就发现,过度医疗在许多手术中都可能存在,这和手术价目的设置有关。以皮肤手术为例,手术的目标是在完全切除皮肤癌的同时,尽可能少切健康皮肤。所以医生先切一块皮肤,算1期手术,如果切缘有癌细胞残留,那就再切一块皮肤,算2期,极少数情况下还有癌残留,那就再切,算3期。可是手术的收费不是按切得够不够、伤口缝得好不好看算的,是按分期来的,这就导致一些医生手术的分期数明显高了。因为医生文化权威的存在,你不能单纯通过分期数就判定一个医生存在过度医疗,所以作者提出一个假设,手术分期的透明化,有没有可能促进外科手术的合规。
于是作者的“睿智进取计划”推出一项调查报告,计算每个医生手术分期的平均数,也就是看看谁动刀的次数最多。研究数据显示,大部分从事皮肤手术的医生人均1—2个手术分期。不过,一些人的平均分期有3—4个。
这样看来,接下来就是举报了,对不对?
然而,“睿智进取计划”不是举报计划,毕竟对于被举报的案例,医生是有一定解释空间的,也就是说,没有机构仅仅通过数据就判定一个医生是否造成了过度医疗,只有这个医生自己心里才知道。
所以这项计划做了一个有趣的操作,它给一半的医生发了私密的信函,这份信函的目的不是质询或者举报,而是向这名医生展示了所有参与者的手术分期曲线,这位医生可以看到平均的手术分期是多少,也能看到自己的分期数处于曲线中的哪个位置。相应地,另一半的医生没有收到这份私密信函,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手术分期数在医疗行业的分布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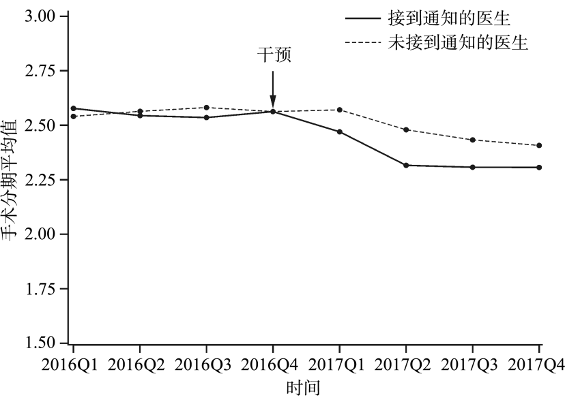
结果,这项计划获得了惊人的反响,83%的医生改进了原有做法,后期调查中的手术分期数有了显著的下降。另外,那些没有被发信函的医生也希望能收到类似的数据,看看自己的手术在行业内的具体位置。有的医生表示说“我非常喜欢它!我之前有好几次想去了解自己的手术平均分期与同行比起来怎么样,我还没来得及行动,它居然就自己来到我邮箱里了!它为我们的手术质量提供了很好的标杆。”同时,无论是接到通知还是没接到信函的医生,在干预后的手术分期数都有下降,只是接到信函的下降得相对更多一些。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看一下我附在文中的图表。
你看,作者用这项“睿智进取计划”成功证实了,当信息一定程度透明之后,医生知道了自己在行业内的位置,他的行为会自动发生改变。所以说,这项计划的目标不是揭发“越界者”,而是潜移默化地改变“越界者”。我国也曾有类似实践,当某地区肺结节切除的良性比例高达20%多的时候,医学会议公布了这个数据。数据公布后,这个地区的良性比例有了显著的下降。当医疗操作的价格和规则透明之后,医生就会处于更多的观察和监管之下,会下意识地约束自己的行为。言外之意,一名医生某台手术切的肺结节是良性的,我无从评判这名医生是否真的在过度医疗,毕竟良性的概率是没法避免的,是科学水平的局限性,但这名医生切的良性比例一直比别人高,他就应该反思一下了。
紧接着,作者的“睿智进取计划”又瞄准了阿片类药物的成瘾问题,也用的相似的方法,让每个开药的医生知道自己在曲线上的位置。在美国,阿片成瘾问题很严重,医生开的药远超过患者的需要量,结果是,许多患者在手术和创伤之后出现了成瘾问题,甚至引发吸毒、暴力等后果。有些患者收到过60片、100片阿片,而这些药未必是医生愿意开的,是药品福利管理人看患者开过,就直接让患者的医生开具续方申请。而医生接到大量申请后,经常是草草签字完成工作,不会多想。事实上,作者本人也这么做过。
针对这个严重的问题,作者组织了一个研讨会,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讨论了医学上最常见的20类手术。对于每一类手术,他都会请一名患者和一名临床医生共同探讨阿片类处方指南的内容,专家投票决出的开药量将成为一致通过的指导意见。最终,多项手术的推荐药量都介于10—15片之间,这个数量要远低于患者经常被开具的30片的数量。
然后,参会的医生们用前面提到的办法,把阿片类药物处方报告发送给开药过量的处方人,让他们知晓自己在曲线上的位置。这些报告按照不同的手术类型进行了不同曲线的描绘,这样一来,某位医生如果有“患者情况不同”这样的借口就站不住脚了。
书中写到,一位团队成员指向统计图上的一个点,这个点代表这位医生平均给每一位术后患者开出的药片数量,而这个数量竟然是45片,作者不禁感叹“那位医生太疯狂了”。紧接着,作者话锋一转,他说了一句让我十分感动的话,“不,那位医生需要帮助。就像几年前的我所接受的一样。”
作者的“睿智进取计划”不仅减少了医疗成本,同时也降低了患者成瘾问题的发生。但作者也发现,医生的人性贪婪并不是导致开药问题的罪魁祸首,要想真正有所改变,医疗系统内规则的改变或许是关键。举个简单的例子,医生都知道要解热、镇痛、抗炎抗风湿,非甾体抗炎药要比阿片类药物更好,但非甾体抗炎药几乎没有医疗保险可以报销,那么医生和患者就只能接受阿片类药物了。结果,医院、保险、药企所裹挟的医疗产业,将健康的代价层层推高。
除了上面的内容,“睿智进取计划”在相当多的领域开展得都很好,例如它发现了许多消化科医生会将本该安排在同一次麻醉中的胃镜和肠镜,分别安排在两天,进行两次分别的麻醉,尽管医生可以解释这是由病人的情况带来的,但是调查发现,医生们对每一个患者几乎都是这样安排的,这就有可能是不当行为了。
试想一下,作者调查到的数据也是一把双刃剑,他完全可以拿这些数据威胁医生或牟利。的确,就有企业提议将这些成果变现,但令人敬佩的是,作者统统拒绝了。因为他想确保这些评价医生的指标继续由医生来确认,并获得医生的背书、对医生友好。医学是一门艺术,不同医生接诊的人群也很多样。只要让越界者知道自己越界了,并引导他们采取最佳实践,实现改进才是目的。因此,我认为,作者并不是一名批判者,他爱这个行业,爱每一位患者,是置身其中的建设者。
好,这本《代价高昂的健康》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当前美国的医疗价格已经高到普通人难以承受的地步,而这种高昂的代价在医疗决策前几乎无法判断,在进行治疗之后又容易陷入破产危机。作者认为,导致健康代价高昂的主要原因是价格不透明和信息不透明。因此作者呼吁明码标价,诚信公平。他开创了一项名为“睿智进取”的计划,算是半官方的自发行为。通过数据调查和私密信函的方式,他让医生群体了解到自己的行为在全部医生当中的位置,从而下意识地自发改变,这为我们解决相似的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方式。但作者希望最终能使国家层面予以关注,并给予制度上的调整和妥协。
在任何国家,诸如价格不透明、过度医疗的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尽管我们一直诟病美国的医疗现状,但不可否认,美国仍是医疗技术和药品研发领域中最先进的国家之一。我也在《医生,你在想什么》这本书里探讨了常见的过度医疗产生的原因和机制,归根结底,我们都希望医疗环境能从底层逻辑的设计上不断改善,避免让健康的代价太过高昂,让患者更好地接受治疗,也让医生向善而为。
好,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
美国的医疗系统是个权力场,医疗文化本质是一种权威,由于患者信服医学权威,因此心甘情愿接受它所制定的规则。
-
美国的医疗价格往往让普通人难以承受,主要原因是价格不透明和信息不透明。